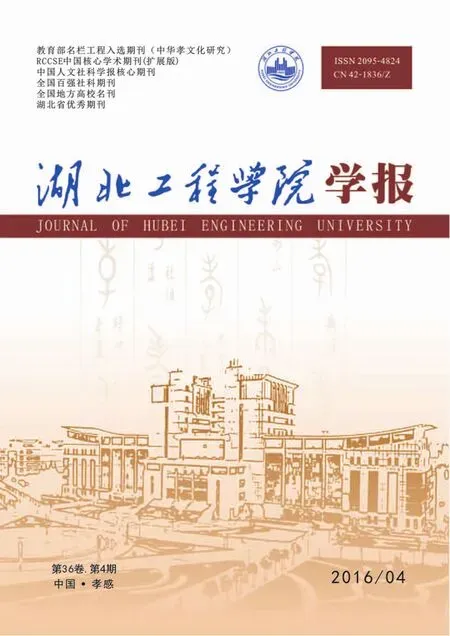試析《橋》的詩化特征
鮑光君
?
試析《橋》的詩化特征
鮑光君
廢名是現代漢語詩化小說的開拓者之一,他的中篇小說《橋》被朱光潛稱作“破天荒”[1]的作品。周作人在《〈棗〉和〈橋〉的序》中說,廢名“用了他簡練的文章寫所獨有的意境,固然是很可喜,再從近來文體的變遷上著眼看去,更覺得有意義”[2]。鶴西在談及廢名的《橋》時也說:“一本小說而這樣寫,在我看來是一種創格,廢名兄也到底還是詩人。”[3]
在創作《橋》時,廢名采用了消解傳統小說成規的手法,使小說帶有濃厚的詩性特征。本文將從詩情、詩意、詩境三個維度來分析廢名是如何將詩歌的文體特點融入小說之中,使《橋》充滿詩性品格的。
一、詩情
詩情是詩歌所表現的情緒。在《橋》中,廢名描繪了一個遠離塵世喧囂的靜謐鄉村,充盈了彼岸世界的朦朧詩情。
1.詩的情思。《橋》并沒有表達強烈激蕩的詩情,而是將一切情緒都蘊藏在沖淡的筆觸下,正如魯迅所說,廢名的小說“以沖淡為衣包蘊哀愁”[4]。廢名試圖以詩人的眼光與獨特的感受力去捕捉一種質樸而富有詩意的田園生活,描寫哀而不傷的故事,傳達出溫煦哀愁的詩情。
廢名處在世紀大變革的時代,現代社會的發展沖擊著他心中的鄉土世界,心靈的失落使他必然遭受無人能解的落寞與哀愁。此外,廢名身上所具有的傳統文人氣質決定了他的哀愁情結。此種境地與心態導致廢名傾向于反現代性的審美追求,其小說題材更熱衷于描寫傳統的鄉土社會。因此,《橋》傳達出的是對鄉土生活的喜愛與眷戀,對美好過往的追憶,對鄉土社會現實狀況的哀思。作者將詩情以溫柔平和的筆觸娓娓道來,使小說充滿了詩的情思。
2.抒情化手法。讀者對小說的語言往往存在一種審美期待,即小說的語言應偏向于敘事。在《橋》中,廢名摒棄傳統小說語言表達方式,不重敘事而重抒情。如:
小林又看墳。
“誰能平白地砌出這樣的花臺呢?‘死’是人生最好的裝飾。不但此也,地面沒有墳,我兒時的生活簡直要成了一大塊空白,我記得我非常喜歡上到墳頭上玩。我沒有登過幾多的高山,墳對于我確同山一樣是大地的景致。”[5]82
此段中,主人公小林用直抒胸臆的手法表達了對于“生死”這一人生課題的理解,他對于生死的超脫態度帶著一種對于人生必然走向墳墓、走向消亡的淡淡愁緒。抒情化手法的運用,將主人公的所見所聞與所感結合在一起,傳達出詩的情思。廢名用當下的視角,轉身去看兒時的童年世界,以詩人的情懷介入小說創作,將自身情思灌注于小說之中,使小說詩情洋溢。
二、詩意
詩意,是指詩人用藝術的方式表達自我感受時所形成的詩的意味。在《橋》中,廢名以寫詩的手法創作小說,使小說如同詩歌一般,字里行間充滿詩意的氛圍。
1.詩的思維跳躍性。廢名在回顧自己的文學創作時說:“就表現手法來說,我分明受了中國詩詞的影響,我寫小說同唐人寫絕句一樣,絕句二十個字或二十八個字,成功一首詩。我的小說篇幅當然長得多,實是用寫絕句的方法寫的,不肯浪費語言。”[6]廢名吸收唐人絕句的創作手法,以跳躍性的詩的思維帶來想象的空間與回味的余地,制造出濃郁的詩意氛圍。如:
琴子拿眼睛去看樹,盤根如巨蛇,但覺得那上面坐涼快。看樹其實是說水,沒有話能說。就在今年的一個晚上,其時天下大雪,讀唐人絕句,讀到白居易的《木蘭花》:“從此時時春夢里,應添一樹女郎花”,忽然憶得昨夜做了一夢,夢見老兒鋪的這一口塘!依然是欲言無語,雖則明明的一塘春水綠。大概她的意思與詩意不一樣,她是冬夜做的夢。[5]91
此段文字的第一句是對眼前的現實景物的描寫,其余則均是由眼前景物所引發的遐想:第二句由樹引起的想象的延伸;第三句承上啟下,寫這棵樹讓琴子想起了白居易的詩,并由此引發了夢境;第四句寫夢中的那口塘;第五句點出琴子的夢中詩意與白居易詩意的差異所在。敘述的展開遵循的是人物內心的聯想,語句的敘述思維帶有明顯的跳躍性。跳躍性的詩的思維創造了想象的空間與陌生化的閱讀體驗。
此外,小說中跳躍性的詩的思維引導并構建著讀者的想象過程,如“他覺得一匹白馬,好天氣,仰天打滾,草色青青”[5]102,這是由馬這一觀念而引發的想象,從馬寫到天氣,又從天氣寫到馬的“仰天打滾”,再從馬的“仰天打滾”寫到“草色青青”,從下、上、下的帶有跳躍性的角度來敘述,引導著讀者跟隨文字的描寫來構建自己的想象過程。
2.詩的形式片段化。《橋》并未遵循傳統小說的敘述模式,即故事發生、發展、高潮、結束的模式,而是吸收詩歌特點,采用片段化的寫作手法,充滿了詩的意味。《橋》中每一章都是獨立的場景與故事,甚至可以作為單獨的存在。如《橋》上部第15章《花》寫小林與琴子的兒女童趣,第16章《“送路燈”》寫小林與琴子對于民俗“送路燈”即對于死的朦朧思考。兩章所寫之事并無必然聯系,卻和諧地統一于整部小說中,這與《橋》通篇采用片段化的詩性敘述結構密不可分。
此外,就整部小說而言,片段化的敘述結構表現在它沒有完整的故事框架、明晰的情節線索,小說講述的無非是小林、琴子及細竹三人吟風弄月、談詩作畫、相伴而游的雅事,或是他們對于人生諸事的思考,呈現出分章敘述的片段化描寫特征。廢名采用詩歌的片段化敘述結構,創造出且行且吟的敘述風格,營造出了閑適安然的詩意氛圍,使小說如同自由流淌的小溪,無波瀾起伏,無始亦無終,全篇充盈著淡淡的詩意。
3.詩性修辭。《橋》中詩性修辭,即隱喻、轉喻、擬人化手法的運用,為小說增添了詩的意味。
吳曉東認為,“《橋》的語言主要表現為一種‘象喻性的語言’。象喻的語言,首先是指廢名的小說對隱喻和轉喻的運用。其次,象喻語言,還試圖強調廢名的小說語言在‘譬喻擬’的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鮮明的具象性”[7]。在中國幾千年來的詩性傳統中,詩歌與隱喻不可分割。高友工、梅祖麟在《唐詩的魅力》一書中,說唐詩的語言“存在著兩種詩性語言,即隱喻語言和分析語言。……而詩性語言中則較多隱喻關系”[8]。《橋》中詩性的隱喻修辭貫穿于整部小說之中,突出表現為用意象隱喻概念,如用“夢”與“樹”來隱喻人生。廢名甚至用隱喻意象作為章節的名稱,如“橋”、“花”、“塔”等。
第二種詩性修辭即是轉喻。在《橋》中,廢名用“頭發林”、“鏡子”、“妝臺”等意象轉喻女兒,表達自身對于女兒的喜愛之情。
此外,廢名還經常使用擬人化的修辭手法,賦予自然景物以人的形態,如“草是那么吞著綠,疑心它在那里慢慢地閃跳,或者數也數不清的唧咕”[5]24。廢名運用擬人化的修辭手法,試圖在自然與人之間構建和諧的比擬關系,達到情景交融之境,形成耐人尋味的詩的意味。
詩的思維、詩的形式以及詩性修辭的運用,是廢名意欲打破詩歌與小說文體界限的一次嘗試,實現了詩性語言對小說的介入與融合,是詩意得以生成的重要條件之一。
三、詩境
詩境,即詩中所表現的意境或詩化的氛圍與情調。在《橋》中,廢名用詩化的筆觸表現鄉村生活的風景及純美的人情,刻畫出世外桃源般純凈美好的世界。此外,古典詩詞與新詩的引入,將詩歌的意境直接引入到小說的具體語境之中,生發出新的詩境之美。
1.詩化風景。吳曉東認為,廢名在“小說中營造了一個讓人流連忘返的詩性的世界”[9]。廢名以詩意之眼與詩化筆觸觀照鄉土生活,他所描寫的鄉土世界如同世外桃源。廢名以沖淡的筆觸與滿腹的詩情來講述他記憶中的鄉土生活,景與情的交融給小說帶來靜謐平和的詩境之美。如:
有一回,母親衣洗完了,也坐下沙灘,替他系鞋帶,遠遠兩排雁飛來,寫著很大的“一人”在天上,深秋天氣,沒有太陽,也沒有濃厚的云,淡淡的,他兩手撫著母親的發,靜靜地望。[5]28
秋高氣爽,淡云飛雁,母親蹲在兒子面前為兒子系鞋帶,兒子用手輕撫母親的頭發,靜靜地看著高天闊景。抒情化的寫作手法將情與景融合在一起,借景抒情,寧靜渺遠的鄉村生活的圖景躍然紙上,天地之間生發出連綿平和的詩化氛圍與情調。淡然的心境與靜謐的風景和諧地統一在一起,一種景色便成一幅畫,一種詩境,渺遠又空靈。
純粹的風景描寫亦為小說增添了詩境之美,如小說描寫史家莊的文字:“現在這一座村莊,幾十步之外,望見白垛青墻,三面是大樹包圍,樹葉子那么一層一層地綠,疑心有無限的故事藏在里面,露出來的高枝,更如對了鷂鷹的腳爪,陰森得攫人。瓦,墨一般地黑,仰對碧藍深空。”[5]6尋常的鄉村之景被灌注了獨特的生機,景色描寫之中生發出無限的聯想與淡然安穩的詩情,營造出靜謐美好的詩境。
2.純美人情。在景之境界之外,人也構成了詩境中的人之境界。在《橋》中,人與人之間淳樸美好的情感以及純潔的人性之美為小說營造了平和寧靜的詩境之美。
小林與琴子已有婚約,然而活潑好動的細竹卻在不經意間插入小林與琴子之間。廢名并未用充滿矛盾沖突的事件來寫他們的復雜關系,而是借用詩歌的表現手法,用沖淡的筆觸淡化了琴子糾結而又痛苦的心緒,在糾結復雜的感情中著重體現淳樸美好的感情與純潔的人性之美。小說寫道:“她的愛里何以時常飛來一個影子,恰如池塘里飛鳥的影子?這簡直是一個不祥的東西——愛!這個影,如果刻出來,要她仔細認一認,應該像一個‘妒’字,她才怕哩。”[5]78琴子并沒有因為情感上的糾葛而與細竹產生嫌隙,她不責怪任何人,反而害怕自己會產生妒忌情緒,這更加凸顯出琴子的心地澄澈與人性之美。
純潔的人性表現在史家莊的每一個人身上,如細竹的天真無邪,史家奶奶的和藹慈善等。人性的純良質樸為世外桃源般的史家莊營造了純潔無瑕的詩化的氛圍,充滿詩境之美。
3.新舊詩的引入。廢名善于將舊詩與新詩的意境直接引入小說的具體語境之中,生發出獨屬于《橋》的詩化意境之美。小說寫琴子之美:在小林心頭“懵懵懂懂地浮上一句詩:‘鬢云欲度香腮雪’”[5]103。這句描寫將古詩原有的意境巧妙地嫁接到小說中來,一句詩便道盡了琴子的少女之美。又如,小說描寫琴子的眉毛:“那眉兒——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吧。”[5]153借魚戲蓮葉來寫琴子眉梢挑動的靈動活潑,眉之妙,躍然紙上。廢名將古典詩詞的意境直接納入到小說的具體語境中來,達到了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效果。
古詩之外,廢名還借小林或他人之口創作新詩,以新詩意境為小說增添詩境之美。如:
關于這河有一首小詩,一位青年人做的,給予我看:
小河的水,
昨夜夢見我的愛人,
她叫我靜靜地走,
一直追到那一角清流,
我的愛人照過她的黑發,
濯過她的素手。[5]13
廢名把新詩引入小說,為眼前的尋常小河營造出一個詩化的意境,情景交融,詩意籠罩的小河給讀者以無限的藝術想象。廢名引入舊詩與新詩,其目的是在有限的語言之外生發出無窮的詩境之美。
《橋》的詩化特征,是廢名反現代性的審美追求與文化選擇的體現。廢名處在世紀大變革的時代,面對現代社會對傳統鄉土社會的沖擊,他更加眷戀記憶中的鄉土世界,并在小說中化為世外桃源般的世界。因此,廢名致力于打破詩歌與小說的文體界限,以詩化的方式來敘說記憶中的鄉土世界,將詩歌的文體特征融入到小說中來。在《橋》中,廢名運用詩歌的抒情化手法表達溫煦哀愁的詩情;以跳躍性的詩的思維、片段化的表現手法以及詩性修辭為小說增添詩的意味;同時,他還以靜謐的鄉村之景、純潔的人性之美與新舊詩的引入營造小說的詩境之美。廢名將詩歌的文體特征引入到小說中來,形成了《橋》耐人尋味的詩性品格。
[參考文獻]
[1]朱光潛.橋[M]//陳振國.馮文炳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178.
[2]周作人.《棗》和《橋》的序[M]//周作人.知堂序跋.長沙:岳麓書社,1987:305.
[3]鶴西.談《橋》與《莫須有先生傳》[M]//陳振國.馮文炳研究資料.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183.
[4]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M].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6.
[5]廢名.橋[M].廣州:花城出版社,2010.
[6]廢名.廢名小說選·序[M]//廢名小說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序2.
[7]吳曉東.廢名《橋》的象喻語言[J].海南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5):20.
[8]高友工,梅祖麟.唐詩的魅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83.
[9]吳曉東.鏡花水月的世界——廢名《橋》的詩歌解讀[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3: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