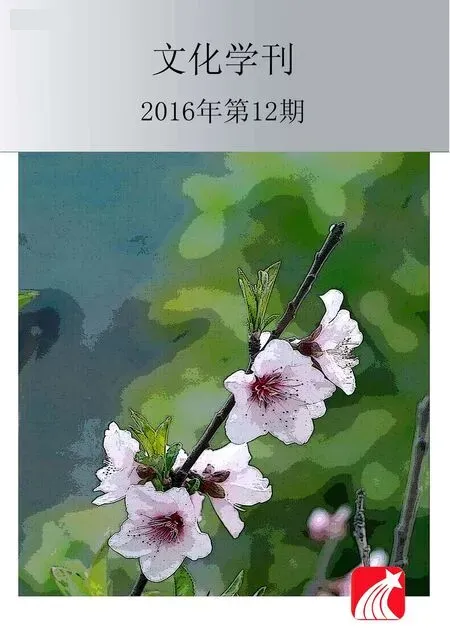論村上春樹小說的后現代性
韓 雪
(太原學院,山西 太原 030031)
?
【文學評論】
論村上春樹小說的后現代性
韓 雪
(太原學院,山西 太原 030031)
作為日本當代文壇最具世界影響力的作家,村上春樹和他的作品一再引起世界范圍內的“村上熱”。自2006年《海邊的卡夫卡》出版后,村上春樹連續10年入圍諾貝爾文學獎,但年年失之交臂,令人惋惜。雖然村上春樹未真正獲得這一世界最高文學獎項,但絲毫不影響他的文學成就及影響力,其作品表現出的后現代性更具研究價值。本文主要從宏大敘事的消解、無邏輯的荒誕以及虛幻的“真實”世界三方面入手,結合具體作品,探討村上春樹小說蘊涵的后現代主義風格及特征,希望能給相關研究人士提供一些參考。
日本文學;村上春樹;小說作品;后現代性
后現代主義屬于哲學范疇,尚未有統一的理論體系,若硬要給其下定義,依筆者拙見,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相對立,后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在文學作品中,后現代主義通常表現為徹底的反傳統和世界的異化,反傳統即其創作刻意跳脫傳統文學的形式、情節、敘事、人物、文本、語言等框架,因而,后現代主義作品往往呈現出碎片化和意識流特征。異化則是作品中的人物、社會、精神世界、價值觀都被異常化處理,如卡夫卡著名的短篇小說《變形記》,講述的主人公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蟲。因而后現代主義作品往往給人以荒誕、魔幻的感覺。在村上春樹絕大多數作品中都體現著后現代主義文學風格。
一、宏大敘事的消解
村上春樹作為后現代主義代表作家,是日本二戰后成長起來的,其作品與戰后日本社會及民眾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其大多數作品的基調輕盈,使得村上春樹成為二戰后彌漫著悲傷、沉重、壓抑情緒的日本文壇中的一股清流。[1]這一時期絕大多數作家都將文學創作置于戰后日本社會、政治、歷史等宏大背景下,如三島由紀夫的《金閣寺》,大岡升平的《野火》、小島信夫的《美國學校》等,還有太宰治、石川淳等無賴派作家刻意回避歷史背景,川端康成倡導虛無主義。而村上春樹與他們不同,其作品并不刻意回避歷史、政治和社會,但其作品中的人物卻是獨立于客觀世界之外的,即村上春樹作品中的主人公對現實世界的態度是冷漠甚至是帶著嘲諷意味的,并且其筆下的人物盡管處于特殊歷史和社會環境中,但其精神世界和命運卻不受外在因素的影響。
村上春樹對宏大敘事的消解,是典型的后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哲學認為人所處世界的本質,是人以自我為中心的假定。簡而言之,后現代主義認為人所看到的“世界”是由意識決定的,不是客觀存在的,因而不存在所謂的社會、政治、義務、榮譽、目標等對人產生的影響,人只會受自己的意識支配。
村上春樹后現代主義代表作——《奇鳥形狀錄》中,主人公岡田亨處于社會中,但又拒絕融入社會。他辭去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對任何事物都毫無興趣。主人公的生存仿佛只為生存而存在,發生任何事,都不會對他造成任何的影響。大部分讀者都認為《挪威的森林》是最能代表村上春樹的一部作品,實質上《挪威的森林》恰恰是村上春樹所有小說中唯一一部偏向現實主義風格的作品。但即便像《挪威的森林》這樣體現現實主義的青春小說,依舊流露出村上春樹的后現代主義思想。譬如,在小說主人公渡邊對當時正在進行的罷課、學潮等大事件毫無興趣,這樣的大事件居然也未對主人公所在的學校產生任何影響。這是有意消解宏大的歷史背景,將人物置于自我意識中的典型手法,同時村上春樹還消解了所謂的普世人生觀。雖然是青春題材的愛情小說,但是在《挪威的森林》中愛情、友情最終的結局都導向死亡。[2]青春在村上春樹的筆下是虛無的,不具任何意義的,這樣的創作是對現代社會精神價值的反叛。
村上春樹的小說作品消解了現代社會所尊崇的宏大意象,被一些讀者誤認為是對現實世界的逃避,但實質上這是村上春樹剝離現實后,對人生和人性本源的審視。人究竟為何而生又為何而死,人生存的價值和意義何在,村上春樹在他的小說中并未給出答案,只是引導讀者去思考和領悟。難怪有讀者說,讀村上春樹的小說仿佛墜入最深的混沌中與自己的靈魂對話。
二、無邏輯的荒誕
后現代主義作品之所以給人荒誕感,主要因為這些作品人物和世界沒有邏輯關系,任何人物、任何事情都不能按常理推斷。例如著名的荒誕戲劇《等待戈多》中,人物的行為沒有任何現實意義,為什么等,等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等待”本身這件事,這樣的“等待”毫無現實意義。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作品中成功運用這種無邏輯荒誕手法的是《海邊的卡夫卡》。
《海邊的卡夫卡》有兩條看似毫無聯系的故事線索。一條故事線的主人公是名叫田村卡夫卡的十五歲少年,另一條故事線的主人公是中田,一位能與貓對話的老年男子。在這部作品中,少年卡夫卡背負著弒父娶母的詛咒,這類似于希臘神話“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在原本的故事中俄狄浦斯王是個悲劇式的英雄人物。[3]但在村上春樹的筆下,這個故事卻散發著濃郁的后現代主義的荒謬氣息。整個故事從情節、語言到人物精神狀態都是虛無荒誕的。卡夫卡對父親的死不僅沒有絲毫悲傷,甚至說“遺憾的是他沒有更早死去”。而卡夫卡父親的死也極其的荒誕,由于卡夫卡父親虐待貓,而被激動的中田誤殺。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是毫無邏輯可尋的,與希臘神話前因后果一目了然的特征不同,在村上春樹筆下這個故事省略了前因,只有結果,至于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事,這樣的事又是如何發生的,這些都不是重點,重點在于這件事發生了。這與希臘神話的宿命論有著本質區別,在原本故事中人因抗爭宿命引發連鎖事件,最終導致悲劇發生,宿命是因,悲劇是果。而在《海邊的卡夫卡》中,宿命論是結果,不是起因。弒父娶母不再是詛咒,詛咒即是宿命本身。
《海邊的卡夫卡》能讓讀者自然聯想到奧地利著名的小說家卡夫卡及他的《變形記》。在《變形記》中人變成甲蟲,雖然也是荒誕的戲劇手法,但整個故事無論從語言、風格還是人物關系上都是統一、完整的。而《海邊的卡夫卡》中的意象表現是支離破碎的,兩條故事主線中的人物關系實質上并不相關,最后僅靠一個人物讓兩條故事線索平行。《變形記》從寫作手法上給人荒誕感,而《海邊的卡夫卡》從文本描述上給人荒誕感,這是村上春樹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
三、虛幻的“真實”世界
在日本有著名的“二次元”世界,“二次元”即虛擬人物生活的世界。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大多也存在兩個世界:一個是充滿現代都市氣息的現實世界,另一個則是獨立于現實世界而虛幻存在的“真實”世界。虛幻是因為這樣的世界不存在于客觀現實中,而“真實”則是村上春樹筆下所描繪的虛幻世界,細膩動人,給人身臨其境的感覺,讓人更愿意相信和生活在這樣的幻想世界中。[4]
在《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所處的現實世界混亂動蕩,但村上春樹卻讓主人公置于現實之外,向讀者展現了一個在當時背景下不可能存在的世外桃源——“阿美寮”,在這個虛幻世界中,渡邊和直子享受著愛情與青春的美好。但這個世界終究是虛幻的,所以,故事的結尾,春上村樹用殘酷的方式粉碎了夢幻。在《世界盡頭和冷酷仙境》《海邊的卡夫卡》中更能明顯看到相互獨立的虛幻的“真實”世界。
四、結語
村上春樹的作品所體現的后現代主義特征值得細細品鑒,但后現代主義特征并非村上春樹作品的全部。村上春樹筆下所蘊含的有關人類精神世界與現實社會的思考,才是村上春樹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作家的根本。
[1]耿海霞.近十年來中國對村上春樹作品的研究述略[J].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2):135-137.
[2]張俏巖,宿久高.從《挪威的森林》看村上春樹的孤獨感[J].日語學習與研究,2013,(4):61-64.
[3]魏大海.村上春樹小說的異質特色——解讀《海邊的卡夫卡》[J].外國文學評論,2015,(3):92-97.
[4]劉海英,關醒.解讀村上春樹的“尋找”意識[J].日本研究,2012,(4):108-112.
【責任編輯:周 丹】
I313.074
A
1673-7725(2016)12-0090-03
2016-10-20
韓雪(1984-),女,甘肅靜寧人,助教,主要從事日語二外教學、日本文學、日語語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