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麗夏·阿奎特:更愛你備受摧殘的容顏
王雅楠++崔秀娜+藺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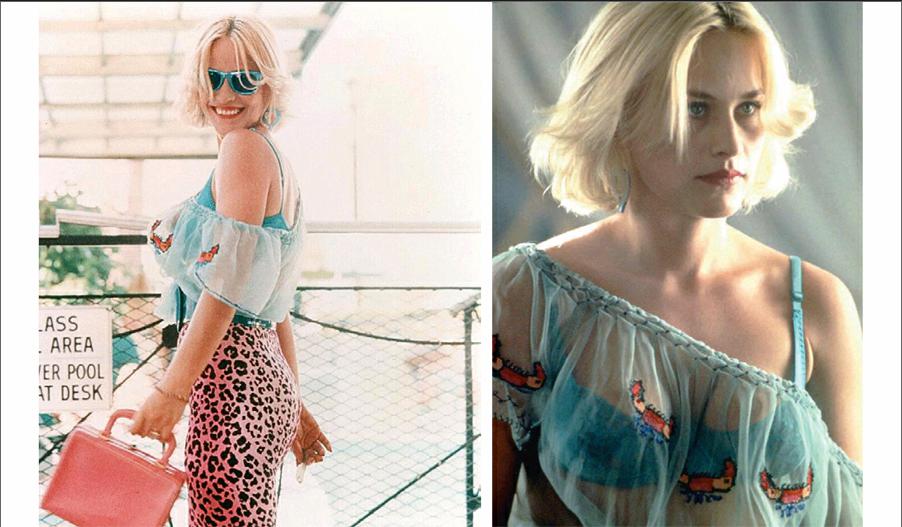

杜拉斯的《情人》中有一段讓人驚心的話:“與你年輕時相比,我更愛你現在備受摧殘的容顏。”聽上去像是男人張口即來的情話,聽之便罷,可細細品來,確有動人的情愫在暗自涌動。永遠的25歲,是男人的心頭所好,也是女人心中抹不去的傷痛。青春永駐,容顏姣好,對于普通女人尚且充滿誘惑,對于活躍在臺前的女星來說,更愿為之傾盡全力。可帕特麗夏·阿奎特卻是個例外,更加奇妙的是,愛她的人,似乎也更愛她備受摧殘的容顏。
12年,容顏衰老,榮耀萬丈
12年,對于每一個女人來說都是珍貴的,也許那就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而帕特麗夏·阿奎特卻用12年來演繹了一個角色,而且還是一個配角。這除了對藝術近乎苛刻的追求,更多的,是勇氣和信念的支撐。2002年,她開始拍攝電影《少年時代》,2014年電影正式上映,長達12年的拍攝歷程,用極盡真實的方式記錄了一個男孩的成長,也記錄了帕特麗夏·阿奎特飾演的母親的變化。年華的流逝不一定非要親飾,高超的化妝技藝可將歲月的變化融于無形,帕特麗夏·阿奎特卻用自己真實的12年,讓每一寸變化生動地出現在銀幕上。2015年,這部影片幫阿奎特攬獲了金球獎、奧斯卡等一系列大獎。用12年演繹一個配角,看似荒誕的決定,卻在這座獎杯的襯托下,顯得光芒萬丈。
電影《少年時代》看上去像是一個充滿叛逆精神的電影。它在開拍時并沒有完整的劇本,因為誰都無法預料在真實的生活中會發生什么。阿奎特飾演的母親,經歷了離婚、再婚,經歷了兒子長大叛逆、離家出走……她頑強地想要為兒子建構穩定的生活,但是又在母子間難以磨滅的隔閡中無比困惑。正是這些發生于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更能夠激起人們對生活的感知。正如阿奎特自己所說的:“生活自有它的韻律,這就夠了,這跟你那些什么難以忘懷的瞬間的感覺是不一樣的,真正的生活,是在這些激動的瞬間之外的東西。這才是生活的主體,而我們恰恰在爭取生命中每一個里程碑的時候忘記了這些真真切切的過程。”
將人生中的12年濃縮于大銀幕上的3小時,將一個倔強的母親形象塑造得惟妙惟肖,阿奎特賦予《少年時代》鮮活的生命力。同樣,真實的殘酷和無常,單身母親面對現實生活的遭遇和困惑,對于阿奎特而言,也是感同身受。
你所有為人稱道的美麗,
不及他第一次遇見你
不為容顏老去而擔憂的女人自然有她為人稱道的美麗,阿奎特不僅美麗,還擁有著為人稱道的愛情。1996年,當時才18歲的她與尼古拉斯·凱奇相遇。彼時的尼古拉斯·凱奇剛剛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意氣風發,可第一次見到阿奎特,便一見傾心,向她求婚。阿奎特自有動人之處,更有自己的驕傲。她向這位受千萬人追捧的白馬王子提出了與一般少女不同的要求,她要塞林格的簽名,還要一株黑色的蘭花。但或許是過于年輕,不肯向彼此低頭,又或許是過于獨立,就在他們滿懷著愛情和期待準備婚禮的時候,尼古拉斯·凱奇卻在機場中對她大發脾氣,兩人也因此分道揚鑣。
美好的帶有童話色彩的愛情轉折讓人欷歔,開頭的美好,第一次遇見的驚艷,更加重了分開之后的傷感,但這感情又異于那些情深緣淺的無奈。9年后,兩個人兜兜轉轉,再次相遇。彼時,卻都不再是初遇時的自己。阿奎特已經是一個單身媽媽,這一次說出“我們結婚吧”的是阿奎特。可到最后,他們還是沒能相伴走完一生。
漂亮的女人是從來不缺少愛情的。阿奎特很快又擁有了絢爛的婚姻。為了娶到她,演員托馬斯·簡也是費盡心思。他舉著“可以嫁給我嗎?”的牌子將自己植入卓別林的影片,然后租下了整個影院來求婚。又是一個女孩子夢想中的求婚場景。然而,仿佛連上天也嫉妒她的幸福,她又一次離婚,變成了單身母親。
婚變后,正如她在《少年時代》中所經歷的那樣,歷經生命的波折變化,體味著單身母親在情感、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困難、困惑、憂慮……這種憂慮淡淡漫開,彌漫于她生活的全部。慶幸的是,她始終是優雅的,但那種優雅的背后,卻是一個獨立堅強的單身母親所做的所有努力和奮斗。
阿奎特的情感經歷,讓我們發現在這個看似嬌小的女人身上,有著多么異于常人的叛逆和個性。這些,從她的成長歷程中便可以窺見一二。小時候的阿奎特就因為個性張揚、喜歡冒險而屢屢更換學校,更為出格的是,她在14歲的時候剃了光頭,離家出走。雖然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但18歲時,她還是憑借著骨子里的藝術天分走入了演藝界。
步入演藝界的阿奎特,對影片有著極高的要求,不僅拍主流電影,更熱衷于獨立電影。接拍如《少年時代》這樣有著特殊拍攝方式的電影,也足以見證她的特立獨行之處。叛逆甚至特立獨行必然不為世俗所容,阿奎特每一步的風光背后都有著不為人知的艱辛。或許也正因著這份艱辛的打磨,阿奎特在表演中才能夠絲絲入扣,打動人心。她可以由歇斯底里的大哭大笑數秒內轉為走心動心的恐懼,那種心內的體悟,恐怕是她波折一生的寫照。
身為女人,不憂亦不懼
美麗的女人,大多難逃花瓶的命運,不過是銀幕上那動人的存在。而阿奎特卻不滿于此。她清楚地知道,隨著年華的逝去,她不能再囿于容顏或者喜愛她容顏的男人,她必須開始脫離糾纏不休的感情,而去為那些竭力為家庭、子女付出的女人們做些什么。正如她在《少年時代》中扮演的母親一角那樣,當她失去愛情和婚姻,當她要為自己的兒子負責的時候,她所做的一切便不再是尋求愛情那么簡單,她不再是那個只在家庭中為瑣事打算的女人。她知道,在現實的社會,女人承受和經歷的,已然超乎人們的想象,也是時候,該為女人們做些什么了。
于是當她憑借一個母親的形象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時候,在那個備受世人矚目的領獎臺上,她發表了一番動人的言論,“生下了這個國家的每一個納稅人和公民的女性們,我們過去為他人的平等權利而戰,現在是我們獲得同等報酬的時候了,是美國女性獲得平等權利的時候了。”這番言論不僅收獲了場內同樣有著演藝功勛的梅麗爾·斯特里普和珍妮弗·洛佩茲的叫好,更得到了希拉里·克林頓的支持。
面對致敬和追捧,她只是淡淡地表示,自己現在有了些微小的力量,愿意傾盡全力,為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道路助力。而這份動力,源自于她的生活體驗,正如她所說:“不要和我談特權,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也曾經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無論我在哪里,我不會忘記女人的掙扎。”“20歲時,我也是一個工作單親媽媽,我知道支付食物和尿布的艱辛,告訴我女性為什么要比別人的酬勞低?”
帕特麗夏·阿奎特,她真實得就好像活在我們的身邊,她用現實生活留給她的痕跡畫出了熒幕上不朽的角色,而對現實的敬畏和奮斗,更為她的執著和頑強添上了動人的滄桑。這樣的女人,是無憂無畏的。也正是因此,她不懼衰老,讓世人更愛她那備受摧殘的容顏。那容顏,寫滿了經歷和倔強、不屈和努力,分外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