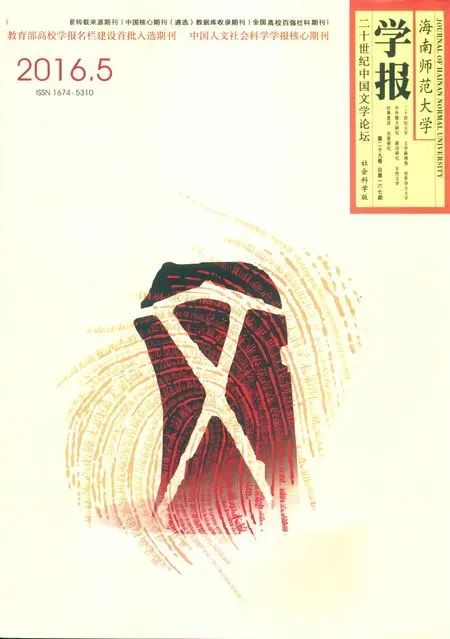基于群落、演化理念的宋詞新史
——評阮忠先生《宋代四大詞人群落及詞風演化》
余 意
(東莞理工學院 中文系, 廣東 東莞 523808 )
基于群落、演化理念的宋詞新史
——評阮忠先生《宋代四大詞人群落及詞風演化》
余意
(東莞理工學院 中文系, 廣東 東莞 523808 )
阮忠先生是我的業(yè)師。記得1998年追隨先生讀研究生時,先生在完成《唐宋詩風流別史》之后,就有意研究唐宋詞風流別的演化,但遲遲沒有付諸實施。沒想到退休之后,先生本可以賦閑以樂逍遙,卻仍執(zhí)著地完成《宋代四大詞人群落及詞風演化》(鳳凰出版社2015年7月版,下引標注頁碼均出自此著。以下簡稱《演化》)一書,距念之初起已然過去十七年矣。我知道,完成這項課題一直是先生的愿望,因此我由衷地為先生高興。
先生在《演化·后記》中提到當年沒有立即著手進行唐宋詞風流別演化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因為劉揚忠先生《唐宋詞流派史》錦繡在前,當時難以有更多的新意與個性。十七年之中,先生雖從事著其他相關研究,但從未放棄對宋詞的思考,曾出版了《宋詞名篇解讀:兩宋名詞的微觀研究》一書及相關研究文章,為《演化》的寫作奠基。今捧讀先生大著,強烈地感受到他所具有的群落及演化的詞史理念、處理材料時的大歷史意識以及歷史敘述的客觀筆調,與當今已有的唐宋詞史著作相比,有自己獨特的個性,稱得上是一部新的宋詞史。
宋詞史,當是詞這種文藝樣式在宋代這個特定時空中的流變,既是詞的,更是歷史的。在宋詞史中,歷史性作為第一屬性,首先必須解決的是如何看待歷史的問題。后人理解前人真實發(fā)生的歷史只能通過前人留下的文字、實物等相關材料,并憑借后人對它們的探索,拼接建構起前人歷史的圖景。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拼接建構起來的歷史圖景可能永遠是歷史的骨架。也許刪繁就簡、保留歷史的主干是歷史研究的要義,有益于人們更好地認識歷史。但是中國史學傳統并不是以告訴讀者歷史答案為目的,諸如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等,均力圖展現歷史的全息圖象,讓具有場景感的歷史啟迪讀者。如何展現歷史的全息圖象,司馬遷創(chuàng)立了“互見法”,雖然將相同時空中的人事物分置不同處敘述,但其敘事的目的則是力求將他們放置在同一層面進行呈現,獲得的是歷史時空的整體認識。而歷史的變化則是在時空的移動中發(fā)生,這是場景的移動,不是點的替代。這樣敘說的歷史無疑更有立體感。先生當年下鄉(xiāng)進廠,有幸閱讀最多的著作是司馬遷《史記》,自然受司馬遷《史記》影響很深。先生說,在《史記》的“歷史的啟迪之外,還有重要的兩點:一是‘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思想方法……”(第466頁),堅持以“通變”眼光審視中國詩文歷史。將“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通變”的歷史思維方法落實到宋詞史,先生別出手眼拈出“演化”一詞,作為宋詞流變的總法則。
“演化”的歷史觀念,既在“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中,遵循著進化的基本法則;又代之以歷史場景的全息圖象,著眼于歷史的變與不變的辯證統一,因而立體感更強,歷史的場景感也更足。先生毫不諱言對“演化”一詞的喜愛,并以此力求把握詩歌風格的“演變和承續(xù)”,注重同一詩風之流下的風格異同之辨,著眼點都在于詩歌風格的縱向與橫向的演化(第463頁)。正是癡迷于“文學漸進的、變動不居的感覺”,先生對于中國文學一直有“演化”或“嬗變”的思考,先后著有《中古詩人群體及其詩風演化》《唐宋詩風流別史》《先唐文化與散文風格的嬗變》,這部《演化》自然是先生文學“演化”或“嬗變”思考在宋詞史中的延伸。可以說,“演進”與“演化”,雖說只有一字之差,內里趣味卻大不相同。在我看來,先生的“演化”或“嬗變”并非僅僅著眼于所研究對象,而是將研究對象置于歷史潮流變動中去考量,從細微處勾勒“化與不化”、“變而不變”的發(fā)展圖景。“化與不化”、“變而不變”對于前后時代如此,對于處在同一群落中的詞人亦是如此。
詞從唐發(fā)展而來,唐詞是宋詞發(fā)展的基礎,是宋詞前傳,宋詞的后續(xù)發(fā)展均可以在前傳中尋找到根據,故先生這部宋詞史為史的完備,并不是直接從宋代開始,而是在引言中簡述詞的源起以及詩樂關系,交待了中唐、晚唐、西蜀、南唐的歷史情形、詞的創(chuàng)作及風格,為宋詞“演化”提供了詞體的起始坐標。到晏歐詞人群落繁茂之時,即“宋仁宗在位的40年(1023—1063年)客觀上成為宋詞發(fā)展的重要時期,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原本只是娛情怡性的詞,也被用來表現社會生活和詞人情志”。而到北宋仁宗時期,既有晚唐五代詞風的遺韻,也有詞體在新時代的新氣象。晏歐詞人群落是如此,蘇門詞人群落也是如此。如先生在后者中專列一節(jié)“蘇門詞人與晏歐詞人及詞的關聯”,說晏歐詞人影響蘇門詞人主要有三個方面:“輕柔香艷的詞風”、“疏朗淡雅詞風”、“俗詞俗風”,“意欲標明的是,蘇門詞人的創(chuàng)新始終是以前人的詞作為基礎的,他們創(chuàng)作上的自覺是社會風氣、自我趣味以及詞體、詞風的影響使然。即使有所超越,也與傳統有千絲萬縷的聯系”,這種堅持歷史前后相循、變與不變的視角無疑是合理的,貼近宋詞流變的歷史實際。
先生縷析每一詞人群落所共有的主題、風格、趣味等傾向,進而分析他們的同中之異,如歷來認為晏、歐詞與柳永詞存在巨大差異,但先生認為“晏殊好賓客之樂、歐陽修好山水之樂、張先、晏幾道好友朋歌酒之樂,柳永好的歌樓妓館之樂,各不相同,但享受生活、消遣人生又是共同的”(第117頁)。但“和晏殊、歐陽修、張先比較,柳永詞的人生詠嘆最為強烈,在求仕進與好青樓的糾結中,他求仕進不忘青樓,好青樓而欲仕進,并不能左右逢源。于是存仕進之心,行為舉止卻是才子風流”(第110頁)等切理饜心之處,所在多有,讀來深受啟發(fā):每一位詞人的創(chuàng)作個性都是立足于傳統的,每一時代創(chuàng)作風格鮮明的詞人是有相同時代性的,傳統與時代決定了他們的相同因素,個人遭際決定了相同傳統與時代之下的個性之異,對宋詞發(fā)展進行立體觀照,彰顯了宋詞發(fā)展的肌理,豐富了對于宋詞發(fā)展的整體感知。
現代學科體系之前,人們認知宋詞史因開示寫作門徑的需要多以名家來組織辨識,典型如清代周濟“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現代文學史學科,作為一知識體系,陸續(xù)出現了諸如名家更替、代群、流派、詞體、紀傳通史等體例或形式,各自均能立足于宋詞呈現出彼此的個性,但總覺于宋詞實際而言,似仍有意猶未盡之感,尚有從其他途徑進入的可能。先生受《史記》影響,希望更加立體地展現宋詞流變,以“演化”作為宋詞歷史研究的指南。但面對詞人、詞學現象以及詞之外的詩文、文化等等,如何將宋詞的整體觀照落到實處,先生另辟蹊徑,采用“群落”作為結撰方式。
群落在生態(tài)學中的解釋大致為生存在一起、與一定的生存條件相適應,并且相互之間具有直接或間接關系的所有生物組成的系統。與生物系統類似,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具備生態(tài)群落具有的特征,凡是呼應于時代主要的精神狀態(tài),體現時代主要潮流的人群,他們之間或有關系或毫無關系,但不妨均以群落稱之。但先生所理解的群落不僅僅是落實于詞人,還是從詞人之間的關系引申到對于時代文學、文化,群落的形成,無疑是時代精神、時代氣質促成的詞人聚集。先生獨具慧眼,于文本細讀中發(fā)現“宋代詞人常有情緒相近、思想相同的地方,如物是人非、及時行樂、人生失意、功名難就等;詞人喜歡用的典故有新亭對泣、擊楫中流、彈鋏歸來、黑貂裘弊等;喜歡說的前賢有王粲、張翰、陶淵明、謝安、庾信等;一些詩人常出現在詞人筆下,如杜甫、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第465頁),從“群落”組織詞史,實則是先生對于宋詞演化歷史現象背后的精神氣質、趣味趨向的深刻把握。
借助現代觀念研究傳統文學,往往會面臨著古今不一致的情形,諸如“流派”“集團”等在現代語境中有意義非常明確的概念,但有些研究者卻生拉硬拽,削現代之足適古人之履,不經過意義的細細辨析,使得相關研究名不符實。先生的《宋代四大詞人群落及詞風演化》專列“‘詞人群落’界說”一節(jié),對于與“群落”相關的概念進行逐一辨析。在“群落”之前,有諸如“群體”“流派”等觀念組織的詞史,先生在辨析“群落”概念時,比較“群落”與“群體”時說:“‘群落’是較‘群體’更為松散的不自覺的詞人結構形態(tài)”(第2頁)、“特別強調‘同一歷史時期有著共同生活、共同趣味或一度有著共同生活、共同趣味的詩人群’。‘群落’與‘群體’的共同性是‘群’即多人構成,但‘群落’中人們在一定時期之內或有聯系、或無聯系,不似‘群體’中人們往往有一定的關聯或追求;詞人‘群落’中的詞人創(chuàng)作,或風格、趣味同趨,或風格、趣味異軌,不似‘群體’中人的風格、趣味多有一致的趨向”(第2頁);比較詞派與群落兩個概念時,先生又說“詞人群落固然由若干詞人組成,但不必探究是否有領袖,不必探究是否有‘一致的審美傾向和相近的藝術風格’,它是在一定時期內一群有交游或無交游、但在詞風上相同或相似的詞人,無所謂領袖或組織者,他們詞的創(chuàng)作各有異彩,又共放芳華”(第6頁)等。王兆鵬曾將“代群”概念引入宋詞流變觀察中,“以作家群體為中心,以詞人的生活年代、創(chuàng)作年代為依據。將同一年齡組(同一世代)、生活和創(chuàng)作又基本同時的詞人劃分為一個代群”*王兆鵬:《唐宋詞史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第8頁。,兩宋詞史劃分為六個階段。表面上看,王兆鵬的“代群”與先生的“群落”頗有相似之處,但在先生看來,“兆鵬沒說‘代群’內詞人的相互關聯,但其‘代群’在我看來仍然是歸于‘群體’之內的”(第7頁),群落與“代群”相似之處在于,形成的基礎是共同的時空,不同點在于代群的文學聯系更為緊密,而群落更僅僅關注在時代精神氣質的影響下詞人共同的時代性、不同的個性,可以將詞壇名家與非名家放在一起進行敘述,希望用生態(tài)學再現一個豐富多彩的歷史整體。
在實際撰述中,《演化》將宋詞歷程分為晏歐詞人群落、蘇門詞人群落、辛派詞人群落、姜張詞人群落的前后相續(xù)。雖然在詞人群落之前冠以“晏歐”“蘇門”“辛派”“姜張”等,不是意味著“晏歐”等是這個時空層面詞壇的領袖。之所以這樣,先生說:“主要是以晏殊、歐陽修為代表的詞人們在傳統詞風下,引領了詞壇的創(chuàng)作走向”(第65頁),是代表,敘述的重點不是他們,而是這個時代的詞人們。另外敘述時不再是以單個詞人進行,而是以在時代主潮之下詞的共同呈現為名,如“晏歐詞人的歌酒之樂與詞的流播”“晏歐詞人的人生詠嘆與追尋”“晏歐詞人的詞體新變及詞的敘事傾向”“晏歐詞人的趨俗風氣與柳永詞風的凸顯”“晏歐詞人都市詞和節(jié)慶詞的景觀”等等,從共同的主題呈現到文學風貌,因而在傳統詞史上因風格特性較強的名家諸如柳永、周邦彥、李清照、吳文英等的散點論述,在這里都并入了時代主潮中,通過詞人群落的關聯凸顯宋詞的基本面貌與演變,詞人的創(chuàng)作個性在相關主潮之下敘述。之所以能如此,無疑是“群落”理念立足于時代精神主潮看待歷史中詞人各自的演化,因而視點更高,也具有更大的含攝效果。
以群落來組織詞史,無疑淡化了先前以詞名家來組織詞史的習慣,而將觀察視點聚焦于詞的創(chuàng)作關聯以及前后詞風的變化,“由于是把一個群落的詞人同類或相近的詞放在一起考察,較之于逐一考察每一個詞人竊以為更能說明共同問題,以及更清楚地看到詞人詞風之間的聯系”(第465頁)。這樣,以群落來組織的宋詞史,關注點是前后相嬗群落各自的同異性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寫出了宋代詞體的演化。雖然先生在書的結語中自謙提到群落研究局限性的四個表現,但在我看來,任何方法都是有局限性的,只要能夠在學理基礎上提供新的認識,這種方法就是有效的,先生大著即是如此,何況先生描述的“這四大詞人群落能夠彰顯宋詞發(fā)展的始末和跌宕起伏的客觀狀態(tài)”(第464)。
讀罷先生以“群落”與“演化”為核心理念組織而成的宋代詞史,非常強烈地感受到“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通變”的歷史眼光,感受到先生對詞在宋代演化現象背后流動的時代精神氣質的深刻把握,正是時代精神氣質作用于不同詞人,才形成了詞人群落的同中之異;正是時代精神生態(tài)氣質的變動造就了詞人群落以及詞體風格的前后演化。如“北宋前60年的詩與詞之隔”,將北宋前期詞之不盛的時代精神分析得頗為精準,“詞人表現男女情戀、離愁別緒具有雅、俗兩種風格,代女性立言的現象漸淡,更多地表現自我情懷以及所見的景象,顯示出創(chuàng)作上的自由狀態(tài)”(第71頁),這個時期之所以詞作不旺,是因為新王朝意識形態(tài)的規(guī)約,使詞從一味單純的“娛情怡性”發(fā)展為“用來表現社會生活和詞人情志”(第76頁),新時代需要新詞,宋初六十年詞壇的寂寞顯示了詞體寫作的強大慣性以及五代入宋的詞人的艱難轉型。
當然,詞風的轉型還有另外的情形。如敘述姜張詞人群落時,先生道:“當辛棄疾沿著南渡詞人之路,深懷江山淪陷之悲、以詞彰顯內心激憤與報國不能的哀痛時,與辛棄疾有些交往的姜夔則受到北宋末年周邦彥雅詞的影響,另為一幟,同時也像辛棄疾一樣擁有自己的追隨者”(第364頁),所不同的是,“稼軒派代表的是南宋前期的時代精神和審美主潮,白石派代表的則是南宋后期的時代風尚與審美趨向”(第365頁),于是,稼軒派詞人群落與姜派詞人群落以及二者之間的演化均得到了合理的闡釋。同時,先生借助對中國文學史的洞見,并以之作為詞體演進過程中更為深遠的歷史背景,使得與詞體相關的一些問題成為文學史的一般性存在。如大約與辛棄疾同時的姜夔沒有選擇英雄式創(chuàng)作,先生以中國文學中詩文普遍規(guī)律來進行解釋:“自有文學以來,寫實的詩與浪漫的詩,散漫的散文與重聲律駢偶的駢文,乃至俗文學與雅文學互為消漲,詞自文人化了以后,雅風與俗風的跌宕一仍存在,詞的曠放與柔婉綺靡也交相影響”;如“辛派詞人以學問為詞的路徑”,不僅追溯了與蘇門詞人創(chuàng)作間的聯系,而且將此視為古已有之的創(chuàng)作現象以及北宋初期西昆體、江西詩派等詩學思潮等在詞中的延伸(第327、328頁),如此等等,將詞體現象置于廣闊的中國歷史和文學視野中,真正實現了宋詞的“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中國史家秉持“不虛美、不隱惡”的精神,客觀冷靜地對待歷史,先生說自己為此書是因為確實太喜歡宋詞,沉吟已久,揮之不去,但先生無論從思考以及行文,一直堅持 “客觀陳述的寫作方法”,在行文中總是保持必要的張力,不以主觀的好惡評論代替對詞史客觀的敘述,“努力多記述,少評說”,是記述體,非論說體,呈現出優(yōu)秀的史家品質。
先生的學術研究譜系中有《莊子創(chuàng)作論》《漢賦藝術論》《兩漢詩歌與傳統文化》《唐宋散文創(chuàng)作風貌與批評》等,現積多年的學術功力,聚焦于《演化》這一課題,無論是進入問題的方式,還是弄筆行文,自有舉重若輕之效。如引用南宋汪莘《方壺詩余自序》中宋詞三變說,“至東坡而一變”“二變?yōu)橹煜U妗薄叭兌鵀樾良谲帯?第65頁),一般人往往就事論事,然經先生輕輕反轉而頓生新義,得出“蘇軾前的詞風不變或說是詞人沿襲了傳統詞風”(第65頁),進入問題的方式出人意料,然而又在情理之中。且全書行文深入淺出,如行云流水,學術引據運用恰到好處,溶化無形,無學術專著的艱澀之弊,可讀性強。
先生是2002年底從武漢調往海南,并在海南退休。蘇軾當年到海南,曰“余生欲老海南村”,可最終離開;先生來到海南,扎根海南,在行政事務之余潛心學術,成為真正的海南人。曾讀先生《天涯守望:蘇東坡晚年的海南歲月》一書,在東坡縱浪大化、不喜不懼的精神行跡中可領會到先生的意趣。是的,天涯守望是蘇軾海南歲月的姿態(tài),又何嘗不是先生海南歲月的姿態(tài)?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家人、學生、朋友,雖處天涯,時時守望;但我知道,其中也有對學術的守望,正因為如此,先生到海南后不斷有新的學術成果產生,這部《演化》方能在跨越十七年之后面世。
(責任編輯:袁宇)
On Ruan Zhong’sTheCommunityofFourMasterCiPoetsinSongDynastyandChangesintheStyleofTheirCiPoems
YU Yi
(Department of Chinese, Donggu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uang 523808, China)
收稿日期:2016-02-05
作者簡介:余意(1971-),男,湖北浠水人,東莞理工學院中文系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I207.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5310(2016)-05-013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