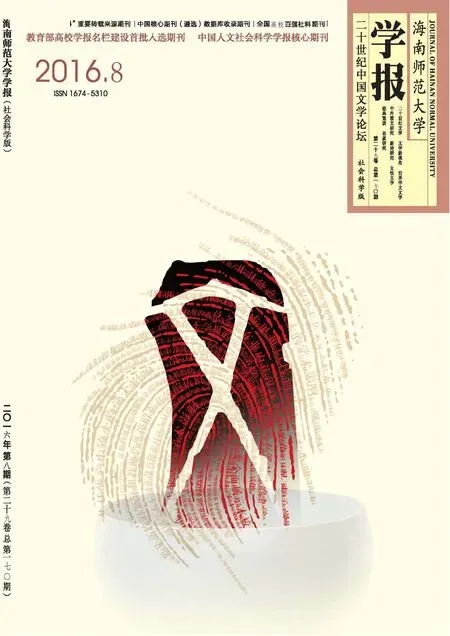以詩修行的先行者
——東蕩子和《東蕩子的詩》
林馥娜
(《中西詩歌》雜志社, 廣東 廣州 510630)
?
以詩修行的先行者
——東蕩子和《東蕩子的詩》
林馥娜
(《中西詩歌》雜志社, 廣東 廣州 510630)
因為摒棄了諸多物質的誘惑,詩人得以靜下心來傾聽萬物的聲音,從東蕩子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自然物象的深切洞察與了解,心靈圖境與詩學精神的永恒性,正是一個詩人賴以安心與歸宿的土壤。
東蕩子;阿斯加;自我挖掘;哲思范式;心靈圖境
“朋友離去草地已經很久/他帶著他的瓢,去了大海/他要在大海里盜取海水/遠方的火焰正把守海水/他帶著他的傷/他要在火焰中盜取海水/天暗下來,朋友要一生才能回來”(《朋友》)。①東蕩子:《東蕩子的詩》,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13頁。本文所引此書均出自此版本。東蕩子仙行了,朋友們要一生才能與他相見,但同時,他又似乎從未離開,他通過他的詩,一直在朋友圈中來而復往。
一、躬行自明:肉身與心靈的苦修
2004年應東蕩子的要求,我寫了一篇關于他的詩《黑色》的更正(在某刊刊出的詩與原詩有出入)與評論后,我對批評這個文體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興趣,因此可以說我走上詩歌批評的道路,是東蕩子間接促成的。《黑色》這首詩凝練精悍,所以即使編排上出現一字之差,也會有害詩意,由此可見東蕩子在詩歌文本上的嚴謹與求精。
自東蕩子到增城定居后,我與他見面的機會少了,但只要有機會在詩歌活動中相見,幾個較常聚的老朋友和詩會上隨機偶遇的一些詩友都會聚在他的房間,一起聊天,常常徹夜談詩論事,有時甚至爭論得不可開交。每次說話最多的都是東蕩子,他那洪亮的聲音伴隨著香煙煙柱在空氣中蕩漾、發散。每次聚會看到他只顧抽煙、喝酒、聊天,我總忍不住要叫他先吃點東西。他卻總說:“沒關系的,食物對我來說不重要,我只要一點點就足夠。你看我不都一直是這樣過來的。”
2004年圣誕節前夕,受汕尾杜青、冷梅之邀,我和東蕩子、世賓、老刀,還有開車的姐姐琳娜,一行五人出發去紅海灣,一路上東蕩子滔滔不絕,像是一個詩歌布道者,一直說著關于詩的話題。乃至到了汕尾,當地的詩友圍著他,向他請教詩歌問題,他依然一一解說,仿佛是一臺強勁的永動機,不知疲倦。姐姐琳娜作為局外人,對他的印象是有點憤青,有點犟。我想,詩人多少都有點憤世吧。詩人是最敏感的群體,往往具有濟世的情懷,對于所洞察到的各種荒謬與殘酷,憤怒是不可避免的,正因為眼里摻不進沙子,詩歌便成為詩人含沙成珠的豐盈產物:
一間茅屋要幾千年才能變成瓦房/建筑從未中止,但拖延也從未中止/誤工和偷工減料、燒毀、坍塌也從未中止/從未中止的還有兵荒馬亂和勾心斗角……殺戮將動物的毛皮緊繃在我們的身上/將它們的聲帶裝進我們的喉嚨……一顆心卻在一夜之間就碎成了粉末/一顆心越來越碎,越來越碎成更多的粉末/它不能回答,它在忙于碎,忙于流血*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48頁。(《上帝從不光顧我們的晚餐》)。
當自然法則與天理被潛規則敗壞與摧毀,無力抓住某些特權階層揮舞的刀子——“往來于各個節氣/然而在低處,從未見你把刀的爪子抓住”*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12頁。(《何等的法則》),當“天空已裂縫”,處于低處的眾生只能哀嘆“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時,“坍塌便不只是掩沒大地的聲音”,而是整個人文世界的坍塌。面對“坍塌的世界”,若要在寫作上達到自由,在心靈上獲得平靜,則取決于對這種內心與現實的沖突怎樣去進行平衡。東蕩子的處理方式是修行,他以苦行僧的方式,為自己的人生不斷地做減法——攝取最低限度的生活所需,以最精煉的表達進行詩寫,并在精神上驅除侵占心靈曠野的各種黑暗,身體力行,躬行自明。他說:“人和萬事萬物都是泥巴捏的,要想不再被捏來捏去,只有砍掉或遠離那些伸來的手。”*東蕩子:《不落下一粒塵埃》,《詩歌與人》專刊2009年4月,第125頁。我在為東蕩子所作的挽聯中有“東士仙行”之語,正是特指他具有“士”的那種修身律己的品格。
因為摒棄了諸多物質的誘惑,詩人得以靜下心來傾聽萬物的聲音,從東蕩子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自然物象的深切洞察與了解:
在空曠之地,或無人跡的角落/土地和植物悄悄腐熟/你轉過身,蘑菇冒出來了/無聲無息。卻全然不像水泡/當著你的面也會冒出/聲響果斷,短促而悠遠/有時還連續冒出一串/在同一個地方,接著便消失。*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16頁。(《水泡》)
這種與自然界的通感與共鳴,把詩人帶入一種無欲無求、無功利得失的虛靜之境:
那一刻來臨,時間在我的周圍靜止/我的心回到了它自己的祖國,它無限寬闊/思緒由此遠去,自由而寧靜/留連所有的事物,但并不思想它們/那一刻我不會像往常,處在喧鬧的人群/去深入他們和他們的事物中探求/我已失去重量,輕松而任意飛翔/在有些事物上,我會停下來/仿佛風從上面拂過,有時又會悄悄返回//那一刻來臨,我已經把我的肉體放在了一邊/沒有痛、沒有感受、世界通體透明/我隨意進去,又隨意出來,像從未來過/我的朋友、我的親人、陌生人,甚至傷害我/和被我傷害的人,以及動物和植物,所有奔走/繁忙和吵鬧,在我前頭閃過,從不打擾/我也不覺得肉體的顫動和心跳。那一刻/所有的一切都孤立,相互連接卻并不糾錯/時間已忘記了它手中的繩子/魚兒在永遠的水中/我在空中*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77頁。(《時間忘記了他手中的繩子》)
這時的詩人,已獲得了一種“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極致——領悟了自然規律之道,并從此進入生命的廣闊境界——對榮辱生死處之淡然。這時的“我”,已無需結繩為記,在時間的節點上設立為之奔忙的目標。
東蕩子與聶小雨結婚后,常對我說的一句話就是“來家里看小雨啊”。在一次《人民文學》組織作家到增城采風時,我和張鴻就來到了他家——九雨樓。一進家門,最打眼的是一長排的簡易書架和長長的書桌,地板配搭鵝卵石圖案的地磚,給人一種簡樸和諧的氣息。我不禁說,好!很簡潔。他滿臉得意地說“這都是我自己做的”。作為木匠的兒子,他有這個能力。這時的他,有一種家常的溫暖與近乎天真的笑臉。小雨則在旁準備煮水待客,家有嬌妻,任是多犟硬的男人,也有溫存的一面。我們也發覺,自從有了小雨,東蕩子的性格也悄悄發生了轉變,不再那么鋒芒畢露。因小雨本身也是作家,這對于兩者的創作,無疑也是相得益彰的,故他們夫妻雙雙摘取廣東省魯迅文學藝術獎。還記得當時得知獲獎消息時是在順德,我們正一起參加第11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的活動,大家紛紛祝賀東蕩子時,他還不忘讓我致電小雨,告訴她這個消息。心安則性平,正是家給他帶來俗世安妥的棲居。
曾經與世賓討論過東蕩子的詩,說起他如果閱讀更多的書,視野的寬闊和豐富的心靈體驗將會有助他的詩歌達到更加輝煌的境界,也曾和東蕩子當面談論過。但到了后來,也就是“阿斯加”出現在東蕩子的詩歌世界那個時段,世賓說,東蕩子就這樣走下去,繼續冥想,繼續走向內心,一條道走到底就行了,這路適合他。這似乎不無道理,隨著年歲的增長,并不斷在寫作中反省自我與他者的共同弱點中,東蕩子之前外露的銳氣已逐漸內化為作品的力量,并發明了“阿斯加”這個詩歌符號,這個既是自我,也是他者的“人”,成為東蕩子自由揮舞詩學之劍的載體,也使他的寫作得到了更加游刃有余的揮灑。他在向內自我挖掘式的思考中,不少詩歌都附著了自我設問與自我解答的哲思范式,使其詩作具有一種答辯式的自足性。比如《上帝從不光顧我們的晚餐》、《我永不知我會是獨自一人》、《信徒》、《何等的法則》等,他的詩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喜愛。
二、修辭的力量與精神修煉的共同發力
東蕩子的詩歌之所以受人喜愛,當與他賦予作品的思想性(詩學精神)與力量感有關。他與世賓、黃禮孩一同提出的“完整性寫作”理論是他為自己的寫作樹立的坐標。
理論并不是用來指導我們每一首詩的寫作,而是我們為自己所歸納和認同的審美方法樹立一個信仰般的思想標尺,這把標尺用于防止自己滑向美的反面,同時推動自己無限接近于心中審美理性的標高。
東蕩子的詩歌有一種占領感,他以演講式的、簡短有力的詩篇開門直入地抓住了讀者。修辭的張力就像是一張拉滿的弓,而一旦修辭上的力量與精神指向上的某一主題互相觸發,則精神主題的利箭便脫弓射向讀者的靶心。像他的《黑色》、《異類》、《讓他們去天堂修理柵欄》、《宣讀你內心那最后一頁》等詩作,都具有直抵人心的、緊崩的力量感。*林馥娜:《曠野淘馥——詩論卷》,廣州:花城出版社,2011年,第59-60頁。
我曾在評論專著中解讀過東蕩子《黑色》這首詩:
我從未遇見過神秘的事物/我從未遇見奇異的光照耀我/或在我身上發出我從未遇見過神/我從未因此而憂傷//可能我是一片真正的黑暗/神也恐懼從不看我/凝成黑色的一團在我和光明之間/神在奔跑模糊一片*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60頁。(《黑色》)
從未見過神是大眾的體驗,神在大眾的心目中是高高在上的,誰都沒有見過神,而東蕩子卻用“遇”這個字,把神拉到了與人平等的位置上,他讓我們領會到,我們隨時都有可能遇見神,他就在我們身邊,就在我們心中。人有時就在神性和人性,甚至是鬼性中穿梭!那既然神可以“遇”,為什么我又沒見過神秘事物、沒在我身上發出光呢?下半闕的詩告訴了我們——如果“我”心存黑暗,則“神”也“凝成黑色的一團”,我們只有規避人性的黑暗面,奔向光明,才可能與神重合,形成神與我一體的“模糊一片”,這時,我們正走在通向光明的路上,呼應了上半闕末句的“我從未因此而憂傷”,因為我們可以用詩學精神修身,走向神性的超我、能夠發出智慧光芒的我。詩學精神是神性的、充滿美與愛的精神,這里的神性并非指神話故事中所指的那類“神”,從唯物主義的角度來講,神其實就是人類心目中用以自律、寬慰、提升靈魂的個人宗教。*林馥娜:《曠野淘馥——詩論卷》,第4-5頁。
人在人性、神性乃至鬼性(惡念)中穿梭,詩人需要建構的,正是去除鬼性,拓展人性與神性,讓人類的行為(包括寫作)及靈魂在不斷批判現實、規避黑暗*林馥娜:《曠野淘馥——詩論卷》,第59-60頁。(“這里黑暗除了政治的,還必須攬括人類事務的所有領域,包括:人類心理內部的怯懦、無可奈何、人云亦云及一切精神性病癥;外部的疾病、戰爭、災難、死亡”*世賓:《夢想及其通知的世界》,《詩歌與人》2005年第9期,第19頁。)中無限靠近光明和諧的前景。
而東蕩子的《世界上只有一個》讓我們體會到每個詩人都是詩學精神的追求者,是驅散自身的黑暗與世界黑暗的修行者。所有的詩人都是詩學之塔的一塊磚,在修煉自己的同時修煉出詩學精神的高塔,修煉出頂天立地的“大詩人”。在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時代,一個重拾往昔珍貴事物的異類是多么孤單——“我孤身一人,只愿形影相隨/叫我異類吧/今天我會走到這田地/并把你們遺棄的,重又拾起”*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27頁。(《異類》)——又是多么可貴!就算被世俗的陰影拖下水,“可他仍然冥頑,不在落水中進取/不聚斂岸邊的財富”*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19頁。(《人為何物》)。這里的“冥頑”,正是一種精神的堅守與人性的修煉。*林馥娜:《曠野淘馥——詩論卷》,第59-60頁。
三、心靈圖境的永恒性
作為社會的一分子,詩人在白晝時必須在代表世俗生活的“長著金屬的面龐”的“一枚硬幣前停下”,但也可以在黑夜里繼續前行,不斷“創造黑夜,鼓足飛翔的勇氣/從此寫下輕于鴻毛的詩篇”*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52頁。(《在一枚硬幣前停下》),以與世人看不見的上帝相見。“上帝一直在我左右/他如喚我,好像他也在躲避/從不跟我討論我錯誤的一生/也不愿把我的靈魂放在合適的地方//當我最后離去/我只在秋天的懷里待過一個白晝/上帝卻在黑夜的林中,我看不見”*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61頁。(《上帝在黑夜的林中》),并通過與黑夜中的上帝——也就是和“超我”(詩性的我)相見——達到驅除“黑暗”,到達光明的境界;使放養的心靈一步步走向更寬廣的牧場,從而構筑出自由的心靈圖境。
而世俗意義上的成功真的能帶給我們幸福嗎?當人們由世俗標準裹挾著,一路狂奔在追名逐利的狹路上,而從不停下來思考人生的意義和真正合適自己的道路時;當我們忙得沒有時間來珍惜身邊的所有時;當我們的精神生活一片荒蕪而如行尸走肉時;這種同一模式的幸福,無疑是一副副枷鎖和鐐銬,這種盲目的、想得到和別人一樣的成功和幸福、無休止的追逐和輪回,不能不說是人類永劫回歸的怪圈。“誰在指使我們/創造光輝的勛章要我們佩戴/我們卻往往在同一爐膛打出枷鎖和鐐銬……也沒有人,不愿意不追求幸福/那好,還是讓我們/來把幸福的含義全部揭穿/它來自人類/它是人類一場永劫的懲罰”*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110頁。(《生存》)。
唯其對人生意義持續的追問和透徹的參悟,才讓詩人卸下了困住心靈的枷鎖,獲得了精神的自由——看淡世事,看輕生死。“他已不再談論艱辛,就像身子隨便挪一挪/把在沙漠上的煎熬,視為手邊的勞動”*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38頁。(《別怪他不再眷戀》)。“一頂帽子無論怎樣變化,即使如夜鶯把夜統領/都只是戴在頭頂。是的,他就這么看”*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39頁。(《他就這么看》)。是的,不管在世俗中擁有多么榮耀的頭銜,那都只是一頂暫時戴在頭上的帽子,一切終會隱入大地的恒久寂穆中。只有觸及靈魂的吟唱依然會在一代代人的共振與時光的淘洗中發出獨立的光芒。“我快要死了,一邊死我一邊說話/有一個東西我仍然深信/它從不圍繞任何星體轉來轉去/倘若它一心發光/死后我又如何懷疑/一個失去聲帶的人會停止歌唱”*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47頁。(《倘若它一心發光》)。我們無法掌握生命的存亡與年輪的長短,但“值得我回味的或許是我已發出自己的聲響/像閃電,雖不復現”*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37頁。(《不要讓這門手藝失傳》),閃電所照亮的人生,雖然仍不可操控,但只要詩藝不失傳,詩歌精神的光芒依然會照亮更多人行進中的前路。
把一個物件放到一個地方/它的位置在那里/但它的思想不一定在那里/任何永恒的東西都不會在心靈之外/我們犯過這樣的錯誤/我們說:鳥兒,飛/鳥兒就飛走了/鳥兒真的就飛走了嗎/我們把碑埋在墓地——不朽啊/我們所看到的人/無非是一個個墓碑的影子/他們孤獨地離去。花束留下了/花束又在那里死去/我們再拿什么獻在花的墓前/甚至一萬年過去/我們仍有許多東西不解/光榮和羞辱/我們應當把它們放在哪里/啊心靈,永恒的塵土/我又一天接近了你/即便你和他們一樣/從不把我放在心上*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88頁。(《塵土》)
不管是先行者還是后來者,一切終究敵不過時間的磨盤,萬物均歸于塵土,而又永生于永恒的塵土——心靈圖境。
我無知而生存/我盲目地有知而生存得如此熱烈/為虛無寫下頌辭,為真實而斗爭/即使痛苦也得用半生來眷戀……我永不知到達山峰還能繼續上升/我永不知那山峰為什么使我前往/我永不知我會疲倦而去像那巨石滾下/我永不知我會是獨自一人*東蕩子:《東蕩子的詩》,第91頁。(《我永不知我會是獨自一人》)
東蕩子獨自一人疲倦而去了,唯有心靈的吟唱永遠伴隨著他,并回旋在親友中,在更多人群中傳誦。反之,心靈圖境與詩學精神的永恒性,正是一個詩人賴以安心與歸宿的土壤。朋友說,東蕩子是天上派來的,現在回去了。是的,東蕩子就是詩神派來傳道的,他完成了他的使命,“別怪他不再眷戀,他已收獲,仿若鉆石沉眠”。
(責任編輯:王學振)
Dong Dangzi andDongDangzi’sPoems
LIN Fu-na
(PeriodicalOfficeofChineseandWesternVerse,Guangzhou510510,China)
Thanks to his abandonment of various material temptations, the poet can calm down to give ear to the voice of all things. In Dong Dangzi’s poems can be discerned his deep insight and understanding of natural objects. In short, the mind map and the eternity of the poetic spirit is the very land on and to which the poet can feel at ease and return.
Dong Dangzi; Asgard; self-exploration; philosophical paradigm; the mind map
2016-05-28
林馥娜(1970-),女,廣東揭陽人,《中西詩歌》雜志社編輯,主要從事詩歌創作與研究。
I227
A
1674-5310(2016)-08-00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