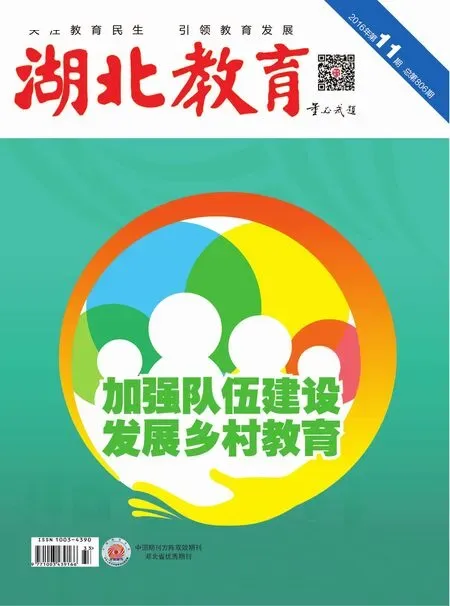農(nóng)村學校的一面旗幟——監(jiān)利縣尺八鎮(zhèn)紅廟中學探秘
●本刊記者曾憲波徐世兵
農(nóng)村學校的一面旗幟——監(jiān)利縣尺八鎮(zhèn)紅廟中學探秘
●本刊記者曾憲波徐世兵
地處長江故道——老江河畔的監(jiān)利縣尺八鎮(zhèn)紅廟中學,是一所“管理區(qū)級”的農(nóng)村九年一貫制學校。該校因教育質(zhì)量高而遠近聞名,2002年以來,中考質(zhì)量綜合考核連續(xù)14年位居全縣前三甲;近三年來,一、二類高中升學率占參考學生數(shù)的88%,高中錄取率近100%。
多年來,在城鎮(zhèn)化步伐逐步加快的背景下,紅廟中學的學生數(shù)不降反增,1300多名學生中有一半來自于其他鄉(xiāng)鎮(zhèn)。全校56名教師,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而且他們大多是“民轉(zhuǎn)公”教師,或是紅廟中學的畢業(yè)生。他們從不抱怨,堅持以愛育愛,在教書育人的崗位上孜孜以求。
民主化和精細化管理讓學校摘掉了“紅老九”的帽子,并進入良性發(fā)展軌道
1987年,龔慶華成為紅廟中學的第九任校長。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紅廟中學因連年考試成績在當?shù)鼐C合排名第九(倒數(shù)第一),被人們笑稱為“紅老九”。當時學校生源萎縮,教師人心不穩(wěn),科班出身的教師大部分“流失”,留下來的絕大部分是“民轉(zhuǎn)公”教師。
龔慶華認為,“紅老九”是壓在全校教師心頭的一塊巨石,要突破學校發(fā)展困境,唯有首先通過改革凝聚人心,然后帶領(lǐng)全校教師謀求發(fā)展。于是,經(jīng)過學校領(lǐng)導(dǎo)班子和職代會充分醞釀和反復(fù)討論,學校決定推行“績效考核”,即對教師的德、能、勤、績進行量化評價,評價結(jié)果與工資掛鉤。此舉開監(jiān)利教育改革之先河,并不斷完善,沿用至今。
在績效考核面前,無論是校長還是普通教師,人人平等。這項在當時看來似乎不近人情的改革,徹底改變了教師慵懶散漫不作為的工作狀態(tài),給每個人的工作立下了“規(guī)矩”,明確了個人教育教學目標和學校發(fā)展目標。此后,紅廟中學的教育教學質(zhì)量開始走出低谷,并且一年上一個新臺階。
2000年前后,紅廟中學生源銳減,雖然對學校的教育教學質(zhì)量沒什么影響,但此時全縣實行撤點并校,這意味著如果教育質(zhì)量上不去,“紅廟中學”的名字有可能將不復(fù)存在。
第十一任校長龔振華根據(jù)校情和撤點并校的嚴峻現(xiàn)實,明確提出了“要把B類學校辦出A類學校水平”的發(fā)展目標,他在完善教師績效考核體系的基礎(chǔ)上,繼續(xù)加大學校制度建設(shè)的力度,抓實抓細教學常規(guī),學校一切工作服從并服務(wù)于教育教學這個中心。
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調(diào)整與優(yōu)化,帶來的是學校教育質(zhì)量的持續(xù)攀升。2003年,在監(jiān)利縣中考質(zhì)量綜合考核評價中,紅廟中學一舉躍至全縣前三強,徹底摘掉了“紅老九”的帽子。
1995年大學畢業(yè)后,舒成名回到母校紅廟中學工作,從一名普通教師一步步走上校長崗位。在他看來,紅廟中學的發(fā)展得益于建立健全了一套科學完備的制度,是民主化和精細化管理讓學校發(fā)展得越來越好。
目前,紅廟中學的制度體系,包括各類計劃、方案等共計二十八大項,涵蓋教育、教學、教研、安全、財務(wù)、后勤、獎懲等方方方面,學校實現(xiàn)了制度管理無死角的目標,每一項工作均有章可循、有據(jù)可依。
這些制度之所以“立”得住、能管用,是因為這些制度都是經(jīng)教代會討論通過后才頒布實行的。試行中如果存在問題,再征求意見和建議并組織職代會代表討論,直至通過為止。比如,學校工作計劃,首先由校長起草,然后提交教代會討論通過,最后形成正式文本并在學校例會上發(fā)布。
在紅廟中學,學校每一項制度的管理與落實,都有專人負責。例如《學生安全管理制度》和《值周教師職責》由該校黨支部副書記兼政教主任負責管理實施,各班班主任和值周教師積極協(xié)助。學校對值周教師的工作進行考評,并將其納入績效考核范疇。
精細化的管理,讓紅廟中學始終以教育教學工作為中心,并且每一項工作都有“規(guī)矩”,每一個崗位都有職責和目標。舒成名說,是科學完備的制度體系保障了紅廟中學這列火車的規(guī)范健康運行。
每個年級每個學生都是重點,把教學常規(guī)做到極致,讓每一個學生成為最好的自己,學校的教育質(zhì)量才會“屹立不倒”
紅廟中學為什么能創(chuàng)造農(nóng)村學校的奇跡?舒成名說:“在紅廟中學,我們的管理不僅看重結(jié)果,更重視過程和教學常規(guī)方面的細節(jié)。”
從七年級到九年級,重點是哪一個學年?很多學校理所當然地確定為九年級。“管理要從基礎(chǔ)、源頭和過程抓起。”舒成名認為,在管理策略上,九年級是重點,但七年級是基礎(chǔ),八年級是關(guān)鍵,所以同樣應(yīng)該給予高度關(guān)注和重視。
舒成名說,“這如同我們跑步,開始拼命跑,而中途不斷掉隊,那最后還怎么沖刺?”紅廟中學提出了“一年中考三年抓,注重七、八、九年級的連續(xù)性和連貫性,同時注重各個年級的側(cè)重點”的管理思路,即七年級側(cè)重習慣養(yǎng)成教育,八年級側(cè)重學科平衡發(fā)展,九年級則堅持狠抓教育教學質(zhì)量的全面提升。
有效的常規(guī)教學管理是提升教學質(zhì)量最有力的保證。在常規(guī)教學管理中,紅廟中學堅持做到突出“五個環(huán)節(jié)(即集體備課、教案編寫、課堂教學、單元過關(guān)和作業(yè)設(shè)計與批改)”和嚴把“一個關(guān)口(即常規(guī)檢查關(guān))”,按照常規(guī)檢查制度,做到推門聽課與上公開課相結(jié)合、月末檢查與隨機抽查相結(jié)合,并公開評分評級。
每次月考,對紅廟中學的教師們來說,并不是對教和學的簡單檢測,而是通過考試抓好教與學的全面分析。質(zhì)量分析不單單看分數(shù),還要看“三率”(及格率、優(yōu)生率和低分率),更要從知識、能力、智力,從課內(nèi)、課外,從教法和學法,從師生互動、信息反饋等方面進行全方位的分析,既總結(jié)成績和經(jīng)驗,也要查找知識上的缺漏和教法學法上的薄弱環(huán)節(jié),進而采取分層指導(dǎo)和課后補救等措施。
在探索提升教育教學質(zhì)量的過程中,紅廟中學教師發(fā)現(xiàn):學校優(yōu)等生數(shù)量不多,進步空間較小;中下等生人數(shù)眾多,進步空間往往非常大。為此,學校倡導(dǎo)“培優(yōu)補差”,重在“補差”的教學策略。
舒成名說,學校班班有絕招,人人有妙法。上學期狠抓學習興趣,攻優(yōu)提能;下學期開展生生結(jié)對搞競爭,利用擂臺賽、小考比、大考評,不拋棄,不放棄,調(diào)動積極性,分層促提高,消滅低分率。
課堂教學的優(yōu)劣是反映教學質(zhì)量高低的主要因素,而提高課堂教學效率關(guān)鍵靠全校教師。比如,張志利老師探索并運用“243”課堂教學模式,即每節(jié)課按2∶4∶3的時間比例,分“自主學習——合作探究——達標總結(jié)”三個步驟來實施課堂教學。
在課堂教學中,張志利老師總是“蹲”下來與學生談心,了解學生學習和生活上的困惑和困難,想辦法幫助其解決,與全班學生交朋友。
作為學校的語文教研組組長,張志利還組織和指導(dǎo)語文教師開展主題教研活動,分年級分層次編寫了《記敘文寫作層級訓(xùn)練》,讓學生不再“怕作文”,并在學校成立了“荊蕾文學社”,學生慢慢由“怕作文”到“愛上作文”。
紅廟中學采用教師積分評價制度,按照《紅廟中學教師常規(guī)教學獎計算方案及教師積分辦法》,把每學期教師任課班級的月考、期中、期末考試成績折算成教師的績效積分,以此來兌現(xiàn)教師的獎勵性績效工資,同時把教師積分作為教師評優(yōu)表模、職稱晉升的重要依據(jù)。
在紅廟中學,無論是管理,還是教學,沒有“權(quán)威”,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是被管理者;每個年級每個學生都是學校工作的重點,都是老師們關(guān)注的對象,他們通過面向全體學生,讓每一個學生都能成為最好的自己。舒成名說,如果能挖掘出全校每個學生的優(yōu)勢和潛能,那么學校的教育質(zhì)量能不好嗎?
圍墻可以圍住學生的人,但圍不住學生的心,尊重并關(guān)愛每一個學生已成為學校的傳統(tǒng)文化
紅廟中學地處江漢平原,四周溝渠縱橫,但學校沒有圍墻,只有一條護校河。
40多年前,紅廟中學搬遷至現(xiàn)址,受當時經(jīng)濟條件的制約,學校一直沒有建圍墻,后來就在學校四周挖了一條護校河,而且一直沿用至今。
學生晚上去網(wǎng)吧怎么辦?學校副書記兼政教主任蔡文華自豪地說,從學校到鎮(zhèn)上開車需要20分鐘,以前偶有學生悄悄溜出去上網(wǎng)的情況,而現(xiàn)在除開正常放假,學生都能自覺遵守紀律,淺淺的護校河本來就攔不住“鋌而走險”的學生,如今基本上算是“形同虛設(shè)”。
“圍墻圍住的是學生的人,但圍不住學生的心。”舒成名說,在紅廟中學,不搞教師跟班上、不搞大循環(huán)、不辦實驗班,但每個科任教師都對學生的家庭教育、性格特點、興趣愛好等情況了如指掌。
學校高度關(guān)注學生的個性差異,對留守青少年實行“愛心包保”,即生活上知情、學習上引路、成長中保護。每名班主任結(jié)對幫扶10名學生,每名學科教師結(jié)對幫扶6名學生。作為結(jié)對幫扶的導(dǎo)師,學校要求定期家訪,幫助學生分析學習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并進行針對性的輔導(dǎo)。學校還爭取企業(yè)和愛心人士的支持,對貧困學生進行幫扶和資助。
多年前,季從明老師為幫助他們班上的學生唐國棟戒掉“網(wǎng)癮”,最后發(fā)展到“陪吃陪睡”,后來干脆把他接到家里“同吃同住”。功夫不負有心人,唐國棟的網(wǎng)癮慢慢戒掉,后來以不錯的成績被一類高中錄取。
在紅廟中學,教師對學生的關(guān)愛沒有“真空”地帶,他們把每一個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來培養(yǎng)和呵護,竭盡所能,全力以赴。
承擔九年級思品三個班教學任務(wù)的學校工會主席薛東輝,承擔九年級歷史三個班教學任務(wù)的總務(wù)主任李玉華,都是九十年代從村小選拔到紅廟中學的。像他們這樣“從田埂上走出來的教師”,在紅廟中學占一半以上,其中“民轉(zhuǎn)公”教師30多人。舒成名說,這些老教師非常敬業(yè),不甘落后,生怕因為自己的工作拖了年級或班級工作的后腿。
張志利也是一名“民轉(zhuǎn)公”教師,2000年從村小選拔至紅廟中學任教,承擔九年級語文、歷史、生物、體育等多門學科,還兼任一個班的班主任,他積極鉆研教學,2014年因教學質(zhì)量佳和管理能力強被評為“全國優(yōu)秀教師”。他告訴記者,“學校領(lǐng)導(dǎo)以身作則,帶主課,搞教研,干得扎扎實實,我們能不兢兢業(yè)業(yè)嗎?”
張志利在學校還推行了“136”班級自主管理模式,即“1”個班主任助理,“3”套班委會,“6”個學習小組自主管理,學生不僅成了學習的主人,也從中體會到了學習的樂趣。
“尊重并關(guān)愛每一個學生,已經(jīng)成為紅廟中學的傳統(tǒng)文化,并且在不斷的傳承與發(fā)展。”在監(jiān)利縣教育局副局長周五一看來,紅廟中學所創(chuàng)造的教育質(zhì)量奇跡,依靠的是教師隊伍精神和行為文化的巨大力量。
學校的“軟件”比“硬件”更重要,是薪火相傳的“紅中精神”照亮了孩子們的發(fā)展之路
學校文化是一所學校的靈魂和血脈,是學校賴以生存的根基,也是學校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精神動力。
舒成名說,紅廟中學教育教學質(zhì)量之所以一直保持強勁的發(fā)展勢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一代又一代的紅中人在工作中積淀形成的獨具特色的“紅中精神”,即艱苦奮斗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團結(jié)協(xié)作的合作精神,勤奮敬業(yè)的進取精神,愛生如子的博愛精神,敢為人先的拼搏精神。
上世紀七十年代,紅廟中學所處的地理位置曾是一片低洼地,當時從異地搬遷過來時,鎮(zhèn)里僅有能力建幾間教室,而操場、食堂、廁所等教學生活用房和教學設(shè)施只能靠學校自己想辦法解決。沒有圍墻,學校想出“土辦法”,組織教師開挖護校河,肩扛背馱,一個冬春的工夫就完工了。
上世紀九十年代,學校有40多名公辦教師,因為大多是“民轉(zhuǎn)公”教師,所以多屬“半邊戶”,僅憑丈夫(或妻子)一人教書,很難養(yǎng)活家人。為了讓教師們“安心從教”,學校利用勤工儉學基地,想出了“挖魚池養(yǎng)魚植藕,在田埂上種菜,還把學生的剩菜剩飯收集起來開辦養(yǎng)豬場”等辦法和舉措,以便安排“半邊戶”教師家屬“就業(yè)”。
近15年來,紅廟中學勤工儉學收入達100多萬元。靠勤工儉學創(chuàng)造的財富,學校修起了辦公樓、學生宿舍、實驗室、閱覽室、倉庫等,為學生添置床鋪百余套,蔬菜、油料基本可以實現(xiàn)自給自足。
“事實證明,學校的‘軟件’比‘硬件’更重要。”舒成名深有體會地說,紅中人不等不靠,憑著艱苦奮斗的“創(chuàng)業(yè)精神”,一步改變著學校的面貌,實現(xiàn)了紅廟中學“起步—崛起—騰飛”的發(fā)展目標。
或許,在很多人的頭腦中,教學質(zhì)量高的學校大多競爭激烈,空氣中會有一種“火藥味”,紅中人也愛競爭,但他們的競爭走出了狹隘的一己之利的局限,更注重團隊協(xié)作。學校領(lǐng)導(dǎo)與教師之間、教師與教師之間,關(guān)系融洽,配合默契,形成了一個團結(jié)協(xié)作的戰(zhàn)斗集體。
這種團結(jié)協(xié)作的精神,首先體現(xiàn)在歷任“校長”身上。學校的發(fā)展規(guī)劃,不是一任校長一個樣,不是推倒重來,而是注重傳承,像血液一樣在人體循環(huán)。有的校長雖然離開了紅廟中學,但是新校長們總會定期把老校長接回學校,虛心求教;老校長們有時不請自來,經(jīng)常“回家看看”,并根據(jù)聽到的新情況和看到的新問題,出謀劃策。
在采訪中,紅廟中學教師之間的團結(jié)協(xié)作精神給記者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學校教師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對紅廟中學有一種深厚的感情,正是這種淳樸的校風,純粹的人際關(guān)系,讓這所學校如此“與眾不同”。
現(xiàn)年50歲的季從明,曾經(jīng)有過幾次更好的去處和發(fā)展機會,評委老師一看他寫的板書,就說“不用上了,我們要了”,但他最終因為舍不得丟下自己的學生,而選擇了放棄。2014年,季從明參評農(nóng)村特級教師,因為沒有專著而失利。他說:“我經(jīng)常看余映潮等大家的教學視頻,我雖然曾經(jīng)是一名民辦教師,但我絕不想落下‘誤人子弟’的名聲。”
舒成名說,“前輩們給紅廟中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chǔ),我們只是在傳承,做了我們應(yīng)該做的和力所能及的事情。”不過,在記者看來,正是薪火相傳的“紅中精神”成就了紅廟中學經(jīng)久不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