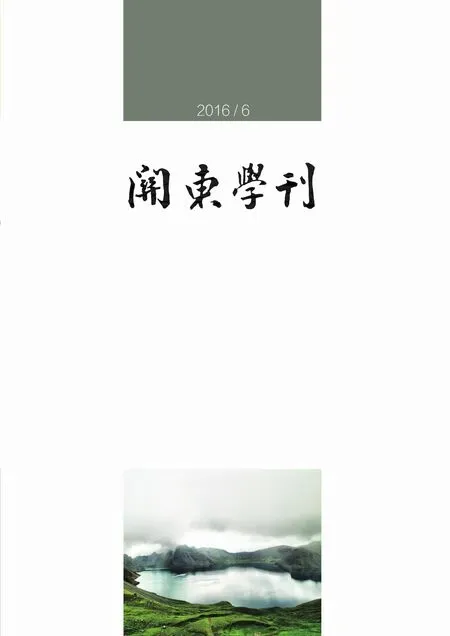“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淺論
向 輝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淺論
向 輝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出自《中庸》首章,歷代儒者的注疏頗有異同,鄭玄以義理釋之,孔穎達以無有釋之,朱熹、王陽明、王夫之諸大儒對此亦各有論說。通過儒者常道、敬慎的詮釋,本文闡明了莫見莫顯的經典意涵,凸顯出誠敬之道的理據及其德性教化的內涵。
莫見莫顯;隱微;敬慎
儒學源自生活,儒學立足經典,儒學追求好的生活與好的社會。因此,經典的詮釋成為儒學學術和儒者生活的基本內容之一。新儒學正是在經典詮釋的過程中,吸納各家學說,使傳統得以創造性轉化,而具有了新的內涵,確立了新的典范,其中《大學》《中庸》不僅為道學提供了基本的心性范疇和工夫范疇,也成為道學心性哲學和工夫理論的核心經典①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第91頁。。《中庸》作為儒家典范之一,內涵著的儒者人文精神,經歷代通儒大儒的不斷詮釋,使之成為內嵌于人們日常話語中的知識儲備,或者說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支援意識,具有其獨特的學術地位和典范意義。雖然《中庸》一書的文本僅3544字,歷代儒者對其的詮釋早已深入到文本中任何一字一句,基本上每一個字、詞、句都有若干相同或相異的詮釋②參見譚宇權:《中庸哲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王岳川:《大學中庸講演錄》,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解頡理:《中庸詮釋史研究》,山東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0年。。相同部分可見儒學的基本理念的恒久性,而相異之處則可觀大儒之間的思想境界和哲學理念的差異,這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儒學本身的多元詮釋的可能性及其包容性。在儒學即將迎來全面復興的時代,對于經典文本的詮釋必將出現新的典范,這應當是可以期待的。當然,在新的典范出現之前,我們有必要對于過往的范式加以梳理,同時對文本理解的多重可能性加以紓解,從而為我們在常識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有益的質料,或許這是當下儒學學術的基礎性工作之一。筆者不揣谫陋,試以《中庸》首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一語之諸先儒的注疏和相關文本為據,略加董理,以為一臠之嘗。
一、早期的不同詮釋路徑
自漢代開始立五經博士之后,五經及其注疏成為后世儒者的典范。其后,經唐宋諸大儒,特別是孔穎達(北齊后主武平五年至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574-648;字沖遠、一字仲達)、朱熹(宋建炎四年至慶元六年,1130-1200;字仲晦、號晦庵)等人的整理、注疏、闡發之后,其文字和義理闡釋成為后世儒者論說的出發點和依據。其中,《中庸》一書先為《子思子》一篇①“《中庸》《表記》《防記》《緇衣》,皆取《子思子》。”魏徵等:《隋書》(卷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88頁。,其后被納入《禮記》一書,由于內涵豐富的儒學義理,重要性日趨凸顯,經過唐宋儒者的大力彰顯述說,最終以《四書》之一而獨立于《禮記》。獨立成書的《中庸》并未在義理上脫離儒學語境,故仍以前儒的注疏作為依據,如首章第三節為:“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孔氏釋莫為無,其后宋明諸儒多以此為據或引申而闡發新意,或駁之而立新說。不過,現代學者失去了對于古典文化的生存體驗,難免產生各種曲解,甚至是誤解,不免不感慨“其語境意義令人費解”,因為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庸》論證結構并非精工細作,概念之間的邏輯聯系并不是很明晰,從一個概念到另一個概念的語義運動,也不構成一種線性的進展,毋寧是中國傳統的詩一般的表達方式,即不以邏輯嚴密精確為鵠的,而是以引起人的內在共鳴②杜維明:《中庸:論儒學的宗教性》,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第5頁。,使人以感通之心加以體會而知其味。當然,我們也需要通過歷代大儒的注疏作為感通知味的橋梁,即通過對不同線索的梳理從而加深我們對于經典文本的理解。
眾所周知,朱子之前,《中庸》注疏以鄭玄(漢順帝永建二年至漢獻帝建安五年,127-200;字康成)注和孔穎達疏為典范,在《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中庸第三十一》中,鄭玄注為:
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于隱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
其情也。若有覘聽之者,是為顯見,甚于眾人之中為之。③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87頁。
鄭玄注經言簡意賅,毫無繁瑣枝節。此處,鄭氏將君子小人處事方式對舉,小人以不睹不聞為隱微,而君子佔聽者看來則為顯見。雖然在《檀弓上》“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之鄭注有“莫,無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④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第339頁。的說法,此處鄭氏注并未以莫為無。顯然,這里鄭氏注重在對文本隱含的意涵加以重新紓解,闡明人行為處事的隱微處之審慎誠敬是君子小人之辨的樞機。與司馬遷《史記》一致⑤“孔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伯魚生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于宋。子思作《中庸》。”司馬遷:《史記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946頁。,鄭玄也認為《中庸》是孔子之孫子思⑥關于《中庸》一書的作者,后世學者多有爭論。徐復觀認為,今日之《中庸》原系分為兩篇,上篇可以推定出于子思,其中或也雜有他的門人的話。下篇則是上篇的發展,它系出于子思之門人,即將現《中庸》編定成書之人。此人仍在孟子之前。徐復觀:《中國人性史論先秦篇·從命到性:中庸的性命思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93頁。所做,記錄、表彰了其先祖孔夫子的圣德,所謂庸非平庸之意,而是常是用,“記中和之為用也”①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第1990頁。“用中為常道也”②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第1987頁。,因此鄭氏之注特注重對于《中庸》文本所闡發的君子所本之性,能循之跡,可脩之行,可仿之治。中庸之道即是君子“出入動作由之,離之惡乎從也”③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第1987頁。之道。就常道而言,社會之中,君子小人各行其道,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即在于他在行動上超越了小人,在道德上陵越了小人,因此,鄭氏對于文本的詮釋多以君子小人之事對舉,在“莫見莫隱”上就理所當然地判定,這是小人自以為其行動非在公眾視野中,是人不睹不聞者,故無所忌憚。然而,君子知有佔聽者能察識其隱,覷破其小人行徑,故君子以小人之隱微之無為有,慎獨即是君子在閑居獨處時亦保持審慎與克制,不肆其情,不恣其意,常以用中,恒以守中,否則即淪為小人。故可以說,在鄭玄的注疏中,“莫”意味著小人漠視而君子知之者。
孔穎達繼鄭氏注之后為《禮記》注疏,部分采用了鄭氏的說法,其疏為: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莫,無也。言凡在眾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皆佔聽,察見罪狀,甚于眾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如此。以罪過愆失,無見于幽隱之處,無顯露于細微之所也。○“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以其隱微之處,恐其罪惡彰顯,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獨居。言雖曰獨居,能謹慎守道也。④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第1989頁。
在孔穎達的疏文中,“莫”字被明確地訓釋為“無”。所謂無是相對于有而言,以孔氏疏文理解,它意味著人之罪愆不因其幽隱細微而不顯于人。很明顯地,孔氏已不再將此作為君子小人之辨的關鍵,而是認為人在眾人前知所敬畏,而其于獨處幽隱之時以為眾人不得見其行為,故恣情肆意,或為非作歹犯有罪過,或無所檢點行為有虧,但人們都能佔聽并能察覺到他的罪愆情狀,而且這種罪愆比起在眾人之前所行者更為惡劣,也更受人鄙夷,故君子需要時刻謹慎其獨處獨居之時。君子正因為知曉隱微之地仍之“無”乃非真正之“無”,故時時慎懼敬畏,使自身行為“無見于”“無顯露于”隱微之所。這就意味著,莫之“無”實際上乃是“有”,此“有”不因其隱微而“無”,因為人人具有佔聽之能,均能判別其罪愆過失。孔氏之疏,將道家思想注入儒者文本的詮釋之中,故其解釋道時本諸老子所說“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而提出“道者,通物之名”,人感自然而生,必修道而行,不違越自然天性,方為中庸之德,方可謂之道⑤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第1988頁。。“道,猶道路也,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于人,人行于道路,不可須臾離也。”⑥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呂友仁整理,第1989頁。就此而言,道路之道乃是人生坦途,人所共知,行于此者,即在眾人矚目之下,而其獨居之時,雖貌似無眾人矚目,卻實有人所佔聽者,故君子之人在其獨居時亦應以常道時的謹慎敬畏行事,如此才能入于道,且謹守其道。
孔穎達之后,有唐儒李翱(唐代宗大歷七年至唐武宗會昌四年,772-844;字習之)著《復性書》三篇特揭《中庸》之旨加以表彰。習之主“性情說”,其所謂性即是佛學中之本心,而情即是無名煩惱,故云:“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⑦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三松堂全集》(第三版),北京:中華書局,2015(2014)年,第699頁。,情之為害在于使性昏與動,故當復性,即中庸之誠。李氏說:
誠者,圣人之性也。……道者,至誠也。……人皆可以及乎此。……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柯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于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復性書上》,《四部叢刊》影印明成化本)
誠是復性的功夫,也是求儒者性命之源的圣人之道,正是在《中庸》一書中,子思闡明了這一復性的修身齊家之道,故李氏特加表彰,認為漢儒注解《中庸》是以事解非以心通,解經需要通乎心,因此從誠明之心來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于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復性書中》)可見,李翱對于莫的詮釋與孔穎達并無差異,均以之為無,不過這里的隱微非但不是不睹不聞之所,反而因為視聽昭昭、人人皆能佔聽,而成為實有顯白之地,君子明乎此,則慎其獨居獨處之時。在漢唐儒者這里,莫見莫顯基本上是從君子之修行而言,所謂莫之無實為有,君子戒慎恐懼其行為之盡于道,故須慎其獨居。
在李翱,“莫”之“無”非但不是沒有,而是實有。無不知、無弗為的道體、心體自然而知,自然而聞,因此復性就是復其無不知無弗為的狀態,慎獨就是歸其寂而不動之體,由此而守中誠明。
二、宋明理學的詮釋路徑
對于鄭孔注疏及李翱復性之說,朱子以為其意未盡,“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①石、朱熹:《中庸輯略》,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儒藏精華編》(第104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9頁。前文所述以莫為無的疏解或許正是朱子所謂雜乎佛老而言之之意。
朱子章句對于此一文本的文字之音韻和含義、詞句的意涵和義理均作了較為細致的解釋,其章句為:
見,音現。〇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于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于將萌,而不使其滋長于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②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20頁。
朱子并未對“莫”字加以章句注疏。朱子解經極為謹慎,一字一句均有多重考量,對于前儒注疏多有采用,為何此處不用孔穎達之疏而是回歸鄭注模式?是否對孔氏注疏有所保留?從此處注疏可見,他對《中庸》首章的詮釋乃是其思想融貫處,即以理學之道加以貫徹之,使之成為理學典范。在朱子,道即是事物莫不各有其當然不易之理,隱微之間雖他人不見而己所獨聞,吾心之靈莫不知之,不容有所欺罔,故莫字若以無詮釋之則無法承載道的內涵,只能以義理加以疏解之,因此其《中庸或問》說:
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也不可離而君子必戒慎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先其事之未然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謹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于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①朱熹:《四書或問·中庸或問》,朱傑人等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554頁。
莫并非無而是有,即人心昭靈明覺,察識動靜,雖隱微亦不例外,故朱子云:“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卻是教人恐懼戒慎,做存養工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慎意。‘故君子’以下,卻是教人慎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個‘故’字,便是方說入身上來做工夫也。圣人教人,只此兩端。”②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二),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505頁。由此可徵,“莫見莫顯”只是非君子之人所自以為之事,實則道心莫不清晰知曉。圣賢之教即是因人日常不可離之道而修之,君子以圣賢之教為學,故因其不可離而持守之。道心貫乎動靜隱微,故所謂隱微不睹不聞只是他人不知而已,己之道心何嘗不睹不聞?其以為人不知者,只是私心人欲的遮蔽,因此,所謂修道之教,正是要人祛除此私欲之蔽,而臻入圣賢之境域。“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③胡廣、楊榮等:《四書大全校注》,周群等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6-147頁。故“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不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于須臾之頃也。”④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20頁。
朱子關于莫之于道的這一詮釋,對后世儒學影響深且遠,明代以其注疏為據的《四書大全》是數百年間士子的必讀書。而至清代,學者關于此節的看法仍不離其說,如劉沅(乾隆三十三年至咸豐五年,1768-1855;字止唐,號青陽居士)《中庸恒解》云:
道也者,四句一反一正,總以明“性外無道,道外無人”。……“莫顯”節,又申明不覩不聞必戒懼之故。不睹不聞,即隱微、即是獨。“隱”言其地,“微”言其幾。己所獨知,常人以為隱微,故子思特地醒之曰“莫見、莫顯”,而以為君子必慎于所獨,以其非隱非微也。“故”字從“莫見、莫顯”生來,語意相銜,次第不爽,若曰:“既常戒懼,于此尤加謹焉。則不睹不聞,又何地也?”不睹不聞,尚不足為隱微,則必其猶有可睹可聞之跡乎?⑤劉沅:《槐軒全書第1冊·四書恒解》,成都:巴蜀出版社,2006年,第56頁上。
止唐解《中庸》發揮了朱子所謂“性無不有,道無不在”的主張,提出“性外無道,道外無人”命題,認為道為天理,萬物得其偏,人得其全,天理賦之于人即為人性,若無此則不為人,由于世教而非人自身的緣故,人或得天理之一偏而不全,理即化顯明于隱微,道若一偏,理若隱晦,則不成其為大道,亦不成其至理,因此,人若要全其天賦之理,必以慎獨為要,以誠身為功,本諸人身,以人之常道而行,故其論莫亦如朱子之旨,以為莫見莫顯并非真正之莫,只是常人如是觀而已,明乎此,則君子必慎之。
朱子學此種詮釋,首先將隱微實質化,即指暗處、細事,由此出發一方面將道貫徹于動靜顯微之間,一方面又認為道心人心有別,故莫見莫顯,乃成為君子警省之塗轍。然而,無論是朱子還是止唐,均無法解釋的問題是,若隱微之地、獨居之時為慎獨,而公眾顯明之時為戒懼,則戒懼慎獨豈非二重功夫而彼此捍格?若慎獨為存養,戒懼為察識,雖是入身功夫,但何以分君子小人?小人在公眾顯明時亦非不敬畏者,此時難道其即為君子乎?顯然,對于儒者來說君子、小人之辨不能以此為分殊之鵠的。那么,所謂涵養察識之功,僅僅針對君子?儒者難道不是為了使社會上更多的人向善,使社會達致和諧嗎?于此,陽明學有不同的詮釋,他主張“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為《中庸》首章。”①王陽明:《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吳光等編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8頁。因此《中庸》的理解詮釋必須與《大學》相結合,至于立誠工夫則不可分離涵養察識,只能之一以貫之者:
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于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后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功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②王陽明:《王陽明全集(新編本)》,吳光等編校,第38頁。
陽明一方面認同朱子關于隱微為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的詮釋,一方面又認為不僅獨處之時,在與眾人相對之時亦是如此,隱微顯白無間,故誠意即是敬,慎獨即是涵養,儒者誠身以立其本,人所獨知處乃在于人心之昭明靈覺,而不是所謂的人之共識處。從一定意義上,陽明是將朱子詮釋中的道為一貫之道和唐代儒者無為實有的詮釋加以貫徹于心,因為人心才是真正隱微之處,因此,修道之教即是致此心之良知,立誠即是敬,由此誠敬之心立定根基變為真儒純儒,否則為支離之說。
陽明之后的儒者,一方面吸取了他關于誠的詮釋,一方面也對朱子學的詮釋加以重新辨析和解釋,如王夫之(萬歷四十七年至康熙三十一年,1619-1692;字而農、號船山)認為朱子釋庸為常于經典無據(實際上孔穎達即已如此詮釋),庸應為用,庸言庸行即為有用之言,有用之行,儒者處世其求道之所用,而非以出世之道為常,因此《中庸》乃是“圣人繼天理物,修之于上,治之于下”③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北京:中華書局,2011(1975)年,第59頁。者,而常人修習經典則為求中以為用,中為一,用則時而措之也。朱子之所以如此乃因“朱子生佛老方熾之后,充類而以佛老為無忌憚之小人,固無不可。乃佛老之妄,亦唯不識吾性之中而充之以為用,故其教亦淺鄙動俗,而終不能奇,則亦無事立平常之名,以樹吾道之壘。”④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第63頁。由此,王夫之認為“莫”并非他人不察識,亦非道貫隱微之際,所以他說:
若謂“顯”“見”在人,直載不上二“莫”字。即無論悠悠之心眼,雖有知人之鑒者,亦但因其人之素志而決之;若淵魚之察,固謂不祥,而能察者又幾人也?須是到下梢頭,皂白分明,方見十分“顯”“見”。螳螂捕蟬之殺機,聞而不覺者眾矣。小人閑居為不善,須無所不至,君子方解見其肺肝。不然,亦不可逆而億之。唯夫在己之自知者,則當念之已成,事之已起,只一頭趁著做去,直爾不覺;雖善惡之分明者未嘗即昧,為是君子故。而中間千條萬緒,盡有可以自恕之方,而不及初幾之明察者多矣,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然必存養之君子而始知者,則以庸人后念明于前念,而君子則初幾捷于后幾。其分量之不同,實有然者。知此,則程子之言,蓋斷章立義,以警小人之邪心,而非圣學之大義,益明矣。①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第75-76頁。
顯然,船山以其“隨見別白”之知和“觸心警悟”之覺對隱微顯白重加詮釋,即“惟性生情,情以顯性,故人心原以資道心之用”②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第83頁。,因此誠意本身即具有天道的意涵,而慎獨則是人對天道的涵養察識。“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自知自覺于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之胸中,即此見天理之流行,方動不昧,而性中不昧之真體,率之而道在焉”③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第75頁。,從體用的術語來說,人心乃是道心之用,道心乃是人心之體,所謂體即意味著它內涵于用之中,而用則只能是對體的彰顯和表達,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即在于其能體貼道心,并以道心的擴展充實為人生修省的基本功夫,故其能誠意而自知莫見莫顯之意,慎獨之學即為誠意而發,并不需要假手小人而諄諄誡勉,因為很明顯的君子誠意自能辨別,隱微中“其為理為欲,顯見在中,纖毫不昧,正可以施慎之之功。”④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第27頁。
從朱子、陽明、船山至止唐,對于莫的詮釋雖有其差異,但均指向了常道本身,即儒者生活世界中,內嵌于人心之道,不僅在于顯現的行為之中,更潛藏在隱微之幾。雖然諸家所述存在差異,但毫無例外的都認為,君子修道的重要性和道的統一性,道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觀的超越的道,而是與人密切相關的日常之道,這就意味著,儒者在其求道的過程中,必然要以自身身心出發而加以探求之,因此君子必慎其獨,所謂慎獨一方面是如朱子所說的存理去欲,一方面也是如陽明所說的精神命脈全在于此。
三、文本關聯及其他詮釋
關于莫的闡釋除了上述有無、常道的詮解之外,還有其他不同的論述,在《中庸》文本內,第十六章引《詩·大雅·抑之》“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度思。”并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⑤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27頁。可徵,在首章中所謂“莫見莫顯”其意在于誡勉君子自警,君子之道須敬慎以行。而末章又云“《詩》曰:‘衣錦尚炯’,惡其文之著也。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談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第40頁。此與首章之“莫見莫顯”相呼應,再次論述了顯微、著隱之間關乎君子小人之道的辨析,君子之道即是儒者之道,其道并非因為隱微之事之所無不顯白,不是因為君子認為人所不知而己獨知,而是君子之德在于篤恭敬慎,于細微處警醒,于獨知時克治,因為君子之道符合天之道,“上天之載,無聲無息”,也唯有如此方能至于“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誠。此誠即《大學》之誠意,“人所以能在獨的地方,省察其是否出于性,所以能一經省察便自然呈現出一標準,作一決斷,正是天命之性在發生作用,正可證明,性在一念之間,立可呈現。”①徐復觀:《中國人性史論先秦篇·從命到性:中庸的性命思想》,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113頁。我們注意到,后世儒者多有持此論說者,如劉向《說苑》一書多引《中庸》,其中卷十“敬慎”章云: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圣人重誡,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誡無垢,思無辱。”夫不誡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詩·小雅·小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②劉向、向宗魯校正:《說苑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40頁。
“莫見莫顯”成為學者引用名言警句,其意在說明圣人教訓乃是誡勉敬慎。隱微之事,常人或許不加留意而忽略之,但圣人告誡說,應審慎對待,保持警醒,則此為修身的路徑和根本。
宋代學者也有如是觀者,如明永樂間儒臣黃淮、楊士奇奉敕編《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圣學》載南宋戴栩(字文子,號浣川,嘉定元年(1208)進士)上疏:
所謂講學者,《中庸》《大學》其首也。……《中庸》之學,自謹獨入;《大學》之學,自致知入。……取二書而觀之,不以廣誦泛說為能,而以切問近思為貴。執中必如虞舜,繼志必如文武,克明俊德必同于堯,日新其德必同于湯。守之以誠,養之以敬,日夜去其所未合,而不忘其所已合,然后講學之功,有補矣。且夫《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經”即《大學》所以治國平天下者也。《大學》之“毋自欺”即《中庸》之“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書二而理一。……能自得師,則優游饜飫,皆是實誼;左右逢源,莫非妙用。惟當使此誠此敬,無一息不存耳。③黃淮、楊士奇:《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圣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24頁。
戴栩認為皇室講學雖然以《大學》《中庸》為據,但多流于無用之虛文,而不切實用。他認為《大學》《中庸》從內涵來講,均指明同樣的道理,即所謂誠敬之道,唯有守之以誠、養之以敬,方能周流不息。
元代儒者同樣有持此論點者,如明永樂間,儒者胡廣、楊榮等奉敕編《四書大全》為明代學者常備之書,其中《中庸章句大全》引元代儒者胡炳文(宋理宗淳祐十年至元惠宗元統元年,1250-1333;字仲虎,號云峰)之詮釋為:
天命謂性是道之體,修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于此獨提起“道也者”三字。“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卻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則幾已動而敬也。……皆不離乎敬而己,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才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遏之也。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厘之有差。④胡廣、楊榮等編、周群等校注:《四書大全校注·中庸章句大全上》,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47頁。
所謂敬就是誠,即是敬慎之意,也就是說在儒者的生活世界之中,身心的修養關鍵在于“修己以敬”,敬慎并不是一種消極的畏懼和嚴肅,不是一種離世的孤獨自我,而是身心情意的內在一致,是人在世的活力所在,它消弭了情與欲的張力,統合了理與知的向度,因此,方能保持、回歸人的本然,如此儒者所追求的好的生活與好的社會才有根本的保障。在此,所謂敬慎并不是要將隱微化為顯白,或者強調“沒有比在隱暗的處所更容易表現的了,沒有比在細微的事情上更容易顯露的了”①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773頁。,也不是要從中找尋人生的根底或答案,而是對這無窮的隱蔽處加以玩味,而這無窮的玩味本身就給我們以美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滿足,因為隱蔽的東西對顯現是一種許諾或預示②張世英:《新哲學講演錄(2版)》,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30頁。,如此方能致其中,行其庸,方能在“喜怒哀樂”之中體味“未發”的意蘊生動,否則往往流入假道學或偽飾而不自知。
此敬慎之說,在儒者思想中一直存有,如今人多以為是屬于子思學派的郭店楚墓竹簡中,《成之聞之》篇云:“君子之于教也,其導民也不浸,則其淳也弗深矣。是故,亡其身而存乎其辭,雖厚其命,民弗從之。”其后又引《尚書》逸文《君奭》云:“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為恒。行不信則命不從,信不著則言不樂。民不從上之命,不信其言,而能念德者,未之有也。故君子之蒞民也,身服善以先之,敬慎以守之,其所在者入矣,民孰弗從?行于中,發于色,其誠也固矣,民孰弗信,是以上之恒務,在信于眾。”③李零:《郭店楚簡校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21、122頁。此篇與《中庸》之旨相同,如果從信與著的角度來理解君子之言辭行為,則君子慎其獨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出來。身服善以先,敬慎以守,均是為彰顯君子之德性,從而不言而信、不動而敬。在此意義上,君子之慎獨絕非是孤立自我的成德之舉,而是尤其社會性的追求,這更加符合儒者在世的學說,對此唐文治(1865-1957;字穎侯、號蔚芝、茹經)《中庸大義》有細致疏解,其云:
《周易大義》“一消一息”,消者,正所以為息也,故隱者正所以為見也,微者正所以為顯也。周子曰:“幾善惡。”又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又曰:“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蓋圣人者,誠而神者也。君子者,善審幾者也。幾者,當念慮初起之時;善者,則擴而充之;惡者,則遏而絕之。故《易傳》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中庸》言率性之道以至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其功皆本于慎獨。《大學》言誠意正心,以至修齊治平,其功亦皆本于慎獨。未有不慎獨而能修己者也;未有不慎獨而能治人者也。“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此曾子相傳之學說也,自后人破“慎獨”二字以為空虛,而詐偽無忌憚之小人遂盈天下。夫“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此不足以欺人也,自欺而已。且不僅自欺也,欺天而已。欺天者不若于道,則天絕之矣。吾愿后世君子,身體力行,發明慎獨之學說,其于今日世界或能有所挽救乎。(唐文治《中庸大義》,民國十三年吳江施氏醒園刊本)
唐文治感于世變,認為“人人有配天之責,而卒至于違天悖天棄天絕天,子思憫焉,于是發明天之道、人之道。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故其經解多凸顯者儒者的世道關懷,就本節而言,一方面以《易傳》《大學》諸經對《中庸》話語加以闡明,一方面亦期待君子身體力行而發明之,庶幾人道不至于廢棄也。其所特揭《中庸》敬慎之道,于今仍有啟發,即經典本身作為文本或許遠離我們當下的生活世界,若執迂闊之見、陳腐之說,不僅不能明經之真義,亦不為儒者之道所容。于述勝師解本節云:“君子所以為君子,即在于他以至隱至微之地為至顯至明之場,惟精惟一,畢誠畢敬。一念之動,善則擴充,惡則克治。自‘道不可須臾離’至‘君子慎其獨’,所言皆敬畏之心、敬謹之功。然‘戒慎恐懼’,乃承‘不可須臾離’而來,強調的是不息其功;‘慎獨’乃承‘莫見’‘莫顯’而來,敬謹于其幾微之際,以收防微杜漸之功。”其用意正與前儒相印者。
在思孟學說中,孟子被認為繼承了子思的學統,我們從“莫見莫顯”一語亦可找到線索,如《孟子·盡心上》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對后一章,朱子注疏云:“此章言萬物之理具于吾身,體而實之,則道在我而樂有余;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①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第328頁。其實若我們從《中庸》出發來予以詮釋的話,則前一章可以理解為,君子之道,費而隱,眾人不著察其隱微,故終身不知儒者之道;后一章可理解為,君子之道,立于誠敬,君子知其道行其道,故樂故仁。儒學語境中的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端賴其誠敬不息。其之所以敬慎,并非因外在的公之于眾的顯白和外在的壓力,也不是對于具體事件或特殊事物而引發其戒慎恐懼,恰恰相反,他所注重的和所警惕的乃是內在自我的隱微,正是對這一隱微之幾的觸發和把捉,使得儒者感通天人之際,以此而日新其德,以此而成己成物。《中庸》所闡述的君子之道,是“人人可以實踐,人人應當實踐的行為生活,即是中庸之道,即是孔子所要建立的人道。”②徐復觀:《中國人性史論先秦篇·從命到性:中庸的性命思想》,第103頁。而首章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即不可能是論說隱微無不顯見,而是提醒儒者注意到:第一、若將隱微實質化,如朱子學的詮釋,則隱微之地之所之時乃是至關重要者,故慎獨為慎其獨居獨處。第二、若將隱微視為對人性彰顯和道德之幾,如陽明學的詮釋,則慎獨為無時無地的謹慎誠敬。兩種詮釋各有其依據,前者重在文本的字義詮釋,使之成為邏輯通貫、文義顯明的典范;后者重在對文本意義的詮釋,使之成為義理流暢、富于生機的典范。對于前者,大風起于青萍之末,謹小慎微,潛修精研,君子可期;對于后者,道貫乎內外動靜,遍包流行,率性修道,誠敬不息,君子可至。
總之,透過“莫見莫顯”一語,我們可以看到,經典文本的詮釋不能離開具體的語境,同時也需考察文本之間的關聯,方能言之有理有據。經典文本的詮釋必有其內在的范式,并不是資料的疊加和豐富就能形成新的理解,也不能由此產生新的典范。每一新的詮釋范式的成立都與詮釋者所依據的理論有莫大關系,同時也與他們的獨特體驗有著密切關聯,正是在歷代大儒的反復注疏之中,經典成為活著的傳統和現實的典范,而不僅僅是一只供學術研討的故物。
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先秦儒家意義——感通的教化哲學研究”(15AZX009);北京師范大學“顧明遠教育研究發展基金”2015-2016年度資助(2015009)。
向輝(1980-),男,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博士研究生,中國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北京100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