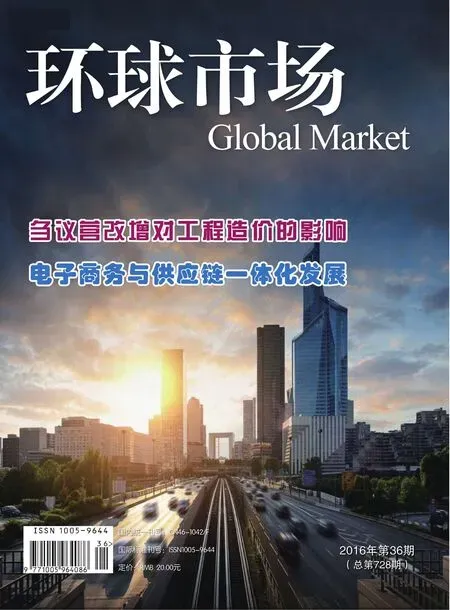從國家自主性視角論中國對現代化轉型社會的國家治理
葛文博
中直機關
從國家自主性視角論中國對現代化轉型社會的國家治理
葛文博
中直機關
中國社會目前正處于深刻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國家對社會的治理暴露出兩大主要問題:一是市場經濟導致社會物質、精神淪喪及貧富分化矛盾加劇,二是多元思想的涌現提高管控難度。本文在對此兩大社會治理難題及其誘因進行詳細論述后,從國家自主性的視角出發論證其背后的經濟與權力因素。通過對國家自主性的兩個剖面即“基礎性權力”和“嵌入性自主”的探討,論證通過“依法治國”和“權力下放”分別增強這兩大國家能力是國家針對性地解決以上兩種社會治理難題的有效路徑。
社會現代化轉型;國家治理;國家自主性;依法治國;權力下放
一、引言
“現代性孕育穩定,現代化過程卻滋生動亂”是國際政治經濟學家亨廷頓的著名論斷。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正在進行深刻的現代化轉型,該過程中暴露出各種嚴重的國家治理問題,這些問題究竟是什么,有什么內在原因,又當如何解決,一直是學界的研究重點。學界對此早有批評類研究,主要從政治學角度出發,論述了中國制度建設的滯后和匱乏,政治和結構改革的遲滯,認為社會矛盾激化,社會關系趨緊,制度恐有崩壞之嫌,并為此提出了一系列對策建議。然而,僅從政治角度出發會導致對經濟因素討論的不足。本文擬從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國家自主性角度出發,突出該學科的經濟與權力元素及關系,通過厘清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國家治理及國家自主性的定義及相互關系,揭示現階段社會的治理困境,最終從國家自主性的“基礎性權力”和“嵌入性自主”兩個剖面入手論述“依法治國”和“權力下放”是中國改進對現代化轉型社會治理的有效路徑。
二、社會現代化轉型危機、國家治理困境與國家自主性的定義
社會現代化指人類使用科學技術改造物質和精神條件的進程。社會現代化轉型危機是指在這一改造過程中,經濟和社會同時具備兩種特征,一是經濟和社會關系發生重大結構性變遷而產生嚴重矛盾和沖突;二是這些矛盾和沖突需要國家干預,不能自我矯正。其表現為歷史性問題和新生問題并存,具體表現為價值觀的多元化、利益分配的不公平、群體性事件的增多、社會秩序的混亂等。
國家治理困境指國家在一段時期內缺乏有效控制和管理社會矛盾及沖突的手段,從而導致統治能力削弱的狀態。具體表現為國家決策權威和能力出現系統性危機,功能失效或僵化,治理主體必須主動或被動變革體制,轉變治理方法,才能擺脫治理危機。
國家自主性,斯考切波將其看做是擁有領土和人民控制權的組織。它能夠定制和追逐自身目標,且不受社會集團、階級或整個社會的利益影響。其實現要素有四點,一是國家擁有獨立的法人主體資格,充分代表公共利益,可以無視社會利益偏好追求自身目標;二是國家自主性擁有制度化保障,專門的人員掌握有限國家權力,不受特殊利益影響;三是國家自主性具備相應的國家能力,保證國家通過社會順利執行其政策。
三、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國家治理難題及其誘因
(一)市場經濟激化人民內部矛盾
社會現代化轉型突出公民權利,調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激發社會活力。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市場經濟成為資源達到最佳配置的不二途徑。但在社會層面上,唯利是圖的市場帶來了各種新問題。一是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淪喪。市場經濟刺激各種欲望,金錢儼然成為衡量一切的標尺,導致道德淪喪,引發民眾恐慌。社會奉行“叢林法則”,很多人為了利益不擇手段,假冒偽劣、有毒產品充斥市場,人際關系、商業關系不斷惡化。“公地悲劇”不斷上演,自然資源遭到破壞性利用,有限的資源遭到破壞導致枯竭,霧霾等自然災害難以治理。二是市場經濟進一步拉大資本和勞動的收益率,加之社會再分配措施存在滯后和短板,催化加速財富分化的“馬太效應”,催生財富新貴,促使權力尋租。這一現象造成了大范圍利益的剝奪、貧富分化的加劇,導致社會不斷分化:大批底層民眾如農民、打工者生活困苦,而不少“富二代”生活糜爛;百姓辦事難,而資本卻與個別權力部門沆瀣一氣,權錢勾結,公權力私有化問題突出;社會拜金主義思想和“仇富”、“仇官”戾氣同時泛濫。
這些深層次的經濟問題最終以群體性事件頻頻爆發顯現出來。近年來,此類事件比比皆是,且更多呈現為非直接利益攸關者的群體泄憤性行為,如“甕安事件”、“漳州PX事件”等。此類事件表面上看體現了部分群眾對利益受損方的同情或對政府處置方式的不滿,但從深層次看卻體現了群眾對地方政府施政偏所造成的的社會利益分配不公、官員腐敗、環境污染后果由底層群眾承擔等現象的不滿。此類事件由于體現了對體制的根本性反對,因此難以很好地解決,往常通過經濟利益直接補償的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盡管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強調制度的作用,但制度設計的不健全和滯后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現象已經嚴重影響人民的切身利益及其對政府治理的信任。
(二)社會訴求多元提高政府管控難度
社會轉型在突出公民權利的另一方面體現為合理利益訴求的多元化。事實上,各方利益達成高度一致是不可能的。可是,當今社會出現一種片面要求民主的思潮,但這種民主是不是真正的民主,不能體現民主的自由、平等價值觀及“在尊重多數人意愿的基礎少,保護少數群體和個人的基本權利”的真正價值和含義,相反,民主概念發生扭曲,帶來巨大的社會分化,社會“碎片化”進一步加劇。民主內涵遭到歪曲,變成自私自利、放任失控及平均主義的代名詞,時刻要求自主,追求自我利益,個體間相互斗爭、傾軋,無視差異性追求絕對平等。這種現象導致民眾心態失衡,打著民主的旗號滿足個人欲望。社會矛盾激化、沖突加劇、穩定性削弱。
面對社會愈加多元的訴求,西方部分所謂民主國家應對方法拙劣,政治體制不穩。一是政黨林立,如意大利等國出現一百余個政黨,組閣難,執政難,政府換屆頻繁;二是政客大打“民主牌”,實則追求個人政治利益,為滿足最大范圍的民眾訴求而推出不切實際的政治綱領和政策許諾,這集中體現在許多西方國家各級別政治選舉中及施政過程中,政客選前和當選后兩幅嘴臉,政治成為光說不做的政治精英游戲;貿然推出的政策打破政策連貫性,損害國家長期利益,希臘、意大利等國家深陷債務危機、政局頻繁更迭的就是典型代表。有些落后國家族群對立不可調和,乃至爆發嚴重內亂、內戰等。
我國面對社會現代化轉型的社會治理手段優缺點都較為明顯。從中央層面來說,現行的政黨體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這種體制優點是,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為政策施行的長期連貫性和切實落地保駕護航,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能在國家層面反映部分階層、團體的不同利益訴求,促使政策更加民主、科學。但是,它也暴露出對新形勢的應對不足的問題:由于人員、組織相對固定,無法顧及或跟上更大范圍、更多元的社會訴求,代表現象就是社會各類團體的增多,通過各類新媒體進行的言論傳播爆炸性增長,而政府應對工具則顯得捉襟見肘。從地方層面來說,部分地方政府和官員出于政績考慮,往往只注重經濟利益,忽視部分民眾需求。其對待民眾訴求的激烈反對,方法也過于簡單粗暴,或者通過強力手段硬推、打壓,事態惡化乃至壓不住時又一般選擇無條件退讓、妥協和補償。
四、強化國家自主性為中國現代化轉型社會治理提供解決之道
(一)通過依法治國強化國家基礎性權力解決市場經濟帶來的矛盾
邁克爾曼曾指出,“國家權力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專制權力,另一個是基礎性權力。所謂專制權力是指國家充分自主行動,且不與社會集團進行例行制度化討價還價的權力。而國家的基礎性權力又被稱為國家能力,是指國家通過對市民社會的滲透在其統治范圍內貫徹政策的能力”。我們平時所說的“將權力關在籠子里”,指代對象是前者,而后者作為保證國家最高權威、維護國家政策施行的必要前提,卻是需要保護和強化的。市場經濟導致激烈的社會矛盾,反映出人們對現行市場經濟中負面因素的巨大不滿,迫切地需要國家作為最高權威出面整飭市場,保證已有的政令順利施行,主導市場規范化運行,對利益進行公平分配,這說明增強國家基礎性權力為針對性解決該治理難題提供了切入點。
增強國家基礎性權力最好的做法是“依法治國”。從定義上看,“依法治國”充分使用遵循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避免將個人或集團的意志作為國家治理依據;要求國家的各方面活動均須嚴格按照法律進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左右。它既能避免各種狹隘利益斗爭,又由于結構性理性和結構性無知而具有一定調試性。這一定義充分匹配國家基礎性權力的要求,是從上至下,從國家向社會的滲透和規范,體現了國家意志,為國家施政提供有力工具。針對社會急需國家和政府提供一個統一“標尺”,“依法治國”以法律及其實施的相對客觀性和固定性成為這一“標尺”的不二選擇,其能針對性地做到:一是能衡量產品優劣,懲戒失德商家,保障市場的良性運轉;二是能衡量人民利益所得并公平分配。“依法治國”就是要求用法制替代人治,用明規則替代潛規則,增加透明度,讓經濟利益分配在陽光下進行,擠壓“關鍵少數”、利益集團和權力尋租的空間。
古人云“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新中國成立以來自1954年起先后推出并多次修改憲法,以法的形式確立了我國的基本制度和歷史任務。1997年黨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和國家的基本方略,十八大以來黨又多次重申并切實踐行“依法治國”的核心精神,推動社會主義國家的建設逐步走向法制正軌,促進法治觀念深入人心,構建社會和諧繁榮。這些都說明我國擁有“依法治國”的思想傳統和推動其進一步貫徹落實的政治制度,這為該解決辦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通過權力下放增強國家嵌入性自主回應社會多元訴求
彼得·埃文斯拓展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鑲嵌”概念,提出“嵌入性自主”,指出“政府官員要通過為社區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塑造其社區成員的身份,并以此獲得社區居民中的高度的認可。”社會訴求的多元化說明人民需要國家和政府增加渠道傾聽社會不同聲音,并及時做出回應,這與“嵌入性自主”的內在思想相吻合,因此增強國家“嵌入性自主”為針對性地解決社會多元訴求問題提供了切入角度。
增強國家嵌入性自主的最好做法是“權力下放”。從定義上看,“權力下放”主要指要扭轉權力在政、經、文、娛等諸多涉及社會治理領域橫向上的過度集中及相關領域下級依附上級的縱向的過度集中的局面,賦予相關單位和個體更多權力和自主性。這一定義符合“嵌入性自主”的要求,增加了國家政府同社會的互動與相互了解,為二者加強連接提供了有力工具。“權力下放”的具體做法應為:一是在原有權力框架內在橫向擴展權力運作范圍,原來都是個別核心機關或黨政一把手等對社會各事務一把抓,應逐漸賦予各直接主管部門更大自主權;二是突破原有權力框架,在縱向上深化權力運作水平,充分做到“信任群眾”、“服務群眾”,賦予社會合法團體更多自主性,讓其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及時向政府反映并幫助后者解決社會問題。通過橫向與縱向的“權力下放”,信息傳遞及權力運作效率將得到顯著提高,有利于社會問題的及時解決。
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家政權逐漸下滲,基本能做到“政權下鄉”、“政策下鄉”和“服務下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新時期,國家培育和挖掘社會的自主性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十八大以來,中央進一步落實機構改革、簡政放權,并相繼推出《非政府組織管理法》等法律,為加強“權力下放”提供了制度保障,增強了該方法繼續推行的可行性。
五、結論
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不斷深化,這一過程中爆發的種種社會矛盾給國家對社會的治理造成巨大挑戰。這一困境以前有,以后也將長期存在并愈發突出,研究和解決這一問題已變得刻不容緩。應當認識到,這一問題不單單是政治問題,更要考慮到經濟與權力因素,加之國家是社會治理的主體,研究應從國家入手。考慮到這兩個因素,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國家自主性角度入手即為順理成章。針對具體的市場經濟帶來的物質與精神困境和多元訴求的大量涌現這兩大難題,我們在國家自主性的諸多定義中找到相對應的兩個剖面,即增強“國家基礎性能力”和“國家嵌入性自主”。在論證過程中我們發現,“依法治國”與“權力下放”這兩種具體方法能夠同國家自主性的這兩個剖面定義以及相對應的問題訴求吻合,成為解決國家治理難題的有效路徑。本文僅論述社會治理中最為突出的兩個問題,對社會治理的諸多其他問題并未涉及;論述工具主要采用國家自主性的兩個剖面,雖可與問題一一對應,但不排除其他剖面的可解釋性和相對應做法的可行性,因此文章全面性仍有提升空間。
[1]徐湘林:《轉型危機與國家治理:中圍的經驗》,《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0年第5期,第1頁到第14頁。
[2]王賜江:《群體性事件的類型化及發展趨向》,《長江論壇》,2010年第4期,第47頁到第53頁。
[3]周平:《對民族國家的再認識》,《政治學研究》,2009年第4期。第89頁到第99頁。
[4][美]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王冠華譯,第1版第3次,北京,生活·湊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年,第38頁。
葛文博(1989~),男,錫伯族,新疆人,本科學歷,中直機關,副主任科員,研究方向:國際政治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