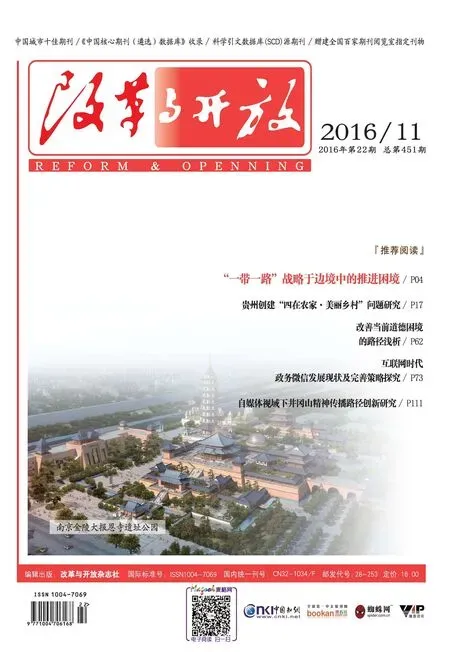談“理性選擇”兼議打造微觀經(jīng)濟(jì)主體釋放活力的舞臺(tái)
楊海波 許彩慧
談“理性選擇”兼議打造微觀經(jīng)濟(jì)主體釋放活力的舞臺(tái)
楊海波 許彩慧
我們每天都在面臨選擇,如何選擇,小則關(guān)乎個(gè)人利益最大化或者損失最小化,大則關(guān)系到國(guó)家繁榮與未來(lái)走向,所以“選擇”必須是“理性選擇”。鑒于“選擇”如此重要,我們就“選擇”問(wèn)題做一番理論梳理以及進(jìn)一步探討,以便個(gè)人、制度供給者更有理性地去選擇。改革開(kāi)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究其制度原因無(wú)非是通過(guò)宏觀層面不斷改革釋放出微觀經(jīng)濟(jì)主體的活力,從而滿(mǎn)足人們?nèi)找嬖鲩L(zhǎng)的物質(zhì)文化需求,這是改革設(shè)計(jì)者們的“理性選擇”。本文從“理性”出發(fā),探索打造能讓微觀經(jīng)濟(jì)主體釋放活力的舉措,讓“為人民服務(wù)”真正成為“理性選擇”。
理性選擇;微觀經(jīng)濟(jì)主體;釋放活力
一、問(wèn)題提出:從日常生活看“理性選擇”
如今寺廟香火旺盛,為搶頭香不惜重金的案例屢見(jiàn)不鮮。有人認(rèn)為這是國(guó)家經(jīng)濟(jì)繁榮的體現(xiàn),亦有人認(rèn)為這是封建愚昧的表現(xiàn)。假使我們用經(jīng)濟(jì)學(xué)思維來(lái)思考,這符合理性人選擇的原理。假設(shè)進(jìn)獻(xiàn)香火者實(shí)現(xiàn)愿望后的收益是W,此事件成功的概率是p,同時(shí)香火費(fèi)用是P,對(duì)于香火進(jìn)獻(xiàn)者來(lái)說(shuō)只要滿(mǎn)足p*W≥P就可以,出價(jià)(P)高是因?yàn)槠谕找妫╬*W)高。
統(tǒng)計(jì)學(xué)有一個(gè)經(jīng)驗(yàn)法則,當(dāng)樣本大于或者等于30時(shí),就可以運(yùn)用統(tǒng)計(jì)相關(guān)規(guī)律。考察某一事件,大部分都做同樣選擇,我們可以說(shuō)就是理性選擇。作為政策制定者和執(zhí)行者,更要有理性思維,用理性視角去觀察社會(huì)現(xiàn)象,只有這樣才不會(huì)被“道德綁架”。尊重人們的創(chuàng)新精神,做到“從群眾中來(lái),到群眾中去”,制定政策才會(huì)接地氣,執(zhí)行政策才會(huì)落地。
二、理論梳理:有限理性、自由選擇與理性選擇
我們要從理解概念出發(fā),探尋“選擇”的不同層次的含義,從而理解“理性選擇”的重要性。
理性人假設(shè)意味著作為經(jīng)濟(jì)決策的主體是充滿(mǎn)理性的,既不會(huì)感情用事,也不會(huì)盲從,是精于判斷和計(jì)算的,其行為是理性、符合邏輯的。在經(jīng)濟(jì)實(shí)踐中,經(jīng)濟(jì)主體追求的是自身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這就是理性行為。理性人的特點(diǎn)一是自利,二是完全理性。越嚴(yán)苛的假設(shè),理論上越完美,且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解釋力往往就越不夠。“理性人”近乎是全能、全知、全在的上帝,為了讓假設(shè)符合現(xiàn)實(shí),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設(shè)——有限理性是指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間的在一定限制下的理性。但是半個(gè)多世紀(jì)以來(lái),理論界對(duì)什么是有限理性并沒(méi)有定論,理論很難建立在有彈性的概念之上,“有限理性”就是一個(gè)有彈性的概念。米爾頓?弗里德曼在其名著《自由選擇》中提出了“自由選擇”理論—— 他強(qiáng)烈反對(duì)政府過(guò)分干預(yù)市場(chǎng),認(rèn)為只有在保障自由的前提下,政府才可以通過(guò)市場(chǎng)與價(jià)格制度、通過(guò)控制貨幣數(shù)量進(jìn)行最低限度的干預(yù)。國(guó)家對(duì)經(jīng)濟(jì)的過(guò)度干預(yù)弊多于利,政府職能要受到限制,同時(shí)政府有責(zé)任在其有限的范圍內(nèi)發(fā)揮其作用,以保證經(jīng)濟(jì)健康運(yùn)行。我們對(duì)“自由選擇”之于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理解是“在法律之下的自由交易”。利用盡可能充分的信息、智慧進(jìn)行判斷,進(jìn)而決策。同時(shí)還要有一套反饋機(jī)制,為今后的選擇提供經(jīng)驗(yàn)與參考。
三、回到斯密:讓市場(chǎng)在資源配置中發(fā)揮決定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huì)關(guān)于《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wèn)題的決定》報(bào)告中指出,“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diǎn),核心問(wèn)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chǎng)的關(guān)系,使市場(chǎng)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fā)揮政府作用”。這一表述即明確了未來(lái)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diǎn),更對(duì)市場(chǎng)的地位和作用進(jìn)行了重新定位,是市場(chǎng)與政府關(guān)系認(rèn)識(shí)上的一次重大理論突破。①
市場(chǎng)起決定性作用不僅僅是一個(gè)提法的改變,而且還是強(qiáng)調(diào)在經(jīng)濟(jì)生活領(lǐng)域?qū)嵭惺袌?chǎng)主導(dǎo)下政府的有效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導(dǎo)下市場(chǎng)的有限作用。從“基礎(chǔ)性作用”到“決定性作用”的改變,體現(xiàn)了中央以更大的決心和魄力推動(dòng)政府向市場(chǎng)放權(quán),理順政府市場(chǎng)關(guān)系,推動(dòng)市場(chǎng)化改革的新突破。改革開(kāi)放以后,我們每次改革都是以釋放微觀經(jīng)濟(jì)主體的活力為落腳點(diǎn),是“看不見(jiàn)”的市場(chǎng)之手與“看得見(jiàn)”的政府之手不斷博弈的過(guò)程。同時(shí),我們對(duì)斯密講的“看不見(jiàn)之手”和凱恩斯提出的“看得見(jiàn)之手”的理解也是一個(gè)逐漸深刻的認(rèn)識(shí)過(guò)程。確定市場(chǎng)的決定性地位,并不是說(shuō)什么都交給市場(chǎng),市場(chǎng)也有失靈的時(shí)候,市場(chǎng)做不了、做不好的地方交給政府做。
四、政策建議:打造讓微觀主體充分釋放活力的舞臺(tái)
打造能讓微觀主體釋放活力的舞臺(tái),這需要作為制度供給者的政府有所作為,為此,我們從政府與國(guó)企、民營(yíng)、個(gè)人創(chuàng)新以及政策最終執(zhí)行者四個(gè)方面提出政策建議:
1.減少權(quán)力干預(yù):簡(jiǎn)政放權(quán)、國(guó)企退出一般性競(jìng)爭(zhēng)領(lǐng)域
公權(quán)力對(duì)經(jīng)濟(jì)干預(yù)達(dá)到登峰造極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對(duì)經(jīng)濟(jì)全領(lǐng)域、全方位的控制。改革開(kāi)放實(shí)際上就是不斷放權(quán)的過(guò)程。但我們現(xiàn)有的管理體制還跟不上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步伐,甚至還掣肘市場(chǎng)體制。本屆政府開(kāi)門(mén)第一件大事是2014年國(guó)務(wù)院第一次常務(wù)會(huì)議,其主題就是“簡(jiǎn)政放權(quán)”,承諾取消、下放現(xiàn)有1700多項(xiàng)行政審批權(quán)。簡(jiǎn)政放權(quán)能理順政府與市場(chǎng)的關(guān)系、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guān)系,各級(jí)行政中心辦理業(yè)務(wù)的“窗口”就是“簡(jiǎn)政放權(quán)”的明證。“簡(jiǎn)政放權(quán)”是政府對(duì)自身的更高要求,更體現(xiàn)對(duì)人民負(fù)責(zé)的態(tài)度。同時(shí)“簡(jiǎn)政放權(quán)”不是簡(jiǎn)單的放權(quán)了事,而是政府要在簡(jiǎn)政放權(quán)后更能有作為。政府與市場(chǎng)的邊界問(wèn)題將會(huì)是進(jìn)一步“簡(jiǎn)政放權(quán)”的議題。
國(guó)有企業(yè)脫胎于政府,是政府職能的延伸,因此我們不能脫離這個(gè)實(shí)際來(lái)談國(guó)企改革。對(duì)國(guó)企進(jìn)行科學(xué)分類(lèi),進(jìn)而區(qū)別管理,國(guó)企管理部門(mén)權(quán)責(zé)由“管資產(chǎn)”轉(zhuǎn)向“管資本”。國(guó)企應(yīng)該全面退出一般性競(jìng)爭(zhēng)性行業(yè)(事關(guān)國(guó)計(jì)民生除外),2010年中央要求78家不以房地產(chǎn)為主業(yè)的央企在完成企業(yè)自有土地開(kāi)發(fā)和已實(shí)施項(xiàng)目等階段性工作后,退出房地產(chǎn)業(yè)務(wù)。國(guó)企退出一般競(jìng)爭(zhēng)性領(lǐng)域,并不代表國(guó)企不參與競(jìng)爭(zhēng),甚至于其還要參與到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中去。再者,對(duì)于公益性國(guó)企的虧損應(yīng)予以補(bǔ)貼,參與到國(guó)內(nèi)競(jìng)爭(zhēng)的企業(yè)應(yīng)該是微利原則,比如四大國(guó)有銀行、“三桶油”、三大移動(dòng)運(yùn)營(yíng)商等。
2.減少政策依賴(lài)型民營(yíng)企業(yè):減稅費(fèi),降低交易成本
2010年七大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的推出,造就了一大堆迅速崛起的明星企業(yè),賽維、尚德就是代表,但這些靠政策、補(bǔ)貼生存的企業(yè)無(wú)不證明著“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規(guī)律。里根采納了拉弗意見(jiàn),實(shí)施減稅政策,史稱(chēng)“里根經(jīng)濟(jì)學(xué)”,造就了美國(guó)20年的經(jīng)濟(jì)繁榮、孕育出克林頓時(shí)代的“新經(jīng)濟(jì)革命”。拉弗曲線也預(yù)示著涵養(yǎng)稅源的重要性。補(bǔ)貼的目的是實(shí)現(xiàn)某種特定產(chǎn)業(yè)政策,而產(chǎn)業(yè)政策是政府制定實(shí)施的,事實(shí)證明,制定產(chǎn)業(yè)政策尤其是新型產(chǎn)業(yè)、高科技產(chǎn)業(yè)經(jīng)常會(huì)事與愿違,市場(chǎng)是瞬息萬(wàn)變的,很難預(yù)測(cè)具體行業(yè)的發(fā)展。產(chǎn)業(yè)政策方面做得最好的日本也意識(shí)到,產(chǎn)業(yè)政策制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業(yè)創(chuàng)造力。
當(dāng)然,雖然我們國(guó)家還處在工業(yè)化中期,肯定還需要產(chǎn)業(yè)政策的支持,但是我們更應(yīng)該看到減稅費(fèi)的重大作用:一是降低了企業(yè)的交易成本,使得企業(yè)資本金充裕;二是寬松的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可以使得企業(yè)安靜下來(lái)生產(chǎn),而不是將資本大量轉(zhuǎn)移到虛擬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2003年以來(lái)的房地產(chǎn)熱就是明證。制造業(yè)始終是我國(guó)最重要的經(jīng)濟(jì)命脈之一,當(dāng)前制造業(yè)困難的原因很多,綜合起來(lái)有兩點(diǎn):一是稅費(fèi)等交易成本過(guò)高,從當(dāng)前情況看,中央政府加強(qiáng)了對(duì)非稅收入的規(guī)范與管理,但某些地方政府為完成增收目標(biāo),卻在稅收不同程度下降的同時(shí),又出現(xiàn)“稅不足費(fèi)來(lái)補(bǔ)”的現(xiàn)象,企業(yè)負(fù)擔(dān)沒(méi)有明顯減輕;二是房地產(chǎn)嚴(yán)重?cái)D壓了制造業(yè)利潤(rùn),導(dǎo)致資源配置方向變異,最終侵蝕實(shí)體經(jīng)濟(jì)發(fā)展基礎(chǔ),房地產(chǎn)的利潤(rùn)高達(dá)75%到100%,而實(shí)體經(jīng)濟(jì)只有5%到10%,這吸引企業(yè)往房地產(chǎn)轉(zhuǎn)移,同時(shí)使銀行的錢(qián)更多地流向房地產(chǎn)。
3.呵護(hù)創(chuàng)新的花朵:需有“星探”“狗仔隊(duì)”精神
創(chuàng)新是人們?cè)谡J(rèn)識(shí)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guò)程中對(duì)原有理論、觀點(diǎn)的突破和對(duì)過(guò)去實(shí)踐的超越。熊彼特認(rèn)為創(chuàng)新包含五個(gè)方面:新的產(chǎn)品、新的生產(chǎn)方法、新的銷(xiāo)售市場(chǎng)、新的原料供應(yīng)來(lái)源、新的組織。創(chuàng)新的實(shí)現(xiàn)離不開(kāi)合理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對(duì)創(chuàng)新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之所以發(fā)生在英國(guó),原因是英國(guó)完成了一整套體制創(chuàng)新,尤其是金融創(chuàng)新。工業(yè)革命眾多發(fā)明的原創(chuàng)地在意大利,但因?yàn)橛?guó)有配套的金融制度,使得發(fā)明創(chuàng)造得以迅速規(guī)模化、產(chǎn)業(yè)化。而對(duì)創(chuàng)新這璀璨花朵的發(fā)現(xiàn)與培育離不開(kāi)兩種力量:一是金融家(投資家),金融資本是最逐利的,只要能創(chuàng)造利潤(rùn),它幾乎無(wú)孔不入,反過(guò)來(lái)正是因?yàn)樗麄冎鹄颐翡J的眼光,驅(qū)使他們?nèi)ふ覄?chuàng)新型人才;二是創(chuàng)新體系的建立,創(chuàng)新體系是將已經(jīng)含苞的創(chuàng)新孕育成鮮艷奪目的花朵,從成長(zhǎng)到成熟、直至轉(zhuǎn)型升級(jí)全方位看護(hù)。假如我們的聰明智慧都能極大地發(fā)揮出來(lái)、將智慧資源資本化,民族之崛起、國(guó)家之強(qiáng)盛指日可待。創(chuàng)新精神、創(chuàng)造力是人類(lèi)智慧頂端上的花朵,它引領(lǐng)人類(lèi)從黑暗走向光明、從愚昧走向文明、從低級(jí)走向高級(jí)。
4.讓“為人民服務(wù)”成為政策最終執(zhí)行者的“理性選擇”:政策落地、干群和諧
政策,即政令,是黨和國(guó)家造福于民、造福于社會(huì)的重要方法,政令暢通,才有政通人和。黨和國(guó)家的政策服務(wù)面廣、涉及對(duì)象多,考慮的是最廣大人民的利益。然而,某些政策受到限制而影響落實(shí),嚴(yán)重影響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眾不能共享發(fā)展成果。為此,在政策“好聽(tīng)”的同時(shí),更需確保政策“落地”。而在如何讓政策落地方面,政策最終執(zhí)行者起著關(guān)鍵作用,所以加強(qiáng)對(duì)政策最終執(zhí)行者的管理,讓“為人民服務(wù)”成為他們的理性選擇。
對(duì)政策最終執(zhí)行者予以充分鼓勵(lì)的目的,是讓“為人民服務(wù)”成為理性選擇,而不是一種口號(hào),讓惠民政策落地生根。如何進(jìn)行激勵(lì),可以從兩個(gè)方面考慮:一方面讓待遇與工齡、業(yè)績(jī)雙掛鉤。政策最終執(zhí)行者大部分在基層,而基層工作者上升的空間很小,而待遇是與級(jí)別職務(wù)掛鉤的,近些年基層公務(wù)員待遇有所改善,未來(lái)鄉(xiāng)鎮(zhèn)一級(jí)資歷老、能力強(qiáng)的非領(lǐng)導(dǎo)工作人員可以享受副處級(jí)待遇(畢竟還是少數(shù))。這還不是一種穩(wěn)定預(yù)期,對(duì)于基層工作人員只要有穩(wěn)定預(yù)期,就會(huì)迸發(fā)出更大的工作活力與熱情。讓待遇與工齡、業(yè)績(jī)雙掛鉤,能給基層工作者帶來(lái)穩(wěn)定預(yù)期,避免只講資歷的現(xiàn)象造成基層工作人浮于事;另一方面加強(qiáng)對(duì)基層工作者的黨性教育。基層就是一線,一線面臨著最直接的現(xiàn)實(shí)環(huán)境,容易被一些歪風(fēng)邪氣影響甚至左右,那么思想教育、黨性培養(yǎng)顯得尤為重要,此次中央群眾教育實(shí)踐活動(dòng)就是基于這樣的目的。對(duì)基層工作者既有物質(zhì)激勵(lì)又有精神指引,“為人民服務(wù)”一定會(huì)成為理性選擇,我們推而廣之,這兩方面對(duì)所有公職人員都適用。
引文注釋
①黨的十二大提出,“發(fā)揮市場(chǎng)在資源配置中的輔助性作用”;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場(chǎng)在國(guó)家宏觀調(diào)控下對(duì)資源配置起基礎(chǔ)性作用”;十六屆三中全會(huì)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發(fā)揮市場(chǎng)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chǔ)性作用”;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fā)揮市場(chǎng)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chǔ)性作用”。
[1][美]弗里德曼.自由選擇[M].北京:機(jī)械工業(yè)出版社,2008.
[2][印]阿瑪?shù)賮喩?以自由看待發(fā)展[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2.
[3][美]奧爾森.集體行動(dòng)的邏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美]巴羅.經(jīng)濟(jì)增長(zhǎng)的決定因素[M].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4.
(作者單位:中央黨校研究生院)
10.16653/j.cnki.32-1034/f.2016.2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