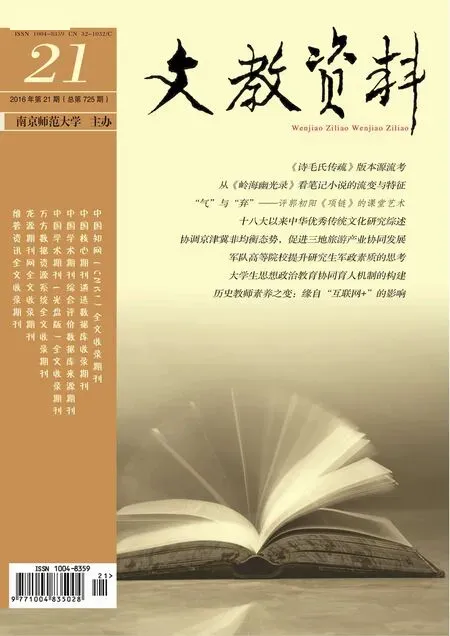翻譯實踐中資本概念的解讀——以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為基礎
楊雯雯 黃 瑞
(中國海洋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青島 266100)
翻譯實踐中資本概念的解讀——以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為基礎
楊雯雯黃瑞
(中國海洋大學 外國語學院,山東 青島266100)
本文以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為基礎,結合翻譯實踐,對資本概念進行解讀,主要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資本的類型,主要討論資本最基本的三種類型,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個具體的方面)、社會資本和與翻譯聯系最緊密的象征資本;各個資本類型的內涵、獲得和積累的過程,以及各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二是翻譯實踐與資本的關系,其中主要探討了象征資本在翻譯場域中的運作及其與翻譯實踐的關系。
布迪厄翻譯社會學資本類型象征資本
1.引言
進入20世紀90年代,越來越多的翻譯研究者開始從社會學的角度對翻譯進行研究(武光軍,2008),從社會學的角度,視翻譯為社會實踐的一種,將其放在整個社會大環境中進行分析,解決許多以前理論無法解決的問題,其中以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最為重要。
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將心理學的個人研究與傳統社會學群體和客觀社會環境的研究相結合,開創了社會學研究的新視角。他的理論實質是一個 “關系型思考”(relational thinking)的模型,目的在于打破個人與社會、主觀與客觀及社會實踐活動內部與外部的二元對立,認為各個方面都存在的相互關系,研究時不能將任何一個方面剝離出來單獨分析。布迪厄的關系模型中有三個最主要的概念:“場域”(field)、“慣習”(Habitus)和“資本”(capital),三者與社會實踐的關系可用公式:[(H)(C)]+(F)=practice表示。“場域”是翻譯實踐進行的地方,是整個理論的基礎,其他概念都是圍繞這一概念衍生而來(Gouanvic2005);“慣習”是指社會實踐參與者自身內在化的性情和選擇傾向,會影響其外在行為,它與外部客觀環境有著“構建”與“被構建”的相互作用(高宣揚,2004);而“資本”的概念,相對于場域和慣習,更像一種隱性的、穿插在整個實踐過程中的東西,它是整個場域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本文的目的是結合翻譯實踐對“資本”這一概念進行解讀,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是資本的類型,主要講了資本的三種類型,特殊的象征資本,以及各資本類型之間的關系;二是翻譯實踐與資本的關系,主要講述了象征資本在場域中的積累和作用。
2.資本的類型
人們在各種社會空間中所外的地位有高低之分,而人們之所以地位不同,從布迪厄的理論看,是由他們所在的特定場域中擁有的資格決定的。人們不可能擁有完全相同的資格,有的人條件優越,在場域中占統治地位、維護規則。條件不優越的只好在場域中被統治(王悅晨,2011)。為了對這些資格進行歸納和分類,布迪厄借鑒經濟學中的“資本”概念解決。場域中最大的特點就是競爭(Bourdieu2011:102),而參與者競爭的動力來源就是資本,它決定了參與者在場域中的地位及他們手中的權力。因此,無論是翻譯實踐還是社會實踐,“資本”都是一個不可不討論的概念。
資本的類型可歸納為三種形式: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另外還有一種特殊的資本類型,稱為象征資本。各種資本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和相互關系,以及轉化機制(經濟資本與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概念沒有區別,所以不做特殊解釋)。
2.1文化資本
文化資本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資源,存在三種形式:具體化的狀態(embodiedstate),以一種持久性的性情存在于人的身體和精神中;客觀化的狀態(objectifiedstate),以文化產品的形式存在,比如畫作、書籍、機器設備等,這些商品以客觀的形式對理論性的東西加以體現;體制化的狀態(institutionalizedstate),嚴格意義上講,它屬于客觀化狀態的一種,但必須做單獨的闡釋,因為是這種體制性的狀態賦予和保證了文化資本最原始的特點(Bourdieu1986:243)。
2.1.1具體化形式的資本
這一資本的獲得是個體自我提升的過程,這個過程往往是無意識的,需要個人的投入,這種具體化的資本是將外部財富內化到個體的內部,融入自身的慣習當中,習得的程度取決于時間、社會、階級及一些細微的東西,不僅來自于學校的教育,而且來自于自身家庭的前期的培養。因此,總是帶有最初條件的痕跡,在習得過程中或明或隱的痕跡,這是文化資本區別于其他文化資本的特征之一。由此看來在具體化資本這個層面上看文化資本是可以繼承的。有的譯者獲得的具體化文化資本的一部分里是靠先天獲得的。
2.1.2客觀化的資本
客觀化資本指的是以可傳遞的、以實物形式體現的文化資本,比如書畫、書籍、紀念碑、器械等。在物質的可傳遞性方面,客觀化資本很近似經濟資本,可以經過投資獲得利益。不過可以傳承的,只是合法的所有權,而原作者在創作作品時,自身所具有的具體化資本是無法傳承的。比如某個人買了達·芬奇的一幅畫作,他擁有的只是這幅畫的所有權,只是這種客觀化的資本形式,而并不能擁有達·芬奇的具體化資本。客觀化文化資本是作為競爭中的一種武器或某種利害關系而受到關注并用來投資的。行為者力量的大小及收獲利益的大小則與他們所擁有的客觀化的資本及具體化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Bourdieu1986:247)。
2.1.3體制化資本
體制化資本指由諸如學校、政府機關等權威社會機構授予和認可的學術資歷、專業或獎勵證書,是文化能力經過文化體制的資格授權后的存在形式。學術資格和文化能力的證書可以保證其擁有者有一種文化的、約定俗成的、持續的、受到合法保障的價值(Bourdieu1986:247)。當然這種體制化的形式必然使文化資本帶有持續證明自身合法性的壓力。例如現在各種翻譯資格證書考試、學歷證書、各種期刊論文的發表都是譯者持續證明自身合法性的典型代表。任何一個行為者都占有體制上認可的文化資本,各種學歷證書還能為譯者帶來榮譽、地位、話語權及物質利益,因此使得文化資本轉換成經濟資本。然而因為學術資格所帶來的物質利益和象征利益是建立在“超常利益”的基礎上,所以當參與者在進行投資時,他們獲得的利益將比預期的少。
2.2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還可以被通俗地理解為“人脈”,就是調動社會資源交際網絡的能力。一個參與者擁有的社會資本總量取決于他實際上能動員起來的社會網絡的幅度,取決于他所聯系的那個社會網絡中每個參與者所持有的資本總容量。所以交際網絡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持續努力的產物,是投資策略的產物。例如一個成功商業人士積累很多社會資本,在場域中擁有很高的地位,很多人在生意場上盡管不認識他,但都會說“我和他很熟”、“我和他有生意往來”、“我看過他的書”之類的話證明他和這個成功人士有關系,以此體現自身的社會資本。
2.3象征資本
象征資本指因其他形式的資本積累而產生的聲望、地位和名譽等社會象征意義,它可以由其他三種資本轉化而來。也有學者認為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都屬于象征資本,直接與經濟資本相對。象征資本的獲得來自于場域內部的認可,當一定量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被場域中的某些參與者提倡,而其他的參與者也認可時,這種資本就實現了某種“合法化”,形成了所謂的“象征資本”。參與者使自己手中的資本具有價值,令其他參與者相信這些資本是值得追求的行為,就是在制定或強化場域的規則,這就是一種權力的體現,布迪厄稱之為象征暴力。因此,象征資本主要不是通過繼承,而是通過被認可獲得的。以文學場域為例,作者必須通過不斷地發表新作品獲得象征資本,而一旦積累到一定程度,象征資本就會變得相對穩固。
對于不同資本類型之間的關系,可以總結為:經濟資本是產生其他資本的根源,其他資本可以看做是經濟資本的變體,這三種資本的基本形式是可以互相轉化的。而對于象征資本而言,都可以由其他資本轉化而來,但經濟資本不能直接轉化,要先轉化成文化資本或者社會資本,再形成象征資本。具體來說,文化資本可以從經濟資本轉化而來,比如對教育進行投資,可獲得教育成果、較高的學歷等;同時文化資本也可以轉化成經濟資本,比如獲得高等學歷的人往往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賺取更多的經濟資本;同時文化資本也可以轉化為社會資本,比如獲得一定教育文憑的人便可以進入一定的商業或學術圈子建立人際關系。而一定量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在某一場域中一旦被認可,就形成象征資本;對于經濟資本而言,可先轉化成其他資本再到象征資本,比如,一個有錢人要進入學術圈需要先購買一個博士文憑,然后才會有一定的發言權。雖然經濟資本是根源和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社會行為都可以簡化為經濟資本的交換,因為這種觀點“忽略了其他類型的資本所能產生的特殊功效”(Bourdieu1986:252)。
3.翻譯與資本
場域最大的特點就是參與者之間的競爭,而競爭的動力則來源于“資本”,它決定了參與者在場域中的位置和擁有的權力,位于邊緣的參與者們往往通過斗爭不斷積累資本來提升自己的地位,而位于中心的參與者,也會為了維護自身的中心地位而繼續不斷地積累資本。因此對資本的探討實際上是對場域內部結構的探討(胡牧,2006)。在場域中各種形式的資本當中,與翻譯聯系最為緊密的就是象征資本(邵璐,2011),因此,對翻譯與資本的討論可以圍繞象征資本與翻譯實踐的聯系展開。
在象征資本的獲取方面,作者和譯者有著本質的不同(Moore2008)。對于作者來說,所在的文學場域中,象征資本的獲得并不是繼承來的,而是通過其他參與者的認可獲得,因此他需要不斷發表新作積累自己的象征資本,一旦他和自己的作品達到經典的地位,象征資本就會變得十分穩定,不會隨時間的變化而被質疑,或者變得易受影響。但對于譯者而言,則并非如此,譯者的象征資本通常不會像原作者那樣穩定持久。通常,他們會從原作者那里獲得一部分象征資本,比如不知名的譯者通過翻譯知名作品,積累象征資本,而使自己變得有名;但反過來,譯者通過翻譯原作,讓譯作在目標語社會中被接受,也會增加原作及原作者的象征資本,比如葛浩文翻譯莫言的作品,使莫言在目標語社會中的象征資本增加,取得一定的地位。因此,譯者和原作者之間是可以相互為對方增加和創造象征資本的,是一個雙向的互惠互利的關系。
譯者象征資本的獲得與積累往往分為兩個方面:一是通過改變自身在整個文學場域中的位置,改變自身的象征資本,比如有的譯者會選擇翻譯一些在目標語場域中被視為正統文學的作品,這樣更容易得到場域中其他參與者的認可,以此增加自己的象征資本,從而提高自己在場域中的地位和知名度;二是通過提升在自身場域中的地位,增加象征資本,比如有的譯者翻譯的文學作品在某個文學場域并不屬于正統文學,認可度并不高,比如偵探小說,但其在整個偵探小說的場域中卻可以占據主導地位,以此建立和增加自身的象征資本。
當譯者在翻譯場域中積累足夠多的象征資本之后,其自身便具有改變規則的權力(Sela2008),例如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等作品,深刻影響近代中國,使他擁有較多的象征資本,因此他有關翻譯的言論在很長一段時間也被人們奉為圭臬,言必稱“信達雅”。“信達雅”在20世紀90年代前成為中國翻譯場域中的主要規則之一,成為衡量譯者和譯作是否合格的重要標準(王悅晨,2011)。此外,譯者在某個領域擁有占主導性地位的象征資本,可能會幫助其開創一個全新的場域,增加某種非正統文學在整個文學場域的地位,比如法國的一位工程師出身的譯者,熱衷于科幻小說翻譯,他與自己的搭檔組成一個團隊,專門從事科幻小說的翻譯,開創科幻小說自身的翻譯場域,積累占主導地位的象征資本,從而利用這種象征資本的優勢提升了科幻小說在法國文學場域中的地位。
4.結語
通過對布迪厄社會學理論的簡單介紹,我們了解到所謂“翻譯社會學”的理論依托和研究方法、視角到底是什么,對于關鍵詞的解讀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結合翻譯來對翻譯實踐進行解釋。資本這一概念是構架場域內部結構的核心概念,是整個場域發展的變化的內在驅動力,參與者本身的權力和地位息息相關,通過對資本的類型及類型之間轉化關系的探討,可以更清楚和了解場域內部的運作形式。對于翻譯而言,最重要的是象征資本的作用,這種特殊的資本是由其他資本形式轉化而來的,轉化的過程即“被認可”的過程,因此象征資本的多少決定擁有者在場域中的地位和話語權。通過將布迪厄的社會學理論引入翻譯中,給了我們翻譯研究的一種新視角,解決一些前人理論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布迪厄社會學理論與翻譯實踐的結合值得進一步探討。
[1]Bourdieu,P.TheFormsofCapital[J].NewYork,Greenwood,1986:241-258.
[2]Gouanvic,J.ABourdieusianTheoryofTranslation,or theCoincidenceofPracticalInstances[J].TheTranslator,2005(11):161-163.
[3]Grenfell,M.PierreBourdieu:KeyConcepts[C].Trowbridge:AcumenPublishingLimited,2008.
[4]Sela-Sheffy,R.TheTranslators’Personae:Marketing TranslatorialImagesasPursuitofCapital[J].Meta,2008(53):613-618.
[5]胡牧.翻譯研究:一個社會學視角[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9).
[6]高宣揚.布迪厄的社會理論[M].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7]邵璐.翻譯社會學的迷思——布迪厄場域理論釋解[J].暨南學報,2011,33(3).
[8]武光軍.翻譯社會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J].外國語,2008,31(1).
[9]王悅晨.從社會學角度看翻譯現象:布迪厄社會學理論解讀[J].中國翻譯,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