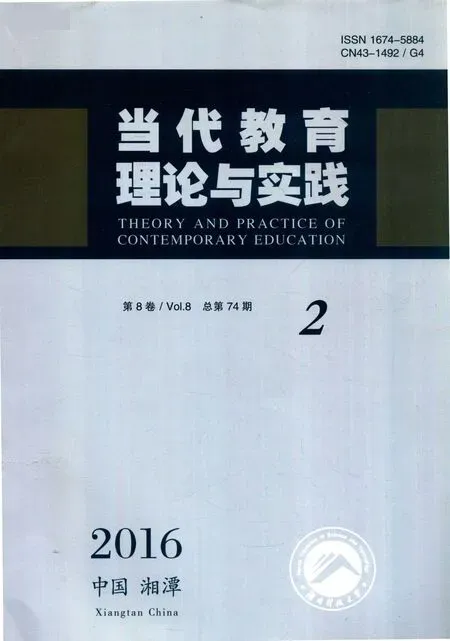述論廣東近代高等教育中的數(shù)學(xué)課程——以《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為例
廖運(yùn)章
(廣州大學(xué) 數(shù)學(xué)與信息科學(xué)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006)
?
述論廣東近代高等教育中的數(shù)學(xué)課程
——以《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為例
廖運(yùn)章
(廣州大學(xué) 數(shù)學(xué)與信息科學(xué)學(xué)院,廣東 廣州 510006)
摘要:《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是潘應(yīng)祺自編的廣東高等學(xué)堂預(yù)科數(shù)學(xué)課本,是當(dāng)時(shí)廣東地區(qū)具有代表性的數(shù)學(xué)論著和流行較廣的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內(nèi)容僅相當(dāng)于現(xiàn)今小學(xué)初中的數(shù)學(xué)水平;采用橫豎混合編排,數(shù)學(xué)符號(hào)中西兼用;以數(shù)學(xué)的邏輯關(guān)系編排教學(xué)內(nèi)容,注重?cái)?shù)學(xué)與生活實(shí)際的聯(lián)系;承載傳播西方數(shù)學(xué)文化的歷史使命,促進(jìn)廣東近代數(shù)學(xué)教育的迅速發(fā)展。
關(guān)鍵詞:廣東高等學(xué)堂;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算術(shù)駕說(shuō)》 ;《幾何贅說(shuō)》
《算術(shù)駕說(shuō)》《幾何贅說(shuō)》又依次稱廣東高等學(xué)堂預(yù)科算術(shù)與幾何課本,是廣東近代高等教育國(guó)人自編的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也是晚晴廣東2本具有代表性的數(shù)學(xué)著作,勾勒了20世紀(jì)初廣東近代數(shù)學(xué)教育的基本狀況。無(wú)論從數(shù)學(xué)教育史視角還是廣東地方史角度,都具有重要的學(xué)術(shù)研究?jī)r(jià)值。
120世紀(jì)初廣東高等教育中的數(shù)學(xué)課程設(shè)置
中國(guó)邁入近代以后,廣東的傳統(tǒng)教育逐漸向近代教育發(fā)展。1901年清廷下詔改省城大書(shū)院為省大學(xué)堂,1902年廣雅書(shū)院(1888年成立)改名為兩廣大學(xué)堂,這是近代廣東第一所高等學(xué)堂,標(biāo)志著近代高等教育在廣東正式啟動(dòng)。1903年朝廷頒布《奏定高等學(xué)堂章程》,規(guī)定各省只能在省城設(shè)高等學(xué)堂一所,同年兩廣大學(xué)堂又改名為兩廣高等學(xué)堂,1906年停招廣西省學(xué)生,改稱廣東高等學(xué)堂,辛亥革命后更名為廣東省立第一中學(xué),1935年改稱廣東省立廣雅中學(xué)。廣東高等學(xué)堂雖辦學(xué)時(shí)間不長(zhǎng)(若從大學(xué)堂開(kāi)辦計(jì)起,由壬寅至辛亥不過(guò)10年),但卻首開(kāi)廣東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
在廣東高等學(xué)堂的建設(shè)過(guò)程中,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師資難聘、經(jīng)費(fèi)難籌、學(xué)生難招。當(dāng)時(shí)能勝任新學(xué)的教學(xué)人員很少,學(xué)堂畢業(yè)生和留學(xué)歸國(guó)人員供不應(yīng)求,如水陸師學(xué)堂畢業(yè)并精通數(shù)學(xué)的曹汝英與潘應(yīng)祺、官費(fèi)留日歸國(guó)的朱執(zhí)信等著名人士擔(dān)任教習(xí)。廣東高等學(xué)堂分預(yù)科、本科,前者3年后者5年即8年為成,招生對(duì)象為中學(xué)畢業(yè)生和文化程度相當(dāng)者,課程分政、藝兩科,政科開(kāi)設(shè)倫理、經(jīng)學(xué)、諸子、詞章、算學(xué)、中外史學(xué)、中外輿地、外國(guó)文、物理、名學(xué)、法學(xué)、理財(cái)學(xué)、體操等13門,藝科開(kāi)設(shè)倫理、中外史學(xué)、外國(guó)文、算學(xué)、物理、化學(xué)、動(dòng)植物學(xué)、地質(zhì)與礦產(chǎn)學(xué)、圖畫、體操等10門。
在學(xué)堂教材的編寫方面,辛亥革命前10年,就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而言,小學(xué)教科書(shū)國(guó)人自編的很多,中學(xué)教科書(shū)翻譯或編譯的多,而自編的少,高等教育的教科書(shū)翻譯的很少,自編的則是寥寥無(wú)幾[1]。廣東高等學(xué)堂的算學(xué)教科書(shū)采用潘應(yīng)祺編撰的《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現(xiàn)準(zhǔn)存古學(xué)堂監(jiān)督咨開(kāi)恭按,奏定章程學(xué)務(wù),綱要內(nèi)載,采用各學(xué)堂講義及私家所纂教科書(shū),其合于教授之用者,準(zhǔn)著書(shū)人自行刊印售賣,予以版權(quán)一條,查高等學(xué)堂算學(xué)教員潘應(yīng)祺,前以積年講授算稿,編定幾何平面六卷,繼以歷年講授預(yù)科學(xué)生算術(shù)課本,編定《算術(shù)駕說(shuō)》十一卷,均裝印成帙。”[2]這是廣東近代高等教育國(guó)人自編的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是當(dāng)時(shí)廣東地區(qū)有代表性的數(shù)學(xué)論著[3]和流行較廣的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是考察廣東高等學(xué)堂數(shù)學(xué)教學(xué)的原始資料。
2潘應(yīng)祺及其數(shù)學(xué)著述
潘應(yīng)祺(1866-1926),廣州番禺化龍西山村人。幼年在鄉(xiāng)隨父耕讀,聰明好學(xué),考取秀才后,又考入當(dāng)時(shí)引入不少西方科學(xué)的廣東實(shí)學(xué)館(后改博學(xué)館、水陸師學(xué)堂),畢業(yè)后曾應(yīng)鄉(xiāng)試考取舉人,之后投身教育事業(yè),先后任教于廣雅書(shū)院、廣東高等學(xué)堂、教忠學(xué)堂等校,教授數(shù)學(xué)。辛亥革命后,曾在廣州市政公所任職(時(shí)曹汝英為坐辦),并曾從事番禺縣志的續(xù)修工作。1924年重執(zhí)教鞭,在香港圣保羅女書(shū)院任教,1925年回廣州開(kāi)設(shè)教館,教授國(guó)文、數(shù)學(xué)、英語(yǔ)等。
潘應(yīng)祺具有很高的數(shù)學(xué)造詣,就讀廣東實(shí)學(xué)館時(shí)跟隨老師方愷“習(xí)算學(xué),先筆算,次代數(shù)、幾何、平弧三角、測(cè)量諸術(shù)。”曾與其他5名同學(xué)在方愷講稿的基礎(chǔ)上整理成《代數(shù)通藝錄》十六卷。方愷(1839-1891),江蘇陽(yáng)湖(今江蘇武進(jìn)縣)人,其父方駿謨(1816-1879)與數(shù)學(xué)家華蘅芳、張文虎等人交厚。光緒八年(1882)初廣東實(shí)學(xué)館開(kāi)館,兩廣總督張樹(shù)聲推薦方愷為漢文教習(xí),教授漢文和算學(xué)。方愷“博覽多識(shí)”“于輿地歷算之學(xué),靡不綜核淹貫,著書(shū)滿家”,數(shù)學(xué)著作有《代數(shù)通藝錄》十六卷、《筆算初階》一卷等。 方愷在廣東水陸師學(xué)堂(1882-1887)的五六年中一直兼授數(shù)學(xué),方愷不會(huì)廣州方言,以板書(shū)代口授,“張壁立書(shū),推本天元借根,鉤稽數(shù)理,建簡(jiǎn)核西術(shù)代數(shù),譯示講誦”,學(xué)生“傳習(xí)算草,各有成帙”,方愷“輒為作序,以獎(jiǎng)勵(lì)之”,學(xué)生們對(duì)他很敬服。方愷在廣東水陸師學(xué)堂的成就很大,先后有130多名學(xué)生從他學(xué)習(xí)數(shù)學(xué),潘應(yīng)祺是其中的佼佼者。

潘應(yīng)祺著有《算術(shù)駕說(shuō)》十一卷、《幾何贅說(shuō)》六卷、《代數(shù)通藝錄續(xù)集》二卷、《經(jīng)算雜說(shuō)》一卷、《算學(xué)雜識(shí)》十卷(與曹汝英合撰)、《佛山書(shū)院算課草》十一卷。其中,《幾何贅說(shuō)》又名《廣東高等學(xué)堂預(yù)科幾何課本》,根據(jù)明末徐光啟與利瑪竇合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改編而成,仍沿用徐光啟等創(chuàng)造的體例;《佛山書(shū)院算課草》由熊方柏鑒定、潘應(yīng)祺與曹汝英覆勘,是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佛山書(shū)院添考數(shù)學(xué)的課卷匯編,主要涉及三元一次方程組求解、等比數(shù)列和等差數(shù)列計(jì)算、勾股問(wèn)題以及平面幾何中的三角形和圓,以解三角形問(wèn)題為多,題目多是實(shí)際應(yīng)用問(wèn)題。
3廣東高等學(xué)堂預(yù)科數(shù)學(xué)教材的內(nèi)容及特色
依《奏定學(xué)堂章程》,高等學(xué)堂伊始就設(shè)置數(shù)學(xué)課程,每周6 d合12 h[4],先后由林汝魁(番禺人)、林慶鎬(新會(huì)人)、羅偉卿、朱孔陽(yáng)、潘應(yīng)祺等人教授。《幾何贅說(shuō)》和《算術(shù)駕說(shuō)》(圖1)是潘應(yīng)祺1903年起任教高等學(xué)堂時(shí)期自編的2本數(shù)學(xué)教材,是其多年研究、教授數(shù)學(xué)的心得與總結(jié)。
3.1 《算術(shù)駕說(shuō)》內(nèi)容特點(diǎn)分析

圖1 廣東高等學(xué)堂預(yù)科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
《算術(shù)駕說(shuō)》總393頁(yè)[5],全書(shū)十一卷內(nèi)容包括:卷一數(shù)名,列位、加法、小數(shù)加法;卷二減法,小數(shù)減法、加減雜題;卷三乘法,小數(shù)乘法、加減乘雜題、十一十二單乘法、推加乘法、截乘法、疊乘法;卷四除法,截除法、小數(shù)除法、用加減乘除各號(hào)及括弧法、加減乘除雜題、附說(shuō)(解乘除試驗(yàn)法之理、解以〇除數(shù)得無(wú)窮之理);卷五析生數(shù)法,求最大公約數(shù)法、求最小公倍數(shù)法、相消法、附說(shuō)(解析生數(shù)法內(nèi)審查除法盡否之理);卷六分?jǐn)?shù),約分、齊分、加分、減分、乘分、除分、重分?jǐn)?shù)、分分?jǐn)?shù)、諸分錯(cuò)雜之式、諸分雜題;卷七項(xiàng)數(shù)(即諸等數(shù)),化大項(xiàng)為小項(xiàng)法、化小項(xiàng)為大項(xiàng)法、項(xiàng)數(shù)加減乘除法、化大項(xiàng)之分?jǐn)?shù)或小數(shù)為小項(xiàng)法、化小項(xiàng)為大項(xiàng)之分?jǐn)?shù)或小數(shù)法、外國(guó)之項(xiàng)數(shù)、斤兩算法、天度時(shí)刻相求法、經(jīng)度時(shí)刻相求法;卷八比例,合率比例、連環(huán)比例、百分法、卷九平方,計(jì)稅畝法、開(kāi)平方、小數(shù)開(kāi)平方法、分?jǐn)?shù)開(kāi)平方法;卷十立方,體積重率、開(kāi)立、小數(shù)開(kāi)立方、分?jǐn)?shù)開(kāi)立方;卷十一 諸乘方,開(kāi)諸乘方、小數(shù)開(kāi)諸乘方法、分?jǐn)?shù)開(kāi)諸乘方法、諸乘方代開(kāi)法;附錄求積法。
該書(shū)例言對(duì)編寫背景作了說(shuō)明,一是《算術(shù)駕說(shuō)》系根據(jù)《奏定中學(xué)堂章程》要求編撰而成,“奏定學(xué)堂章程中學(xué)堂各學(xué)科分科教法算學(xué)條下云,外國(guó)以數(shù)學(xué)為算法各種總稱,……其中以實(shí)數(shù)計(jì)算為算術(shù),……茲編所說(shuō),皆以實(shí)數(shù)計(jì)算者,故名算術(shù)。”二是闡述書(shū)名的由來(lái),“駕,傳也。……茲編雖或間有發(fā)明,亦不過(guò)引申舊緒,傳述前聞而已。題曰算術(shù)駕說(shuō)”,意為傳述前人的數(shù)學(xué)知識(shí),并非自己創(chuàng)造,因此得名。三是闡釋教法與學(xué)法,“凡算理算法,勢(shì)必相輔而行。……惟間遇算理稍繁者,似宜先言法而后言理。”以方便學(xué)生領(lǐng)會(huì),“每言一法,后繼以習(xí)問(wèn)”,鼓勵(lì)學(xué)生勤加練習(xí),學(xué)習(xí)應(yīng)循序漸進(jìn),不能“躐等求速”。四是對(duì)“算術(shù)推之則難明,以代數(shù)推之則易解”的算術(shù)問(wèn)題,“統(tǒng)俟習(xí)代數(shù)時(shí)言之,自然迎刃而解。此時(shí)似不必勞精敝神而為之也。”而“求積之法,頗切實(shí)際用”,則“附錄于本編之后”,注重?cái)?shù)學(xué)與生活實(shí)際的聯(lián)系。顯而易見(jiàn),這些數(shù)學(xué)教學(xué)理念至今仍有現(xiàn)實(shí)意義。

3.2《幾何贅說(shuō)》內(nèi)容特點(diǎn)分析
《幾何贅說(shuō)》含照會(huì)1頁(yè)、吳道镕序2頁(yè)、利瑪竇序5頁(yè)、徐光啟序2頁(yè)、徐跋1頁(yè)、徐雜議2頁(yè)、《贅說(shuō)例言》3頁(yè)、正文281頁(yè),總297頁(yè),由《幾何原本》前六卷構(gòu)成,包括歐幾里得平面幾何的全部?jī)?nèi)容[6]。卷一“界說(shuō)”(定義)點(diǎn)線面等36個(gè)幾何概念,給出4條公設(shè)(“求作”)、19條公理(“公論”)和48個(gè)命題,作為基于定義、公理之嚴(yán)密邏輯推理體系的基礎(chǔ),內(nèi)容涉及三角形、平行四邊形作法及其性質(zhì);卷二主要論及平面直角形的等積變換,用幾何語(yǔ)言敘述代數(shù)恒等式;卷三討論圓及其性質(zhì);卷四為圓內(nèi)接、外切形及其性質(zhì);卷五介紹數(shù)量(線段、面積、體積等)成比例、比例式及其性質(zhì);卷六是平面相似形及其性質(zhì)。
《幾何贅說(shuō)》以《幾何原本》為藍(lán)本,在內(nèi)容編排、知識(shí)呈現(xiàn)、例題選擇、數(shù)學(xué)符號(hào)使用等方面基本一致,數(shù)學(xué)程度與現(xiàn)今初中圖形與幾何水平相當(dāng)。但在知識(shí)點(diǎn)的講解上,《幾何贅說(shuō)》并沒(méi)有照本宣科,直接套用《幾何原本》的解說(shuō),而是在充分理解之后,加進(jìn)自己的領(lǐng)悟與說(shuō)明,選取或編增適當(dāng)實(shí)例(如“以代數(shù)釋幾何”、用數(shù)代替線段講述卷五的分?jǐn)?shù)概念)詮釋知識(shí),去繁就簡(jiǎn),例題書(shū)寫也更簡(jiǎn)潔、一目了然,整體上更有利于學(xué)生理解與掌握。同時(shí),每卷之后都編選、增加一些相關(guān)例習(xí)題,供學(xué)生練習(xí),凸顯教材本質(zhì)。
囿于《奏定學(xué)堂章程》只規(guī)定初等/高等小學(xué)堂的具體數(shù)學(xué)課程,中學(xué)堂以上僅羅列學(xué)科名稱如算術(shù)、代數(shù)、幾何、薄記、三角等,其中具體內(nèi)容不加限制,由學(xué)堂自行決定。潘應(yīng)棋則很有見(jiàn)地沿用清代同文館和一些西學(xué)堂把《幾何原本》作為必讀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的傳統(tǒng),并結(jié)合高等學(xué)堂實(shí)際編成《幾何贅說(shuō)》,推動(dòng)了幾何公理化思想在廣東近代教育中的傳播,百年的數(shù)學(xué)教育實(shí)踐表明潘應(yīng)棋的遠(yuǎn)見(jiàn)卓識(shí),至今這些幾何知識(shí)仍是中小學(xué)數(shù)學(xué)教育的核心內(nèi)容,潘應(yīng)棋及其《幾何贅說(shuō)》廣受后人推崇[7]。
4《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的歷史貢獻(xiàn)
第一,依托良好的數(shù)學(xué)教育環(huán)境,傳承廣東重視數(shù)學(xué)教育傳統(tǒng),傳播優(yōu)秀西方數(shù)學(xué)文化。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降,受求強(qiáng)求富、中體西用等洋務(wù)思想以及務(wù)實(shí)、開(kāi)放、兼容、創(chuàng)新為特征的嶺南文化影響,晚晴廣東數(shù)學(xué)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長(zhǎng)足發(fā)展,形成良好的數(shù)學(xué)學(xué)習(xí)氛圍,一些書(shū)院、學(xué)堂始設(shè)數(shù)學(xué)課程,先后出現(xiàn)一批學(xué)貫中西、專心數(shù)學(xué)研究并熱心傳播數(shù)學(xué)的數(shù)學(xué)教師群體,如學(xué)海堂的陳澧與鄒伯奇、廣州同文館的吳嘉善、廣東實(shí)學(xué)館的方愷等[8],都是當(dāng)時(shí)享有全國(guó)聲譽(yù)的數(shù)學(xué)名家,潘應(yīng)祺的教科書(shū)正是順應(yīng)大眾學(xué)習(xí)西方數(shù)學(xué)熱潮的時(shí)代產(chǎn)物,承載著傳播西方數(shù)學(xué)文化的歷史使命,以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數(shù)學(xué)與西方數(shù)學(xué)的順利合流。
第二,作為國(guó)人自編的近代高等教育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推進(jìn)了中國(guó)數(shù)學(xué)教育的近代化進(jìn)程。隨著癸卯學(xué)制的頒行,各級(jí)各類學(xué)堂都不同程度地開(kāi)設(shè)數(shù)學(xué)課程,數(shù)學(xué)教育由是漸得普及,但新學(xué)堂的大量劇增使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供不應(yīng)求,高等學(xué)堂和大學(xué)堂尤甚,一般直接采用外文本。潘應(yīng)祺將其研究數(shù)學(xué)的心得與多年進(jìn)行數(shù)學(xué)教學(xué)的體會(huì),撰寫了適合高等學(xué)堂預(yù)科算學(xué)教學(xué)的課本《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并成為當(dāng)時(shí)嶺南地區(qū)流行多年的數(shù)學(xué)教科書(shū),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有效地促進(jìn)廣東近代數(shù)學(xué)教育的迅速發(fā)展。
第三,體現(xiàn)數(shù)學(xué)教育的實(shí)用觀,即數(shù)學(xué)教育的目的是訓(xùn)練一種技能,以為工藝制器、經(jīng)世致用之具,而不是訓(xùn)練科學(xué)精神與方法,借以提高人的素質(zhì),這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數(shù)學(xué)實(shí)用性在數(shù)學(xué)教育中的反映。在合流于主流數(shù)學(xué)教育100年后的今天,數(shù)學(xué)教育重視數(shù)學(xué)的文化功能得到普遍認(rèn)可,但數(shù)學(xué)的技術(shù)功能一定程度上被忽視了。因此,具有濃厚應(yīng)用數(shù)學(xué)色彩的《算術(shù)駕說(shuō)》,以及側(cè)重演繹推理的《幾何贅說(shuō)》也“其講幾何,須詳于論理,使得應(yīng)用于測(cè)量、求積等法”[9],無(wú)疑對(duì)當(dāng)代數(shù)學(xué)教育著力發(fā)展學(xué)生的數(shù)學(xué)建模(應(yīng)用)意識(shí)與能力方面,仍具備現(xiàn)實(shí)的指導(dǎo)意義。
第四,內(nèi)容雖無(wú)微積分等高等數(shù)學(xué)內(nèi)容,但能真實(shí)反映高等學(xué)堂的數(shù)學(xué)教學(xué)水平。 20世紀(jì)初,中國(guó)傳統(tǒng)數(shù)學(xué)研究中斷,中國(guó)數(shù)學(xué)完成自明末清初以來(lái)西方化歷程,實(shí)現(xiàn)與近代主流數(shù)學(xué)的合流,學(xué)界重在關(guān)注西方變量數(shù)學(xué)如微積分等的學(xué)習(xí)吸收,數(shù)學(xué)教育則以西方常量數(shù)學(xué)為主,因教材、師資、生源等原因,預(yù)科修業(yè)等同舊制中學(xué),大學(xué)堂與中學(xué)堂名科雖不同,而學(xué)生程度則并無(wú)差別,高等學(xué)堂以上的數(shù)學(xué)課程并未及時(shí)實(shí)施,大學(xué)堂算學(xué)門終清之世亦未曾建立[10],如《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等初等數(shù)學(xué)遂成為我國(guó)近代高等教育數(shù)學(xué)教學(xué)的主要內(nèi)容,為辛亥革命后制度化的高等數(shù)學(xué)教育奠定必要的準(zhǔn)備與基礎(chǔ)。1924年,廣東大學(xué)成立并設(shè)立數(shù)學(xué)系,1926年更名為國(guó)立中山大學(xué),數(shù)學(xué)系則改為數(shù)學(xué)天文系,廣東高等數(shù)學(xué)教育從此走上制度化發(fā)展道路,目前廣東省內(nèi)的中山大學(xué)、華南理工大學(xué)、華南師范大學(xué)、廣州大學(xué)擁有數(shù)學(xué)一級(jí)學(xué)科博士學(xué)位授予權(quán),汕頭大學(xué)擁有基礎(chǔ)數(shù)學(xué)二級(jí)學(xué)科博士學(xué)位授予權(quán),廣東已形成從中小學(xué)到大學(xué)的完備現(xiàn)代數(shù)學(xué)教育體系,《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功不可沒(méi)。
當(dāng)然,《算術(shù)駕說(shuō)》與《幾何贅說(shuō)》用舊式文言文敘說(shuō),不免古舊,但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后的1920年,教育部頒令“凡國(guó)民學(xué)校年級(jí)國(guó)文課教育也統(tǒng)一運(yùn)用語(yǔ)體文(即白話文)”,白話文才取代文言文,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數(shù)學(xué)教育轉(zhuǎn)向西式數(shù)學(xué)教育的時(shí)代,這是可以理解的,不妨礙它為廣東現(xiàn)代高等數(shù)學(xué)教育發(fā)展所作的奠基性貢獻(xiàn)。
參考文獻(xiàn):
[1] 李兆華.中國(guó)近代數(shù)學(xué)教育史稿[M].濟(jì)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5.
[2](淸)羅汝楠.中國(guó)近世輿地圖說(shuō)(二十三卷首一卷)[O].廣東教忠學(xué)堂石印本,宣統(tǒng)元年(1909).
[3] 黃世瑞.創(chuàng)新與進(jìn)步:廣州百年科技發(fā)展尋蹤[M]. 廣州:廣州出版社,2001.
[4] 張耀榮.廣東高等教育發(fā)展史[M]. 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5](淸)潘應(yīng)祺.算術(shù)駕說(shuō)(十一卷)[O].番禺潘氏扈離館刊本,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 .
[6](淸)潘應(yīng)祺.幾何贅說(shuō)(前六卷)[O].番禺潘氏扈離館刊本,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 .
[7] 楊澤忠.《幾何原本》傳入我國(guó)的過(guò)程[J].自然辨證法通訊,2005(4):87-91.
[8] 田淼.清末數(shù)學(xué)教師的構(gòu)成特點(diǎn)[J].中國(guó)科技史料,1998(4):19-24.
[9] 舒新城.中國(guó)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cè))[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
[10] 郭書(shū)春.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史·數(shù)學(xué)卷[M]. 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10.
(責(zé)任校對(duì)晏小敏)
中圖分類號(hào):G649.29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674-5884(2016)02-0031-04
作者簡(jiǎn)介:廖運(yùn)章(1964-),男,仫佬族,廣西羅城人,教授,碩士,從事數(shù)學(xué)教育與數(shù)學(xué)史研究。
基金項(xiàng)目:《廣州大典》與廣州歷史文化研究資金資助項(xiàng)目(2014GZY10)
收稿日期:20151015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6.0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