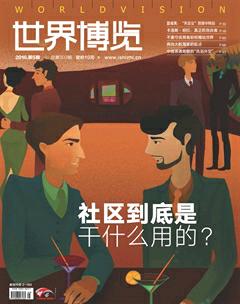開放型社區的利與弊
齊媛
近些日子,網上關于“推廣街區制”的討論,逐漸發酵出極大爭議,這里對美、印、俄、日等國的城市規劃進行對比分析,可見無論是開放的街區制還是封閉式的社區都有各自鮮明的特點,對我們的城市規劃都應該有著一定的借鑒作用。
關于“封閉住宅小區原則上不再建”“已建成的住宅小區和單位大院要逐步打開”的初衷,顯然是為了治療“毛細血管不暢”等“城市病”,但“打開”后社區治安管理、居民安全、生活質量等問題,又確實是民眾實實在在的關切。
美國:小區是否開放,業主投票決定
歐美最早時的城市規劃思路也是功能分離,如國際現代建筑協會1933年8月制定的關于城市規劃的綱領性文件《雅典憲章》所述,小區就是小區,道路就是道路,工廠就是工廠,商業就是商業,都是各管各的。相關的變革出現在上世紀60年代。社會活動家簡·雅各布斯女士1961年出版《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書中提到紐約應搞“小街道、小社區”的設想。該書對美國社會沖擊很大,當時也有很多尖銳反對的意見,但后來歐美國家還是一步步發生變化,特別是一些國際城市規劃師1977年在利馬開會,通過《馬丘比丘》憲章以后。
在美國芝加哥等大城市市區,封閉住宅小區很少。因為芝加哥市區基本上是街區制,初來者根據街區門牌號基本能縱橫定位找到地址。在郊區,才有一些高檔社區是封閉的。這些社區里的道路不對外開放,保安和門衛都由小區物業負擔,因此物業管理費比一般小區高很多。
為居民區內部交通安全考慮,芝加哥政府對過路車輛使用小區內道路有嚴格限制,比如非高速的干道限速一般每小時40英里(1英里約為1.6公里),而在小區內部,無論是封閉還是開放小區,一般限速每小時25英里。很多開放社區會采取措施限制外部車輛流量或讓司機減速,如用小型環島取代十字路口,減少干線和小區道路的進出口。還有很多小區在高峰時段禁止路過車輛拐入小區“抄近路”,如芝加哥西郊的Elmhurst在IL 83號公路上立了很多高峰時段不準右轉進入小區的標志。美國封閉小區的社區物業委員會由業主自己選舉產生,管理小區的物業財務和各種計劃。業主可以自己投票決定是不是要開放小區還是封閉小區。至于安全支出,如果當地居民比較富裕,房地產稅比較多,警力就強一些,治安也會好一些。
甚至美國其他州的很多城市住宅,都沒有圍墻,沒有鐵門,也不是大院子。比如富豪巴菲特就居住證一棟灰色的小樓里,就緊挨著旁邊的馬路。巴菲特對這棟小樓確實不離不棄。巴菲特住房是美國住宅文化的一種縮影,在幾乎所有的美國小區,很少見有一道聳立的圍墻,小區道路一般不會太寬敞,雙向兩車道,社會車輛也可通行;即使是富人所在的別墅區,也是開放式的,屋門之外是自家草坪,自家草坪外就是馬路,最多是個綠化帶或低矮籬笆隔開。
韓國:開放小區亂停車,小心被貼條
韓國住宅區主要分為兩大類:獨棟住宅和公寓小區。老城區的住宅區大部分是獨棟住宅,這類住宅區實行街區制,一個區塊內有若干棟獨棟住宅,區塊周邊為公共道路。中國游客經常到訪的首爾北村韓屋村就是這種住宅區的代表。這種住宅區就是韓國的“洞”,洞的道路一般比較窄,如同樹枝般延展,但大多只能車輛單向通行。結束日本殖民統治及朝鮮半島光復后,韓國新建的住宅區也是如此,當時獨棟住宅占絕大多數。這類獨棟住宅過去一般是一層平房,墻內有庭院和植物,后來不少住宅不斷增高成了一棟棟小樓,但樓外的道路仍然是公共空間。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韓國1957年在首都地區的鐘巖洞建起第一棟公寓住宅樓。1962年開工興建的麻浦公寓是韓國首個住宅小區。之后隨著韓國經濟的騰飛,大量勞動力進入大城市,獨棟住宅已難以滿足需要,郊區出現越來越多住宅小區。
以現在首爾市東部的一山新都市為例。除部分新建獨棟住宅之外,新建的小區道路一般方方正正,“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每個街區一般為長寬在500米內,街區內即為一個小區的四個“團地”,有時街區一角也會建有幼兒園、公園等公共設施。團地內“管車不管人”,車輛進入需要登記領出入證,人員則出入自由,但每棟樓有電子門禁。在團地內的商業活動需要小區物業批準,不過餐館外賣和課外補習班廣告還是經常出現在各戶的門前,一般是掛在門把手或者用磁鐵吸在鐵門上,這種小廣告很容易清理,所以不招人討厭。
首爾市內一些獨棟住宅的聚居區正逐步面臨改造,這些住宅區被稱為“再整備區域”,過去的密集的獨棟住宅經過改造后變成一棟棟高樓,細密的道路也被小區內的道路取代,這些小區也是封閉式,但主干道不會被取消。當你進入首爾幾個開放內部道路的小區,這些小區外部沒有圍墻,門口沒有警衛,被當地人俗稱“鄉村巴士”的公交車在小區內穿行。有時,這些開放的內部道路也不好走,主要是占道停車現象嚴重,路被占去大半。在這樣的開放式小區停車也需要注意,如果是外部車輛長時間停車,小區物業會給車主點“教訓”——貼上很難清除的警告信。
新加坡:議員每月來家里聊天
很多討論稱,西歐國家包括美國等地多屬于人口少,土地多的狀況。但是中國的國情卻很不同。像中國內地這樣的高密度人口和住宅情況,或許從全球來說,只有新加坡,乃至中國香港情況類似,而它們的管理經驗或許可以借鑒。
在新加坡有政府組屋、公寓和執行共管的公寓(也由政府開發)這些類型。政府組屋是非封閉式的,而公寓(商業開發)和執行共管的公寓是封閉式。公寓類似于國內商品房概念。新加坡80%的人都住在政府組屋。這種政府組屋是非封閉式管理的,而且沒有保安。“我們住的樓里沒有保安,也沒有覺得需要保安。在樓道里都有攝像頭,一旦有可疑的人物,警察自然就可以發現。”
新加坡政府的社區管理措施很受市民歡迎,每個月都有議員會安排一兩個晚上跟居民直接對話。小區門口都會張貼出,議員與居民對話的時間和地點,所以如果居民有什么困難或者問題都可以直接告訴議員。有時候議員還會親自敲門入屋和居民聊天。新加坡也依然有居民區的概念,這點和國內類似。小的社區和國內一樣就叫居委會。這些居委會也就位于組屋區內,常常也是一群老人坐在里面或看電視或聊家常,又或者是一群人穿著同樣的T恤在組織活
印度:公共服務跟不上,街區臟亂差
多數印度城市的布局是街區制,以新德里核心區為例,各處道路平整、筆直,四通八達,而且多被綠茵覆蓋,不過道路旁的宅院主要是高官府邸。由于市政公共服務體系跟不上,新德里市區有很多街區呈現出一種混亂、無序的狀態。即使在高檔社區也有類似問題。例如新德里幾個“富人區”,這里一棟棟別墅都價值數千萬人民幣,除房主自住也會出租。雖說是“富人區”,但最大缺陷是內部道路狹窄,私家車和流浪狗太多。
在新德里舊有街區無從改造之際,新富階層看上古爾崗和諾伊達等衛星城,那里高樓林立,交通縱橫,每一個封閉式的小區都可被看成是印度現代化發展的模型。小區內數十層的塔樓連成排,地上地下車庫俱全,健身房、小賣部等各類服務設施齊備。但在新德里有不少新德里人死活看不上古爾崗或諾伊達,認為那里就是“孤島”,居民出行的軌跡就是駕車從小區駛向大商場,缺少大城市里人與人的親近感。可見,新德里以及印度多數大城市的交通都很糟糕,這不完全是街道設置的問題,與人口數量、機動車數量以及城市總體布局等都有關系。
日本:高高在上的大學敞開了大門
高校如何逐步“打開”也是大家關注的話題。日本高校的一些做法值得參考。日本很多大學過去都高度封閉,給人高高在上的感覺,現在則加強同周邊區域的良性互動。日本越來越多的私立大學開始傾向修建“無門”大學,一是由于地價昂貴,不得不分散院系;二是向歐洲名校學習,試圖把校園和整個街區融為一體。
早稻田大學素來以“沒有正門”著稱,西校區非但不見大門,甚至不見牌子,只有一尊早大創始人大隈重信的銅像。按照早大官方說法,此舉意為“學校向任何人都敞開大門”。由于地處東京城區,沒有足夠大的整塊空間,早大有些院系還分散在主校區周邊的住宅區里。再以名古屋大學為例,主校區被一條寬闊的公路隔開,社會車輛正常行駛,路上有紅綠燈,路邊是地鐵站、公交車站、郵局和銀行等公共設施。教授、學生和周圍居民你來我往。由于日本人很注意公眾場合保持安靜,因此,正常的教學不受影響。東京大學本鄉校區幾乎看不到圍墻和柵欄,各個院系的教學設施集中在一起,反而形成一個獨特空間,能和“外面的世界”明顯區分。
事實證明,推動街區制時會面臨很多操作性問題,關鍵在于不要搞短時期運動式推進。比如,打開小區,是為了通車還是為了步行更方便?如果是因為主干道車太多,而盲目把車流引進小區,恐怕也是很恐怖的一個場景。至于安全問題,從紐約、倫敦等城市來看,起主要作用的是單幢樓里的安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