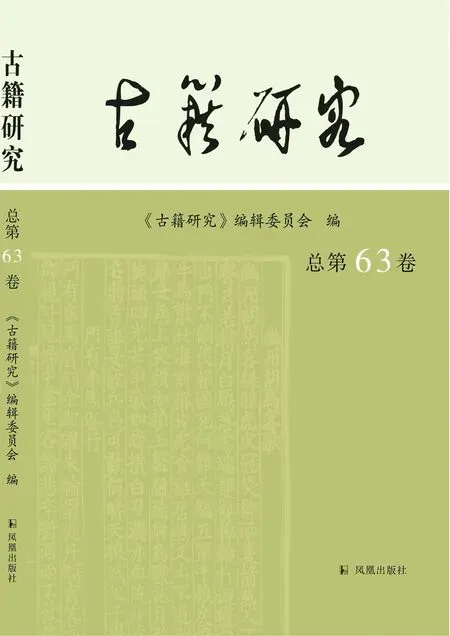空間、地域文化與文化觀念
——論班固的地域移動與《漢書》正統史觀的形成
楊 霞
(作者單位:安徽廣播電視大學文法學院)
空間、地域文化與文化觀念
——論班固的地域移動與《漢書》正統史觀的形成
楊 霞
《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同時也是一部“宗經矩圣”*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之《史傳第十六》,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70頁。、充滿正統思想的政治文本。“正統”本指血統純正,而后發展為一歷史政治概念,多指某一政權建立、存續的合法性。《漢書》以儒學為尊,以神化帝王之出生情境來附會“君權神授”論;以大量災異記錄來凸顯“災異譴告”說;強調等級制度,主張“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班固:《漢書》卷92《游俠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3697頁。;抨擊王莽代漢之舉,指出“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漢書》卷99下《王莽傳》,第4194頁。。——所極力呈現的正是“天乃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嚴可均:《全后漢文》卷26《典引》,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256頁。的政治信念,以證西漢政權的合法性,同時也意在說明光武政權乃西漢王朝的繼續與發展。這一政治立場鮮明的著作得到統治者的褒揚和推廣。“《漢書》一出,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范曄:《后漢書》卷40上《班固傳》,中華書局,1965年,第1334頁。。在其后歷代,“始自漢末,迄乎陳世。為其注解者,凡二十五家,至于專門受業,遂與《五經》相亞”*劉知幾撰、浦起龍釋:《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39頁。,——已然是史學正宗。
《漢書》由班彪、班固、班昭、馬續相繼成之:先是班彪“繼采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后傳》(即《史記后傳》數十篇)”*《后漢書》卷40上《班彪傳》,第1324頁。,乃《漢書》編撰之發軔期;班彪去世后,班固續修其業,自二十余歲始,前后歷時二十余年,在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此著;班固卒,班昭、馬續分別撰寫“八表”與《天文志》,正式完結此書。
作為《漢書》最重要、最主要的編寫者,班固本人的正統意識是《漢書》正統史觀的思想來源,而他本人濃厚的正統意識的形成,不僅與其學識、家學、時代有關,與其一生行跡也有大關聯。本文嘗試以班固的地域流動為考察對象,對其濃厚的正統史觀的形成作一論述。
一、 地域流轉:扶風故里與洛陽新都
(一) 班固一生行跡
班固生于光武帝建武八年(32),卒于和帝永元四年(92)。據《后漢書》記載以及有關學者的論述,可將班固一生行跡作大致歸納。其中,考慮班固入竇憲幕府發生在89年,而此前數年,也即章帝建初七年(82),班固已將《漢書》上呈朝廷,所以這里重點梳理章帝建初七年(82)之前班固的流動軌跡,大致若此:
1. 少居洛陽
光武帝建武十二年(36),河西大將軍竇融征還洛陽,“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余兩,馬、牛、羊被野”*《后漢書》卷23《竇融傳》,第807頁。。后光武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由這兩則材料可知作為竇融從事的班彪攜家屬一同至洛。《后漢書·班固傳》記載“(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又《后漢書·崔骃傳》記載“(骃)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可知班固一度受業于太學。
2. 丁憂安陵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卒。班固返回扶風安陵,為父丁憂。其間,“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后漢書》卷40上《班彪傳》,第1333頁。。
3. 陷京兆獄
在安陵期間,“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后漢書》卷40上《班固傳》,第1334頁。。時間約在漢明帝永平五年(62)或稍前一段時間。
4. 重返洛陽
漢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弟班超“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關于班固何時除蘭臺令史,可參見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392頁。。此后班固常居蘭臺,觀書、修史、論難、編書。直至漢章帝章和元年(87),班固因丁母憂再返故里扶風安陵*關于班固丁母憂返回扶風的時間,可參考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之分析。。次年十月,“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與參議”*《后漢書》卷40下《班固傳》,第1385頁。。
綜上可見,班固一生大部分時間居于京都洛陽,次為扶風安陵故里。因此,洛陽與扶風也就成為了我們研究班固思想的空間背景。
(二) 學術發達的扶風安陵
班氏本為楚國貴族,“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后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今山西、河北一帶),“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樓煩”(今山西雁門一帶)。西漢成帝之初,班氏“徒昌陵。昌陵后罷,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漢書》卷100上《敘傳》,中華書局,1962年,第4197-4198頁。。王莽之世,班彪一代徙居扶風安陵,安陵也就成為班固的故邑所在。
扶風所在的三輔地區,一直是西漢的學術、政治中心,眾多名士出入此間。至東漢之初,該地域學術實力依舊不衰。據盧云《漢晉文化地理》推測其時三輔士人在京師者就有六百人左右*盧云:《漢晉文化地理》,陜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頁。。這一時期、這一地域還有一位重要文化人物,即“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余萬言”、被“學者宗之”*《后漢書》卷36《賈逵傳》,第1240頁。的經學大師賈逵。
而作為班固本籍的扶風安陵是三輔地區文化最為發達的郡縣之一。三輔地區以長陵、安陵、陽陵、武陵、平陵五縣最為發達,“五縣游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蕭統編、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卷2《京都賦》李善注“五陵”,中華書局,1987年,第52頁。。安陵縣學術之發達由此可見一斑。
班固所在的班氏家族更是為故邑文化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西漢成帝時期,班氏就有班伯、班斿、班稚以學行馳名于世。班伯少受《詩》于師丹,后師從其時著名經學家鄭寬中、張禹學習《尚書》《論語》。班斿博學有俊才,以對策為議郎,曾與劉向共同校書,成帝賞其才華,賜書于他;其子班嗣是當時著名學者。班稚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性格“方直自守”。班彪是班稚之子,其從小好古敏求,“幼與從兄嗣共游學”。正如班固所總結兩漢之際的班氏“家有賜書,內足于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云以下莫不造門”*分別見《漢書》卷100上《敘傳》第4203、4205、4205頁。。而班固留居故里之時,州郡之中更有“宿儒盛名,冠德州里”的故司空桓梁、“好古樂道、玄默自守”的京兆祭酒晉馮、“廉清修絜、行能純備”的扶風掾李育等名士*《后漢書》卷40上《班固傳》,第1331-1332頁。,且與班固相熟、相善。
(三) 名士聚集的京都洛陽
班固幼時因父職而得以居于洛陽,三十歲因禍得福返回洛陽。此后至章和元年(87)復歸故里丁母憂止,班固都生活在洛陽。
就在此間的幾十年里,洛陽學術在光武、明、章三帝王的倡導下獲得極大發展。先有光武“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的文化感召,四方名士云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次有漢明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的躬身示范,以致“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再有漢章帝召集諸儒集于白虎觀,論定《五經》異同,數月乃罷。
在最高統治者的大力推動下,儒學昌盛一時,眾多名士宿儒由四方匯聚京城,連“朝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匈奴亦遣子入學”。就班固自身經歷而言,早在少時,他便與傅毅、崔骃、李育、王充等同在太學*分別依據《后漢書·崔骃傳》“(骃)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同時齊名”、《后漢書·儒林列傳》“(育)知名太學,深為同郡班固所重”、《后漢書·班固傳》李賢注“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置身蘭臺后,先“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又與賈逵、楊終、孔僖等經學大家相交*可參見梁宗華《班固師友交游考》中對班固與賈逵、楊終、孔僖交游的考論,《齊魯文化研究》第12輯。。
綜上,班固無論身在故里還是京城,都浸潤于濃厚的儒學之風。特別是居于洛陽之時,他與上層關系密切,更是自覺、不自覺地受到正統儒學帶來的全面沖擊。
二、 心境變遷:從囹圄到朝堂
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固因父喪丁憂故里,開始致力于父親班彪未竟的修史事業。建武中元二年(57),光武帝崩,明帝即位,其弟東平王劉蒼以至親身份拜驃騎將軍輔政,并“開東閣,延英雄”。班固借此良機作《奏記東平王蒼》,向劉蒼推薦桓梁、晉馮、李育、郭基、王雍、殷肅六位“有殊行絕才,德隆當世”的名士。從奏記主要內容來看,這是身在故邑的班固向朝廷推薦賢達,而仔細體會,可發現,這又是班固的一封自薦書。在奏記開篇,班固自言“幸得生于清明之世”,因而“私以螻蟻,竊觀國政”,在文末更殷切希望劉蒼“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荊山、汨羅之恨”,表達了自己不愿歸于塵土,欲發奮有為的士子情懷。然而,劉蒼閱后,對班固推薦的名士“納之”,卻沒有將班固一并延攬*《后漢書》卷40上《班固傳》,第1330-1333頁。。
欲有為政治而自薦不成的班固轉而繼續漢史編寫工作。漢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人告發私改國史而收系于京兆獄。有關班固下獄時的心情,我們無法從現存文獻中覓得。但觀其先前“竊觀國政”以為朝廷士的遠大理想到突然淪為階下囚的殘酷現實的巨大反差,我們大約也可以想象班固此時的驚恐之狀。此后,經班超陳其意、州郡上其書、明帝奇其才,班固非但沒有罹禍,相反被朝廷召至蘭臺,自此開啟長達二十余載的洛陽仕宦生涯。
入洛后,班固相繼得到明帝、章帝賞識。他不僅奉明帝詔令參與編撰《世祖本紀》《列傳》《載記》,還得以繼續修撰西漢歷史;章帝雅愛文章,班固更加得幸,“數入讀書禁中,或連日繼夜。每行巡狩,輒獻上賦頌,朝廷有大議,使難問公卿,辯論于前,賞賜恩寵甚渥”*《后漢書》卷40下《班固傳》,第1373頁。。
細觀班固安陵自薦、京兆下獄、洛陽得意的行跡,再仔細體會其時心境后,就不難理解班固在《漢書》中“光揚大漢”的用心與努力了。這種用心與努力不僅是大時代儒風熏染、家學傳承、自身學識的驅動,也來自班固獨有的經歷。作為一個博貫載籍、入仕無門,且一度身陷囹圄、有性命之憂的普通士子,在其因才華獲得帝王肯定而逃出生天,并由此進入仕途且一路恩寵有加后,他的才華也就要得到最大程度地展現了——于史家班固而言,這種才華在《漢書》中得以充分發揮。前文已提及,班固修史,本因其父“所續前史未詳”而欲補充完善之,也就是延續《史記》體例,將其未竟的漢武帝太初年間后的歷史補充完畢。而后經過入獄、赦免、征召等一系列事件之后,班固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他認為“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當可獨立一史”*《初學記》卷21《史傳第二》,中華書局,1962年,第503頁。,將漢劉地位從“百王之末”提升到“獨立一史”,或許正是班固有感知遇之恩而作出的一份最有力量的擁漢宣言。正如他在《典引》(序)中的心跡自陳,“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最深,誠思畢力竭情”以“啟發憤懣,光揚大漢,軼聲前代”*《全后漢文》卷26《典引》,第256頁。。
三、 成書洛陽:官修與私撰
《漢書》濃厚正統史觀的形成,與其成于洛陽這一地域也是分不開的。作為政治中心、學術中心的洛陽對《漢書》的成書意義重大。
東漢政權是作為西漢政權的延續而存在的。所謂“光武中興”之“中興”,正是越過王莽新朝對西漢劉氏所作出的呼應。東漢定都洛陽后,“更以河南郡為尹,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后漢書》志27《百官四》,第3614頁。。東漢歷代皇帝也多有“巡幸長安”之舉。光武帝先后六次“幸長安”,明帝、章帝、安帝、順帝、桓帝也至長安謁高廟。這些都意在說明兩漢政權的延續性。
就《漢書》成書的東漢初期而言,經過了王莽代漢這樣一段插曲,東漢初期的政府更需要采用各種舉措來論證、宣揚漢室的正統地位。西漢后期,社會上流傳“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漢書》卷75《李尋傳》,第3192頁。的預言,王莽也正是依據于此得到士人群體支持,從而順利代漢。有鑒于此,東漢政府一直都重視史書的編撰,重視書籍中的輿論導向。從與班固同時代的同郡士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后漢書》卷40上《班固傳》,第1334頁。事件就可知當時政府對不同言論的警惕與控制。故當有人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朝廷即收捕其人、盡取其書,足可見上層對士人思想動向的重視。
其后班固被釋的最主要原因是班超向明帝澄清“固所著述意”。關于班固的著述之意,史書有載:“以彪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究,欲就其業。”——僅作完善而已。而班彪著述之意,是有感于前人所續《史記》“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更有“褒美偽新”之作(如揚雄、劉歆的撰述),“誤后惑眾,不當垂之后代者也”*《史通通釋》卷12《古今正史》,第338頁。。因此,班彪著述的根本意圖在于矯正視聽,更是忠于漢室之舉。因此,與其說,“顯宗奇之”,感嘆的是班固的才華,不如說,是班固父子對漢室的忠誠打動了明帝。
即使班固被明帝奇之,并召至洛陽為蘭臺令史,也并不是立刻開始了續寫《漢書》的進程。班固先是參與編撰《世祖本紀》,后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在這些完成之后,明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即《漢書》。這里,我們或許可以將班固續西漢史之前先撰東漢史這一過程視為東漢政府對他的再一次考察。《漢書》也就此完成了私撰到官修的性質的轉變。官修史書打上了國家意志的烙印,正統性得以大大提升。
四、 見賢思齊:王充與班固
班固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結識的士人對他的正統意識的形成也有影響。前文已經提及的與班固有交集的洛陽名士,如同在太學的崔骃、傅毅,共撰史書的陳宗、尹敏等。在諸多名士中,王充與班固的關系值得探究一番。
王充,會稽上虞人。少游太學,師事班彪。學成后“歸鄉里,屏居教授”*③ 《后漢書》卷49《王充傳》,第1629頁。,著有被后世譽為“奇書”的《論衡》一書。該書以“疾虛妄”為宗旨,大力宣揚天之無為、譴告之繆和祥瑞之虛,似與當時政府所極力宣揚的正統儒學思想格格不入,與班固所秉持的正統思想就更是“道不同”了。而事實上,班固、王充彼此相熟。并且,二人有諸多相通之處:
兩人年齡相仿:班固生于32年,卒于92年;王充生于27年,卒于97年。二人有共同的時代背景,也有足夠漫長的時間來維系這自少年時代就開始的同學情誼。
兩人同在洛陽:班固幼時因父至洛,時間大約在36年;王充于44年游學洛陽,投于班彪門下。兩人又分別于54年、59年離開洛陽*有關王充離洛時間,可參看劉躍進《秦漢文學編年史》,第384頁。。兩人同在洛陽的時間從44年至54年,有十年之久。這十年時間,也正是二人學業有成、思想日趨成熟的重要時期。
兩人學術背景相同:班固“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受學于班彪;王充則直接師承班彪。
兩人治學態度相似:班固“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不為章句”;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③。
兩人至少還有一個共同的朋友:會稽謝夷吾。明帝永平十八年(75),班固作《為第五倫薦謝夷吾疏》,代第五倫向朝廷推薦謝夷吾,贊其“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全后漢文》卷25《為第五倫薦謝夷吾疏》,第244頁。;而謝夷吾不僅與王充同在一郡,兩人更是好友。謝夷吾曾上書力薦王充,稱“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揚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全后漢文》卷29《上書薦王充》,第296頁。。
此外,王充“為人清重,游必擇友,不好茍交”*黃暉撰、劉盼遂集解:《論衡校釋》卷30《自紀篇》,新編諸子集成本,中華書局,1990年,第1190頁。,卻對班固贊賞有加,曾預言班固“必記漢事”*⑩ 《后漢書》卷40上《班固傳》,第1330頁。,日后也多次贊美班固“名香文美”*《論衡校釋》卷13《別通》,第602頁。,“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論衡校釋》卷13《超奇》,第615頁。,有大國氣象。同時,班固“性寬和容眾”⑩。因此,兩人成為密友可能性極大。
那么,如何解釋《論衡》《漢書》不同的思想呢?后世多因王充在《問孔》《刺孟》《異虛》《自然》《亂龍》等篇中質疑圣人、批判災異譴告的言論而將其放置在與同一時期官方意識形態對立面。而事實上,細觀《論衡》,可發現王充對劉氏政權多有溢美之辭。特別在《宣漢》篇中表示要“高漢于周,擬漢過周”,而作《恢國》目的竟是“論漢國在百代之上”,甚至于前文說“鳳凰麟龍皆謂不足為世瑞”,而后文“揚厲漢家之功德則又備著其佳祥”*王洲明:《中華大典文學典·先秦兩漢文學分典·漢文學部》,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187頁。。可見,王充并非對東漢政權不滿,更不是質疑其政權的合法性。相反,他認為“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論衡校釋》卷19《宣漢篇》,第818頁。。由此可見,王充也是擁護劉氏政權的“正統”士人。這一點,也可從王充晚年被謝夷吾推薦于朝廷,而“肅宗特詔公車征”的禮遇可知:漢室未曾將王充視為異類,而王充也從來就不是漢室的反對者。
綜上所言,作為班固密友的王充非但沒有影響班固的判斷,反之,兩人在“頌揚漢德”的深層思想與具體文章層面都達成了根本性的一致。
五、 田野派與學院派:司馬遷與班固
班固《漢書》是西漢一代歷史,起自漢高祖元年(前206),終于王莽地皇四年(23)。司馬遷《史記》是通史,其中西漢部分止于漢武帝太初年間。兩部史著從漢高祖到漢武帝時代重合。《漢書》對這一時段的撰寫,大部分借鑒了《史記》,但同樣由于正統史觀的影響,即使是同一時間、同一人物、同一事件,仍然表現出不同的態度與傾向。比如,對屈原的態度,對游俠的態度,包括高祖劉邦的出生的情景描述等。有關司馬遷與班固著史的同異之處及其原因,學界已有很多成果論及。這里僅從二人的游歷來看兩部史著的成書及其中的差別。
首先,兩人自身游歷不同。
司馬遷少時耕于河山之陽,及長,游學于長安,先后師從大儒伏生、孔安國、董仲舒。弱冠之年,司馬遷開始漫游全國,先后“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司馬遷:《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中華書局,1963年,第3293頁。。同時,在對自然山水的考察中,司馬遷對富含文化氣息的歷史人文地理也給予了極大關注,比如,“秦漢之際,兵所出入之途,曲折變化,唯太史公序之如指掌。……蓋自古史書兵事地形之詳,未有過此者。太公胸中固有一天下之勢,非后代書生之所能及也”*顧炎武:《日知錄》卷26《史記通鑒兵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431頁。。在游歷中,司馬遷又結識了不少士人,由此得以耳聞目見諸多史實,而非盡取自于書。
進入仕途后的司馬遷依然游歷不止。其間,除去曾“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第3293頁。之外,又多跟隨漢武帝巡行郡縣、東巡封禪、祭祀五帝,曾“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浮江淮”*《史記》卷1《五帝本紀》,第46頁。。從元狩五年司馬遷出仕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漢武帝最后一次封禪泰山止,司馬遷更隨武帝36年,巡游26次。
相對司馬遷一生豐富的地域流動,班固的學習于太學,仕宦于蘭臺及幕府的經歷就稍顯單薄。特別是當其處于蘭臺期間,一方面,蘭臺所秘藏的皇帝詔令、臣僚章奏、國家重要律令、地圖、郡縣計簿與各種書籍為班固撰寫西漢史實提供了最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但同時,也將班固禁錮于文獻之中,以致對文本之外的各地域的山川風物、百姓民生等自然地理與歷史人文地理接觸較少。這種地域流動的差別會導致二人的視野有差、心態有別。司馬遷更有歷史縱深感,也更有全局眼光,特別是他還身處國力強盛、意氣風發的漢武時期。“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著述理想是這樣大的時代背景下,個體士人通過廣泛游歷而開闊眼界、增益見聞的產物。
其次,兩人對“游”的態度也有差別。
可以《史記·游俠列傳》和《漢書·游俠傳》作對比。在司馬遷陛下,游俠“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史記》卷124《游俠列傳》,第3181頁。。更甚者,司馬遷游歷時還曾與燕趙豪俊交游,因此宋代蘇轍評之以“其文疏蕩,頗有奇氣”*陳宏天、高秀芳點校:《蘇轍集》卷22《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華書局,1990年,第381頁。。相反,班固對游俠則持否定態度。班固所謂的游俠中包括“學經傳”、“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的樓護,包括“略涉傳記,贍于文辭,性善書”的陳尊。可見班固所謂的游俠有的具有相當高的文化修養,與我們今天說到的東漢流動之士并無本質不同。班固認為游俠促成了“背公死黨之義成,守職奉法之義廢”的不良習氣,同時,更是對等級制度的沖擊,“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其上,而下無覬覦”。而類于游俠郭解等人,“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僭越之舉,“罪已不容于誅矣”*分別見《漢書》卷92《游俠傳》,第3706、3711、3697、3697、3699頁。。
司馬遷之寬容、班固之批判,兩者態度的不同,還是要回到開始說的第一點,即與二者的自身游歷有關。司馬遷有豐富的游歷經驗,且是主動出行,結交名士、感受風俗,他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普通民眾,也因此對很多正統史家所不能理解之事懷有深沉的“理解之同情”。而班固自十余歲游學洛陽,后又入蘭臺、校書籍、參加白虎觀會議,傾聽各位大儒講解五經異同,奉命撰寫《白虎通德論》,親身參與儒學讖緯化的改造——接收到的都是正統的儒學思想。觀兩位行跡所至,可以說,司馬遷走的是一條田野派的路線,而班固則是正統的學院派士人。
結 語
正統史觀經由班固系統、具體地呈現于《漢書》這部史學名著之后,遂成為后世撰修史書的重要法則,《漢書》也被后世史學奉為“不祧之宗”*章學誠:《文史通義》卷1《內篇一·書教下》,上海書店,1988年,第14頁。。而這一正統史觀的形成又與作者所處時代有關,與作者在這一時代中的地域流轉、心境變遷有關。就班固而言,其一生所至之地域,儒學大行其道,儒者環于四周,原本承襲其父志,后又得遇于明帝,因此,其正統史觀之形成,既是國家意志之體現,卻更是作者個體地域流轉、情感浮沉、思想也隨之漸趨成型的必然產物。
(作者單位:安徽廣播電視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