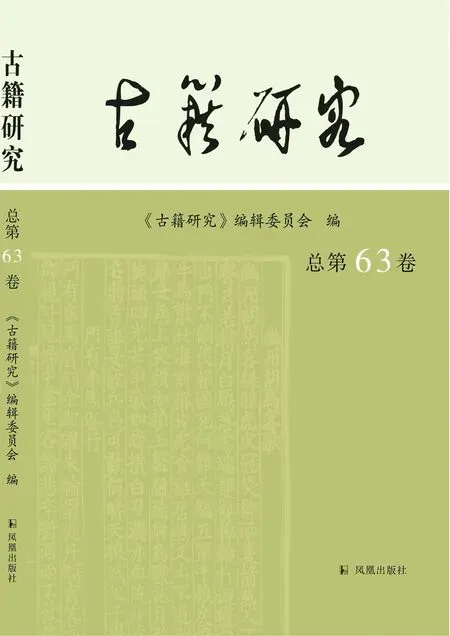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的作者從屬
魏耕原
(作者單位:西安文理學院人文學院、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學術叢札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的作者從屬
魏耕原
《飲馬長城窟行》是建安詩歌的名篇,亦是陳琳最負盛名的代表作。徐陵《玉臺新詠》卷一收有兩首以此為題的同題詩,一是蔡邕“青青河邊草,綿綿思遠道”一首,一是陳琳“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一首。徐公持先生《魏晉文學史》詳慎嚴謹,論及陳琳此詩,認為“作者問題,頗存疑問待考”,態度很審慎。又在該節之后有一長注作了周詳審慎的考證,所得結論,“此歌辭應是樂府古辭”*徐公持:《魏晉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23、132頁。,而非陳琳所作。
其依據可撮述以下幾點:
一、 此詩始見于《玉臺新詠》,不見于《宋書·樂志》。而徐選鑒別不精,所收“枚乘雜詩”“蘇武詩”等,皆甚淆亂。收錄蔡作此首,《文選》卷二十七署名題作“古辭”,《樂府詩集》亦同。也有兩可其說,如《樂府解題》曰:“古詞……或云蔡邕之辭。”《文選》《玉臺新詠》成書幾乎同時,編者蕭統、徐陵關系亦頗親近,出現此種捍格,難以解釋。
二、 此詩用語質樸,以及所采用的對話與雜言,皆顯示漢樂府古辭與民歌之本色。其產生的時間應早于《古詩十九首》(漢末桓、靈間),而與前期漢樂府民歌如《戰城南》《孤兒行》等接近,以之署為漢末建安文人陳琳名下,顯然不當。
三、 今存陳琳《游覽》二首、《宴會》,包括失題詩及逸句,全為五言之作。且用語典雅,重詞采與駢偶,文人化色彩很重,不似此詩渾樸自然,故此詩非出于一手。
四、 漢樂府古辭,一般篇首語句與樂曲名相合,幾無例外,依此可作為判斷是否樂府古辭之規律,不合者則為后之擬作。據此則“此歌辭應當是樂府古辭”。
五、 楊泉《物理論》:“秦筑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撐拄。’其冤痛如此。”此四句“民歌”,亦見于此詩,故此詩確為樂府古辭。楊泉上距陳琳僅二三十年,不應誤指陳琳之作為“民歌”,這比后此二百余年徐陵之說更可靠。
以上分別從出處,二者之風格,以及樂府古辭曲名與首句相合之規律與民歌之關系,提出問題。問題本身提得極好,使我們對長期以來忽而不察的問題引起注意,特別是把樂府古辭與曹魏擬樂府的區別,提到詩論與詩體的規律范疇,就非常具有學術見地。徐先生的論據周詳,很能啟發對問題的進一步思考。
首先,由于東漢末年至唐初,社會動亂四百多年,文獻散失極為嚴重,以致作品作者從屬混亂。徐選與《文選》都有舊題蘇武詩,后者還有舊題李陵詩。《文選》所收的《古詩十九首》,徐選則題為枚乘。雖然《飲馬長城窟行》“青青河畔草”一首徐選題作蔡邕,而蕭選視為“古辭”,“河畔”作“河邊”;同題“飲馬長城窟”一首,蕭選未收,而《樂府詩集》卷三十八亦作陳琳。郭茂倩題解說:“一曰《飲馬行》。長城,秦所筑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古辭云‘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言征戍之客至于長城而飲其馬,婦人思念其勤勞,故作是曲也。”所引《水經注》言秦筑長城,“民怨勞苦,故楊泉《物理論》曰:‘秦筑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脯。不見長城下,尸骸相撐拄。”’其冤痛如此。今白道南谷口有長城,自城北出有高阪,傍有土穴出泉,挹之不窮。《歌錄云》:‘飲馬長城窟。’信非虛言也。”又引《樂府題解》曰:“古詞,傷良人游蕩不歸,或云蔡邕之辭。若魏陳琳辭云‘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則言秦人苦長城之役也。”*(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2冊,第555頁。郭茂倩謂古辭為“婦人思念其勤勞”,則為婦人作或為代言體而出之婦人語氣。符合徐選所題蔡邕一首的內容與語氣。楊泉《物理論》所引“民歌”,可見當時筑長城之苦者,非止一首。而據此為“民歌”,不能斷言此四句即屬《飲馬長城窟行》中歌辭,亦不能謂陳琳一首即屬“民歌”古辭。因為民歌四句全為五言,而陳琳詩此四句的前二句與民歌相同,而后二句改作七言:“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我們知道建安詩人樂于取法民歌,曹操《短歌行》兩次以《詩經》成句六句入詩,曹植《野田黃雀行》即取法民歌與禽鳥寓言以言自家處境,阮瑀《駕出北郭門行》亦為取法漢樂府之著例。所以陳琳很有可能把五言四句“民歌”引之入詩,并改動后二句為七言。吳景旭《歷代詩話》卷二十四即言“孔璋乃用其時之諺語也”。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七亦言“‘生男’四句用古歌辭”。
《樂府詩集》所引《樂府題解》已失傳,而北宋初《崇文總目》已載其書,未著撰人姓氏,并言與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所余二卷《樂府古題》頗同。《四庫全書總目》“樂府古題要解”條說:“今考郭茂倩《樂府詩集》所引《樂府題解》,自漢鐃歌《上之回》篇始,乃明題吳兢之名,則混為一書,已不始于近代。然茂倩所引,其文則與此書全同,不過偶刪一二句,或增入樂府本詞一二句,不應互相剿襲至此。疑兢書久佚,好事者因《崇文總目》有《樂府題解》與吳兢所撰《樂府》頗同語,因捃拾郭茂倩所引《樂府題解》偽為兢書。”*(清)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下冊,第1796頁。由此可知《樂府題解》至晚為北宋前著作,或許與吳兢同時。據郭氏所引該節把《飲馬長城窟行》分為兩種,一是“古詞”,內容為“傷良人游蕩不歸”,即“青青河畔草”一首,并謂此辭已有兩屬之說。“或云蔡邕之辭”,可能指徐選而言;二是“飲馬長城窟”一首,內容為“言秦人苦長城之役”,并謂為陳琳所作。可見由徐選以及《樂府題解》至《樂府詩集》,均認為是陳琳所作,著錄有序,而非蔡邕一首已有兩屬歧說。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陳琳序》謂“袁本初書記之士,述喪亂事多”。就陳琳詩而言,除了這首《飲馬長城窟行》外,則無“述喪亂”事,明清古詩選本凡入此詩者,均視為陳詩而無異詞。明人張溥說:“孔璋賦詩,非時所推。……詩則《飲馬》《游覽》諸篇,稍見寄托,然在建安諸子中篇最寥寂。”*(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陳記室集題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75頁。宋長白說:“《文選》作古辭,《玉臺》謂蔡中郎作。……陳孔璋亦有此題,以長短句行之,遂為鮑照先鞭。思王所謂‘鷹揚于河朔者’,良不誣也。”*(清)宋長白:《柳亭詩話》卷十四“飲馬長城窟”條,見河北師范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研編《三曹資料匯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04頁。沈德潛《古詩源》卷六:“無問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與漢樂府競爽矣。”*(清)沈德潛:《古詩源》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129頁。張玉谷《古詩賞析》卷九說:“此傷秦時役卒筑城,民不聊生之詩,比漢蔡中郎作為切題矣。”*(清)張玉谷:《古詩賞析》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15頁。又謂“生男”四句“語本漢語,神理恰合”。以上就其出處與楊泉所引民歌以及與陳詩之關系看,似均為陳琳所作。
其次,就此詩與陳琳其他詩的語言風格看,確實差異很大。其懸殊之大出于兩個原因,一是《飲馬》敘民不聊生,自然要用語質樸,切合役卒村婦之語;而現存陳琳詩四首,除《飲馬》外,則是《游覽二首》與《宴會》,全為歸曹后在建安文學集團中所作公宴游覽詩,題材不同,所用語言自然有所區別。如曹植《送應氏》二首,其一言洛陽之荒蕪,其二敘寫餞別的宴會,語言亦成兩樣。如以其一與《美女篇》《名都篇》相較,差別則更大。所以詩人則根據不同場合采用不同語言,原本為情理中事。如杜甫的《麗人行》與“三吏”“三別”語言華飾與質樸差異就極為懸殊。此亦為相題所宜,為題中應有之義。陳詩的高人雅士宴游的雅言與役卒民婦間瑣語,二者間的差異,并不詫異。至于采用對話體與雜言,則屬漢樂府古辭與民歌本色。其實此與語言風格屬于同一道理。同屬建安七子的阮瑀《駕出北郭門行》語言質樸,同樣采用對話體,同樣與阮瑀其余詩的風格亦有與文士語的差異。然不能據此,就認為《駕出》詩應為漢樂府古辭,而非屬阮瑀之作。
再則《飲馬》是由五言與七言兩種句式組成,整齊中略有變化。若從長短不齊的雜言看,倒應不屬于漢樂府。漢樂府雜言詩,這類詩一般句式變化較大。如徐先生所舉的《戰城南》《有所思》為三、五、七言,還有《婦病行》為二、四、五、六、七、八言,《雉子斑》與《孤兒行》為二、三、四、五、六、七言,《蒿里》為一句五言,三句七言,《薤露》兩句三言,兩句七言。還有不少名作,如《陌上桑》《十五從軍征》《上山采蘼蕪》《孔雀東南飛》等均為五言詩。像《飲馬》這樣以五、七言交錯的長篇,在漢樂府里幾乎找不到一首。如果從句式的角度看,五七言交錯至28句,變化又極其自然,甚至在對話中省去問答者,而安頓井然浹切,明顯取法于漢樂府民歌的對話與雜言,以此結構成篇。
此詩當為陳琳在河北袁紹時期所作,或身臨長城,或所聞長城事,有所感觸而成篇。寫民間哀怨事,自然取法漢樂府諸種手法。他本是廣陵射陽(今江蘇任安東南)人,此種題材對于來自南方的作者本有特別的激發。加上長期飄蕩,其中也不無多少有些自家處于亂離的感受。而投曹以后,建安諸子包括曹丕兄弟的公宴游覽詩均為五言,所以陳琳另外三首自然也會成為五言。陳琳集在《隋書·經籍志》里著錄為三卷,兩《唐書》的《經籍》《藝文》志與《宋史·藝文志》均為十卷,但到了明人張溥所輯《陳記室集》僅余一卷。大約在元代前后亡佚過甚。所以《樂府題解》的作者與南宋的郭茂倩都有機會看到十卷本的陳集,故把《飲馬》稱為陳琳所作,一定是有所根據的,不僅是出于徐選的原因。
再次,徐注提出了頗引發興趣的樂府古辭與后人擬作區別的規律:“若歌辭內容特別是首句語辭與曲名相合,此歌辭即為古辭;若二者不合,此歌辭即非古辭,而是后人擬作歌辭。”*《魏晉文學史》,第132頁。據此徐選“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其曲名正與歌辭內容相合,此歌辭首句正作“飲馬長城窟”。所以,非陳琳所作,應當是樂府古辭。這種規律與詞的早期詞牌與內容相同很有些接近。漢樂府確實有這些規律,但也有例外。如著名的《陌上桑》內容與曲名相合,但開首“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與“陌上桑”曲名并不相合。《白頭吟》開頭的“皚如山上雪,皎若云間月”,亦屬這種情況。《長歌行》開頭“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晞”,另兩首亦與此同,均與題目不合。還有《善哉行》開頭為“來日大難,口燥唇干”,《隴西行》開頭“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以及《步出夏門行》《折楊柳行》《上留田行》《雁門太守行》《艷歌何嘗行》《艷歌行》《怨歌行》《梁甫吟》《滿歌行》《傷歌行》《咄昔歌》等,均屬于首句語辭與曲名不相合,然均為古辭。由此可以發現,一般來說,敘事性的詩首句則與曲名相合,而不相合者大多是言情之制,當然,這只是個大概情況,不能視為絕對。如《陌上桑》為敘事詩,首句即與曲名不合。至于擬作也有往往首句與曲名相合,如《戰城南》,吳均、張正見、劉駕等作即是如此。若以徐先生所提出規律看,《飲馬》古辭“青青河畔草”一首無論首句與內容均與長城無關,倒應是擬作了,而陳琳一首首句與內容全與曲名相合,反倒成了古辭。梁啟超曾對陳琳此詩說:“此一首純然漢人音節,竊以此為《飲馬長城窟》本調。前節所錄‘青青河畔草’一首,或僅是繼起之作。辭沉痛決絕。杜甫《兵車行》不獨仿其意境音節,并用其語句。”*梁啟超:《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見陳引馳編《梁啟超學術論著集》文學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2頁。明人陸時雍也有懷疑,然意見卻很相反:“輕飄矯捷,似不類建安體裁。剖衷瀝血,剜骨錐心,遂作中唐鼻祖。”*(明)陸時雍:《詩鏡總論》卷六,見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0冊第10678頁。嚴羽《滄浪詩話·詩體》有建安體,陳琳此詩與阮瑀《駕出北郭門行》,以及王粲《七哀》其一,均可謂非建安體,因為都是作于未歸曹魏之前,而有自家的真性情在,尚未受到建安文學集團的影響。陳琳此詩風格就決絕與矯捷看,則與他的檄文頗為接近。
總之,我們覺得徐先生提出的疑問與考察,很具有學術眼光與價值。問題本身倒不在于結論的正確與否,而在于問題本身所涉及的學術價值。其中必須對漢樂府古辭與擬作各自特點做深入審察,更重要的是使我們注意到建安諸子在歸曹之前與身列建安文學集團以后的創作有何變化,引起我們由平面靜態的觀察層面,深入到變化的動態審視比較角度,真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徐先生的態度很謹慎,只在《魏晉文學史》正文提出疑問待考,而考據僅列入注文,所提問題與結論又從以大觀小的角度去論證,這些都讓人欽佩。至于我們的討論就所涉及的學術維度,作了進一步的思索。當然結論并不一定正確,換句話說徐先生疑問與結論并不一定錯誤。因為都是在沒有最為直接的《陳琳集》十卷本情況下,作為情理性推測。既是屬于推測,其間出入的空間就大得多了,橫嶺側峰,或者視朱為碧,都有可能。
最后附帶一提,徐先生的《魏晉文學史》厚重翔實,對問題的討論深入而又謹慎。另外,他又是敢講肺腑之言的長者。他為吳云主編的《建安七子集》所寫序言,就覺得真切感人,每讀一次都會引起共鳴與感慨。
(作者單位:西安文理學院人文學院、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