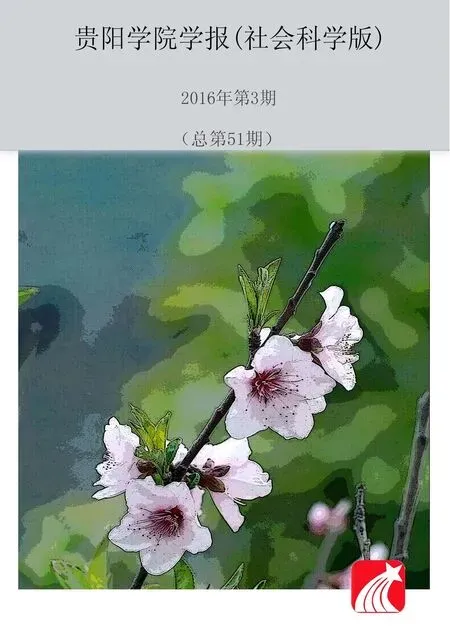合內外之道—吳澄的“知行兼賅”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比較*
吳立群
(上海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上海 200044)
?
合內外之道—吳澄的“知行兼賅”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比較*
吳立群
(上海大學 社會科學學院,上海 200044)
知行觀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內容。儒家知行觀以“性”與“天道”為中心論題。成圣如何可能以及如何成圣成為知行觀的關注焦點,知行問題由此而來,并因此與心性論、工夫論緊密相聯。吳澄與王陽明的知行觀首先從格物致知說展開。吳澄的格物致知說主要針對朱學之失而發,強調以陸學之長補朱學之失,并以內外合一為其理論前提闡發“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的觀點。王陽明則明確指出,析心與理為二是朱熹錯解格物致知的根本原因,以“心即理”觀之,格物致知無內外之分。二人均以內外合一之道闡明格物致知,所見略同。關于知,吳澄以“本心之發見”為“知”,并認為知是在實踐中獲得的,知而不行,仍是未知。在以“實悟為格,實踐為誠”論知行關系之后,吳澄提出了“知行兼賅”的主張。王陽明則指出,知行工夫本不可離。他首先闡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進而提出知即行,知行合一,并以知—行—知的動態展開過程說明知行如何獲得統一。在王陽明那里,知行合一是一個動態展開的過程。在從自在之知到自為之知,從本然之知到實然之知的過程中,知行合一得以完成。在知行關系上,吳澄和王陽明均認為知行不相離,并視知行合一為動態統一的過程。
吳澄;王陽明;“知行兼賅”;“知行合一”;動態統一
知行觀是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內容。對于儒家哲學而言,知行問題主要并非認識和改造外部世界,而是更多地表現為道德認知和道德實踐的關系問題(知識論),并與道德實現的根據(心性論)以及道德實現的途徑(工夫論)相聯系,其最終目的在于成就理想人格,完成對“道”的體認和把握,在人道與天道的貫通中實現儒家的社會理想及人生意義。換言之,儒家知識論仍不離“性”與“天道”。知識論與心性論、工夫論緊密相聯。
一、儒家知行觀特征及宋明時期論爭焦點
自《尚書》提出:“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尚書·說命中》)的思想以來,知行關系問題成為中國歷代儒家學者的重要論題之一。在儒家那里,“知”總是與“道”相聯系(知道)。儒家的價值目標是成人,其最終目標是成圣。儒家認為,理想人格不僅表現為內在的德性,更需要外化為具體的行為。因此,成圣如何可能以及如何成圣成為知行觀的主要內容,知行問題由此而展開。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論語·季氏》)“生而知之”者,即儒家理想中的圣人;“學而知之者”則是儒家道德教化的主要對象。孔子強調知與行的統一,反對言行不一,主張“言之必可行”(《論語·子路》)、“言而過其行”(《論語·憲問》),并提出“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先行其言而后從之”(《論語·為政》)等主張。孟子繼承并發揮了孔子“生而知之”說。孟子云:“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又云:“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四端”乃“仁”“義”“禮”“智”四德之端始,是天賦的道德意識和道德能力。孟子稱之為“良知”“良能”。孟子認為,“四端”僅為“四德”之可能,而非必然。天賦的“良知”、“良能”雖“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但須通過“反身而誠”(《孟子·盡心上》)才能使其顯現。在孟子那里,發現天賦的良知、良能即為“知”,亦是“行”。“知”的內容為天賦的良知、良能,“行”則是將其“擴而充之”。在孟子看來,成圣需要經歷“盡心”“知性”“知天”的過程。如其所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與孟子不同,荀子認為人的道德認知并非先驗的,而是后天學習、教育的結果。知源于行,并最終落實到行。荀子云:“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于行而止矣。”(《荀子·儒效》)
在儒家重要典籍中,《大學》以“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概括說明了知行的統一過程。《中庸》則以“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環節把儒家的知行學說系統化、綱目化。《大學》、《中庸》所提出的知行觀對后世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至宋代,理學家將《大學》中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稱之為“八條目”。“八條目”中的后七條在《大學》中都有所說明,唯有“格物”未作解釋。“物”是什么?如何去“格”?后世儒者各說其是。宋儒有關知行先后、難易、輕重、分合等激烈論爭亦由此而發。
程頤明確提出知難行易、知先行后,并認為能知必能行①*①程頤曾云:“須是知了方行得”,“須是識在所行之光,譬如行路,須得光照”,“故人力行,先須要知”。參見《二程遺書》卷十八【宋】程顥,程頤:《二程遺書》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235頁。。朱熹則以“知行相須”說明知與行相互依賴、相互生發的辯證統一過程。朱熹說:“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后,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1]至元代,許衡倡“慎思”、“踐履”之“治生”之學[2];吳澄以“本心之發見”為“知”,認為知是在實踐中獲得的,并在以“實悟為格,實踐為誠”[3]648論知行關系的基礎上,提出了“知行兼賅”的主張。明初謝復首先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4],王陽明則明確反對將知行截然分做兩件,以“知行合一”作為“致良知”的邏輯展開,從工夫與本體,德性與知識等多個層面發前人所未發,對知行關系進行了系統闡述。
盡管知行問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主張和見解,但歷代儒家學者均圍繞知識與德性,以及德性對行為的制約作用而展開言說。正如馮友蘭先生所說:“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積極的知識(積極的知識,我是指關于實際的信息),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獲得高于道德價值的價值。”[5]就知識的內容而言,傳統儒學不出“經史子集”,然究其學問宗旨,卻涵蓋社會與人生。儒家之“知”,既包括形而下之經世致用,更包括對形而上之“性與天道”的不懈追求。儒家治國安邦的入世態度以及以人為本的治學風格決定了儒家論“知”必與“行”相聯。在回答“知”從何而來、“知”如何可能、怎樣“知”、如何“行”等問題的過程中,知識論又不可避免地與心性論、工夫論交織在一起,相互闡發,相互發明。歷代儒家學者正是在知識論、心性論、工夫論這一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整體論域中展開論爭,形成各自的知行觀。其中對知行先后、知行難易、知行分合的不同時代的不同表達不僅表現出不同時代的理論思考,也反映了歷代儒者對世風時弊的現實回應。
儒家哲學在宋明時期的理論形態—理學—往往被后世學者稱作“性理之學”,并理解為“希圣之學”[6]。理學家們以儒家經典為依據探討“天地萬物之源”“道德性命之本”以及“天人之際”等哲學根本問題,對傳統儒家日用倫常的“心”“性”“理”“道”等范疇重新詮釋,賦予其宇宙論、本體論的意義,在精深微密,辨析毫芒的探究中建立各自的理論。宋明時期盡管學派林立,論說紛呈,但“性與天道”始終是理學的核心話題。理學將人的內在精神的規定(性)與一個外在的絕對的客觀精神實體(天道)聯結起來,并認為人的終極關切就是向天理的復歸,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就是與天道的合一。復歸天理、與天道合一亦可謂“希圣”、成圣。
論及宋明理學,不能不提及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大派別的相互詰辯和相互滲透。與此相關,朱熹與王陽明作為“理學”與“心學”的兩大代表人物,始終居于理學論說的中心地位。南宋自朱熹之后,或述朱,或諍朱,所謂“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7],始終以朱熹為論說中心。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中對朱熹的學術地位作了如下評價:“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矣。江西之學,浙東永嘉之學,非不岸然,而終不能諱其偏。”[8]在全祖望看來,相較同時期的江西陸象山之學、浙東葉水心之學而言,朱學更為廣大精微,堪稱理學之集大成者。
至明代,程朱理學的正統或曰意識形態化已基本得到實現。明中期,陳獻章倡“自得之學”,王陽明揭“致良知”之教,學風為之一變。此后,“理學”漸趨式微,“心學”漸興。明清之際出現了不少有關理學發展的斷代學術史專著,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明代理學家們對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等理學思潮重新整理,并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見解。黃宗羲謂明代理學“牛毛繭絲,無不辨析,真能發先儒之所未發”[9]。此一評價可謂明儒“窮理盡性”之真實寫照。自宋以來程朱理學的流弊引發了明代王陽明心學的興起。陽明心學以其簡易對治朱學之支離繁瑣,別開生面,風氣一新,正如顧憲成所說:“一時心目懼醒,恍若撥云霧而見白日。”[10]明代自王陽明之后,或述王,或諍王,亦以王陽明為中心。
朱學與王學的異同是理學內部的分歧。探討王陽明心學需從程朱理學談起,理解心學與理學之異,亦需從心學與理學之同談起。因此,論及王學必與朱學相比較,此為研究王學之必要,自無疑義。然而,由宋至明,在從程朱理學向陸王心學的歷史演變中,元代理學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它又是否為明代王學的興起作了思想上的準備和理論上的鋪墊?元代理學家又是如何理解知行問題的?朱熹的知行觀是否就是將“知”與“行”分作兩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否就是模糊“知”與“行”的界限?“知行合一”與“心即理”又有怎樣的聯系?如何理解王學之簡易而又不易?圣學之道何以“失之毫厘,謬以千里”?以上問題的討論或可為王學研究的深入拋磚引玉。
二、“直透大義,反向自心”:朱學之失與立學宗旨
元代理學有別于宋代。民族文化的交融與沖突,元政權推行漢法的一波三折,科舉制度的行與廢等諸多原因,一方面使元代理學的內容豐富多彩,另一方面又使理學在元代的發展歷盡艱辛。學派間的明爭暗斗以及學術與政治間的若即若離糾纏在一起,使得元代理學呈現出斑駁陸離的復雜面貌。元代著名理學家當數吳澄與許衡,時人有南吳北許之謂①*①元人揭係斯謂:“有元一代,以理學后先倡和,為海內師資者,南有吳澄,北有許衡。”([元]揭係斯:《神道碑》,《吳文正集附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第945頁。)錢穆先生亦就元代“南吳北許”二位大儒作過一番比較。他說:“朱子后闡揚朱學,于學術史上有貢獻者,宋末必舉黃震東發,明代必舉羅允升整庵,清初必舉陸世儀桴亭。此三人雖所詣各不同,要為能得朱子學之大體及精旨所在。然元代有吳澄草廬,當時有北許南吳之稱。許衡先仕于元,提倡朱學,亦不為無功。然論學問著述,惟草廬堪稱巨擘。”(錢穆:《吳草廬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卷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頁。)足見吳澄在學術史上的地位。。
許衡堪稱元代理學的泰斗。由許衡創立的魯齋學派是北方理學的大宗,影響了整個元代。全祖望說:“河北之學,傳自江漢先生,曰姚樞、曰竇默、曰郝經,而魯齋其大宗也,元時實賴之。”[11]許衡推崇朱學之傳注與義理,并指出治學之道需“慎思”、“踐履”。所謂“慎思”,就是要審慎、精思,不可盲從。他說:“視之所見,聽之所聞,一切要個思字。”[2]370“踐履”意即將所學之傳注義理于倫理綱常中實踐運用。如果說“慎思”強調的是“知”,那么“踐履”強調的則是“行”。許衡將慎思(知)與踐履(行)相結合的治學之道稱之為“治生”之學。他主張理學不應空談心性,而應與儒家修齊治平之道相一致,如其所云:“茍生理不足,則于為學之道有所妨。”[2]452
吳澄是元朝中期南方著名理學大師,其學術思想的顯著特征是兼綜百家、弘揚心性。吳澄注重自覺。自覺意即自誠其意,自覺其心,亦即孟子所謂“盡其心”、“知其性”。吳澄認為,天理非外在于人心,自覺亦非外求。因此,吳澄雖于“格物致知”、“敬義夾持”處多有精論,但更注重反求諸己、“自新”、“就身上實學”[12]32。吳澄對“心學”的重視與許衡側重“以六經如法家律令”的觀念形成鮮明對比。[13]時人謂吳澄其學相較許衡而言可謂“正學真傳,深造自得”[14],并稱其“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圣之閫奧……考據援引,博極古今,……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15]80元代揭傒斯認為,許衡對元代儒學有興創之功,“其用也弘”,而吳澄則使元代儒學發揚光大,“其及也深”,相較而言,似乎吳澄的影響力更為深遠②*②元人揭傒斯:“許公居王畿之內,一時用事,皆金遺老,得早以圣賢之學佐圣天子,開萬世無窮之基,故其用也弘。吳公僻在江南,居阽危之中,及天下既定,又二十六年始以大臣薦,強起而用之,則年已五十余矣。雖事上之日晚,而得以圣賢之學為四方學者之依歸,為圣天子致明道敷教之實,故其及也深。……臣竊惟我國家自太祖皇帝至于憲帝,凡歷四朝、五十余載,天下猶未一,法度猶未張,圣人之學猶未明。世祖皇帝以天縱之圣,繼統纂業,豪杰并用,群儒四歸,武定文承,化被萬國,何其盛歟!至如真儒之用,時則有若許文正公,由朱子之言、圣人之學,位列臺輔,施教國子,是以天啟昌明之運也。乃若吳公,研磨六經,疏滌百氏,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雖不獲任君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又豈一材一藝所得并哉?”參見【元】揭傒斯:《神道碑》,《吳文正集》附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第946頁。。
王陽明亦論及許、吳二人。在回答立志是否需要為善去惡時,王陽明說:“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處。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16]22儒家道德教化總是從立志談起。志不立,則無事可成。王陽明所謂“立志”即立此“善念”。“善念”存時,即是“天理”。這樣,在“立志”―“善念”―“天理”的解讀中,何謂立志(是什么)的問題便轉化為如何存此善念(怎樣做)的問題。如果說“立志”(是什么)屬“知”,那么“存此善念”(怎樣做)則屬“行”。既然“立志”與“存此善念”均以“天理”為其內容和目標,那么“知”與“行”便不是兩件事了。具體而言,立志(知)就是要復歸天理,而天理就在每個人的心中,因此向內收斂于一心方可存此善念(行);存此善念(行)即謂立志(知),立志意即復歸天理。在知―行―知的展開過程中,知與行達成統一。王陽明認為,立志、存此善念等均應以收斂為主,至于發散(即向外探求),乃不得已而為之。在王陽明看來,許衡的治生之學恰恰混淆了這一主次關系、顛倒了這一先后次序。因此,王陽明指出“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16]22
許衡于元初受元世祖之命出任國子監祭酒,以朱熹理學教授弟子。其后,朱學被尊為官學,陸學衰微,而朱子后學日益流于訓詁之弊③*③元人虞集有曰:“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為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于圣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而后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為玩物而從事于文章,謂辯疑答問為躐等而始困其師長,謂無猷為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為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瞽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參見【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7冊,第80頁。。吳澄為朱學傳人④*④從師承上說,吳澄為朱熹的四傳弟子。吳澄初從饒魯弟子程若庸,屬朱學一系。朱子學傳至黃幹門下,有金華、江右兩支,黃幹高足饒魯即為江右斗杓,而吳澄為饒魯再傳,即為朱熹四傳弟子。(朱熹→黃幹→饒魯→程若庸→吳澄)《宋元學案》謂:“草廬出于雙峰(饒魯),固朱學也。”參見【清】黃宗羲輯:《草廬學案》,《續修四庫全書》第519冊,第641頁。,受朱學影響亦深。吳澄談及朱學之失時說:“自孟氏以來,圣傳不嗣,士學靡宗,誰復知有此哉?漢唐千余年間,儒者各矜所長,奮迅弛騖,而不知其缺。……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子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于此而溺其心。……澄也鉆研于文義,毫分縷析,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如夢之得覺,醉之得醒,而今而后而知四十四年之非也。”[17]吳澄指出,朱學之失使人“滯于此溺其心”,偏離了儒學之道。吳澄自己亦墮此窠臼四十年方如夢初醒。有見于此,吳澄力倡以“尊德性”為主的“本心”說,以“明指本心”[18]499的心學觀點對治朱學末流拘滯于文義句讀而不得要領之流弊,意欲糾朱學之偏①*①朱學在元代成為官學,所謂“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7冊,第490頁。)自朱學被列為科場程式,成仕途捷徑,原本是朱學的人,自然受官方支持而標榜其學派之正統性;有些陸學的人,也不得不打起朱學的旗號。吳澄雖師出朱門,卻私淑象山。他曾作詩云:“臨川捷徑途,新安循堂序。本得近定慧,末朱墮訓詁。”(【元】吳澄:《韻語》,《吳文正集》卷九十一,第841頁。)“新安窮格功,臨川修省處。三人有我師,況此眾父父。”(【元】吳澄:《韻語》,《吳文正集》卷九十一,第842頁。)臨川即陸九淵故里,新安乃朱熹故里。在這里,吳澄暗喻陸學簡捷,朱學循序,而朱學末流則流為訓詁。。
在吳澄看來,陸學簡易,朱學循序,而朱學末流則淪為支離。王陽明對此表示贊同。在《答劉子澄》中,王陽明大段摘錄吳澄此論以示其門人②*②《答劉子澄》載:“朱子之后,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見于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于后。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然自圣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余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于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后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圣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之超于人,而謂有得于圣學則未也。況止于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圣學大明于宋代,而踵其后者如此,可嘆已!澄也鉆研于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為未精,饒為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于尊之之道殆庶幾乎?于此有未能,則問于人,學于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于《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參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9-161頁。。王陽明指出,朱學之失在元代已多有論說,其中吳澄之見尤為肯切精當。吳澄晚年著有《禮記纂言》③*③吳澄晚年著有《書纂言》、《易纂言》、《易纂言外翼》、《禮記纂言》、《五經纂言》等。其中《禮記纂言》意續朱熹未竟之志。,王陽明亦稱其不拘于朱說,于《禮》多有發明④*④王陽明在為《禮記纂言》所作序中肯定了吳澄之說于《禮》多有發明:“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后之言禮者,吾惑矣。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其后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于朱說,而于先后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禮記纂言序》)參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全三冊),第271-272頁。,并專為此書作序。可見王陽明對吳澄之學的肯定與欣賞。在王陽明看來,許衡以朱學為宗,其“治生”之學流于朱學之失,未及大本,而吳澄對朱學之訓詁、條理之弊鞭辟入里,深得儒學之道。
王陽明指出,對于支離之病,朱熹晚年已有悔悟。朱學在元代被定為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15]490。明代同樣如此。王陽明為避免引起爭端,引朱熹自述其支離之病,以針砭時弊⑤*⑤王陽明在《與安之》中道:“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參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全三冊),第194頁。:“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己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一而已。”[16]146(《答呂子約》)“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16]146(《與周叔謹》)“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16]146(《答陸象山》)王陽明指出,盡管朱熹晚年對其支離之病多有悔悟,然而后世學者依然抱守朱熹中年未定之說,墮其科臼而無法自拔。王陽明嘆曰:“予既自幸其說之不謬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于異端。”[16]145
朱熹強調格物窮理,其后學不免趨向言語訓釋,流為訓詁之學。正如全祖望所指出的那樣,朱學在宋“端平以后,閩中、江右諸弟子,支離、桀戾、固陋,無不有之”[19]。朱門后學空談性理,日漸偏離了儒家修齊治平、經世致用之傳統。至明中葉,程朱理學的“存天理、滅人欲”在現實社會中已喪失其在道德規范上的至高話語權。在“人欲”之常情得到公開肯定的情況下⑥*⑥宋代理學家以天理為“公”,并以公為形上本體。這一立場自明代開始遭到反對,此后,私的觀念得以公開表達。詳見吳立群:《從公私觀念的演變看儒家價值觀》,《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2期。,世俗世界的普通民眾不再接受外在天理的強制與約束,受程朱理學熏陶的儒者也開始失去對那超越的天理的敬畏與歸屬。時局一時“如沉疴積萎”。如何重塑道德規范,以儒家之道統攝人心、觀照現實,成為其時學者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
王陽明對此有論:“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徒事于圣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圣之學,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嘵嘵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詆笑訾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于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16]314“道之不存,我心之憂”的憂患與擔當,促使王陽明“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以“正人心”,“息邪說”,“明先圣之學”。
錢穆先生在《陽明述要·序》中指出,研究王陽明心學“須脫棄訓詁和條理的眼光,直透大義,反向自心,則自無不豁然解悟。”[20]在朱學成為官學的元代,吳澄擺脫朱學“訓詁和條理”的束縛,以陸學之“直透大義,反向自心”糾偏救弊。至明代,朱學由于強調“格物”、“下學”、“博學”的踐履篤實工夫,流為訓詁之學,日見支離煩瑣,昧卻本體。王陽明亦以救時弊自任,倡其心學。如此看來,擺脫訓詁和條理的束縛,“直透大義,反向自心”或可為元代吳澄之學與明代王學之共同特征。
三、毫厘千里之辨與簡易不易之學
理學在南宋時出現朱陸分歧,后來形成門戶之爭。吳澄認為,朱陸后學的門戶之爭偏離了當年朱陸為學宗旨。吳澄任國子監丞時曾言及陸學與朱學,似有褒陸貶朱之意①*①元代以朱學為官學。吳澄卻在國子監公開發表贊同陸學的言論,他說:“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卻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于德性,則其弊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清】黃宗羲輯:《草廬學案》,《續修四庫全書》第519冊,第641頁。)此語一出,便有人稱引他問學須以“尊德性”為本的觀點,將他劃入陸學的陣營。元代官學尊尚朱熹學說,指吳澄為陸學就是公開聲言他不宜居國子監師儒之職。吳澄因此棄職南歸,抱恨深隱。。在論及為學次第時,吳澄又以“尊德性”為先,視“道問學”與“尊德性”為下學上達的關系,此說亦被人目為是陸非朱。事實上,吳澄在推崇陸九淵的同時,并未否定朱熹之學②*②吳澄一生治學行事受宋代諸儒影響頗深。其“敬義夾持”、“心”說等觀點均秉朱熹而來。在元代,有人以吳澄為陸學,并非單純的誤解,而是排斥異己的口實。詳見吳立群:《吳澄理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吳澄強調反求吾心,以“尊德性”為先,乃就朱門后學日益墮入訓詁之流弊而發,意欲矯朱學之偏。吳澄指出,朱學有窮理格物之功,陸學有修身自省之實,二者皆有所長,并無二致,如其所云:“朱子之教人也,必先之讀書講學,陸子之教人也,必使之真知實踐。讀書講學者,固以為真知實踐之地;真知實踐者,亦必自讀書講學而入。二師之為教,一也。”[21]王陽明論及朱陸異同時亦云:“象山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晦庵……專以道問學為事,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而遂議其支離。”[16]890在王陽明看來,朱學陸學雖于“尊德性”與“道問學”各有側重,然究其實質并無根本分歧,后學“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終致支離。
吳澄在提倡以“本心”之學對治朱學支離之病的同時,對陸學后學率心由性、流于空疏的偏失亦保持警醒。他指出,所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去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18]499。正像朱學在其后學中面臨墮為“俗學”的危險一樣,“今人說陸之學,往往曰‘以本心為學’,而問其所以則莫能知。……徒習聞其名而未究竟其實也。夫陸子之學非可以言傳也,況可以名偏求哉。”[18]499吳澄主張拋棄門戶之見,以維護儒道為重,在朱陸之間取其長而避其短,將朱熹格物致知的篤實工夫與陸九淵發明本心的簡易原則結合起來,避免泛濫無歸、談空說妙。王陽明亦指出,朱學之失乃君子之過,象山之學亦未及“精一”。王陽明在為《象山先生全集》所作之序中雖對陸學之簡易直截給予了充分肯定,然其“庶幾精一”一語亦有陸學未達“精一”之意。他說:“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孟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后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于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氏之傳。……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低以為禪。”[22]在王陽明看來,朱陸之學本各有所長,各有所短,而世之學者厚朱薄陸,實為小人之見。
王陽明認為,世人厚朱薄陸不僅有薄于象山,更有薄于朱子。他說:“世之學者以晦庵大儒,不宜復有所謂過者,而必曲隱飾增加,務詆象山于禪學,以求伸其說,且自以為有助于晦庵,而更相倡引,扶之為正論。不知晦庵乃君子之過,而吾反以小人之見而文之。……而世之儒者,事之以事小人之禮,是何誣象山之厚而待晦庵之薄耶!仆今者之論,非獨為象山惜,實為晦庵惜也。”[16]892對于朱陸之爭,王陽明指出:“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論學而務以求勝……皆失之非……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16]888是朱非陸雖已成定論,但朱陸后學囿于門戶之淺見,爭論勝負,“皆失之非”,“亦皆未得其所以是”。議論好勝實為學者大病。王陽明對此多有所論,他說: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為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于心,不必茍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于是而已。……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于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為之竦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悍然不顧,略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某之于道,雖亦略有所見,未敢盡以為是也;其于后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為非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為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16]300
王陽明認為,學者治學,各有主張,自然有深淺同異,亦難免學術論爭。若以求是之心、懷問道之志,則治學可得精進;若為勝負之爭,抱門戶之見,則無異于自筑藩蘺,自障其目,更何談求是問道?
王陽明其時力倡心學,亦被指為禪學,為世人所非。有感于此,王陽明說:
夫圣人之學,心學也。……圣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閧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圣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騖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16]286
因見支離之病日甚,“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王陽明遂以“求是”為念,倡其心學,欲反本求源,闡明“道心”之“微”、“人心”之“危”,以重回儒學之正道、重塑天理之形上根據,使天理重回人心。在王陽明看來,其時學者有受舊習所蔽而不自知者,抵王學為禪,自不當怪罪(不知者不為怪),而明知支離之病仍固守其說者,則確為門戶之見,王陽明稱其為“自私者”;更有既知而“冥然不以自反者”,王陽明稱其為“自棄者”。
面對種種抵謗,王陽明表示,因堅持自己的學術主張而不為世人理解甚至遭到惡意詆毀的情形古已有之。“昔之君子”不因“一時毀譽而動其心”,皆因其內心以求真、求是為信念。正所謂學術“亦求其是而已矣”。他說:
四方英杰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茍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于我,彼其為說,亦將自以為衛夫道也。……乃不知圣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真,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后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為盡非?[16]209(《與陸原靜》)
王陽明對種種抵謗表示寬容與理解。朱學之失在明代積弊已久,世人理解王陽明所倡心學確非易事。王陽明在《書汪汝成格物卷》中這樣說道:“汝成于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16]299(《書汪汝成格物卷》)時人汪汝成對王陽明之說經歷了“始而駭”、“既而疑”、“又既而大疑”、“又既而稍釋”、“稍喜”、“而又疑”的輾轉反復,最終似有所得,又似無所得,正如王陽明所謂“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可見王學雖以簡易行世,但理解其理論邏輯并非易事。何以如此?王陽明對其簡易而又不易之學作了如下說明:“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里,亦與圣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厘,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掇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于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16]224(《寄鄒謙之》)
對“道”的追問是儒家高度自覺的思想主題和致思目標。在“道”的指引下,人的生命有了意義,社會發展有了方向。宋明時期,“道”亦稱為“天理”,因此便有“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王陽明認為,此說看似簡易可行,卻未免捕風捉影,流于空泛。正如陸九淵主張發明本心,而其后學從楊簡起,把發明本心極端地發展為以“明悟”為主,“不起意”為宗[23],以至“不讀書、不窮理、專做打坐工夫”[24],一如全祖望所謂“一往蹈空,流于狂禪”[25]。王陽明指出,捕風捉影,流于空泛,自然無法體認天理;而“縱令鞭辟向里”,亦與王陽明所倡“致良知”隔了一塵,同樣無法體認天理。在王陽明看來,即使是“著實能透徹者”亦不能從“隨處體認天理”之說中尋其大本達道,更何況“世間無志之人”,既受詞章之學所羈絆,又受“似是而非之學”所誤導,終身不得出頭,體認天理更無從談起。可見,“隨處體認天理”之說看似簡易可行,實則完全行不通。這正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
有見于此,王陽明對毫厘千里之辯反復論說。他說:“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于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于不辯者,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謬矣。”[16]205-206(《答方叔賢》)在王陽明看來,王學與朱學之異并非有心求異,而是因為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里之分,乃不得不辯①*①《傳習錄》載:“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為人門下手處有毫厘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余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參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頁。。王陽明以詩寄懷:
洙泗流浸微,伊洛僅如線;
后來三四公,瑕瑜未相掩。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遠。
屢興還屢仆,惴息幾不免。
道逢同心人,秉節倡予敢;
力爭毫厘間,萬里或可勉。
風波忽相失,言之淚徒泫。[16]750
又云:
毫厘何所辨?惟在公與私。
公私何所辨?天動與人為。
遺體豈不貴?踐形乃無虧。
該系統為雙CPU處理系統,DSP28335與STM32F103均需一套程序獨立運行,二者的合理配合是整體系統性能優秀的保障。程序處理流程如圖6所示。
愿君崇德性,問學刊支離。
無為氣所役,毋為物所疑,
恬淡自無欲,精專絕交馳。
博奕亦何事,好之甘若飴?
吟詠有性情,喪志非所宜。
非君愛忠告,斯語容見嗤;
試問柴墟子,吾言亦何如?[16]753
四、“訂致知格物之謬”與合內外之道
王陽明的毫厘千里之辯首先從格物致知說開始。在王陽明看來,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皆為窮理盡性而分別言說,就其實質而言并無二致。他說:“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辟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16]87在王陽明看來,天下本無性外之理,亦本無性外之物。人們將天理視為外在于我的一個超越存在,把物看作是一個外在于我的認識對象,是隔絕天人、對立物我,是錯誤的。這種錯誤認識早在孟子那里就被批評為“義外之說”,而世人仍陷其中而不自知。世人拘滯于此,皆因誤解心與理、道與器的關系,將心與理析而為二,將道與器離而為二。對心與理、道與器的關系,王陽明再三強調:“此心還此理,寧論己與人”②*②《赴謫詩五十五首·其四》:“此心還此理,寧論己與人!千古一噓吸,誰為嘆離群?浩浩天地內,何物非同春!相思輒奮動,無為俗所分。但使心無間,萬里如相親;不見宴游交,徵逐胥以淪?”參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50頁。、“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③*③《赴謫詩五十五首·其五》:“器道不可離,二之即非性。孔圣欲無言,下學徒泛應。君子勤小物,蘊蓄乃成行。我誦窮索篇,于子既聞命;如何園中士,空谷以為靜?”參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51頁。。
王陽明此論并不為當世學者所認同。與王學持不同論者認為,“心即理”之說專事反觀內省,遺棄講習討論,沉溺于枯槁虛寂,并認為“是內非外”是王學之錯誤所在。王陽明對此申明,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所謂“毫厘之差,千里之繆”即于此而起,故不可不辯。王陽明說:“凡執事所以致疑于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內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于反觀內省之為,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于綱領本原之約,而脫略于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于枯槁虛寂之偏,而不盡于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于圣門,獲罪于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況于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況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于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于其中。但為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厘之差耳。然毫厘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于此,不可不辨”[16]87。王陽明指出,朱熹之格物致知說以“盡心、知性、知天”為格物、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為誠意、正心、修身;以“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為知至、仁盡,圣人之事①*①《傳習錄上》載:“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為格物、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為誠意、正心、修身,以‘夭壽不二、修身以俟’為知至、仁盡,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參見【明】王守仁撰,吳光等編校:《王陽明全集》(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頁。。朱熹此說“析心與理為二”,可謂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具體而言,朱熹所謂即物窮理,即于事事物物上求其理。如此便將“物”與“理”均視為外在于“吾心”的存在。在王陽明看來,“天理”本在吾心,如何向外求得?如其所云:“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為二矣。”[16]50
朱熹論格物致知析心與理為二,王陽明論格物致知則以心與理為一。王陽明說:“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于孺子之身歟?抑果出于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辟也。條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為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16]51王學所見與朱學正相反。王陽明認為,所謂致知格物,即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而吾心之良知即天理。所以,致知格物意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如此,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在王陽明看來,對照朱子晚年悔悟,二者孰是孰非,不言而喻。
針對與王學持不同論者的批評,王陽明予以了回應。王陽明認為,理學所學無非“性”與“理”,所謂“性理之學”是也。既然“理”無內外之分,“性”無內外之分,那么,“學”亦無內外之分。講習討論未嘗不以性與理為題,未嘗非內,反觀自省自當從日用常行、事事物物中反省,亦未嘗非外。世人視“反觀自省”與“講習討論”為內外對立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說:
夫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于外求,是以己性為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內省為求之于內,是以己性為有內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內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為外,認物為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辟之。乃至襲陷其內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16]86-87(《傳習錄中·答羅整庵少宰書》)
在這里,王陽明分析了兩種錯誤傾向。其一,“義外”。即將性視為外在于我的對象,試圖通過理智分析來把握,而不思自反;其二,“有我”。即以性為內在于我,自私其心,而于身外事事物物皆無察照。
儒家向來主張內外兼修,而非二者對立。己與人、心與物并不存在必然的沖突,而是相互構成、同為整體中不可或缺之分子。“修己以安人”、“成己為人”、“萬物一體”正是內外統一,相輔相成的習慣表達。儒家以“為己之學”自稱。自我在儒學中始終處于中心地位。在儒家那里,自我的塑造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儒家把自我的培養和完善放到社會、國家乃至宇宙的大背景中去認識、探索。一個人若能完成自我的修身,達到與家族、社會、國家的交融,進而達到主客交融無差別的境界,就能實現人與宇宙的合一,也就完成了自我的塑造。可見,在儒家那里,內在自我的實現與外部社會、國家乃至宇宙緊密相連;另一方面,人們對社會、國家乃至宇宙等外部世界的關注,最終需要回到人自身。“人”又是由“己”組成的,如果抽象地談“人”而不落實為“己”,那么,道德修養便喪失其實踐性,難以成為人們行為規范的價值準則。由此可見,在儒家那里,內外統一而非矛盾,成己與成人、為己與為人,是一個有機的統一體。
由此可見,以內外對立的觀點理解“性”“理”“學”是錯誤的。若以內外合一觀之,《大學》所謂“正心”“誠意”“格物”“致知”均以修身為最終目標,則無內外彼此之分。這樣,“格物”不僅為入門下手處,而且貫通儒家修身成圣之始終。換言之,成圣工夫亦只此“格物”而已。王陽明指出,所謂“格物”,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所謂“正心”,即正其物之心;所謂“誠意”,即誠其物之意;所謂“致知”,即致其物之知。如此看來,“正心”“誠意”“致知”都只是“格物”;“格物”亦即“正心”“誠意”“致知”。成圣工夫只此“格物”而已。何以如此?“理一而已”。
王陽明進一步指出,“理”“性”“心”“意”“知”“物”諸范疇雖各有所名,但都是就“理”的不同表現、不同方面而分別言說,并非在“性”之外、“心”之外、“意”之外、“知”之外、“物”之外又有一“理”。與以上諸范疇相對應,便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盡性”“窮理”之謂。由此可知,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實則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換言之,只有在內外統一的思維框架中,才能正確理解性理之學。格物致知之學須以“心即理”為其理論前提。
吳澄的“格物致知”說同樣在此框架下展開。他說:“夫聞見者,所以致其知也。……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12]25所聞所見雖然是從外部世界獲得,但所聞所見之理則是內在于心的。因此,“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這樣,心與理、內與外便統一起來。可見,吳澄亦從內外兩方面來說明格物致知,并稱格物致知為儒者內外合一之學。
在對“格物致知”的闡發中,吳澄分析了朱陸之異同,并贊同陸九淵以反觀自心為“致知”的觀點,同時又不完全拘于陸說,在強調內心道德的自覺性上又有所發明。與此相關,吳澄又以“尊德性”與“道問學”論“正心誠意”與“格物致知”。在“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關系上,吳澄強調,為學次弟當以“尊德性”為主,同時又必須有“道問學”的工夫予以充實。“尊德性而道問學”意即“尊德性”與“道問學”相統一,內外兼修。在這里,吳澄實際上是主張以陸學的“高明簡易”與朱學的“篤實邃密”結合起來,在朱陸之間取其長而補其短。就陸學而言,雖然立大本之心有“頭領”,但缺乏朱學“縝密”的“致知”工夫;就朱學而言,雖有篤實的“致知”工夫,但因其陷于下學而趨于煩瑣,缺乏上達的“力行之效”。因此,吳澄認為,儒者應拋棄朱陸門戶之見,使下學與上達統貫起來,使“格物”與“致知”、“尊德性”與“道問學”結合起來,回到儒學正道。[13]
如此看來,吳澄與王陽明均以內外合一為理論前提闡明格物致知,所見略同。但吳澄主要針對朱學之失而發,強調以陸學之長補朱學之失,在格物致知的學理分析上不足,其理論邏輯亦不夠周延。同樣有見于朱學之失,王陽明則在深入分析“理”“性”“心”“意”“知”“物”諸范疇之內涵的過程中,厘清了正確理解格物致知說的重大理論障礙。
五、知行合一與知行兼賅:知與行的動態統一
前已述及,王陽明指出,析心與理為二是朱熹錯解格物致知的根本原因,而知行分離的錯誤根源亦在于此。王陽明說:
理豈外于吾心邪?晦閹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后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暗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16]48
朱熹以“心與理”之學概括儒家之學,并分別從心與理兩方面加以說明:心為一身之主,宰萬物之理;理雖散在萬物,亦不外乎人心。雖然朱熹言詞中并無“心非理”、“理非心”之意,但王陽明認為,“心與理”之“與”字易使學者誤以為心與理為二。由于朱熹強調內外兼顧,后世便有所謂“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亦即顧此失彼之患。王陽明認為,“心與理”之說致使學者向心外求物理,必有其不達之處。“心與理”之說正是孟子所批評的“義外”之說。王陽明以“心即理”更正朱熹之“心與理”。在王陽明看來,心一而已,所謂“仁”“義”“理”之詞均為就“心”的不同表現、不同方面而分別言說。正如不可于心外求“仁”、于心外求“義”一樣,“理”亦不可于心外求得。將知與行一分為二的錯誤原因正在于向心外求理。以“心即理”觀之,則可知“知行合一”方為儒家正道。
在回答門人問知行合一時,王陽明說:“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此是我立言宗旨。”[16]109-110王陽明倡知行合一,其立言宗旨即在于糾正知行分離的錯誤,如下文所示:
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個,亦是要人見個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只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個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上亦不妨,亦只是一個。若不會宗旨,便說一個,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16]5
在王陽明看來,古人以知行言說,只是一個方便的說法。知行是一個知與行統一的過程。所謂“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所表達的是在知行過程中,從知開始,到行完成,即從開始到完成的一個過程。如果能理解知行本是一個由起點向終點的過程,那么,只說一個知,便知有行,只說一個行,亦行有知。古人之所以既說知,又說行,是因為人們有時不假思索而行,有時又苦思冥想而不行。因此,既要說個知,以思維省察避免冥行妄作,又要說個行,以躬行踐履避免懸空揣摩。古人既說知又說行,實為補偏救弊,乃不得已而為之。事實上,知即行,行即知,知行二字,一言足矣。世人卻以“知先行后”等字面文義誤解古人言知行之宗旨,自然無法把握知行命題之真義。正是有見于此,王陽明有感而發,倡知行合一,以救時弊。王陽明指出,如果對其知行合一說之立言宗旨能有所領悟,那么,即使既說知又說行,仍然只是知行合一;反之,則即使只說一個,亦無濟于事。換言之,理解其知行合一說,首先應明白其立言宗旨。其知行合一說乃針對其時之學術問題及社會弊癥而發,實為補偏救弊之方。學者需切實躬行,不可只在字面文義上鉆究。
在王陽明看來,知行工夫本不可離。他說:“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16]47-48其時學者對“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一語之知與行多有困惑。王陽明以“溫凊”、“奉養”為例對知行之所謂加以說明。他說:
此乃吾子自己意揣度鄙見而為是說,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后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后謂之致和。溫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于溫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凊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于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后謂之格物。溫凊之物格,然后知溫凊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后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溫凊之良知,而后溫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后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后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16]55(《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
在這里,王陽明以“溫凊”“奉養”之事為例對“意”“知”“物”與“誠意”“致知”“格物”作了明確區分。他指出,有溫凊、奉養之意,不可謂之誠意。必實行溫凊、奉養,然后方可謂之誠意;知溫凊之節、奉養之宜不可謂之致知,必致溫凊、奉養之知,然后方可謂致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可謂物,未可謂之格物,必以良知之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在溫凊、奉養之事中實行,方可謂格物。此即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溫凊”、“奉養”指侍奉父母之禮,每個人對此都有切身體會。王陽明以此為例說明知行關系,不僅通俗易懂,而且自然引出如下結論:“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則知知行之合一并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16]51-52
王陽明上述就“意”非“誠意”、“知”非“致知”、“物”非“格物”的特別區分,正是就“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一語的反向說明,意即:“知未真切篤實不可謂行,行未明覺精察不可謂知”,亦即:“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然而,在現實社會中,“知而不行”現象并非罕見。門人徐愛即就此對知行合一說提出了疑問。[16]4徐愛的看法是:人人盡知孝悌,卻有不孝不悌。可見,知孝悌并不能行孝悌,那么知與行分明就是兩件,又如何說知行合一呢?換言之,知行合一又是如何達成的?
知識與德性、德性與德行、化德性為德行是儒家知行觀討論的主題。儒家學說歷來重視教化問題,而又普遍認為垂教的本原在于人的心性。換言之,儒家教化的理論基礎即心性論。孔子的仁學思想中已經包含了心性論的因素。之后,從《孟子》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孟子·盡心上》),到《中庸》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從《荀子》的“心也者,道之工宰也。”(《荀子·正名》),到《大學》的“誠意”、“正心”,無不闡明一條由人道上達天道,以修心養性而成賢成圣的心路歷程。可見儒家論修養工夫不離心性基礎。至宋代,理學中有一個重要預設,即天道與人心并非彼此隔絕、無從貫連。人心中潛含著的“明德”“良知”即天道在人心的體現。朱熹說:“理在人心,是之謂之性。……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26]外在天理在人心中的體現即性。人可以通過持敬、存養、省察、正心誠意等主觀意志活動,通過“盡性”的過程,體達天道,實現天人合一,獲得有限人生的充實意義。儒家修養工夫的心性基礎在理學那里實現了形上化。可見,在儒家那里,知識論、工夫論、心性論始終緊密相連。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亦以復歸天理、成賢成圣為依歸。前已述及,在回答立志是否需要為善去惡時,王陽明說:“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逾矩’,只是志到熟處。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16]22儒家道德教化總是從立志談起。志不立,則無事可成。王陽明所謂“立志”即立此“善念”。“善念”存時,即是“天理”。這樣,在“立志”―“善念”―“天理”的解讀中,何謂立志(是什么)的問題便轉化為如何存此善念(怎樣做)的問題。如果說“立志”(是什么)屬“知”,那么“存此善念”(怎樣做)則屬“行”。既然“立志”與“存此善念”均以“天理”為其內容和目標,那么“知”與“行”便不是兩件事了。具體而言,立志(知)就是要復歸天理,而天理就在每個人的心中,因此向內收斂于一心方可存此善念(行);存此善念(行)即謂立志(知),立志意即復歸天理。在知―行―知的展開過程中,知與行達成統一,“立志”即立此“善念”。“善念”存時,即是“天理”。在這一回答中,“知”即“行”,并且知行合一是一個動態展開的過程。
王陽明認為,致知工夫展開于踐履過程之中。“知行合一”即致良知的展開過程。具體而言,知行合一即展開為知—行—知①*①楊國榮指出:“知行的統一作為一個過程,以知(本然之良知)—行(踐履)—知(明覺之知)為其內容。”參見楊國榮導讀,【宋】陸九淵撰:《象山語錄》;【明】王守仁撰:《陽明傳習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頁。的統一過程。就知—行—知而言,分而言之,前一“知”指天賦良知,即道德修養的根據,亦即心性論所謂本原或本體。它是先驗的、自在的、本然的;“行”即踐履,亦即工夫論所謂工夫;后一“知”指主體通過踐履(行)之后而自覺其天賦良知,它是自為的、實然的。換言之,先驗的道德良知只有在后天的致知活動中,才能為主體所自覺、所把握。知行在此環節獲得統一,在從自在之知到自為之知,從本然之知到實然之知的過程中,知行合一得以完成。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首先從“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展開。吳澄亦認為知不離行,并強調“知”為“實踐”之知,進而提出知行兼賅的思想。
在儒家那里,“知”并非對外部世界的認知,而是對自我的認知;“行”亦非改造物質自然的活動,而是對“性理”的認知活動,是以自我實現為宗旨的道德實踐。吳澄以“發見本心”為“知”,以“固守本心”為“行”。他首先對“知”作了疏解。吳澄將詞章記誦、政事功業歸為“見聞之知”,并稱其為外學。他說:“詞章記誦,華學也,非實學也;政事功業,外學也,非內學也……然知其所知,孰統會之?行其所行,孰主宰之?無所統會,非其要也。無所主宰,非其至也。”[27]94張載曾明確把“知”區分為“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見聞之知”通過耳目見聞而獲得,又稱“學問之知”;“德性之知”又稱“明德”、“良知”,即先驗的道德知識,亦即關于人性的自我認識,它通過自我反思而發明。張載說:“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于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29]張載認為,見聞之知并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亦非由見聞而來,故有“見聞之知”與“德性之知”之別。吳澄以詞章記誦、政事功業為“見聞之知”,并認為“見聞之知”因其外求,因其非內、非實,故不可謂真知。可見,吳澄不以“見聞之知”為真知。
吳澄認為,發見本心方可謂知。他說:“所謂性理之學,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當用功知其性,以養其性。能認得‘四端’之發見謂之知。”[12]32吳澄曾強調“尊德性”的重要性,但同時亦指出尊德性僅為“先立乎其大”,道德修養的完善仍須有“道問學”予以充實,方不致流入佛老之異端。[13]因此,吳澄在以“發見本心”為“知”的同時,提出以“固守本心”為“行”。他說:“應接酬酢,千變萬化,無一而非本心之發見,于此而見天理之當然,是之謂不失其本心,非專離事物,寂然不動,以固守其心而已也。”[18]499-500在吳澄看來,“本心之發見”離不開行。吳澄反對“外心而求道”,并非要人們“離去事物”空談義理。他說:“讀《四書》有法,必究其理而有實,非徒誦習文句而巳,必敦謹其行,而有實踐,非徒出入口耳而已。”[3]648吳澄強調,“知”是在實踐中獲得的。知而不行,仍是未知。如其所云:“若徒知而不行,雖知猶不知也。”[12]32可見,吳澄所謂“知”既非“見聞之知”,亦非“德性之知”,而是實踐之知。吳澄以“發見本心”為知、又以“固守本心”為行,意在說明知不離行,如其所云:“知必真知,行必力行。實矣,內矣。”[27]
在吳澄看來,強調真知實行的知行合一是孔子“一以貫之”之道。他說:“凡學之大端有二:知必致也,行必篤也……夫子以貫之一言……朱子釋曰貫通也。”[29]吳澄指出,儒家之學無非知行而已,朱熹將知行關系解釋為貫通,意即知行不相離。因此,知而不行,仍是未知①*①吳澄指出,在知行的統一過程中雖有行而不知,但無知而不行。他說:“夫行之而不知,有矣,知之而不行,未之有也。知之而不行者,未嘗真知也,果知之,豈有不行者哉?”參見【元】吳澄:《學則序》,《吳文正集》卷二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第228頁。。換言之,知不離行。《中庸》提出了學、問、思、辯、行五個為學方法。吳澄從知行的角度對此作了發揮,他說:“學之博然后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錯綜之以有所疑而質諸問……問之審然后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講明之以發其端而反諸思……既已因其學問之所得而謹思之,則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辯,又因其思之所及者而明辯之,乃無所疑惑,而可以見于行。”[30]吳澄把《中庸》提出的學、問、思、辯、行概括為知與行,并認為知行不相離。在吳澄看來,孔子以文、行、忠、信立教亦可以學、問、思、辯、行范圍。他說:
夫子之以文、行、忠、信立教也。四者之施有先后爾,非專一偏于一而不該不遍也。……首之以學文,而誦習之、究索之,則能明其道于心矣。所明之道,我所固有,加之心學行,而修踐之、持守之,則能履其道于身矣。所履之道不誠實,是欺也是誣也。盡己之誠為忠,循事之實為信。繼之以學忠與信,而內外一于誠實,則踐真守篤,無虛偽矣。既能明于心,又必履于身;既能履于身,又必誠于內、實于外。圣人之教人也,始終該遍如此哉![31]
文行忠信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吳澄指出,知識(文)、實踐(行)、忠誠(忠)、守信(信)看似分別就書本知識、社會實踐、道德修養等不同方面而言,實則彼此并無隔離。道是儒家追求的人生目標。文以載道、體道行道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知行兩方面的內涵,它們之間有著內在的統一性。儒家之知以性與天道為其主要內容,故求知即明道;明道亦即對道的躬行踐履,此亦即行。換言之,知即在行中,若能知便可行。
基于對知行關系的理解,吳澄在擔任太學司業時即以“多學”、“多識”為原則定“教法四條”,即“經學”“行實”“文藝”“治事”。據《神道碑》載:“仁宗即位,進司業。乃損益程淳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大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未及施行,為同列所嫉。”[32]吳澄在參考程顥、胡瑗、朱熹等人的教學主張的基礎上,提出了四條教法的改革方案。四條教法中的“行實”、“治事”即倡導將“知”與“行”相結合:既學以致用,又在實踐中求得真知。吳澄還以“實悟為格,實踐為誠”[3]648論知行關系。在他看來,知行本不相離。如果以“悟”、“誠”為“知”,以“格”、“踐”為“行”,那么,“實悟為格”意即真知即是行,“實踐為誠”意即實行即是知。此說似與前論王陽明所謂“意非誠意”“知非致知”“物非格物”之意若合符節。
在吳澄那里,知行以德性的完善為目標,知行統一是一個不斷完善的動態過程。吳澄援引《周禮》中的至德、敏德、孝德三德[33],將知行統一的程度分為遞進的三個層次。他說:“周官三德之教,一至德,二敏德,三孝德。至德者何?能知能行,明誠兩盡,德之極至者也。敏德者何?知有未偏,行無不篤,德之敦敏者也。孝德者何?百行之中莫先于孝,庸德之行專務其本者也……蓋知行兼賅者,上也。二者不可得兼,則篤于行,而知未逮者,亦其似也。然所行非一端而已。茍未能一一純備,先務其大而有孝之一德者,又其次也。”[34]在這里,至德、敏德、孝德分別對應“知行兼賅”“行而未知”“行而不備”等知行統一的三種情形:一為“至德”,此為上。若能知能行,則可達儒家道德修養中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自明誠”而“自誠明”、內外兼備的至德境界。能知能行亦即知行兼賅;二為“敏德”,為其次。雖在知的方面未達完備,但在行的方面卻無有不達。如此亦可增進道德修養;三為“孝德”。在行的方面,篤于“孝行”。雖于孝行之外的其他方面未有所達,但仍不失為“百善孝為先”之闡揚,為善行之始。如此亦可進德。通過對“進德”層次的劃分,吳澄給出了切實可行的為學目標:若知行兼賅,可達“至德”;若篤于“行”,可得“敏德”;若僅篤行于孝,可進“孝德”。如此看來,知行合一非“能”與“不能”,乃“為”與“不為”。知行是一個不斷完善的動態統一。概而言之,在知行關系上,吳澄明確提出了“知行兼賅”的思想,并將知行視為動態統一之過程。
六、結語
綜上所述,吳澄與王陽明的知行觀首先從格物致知說展開。吳澄的格物致知說主要針對朱學之失而發,強調以陸學之長補朱學之失,并以內外合一為其理論前提闡發“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致”。王陽明則明確指出,析心與理為二是朱熹錯解格物致知的根本原因。王陽明認為,以“心即理”觀之,“理”“性”“心”“意”“知”“物”諸范疇雖各有所名,但都是就“理”的不同表現、不同方面而分別言說,并非在“性”之外、“心”之外、“意”之外、“知”之外、“物”之外又有一“理”。與以上諸范疇相對應,便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盡性”“窮理”之謂。由此可知,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所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實則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因此,格物致知無內外之分。可見,二人均以內外合一之道闡明格物致知,所見略同。
關于知,吳澄以“本心之發見”為“知”,認為知是在實踐中獲得的,知而不行,仍是未知。在闡明知行不相離的觀點之后,吳澄又以“實悟為格,實踐為誠”[3]648論知行關系。如果以“悟”、“誠”為“知”,以“格”、“踐”為“行”,那么,“實悟為格”意即真知即是行,“實踐為誠”意即實行即是知。此說與王陽明所謂“意非誠意”、“知非致知”、“物非格物”之意若合符節。在此基礎上,吳澄提出了“知行兼賅”的主張。吳澄以《周禮》中的孝德、敏德、至德分別對應“行而不備”、“行而未知”、“知行兼賅”,即知行統一的三個遞進程度。知行兼賅意即將“尊德性”與“道問學”相結合,“自明誠”與“自誠明”相結合,內外兼修。王陽明則指出,知行工夫本不可離。他首先以“意”非“誠意”、“知”非“致知”、“物”非“格物”的觀點闡明“知而不行,只是未知”,進而提出知即行,知行合一。接著,王陽明以知—行—知的動態展開過程說明了知行如何獲得統一。在王陽明那里,知行合一是一個動態展開的過程。在從自在之知到自為之知,從本然之知到實然之知的過程中,知行合一得以完成。可見,在知行關系上,吳澄和王陽明均認為知行不相離,并視知行合一為一動態統一。
如何重塑道德規范,以儒家之道統攝人心、觀照現實是吳澄和王陽明在各自的時代所面臨的共同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二人均以辟門戶之見、倡求是新風為其立言宗旨。自宋以來,朱陸后學各立門戶,相互排斥,使學術發展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在朱學成為官學的元代,吳澄對章句之學予以大膽批判,以陸學之簡易補朱學之支離,并使陸學借朱學得以薪傳。陸學不僅在陸學系統中延續下來,而且也滲入朱學系統,為朱學所兼取。吳澄立足于學術發展,客觀理性地看待朱陸分歧,沖破了狹隘的道統藩籬,使理學在元代得到了一定的發展[13]。吳澄強調朱、陸之學的根本一致,不僅體現了元代理學的學術特色,也預示著理學演變的方向。明代王學的出現并非偶然。盡管陽明心學是否就是對吳澄心學的繼承和發揮尚有待考察,但吳澄兼綜百家、弘揚心性、以道自任、獨立省察的治學態度確實有利于學術的正常發展,從中亦可窺見理學發展演變的端倪。至明中期,朱門后學空談性理,日漸偏離了儒家修齊治平、經世致用之道。王陽明亦以救時弊自任,倡其心學。在王陽明看來,王學與朱學之異并非有心求異,而是因為入門下手處有毫厘千里之分而不得不辯。王陽明以求是為本,意欲重返儒家之道、重塑天理之形上根據,使天理重回人心。
對“道”的追問是吳澄和王陽明高度自覺的思想主題和致思目標。以此為依歸,二人指出,人們將道、天理視為外在于我的超越存在及認識對象的這一觀念是錯誤的。錯誤的原因即在于視心與理、道與器為內外對立的矛盾關系。在以合內外之道對格物致知、知行關系等知行觀基本問題進行了具有積極意義的疏解之后,二人均提出了知行不離、知行合一的主張,并均視知行為一動態的統一過程,建立了各自的知行觀。就其理論體系而言,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與其“心即理”、“致良知”的思想融會貫通,其知識論與心性論、工夫論互為闡發,理論邏輯較為周延。相較而言,吳澄的理論建構則較為粗糙。
吳澄的“知行兼賅”與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所表現出的理論思考亦表明儒學自身所具有的批判性是儒學不斷發展的不竭動力。正如當代學人所指出的那樣:“儒學歷來都具有批判性,這種批判性既表現在對世俗社會風氣,當然還表現在對儒學內部不同傳統的批判方面。儒學正因為自己傳統內部充滿著批判性,因而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發展出了一種批判儒學,從而推動儒學向前發展”[35]。
[1]朱熹.朱子全書·二十二[M].朱杰人,等,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98.
[2]許衡.魯齋遺書[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3]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九十二[M]//續修四庫全書:第519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648.
[4]吳雁南.王陽明的憂患意識與“知行合一”[J].貴州社會科學,1995(2).
[5]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涂又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5.
[6]錢穆.朱子新學案[M].成都:巴蜀書社,1986:47.
[7]黃宗羲.姚江學案·敘錄[M]//明儒學案·卷十.北京:中華書局,1985:179.
[8]黃宗羲.宋元學案·晦翁學案上:第二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6:1495.
[9]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M]//黃宗羲全集:第七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5.
[10]顧憲成.小心齋札記·卷三[M].[萬歷間刻本].
[11]黃宗羲.魯齋學案[M]//續修四庫全書:第519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622.
[12]吳澄.吳文正集·卷二[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32.
[13]吳立群.吳澄理學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11.
[14]虞集.吳文正集附錄[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945.
[15]虞集.道園學古錄[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7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80.
[16]王守仁.王陽明全集[M].吳光,錢明,董平,等,編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17]吳澄.吳文正集·卷四十[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421-422.
[18]吳澄.吳文正集·卷四十八[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19]黃宗羲.東發學案[M]//續修四庫全書:第519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567.
[20]錢穆.陽明學述要[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1.
[21]吳澄.吳文正集·卷十五[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57.
[22]陸九淵.陸九淵集[M].鐘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0:538.
[23]黃宗羲. 慈湖學案[M]//續修四庫全書:第5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376.
[24]陳淳.北溪文集大全[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686.
[25]黃宗羲.絜齋學案[M]//續修四庫全書:第51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404.
[26]黎靖德.朱子語類(三)[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0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22.
[27]吳澄.吳文正集·卷七[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28]張載.湯勤福導讀:張子正蒙[M]. 王夫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44.
[29]吳澄.吳文正集·卷九[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16.
[30]吳澄.雜識四[M]//草廬吳文正公全集·外集. [清]萬璜,編.[清乾隆丙子年臨川吳氏刊本].
[31]吳澄.吳文正集·卷十[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19.
[32]揭傒斯.吳文正集(附錄)[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944.
[33]錢玄.周禮[M].長沙:岳麓書社,2001:125.
[34]吳澄.吳文正集·卷二十一[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228.
[35]吳根友.儒學的批判性與批判儒學[J].孔子研究,2013(2).
責任編輯 何志玉
The idea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ultivation-Compare Wu-Cheng’s“knowledge and behavior” with Wang-Yangming’s“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WU Li-qun
(Shanghai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hanghai,200044,China)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The central thesis of it is “character” and “natural law”. Will it be possible to be sanctified, and how to be sanctified has been the focus-set of this theory. Accordingly, the resulting questions of knowing and doing closely connect to the temperament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Ontology. Both Wu Cheng and Wang Yang-ming’s theory begin with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Wu-Cheng’s investigation of things and extension of knowledge was mainly focusing on the lack of Zhu Xi’s study by emphasizing the strength of Lu school to cover the shortage of Zhu Xi’s theory, and illustrating the unity of external and internal cultivation by taking the idea as its premise. Wang Yang-ming pointed out that Zhu Xi misunderstood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because he put the reason and mind second, and in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mind is principle”,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was neither internal nor external. They both had similar views on explaining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As to knowing, Wu-Cheng regarded the innate mind as knowing. He also believed that knowing only came from practice. Wu Cheng promoted the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behavior after analyzing the theory of knowing and doing in the aspect of “enlightenment is investigation, practice is truth”. But Wang Yang-ming claimed that knowing and doing and Ontology were inseparable from one another. First he explained that “knowing without doing is nothing”, and he further theorized that “knowing is practice”. Then he explained how knowing and doing came up with the unity based on the dynamic process of knowing-doing-knowing. In Wang Yang-ming’s opinion,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was a dynamic process. From self-knowledge to things-in-itself, the unity of knowing and action can be completed in the process of natural knowledge and actual knowledge. A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ing and doing, Wu and Wang both believed that they were a dynamic process and never took apart.
Wu Cheng; Wang Yang-ming; knowledge and behavior;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dynamic unity
2016-03-22
吳立群(1968-),女,江西崇仁人,上海大學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儒家哲學。
B244;B248.2
A
1673-6133(2016)03-00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