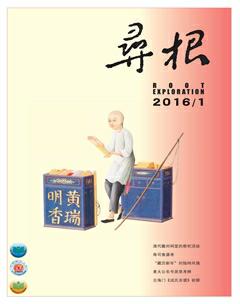汪曾祺筆下的清真食物與梨園行
楊秀明
談及“京味”,汪曾祺是不能繞過的作家。北京的清真食物在汪曾祺的很多作品里時常出現。比如在小說《講用》中,主人公郝有才在舞臺工作隊干雜活,是個極其普通的人,就是過日子仔細一點,干了件不大露臉的事:在回民食堂挑了五個羊蹄,趁著人多,售貨員沒注意,就沒給錢。又如另外一篇小說《撿爛紙的老頭》,開篇第一句是“烤肉劉早就不賣烤肉了,不過虎坊橋一帶的人都還叫他烤肉劉”(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接著作者描寫這家平民化的回民館子,東西實惠,賣大鍋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也賣小勺炒菜:大蔥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比較貴一點的是黃燜羊肉,不過“也就是塊兒來錢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臉盆端出來,倒在幾個深深的鐵罐里,下面用微火煨著,倒總是溫和的”(同上)。汪曾祺熱心描寫北京的清真食物,盡管自己是南方人,并不限于人們對于飲食的地域偏好。汪曾祺對清真食物的精心刻畫除了被羊肉的鮮美吸引,最重要的應該是對“野”味的愛好。回族的飲食帶有少數民族的獨特風情,這在食物較為精致化、程式化的古都北京更顯得另類,與傳統漢族的食物相比形成另一道風景。汪曾祺還曾將北京的清真飲食同梨園行的藝人聯系起來。汪曾祺認為,梨園行是北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沒有梨園行就沒有北京,也沒有京味”(同上)。他在《當代野人系列》中塑造的靳元戎這一回民京劇演員形象具有極強的個性,在時代的風云變幻中寵辱不驚、堅持自我,這與清真飲食通達樂觀卻又保持教門原則的特點“野”味相投,因此這種人物描寫并不是偶然。
最能表現清真食物“野”味的莫過于烤肉,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某種發明或本源性的權威地位。汪曾祺在《貼秋膘》一文中對烤肉的發源做了考證。他認為烤肉大概源于少數民族的吃法,日本人稱烤肉為“成吉思汗料理”,似乎是蒙古人的東西。《元朝秘史》記載成吉思汗一頓可以吃一整只羔羊,但似乎是白煮,即使是烤,也是整只烤,與北京的烤肉不同,因此對北京烤肉是蒙古料理的說法存疑。隨后,作者寫道:“北京賣烤肉的,都是回民館子。”(同上)齊白石為“烤肉宛”題寫“清真烤肉宛”,并在后面加注腳:“諸書無烤字,應人所請自我作古。”汪曾祺經過詢問語言文字學家朱德熙,得知古代字書上確實沒有“烤”字,這個字是近代人造出來的。可見“烤”肉從文字表層上已具有了十足的“野”味。同時,雖然汪曾祺指出“北京烤肉有名的三家:烤肉季,烤肉宛,烤肉劉”,這三家都是回民館子,但是并未企圖樹立清真飲食在烤肉上的正統地位。他去過回民集中的西北,如蘭州、烏魯木齊、伊犁和吐魯番,也并未發現如北京烤肉一樣的烤肉,羊肉串當然是另外一種。因此,北京的烤肉起源于何時,是哪個民族發明的都已不可考,但正是這種無所歸屬、無史可依的“野”味讓烤肉更加吸引被囚于文明都市中的人們。
汪曾祺對北京烤肉有詳細的描寫。首先,北京烤肉是在“炙子”上烤的。“炙子”是一根一根鐵條釘成的圓板,下面燒著大塊的松木或果木。“炙子”的鐵條之間有小縫,下面的柴煙火氣可以從縫隙中透上來,不但整個“炙子”受火均勻,而且使烤著的肉帶柴木清香;上面的湯鹵肉屑又可填入縫中,增加了烤炙的焦香。其次,北京烤肉并非如同其他菜肴經由廚師烹飪后裝盤上桌,而是店伙計將拌好作料的薄羊肉片、牛肉片交給顧客,用長筷子平攤在炙子上烤。“過去吃烤肉都是自己烤。因為炙子頗高,只能站著烤,或一只腳踩在長凳上。大火烤著,外面的衣裳穿不住,大都脫得只穿一件襯衫。足蹬長凳,解衣磅礴,一邊大口地吃肉,一邊喝白酒,很有點剽悍豪霸之氣。”(同上)這段精彩的講解,可以看出汪曾祺對烤肉行為的津津樂道并不亞于對美味的單純食欲。
烤肉的樂趣盡在于“野”味。火是人類走向文明的象征,同時它帶來的光和熱也具有原始社會的激情、詩意與自由。繼承了京派作家周作人、廢名和沈從文的一脈,追求閑適與自然的汪曾祺寫道:“從前北京人有到野地里吃烤肉的風氣,玉淵潭就是個吃烤肉的地方。一邊看看野景,一邊吃著烤肉,別是一番滋味。聽玉淵潭附近的老住戶說,過去一到秋天,老遠就聞到烤肉香味。”(同上)與“從前”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北京現在還能吃到烤肉,但都改成由服務員代烤了端上來,那就沒勁了。我沒有去過。”(同上)汪曾祺關于清真食物的散文不僅局限在對昔日烤肉“野”味的懷念,也通過獨特的人物形象寄托文化理想中的“野”味,比如《當代野人系列》中的靳元戎。
必須指出的是,汪曾祺在《當代野人系列》里描繪的“野人”有著雙重意味。第一種,即絕大多數“野人”,是“文化大革命”中盡顯人的獸性與荒誕的京劇演員。比如:庹世榮為了阻止乙派把走資派拉走,那樣的話自己所在的甲派就沒有批斗對象了,竟然躺在汽車前面威脅司機,這一“壯舉”使得全團對他刮目相看。耿四喜本來因為熟讀《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京劇界合稱為“三列國”)被送了個外號“耿三列”,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熟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每晚給黑幫輪流講馬列主義,他的外號變成了“三列馬”。以前在劇團打鑼,“文化大革命”時期擔任造反派頭頭的郝大鑼,為了挖反革命絞盡腦汁編造莫須有的罪名,指控編劇筆下的“大尾巴貓”是毛主席。造反派夏構丕是個流浪孤兒,雖然不識字卻還仔仔細細地翻看“我”寫的劇本,搜查反革命罪證,還鬧出了“去年屬馬”的笑話。唱丑角的葉德麟是個汗包,動動就出汗,臺上沒戲,但很有組織行政才能,擔任演員隊隊長,逢年過節演員們多想走葉德麟的門子。“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的親信掌管劇團,把原來黨委的老班底全部踢開,只留隊長葉德麟。他本以為自己深受領導賞識,卻發現去澳大利亞出國的事沒有他,領導壓根兒沒把他當作自己人,他差一點當場暈死過去。以上這幾位“野人”,在政治運動里暴露出人性中陰暗和獸性的一面,“盲從、自私、殘忍、野蠻”(同上),作者由此呼吁我們的民族文明起來。
如果說這次“野人”群像的繪制全在于揭露民族心理的扭曲也是不準確的,因為汪曾祺也在“系列”中塑造了健康的“野人”,即第二種“野人”形象靳元戎。與此前對“野”的負面意義的展示不同,靳元戎身上的“野”是隨遇而安,與人為善,對待人生沉浮的單純淡然,帶有一種積極意義。這種“野”是樸拙無華的人性本真。作為“系列”中最后出場的一個人物,他給作品帶來了唯一的光亮色彩,寄托了作者的文化理想與希望。他是眾多“野人”中唯一得到善終者。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出了大風頭的庹世榮血壓高得異乎尋常,抽的一管血里有半管是油,最終沒有入成黨,遺體比平常瘦小了好多,“他抽抽了”(汪曾祺:《汪曾祺文集》,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耿四喜死于大面積心肌梗死,追悼會上,“火葬場把蒙著他的白布單蓋橫了,露出他的兩只像某種獸物的蹄子的腳,顏色發黃”(同上)。郝大鑼沒有當上局長,得了小腦萎縮,對過去的事什么也想不起來了。葉德麟也死于大面積心肌梗死急性發作,參加追悼會的人稀稀落落,大家都對他沒感情,因為他對誰也沒有感情。《當代野人系列》的最后一句是“他現在還活著,但已是滿頭白發,老矣”。這個“他”便是靳元戎。
靳元戎的性格特點是“凡事看得開”,“說話很‘個”(同上)。“四人幫”時期,他被精簡下來,下放到干校勞動。與其他人滿腹牢騷不同,他在干校地里織網逮麻雀,把逮的麻雀撕了皮,醬油、大料腌透,入油炸酥下酒,或是捉螞蚱,摘去翅膀放在瓦片上烘干,卷烙餅,活得有滋有味,自得其樂。面對干校“領導”一再要求提高生產指標,靳元戎和“領導”逗樂,提出把地掏空了種兩層糧食的“建議”。靳元戎在劇團唱丑角,“四人幫”垮臺后回到劇團,擔任演員隊的隊長。由于秉公辦事和平等待人,他和周圍人的關系很好,對誰的稱呼都是“爺們兒”。“他好吃,也會做。有時做幾個菜,約幾個人上家里來一頓。他是回民,做的當然都是清真菜:炸卷果、炮糊(炮羊肉炮至微糊)、它似蜜、燒羊腿、羊尾巴油炒麻豆腐。有一次煎了幾鐺雞肉餡的鍋貼,是從在雞場當場長的老朋友那兒提回來的大騸雞,撕凈筋皮,用刀背細剁成茸,加蔥汁、鹽、黃酒,其余什么都不擱,那叫一個絕!”(同上)除了簡單的調料“其余什么都不擱”帶來的美食之“絕”,無疑也是一種對單純、簡單和自然“野”味的追求。回族演員靳元戎的語言也頗具特色。他好喝酒,又得過心絞痛,有人勸他少喝一點,他說:“沒事,我喝足了,就心絞不疼了。”(同上)“文化大革命”期間,有同行狠斗同是唱丑的馬富祿,靳元戎認為太過火,就說:“你就是把馬富祿斗死了,你也馬富祿不了啊!”(同上)“心絞不疼”和“馬富祿不了”都是“欠通至極”的語言,但是出自一位閑淡瀟灑、怡然自得的“當代野人”之口,卻是十分通順質樸、合情合理的。
在靳元戎之外,汪曾祺的一篇小說《晚飯后的故事》講到了京劇演員郭慶春與胡同口賣“炒疙瘩”的許大娘、許招弟的故事。因為郭慶春的家貧和倒倉(年輕的京劇演員變聲),與其青梅竹馬的許招弟嫁與他人,多年以后成名的郭慶春帶著復雜的心情把許招弟的女兒招進了劇團。雖然文本沒有言明后者的回族身份,但“炒疙瘩”是北京特有的一種清真小吃,源于北京有名的回民飯館“穆家寨”,由穆老太太和她的女兒創辦。后者則是京劇演員馬連貴的夫人、馬連良之弟媳。因此這個梨園行的故事原型與回民也有一些關聯。
至于北京的清真食物與梨園行的特殊聯系,深諳北平美食與民俗的滿族作家唐魯孫認為,“早先梨園行的人好住在南城外,不管哪一工都要注意保護嗓子的。大家都認為吃豬肉最愛生痰,所以不論大教、清真教、梨園行的朋友,都喜歡到教門館吃牛羊肉。兩益軒占了地利的好處,于是就讓梨園行給捧起來了”,“馬連良在梨園界可算是美食專家,只要是對蝦季兒,一到兩益軒定先來個烹蝦段滲酒,跟著再來一個兩個都說不定”。(唐魯孫:《再談吃在北平》,載于聯副三十年文學大系編輯委員會編《散文卷七·人間壯游》)除了這個客觀原因,汪曾祺對北京清真食物與梨園行的書寫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聯系。第一,二者都具有突出的平民化特點。與過士行筆下給“他者”帶來不小壓力的東來順涮羊肉不同,汪曾祺筆下的清真烤肉并未強調其技藝的高超和烹飪的難度,反而格外強調其平民性,甚至以一句“烤肉劉早就不賣烤肉了”,干脆打破了老字號給平常人帶來的權威感和隔膜感。汪曾祺筆下的京劇演員很少大富大貴,童年學戲生活很苦,被稱作“蹲了八年大獄”。靳元戎做的清真菜工藝并不復雜,許大娘給郭慶春做的炒疙瘩無非“放了好些牛肉,加了半勺油”(汪曾祺:《晚飯后的故事》,《人民文學》1981年第8期),出現在汪曾祺筆下的清真食物和梨園行都是最普通、親切和平民化的。第二,清真食物與梨園行之間最重要的連接點在于二者的“野”味相投。這種“野”不是庹世榮、耿四喜、郝大鑼、葉德麟之流對社會人性的摒棄和向自私獸性的屈服,而是一種對散淡人生的享受。無論是汪曾祺對清真烤肉樂趣的追求,還是對京劇演員的描摹,他所熱衷刻畫的都不是精致,而是“野”味。這種“野”味是中國文人的一種詩意理想,它看重“個體生活的自適”及友好和諧的人際關系。清真食物與梨園行在汪曾祺筆下的相遇不是偶然,對“野”的回味是對人與人最初相遇時的真誠和信任的懷念,作品將單薄的食物敘事推向了民族交往情感的更深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