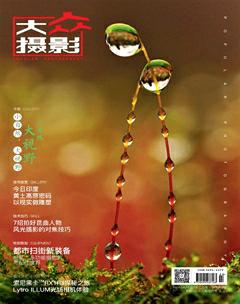越過山丘步履不停
楊越巒 張甘
楊越巒拍攝的野長城專題近年廣受關注,作為攝影家,他在熟悉的題材上不斷創新。作為地方攝協的工作者,他希望能夠引導本地攝影家做轉變,希望找到與本土與當下匹配的攝影工作組織方式。
2015年12月30日早上六點多,楊越巒從杭州輾轉上海坐了一夜火車回到石家莊,他剛剛去杭州參加了“戰爭時期的中國攝影”國際研討會,第二天下午,又要出席一個攝影活動現場,之后再乘深夜的火車趕往秦皇島,用元旦假期拍攝那邊的野長城。“我現在有在火車上記日記的習慣,我算了算,今年有一百八十多天出差,大部分都是坐火車,出差和職務工作占的時間多了,出去拍照的時間就少了,需要擠。”從2009年起,楊越巒持續拍攝野長城已經六年,拍攝范圍也從河北擴展到全國。
楊越巒1985年從河北師范學院畢業,作為從中學開始就有文學夢,大學時期發表過作品的“文學青年”,他的志向是當作家。畢業后他留校在宣傳部負責校報的編輯,工作需要拍照,于是拿起相機,成了一名攝影愛好者。“當時的熱情還是在文學,在寫東西上”。
1989年,楊越巒離開河北師范學院,調到省稅務局的一本雜志工作。因工作關系,他與河北省攝影家協會有了工作往來,接觸到一些攝影家,越來越多的發現了攝影的樂趣;接著就是參加協會組織的攝影函授班,成了不折不扣的“發燒友”。至于拍長城,是很早就開始了,“以前就是拍風花雪雨,司馬臺、金山嶺、箭扣這些地方,云海、日出、下雪,就沖著這樣的天氣去的,至于拍攝思路發生的變化,和我在省攝協工作,接觸信息比較多有關,這個變化有個節點,這很明確”。
2009年4月,為組織雞鳴驛的攝影展覽,楊越巒和一些攝影家來到河北省懷來縣雞鳴驛拍攝。為了挖掘更多的攝影資源,在當地朋友帶領下,他們來到了陳家堡長城。和八達嶺、金山嶺等近年整修過的長城不同,這里的長城保持著原始的狀態,“城磚散落,雜草叢生,就是驢友們常來玩兒的野長城。眼前長城的這種狀態特別能打動人。有一次和李樹峰老師交流,他說這么多人拍長城,但是對長城歷史滄桑感的表現不夠。他這話提醒了我,強化了我的這個意識”。由此,他開始拍攝河北境內的野長城。幾個月后,他由一組野長城作品獲得了第八屆中國攝影金像獎。
談到獲得金像獎,楊越巒覺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他覺得河北有豐富的攝影資源,省攝協的組織工作在李英杰主席的帶領下做得比較好,所以河北的攝影在“國展”中成績一直不錯。但是河北攝影呈現較單一的沙龍攝影風格,多樣的攝影創作、多元的攝影家群體沒有建立起來。“時代在發展,社會在進步,唯美的東西不能作為攝影的全部內容,我覺得需要多元化,需要更多關注河北本土的攝影。但是你空口對別人說應該怎樣去做,缺乏示范意義;我想能不能從自己的攝影下手,作一個探索實踐,那就從拍長城開始”。在攝影家的身份之外,楊越巒的另一個身份是河北省攝影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他考慮的很多問題,是關于河北省的攝影該如何發展,如何為河北的大局服務。
在之后的幾年中,他持續拍攝河北境內的:野長城,并在2012年推出畫冊《中國·野長城》,在業界獲得了一定反響。他并未停止拍攝的腳步,如果說畫冊中的作品是一種蒼涼而非唯美的、寫實而非浪漫的風景,那么在2015年內的幾次展覽中,他的這個“長城項目”距離傳統的風光攝影專題更遠了。他開始拍攝全國范圍內的長城,也將拍攝內容由野長城風景擴展到長城周邊的人居環境和產業狀況:長城腳下的“空心村”,長城內外的經濟建設,甚至是一些荒敗、荒唐的景觀。這個“長城故事”的語氣在變,長城也在他鏡頭中退到更遠處,成為觀察、紀錄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背景。
對于主持河北省攝協日常工作的楊越巒來說,省攝協工作所面臨的轉型是一個嚴峻的課題,要引導河北攝影人關注現實,關注身邊。并且突出鮮明的個人特色,這確實是個難題。“這一點也成為省攝協主席團的共識,主席劉瑞新和幾位副主席都開始了自身的攝影實踐。現在的攝影展覽活動頻繁,但征上來的作品常常并不理想,浮光掠影的多,深入生活、反映現實的少。多數攝影人還沒有這個意識,多停留在娛樂的層次。這就需要我們進行引導和培養,對我們的組織、展示、傳播工作是很大的挑戰”。上一屆“省展”在作品分類方面做了比較大的調整,取得了一定成效。新的一屆“省展”正在醞釀更大的改革,用楊越巒的話說是“壯士斷腕”:甚至可能取消單張作品,對投稿的要求就是組照、專題和系列作品。這更是前所未有的挑戰。
“這幾年河北攝影界的變化還是明顯的,不少攝影家開始拍“自己的東西,比如邯鄲的王進元拍攝太行山傳統村落,唐山的劉曉冬拍鋼鐵企業,石家莊的李君放拍家鄉的抗戰老兵,秦皇島的肖吉地拍家鄉的大海與鄉村……這些都不是一張作品,都是專題性的拍攝。”
談到影像方式轉變的問題。楊越巒感覺這不僅是河北省的問題。“例如反映鋼鐵企業的攝影作品,以前給人的印象就是鋼花四濺,工人汗流浹背,那種方式的工業生產現在已經非常少了,不具備代表性,是正在被淘汰的落后產能。但現在你看全國影展,那樣的東西還在拍。說到工業影像,如果不是傳統的浪漫抒情或是控訴式的,那么現代工業應該在影像上如何表現,怎樣實現這個轉變和突破?”他一直在思考這個課題,如何從拍攝理念、表達方式上進行突破,找到匹配今日中國社會發展的影像表現和攝影工作組織方式。
在與其他省市攝影組織的交流中,楊越巒常常感到差距。說起各地攝影的發展,他如數家珍。從實力雄厚的河南攝影家群體,四川省近些年涌現的青年攝影師群體,浙江省的“新鋒計劃”,“攝影新銳”等這些帶有導向的活動,他都非常關注。“局限于自己的年齡和知識結構,對年輕人的東西設有完全理解,但這些對我也有啟發。實際上自己的思想很老套了,必須盡量學習,跟上這個時代。”2016年,他計劃辦兩次“攝影工作坊”,第一次是做具有當代意味的紀實影像,第二次則側重傳統紀實影像。省攝協做組織發動工作,邀請有創作實力的中青年攝影骨干參加學習。“我覺得做工作坊可能是突破的一種方式,也有思想準備,這一期可能會讓很多人摸不著頭腦,但是我想先對這些人的理念有一些沖擊,逼著大家去做更專業的攝影思考和實踐。”
楊越巒曾經是一名“文學青年”,這是一個帶有八十年代印記的詞匯,在出版《中國·野長城》之前,他曾經出版過文學作品集《青春牧歌》,散文、攝影作品集《聆聽自然》。說到當年自己由稅務系統轉來從事攝影工作,他說:“我可能還不算特別務實吧,在內心里我是個有點浪漫情懷的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