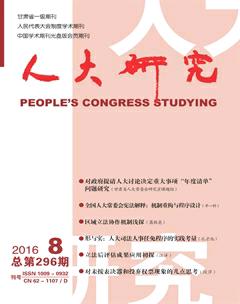關于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幾個具體問題的思考
董高群
2015年3月15日,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作出修改立法法的決定,賦予設區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這對完善我國立法體制,促進地方治理法制化建設,無疑會產生深遠影響。但從地方立法權行使的實踐層面觀察,仍有幾個問題待廓清。
一、關于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邊界
地方立法權作為一種重要的公權力,必然要遵循職權法定原則。奧地利法學家凱爾森甚至認為,一個并不作為國家機關而起作用的個人,被容許做法律秩序所并不禁止他做的任何一切事情,而國家,即作為一個國家機關而起作用的那個人,卻只能做法律秩序授權他做的事情[1]。所以,從法律技術的角度來看,禁止國家機關做任何事情都是多余的,不授權它就夠了。大概基于“公權力法無授權不可為”尚未成為公權力行使者的自覺,相關法律對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力邊界既有正向列舉,也有反向列舉。
1.立法調整的事項范圍。我國國家結構形式是單一制,因此,地方立法權源于中央的授權,而且立法的范圍有限。總體而言,僅限于三類事項。一是執行型立法。即為貫徹法律、行政法規,結合本行政區域實際作出具體規定。二是特色型立法。即地方事務,不需法律、法規和本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對此作出統一規定或者在可預見的期間上位法不會對此作出規定。三是實驗型立法。在上位法沒有規定,而實踐中確有必要調整的事項,先行一步立法。而設區的市還僅限于三類事項中的三個方面事務,即城鄉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三方面,雖立法法表述為等事項,但作為授權法律,應作限縮解釋,即為等內而非等外。此外,還不得涉及國家立法權事項:國家主權的事項;國家機關的產生、組織和職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特別行政區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犯罪與刑罰;對公民政治權利的剝奪、限制人身自由強制措施和處罰;稅種的設定、稅率的確定和稅收征收管理基本制度;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征用;民事基本制度;基本經濟制度及財政、海關、金融、外貿的基本制度;訴訟和仲裁制度。
2.不得與上位法相抵觸。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不得與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特別是不得超過法律法規規定的權限設定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處罰法規定,地方性法規不能設定限制人身自由、吊銷營業執照的處罰措施。行政許可法規定,地方性法規可以設定行政許可,但不得設定統一由國家確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資格、資質的許可。同時,法律法規已對某一事項作出規定并沒有設定行政許可的,地方性法規也不得設定行政許可。行政強制法規定,地方性法規只能設定查封、扣押的行政強制措施,不能設定行政強制執行措施。
上述規定為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確立了邊界,但有些模糊區塊尚待明晰。一是可否制定討論、決定重大事項的地方性法規?人大及其常委會有討論、決定重大事項權,地方組織法對此僅作了原則性的規定,具體哪些屬于重大事項,以及如何討論、決定重大事項,以前沒有立法權的市一般通過制定規范性文件進行明確。設區的市開始行使立法權以后,能否上升為地方性法規?肯定的理由,是討論、決定的重大事項大體屬于城鄉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三方面。而且,省級人大常委會一般都制定有相應的地方性法規。否定的理由,是討論、決定重大事項的相關規定,屬于人大常委會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的程序性規定,不在城鄉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范圍之列。二是中央專屬立法事項可否授權地方制定地方性法規?立法法僅規定經濟特區所在地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可以獲得授權,制定經濟特區法規。但其他地方也有一定的需求,如稅種的確立、稅率的確定屬中央專屬立法權,但房地產稅顯然屬地方稅種,各地情況千差萬別,如何確立和開征交由地方決定更具合理性。這些問題,都有待相應的解釋加以明確。
二、關于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位階
所謂位階,是指每一部法律在法律體系中的縱向等級,下位階的法律必須服從上位階的法律。我國的立法體制是一元多層次:一元即只有一個法律體系,不同于聯邦制國家;多層次,是在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擁有國家立法權的前提下,還存在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立法。但立法法沒有具體明確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位階,而且依照對相關條文的理解,存在前后矛盾。立法法第七十二條第二款規定,設區的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在不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本省、自治區地方性法規相抵觸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規。依照此款理解,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位階應該在本省、自治區制定的地方性法規之下。該款又規定,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須報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批準后施行。第九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第四項規定,省、自治區人大有權改變或撤銷本級人大常委會制定或批準的地方性法規。依照這些條文的理解,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位階與本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應該相同,而且在本行政區域內,如與本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其他地方性法規不一致的,應按照新規定優于舊規定,特別規定優于一般規定辦理。
還有,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與本省、自治區政府制定的規章的關系。立法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規定,地方性法規的效力高于本級和下級政府的規章。如果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等同于本省、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則顯然高于本省、自治區政府制定的規章;如果低于本省、自治區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則其與本省、自治區政府制定的規章之間,還無法判定位階的高低。
筆者認為,既然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由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批準,其位階應與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相同。這樣,也便于實踐操作。
三、關于“不適當”的外延
不適當,作為法律語言,一般指不合理,不公平。按照慣常語言習慣,其外延僅限于合理性判斷,不包括合法性判斷[2]。《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導讀與釋義》中將其界定為:(1)要求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執行的標準或者遵守的措施明顯脫離實際;(2)要求公民、法人、其他組織履行的義務與其所享的權利明顯不平衡;(3)賦予國家機關的權力與要求其承擔的義務明顯不平衡;(4)對某種行為的處罰與該行為應承擔的責任明顯不平衡,違反比例原則。但地方組織法、監督法、立法法中對“不適當”外延的界定不盡一致,甚至同一法律不同條文之間也有不一致。地方組織法第八條第十項,立法法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四項中的“不適當”,應該既包括不合理,也包括不合法。監督法第三十條更是明確不適當的情形包括:超越權限、與上位法相抵觸以及其他不適當的情形。但立法法第九十六條第四項規定,規章的規定被認為不適當,應予改變或者撤銷的。與之并列的第一、二、五項分別規定為:超越權限、違反上位法規定、違背法定程序,均為不合法的范疇。依照邏輯推理,第四項應為不合理范疇。筆者認為,從長遠來看,應通過相關法律的修改,使其一致。當前,宜通過解釋,明晰“不適當”在不同條文中的外延。
四、關于省、自治區與設區的市之間立法資源的配置
立法法對省、自治區和設區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規的權限僅作了原則性規定。相同的是,二者均限于執行型立法、地方特色型立法、實驗型立法三類;不同的是,設區的市立法范圍更窄,只包括城鄉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三方面。立法實踐中,二者共同作為地方性法規的制定主體,特別是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還要對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行使批準權,因此,合理配置立法資源,既避免重復浪費,又相互協調吻合,就尤為重要。筆者以為,省、自治區制定地方性法規應偏重兩方面:(1)城鄉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之外的事項;(2)涉及城鄉建設和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方面的事項,僅作原則性規定,盡量給設區的市立法預留出空間。而設區的市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應講求可操作、有特色,立足拾遺補缺,切忌貪大求全,照搬照抄。此外,省、自治區與設區的市人大常委會之間應就立法規劃、立法計劃的編制做好銜接,保持一致性。
五、關于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解釋程序
有一句法諺,法律從制定的那一刻起,它就落后了。其固有的滯后性和不周延性,是無法克服的弊端。解決這一問題的思路,除了修改、廢止外,解釋是一個重要途徑。法律需要解釋,地方性法規同樣需要解釋。立法法第四節僅規定了法律的解釋程序,其他法規、規章都只能參照。而行政法規、規章及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地方性法規皆可以由制定機關參照制定程序進行解釋,但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制定機關和批準機關不同,其解釋程序不能直接類比。這是法律規定的不明確,造成立法實踐中的混亂。有的由制定機關解釋,然后報批準機關備案。如《蘇州市制定地方性法規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地方性法規解釋草案經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后,由常務委員會發布公告予以公布,并在公布后十五日內報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有的僅規定由制定機關解釋,沒有規定向批準機關備案。還有的要求報請批準機關批準。筆者認為,既然設區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規的批準機關是省、自治區人大常委會,就應賦予其必要的監督權,以便對越權解釋或者解釋不適當及時進行處理,但基于工作量的考慮,建議由制定機關通過后向其備案。當然,這一方式也有待制定相關程序性法規時加以完善。
參考文獻:
[1]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商務印書館,第378頁。
[2]喬曉陽:《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導讀和釋義》,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第300頁。
(作者系湖南省常德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