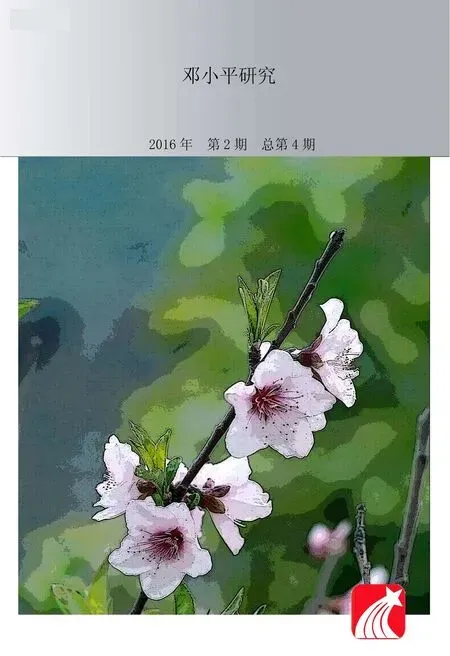論鄧小平對新解放區土改政策轉變的歷史貢獻——重溫《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
何 薇 趙曉丹
(西南交通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 成都 611756)
?
論鄧小平對新解放區土改政策轉變的歷史貢獻
——重溫《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
何薇趙曉丹
(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四川成都611756)
〔摘要〕1947年秋,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挺進大別山,開辟新解放區。為了在大別山站穩腳跟,鄧小平把土地改革作為創建根據地的有力武器,緊密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以敏銳的洞察力、堅定的原則精神、細致周密的觀察思考,親自起草了《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六六指示”系統地提出了新區農村土改的工作方針和策略步驟,即在中原地區實行分區域、分階段的“雙減”土地改革政策,將新區分為三個不同區域采取不同的調整政策,堅決糾正土改中“左”的錯誤傾向和城市工作中的“左”傾偏向,從而為中共中央關于新區土改工作政策的轉變和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六六指示”蘊含著豐富的政策、策略思想,顯示了強烈的務實性和人民性,彰顯了鄧小平依靠群眾、一切從實際出發、大膽實踐、心系民生的優秀品格。
〔關鍵詞〕鄧小平;“六六指示”;新區土改
1947年7月7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了紀念抗戰十周年的口號,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命名為人民解放軍,隨著中共在軍事上轉入全面進攻,“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強勁有力的戰爭動員口號。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軍各路大軍在中共中央統一部署下,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進攻的主要方向是中原地區,中原南部的大別山地區是重點。出擊中原,建立根據地,就可以南扼長江,東懾南京,西逼武漢,直接威脅江南。〔1〕為了加強統一領導和組織各方面力量,確保這一戰略任務的完成,1947年5月16日,中央決定組成以鄧小平為書記的中原中央局。6月30日晚,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四個縱隊12萬余人挺進大別山,開辟新解放區——大別山根據地。為了在大別山站穩腳跟,鄧小平把土地改革作為創建根據地的有力武器,推行了一條適合新解放區(以下簡稱新區)的土改政策,把“平分土地”政策,轉變為“減租減息”政策,在中共關于新區土改工作的政策轉變和形成中作出了重要貢獻。
關于鄧小平對新區土改政策調整的歷史作用和貢獻,學界最早的研究成果是冷溶的《鄧小平與新解放區農村工作政策的轉變》,他將新區農村工作政策的轉變分為三個階段,分別論述了鄧小平在不同階段的具體貢獻,對鄧小平起草的《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作了富有權威性的解讀。〔2〕在這之后,1994年7月《黨的文獻》第3期登載了《毛澤東、鄧小平關于根據地工作的來往文電選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六月)》〔3〕,披露了一組珍貴檔案文獻,帶動了國內學術界開始研究鄧小平創建大別山根據地的貢獻和作用,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毛澤東、鄧小平與新解放區土地政策的形成》〔4〕、《鄧小平與新解放區急性土改的停止》〔5〕等。2014年在主題為“鄧小平與中國道路”的全國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有兩篇文章論及“鄧小平與大別山新區土改”〔6〕和“鄧小平與大別山根據地的創建”〔7〕。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學界充分重視并肯定了鄧小平在新區土改政策轉變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我們認為,還需要對1948年——這個重要的歷史節點進行深入研究,梳理其間鄧小平與毛澤東往來電文,對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的鄧小平親自起草的《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以下簡稱“六六指示”)進行文本分析,進一步弄清楚1948年中共中央是如何完成新區土改政策轉變的,從而也能更清晰地展現鄧小平從中所起的關鍵作用。
一、對大別山根據地進行實際調查
1947年6月21日,鄧小平在晉冀魯豫野戰軍直屬隊股長營級以上干部會議上作了戰略反攻的動員報告,他用特有的川北口音生動地說道:“從軍事上看,敵人采取重點防御,我們就占‘面’,有機會就占地方。地方占多了,人口增加了,兵員解決了,財政也解決了。……能不能站住腳?能,一定能夠站住腳!客觀條件是具備了。但有一條,要看我們三大任務*“三大任務”是指作戰、發動群眾和籌款籌糧。完成的好不好。”〔8〕為了使正在勝利挺進的解放戰爭獲得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支持,必須充分調動廣大農民的革命和生產積極性,更加普遍深入地開展土地制度的改革運動。按照中央指示,中原局一進入大別山,就把發動群眾進行土改作為戰略展開的一項重要任務。1947年10月12日,鄧小平起草并簽發了《關于放手發動群眾創造大別山解放區的指示》,提出要把土改作為創建根據地的有力武器,堅決反對右傾現象,在有初步基礎的地區,立即放手發動群眾分浮財、分田地。中原局積極響應和貫徹中央精神,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央批示:“我們認為中原局此一指示完全正確,一切進入國民黨區域作戰及工作的部隊完全適用此指示所指出的方針及辦法,望各地轉飭所屬,一體遵行。”〔9〕
但是,這場急風暴雨般“徹底平分土地”的群眾運動,在許多地區出現了擴大打擊面的“左”的偏向。許多地方喊出了“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對民族工商業戶征收過重的捐稅;對地主和富農、地主中的惡霸和非惡霸地主不加區分,以同樣方式進行斗爭,甚至一度發生“掃地出門”和亂打亂殺的現象;在一些新區還出現了形式主義的假分地。中共中央從1947年底著手糾正這些錯誤,但隨之而來又出現一個新問題:1947年7月至9月,人民解放軍在各戰場相繼轉入戰略進攻后,一批新解放區紛紛創建起來,中共中央對新區的具體情況不是很了解,這些區域又該如何進行土改呢?為此,1948年1月14日,毛澤東致電鄧小平從六個方面詢問新區情況,特別征詢新區土改的問題:“(一)在新區是否應當分為兩種區域,一種是可以迅速建立鞏固根據地的,一種是要經過長期拉鋸戰才能建立鞏固根據地的,對兩種區域的工作采取不同政策?(二)新區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綱分平,還是對富農及某些弱小地主暫時不動?新區中富農及弱小地主的態度如何?(三)是否有開明紳士和我們合作?(四)是否有許多知識分子和我們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階層商人態度如何?我軍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區工商業資本家進行籌款?如果籌款,方式如何?(六)如何處理國民黨政府、黨部、三青團的各種人員?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爭取的?如何處理保甲長?”〔10〕
在接到毛澤東征詢新區土改情況的電報后的第二天,鄧小平和劉伯承就回復毛澤東,報告了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進入大別山四個月來的發展情況:“現在看來我們業已站住,不管情況如何嚴重,敵人是攆不走我們的。……其關鍵在于完成土改、消滅土頑兩件大事”,“近來各地已開始獲得經驗,采取結合土改消滅土頑,耐心爭取群眾,劃定區域,統一軍區領導,這樣消滅土頑是不會難的。”〔11〕1月22日鄧小平再度致電毛澤東,結合大別山根據地的情況,對新區土改問題向毛澤東和中央作了更詳細的回答。首先,電文說明了大別山的政治形勢特征是:地主、富農有很高的政治警覺與豐富的反革命經驗,群眾則經過了多次失敗的教訓,不敢輕易起來,凡是執行貧農路線與消滅地主武裝有成績的地方,工作很易起來,并提出8月初地主、富農就已經開始逃跑。如果對地主不是一律“掃地出門”,而是給以生活出路的政策(分田、沒收,給逃亡地主留了田),可以爭取大部分中小地主回家經營田產。其次,電文分析了大別山(包括鄂豫、皖西兩區)貧農的現狀,提出應該實行充分的貧農路線,滿足貧農要求,對策是將富農的糧食、耕牛、農具、土地、埋藏現金分給貧農,以此才能解決貧雇農生活困難的問題。同時要注意在對小地主的衣物、家具進行分配時,要留出自用的部分,不能一掃而光。第三,明確提出在土地平分中最大的問題是對中農的方針,認為在新區一般采取中農不動的政策為好。第四,大別山根據地有1200萬人口,經歷了蘇維埃土地革命和抗日戰爭兩個時期,土地革命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以及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均對各階層發生了很深影響。鑒于這些因素,鄧小平認為,應該在這個地區劃分兩種區域,即鞏固區和游擊區。在鞏固區可以進行土改,在游擊區暫時“還談不上平分土地,應該深入宣傳土地法大綱。對一般的小地主、富農應該暫時不動,但對其中的反動分子,則堅決打擊沒收”〔12〕。
在電文中,鄧小平明確表述要根據新區特點區分兩種不同區域,分別實施不同的土改政策。與鄧小平聯系和交換意見后,毛澤東對新區如何實施土改心里有了底。2月3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指出:土地法實施應當分三種地區,即新區、老區、半老區,三種地區分別采取不同策略。這封電文明確指出新區的劃分標準,即1947年8月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區,叫新區。這些地區實行土改應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中立富農,專門打擊地主,先分打地主的浮財,分大中地主的土地,照顧小地主,然后再分配地主階級的土地;第二階段,將富農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財產予以分配。毛澤東特別叮囑,土改不能性急,“新區土改第一階段,大約須有兩年時間;第二階段,須有一年時間”,“老區和半老區的土地改革和整黨,也須要三年時間(從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辦不好”。〔13〕
從鄧小平與毛澤東電文來往的時間和內容看,毛澤東顯然是吸收了鄧小平關于“新區土改分兩種區域”的主張。在鄧小平提出的意見的基礎上,中央開始制定新區土改的具體政策。2月6日,毛澤東向鄧小平征詢了對新解放區土地改革的斗爭策略和組織形式的意見。〔14〕隨即鄧小平在2月8日復電毛澤東,提出新區土改工作應分階段、分區地逐步深入的意見,提出暫時不斗富農底財,對小地主不能一掃而光,對中農打亂平分要采取自愿原則,不要勉強。〔15〕毛澤東收到鄧小平電報后,表示十分贊許,并于17日將鄧小平8日來電轉發給各區并附上了批語:“(一)小平所述大別山經驗極可寶貴,望各地各軍采納應用”;“(二)分階段分地區極為必要”;“(三)確定先組織貧農團,樹立貧雇農威信,幾個月后再組織農民協會,團結全體農民,并嚴防地富及壞人混入”。〔16〕
在向中央提出新區土改工作應分階段、分區進行的意見后,3月8日鄧小平致電毛澤東,對進入大別山后發生的“左”的錯誤作了分析,認為錯誤的根源在于“左”傾冒險的急性病,具體指出了六個方面的錯誤表現。〔17〕對鄧小平既正確評價成績和缺點、又勇于自我批評的態度和精神,毛澤東非常贊賞,3月14日毛澤東致電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負責人,轉發鄧小平的這份電報,特別在批語中表揚說:“小平同志的這些負責的自我檢討是非常好的。有了這樣的自我檢討就有使廣大干部逐步學會黨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的可能。”〔18〕毛澤東進一步重申:“沒有全般的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中國革命是永遠不能勝利的。最可怕的是領導同志的自滿自是,自己缺乏策略觀點與政策觀點,而又對中央的指示熟視無睹(不細看這些指示,不研究這些指示,忙于不應當忙的事務工作,而忽視了策略指導與政策指導這種自己責任上的主要工作)。”〔19〕
這段文獻充分說明,鄧小平進入大別山后立即進行調查研究,密切關注土改運動的發展,采取措施,制定對策,及時糾正“左”的偏向,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前委負責人中起到了表率作用。這不僅對人民解放軍在大別山根據地“站穩腳跟”至關重要,也為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健康進行提出了重要的、符合客觀實際情況的正確思路。
二、新區土改政策醞釀和“六六指示”出臺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土地改革運動進一步在新區開展起來。但由于沒有從發動群眾、提高群眾政治覺悟入手,中央的土地改革政策就成了形式主義的假分田。對于部分干部沒有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就盲目開展土地改革,鄧小平大為光火,他親自進行調查研究后得出結論:“統計起來約有八十萬人到九十萬人分了田,以鄂豫、皖西這兩個軍區來看,只占十二分之一,而這八十萬人中間還有極大部分假分田。可以確定百分之九十九是假的。”〔20〕為了糾正土改中分浮財和分田地過程中存在的一些“過火”錯誤,1948年元旦前后,鄧小平帶頭來到河南新縣、安徽金寨、湖北麻城等地檢查工作。緊接著4月份,鄧小平又率中原局、中原軍區機關在鄂豫皖和豫鄂陜兩個大區進行大面積調查。他確定:在新區,不管是何種地區,馬上動手分浮財、分土地都是不合時宜的,黨的主要精力應該放在發展農業生產、穩定社會正常秩序、為戰爭做準備等方面。
1948年4月24日,鄧小平在豫西干部會議上針對新區土改問題作出指示,要求新區工作要以土改為中心,結合實際,講究策略和依靠群眾,否則,“就是分了地,也是拿不穩的,地主是會反攻的”〔21〕。并且根據中央指示,他重申中原局的土改政策就是消滅封建地主,只有團結百分之九十的中農,才能完成土改任務。〔22〕
緊接著第二天的4月25日,鄧小平在河南魯山縣召開的豫陜鄂前委和后委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提出了躍進中原的勝利形勢與今后的政策策略。鄧小平嚴正指出:“現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據地的經濟建設好。”〔23〕他特別強調:“策略的意義,在于排除障礙,使得我們可以大踏步地正確前進。”〔24〕
5月9日鄧小平致電毛澤東,提出豫皖蘇、豫陜鄂地區當前工作的重點要放在財經工作上,“即依原來工作情況、干部強弱,選擇重點,創造典型,積累經驗,訓練干部,準備今冬明春大的土改運動”〔25〕。中央和毛澤東非常重視鄧小平為書記的中原局立足大別山根據地所進行的組織工作,明確表示:“我們正以你們為模范,要求全黨全軍均面向蔣管區,將戰爭引向更遠的敵后,同時加強解放區在土改后的生產、節約、支前”〔26〕。在電文中還特別叮囑鄧小平:“目前中原正處在作戰及地方工作的有利而又緊張時期,鄧小平不宜離開,等冬后看情形再定是否可來中央面談一次。”〔27〕字字情切,表達了黨中央和毛澤東牽掛著新區土改政策的實施以及新區的經濟建設問題,也表現出對鄧小平寄予厚望與重托。
以實干著稱的鄧小平在一個星期后的5月15日主持召開了中原局豫西陜南負責人會議,會議確定了今后陜南豫西的工作方針:(一)建立反蔣胡(宗南)的統一戰線,包括一切反蔣胡的地方實力派,在政治上只打擊首惡分子。(二)不分浮財,不打土豪,連大地主也不打。(三)實行征借糧食、款子的政策,解決軍需。(四)保護一切工商業。關于這次會議的情況,5月29日鄧小平隨即向中央和毛澤東作了詳細匯報,就會議制定的關于中原地區的土地改革、工商業等方面的工作方針向中央請示。〔28〕這次會議將中原地區新區土改方針確定為:在政治上只打擊首要分子,即惡霸、反革命分子和鄉保長中最反動的分子,不分浮財,不打土豪,連大地主也不打。〔29〕
3月27日到3月29日,毛澤東同周恩來、任弼時到達晉綏邊區領導機關所在地興縣蔡家崖,聽取賀龍、李井泉匯報土改工作,并先后召開貧農團代表、土改工作團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座談會,詳細調查農村各階級的比例、土地占有、土改工作團怎樣發動群眾等情況。〔30〕4月4日到4月13日,又到晉察冀軍區所轄的岢嵐縣、代縣、繁峙縣、阜平縣,與村干部座談農村土地改革、農村生產和人民生活情況。〔31〕經過近一個月的調查研究,毛澤東終于下決心改變新區農村工作的政策,變土改為“雙減”,并立即將這一決定首先告訴鄧小平,當時鄧小平已經被任命為中原中央局第一書記、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政治委員。〔32〕1948年5月24日毛澤東致電鄧小平,指示新區在解放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只實行減租減息和酌量調劑種子、口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而不立即實行分浮財、分土地的社會改革政策,把主要打擊對象限于政治上堅決反對我黨我軍的重要反革命分子,以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滅國民黨反動派。〔33〕毛澤東特別強調:“這一個減租減息階段是任何新解放地區所不能缺少的,缺少了這個階段,我們就要犯錯誤。”〔34〕5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6月3日中共在香港發行的黨刊《群眾》周刊全文刊發了這個文件。〔35〕當時中央急切希望借助香港這個特殊地區向海外宣傳中共關于土改政策的新變化,盡力挽回“左”的偏向帶來的負面影響。根據中央精神,鄧小平于6月6日起草簽發了中原局《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即“六六指示”)。
1948年這段時間鄧小平與毛澤東電文往來密集,當時正值中央建立了報告制度,“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規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自己動手每兩個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綜合報告”〔36〕,目的是讓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中央“及時反映情況,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爭取革命戰爭更加偉大的勝利”〔37〕。中央集中精力研究和制定政策,其意義正如1948年4月25日鄧小平所說:“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如果沒有政策和策略,黨的路線就是空的。正確的路線一定要用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來保證。全黨同志都要學好黨的政策和策略,這樣,我們才會無比的強大,誰也不能戰勝我們。”〔38〕
三、“六六指示”系統、詳盡地提出了新區農村土改工作方針和策略步驟
1948年6月6日,初夏時節,在豫西一個名叫張莊的小村莊,鄧小平完成了由他親自起草的《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整篇文獻近兩萬字,緊緊圍繞中央的指示和精神,那就是:“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實行減租減息和酌量調劑種子食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以便聯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聯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幫助人民解放軍消滅一切國民黨武裝力量和打擊政治上最反動的惡霸分子”〔39〕,詳盡地提出了關于新區農村土改工作方針和策略步驟,其基本內容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明確指出“土地改革是我黨始終要貫徹的方針”,“我們暫時改為雙減,是因為土改條件尚不成熟,雙減政策在目前對人民比較有利的原故”。〔40〕鄧小平從十二個方面詳細解釋和說明了新區土改工作方針轉變所面臨的各方面問題,涉及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對敵政策、政權建設、加強武裝、宣傳工作、群眾工作、生產和軍隊供給等。比如,如何向干部群眾做解釋說服工作;對已分了土地的農戶該怎樣做,分得不徹底的農戶和沒分到土地的農戶該怎樣做;工商業政策如何調整;軍需如何解決,等等,結合這些具體情況提出具體措施。〔41〕為了“有效地團結一切社會力量反對美蔣,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務,全區應立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財,停止亂沒收,禁止一切破壞,禁止亂打人、亂捉人、亂殺人等現象”〔42〕,鄧小平特別指出,“必須向群眾作充分的宣傳和解釋,不要懼怕在群眾面前進行自我批評”〔43〕。
第二,提出將新區分為三個不同區域的新觀點。鄧小平發展了他原來將新區分為兩個區域的觀點,根據新區的發展和變化,提出應區分三種不同區域,即控制區、游擊區和嶄新區,不同區域要采取不同的調整政策。如對控制區,“凡是沒有分土地的地方,即應停止分配土地的宣傳,進行減租減息及合理負擔的宣傳”,并分步驟逐步開展“雙減”,凡是分過土地的地方,則應區別是真分還是假分,“真分的一般應該確定地權財權,不再變動,假分的應該說服群眾自愿改為租佃關系,實行減租減息”〔44〕。在游擊區,要“保護基本群眾及各階層的利益,并按照環境及群眾要求,適當地實行雙減政策”。在嶄新區,“應該采取更為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一切社會力量,反對美蔣和地方上最反動的分子,以便于我們消滅敵人,站穩腳跟……在社會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財,不作經濟上的沒收,只對個別業已判處死刑的最反革命的分子的本人財產實行政治的沒收,并分給群眾”〔45〕。
第三,指出土改“左”傾錯誤的表現及其認識根源。鄧小平列舉了十二條錯誤和教訓:脫離新區客觀實際的主觀主義;缺乏政策策略思想;普遍實行走馬點火、分浮財的錯誤做法;違反工商政策;殺人過多;急于建立后方;忽視政權作用;忽視宣傳作用和錯誤的宣傳內容;破壞公物;外來干部作風壞;缺乏進入新區的動員和準備;缺乏斗志,有茍且偷安的右傾情緒。鄧小平尖銳地指出,脫離新區客觀實際的主觀主義、缺乏政策策略思想是產生“左”傾偏向的認識根源。為什么會發生“左”的錯誤?鄧小平認為其主要原因是不從客觀實際情況出發,首先沒搞清楚新區的環境和敵我力量對比,忽略了敵人的力量;其次是沒有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和組織程度,為某些假象所迷惑,把群眾一時的熱情當作群眾的覺悟。他認為這種主觀主義的表現形式是經驗主義,即憑以往經驗,主觀地認為群眾一定擁護土改,只要“槍桿子加土改”就可以把中原問題解決,結果適得其反。他深刻地指出:“當我們在軍事上還沒有取得面的控制,國民黨和地富武裝力量還沒有在當地被肅清,大多數農民還沒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組織起來,本地的正派的區村干部還沒有大批涌現出來,而外來干部又尚未熟悉情況和聯系群眾的時候,就馬上實行土地改革,不僅是主觀主義的,而且是冒險主義的。”〔46〕這不僅損害了中農的利益,甚至還損害到貧農的利益。“六六指示”主要是針對“左”的錯誤和教訓而寫的,但是,鄧小平沒有忽視當時存在的右的錯誤。他列舉了右的傾向的種種表現,指出右的傾向同“左”的傾向一樣,都會給我們以不小的損害,必須堅決予以克服。鄧小平具體細致地考慮了新區農村政策轉變中已出現或可能出現的問題。
第四,特別注意糾正城市工作中的“左”傾偏向。中原部隊對于公共建筑、工廠學校、文化事業、教堂廟宇等作了相當普遍的、嚴重的破壞。鄧小平嚴厲批評在占領城市初期就不斷發生違反政策和紀律的錯誤,他說:“我們許多領導同志,至今還沒有真正覺悟到這種農業社會主義的破壞性是反動的、罪惡的行為,對于人民的利益和黨的政治影響都是難以估計的損失。”〔47〕鄧小平闡明了農村土改工作與城市工作之間的關系,“為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以便保障人們生計和支援戰爭,必須注意領導人民加緊生產,必須堅決執行保護城市、保護工商業政策,糾正相當普遍存在的輕視城市、放棄城市工作領導的錯誤傾向”〔48〕。
鄧小平重視把中共土改與保護民族工商業以及保護城市聯為一體,糾正城市工作中的“左”傾偏向。他在1948年4月25日于河南魯山召開的豫陜鄂前委和后委聯席會議上作報告時就指出:“資本家做生意,當然要賺錢,而且要有剝削,但是一個商號倒閉了,或者我們把它沒收了,要影響到比資本家剝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計。我們要看看自己的腳究竟站在哪里,怎樣做才是更好地為群眾。說不讓資本家剝削,聽起來是革命思想,一算帳就知道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敗。我大軍在中原,幾十萬人要吃飯,要穿衣,不注意工商業,根本不能維持。”〔49〕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問題”,而鄧小平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重視在當時各中央局和分局負責人中是走在前面的。
第五,強調充分宣傳黨的土改政策的重要性。鄧小平指出和批評了在宣傳工作中出現的問題,認為普遍忽視宣傳工作,沒有加強宣傳隊、劇團、文化工作的組織和領導,而是把這些機構的干部分散去進行土改工作,削弱了宣傳機構的作用。另外,在宣傳內容上,一般只注意土改宣傳,而忽視了黨的各方面正確政策的宣傳。“左”的口號、“左”的詞句掩蓋或減弱了黨的正確口號和主張的力量。鄧小平強調:“展開充分的宣傳活動,擴大黨的全部正確政策的宣傳,揭露敵人的欺騙和罪惡,首先在群眾中建立和占領思想陣地,這對新區戰勝敵人與發動群眾關系極為重大。”〔50〕
第六,全面評價中原區的工作。鄧小平指出要全面正確地評價中原區的工作,不能因為存在一些缺點錯誤就看不到中原區在戰略進攻中所取得的偉大成績,指出:“必須著重指出,所有上述這些錯誤和缺點,都不能掩蓋了我們大舉進攻后在全中原區的偉大勝利和偉大成就”〔51〕。毛澤東在審閱“六六指示”的這一部分時,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并親筆增寫了兩段文字:“由于我們的進軍,吸引了大量的人到中原方面,這樣就從根本上破壞了敵人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企圖摧毀解放區的反動計劃,而將戰爭引向了國民黨統治區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區的基本區域,而且使我友軍在山東,蘇北,魯西南,豫北,晉南及陜甘寧邊區各地順利地殲滅了大量的敵人,恢復了廣大的失地,使全局都轉入了攻勢”〔52〕。
“六六指示”對中央指示進行了全面系統的闡述,毛澤東十分重視。6月28日他復電鄧小平說:“完全同意你們六月六日的指示,即望發給中原全黨全軍切實執行”〔53〕,并將這個文件轉發給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毛澤東認為鄧小平起草的“六六指示”把中央的規定具體化了,可以作為中央指示的補充和說明。中央5月25日的指示和中原局“六六指示”的發表,標志著中共中央經過五個多月的醞釀,最終完成了對新區土改政策的轉變,也是中共中央堅決糾正土改中“左”的錯誤偏向的標志性成果。1948年9月,在新區停止平分土地政策,實行減租減息,大批從事土改工作的中共干部深入鄉村,把土地改革、整黨建設和準備春耕結合起來,黨的正確路線和政策為爭取土改和戰爭勝利提供了重要保證。
四、結語
1947年7月12日晉冀魯豫《人民日報》轉引美國人主辦的《密勒氏評論報》的署名文章《論中國內戰的前途》,文章說:“內戰戰場的真正分界線是在這樣兩種不同的地區中間,一種地區是農民給自己種地;在另一種地區是農民給地主種地。”〔54〕當時在國統區發行的唯一的中共理論刊物《群眾》周刊也登載過美國記者白蒂格蘭恩的署名文章《中共的土地改革》,文章說:土地改革“是國民黨比什么都害怕的事,它知道這是共產黨唯一的‘秘密’武器——它比任何新式武器更有效地給當前的蔣政權以致命的打擊”。〔55〕但是,土改工作中政策問題至關重要,如果把握不好,事態會向反面發展,那將導致“人們不喜歡蔣介石,也不喜歡共產黨”〔56〕,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決策層清醒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從1948年1月起的幾個月里,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集中全力解決土改、整黨、工商業、統一戰線、新區工作等方面的具體政策和策略問題,特別是糾正“左”的偏向。這恰恰是解放戰爭進入反攻階段,毛澤東稱“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57〕而土地問題隨即成為影響戰爭進程的決定性因素,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牽動著中國全社會的各個階層和階級。4月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更加完整地概括了土地改革的總路線,即:“依靠貧農,團結中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58〕這條總路線提出的前前后后,中央和毛澤東都及時向中央局各局、各分局進行征詢,要在不同的地區制定實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可以說新區土改政策從“平分土地”到“減租減息”的轉變,對隨即到來的淮海戰役乃至全國解放戰爭的勝利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鄧小平女兒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中寫道:鄧小平沒有秘書,在軍情如火如荼的戰爭年代,向中央的報告和電報都是鄧小平親自提筆撰寫,一切親力親為,無成規、無繁文,表現了鄧小平的實干作風。〔59〕回顧這段崢嶸歲月,我們再認真研讀鄧小平為中原局起草的《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更能真切地感受文獻蘊藏著豐富的政策、策略思想,以及鄧小平大膽實踐、尊重群眾、心系民生的優秀品格。鄧小平以敏銳的洞察力、堅定的原則精神、細致周密的觀察和思考,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及時將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加以系統說明,使中央政策在實踐中得到更好的貫徹與落實。由于指導思想明確,糾正錯誤的原則和具體辦法細致周密,中共糾正新解放區土改中出現的“左”的偏向行動果斷、措施得力,較快地糾正了錯誤,使土地改革運動取得預期的成果。42年后,鄧小平在回憶大別山斗爭時說:“這場斗爭,主要是我們政策對頭”,“大別山的斗爭不決定于消滅好多敵人,而決定于能不能站住腳”。〔60〕1948年底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鄧小平主政大西南的解放、建設工作,而大別山根據地土改工作的經驗則讓鄧小平受益匪淺,迅速地完成西南地區社會穩定工作。到1949年下半年,全國戰局有了重大發展,新區土改有步驟地開展起來,那時劉鄧大軍打到西南,而中原區已經成為有較好工作基礎的、鞏固的解放區了,鄧小平功不可沒。
歷史表明,黨的政策只有從具體實際出發,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性,才能促進革命工作的勝利發展。鄧小平對中共關于新區土改政策轉變所作的貢獻,讓我們清楚地了解到1948年中共對土改中所犯的“左”的偏向錯誤是如何進行糾正的,也更好地詮釋了“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這一真理。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下)[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751.
〔2〕冷溶.鄧小平與新解放區農村工作政策的轉變[J].中共黨史研究,1989,(6):1-6.
〔3〕毛澤東、鄧小平關于根據地工作的來往文電選載(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九四八年六月)[J].黨的文獻,1994,(3):3-32.
〔4〕郭曉平.毛澤東、鄧小平與新解放區土地政策的形成[J].黨的文獻,1997,(1):84-87.
〔5〕羅平漢.鄧小平與新解放區急性土改的停止[J].文史天地,2004,(3):12-16.
〔6〕徐京.鄧小平與大別山新區土改[C].//鄧小平與中國道路——全國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7〕王新生.鄧小平與大別山根據地的創建[C].//鄧小平與中國道路——全國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10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
〔8〕〔11〕〔12〕〔15〕〔16〕〔17〕〔18〕〔21〕〔22〕〔23〕〔24〕〔25〕〔26〕〔27〕〔28〕〔29〕〔48〕〔53〕中央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699-670,710,712,716,716-717,722-723,723,732,733,734,735,736,736,737,740,740,743,743.
〔9〕〔20〕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與三軍經略中原:中[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108,621.
〔10〕〔13〕〔14〕〔19〕〔30〕〔31〕〔32〕〔33〕〔34〕〔37〕〔5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267,276,277,295,298,299-301,309,311,311,264,319.
〔35〕群眾,1948年6月3日,2(21):2-3.
〔36〕〔38〕〔39〕〔40〕〔41〕〔42〕〔43〕〔44〕〔45〕〔46〕〔47〕〔49〕〔50〕〔51〕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4,107,109,121,121,116,121,116,117,110,113-114,106,113,115.
〔54〕密勒氏評論報.論中國內戰的前途[N].晉冀魯豫人民日報,1947-07-12.
〔55〕[美]白蒂格蘭恩.中共的土地改革[J].群眾,1947-03-02,14(9).
〔56〕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23.
〔57〕〔58〕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44,1312.
〔59〕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569.
〔60〕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功載中原[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102.
(責任編輯肖雪蓮胡學舉)
〔中圖分類號〕A8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6-0921(2016)02-0113-11
〔作者簡介〕何薇(1963),女,四川成都人,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上海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美國佐治亞西南州立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訪問學者,主要從事中共黨史研究;趙曉丹(1991),女,山西呂梁人,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共黨史研究。
〔基金項目〕西南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資助項目“鄧小平研究在美國”
〔收稿日期〕2015-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