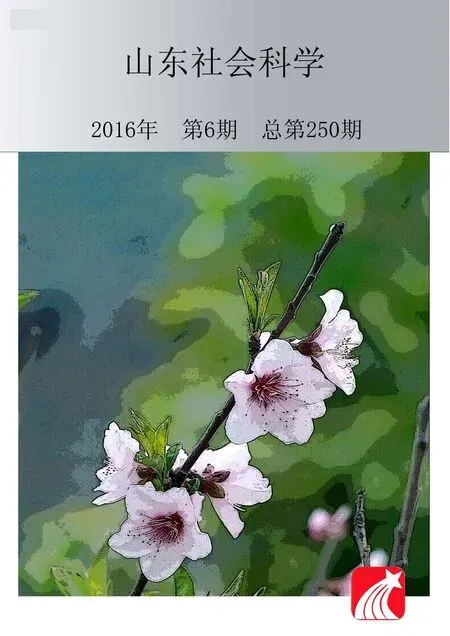單位社會背景下公共性結構的形成及轉換
田毅鵬 劉 博
(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單位社會背景下公共性結構的形成及轉換
田毅鵬劉博
(吉林大學 哲學社會學院,吉林 長春130012)
[摘要]隨著近年來社會矛盾的凸顯和“公”“私”界限的論爭,公共性主題成為理論界研究的新寵。單位制作為新中國社會整合與管理的典型制度,對中國社會“公共性”的結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單位制形成前,傳統社會結構的特性壓制了現代意義的公共性的生發與擴展。單位制的構建使得國家主導的“大公共性”不斷彰顯,但其實際運作邏輯則凸顯了“小公共性”的集體利益。市場化改革后的單位制變遷使得大小“雙重公共性”之間的同構性被打破,基于單位自身利益的“自主型公共性”成為局部消解“大公共性”的力量。“后單位社會”背景下正在呼喚一種“新公共性”的到來,如何調動社區力量構建“新公共性”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管理體制本土性與復雜性交融的實踐場域。
[關鍵詞]單位制;公共性;社區;社會整合
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與變遷,國家權威主義不斷膨脹,社會公共領域的不斷壓縮和各種社會沖突都將矛頭指向了傳統意義上“公”與“私”之間的邊界與關系。而破解這對矛盾的關鍵則正是“公共性”得以實現的載體、途徑和條件,因此公共性話題成為了當前理論界的研究熱點。學術界一般將公共性理解為與個人主義和“私”域相對應的一個公共空間和場域。百余年來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遷的本質就是此種公共空間和場域的不斷演進和變化,而此種演變所導致的“公”“私”界限的變化最終形塑了中國社會的基本結構。欲理解此種公共性的變遷,則必須將視閾集中于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而貫穿其中的一個重要制度設計無疑是伴隨新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單位制”。 因此,以單位制為考察背景和線索去理解中國社會的公共性變遷,可以通過把握“單位”這一總體性的制度去厘清單位制發展的不同時期公共性的作用空間和運行邊界。因此以單位制形成、發展、消解的視角,探尋其與公共性結構變遷及轉換過程中的交互影響便具有了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中國社會公共性的傳統及其特質
審視當代中國社會公共性的結構變遷,必須將問題置于近代中國社會“新陳代謝”的轉型進程中,方可獲得深入理解。因為正是百余年來現代化進程的跌宕起伏才引致了中國社會公共性結構經歷的復雜變化。從現代化進程的角度看,單位制的形成正是在資源嚴重匱乏的狀態下為了擺脫百余年來中國社會所面臨的總體性危機所做出的體制選擇。此種社會運行機制曾在中國現代多民族國家的建構中發揮過非同尋常的作用,并與當下中國社會的公共性結構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以歷時態的視角考察公共性的變遷首先要回顧公共性的概念源起以及單位體制生成之前中國社會公共性的特征。
(一)公共性釋義
作為一個現代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專用術語,公共性是一個內涵復雜、概念邊界較為模糊并充滿爭議的概念。從一般意義上來說,公共性是與私人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從公共性的詞義來看,這個概念同時包含著“公”和“共”兩個涵義。“私,禾也”*許慎:《說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頁。,私的本義是指莊稼。其后,“私”演變由個人而掌握和占有的生產資料。“公,平分也。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為公’。”*許慎:《說文解字》,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頁。這就是說,“公”的含義是與私相對立的,“公”是均等地或平等地分配的意思。而在西方的語匯中,現代英文一般用“publicity”來表達公共性,來源于古希臘詞匯“koinon”,其涵義為在相互工作和生活中個體之間的照顧與扶助。*王鑫、周育國:《公共性的解讀》,《大連海事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無論從何種詞源考察,公共性都表現為一種超脫出個體的生活世界而走入公共生活與交往的一種屬性。學者李明伍更是直接將公共性界定為“某一文化圈內成員所能共同(其極限為平等)享受某種利益,因而共同承擔相應義務的制度的性質”*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類型及其若干傳統模型》,《社會學研究》1997年第4期。。
從這個角度來看,筆者認為公共性觀念可以包括以下一些維度:(1)它既包含一定的空間領域,動態與靜態形式都是此領域的表現方式。(2)同時它也是范疇可以縮展的實體性的共同體。(3)公共性相關的行為主體同時包含作為集合體的公眾和與私人相對應的公民,并且公共性也強調公共參與、公開討論的行動過程與言說方式。*譚安奎:《公共性二十講》,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頁。通過以上這些維度,我們有望從結構與主體、態度與行動等角度構建起一個更加全面的公共性概念框架。
公共性作為一個在西方語境中內生的概念,圍繞其不同的界定使得西方學術界對此形成了眾多的流派。哈貝馬斯認為西方社會公共性得以產生的重要基礎——“公共領域”是一個內嵌于文化與制度之中而形成的社會空間。“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領域不僅需要法治國家機制的保障,也依賴于文化傳統和社會化模式的合拍,依賴于習慣自由的民眾的政治文化。”*[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頁。不管是阿倫特對于“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作用空間的區分,還是盧曼的“合法至上論”的公共性以及羅爾斯基于自然法論而展開的公共性論述都是依托于西方制度與歷史文化的進程所作出的劃分。作為深受文化與歷史影響的概念范式,中國的公共性概念是在民族國家建構與現代化的過程中從西方引進的。而以黃宗智、曹衛東、楊念群等為代表的學者均認為中國社會的公共性有別于哈貝馬斯和阿倫特所論及的西方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因此,從本土化的視角出發,結合中國社會的結構特征和體制背景考察中國社會特有的公共性特征成為了對公共性進一步研究所必須著力的方向。
(二)中國傳統社會公共性特征
公共性釋義的多元化取向一直是中外學者解讀此概念的基礎,不同的地域和歷史文化都會對公共性的存在形態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欲考察中國傳統的公共性模式,則需在把握西方公共性概念的基礎上深刻挖掘中國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所表現的公共性特征:
1.承載主體的單一與“公”權力的擴張
中國的傳統社會并未形成明晰的公共性概念,而只有所謂“公”的概念。在中國傳統文化與社會中,“公”最原始的意涵是朝廷、政府或國家。根據學者的研究,甲骨文、金文中的“公”主要有祖先、尊長、國君等義。“公”與“私”的邊界沒有明確的制度劃分,使得公權具有了至上的地位并可以擴展至個人空間,各種制度也主要是為了保證公權力可以暢通無阻。*薛冰:《歷史與邏輯:公共性視閾中的公共管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7頁。在中國傳統文化中, “國家=官=公”一直是“公”的觀念的主要表現方式,也就是說“公”的定義總是指向朝廷、政府和國家所作用的政治領域。這種公共性承載主體的單一性特點不僅存在于中國社會,對于同樣深受儒家倫理思想影響的東亞社會也表現出極大的趨同性。“雖然中國和日本的‘公私觀念’存在著一些重要的差別,但如果從‘空間’角度對其加以分析,會發現兩國空間性的‘公家’‘公門’都是指與‘君’‘官’有關的場所,到近代,進而引申為‘政府’或‘國家’的領域。”*田毅鵬:《東亞“新公共性”的構建及其限制》,《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5年第6期。因此,東亞社會“公”的承載主體主要是“官”這一特殊的社會群體,由此而形成了中國社會所特有的“官尊民卑”的傳統文化。
同時,中國傳統社會還將“官”這一公共性承載主體所擁有的權力活動也視為公共性的延伸。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在論述中國社會“公”與“私”的區隔時曾言:“公的初義為公宮……公私關系是統治者與服屬者的關系,支配私的是公,公指族長領主”*[日]溝口雄三:《公、私》,載賀照田:《在歷史的纏繞中解讀知識與思想——學術思想評論第十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1頁。。因此,中國傳統社會的“公”只能表現為代表統治者和政府的相關利益,而絕非是社會和民眾利益的代言。這種公共性承載主體的單一性與西方社會產生于公民與公權對抗基礎上生發的“公共領域”顯然有著本質性的殊異。中國傳統社會的民眾與公權之間并非是對抗的關系,而是一種服從和一體化的關系,因此西方意義上的“公眾”并沒有從中國社會內生出來。這進一步強化了傳統社會公共性主體——“官”所擁有的強大的權力空間和責任屬性。
2.公共性層級的多元性
考諸中國傳統社會公共性的具體形態,則可以發現文化傳統、政治制度、思想教育以及國民性格等因素都使得中國傳統社會的公共精神呈現出異常復雜多元的格局。這種復雜的格局既表現為理念層面的“大公”盛行與實際運作的“小公”邏輯,也體現為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公”“私”之間邊界的不斷變遷。
(1)理念層面的“大公”傳統
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在理念上十分推崇群體性的“大公”觀念與價值,統治者通過宣揚諸如“天下為公”“大公無私”“公爾忘私”等口號加強和確認自身統治的合理與道義。作為儒家思想家治國理政的主要觀念,“公”的概念發展成為一整套完備的道德倫理體系,它成為傳統中國社會封建中央集權政治秩序得以維系的有力思想依托。“大公”觀念不斷發展和演化成了“崇公”的價值體系,此種價值體系推崇“公為上”“公為善”等思想,有礙于此種思想的觀念與行為皆為“私與惡”。在“崇公抑私”的理論體系之中,“大公”觀念超脫出了僅僅將“公”理解為共同體內部的公平、平均的生活意識層次,并擴展到了天、天下這種普遍世界。這使得“公”的概念有了公理、天意等倫理性的意涵,從而成為天地萬物的最高主宰準則。“公”這種抽象的至德需要借助一個載體將其從形而上的理念狀態轉化為形而下的操作準則,而充當中介的唯有能承載天地之至德的君主方可代表。如《禮記·經解》云:“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鐘肇鵬:《春秋繁露校(〈王道通三〉篇與〈深察名號〉篇)》(校補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因此,作為天道的化身和繼承人,君主成為了代行天道和公理在現世生活的代言人。唯有其可以解釋天理、遵守公義、平均天下、主持公道,所有的臣民則只能接受君主的統治。
因此,作為“大公”理念化身的君主及其權力的擴展成為了傳統中國社會一切社會生活和價值準則的核心。“天下為公”的至高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君主代表公權力的絕對力量和民眾對此權力的服從,導致了社會生活徹底的等級化與政治化。中國傳統道德領域所凸顯的“無我”“無私”“無欲”等思想是“大公”觀念實現的倫理基礎和邏輯前提。作為凸顯公共性本質內涵的“公共領域”表現為國家政治領域和個人生活領域之間的公共空間,在此空間中個人可以通過言說與交往等方式關注公共生活的諸多議題并形成影響公共生活共同體的能力。但中國傳統社會顯然不存在此種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因為在“大公”的意識形態統攝下,皇權具有壓倒一切世俗權力的能力。在這種政治形態之下,公共性得以維系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空間都十分有限,因而傳統中國社會“大公”理論體系成為公共性難以孕育的制約因素。
(2)實際運作的“小公”邏輯
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公”主要是指朝廷、政府,主張“立公滅私”,導致朝廷以外的“公”不發達。理論和傳統文化教育雖然不斷提倡“立公滅私”,但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實際運作中卻一直無法有效落實,反而催生了陽公陰私、假公濟私、化公為私、援私為公等行為的產生。傳統中國社會出現公私之間纏繞難分、糾葛混沌等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私域性的血緣因素摻雜其中致使大公逐漸被血親私域所侵蝕。個體“化公為私”的目的則是為了小共同體的“公”。因而傳統社會所表現的“私”本質上是一種被血緣、地緣共同體所分割的,有著“小公”屬性的社會空間與利益。
內生于中國鄉土社會之上的“小公”將倫理親情作為維系社會關系的準則。為此,費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論十分準確地把握了鄉土中國的社會“小公”發達的結構特征:(1)血緣關系之重要性; (2)公私、群己關系的相對性;(3)自我中心的倫理價值觀;(4)禮治秩序,即利用傳統的人際關系和倫理維持社會秩序;(5) 長老統治的政治機制。*費孝通:《費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年版。這使得中國人在行為選擇上“以親己之人事為重,以疏己之人事為輕”。依照血緣、地緣的親疏關系,中國人實際上被整合進或大或小的各類家族、宗族、村落等宗法共同體之中。此種封閉且具有“小公”屬性的農業社會的交往模式在傳統中國社會是難以產生哈貝馬斯所言的“公共領域”,以及在這種公共領域中所產生的開放的市民社會的公共性。
(3)近代社會的“公共性”演進
19世紀中葉以降,西方勢力以堅船利炮為依托,逐漸介入和影響了中國社會與政治的發展變遷進程,代表國家“大公”的政府和王朝統治力量不斷被削弱。西方政治經濟勢力在中國的不斷發展侵蝕了政府的行政權威,使得政府壟斷所有社會資源和政治權力的能力受到了挑戰。隨著清末新政的推行和地方自治運動的開展,地域社會的活力開始增強,以地方性的社團的大量涌現為標志的地域性的公共性得以萌發。地域性社團在近代勃興于國家與私域之間,主要承載地域社會“公”的職能,隨著社團履行公共職能范圍的擴展,“公”領域也不斷得以發展。依托于民間社團活動而逐漸明晰的國家與民間社會之間的“公”領域,其本質上屬于介于二者之間的社會空間,國家與民眾均意識到了它的存在。恰如蘭金(Rankin)在考察19世紀后半期中國社會時所發現,“公共領域作為地方精英們活動的場所開始逐步形成并壯大起來,帝政后期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官”—“公”—“私”三個領域”。*Rankin, M.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Zhejiang Province,1865—1911,Stanford Univ.Press,1986.這時期的社團運動通過吸收地方精英與各階層民眾,在抵御外敵和爭取民族權利的斗爭中將整個社會的連帶感得以增強,最終產生了代表民族主義的強有力的政黨組織。可以說,晚清直至近代時期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組織結構和公共性形態逐步走向瓦解,公民社會初步發展,并呈現出一種掙脫政府和國家控制的趨向。正如小浜正子在考察上海城市公共性時所發現的——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社團”組織所生發的公共性雖然具有自發和獨立的意愿,但與西歐在資產階級革命以前就存在的、具有身份等級性質的社團在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近代社會的社團組織除了自發性因素之外,依然具有強烈的官方色彩和封建色彩,社團發展形成與官方控制和傳統的宗族組織存在著強烈的連帶關系。國民黨執政后更是以“黨治”的名義整編城市社團,因此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公共性雖然有所發展仍然是十分弱小的,尚未形成西方意義的公共領域以及真正意義上的強大的資產階級。*[日]小浜正子:《近代上海的公共性與國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頁。
由以上的論述可見,雖然中國傳統社會公共性特征表現出各種多元的結構,筆者的研究也遠未充分發掘對公共性產生影響的各種社會因素。但傳統中國社會公共性的結構特征主體上呈現出“大公”理念的獨大和“小公”邏輯的運作,以及在近代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公共性的萌發與畸形。如果以現代性的視角考諸公共性的內涵,顯然中國傳統社會特殊主義的原則必然引致公共性的極度萎縮。此種公共性的結構形態與西方社會的公共性有著重大的區別,這一方面是由于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迥異的文化傳統和生產方式,同時也體現了兩者在發展上的“時差”。
二、單位社會公共性的層級及其特質
遵循上文的研究邏輯,中西比較基礎之上對公共性的表現特征及差異的界定是我們理解公共性的基本前提。而考諸百余年中國的發展歷程,工業化與單位體制的構建則成為影響公共性的一個重要變量。學術界以往的研究忽視了單位這一“生產的體制”和“社會的機制”對于中國傳統公共性的重要影響。筆者正是在這一意義上嘗試揭示單位制的發展對傳統社會公共性的影響進路。
(一)“單位制”的構建:一種大公共性的初現
1.“單位制”與大公共性的內涵
單位是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再分配體制下的制度設計,筆者認為單位制是依托于新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制度所構建的特殊機制,是國家進行社會控制、資源配置以及社會整合的制度化形式,同時包含社會保障、身份定義、社會生產等多種社會職能。各級黨政機構、事業單位以及國有企業是單位制最主要的承載主體。作為“舉國體制”的中國單位體制構建的目標是告別晚清以降的社會總體性危機,將民眾組織起來,以推進民族國家構建和實現趕超發展的國家敘事。在這種舉國體制的“大共同體”構建中,城市社會的組織結構演變為“國家—單位—個人”的模式,而農民則被組織進了政治、經濟功能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中。20世紀50年代末期又相繼出臺了糧食統購統銷制度和嚴格的戶籍制度,使得國家財政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擴張。如此的制度構建使得傳統中國“差序格局”的社會結構受到了沖擊,瓦解了中國傳統社會中公共性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單位組織的建立也使得社會成員不得不走出家庭和他們熟悉的血親群體從而被整合進更大的共同體之中,社會意識形態領域也宣揚大公無私的社會主義精神。這一系列的制度使得傳統中國社會的“公共性”存在形態受到了挑戰,一種告別家庭與個體私域的“大公共性”開始出現,當然這種轉變是由一系列制度的建構和運作得以實現的。
2.公有制的單位產權:國家主導的公共性架構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盡快擺脫受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和市場秩序,國家增強了對財政金融和整個社會領域的控制。隨著國家加大汲取社會資源以服務于現代化工業建設以及“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公有制產權結構成為一切社會制度和單位組織的前提。作為國家主導“大公共性”的物質基礎,經過如下幾個階段公有制產權的主導地位最終得以確立:第一,中央政府統一全國財政經濟。“1950年12月,政務院公布了《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對全國的外貿交易進行管制,同時中央政府在50年代初期打擊投機資本和穩定物價的過程中掌握了市場領導權。”*路風:《中國單位體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第4期。隨后實行的國家對私營企業加工訂貨和統購包銷制度也控制了私營經濟的自主權,這些措施使得“小公經濟”得以生存的私人資本和自由市場極度萎縮。第二,社會主義改造的大力推進。1955年農業合作化進入了高潮,同年年底中央決定對全行業的資本主義工商企業實行公私合營。三大改造的完成從產權的意義上剝奪了私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和物質資本,使得國家成為全社會資源的唯一擁有者,借助其所掌握的資源而獲得了超凡的支配能力。第三,“一五計劃”的順利完成。隨著建國后工業化建設序幕的展開,以蘇聯援建的156項大型工業項目為依托構建起了“一五時期”新中國的工業基礎。國家在改造后和新建立的單位都學習蘇聯經驗落實了統收統支的財務制度,這種財務制度保證了企業利潤能夠最大程度被國家財政所汲取,國家財政能力得以迅速增加。從單位產權看,政府成為所有企事業單位的出資者和所有人,對各單位具有最終決策權。
3.“一元化”的社會結構:公共空間的退場
國家力量空前膨脹,徹底告別了傳統“郡縣中國”社會中“皇權不下縣”的歷史,使得鄉村社會的權力文化網絡和舊中國城市的“社團”與“行會”組織在國家加大汲取的過程中走向衰敗。傳統中國鄉村社會中以宗族、家族、村廟等組織體現自身的“私人領域”,在政治經濟功能合一的人民公社中這些“私域”被當作封建殘余勢力予以取締和限制,使得由國家主導的公共性在鄉村社會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擴展。在城市社會則通過“街居制度”將公眾組織起來,“1954年12月,全國人大相繼通過實施了《城市街道辦事處組織條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條例》《公安派出所條例》。”*路風:《中國單位體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第4期。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建立的這些機構和組織,構建起了除單位外另一套平行的組織城市居民的管理系統——“街居制度”。街居制度的形成體現出在常態化的社會運行過程中黨的組織權威在城市社會的觸底,使其逐漸被納入行政科層體系而作為城市基層政權而發揮作用。這使得城市社會民眾的活動也被納入進了國家所控制的空間之中。
而傳統中國城市社會各類行會組織和社會團體一直被視為中國社會的“中間組織”而得以存在,經由中間組織的活動與發展擴大了地域社會的活力與功能,這個中觀層次的“公共空間”連通國家與個體私域,成為近代中國“社會”得以孕育和展開的基礎。雖然近代中國社會自發性構建起來的社團網絡和社會空間柔弱且富于流動性,但作為國家與民眾之間的公共空間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社會公益的發展和資產階級的形成。新中國建立后,政府通過三大改造運動使得社團組織和中觀層次的“社會”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而城市中廣泛建立的單位和街道系統則整合了原屬于這一領域的全部民眾。由于單位制度構建過程中將原屬于社會的組織資源通過改造運動同構或者吸納到國家之中,這使得公民的“私人領域”天然地“內嵌”于國家體制之內,單位制度則徹底統合了國家與社會。
4.高度權威化的單位:總體性的公共性結構
單位體制構建過程中,黨開始在新建立的單位貫徹自身的權威。“1950年4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加強青年團及其他群眾團體工作的指示》指出要加快建立接受黨的指揮與領導的各級工會、農會、青年團等群眾團體。”*路風:《中國單位體制的起源和形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年第4期。依托于各單位的群眾組織,黨的組織系統向一切社會基層單位延伸,同時通過廣泛建立的群眾組織吸收了大量的積極分子入黨。經過民主改革,在國營企業中,黨的組織被全面建立起來,并實行廠長負責與黨委領導相結合的新領導體制。在歷時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政府再一次全面下放了財政計劃和物資的管理權限,國家行政系統被大大削弱。因而“各單位普遍實行了全面的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各級黨委成為管轄范圍內集黨務、行政、司法等各種權力于一身的唯一權力來源”*楊曉民、周翼虎:《中國單位制度》,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頁。。黨的權威向城市基層單位和社會的貫徹建構起了單位社會中新型的組織關系特征:即整個單位體制的基礎建立在黨組織對群眾的直接掌控之上。這種將行政與黨的組織延伸到社會基層的制度成為所有單位政治權威的主要來源,使社會生活和民眾逐漸被納入到一個嚴密的行政組織網絡之中,同時使得法律難以成為社會調控的主要手段。以公共性的視角反觀黨組織的公共職能的承載,可以發現黨和行政組織所承載的公共職責已經演變為一種“總體性”模式的公共性。這種高度總體性的公共性是以一元化黨的領導和強力化的行政力量加以保證,而在“國家—單位—個人”一體化模式下使得公共性成為了國家的附屬物而失去了獨立的空間。在這種公共性模式中,“黨組織不是作為國家和私人領域之間的公共性組織, 而是政治體制的一部分, 特別是黨政關系尚未理順, 執政黨通過強大的網絡組織對社會形成了相當程度的控制”*許耀桐、傅景亮:《當代中國公共性轉型研究》,《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07年第4期。。而這種控制除了組織上的集中之外,各種“集體主義、大公無私、舍私為公”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宣傳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綜上所述,新中國建立后所建構起的單位制度表現為一種國家主導的“大公共性”結構。可以說在單位體制的建構過程中,單位往往成為國家目標和政治統治的作用主體和落實場所而承載了國家主導的大公共性特征。但令人吊詭的是,隨著對單位制度運行邏輯的深入研究,我們發現在單位制度所表現的大公共性之下,一種維系“單位共同體”內部利益的“小公共性”正在不斷地試圖掙脫“大公共性“的制度枷鎖而實現自身的運作。
(二)“單位制”的運行,“小公共性”的凸顯
“大公共性”在單位制的構建中代表了國家的意志,但是在單位體制的實際運作過程中又向我們展現出單位的另一個重要面相,即功能日益多元化的單位組織逐漸演變為一個充滿溫情的“單位共同體”,通過“包下來”的福利制度踐行革命成功前對社會成員和工人階級的歷史承諾。“每一個單位都逐漸演變為一個福利化的單元,在全能主義的框架下,單位共同體是其成員的看護者,需要像慈父一般去回應其成員的各種需求。”*田毅鵬:《“單位共同體”的變遷與城市社區重建》,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77頁。這使得單位成為職工成員公共事務的承載主體,在封閉的單位空間中單位成員逐漸養成了濃郁的“單位慣習”和“單位意識”。全能主義的單位實際上是用“單位空間”取代了“公共空間”,由資源再分配而形成的單位成員對本單位的依賴使得“單位認同”替代了“社區認同”。這種代表著單位集體主義生發出的“小公共性”構成了調和國家主導的“大公共性”和具體社會成員的中間地帶。
考諸單位小公共性的制度來源則可以追溯至單位制的起源研究,在學界早期的單位研究中,學者路風認為民主革命時期共產黨在根據地所開展的管理社會和公營企業的經驗在革命成功后為單位制的建構提供了制度上的借鑒。美國學者賽爾登也認為共產黨在革命根據地建設中所形成的“‘延安道路’是一條獨具特色的發展經濟、改造社會和進行人民戰爭的途徑……它毫不含糊地拒絕上層行政干部或技術干部通過集權制的官僚政治來支配一切,而是強調民眾參與、地方分權和依靠社會力量。”*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局編譯處:《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論點摘編》,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223頁。而呂曉波在上述“根據地經驗說”的基礎上,搜集了大量的經驗材料和數據提出了根據地的“小公經濟”成為建國后單位制的雛形的觀點,并認為這種小公經濟所暗含的“獨立自主、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原則在單位制的構建中得到了延續。*Xiaobo Lu,“Minor public Economy: The Revolutionary Origins of the Danwei”//“Danwei the changing Chinese workplace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ed. By Xiaobo Lu and Elizabeth J. Perry,M.E.Sharpe,Armonk,New York,London,England.小公經濟在制度上允許各部隊保留一部分生產成果,以用于改善本單位的福利水平。“小公經濟”的分配特征誕生了“大公共性”與“小公共性”之間的矛盾,各部隊往往通過瞞報產量和虛報等方式盡量擴大小公經濟的規模,從而構成了一個閉合的“小公共性”體系。這種小公經濟在單位制構建后受到國家統一的財政制度和高度的生產調撥計劃所束縛,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國家無法也不可能完全清楚單位生產消費的全部細節,加之“單位辦社會”模式的落實使得依托于小公經濟而生發的“小公共性”一直是單位制運作的現實邏輯。單位運行中一些具體的制度設計也助推了“小公共性”的擴展,并為其提供了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合法性基礎。
1.“小公共性”的制度支撐
在改革前的中國社會,單位一直是國家調控體系的基本單元,兼具國家政策的落實者和社會資源占有者的雙重身份。在資源總量匱乏和國家嚴格落實“先生產,后生活”的投資模式下,社會為居民提供生活服務的能力嚴重不足,因此“單位辦社會”模式也就變成了幾乎所有單位不得不為之的選擇。單位將所有的公共職能濃縮其中,為職工提供醫療、教育、文娛、體育和托幼等幾乎全部福利。雖然這種福利保障具有初級性和簡約性,但就其覆蓋范圍而言,的確形成了改革前蔚為大觀的“單位福利化”景觀。這種充滿“父愛主義”式的單位福利使得單位在物質福利分配上的主權意識日漸濃厚,限制了國家主導的神圣和平均主義的資源分配的公共性。并且受制于單位空間的封閉性和不同單位之間業緣壁壘的限制,單位所提供的福利化設施與資源只能為本單位職工和家屬享用,這種獨占性可被視為單位獨大式的“小公”而缺乏國家與社會共濟性的“大共”。
在依賴性的資源再分配模式下,只有通過服從單位權威而獲取資源、身份和權力,因而各單位普遍形成了沃爾德在考察中國工業企業時所發現的“庇護主義”和“派系結構”共存的現象。這種庇護主義主要體現在工廠內部出現了一個由領導和少數積極分子建立的施恩回報關系網絡,即小團體的庇護網絡。*[美]沃爾德:《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業環境和權力結構》,龔小夏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李猛等人的研究在沃爾德的基礎上更是強化了對單位制“意外后果”之一的派系關系的再認識,提出單位中權力運作的基本模式是“上下延伸、平行斷裂”的派系結構。*李猛、周飛舟、李康:《單位:制度化組織的內部機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6年第16期。單位內部的庇護網絡和派系結構作為一種追求“小共同體”利益的結構,與規范制度中追求公共利益的“大公”相沖突,逐漸演變為單位運行的制度性障礙。
2.“小公共性”的產權基礎
遵循著“包下來”的福利傳統,單位逐漸形成了一整套為本單位職工所共享的勞動就業制度,以及在此制度基礎上形成的“集體企業”的“小公產權”。集體企業是由全民所有制的國有企業出資建立的“次級單位”,從產權意義上從屬于母廠而不具備全民所有制的產權身份,因而被視為一種集體所有的產權。在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之前,國企興辦的集體企業往往是在母廠的全力庇護下才得以運行的,具有極強的依附性,通常通過“化大公為小公”的方式擴大自身的規模。通過對“大公”母廠生產設備、技術力量、人員物資、福利設施的轉移與侵占而強化自身“小公”屬性,而母廠也往往通過資源的轉移完成產權的置換,從而實現本單位共同體物質資源的擴充,進一步強化自身的福利主義取向。可見,封閉性的單位就業制度和產權模糊的集體主義企業為單位擴大自身“小公”的利益提供了制度性的動力與合法性基礎,單位逐漸形成了帶有“家族化”色彩的“小共同體”利益格局。
(三)“大公共性”與“小公共性”的關系
在改革前的歷史背景下,“大公共性”建設主要著眼于單位制的構建、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秩序的維護。隨著黨組織在單位中的建立、街居制度的確立、單位內部不斷進行的意識形態宣傳和生產動員、以及公有制成為單位唯一的產權形態,國家主導的“大公共性”表現出了一些明顯的特征。這種大公共性是一種高度集權型的公共性,各種政治性的群眾運動和意識形態宣傳成為這種公共性的主要內容。同時“黨—國家—單位”一體化的社會格局使得公共性并未成為公共活動的場域而成為國家的附屬物。與此同時,單位體制所表現出的制度特性與產權屬性聯合作用,催生了單位共同體成員共享利益的“小公共性”。
作為國家宏觀制度的具體承載者,單位是代表國家進行資源分配和社會整合的中介,其所代表的民族國家視閾的“大公共性”要素與單位共同體內部集體主義的“小公共性”利益之間一直存在著內在的張力,這種復雜的“雙重公共性”模式是改革前單位運作的常態。但是由于單位組織僅是作為自上而下單位體制的一環而存在,這兩種公共性在作用方向上大體保持了一致性。客觀存在并且不斷擴展的單位“小公”非但不是制約國家、與國家相對抗的力量,反而是存在于國家內部借助國家所賦予的特權來實現的。單位總是使用國家“大公”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原則實現自身的“小公”,國家現代化事業的“大公”在范圍和力量上也遠勝于單位共同體內部的“小公”。雙重公共性內在的張力并未走向兩者在本質上的差異和制度上的對抗,“小公”的利益總是在國家“大公”所準予和尚未覆及的領域內努力擴大自身的規模。
三、“后單位社會”公共性的結構轉換及其困境
改革開放后,隨著中國城市和農村全面改革的不斷推進,傳統的單位制也經歷了重大的變革,單位外社會資源的增加和城市社區建設的勃興使得單位的社會整合能力逐漸式微。但改革后的社會運行同樣受制于單位制度組織方式和管理模式的路徑依賴,因此以市場化和全面轉型的“后單位社會”為視角考察新時期中國社會公共性模式成為了當下之舉。
(一)“后單位社會”背景下公共性內涵的變遷
循著單位制的理論視閾,學術界往往將市場化改革后的中國社會稱之為“后單位社會”。作為背景性的概念,“后單位社會”主要指20世紀90年代全面市場化改革以來,單位功能弱化與單位返祖現象相互交織、單位運作機制與市場運作機制并存的社會發展階段及其運行狀態。由于制度自身所具有的強大的“路徑依賴”特性,對當今中國社會的公共性考察不能擺脫對改革后單位體制與公共性之間共變過程的審視。在改革后“權力下移”的背景下,單位從對國家的依附性中有限度地釋放出來,并獲得了一定的自主權與較強的發展動力。伴隨著“單位辦社會”功能的轉移,單位所具有的小福利國家的“小公”屬性受到了削弱,但受制于市場體制和傳統體制的雙重影響,單位又演化為“以內部化管理為主的特定單位或行業集團所有制”*劉平、王漢生、張笑會:《變動的單位制與體制內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國有企業為例》,《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3期。。這種單位產權模式的新變化和單位運行體制的新模式使得傳統上由單位所承載的國家目標與公共職能逐漸式微,單位與國家同構的“大公共性”面臨著失序的挑戰。在“后單位社會”的背景下,公民社會和基層自治組織的發育催生出了從市民社會中逐漸獨立的公共領域,承載了一部分從單位轉移出的公共性職能。這種變化使得原本由國家、單位承載的公共性逐漸讓渡給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社區重新成為社會整合與公共服務的主體。筆者認為,在“后單位社會”時期,傳統的單位體制和自生性的社會力量共同角力和塑造著新型的公共性形態。在構建后單位社會“新公共性”的過程中,必須清晰地意識到此過程需要克服單位制度的巨大慣性和變革形態對構建新型公共性的制約作用。
(二)“單位制”的變遷,“自主型公共性”的發育
肇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改革,改變了傳統單位體制所依賴的制度環境。在單位制影響顯著的工業企業領域,80年代中期啟動了全面的改革進程,經由“松綁放權”“利潤留成”“企業承包”“股份制”等改革,傳統上國家與單位之間的“命令—服從”關系轉變為了契約性的“委托—代理”關系。正如美國學者布坎南所言:“市場是一個人們彼此相互作用、不管是誰都追逐自己目標的制度化過程。”*[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市場與國家——八十年代的政治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7頁。面對市場化改革給單位制帶來的沖擊,國內社會學者的研究呈現出一邊倒的態勢,即制度性變革使得單位體制從根本上出現了松動。孫立平認為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市場化改革給單位但來了幾個方面的影響:(1)單位角色職能化;(2)單位利益獨立化;(3)單位責任具體和內向化;(4)單位的家長角色得以強化。*孫立平、王漢生、王思斌等:《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2期。而劉平、王漢生等在對占有自然資源和制度資源的限制介入性大型國有企業進行研究后發現,與傳統單位制相比這類企業產生了三大變化:(1)企業管理從外部化控制轉變為內部化控制;(2)國家資源從社會化占有變為單位化占有;(3)個人從對國家的依賴轉變為對單位的依賴。劉平等人并未將此類企業稱為“非單位組織”,而是繼續沿用單位的概念,稱其為“新單位制”*劉平、王漢生、張笑會:《變動的單位制與體制內的分化——以限制介入性大型國有企業為例》,《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3期。。學界的經驗研究揭示了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使得傳統的單位組織在運行過程中獲得了巨大的自主性空間,單位逐漸憑借對國有資產的經營與管理將優勢資源轉變為內部福利。不斷膨脹的“單位自主性”作為單位市場化改革的“意外后果”之一,表現為在國家主導的“大公共性“的調控體系之外,單位獲取了獨立于國家控制的優勢地位與物質資源,形成了局部消解國家權威的“自主型公共性”。
1. “自主型公共性”的表現
“自主型公共性”的萌發對單位制的運行環境以及國家與單位之間的關系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具體表現為:
(1)“自主型公共性”弱化了單位與國家間存在的強依附關系。改革前國家通過對單位所需資源的控制和單位領導的任命來實現對單位組織的全面管理,但市場化后的企業逐漸變身為一個獨立的經濟法人組織,相當部分的事業單位運營則依賴自身在市場中的贏利能力“自負盈虧”,因而以國家對單位成員的再分配而表現出的依賴性已明顯弱化。
(2)“自主型公共性”造成了單位的“法團主義”傾向。香港中文大學李南雄教授將改革以來的中國單位制變化的趨勢稱為法團主義,即企業單位雖然從屬于國家機構,但是本身具有了一定的地位、作用和價值。這種法團主義不同于單位共同體內部的“小公共性”,小公共性體現的單位與國家的關系本質上屬于“命令—服從”的結構之下。但由“自主型公共性”所表現出來的法團主義實質是在“委托—代理”的關系中單位內部不斷強化的內部人控制,即在單位活動中管理者與單位職工獲得了對于本企業相當大的控制權,而此種控制權甚至會導致所有者的利益損害。
(3)“自主型公共性”具體表現為單位的超分配和福利化傾向。隨著單位內部人控制權的擴大,“內部人的基本行為目標可以概括為利用他們的信息優勢和所掌握的控制權追求自己收益的最大化”*[日]青木昌彥、錢穎一:《轉軌經濟中的公司治理結構——內部人控制和銀行的作用》,中國經濟出版社1995年版。,而這種最大化的收益則體現為企業的日趨福利化和腐敗現象的凸顯。逐漸膨脹的單位福利化傾向,不斷突破國家“大公”的制度邊界,為單位職工提供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現金和福利分配,形成單位集體福利最大化的目標。這種目標可以視為“自主型公共性”的最終表現,如果說改革前單位“小公共性”的表現之一是單位成員享有國家再分配的福利權利,那么這種這種“自主型公共性”所體現的超分配和福利化則可以視為單位法團主義中的福利。
(4)“自主型公共性”并未從根本上擺脫“強國家—弱單位”的行政管理和社會動員模式。固然改革后單位依托于資源來源的多元化和管理活動的自主化極大地擺脫了國家與單位之間“命令—服從”的關系模式,使得傳統上對單位成員進行政治動員和行政命令的能力逐漸式微。但這并非意味著國家力量和行政力量完全從各級單位中“退場”,單位作為國家與民眾之間的最重要的中介組織仍然發揮著一定的社會管理和組織動員的使命。例如在2003年重大公共疫情非典肆虐之時,由于新興的社區和社會組織依然欠缺對社會成員的組織動員能力,對抗疫情的核心力量仍然由政府和單位組織所組成。各級單位在極短的時間內迅速調動一切物質資源和組織力量,使得每一個單位都變成了具有強大管理和控制能力的對抗疫情的“堡壘”。非典事件表明改革后單位制作為國家垂直行政管理與社會調控的機制依然有效,單位從根本上并未從國家主導的“大公”中獨立出來而僅僅承擔其自身的市場角色和職場空間。這也從一個側面表明“后單位社會”所特有的對于傳統制度的路徑依賴和單位制的巨大慣性對于新型公共性模式構建的制約。
2. “自主型公共性”的實質
改革后這種“自主型公共性”模式的凸顯,本質上是依托于單位共同體集體利益的“小公共性”不斷發展的反向后果。表面上看基于單位共同體自身利益的“小公共性”與此種“自主型公共性”有異曲同工之處,實則兩種公共性所賴以生發的制度環境和作用方式具有本質的差異。單位制運行所顯現的小公共性主要是產生于單位在對國家依附性的制度下所具有的“單位辦社會”職能,它服從于國家統一的行政支配制度、高度集中的財政體制、平均主義和統一的工資身份制度,這使得其運作的空間非常有限。改革前只要這種“小公”利益對國家主導的“大公”目標產生重大的阻礙,國家便可以利用政策手段和群眾性的運動輕易地予以化解。改革后單位“自主型公共性”的凸顯與單位“小公共性”利益的根本區別在于這種超分配的福利化取向,這種取向既突破了單位“小公”所受制于的國家規范的工資和分配制度,又突破了國家“大公”目標與單位“小公”利益本質上的同構性,使之演化為消解國家“大公”目標的一種解構性力量。
(三)后單位社會“新公共性”的構建
1.“新公共性”的內涵
當前中國的單位制社會正在轉型,以“單位社會”逐步走向消解為契機,曾經的“單位人”轉變為“社會人”, 使得原本從屬于單位和國家的公共性讓渡給逐漸形成中的”社會“。在權力下移至基層的背景下,“社區”成為了新型社會組織和整合的模式開始受到重視。“如果我們把20世紀90年代前中國社會在建立民族國家進程中形成的以‘單位’為主要載體的公共性作為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公共性的‘典型構造’或‘舊公共性’的話,那么,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以全球化、市場經濟的發展、消費社會的形成、老齡社會的到來等因素為背景,先后出現的在政府和“單位”以外的公共性訴求則可視為是一種‘新公共性’。”*田毅鵬:《轉型期中國社會原子化動向及其對社會工作的挑戰》,《社會科學》2009年第7期。面對眾多單位組織的消解和單位體制在總體上的式微,尋回社會的主體性,達致新型的公共性成為當前社區建設的重點。這種“新公共性”的創新之處在于其運行動力來源的“社會性”與“多元性”,從而告別了以往公共性由國家與單位的絕對壟斷,基于社區居民自我服務與管理的模式成為了新公共性的主要來源。
2.“新公共性”的實現路徑
(1)單位組織公共性的轉型
伴隨著市場化實踐的擴展和單位體制全方位的變革,傳統上社會成員依附于單位共同體的格局被逐漸打破,社會成員逐漸由“單位人”轉變為原子化狀態的“社會人”。在社區尚無法完全承載單位所轉移的社會責任與職能情況下,也同時亟需單位組織公共性的有效轉型。隨著現代企業制度的真正落實,使得職工由單位福利分配轉變為績效分配,告別了傳統上基于平均主義和“公”的分配方式,社會成員不再僅僅通過單位組織的內部利益傳導渠道與公共生活和公共議題產生聯系。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傳統單位工會的政治動員能力和意識形態資源也趨于弱化,社會成員的利益表達和集體行動也因此變得更為困難。欲使改革后單位組織公共性形態能夠超越西方經驗的“對抗的公共性”,必須一方面在產權意義上變“單位人”為“職業人”,走向梅因在《古代法》中所言的從“身份”走向“契約”。另一方面則需汲取傳統單位制的凝聚力和溫情感,兼顧市場體系所要求的平等、自由、權利等公共性理念,走向一種市場與單位“共生的公共性”模式。
(2)社區公共性的培育與困境
社區作為公眾日常生活與實踐的主要場域,是國家“公域”與個體“私域”的中間地帶,從而起到促進公與私融合的作用。哈貝馬斯曾說:“公共性原則在功能上的轉移是建立在作為一個特殊領域的公共領域的功能轉移的基礎之上的。”*[德]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曹衛東等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頁。因而加緊構建社區服務和各種志愿性的社會組織以便創造出一個承接單位公共性的“公共領域”成為了當下“社會建設”的要務,通過激發社區成員積極參與社區公共活動從而獲得新型的社會合作與聯結成為破解社區成員“原子化”狀態的主要途徑。眾所周知,單位體制的巨大慣性和強烈的單位意識的存在使得當前社區“新公共性”的構建依然存在著推力不足、資源匱乏、參與乏力等問題,需要通過多方力量的參與共同破解,表現在:
首先,擺脫單位依附,提升社區“新公共性”主體作用。“單位辦社會”的終結使得大量的公共性的社會功能從單位轉移到了社區,但是由于政府對社區投入的欠缺,社區難以完全承接從單位轉移出的公共性職能。因而造成了社區依然嚴重依賴于街道辦和駐區單位的境況,大量由單位生活區直接轉化成的社區更是存在著對原單位全方位的資源和組織依賴。唯有告別單位壟斷公共性的資源,使社區公共性資源提供更加多元和擴散方可弱化對單位的依賴。
其次,激發社區社會性,開拓社區“新公共性”實現空間。“新公共性”的核心是構建新型的社會整合與聯結方式,在單位制走向終結的背景下,需要以“社區活動”激發成員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從而將社區打造成真正承載社區成員公共性訴求的生活“共同體”。
再次,構建志愿性非盈利組織,推進社區“新公共性”行動落實。理論界已經意識到,要想徹底走出以單位為載體的傳統公共性形態,就必須建立起各類社區性的非盈利的志愿組織以便落實新公共性的活動。社區成員通過參與志愿性非盈利組織的活動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實現了利他主義的功能,利他取向的行動構建起了社區層面互助的“公共領域”,而此種承載著新的“社群生活”和“公共言說”的空間正是“新公共性”得以孕育的土壤。通過構建志愿組織開展社區的自我服務與管理,使得社區行動徹底告別了單位社會中縱向一體化的行政式的活動方式,社區的公共性形態才真正得以創新。
固然“后單位社會”新型公共性的構建面臨著諸多的限制與困境,但社區發展的勃興與社會力量的不斷壯大逐漸促進“新公共性”從理念走向實踐。與此同時,單位體制的消解和不斷涌現的反向運動使得“新公共性”的實現途徑與表現形態尚顯模糊。而新公共性的內涵則是社會性的“公”與個人利益的“私”的有機結合,“個體在置身于‘公’的場合中獲得生活的領域,這種情況下‘個’性并沒有消亡,而是成為新的‘公’中所攜帶著的‘個’的內核。”*[日]佐佐木毅、[韓]金泰昌主編:《21世紀公共哲學的展望》,卞崇道、王青、刁榴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頁。作為“公”和“私”有機融合的公共性形態,必須“賦予所有人——不分社會地位,文化或職業的所屬性——以關注公共性事物的權利”*[德]沃爾夫岡·霍爾等:《阿倫特手冊》,王旭、寇瑛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546頁。,并在此基礎上積極開展互助性的社區活動,從而實現更加和諧與多元的“新公共性”。
(責任編輯:陸影)
收稿日期:2016-04-25
作者簡介:田毅鵬,政治學博士,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發展社會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當代中國單位制度形成及變遷研究”(項目編號:11&ZD147)的階段性成果。
[中圖分類號]C9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45[2016]06-0040-11
·單位制變遷與社會治理(學術主持人:田毅鵬)·
劉博,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社會學博士研究生,黑龍江中醫藥大學社會工作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發展社會學。
主持人語:近年來,伴隨著社會治理話語不斷走向高漲,在社會治理研究和實踐中出現了一種技術化和微觀化的觀點和趨向,而對社會治理自身所蘊涵的結構性變遷的根本性意義和價值重視不夠。而本組的3篇論文則試圖強調社會治理過程中微觀視域與宏觀面相的結合,認為只有將當下的社會治理置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總體的社會結構轉型進程之中,才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理解。因為計劃經濟、單位體制等制度性因素既是當下中國社會治理展開的背景,又是作為真實的社會元素影響和參與到社會治理的具體過程之中的。
本組論文試圖通過對單位制變遷的解讀,來理解中國社會當下正在展開的社會治理和變遷。田毅鵬和劉博將公共性理論與公共性結構形成及轉換結合起來,認為單位制作為新中國社會整合與管理的典型制度,對中國社會“公共性”的結構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單位制形成前,傳統社會結構的特性壓制了現代意義的公共性的生發與擴展。單位制的構建使得國家主導的“大公共性”不斷彰顯,但其實際運作邏輯則凸顯了“小公共性”的集體利益。市場化改革后的單位制變遷使得大小“雙重公共性”之間的同構性被打破,基于單位自身利益的“自主型公共性”成為局部消解“大公共性”的力量。“后單位社會”的來臨正在呼喚一種“新公共性”的到來,如何調動社區力量構建“新公共性”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管理體制本土性與復雜性交融的實踐場域。蘆恒則將研究目光鎖定在走向老化的單位居住區。提出當前城市棚戶區改造后的回遷社區成為社會治理的盲區,其治理之道不僅在于簡單地進行空間改造,而是堅持一種基于歷史連續性治理理念的指導下,將城市棚戶區的形成與回遷等問題均置于單位體制變遷的新舊因素互動框架之中,挖掘單位社會自身在組織、動員、社會空間、單位人主體性等方面的優勢,在單位人再組織化、健全動員機制、重塑社區認同感、激活單位人抗逆力等方面,對棚戶區進行優勢治理。張曉溪通過對工業主義與單位制關系的解讀,來把握單位制度變遷的深層內涵。認為在單位制度變遷與革新過程中,應對工業主義進行合理的反思與反省,以推陳出新。與工業主義相抗衡的是單位制度觀念、血緣親情倫理,而并非單純的精英主義。單位制度一方面要吸納工業主義的優勢——工序管理的數字化、精細化、開放的市場化,另一方面也要在共享價值與意義的活動與儀式中回歸與呈現集體情感的愉悅與暢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