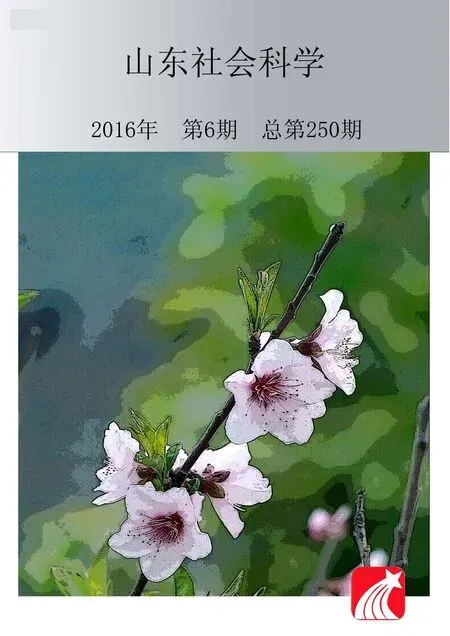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中個人主義話語的邊緣化
徐紅妍
(山東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 山東 濟(jì)南 250014;洛陽理工學(xué)院 中文系, 河南 洛陽 471023)
論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中個人主義話語的邊緣化
徐紅妍
(山東師范大學(xué) 文學(xué)院, 山東 濟(jì)南250014;洛陽理工學(xué)院 中文系, 河南 洛陽471023)
[摘要]個人主義作為西方社會文明的精髓,在晚清至“五四”時期傳入中國并成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轉(zhuǎn)型期的一個關(guān)鍵性概念。但個人主義是源于西方的文化觀念,在現(xiàn)代文學(xué)發(fā)展期間,個人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左翼文學(xué)等不斷發(fā)生沖突與摩擦,直到最終被徹底否定,個人主義話語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中呈現(xiàn)出了一種邊緣化困境。
[關(guān)鍵詞]現(xiàn)代文學(xué);個人主義;集體主義;邊緣化困境
個人主義作為西方社會文明的精髓,在晚清至“五四”時期傳入中國并成為“五四”文學(xué)批判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和禮教秩序的思想武器。個人主義在西方有著強(qiáng)大的文化傳統(tǒng)與社會根基,法治精神、契約社會、自由傳統(tǒng)都保障了個人主義在西方的通行,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忠、孝、仁、義等普遍價值在某種程度上與西方的個人主義相互排斥,因此,個人主義在傳入中國后不斷與傳統(tǒng)文化、左翼文化發(fā)生沖突并處于一種邊緣化的困境。個人主義在中國的艱難處境表現(xiàn)出西方文明在植入中國時所缺乏的文化根基,直到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確立了文學(xué)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文學(xué)觀,擴(kuò)大了集體主義話語的影響,個人主義話語從此失去了它的合法性與生存空間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一、中西文化碰撞中“人”的沖突
中國傳統(tǒng)文化語境中的“人”與西方個人主義話語中的“人”在內(nèi)涵上有著根本不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很早就有“人”的觀念,但中國的“人”是倫理中的人。儒家文化最重要的一點(diǎn)是“仁者,人也”*王國軒譯注:《大學(xué)·中庸》,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95頁。。“仁”字從字形構(gòu)造來看是“人”字旁邊有“二”,也就是說,“人”是在二人或多人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中的概念,“仁”則是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之道。在人與人的相處中,理想的關(guān)系便是以仁的態(tài)度處處以別人為重,即“親親為大”*王國軒譯注:《大學(xué)·中庸》,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95頁。。除此之外,中國傳統(tǒng)文化還將“人”納入五倫秩序中:“中國的五倫就是中國社會組織,離了五倫別無社會。把個人編入于這樣的層系組織中,使其居于一定的地位,然后課以那個地位所應(yīng)盡的責(zé)任。”*張東蓀:《理性與民主》,岳麓書社2010年版,第81-82頁。人在這種倫理關(guān)系中承擔(dān)的是無條件的義務(wù),而沒有為自己而存在的空間和權(quán)利。
在西方個人主義話語中,“人”一般稱為“個人”,“個人”對應(yīng)的詞語是“individual”,這一英文詞源于拉丁文“individunns”,本意為不可分割的,用“individual”一詞來指涉一個人意味著個人是不可分割的最小的社會單元。“individual”一詞被用以表達(dá)人權(quán)觀念是在17世紀(jì),這一時期西方現(xiàn)代社會組織逐步成熟,個人成為自然權(quán)利的主體,個人擁有權(quán)利和表達(dá)權(quán)利成為西方個人觀念的核心。個人成為權(quán)利主體,社會組織的基本單位只能是個人。*金觀濤、劉青峰:《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演變及其形態(tài)初探》,《二十一世紀(jì)》2004年8月號,總第84期。因此,西方個人主義話語的個人是獨(dú)立的、作為權(quán)利主體和社會組織基本單元的個人。
因此,中西文化語境下“人”的根本區(qū)別在于:中國文化語境下的“人”是作為道德主體和倫理關(guān)系中的人,人是在與其他人的關(guān)系中獲得自己的位置,因此,中國的“人”強(qiáng)調(diào)義務(wù)、孝道等;而西方的“人”更注重個人權(quán)利和自我實(shí)現(xiàn)的價值,強(qiáng)調(diào)人的獨(dú)立自主性,這是中西兩種文化中“人”的根本區(qū)別。
“五四”時期,陳獨(dú)秀、李大釗、胡適、周作人、魯迅、傅斯年等人極力宣揚(yáng)個人主義,倡導(dǎo)青年人做獨(dú)立自主的“個人”。陳獨(dú)秀的《敬告青年》、胡適的《易卜生主義》、周作人的《人的文學(xué)》、李大釗的《萬惡之源》、傅斯年的《人生問題之發(fā)端》等文章提出個性發(fā)展、獨(dú)立人格、自我實(shí)現(xiàn)等個人主義的基本內(nèi)涵,這種個人觀念與儒家倫理規(guī)范的“人”拉開了距離,體現(xiàn)出一種現(xiàn)代個人觀。新文化運(yùn)動先驅(qū)者中魯迅最早提倡個人主義,1907 年的《文化偏至論》已將西方個人主義鄭重介紹到中國,十年以后《狂人日記》中著名的“吃人”意象揭示了幾千年文明史上“個人”一直被吃掉的現(xiàn)實(shí),*關(guān)于《狂人日記》主題所謂“禮教吃人”,近年有研究指出,實(shí)質(zhì)揭示的是“對人的自由意志的壓制和褫奪”。參見周南:《〈狂人日記〉吃人意象生成及其相關(guān)問題》,《東岳論叢》2014年第8期。而魯迅認(rèn)為,只有這種現(xiàn)代個人才能夠承擔(dān)建設(shè)“人國”的重任:“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zhuǎn)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dú)見于天下。”*魯迅:《文化偏至論》,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頁。在“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先驅(qū)的極力倡導(dǎo)下,個人主義話語成為一種極具感召力的人生觀念,青年一代大膽追求個人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反抗倫理本位的人,突破傳統(tǒng)文化對人作為道德主體的定義與限制,一時間個人主義話語中的“自我”、“個人”、“自由”、“個性”、“權(quán)利”成為熱門詞匯并形成了一股個人主義文學(xué)思潮。
在個人主義話語的影響下,“五四”文學(xué)作品中塑造的個人已不再遵守傳統(tǒng)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而是有了個性追求,“五四運(yùn)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fā)現(xiàn)。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xiàn)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郁達(dá)夫:《〈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散文二集〉導(dǎo)言》,載趙家璧主編:《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第七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35年版,第5頁。“個人”的發(fā)現(xiàn)確立了人的自主地位,肯定了人之為人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郁達(dá)夫《沉淪》中主人公對愛情的追求、對性欲的袒露是作為一個獨(dú)立個人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我”無論是追求愛情還是袒露被壓抑的性欲都有一種置傳統(tǒng)禮教于不顧的個性意識與權(quán)利意識。郁達(dá)夫《茫茫夜》中的同性戀、魯迅《傷逝》中子君與涓生的未婚同居等都在強(qiáng)調(diào)他們作為個人的自主權(quán)利:“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quán)利!”這種個人的權(quán)利意識完全是西方文化概念,“中國的道德語言是產(chǎn)生不了‘權(quán)利’的觀念,只有義務(wù)的觀念。此外,權(quán)利是以個人為本位,這又和中國的家族一體的想法不合”*余英時:《中國近代個人觀的改變》,載《現(xiàn)代儒學(xué)的回顧與展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2年版,第86頁。。中國社會是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人”是倫理中的人,每個人對自己的角色既要遵守倫理秩序,又負(fù)有義務(wù)。郁達(dá)夫、魯迅、郭沫若、廬隱、馮沅君、倪貽德等作家筆下的個人有強(qiáng)烈的個性意識,他們不再遵守綱常倫理,更沒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德預(yù)期,他們看重的是自由與個人權(quán)利,這種個人觀念顛覆了傳統(tǒng)文化中人的觀念,“個人一語,入中國未三四年,號稱識時之士,多引以為大詬,茍被其謚,與民賊同。”*魯迅:《文化偏至論》,載《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51頁。魯迅的這段話精準(zhǔn)地道出了個人主義話語在傳入中國后遭遇到的“水土不服”的文化困境。正是中西文化語境的不同使個人主義在中國經(jīng)常被誤解為自私自利和不負(fù)責(zé)任,這在本質(zhì)上是中西兩種“個人”觀念的沖突。
“五四”文學(xué)創(chuàng)作明顯蘊(yùn)含著中西兩種“個人”觀念的沖突,而且這種沖突成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痛苦根源。魯迅的《狂人日記》、《孤獨(dú)者》、《在酒樓上》等作品中的人物努力做一個獨(dú)立的有個性的人,在他們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狂放不羈的個性、迥異于世俗的行為與傳統(tǒng)文化對人的預(yù)期大相徑庭。傳統(tǒng)文化中的人對道德、倫理秩序的遵守是一種義務(wù),“‘仁義道德’掩蓋了四千年文明背后真實(shí)的奴役關(guān)系”,這是魯迅“震驚的絕望與黑暗”*周南:《〈狂人日記〉吃人意象生成及其相關(guān)問題》,《東岳論叢》2014年第8期。。因此狂人、魏連殳、呂緯甫等人追求的現(xiàn)代個人觀與傳統(tǒng)文化的個人觀產(chǎn)生的激烈沖突造成了他們精神上的痛苦。郭沫若的《殘春》描寫了不為傳統(tǒng)所容納的婚外情,主人公的個性追求最終幻化為悲劇。巴金《家》中的高覺新是被傳統(tǒng)文化塑造的符合倫理規(guī)范的人,但他內(nèi)心覺醒的自我意識又使他體驗(yàn)到這種倫理人的痛苦。廬隱、馮沅君、蘇青、冰心等作家描寫了新一代的青年拒絕做倫理化的人,而是以自由意志勇敢地主宰自己的命運(yùn),試圖做一個現(xiàn)代化的個人,但是來自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道德觀念卻阻礙他們,他們追求的現(xiàn)代個人觀無法被傳統(tǒng)文化所接受、所認(rèn)可,最終導(dǎo)致他們的精神痛苦。
現(xiàn)代個人觀源于西方現(xiàn)代社會的成熟,霍布斯的《利維坦》、洛克的《政府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的精神》等著作提出了現(xiàn)代社會的組織形式。現(xiàn)代社會承認(rèn)個人是自然權(quán)利的主體,契約與法律成為組成社會的根本機(jī)制,并最大限度地保護(hù)個人自由、維護(hù)個人價值、肯定個人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的先驅(qū)將個人主義話語引進(jìn)中國,并將其作為思想啟蒙的工具與觀念,號召青年人充分發(fā)展自己的個性,但他們忽視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體系與社會基礎(chǔ),更沒有預(yù)想到個人主義話語在融入中國文化語境時可能遭遇的困境,因此,當(dāng)中國社會面臨政治混亂和頻繁戰(zhàn)爭時,個人主義話語很快就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并逐漸成為一種邊緣化存在。
二、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摩擦
個人主義話語在“五四”時期的廣泛傳播促進(jìn)了“人”的覺醒、個性意識的萌芽,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張表現(xiàn)自我、突出個性,打破傳統(tǒng)文學(xué)“文以載道”的文藝觀,從而革新了一代人的文學(xué)觀念,帶來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新面貌。但20世紀(jì)20年代隨著階級意識的興起,強(qiáng)調(diào)集體主義的左翼文學(xué)迅速發(fā)展,“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以后,普羅文學(xué)就執(zhí)了中國文壇的牛耳”*郁達(dá)夫:《光慈的晚年》,載《郁達(dá)夫全集》第3卷,浙江大學(xué)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頁。,左翼文學(xué)秉持集體性、工具性的文學(xué)觀,強(qiáng)烈排斥個性意識與自由觀念,否定文學(xué)的個人主義話語。“五四”文學(xué)的個人主義話語與左翼文學(xué)的集體主義話語的根本沖突是“小我”與“大我”的沖突。所謂“小我”指的是個人主義話語中的“個人”,“大我”則是集體主義話語中的“我們”。“小我”強(qiáng)調(diào)自由、個性與權(quán)利的同時,也不否認(rèn)集體的存在,但是“小我”觀認(rèn)為集體只是無數(shù)個人的集合,個人不是任何人或任何集體的工具,“個人參加團(tuán)體之后,既不可能獲得新的權(quán)利,也不可能失去他所應(yīng)該具有的權(quán)利。”*[美]愛因·蘭德:《新個體主義倫理觀——愛因·蘭德文選》,秦裕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101-102頁。“大我”在左翼文學(xué)的集體主義話語中是消融了個性和權(quán)利的“我們”,個人的價值以是否服務(wù)于集體、服從集體利益為衡量標(biāo)準(zhǔn)。左翼文學(xué)的集體主義話語將中國傳統(tǒng)倫理中的“人”置換為集體中的“我們”,這與“五四”文學(xué)所宣揚(yáng)的“個人”發(fā)生了沖突。
早期的創(chuàng)造社主張個性解放和自我表現(xiàn),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著鮮明的個人主義傾向,郭沫若、郁達(dá)夫、田漢等人作品中“小我”的個性鋒芒曾一度激起眾多文學(xué)青年的共鳴。隨著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xué)在中國的興起,創(chuàng)造社成員開始重新調(diào)整自己的文學(xué)主張,他們逐漸放棄“小我”轉(zhuǎn)而追求“大我”。 一向標(biāo)榜文學(xué)是自我表現(xiàn)的郭沫若在轉(zhuǎn)向后稱“個人主義的文藝?yán)显邕^去了”*麥克昂:《英雄樹》,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革命文學(xué)”論爭資料選編》(上),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0年版,第58頁。,他的《革命與文學(xué)》、《留聲機(jī)的回音——文藝青年應(yīng)取的態(tài)度的考察》等文章論述了革命文學(xué)的正當(dāng)性,反對個人主義文學(xué):“我們對于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要根本劃除,對于浪漫主義的文藝也要取一種徹底反抗的態(tài)度。”*郭沫若:《革命與文學(xué)》,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革命文學(xué)”論爭資料選編》(上),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頁。李初梨聲稱前期創(chuàng)造社的文學(xué)使命已經(jīng)完結(jié),“當(dāng)時文學(xué)上的標(biāo)語,是‘內(nèi)心的要求’,‘自我的表現(xiàn)’,這的確是小布爾喬亞意識的結(jié)晶”,目前要“以無產(chǎn)階級的階級意識,產(chǎn)生出來的一種的斗爭的文學(xué)”。*李初梨:《怎樣地建設(shè)革命文學(xué)》,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革命文學(xué)”論爭資料選編》(上),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120頁。“階級意識”是一種與個人意識相對的集體意識,創(chuàng)造社成員對階級意識的認(rèn)同意味著他們放棄“小我”融入“大我”,“自覺個性的消失,以及感情和思想轉(zhuǎn)向一個不同的方向,是就要變成組織化群體的人所表現(xiàn)出的首要特征”*[法]勒龐:《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馮克利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頁。。
創(chuàng)造社成員不僅自己完成了從“小我”到“大我”的轉(zhuǎn)換,而且與太陽社以及其他左翼作家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以聯(lián)盟的形式表達(dá)革命文學(xué)主張和政治主張,“批判一切個人主義、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等類的腐化的意識”*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載《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頁。,營造了聲勢浩大的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以個人主義、個性解放為思想基礎(chǔ)的“五四”新文學(xué)在十幾年的發(fā)展時間里,批判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的舊文藝,反對“文以載道”的舊式文藝觀,積極倡導(dǎo)“為人生”或“為藝術(shù)”的文學(xué),革新了一代人的文學(xué)觀念,使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在最早的十年里有了重大收獲。郭沫若等人的突然轉(zhuǎn)向以及對個人主義文學(xué)的猛烈攻擊,引發(fā)了左翼文學(xué)與梁實(shí)秋、林語堂等人之間的沖突。
新月派是這一時期重要的個人主義文學(xué)社團(tuán),它在文藝上持個人主義主張,反對無產(chǎn)階級文學(xué),主張文學(xué)的獨(dú)立、自由、健康、尊嚴(yán)。新月派的個人主義文學(xué)主張招致了彭康、馮乃超等左翼成員的猛烈抨擊,他們指責(zé)新月派的文學(xué)自由論和超階級的人性論是一種反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文學(xué)觀點(diǎn)。作為新月派成員的梁實(shí)秋反對左翼文學(xué)以集體的名義對人的個性進(jìn)行抹殺,“無論文學(xué),或是革命,其中心均是個人主義的,均是崇拜英雄的,均是尊重天才的,與所謂的‘大多數(shù)’不發(fā)生任何關(guān)系。”*梁實(shí)秋:《文學(xué)與革命》,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革命文學(xué)”論爭資料選編》(下),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2010年版,第783頁。梁實(shí)秋的“所謂大多數(shù)”指的是集體的“大我”,他認(rèn)為革命文學(xué)強(qiáng)調(diào)階級性和集體性造成了對“小我”的壓抑。
林語堂的個人主義文學(xué)觀同樣遭到了左翼文學(xué)的攻擊。林語堂于1932年和1934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論語》、《人間世》等刊物,提倡個性化的小品文,并在《人間世》發(fā)刊詞中提出“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格調(diào)”的創(chuàng)作主張,在取材方面林語堂也主張自由與個性——“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取材”*林語堂:《發(fā)刊〈人間世〉意見書》,《論語》第38期,1934年4月1日。,林語堂的小品文主張體現(xiàn)了他的個人主義文學(xué)觀,得到了眾多個人主義作家的支持與響應(yīng),周作人、廢名、施蟄存、朱光潛、俞平伯、孫伏園等作家都積極在《論語》、《人間世》上發(fā)表作品。林語堂倡導(dǎo)的小品文促進(jìn)了個性化散文在這一時期的發(fā)展,豐富了現(xiàn)代散文創(chuàng)作的風(fēng)貌。但這種小品文卻遭到了左翼文學(xué)作家的非議,他們指責(zé)林語堂背離了社會環(huán)境一味追求消閑,作品缺乏戰(zhàn)斗性和時代氣息。為了對抗林語堂提倡的個性小品文,左翼作家創(chuàng)辦《太白》半月刊,專門發(fā)表戰(zhàn)斗性的小品文,以“大我”的話語與林語堂的“小我”話語形成對壘。
“五四”時期個人主義話語的興起曾經(jīng)鼓舞過無數(shù)青年人,給予他們反抗壓迫、追求自由的力量,“回想當(dāng)年,個人主義曾經(jīng)和‘個性解放’、‘人格獨(dú)立’等等的概念相聯(lián)系,在我們反對封建壓迫、爭取自由的斗爭中給予過我們鼓舞的力量”*周揚(yáng):《文藝戰(zhàn)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人民日報》1958年2月28日。。但左翼文學(xué)卻將個人主義視為阻礙革命前進(jìn)的絆腳石,強(qiáng)調(diào)青年人必須克服個人主義思想,實(shí)現(xiàn)去個體化過程,將“小我”融入“大我”的血色激情之中才能獲得生命的意義。正是基于這樣的邏輯思維,左翼文學(xué)構(gòu)建了與“五四”個人主義文學(xué)完全不同的審美形態(tài),華漢的《地泉》、蔣光慈的《沖出云圍的月亮》、胡也頻的《到莫斯科去》、茅盾的《子夜》、洪靈菲的《流亡》等作品中濃郁的革命意識與“大我”話語取代了“五四”以來的個人主義話語,展示了“大我”對“小我”的征服。左翼文學(xué)通過對集體意志的強(qiáng)調(diào),指出個人放棄自我融入集體之后,不僅沒有憂郁、恐懼、懷疑等情緒,而且還獲得了某種永恒的價值,這種集體至上的革命話語使個人主義話語面臨著被“組織化”的困境。左翼文學(xué)作家也不再是有著主體精神的獨(dú)立個體,而是變成了集體主義的代言人,他們以集團(tuán)的形式、以排山倒海的氣勢極力宣傳革命文學(xué)的正當(dāng)性和前衛(wèi)性,這使一向崇尚自由、獨(dú)立且不善以集體面貌示人的個人主義作家無法抵擋這種強(qiáng)烈的話語霸權(quán),當(dāng)他們以自由、個性、獨(dú)立等個人主義詞匯去對抗階級、革命、集體主義等“救國救世”的宏大話語時更顯蒼白無力,個人主義話語在與集體主義話語的沖突中越來越滑向現(xiàn)代文學(xué)的邊緣。
三、民族救亡意識下個人主義話語的“末路”
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進(jìn)入全面抗戰(zhàn)狀態(tài),不同團(tuán)體的作家此時團(tuán)結(jié)在一起,并于1938年在武漢成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簡稱“文協(xié)”。“文協(xié)”成立后,民族救亡意識在文學(xué)上的表現(xiàn)空前高漲,產(chǎn)生了大量閃耀著熾熱的抗日救亡精神的文學(xué)作品。由于抗日文學(xué)作品多數(shù)是短時間內(nèi)的急就章,主題又統(tǒng)一指向抗日,在藝術(shù)上難免存在不少缺陷。針對這一情況,梁實(shí)秋、沈從文、施蟄存等個人主義作家都不同程度地作出了批評,引發(fā)了個人主義與民族救亡意識之間的論爭與沖突。
梁實(shí)秋在抗戰(zhàn)時期無意間挑起了文學(xué)界“與抗戰(zhàn)無關(guān)論”的爭論。1938年12月1日,梁實(shí)秋接編重慶《中央日報》的副刊《平明》并發(fā)表了《編者的話》,文中的一段話引起了文壇的軒然大波,“現(xiàn)在抗戰(zhàn)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筆就忘不了抗戰(zhàn)。我的意見稍為不同。于抗戰(zhàn)有關(guān)的材料,我們最為歡迎,但是于抗戰(zhàn)無關(guān)的材料,只要真實(shí)流暢,也是好的,不必勉強(qiáng)把抗戰(zhàn)截搭上去。至于空洞的‘抗戰(zhàn)八股’,那是對誰都沒有益處的。”*梁實(shí)秋:《編者的話》,《中央日報·平明》1938年12月1日。梁實(shí)秋反對沒有個性的“抗戰(zhàn)八股”,提倡有個性的創(chuàng)作。但在全民抗戰(zhàn)的高漲情緒下,個性自由、個性文學(xué)與民族存亡相比顯得微不足道,因此,梁實(shí)秋的文章引起了社會的激烈反擊。羅蓀與宋之的分別發(fā)表《與抗戰(zhàn)無關(guān)》、《談“抗戰(zhàn)八股”》等文對梁實(shí)秋進(jìn)行批駁,此后一段時間,《大公報》、《國民公報》、《抗戰(zhàn)文藝》、《文藝陣地》、《文學(xué)月報》等刊物相繼發(fā)表多篇批判梁實(shí)秋的文章。面對文壇咄咄逼人的氣勢,梁實(shí)秋只好匆匆辭去《中央日報》副刊主編的職務(wù)。
同樣持個人主義文學(xué)觀的沈從文也不滿當(dāng)時文壇的創(chuàng)作狀況,他在《再談差不多》一文中說:“是好好的多用點(diǎn)心思,寫出些有風(fēng)格有個性有見解的作品好,還是不思不想寫點(diǎn)不三不四應(yīng)景湊趣小文,且跟隨著風(fēng)氣來嚷嚷罵罵好?”*沈從文:《再談差不多》,載《沈從文全集》第17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頁。沈從文批評跟風(fēng)文學(xué),強(qiáng)調(diào)作家獨(dú)立自由的精神,這種個人主義話語與全民抗戰(zhàn)的氛圍格格不入,很快引來了眾多作家的批判。郭沫若在《新文藝的使命》一文中斥責(zé)這種個人主義文藝觀是“逆流”:“在這種洪濤激浪的澎湃當(dāng)中,總也不免有些并不微弱的逆流。起先我們是聽見‘與抗戰(zhàn)無關(guān)’的主張,繼后又聽見‘反對作家從政’的高論,再后則是‘文藝的貧困’的呼聲——叫囂著自抗戰(zhàn)以來只有些田間式的詩歌與文明戲式的話劇。”*郭沫若:《新文藝的使命——紀(jì)念文協(xié)五周年》,載《郭沫若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頁。郭沫若的這篇文章反映了當(dāng)時文學(xué)界對個人主義的態(tài)度,也為日后對沈從文等人的清算埋下了伏筆。建國前夕郭沫若的《斥反動文藝》則把沈從文、朱光潛、蕭乾等個人主義作家徹底打入了反動者行列,這預(yù)示著個人主義話語在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徹底失去生存的空間與合法性。
民族抗戰(zhàn)的形勢造就了國統(tǒng)區(qū)和延安地區(qū)并存的局面,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延安地區(qū)在抗戰(zhàn)時期成為眾多知識青年神往的革命圣地,蕭軍、丁玲、王實(shí)味、何其芳、艾青等作家正是帶著自由、平等的個人主義文學(xué)想象來延安尋求新的生活的。由于這些作家深受“五四”個人主義話語的影響,個性自由和個性解放既是他們的價值觀,也構(gòu)成了他們的文學(xué)想象。來到延安之后,這些作家依然保持著個人主義的文化痕跡與創(chuàng)作趣味,對延安地區(qū)的官僚作風(fēng)和等級觀念提出了批評。丁玲的《三八節(jié)有感》抨擊了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長至上”的官僚作風(fēng),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批評了基層領(lǐng)導(dǎo)干部對上奴顏婢膝、對下頤指氣使的不良風(fēng)氣,王實(shí)味的《野百合花》尖銳地抨擊了延安的等級制度和官僚化趨向,揭露了延安“新生活”的陰影,反映了知識青年在理想破滅后的失望和沮喪,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提出作家要有寫作的自由。這些文章對延安地區(qū)的尖銳批判彰顯了作家的個性意識和主體精神,蘊(yùn)含著一種個人主義的文學(xué)價值觀,閃耀著“五四”個人主義話語的光芒。
由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延安在各種政治力量的夾縫中求生存,這使它在意識形態(tài)上追求高度的一致性,在文學(xué)藝術(shù)上要求文藝無條件地服從政治需要,形成了文學(xué)為政治服務(wù)的藝術(shù)倫理。丁玲、蕭軍、王實(shí)味等人鼓吹的民主、平等、自由、個性等個人主義思想和延安地區(qū)集體至上的精神格格不入,如果任由這種個人主義思想自由發(fā)展,必然引發(fā)人的主體精神和個性意識的高揚(yáng),而確立集體至上的目標(biāo)必須削弱個性意識,“想要把一個人完全同化到集體,對個人特殊性的抹殺必須徹底”*[美]霍弗:《狂熱分子:碼頭工人哲學(xué)家的沉思錄》,梁永安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8年版,第92頁。。因此,丁玲、蕭軍、王實(shí)味等人宣揚(yáng)的個人主義思想成為一種必須予以清除的思想障礙,于是便有了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延安講話的文藝觀遏制了個人主義思想,糾正了文藝界的個人主義傾向,是左翼革命文學(xué)觀的進(jìn)一步深化,從此延安文藝界的氣氛和創(chuàng)作方向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改變了“五四”文學(xué)以來開創(chuàng)的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使文學(xué)朝著一元化的格局發(fā)展。許多作家在講話發(fā)表后終于爆發(fā)了“靈魂深處的革命”,開始有了脫胎換骨的轉(zhuǎn)變。何其芳拋棄舊我走上了自新的道路,創(chuàng)作出了《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生活是多么廣闊》等符合講話精神的詩歌。丁玲在目睹王實(shí)味走向自我毀滅的道路之后態(tài)度發(fā)生了徹底轉(zhuǎn)變,她對自己作為主編刊發(fā)了王實(shí)味的《野百合花》而深刻反省自責(zé):“馬馬虎虎的發(fā)表了這樣反黨的文章在黨報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恥辱和罪惡。我永遠(yuǎn)不忘記這錯誤,我要時時記住作為自己的警惕。”*丁玲:《文藝界對王實(shí)味應(yīng)有的態(tài)度及反省》,載張炯主編:《丁玲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頁。在懺悔了自己的思想錯誤之后,丁玲迅速跟上講話精神的步伐,創(chuàng)作出了一批符合新文藝規(guī)范的作品,終于成為新文藝路線的代表作家。《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使很多作家的世界觀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而改變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方向,開啟了當(dāng)代文學(xué)的發(fā)展格局與風(fēng)貌,個人主義話語在隨后的文學(xué)作品里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建國之后更是被當(dāng)作毒素予以清除。通過對作家思想和文學(xué)作品的不斷“純化”,個人主義話語在當(dāng)代文學(xué)中幾乎銷聲匿跡。
個人主義自“五四”時期興起,到與左翼文學(xué)、抗戰(zhàn)文學(xué)的論爭,再到延安時期的被肅清,其曲折經(jīng)歷顯示了外來文化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所遇到的各種困境。個人主義首先遭遇文化的“水土不服”,使其無法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展開有效的對接與融合;在傳播過程中又遇到中國社會的頻繁戰(zhàn)亂和動蕩不安,民族救亡的社會環(huán)境使個人主義話語很快失去了吸引力。作為少數(shù)知識分子的烏托邦理想,個人主義始終難以融入中國的文化語境,更難以成為中國的社會現(xiàn)實(shí),因此,個人主義話語最終在集體主義話語的擠壓下漸漸退出歷史舞臺。
(責(zé)任編輯:陸曉芳)
收稿日期:2016-02-15
作者簡介:徐紅妍(1978—),女,山東高密人,山東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博士生,洛陽理工學(xué)院中文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yàn)橹袊F(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45[2016]06-008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