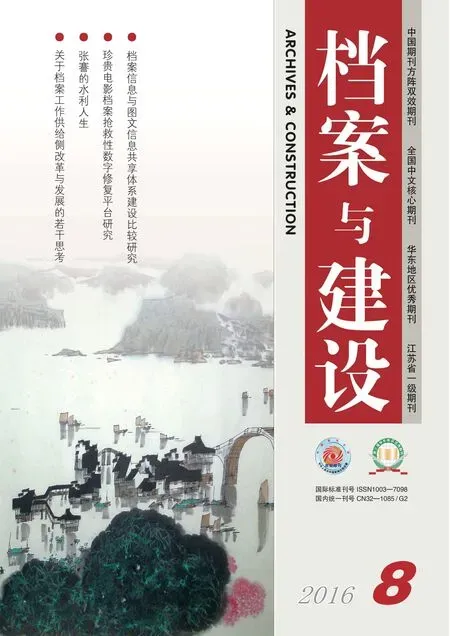檔案信息與圖文信息共享體系建設比較研究*
胡 杰 張照余(.蘇州科技大學圖書館,江蘇蘇州,5009;.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江蘇蘇州,5000)
檔案信息與圖文信息共享體系建設比較研究*
胡杰1張照余2
(1.蘇州科技大學圖書館,江蘇蘇州,215009;2.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江蘇蘇州,215000)
文章對檔案信息與圖文信息的共享體系進行了比較與分析,總結了兩者在建設背景、現狀、組織、標準和技術等方面的異同點,并借鑒圖文體系的成功做法對建設全國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提出建議與啟示。
檔案圖書文獻共享體系比較
網絡環境下,檔案信息與圖書文獻信息都致力于建設各自的資源共享體系,有學者認為應該整合圖書、情報、檔案資源建立一體化的信息資源共享體系,然而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以下簡稱檔案體系)與圖書文獻信息資源共享體系(以下簡稱圖文體系)在建設目標、組織標準等方面都不盡相同,本文擬對兩者的建設情況進行比較和分析。同時有鑒于國內圖書文獻共享體系起步較早,CALIS等體系已較為成熟,總結其經驗可以為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建設提供一些借鑒與啟示。
1 建設背景比較
圖書館界在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方面探索已久,早在1957年國務院就曾制定過《全國圖書協調方案》,但離開互聯網絡技術,要實現手工條件下的文獻資源共享可以說是天方夜譚。因此,圖文體系與檔案體系大規模建設都離不開互聯網絡發展的時代背景。
1.1相同點分析
互聯網的發展已經歷了30多年的歷史,是20世紀最具影響的技術成就之一,對各行各業都具有巨大的滲透力。圖書、情報、檔案作為傳統的信息服務產業要在網絡環境下尋求立足之地和新的發展機遇,也必須借助互聯網絡技術整合全國甚至全世界的資源以提供信息服務和利用。在此背景下,圖書館依托CERNET建立聯機編目系統,檔案館構建Internet之上的基于超鏈的全國檔案網站集群,奠定了各自資源體系的基礎。云計算技術是互聯網未來發展的趨勢,利用云計算技術可以將大量用網絡連接的計算資源統一管理和調度,構成一個計算資源池并按需服務,目前已經被廣泛應用在科研、網絡安全、醫學等領域。在信息服務和信息共享方面,云計算技術具有安全性強、對用戶端設備要求低、可租用、交付的是服務等優勢[1,2],因而在云計算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勢必會推動全國范圍圖書館和檔案館信息資源的整合與共享。
此外,檔案體系與圖文體系的發展都借鑒了國外相關領域的成功經驗,如美國的OCLC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合作網,從1971年實現聯機計算機檢索以來,OCLC已為全世界112個國家和地區的71000多個圖書館提供信息服務[3]。而美國檔案與文件署(NARA)也是世界上第一個通過信息網絡實現檔案資源共享的機構,其檔案信息導航系統(NAIL)能檢索到200多個檔案館的數字化檔案[4]。國外的成功經驗首先拓展了我們的視野,為我們勾勒了資源共享的藍圖。吸收和采納國際上的先進理念,是推動我們共建共享的重要動力。其次,在共享體系具體的組織、利益分配、建設標準等方面國外模式也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1.2不同點分析
檔案體系與圖文體系建設具有相同的外在背景因素,但在建設的緊迫性和內在動機上卻存在較大的差異。20世紀90年代,圖書館理論界提出“擁有與獲取理論”,指出“獲取”比“擁有”更重要,主張通過館際互借、文獻傳遞、數據庫及因特網服務等服務方式彌補單個館藏的不足,實現文獻信息資源的共建共享。而現實中90年代前期外文圖書期刊訂購年年漲價,高校圖書館經費年年緊縮,“剪刀差”越來越大[5]。在此背景下,1996年北京大學向教育部提出建設文獻保障體系的初步建議,并于1998年正式立項建設。可見,建設圖文體系是解決日益增長的文獻采購開支與滿足用戶文獻需求之間現實矛盾的“逼上梁山”的結果。
相比而言,檔案資源的共享囿于安全考慮一直較為保守,學界關于重藏還是重用的討論持續多年。檔案由具有保存價值的現行文件轉化而來,當現行文件作用發揮完畢時具有保存價值的那部分文件轉為檔案并經過一定的手續由文件形成部門移交到檔案館。對于用戶而言檔案的價值是其原生性的特點,檔案部門不必通過不斷采訪和擴充館藏來滿足和吸引用戶,因此不存在必須聯合共建以減少采購成本的主觀動機和緊迫性。總的來說,建設檔案資源共享體系是在信息化、網絡化以及政府信息公開化的形勢背景下,積極促進檔案事業發展以適應社會要求的必然趨勢。
2 建設現狀比較
國內圖書文獻信息資源保障體系建設已經初見成效。首先,各地區的區域性圖書館聯盟蓬勃發展,如“上海市文獻資源共建共享協作網”“北京高校網絡圖書館”“天津市高校數字化圖書館”“廣東網絡圖書館”“蘇州高校數字服務平臺”等,這些區域性圖書館聯盟對促進本區域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其次,以某一文獻資源種類為建設重點的專業性共享體系也日漸成熟,如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文獻中心(China AcademicSocialSciencesand Humanities Library,簡稱CASHL),重點建設全國性的人文社會科學外文期刊保障體系。國家科技圖書文獻中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igital Library,簡稱NSTL)提供科技類文獻信息共享等。最后,全國范圍的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China Academic Library&Information System,以下簡稱CALIS),自1998年開始建設以來,經過三期項目建設,也初步建成了覆蓋全國各類高校圖書館的共享網絡。CALIS可以為全國近2000所高校成員管提供標準化、低成本、自適應、可擴展的數字圖書館統一服務和集成平臺,構成全國高校數字圖書館三級共建和共享服務以及多館服務協作的聯合體系,共同為全國用戶提供全方位的文獻服務、咨詢服務和個性化服務[6]。CALIS整合的資源包括4.5萬種期刊的8074萬篇論文目次、678萬種中文圖書、240萬篇中文學術論文、63萬冊(件)中文古籍、300余萬冊(件、篇)特色資源等[5],是目前國內最大的圖文信息資源保障體系。
當前,我國檔案信息資源區域性共享的實踐項目也在多地開展,如上海市浦東新區檔案區域協同分級管理服務系統建設和廣東省區域性檔案目錄中心建設,在區域性檔案信息資源管理與利用方面獲得了較好的效果。其次,在歷史檔案資料專業領域,自1992年起,我國已經逐步建立起全國性的明清、民國、革命歷史檔案資料目錄中心,明清檔案資料目錄中心采集全宗目錄677條,建立了全宗目錄數據庫,出版了《明清檔案通覽》;民國檔案資料目錄中心采集全宗目錄14522條,全國民國檔案全宗目錄數據庫已投入使用;革命歷史檔案資料目錄中心采集全宗目錄2600條,將原來的全宗級目錄、案卷級目錄、文件級目錄分三步采集變成全宗級目錄采集完成[3]。最后,我國檔案事業的“十五”和“十一五”規劃中均明確提出了“共建共享、互聯互通”,在全國范圍建設檔案信息資源網絡共享的目標。如現實推進中的“國家數字檔案建設與服務工程”(簡稱“金檔工程”)將以3127個國家綜合檔案館為建設對象,以分布式檔案數據庫建設為核心,建設涵蓋全部館藏的全國性、超大型、分布式、規范化、可共享的檔案目錄數據庫、紙質檔案全文數據庫和多媒體檔案數據庫,建立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的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7]。
3 建設組織比較
本文以討論全國范圍的資源保障平臺建設情況為主,從兩者的建設現狀上看,圖文體系的CALIS即中國高等教育文獻保障系統在建設的時間、廣度、深度上都更為成熟,這與其職責清晰又積極靈活的組織體系分不開。
3.1相同點分析
與美國的OCLC等資源體系建設采用董事會和市場化運作的方式不同,我國圖書館事業和檔案事業都實行集中統一式的管理體制,在國家統一安排下,由最高行政管理機構統一領導,實行國家統一調撥經費。CALIS體系是由北京大學牽頭,由教育部批準立項、提供經費扶持并納入“211工程”頂層設計的項目,受全國教育系統最高行政管理機構即教育部的統一領導和部署。
我國檔案體系建設的組織體系則更為嚴密和復雜,包括參與網絡共享的各級各類國家綜合檔案館、專門檔案館、部門檔案館,各種性質的機關、企事業單位檔案室或檔案館,其他性質的檔案、資料保管機構等。它們嵌入在我國嚴密的黨政管理等級體系中,按照“以條為主,以塊為輔,條塊結合”的組織架構,管控著我國地方和行業的檔案管理事務[8]。有學者認為,這種集中式的行政隸屬關系喪失了檔案體系建設積極的內在動力[3]。另有學者認為,這是通過行政力量對一個國家、地區或系統的文獻信息資源作出預先的合理安排[9]。
3.2不同點分析
盡管圖文體系同樣受制于集中統一式的管理體制,但其通過國家立項,建設主體比較明確。在組織體系上,CALIS搭建了全國中心—地區中心—省中心的三級服務體系。北京大學圖書館作為責任單位,組建CALIS項目管理中心,和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南京大學、武漢大學以及其他“211工程”重點院校圖書館一起作為全國中心,是服務體系中的第一層。CALIS建設初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北京大學CALIS項目管理中心的全面部署和協調下,充分整合全國中心的資源,建設聯合目錄數據庫并開放聯機合作編目,為之后開展二期和三期項目奠定了基礎。而反觀檔案體系則存在建設主體不明,各自為政的現象,建設至今并沒有形成有效的保障體系。
3.3借鑒與研究
(1)以項目為支撐,明晰建設主體
借鑒圖文體系的建設經驗,首先應該明晰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建設的主體。理論界有學者認為,可以由國家檔案局牽頭,通過國家立項,開展由各地檔案部門(主要是各級綜合檔案館、專業檔案館以及部分企業檔案機構)參與的國家規模檔案資源整合與共享工程[10]。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將建設主體冠名為“全國檔案信息共享網絡管理委員會”,將其常設機構并入國家檔案共享網絡運行中心,成立兼具行政功能和網絡管理功能的“國家檔案共享網絡管理運行中心”[8]。
(2)分級、分層、分期實施建設
建立分級分層的檔案體系框架,以項目推動分期實現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建設。筆者認為,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的初期建設應該建立在省市級以上的框架范圍,對于市級以下基層檔案館的部署可以等到體系較為成熟后再作為成員館加入。因為基層檔案中心多為本地化資源,并不是共享體系資源的主要建設者,其作用主要是利用共享體系資源為本地用戶提供服務。項目初期不納入基層檔案館,可以降低組建體系的難度和成本,集中力量辦好標準化規范、實施方案、資源建設、技術路線等重大的核心問題。
(3)強調協同發展
比照國內外共享體系建設的成功經驗,結合中國國情,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建設的組織不能完全依賴行政力量,也不能完全采用市場經濟模式,而是應該將兩者有機結合。總的來說,發揮行政力量的積極因素,全國一盤棋,以充足的財政資金保證完成各階段的分期建設目標。同時,強調實現資源共享的共同愿景,加強彼此協同發展的合作關系,并堅持互利互惠的原則。充分考慮檔案網絡建設者與承建者之間、檔案機構與機構之間、機構與用戶之間的利益關系,考慮健全檔案網絡共享的利益制度,協調利益關系,從宏觀上規定各方面利益分配的基本框架,使利益分配保持合理穩定的格局,保證檔案網絡共享的可持續發展[7]。
4 建設標準比較
圖文體系大多建立在聯機合作編目的基礎上,執行統一的格式、統一的標準和共同的信息交換協議,以CALIS為例,項目在操作上依托CERNET,遵循Z39.50協議,館際互借協議和MARC格式的編目標準協議[11]。其中,機讀格式MARC(Machine Readable Catalogue)是圖書情報領域廣泛應用的標準格式,建立在MARC標準上的聯機合作編目不僅可以實現數據的可共享性和長久有效性,還能保證數據庫內同種文獻只保留一條書目記錄,減少體系整合時的重復建設。
相比而言,長期以來我國檔案資源的元數據標準不統一,各專業或專門檔案的元數據都有各自不同的元數據標準,如《文書類電子文件元數據方案》(DA/T46 2009)、《核電電子文件元數據》(EJT1224-2008)、環境保護檔案元數據標準等。筆者認為,不同的元數據標準雖然能細化各行業分工,但不利于全國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的建設,應該參考國際標準,制定既兼容國際規范又適應本土化開發的統一的機讀格式標準。值得注意的是,在2014年底,國家檔案局發布《電子檔案基本術語》(DA/T58-2014),該標準覆蓋了電子文檔—文件—檔案全生命周期,適合文書、科技等各類文件/檔案的資源類型[12],并且遵循ISO國際標準。相信基于該標準,全國貫徹實施對文件級檔案統一著錄格式將為建立全國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破除建設標準層面的障礙。
5 建設技術比較
前文提到云計算技術是未來互聯網應用的趨勢,CALIS三期項目即采用了云服務技術,開發了一套基于SaaS技術的共享版系統。該系統不用各個成員館安裝系統,只部署在省中心或者共享域中心,以免費租用的方式提供給多個圖書館或機構共同使用,降低了成員館部署和管理系統的技術成本和難度,大大提高了各省院校的參與度。截至目前,CALIS三期的成員館數量飛速增長,已達到1000多家,覆蓋了全國31個省份。而從用戶的角度來說,云服務能夠提供基于統一認證的一站式服務,使用戶能在各個CALIS云服務中心和圖書館本地平臺之間實現跨域的單點登錄和身份認證[6]。
檔案體系建設中,信息安全是首要考慮因素,理論界有學者撰文探討云計算技術在檔案體系的安全性問題,認為“云技術能夠滿足檔案信息資源的特殊安全要求”[1],且縱觀云計算技術已經在金融、網絡安全等對數據安全有極高要求的領域取得廣泛應用。
筆者認為,云計算技術能應對檔案體系建設中的諸多難點。首先,統一認證難題。統一認證是實現服務整合的前提,運用云技術能夠提供統一接口的安全調用和身份認證功能,確保本地用戶通過安全訪問被托管的受控的API服務。其次,服務整合難題。云技術以服務方式按需(免費或租用)提供給用戶,能夠提供通用的注冊、授權、計費和安全等管理服務,簡化服務集成,支持服務的調度、接入和交付。最后,安全備份難題。云計算技術通過“虛擬資源池”可以打破傳統檔案館之間的“信息壁壘”,實現另一種形式的“異地備份”,有效保證數字檔案資源的信息安全[13]。
6 總結與啟示
上述總結了圖文體系和檔案體系在建設背景、建設現狀、建設組織、建設標準和建設技術上的相同點與不同點,但實踐中檔案信息資源共享體系建設還面臨著大量的問題,其中最核心的還是理念鴻溝和協作障礙。人們往往首先看到有形的共享技術設施條件,然而相比人際協作因素,它的重要性和難度要低得多[14]。
6.1更新理念,注重協作
結合國內外圖文體系如OCLC、CALIS發展的歷程,我們發現資源共享的理念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協作精神,在這種精神的指導下,資源共享內化積淀成為組織文化。檔案部門雖在理論上認識到資源共享的重要性,但協作意識缺乏,傳統觀念和思維方式仍然存在,“條塊分割”的弊端尚未消除,“重藏輕用”的思想依然作祟;往往寄期望于檔案信息資源共享,而不是主動參與[3]。實現資源共享是全體檔案從業者的共同愿景,需要全體檔案從業者竭誠合作,共同努力。
6.2加強溝通,提升服務
體系建設的最終目標是提供用戶更便捷的服務和更廣泛的利用,提升檔案信息服務水平。圖文體系在成功建構CALIS、CASHL等文獻保障平臺之上充分利用QQ等即時通訊工具搭建館員交流平臺、借助發達暢通的物流業務實現圖書文獻資源的全國范圍內的文獻傳遞和館際互借,滿足用戶多方位的文獻需求。在當前政府信息公開化的背景下,全國檔案資源共享體系建成后可以開放現行文件直接提供用戶原文下載,從而更大程度實現資源的共享。
6.3抓大放小,分期實現
盡快推動檔案信息共享體系的初期建設,以項目為支撐,如通過國家立項設立重大歷史檔案資料的共享項目,建立省市級以上的框架范圍,利用云技術搭建系統平臺,實現檔案全文資源提供方與利用方之間的協調、調度、接入和交付任務,解決認證、注冊、授權、計費和安全等核心問題,簡化服務集成,為之后分期推動共享體系建設奠定基礎。
*本文系蘇州科技學院科研基金項目“用戶視角下的圖書館學習共享空間研究”(XKQ201404)成果之一。
[1]彭小芹,程結晶.云計算環境中數字檔案館服務與管理初探[J].檔案學研究,2010(6):71-75.
[2]呂元智.國家檔案信息資源“云”共享服務模式研究[J].檔案學研究,2011(4):61-64.
[3]黃廣琴.OCLC對構建區域性檔案目錄中心的啟示[J].檔案與建設,2011(5):13-16.
[4]胡杰,張照余.檔案信息與圖情資源網絡共享的比較研究[J].檔案管理,2009(1):10-12.
[5]李曉明.文獻資源共建共享與CALIS[Z].“我與CALIS”征文獲獎作品集,2013:1-3.
[6]王文清,陳凌.CALIS數字圖書館云服務平臺模型[J].大學圖書館學報,2009(04):13-18.
[7]張照余.構建檔案共享網絡的效益與利益機制研究[J].檔案學研究,2011(03):54-58.
[8]張照余.基于VPN的全國檔案信息共享網絡的組織體系研究[J].檔案與建設,2009(12):4-7.
[9]馬費成,裴雷.我國信息資源共享實踐及理論研究進展[J].情報學報,2005(6):10-15.
[10]何振,蔣冠.國家檔案資源整合與共享工程建設構想[J].檔案學研究,2005(4):32-36.
[11]謝琴芳,白新萍.書目資源的共建、共知和共享——CALIS聯合目錄數據庫建設思路[J].大學圖書館學報,1999(2):7-9.
[12]黃玉明.文件/檔案及相關資源元數據再研究——國際源流與中國體系構建[J].檔案學研究,2010(06):59-65.
[13]程結晶.云技術中數字檔案資源共享與管理體系的構建[J].檔案學研究,2013(1):38-41.
[14]羅志勇.知識共享機制研究[M].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胡杰,女,蘇州科技大學圖書館館員,主要研究方向為圖情檔一體化建設。
張照余,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檔案信息化和電子文件管理。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tuation between Archives and Libraries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Hu Jie1,Zhang zhaoyu2
(1.Library of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Suzhou,Jiangsu,215009;
2.School of Society of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Jiangsu,215000)
This article make a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archive and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summarized both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n background,the present situation,the organization,the standard and technology etc,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construction of archive information system from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
Archives;Libraries;Sharing System;Comparative Studies ?
G2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