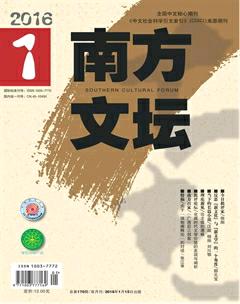關(guān)于“強制闡釋論”的對話
一、強制闡釋現(xiàn)象普遍存在
張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把理論的國門打開,大量地學習、借鑒、翻譯當代的西方文藝理論,及西方各種理論,這對中國的改革和發(fā)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這一點沒有人否認。我們還要用更寬廣的視野、更謙遜的態(tài)度去學習、去借鑒、去傳播當代西方世界各種各樣有利于我們民族進步和發(fā)展的先進理論。但是,三十多年的實踐讓我們深刻地體會到,在對西方當代文學理論學習、傳播、借鑒的過程中,西方文藝理論本身的缺陷沒有引起中國學者的足夠重視。換一個角度講,當代西方文學理論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民族化問題沒有得到很好解決。許多中國學者生吞活剝地把當代西方文藝理論搬到中國來,用西方理論強制地闡釋中國的經(jīng)驗和中國的實踐。事實是,用西方理論來建構(gòu)自己本民族的文學理論時,我們會遇到很多障礙和困難,所以,我們希望能從闡釋學的角度出發(fā)講一講強制闡釋的弊端。
我認為,從闡釋學的意義上說,西方文論的強制闡釋背離了文本話語,消解了文學指征,以前置的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做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jié)論的闡釋。“背離文本話語”是指闡釋者對文本的闡釋離開了文本本身,對文本做了文本以外的話語發(fā)揮。文本只是闡釋的一個借口,一個角度,是闡釋者闡釋其理論、觀點、立場的一個工具。“消解文學指征”是指闡釋者對文本和文學做了一種非文學的闡釋,這些闡釋可能是哲學的、歷史的、社會學的,以及那些實際上并不包含文學內(nèi)容的諸多文化闡釋。文學理論偏離了文學,實質(zhì)上是政治理論、歷史理論、社會理論。“前置立場”是指強制闡釋的立場是事先預(yù)定的,批評者的站位、姿態(tài)已經(jīng)預(yù)先設(shè)定,批評的目的不是要闡釋文學和文本,而是要表達和證明批評者自己的立場,而且常常是非文學的立場。“前置模式”是指批評者預(yù)先選用確定的模板和式樣框定、沖壓文本,其目的是作出符合論者目的的批評和理論上的指認。經(jīng)過這種前置模式壓迫所產(chǎn)生的所謂文學理論的闡釋,實際上經(jīng)常是一種數(shù)學、物理的闡釋,而非文學的闡釋。符號學的各種各樣辦法就可歸于此列。“前置結(jié)論”是指批評的最終判斷和結(jié)論不是在對文本的實際分析和邏輯推演之后而產(chǎn)生,而是在批評之前已經(jīng)確定。批評者的批評不是為了分析文本,而是為了證明結(jié)論。
“強制闡釋論”中還涉及更廣闊理論空間的一些概念,涉及闡釋學近百年來很多很尖銳的、沒有結(jié)論的原點問題,這都需要我本人繼續(xù)努力探索。
阿納斯塔西婭·巴什卡托娃(俄羅斯文學批評家、《獨立報》經(jīng)濟部副主任):張江先生提到的“強制闡釋”的問題,不僅存在于西方文論中,同樣也存在于當下的俄羅斯文學批評中。而且,各種強制闡釋的手段,比如說濫用“場外理論”、前置立場、預(yù)設(shè)觀點、論證的非邏輯化等,在當下的俄羅斯文學批評中都不鮮見。
娜塔莉婭·科爾尼延科(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在俄羅斯文學中一直存在著一個傳統(tǒng)的對抗,即文學與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對抗,作家與批評家的對抗。實際上,這個沖突在19世紀就已經(jīng)有了。“任何一個理論,不管是什么樣的理論,都有其正面的部分,但是,它也有其反面部分,它的不正確的部分很容易就被看出來,理論是意義的限制,這個時候便會出現(xiàn)生活對理論的反抗。”這段話引自阿波羅·格里高利耶夫19世紀60年代寫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題目就比較適合于我們今天的研討會,他的題目是《論當代藝術(shù)批評的基礎(chǔ)、意義和手法》。
事實上,我看到一個令人擔憂的情況:現(xiàn)在有更多學者喜歡強制闡釋。這會讓讀者越來越不了解這個作家、作家的作品、作家的生活細節(jié),對那個時代的知識知道得越來越少,所以這個趨勢是很危險的。在20世紀出現(xiàn)了一些研究,理論壓倒了生活,理論壓倒了具體的文本。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全球化的一個產(chǎn)物,因為全球化要消滅國界,要消滅各個文化之間的區(qū)別。
我們有些研究蘇聯(lián)文學的人,最近幾十年來不斷尋找新方法來闡釋蘇聯(lián)文學,這個潮流令人擔憂。因為我們那些蘇聯(lián)作家,在被這些新的方法分析之后,在通過精神病學的心理分析之后,他們就變得完全不一樣了,失去了他們原來的優(yōu)長。實際上,這些文論家只是想利用蘇聯(lián)文學,他們通過時空理論、復(fù)調(diào)理論、莫斯科藝術(shù)理論、西伯利亞藝術(shù)理論這些新詞兒揚名立萬,但是他們實際上對文論的貢獻十分有限。任何一個文學理論,都要從文學的實踐出發(fā)。
瓦列里婭·普斯托瓦婭(《十月》雜志批評部主任):俄羅斯有不少批評家學習西方文論,很多人把文學分析變成了文學政治,張江先生對此做了很好的描述。這是一種“強制闡釋”,是文學理論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一種后果。與此同時還有另一種趨勢,即夸大文學批評的聲音,認為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其實沒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這些批評近似小圈子批評,多出現(xiàn)在網(wǎng)上論壇,在最好的情形下近似于政論文章,就整體而言,批評的語文學基礎(chǔ)和專業(yè)化基礎(chǔ)十分薄弱。結(jié)果也出現(xiàn)了一種“強制闡釋”,它源自對于文學的庸俗讀物式的理解,把文學批評當成了一種娛樂讀者的工具,批評在這種情況下要解決的任務(wù)不是文學分析,而是新聞、公關(guān)、溝通的任務(wù)。
瑪麗婭·納德雅爾內(nèi)赫(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實際上,當今拉美文論界的一些做法,也可以用“強制闡釋”這個概念去定義。有一位德國學者認為,拉美文論中出現(xiàn)的一些新概念都不是什么新概念,都是在用新的概念偷換過去的概念,比如,所謂“混合性”和“異質(zhì)性”就是合成,“文化地理學”就是“文化史學”等。很多文論專家很少利用文本本身,他們的很多著作并不是要對文本本身進行研究和批評,而是要研究上述提到的那些“新概念”。
葉蓮娜·塔霍-戈基(莫斯科洛謝夫之家圖書館館長):談到強制闡釋,人們對洛謝夫的態(tài)度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最近10年,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關(guān)于洛謝夫所受影響的“強制闡釋”。比如有個專家認為,洛謝夫不是弗拉基米爾·索洛維約夫的繼承者,他的觀點與索洛維約夫并不相干,索洛維約夫在俄羅斯文化中的真正繼承人是馬克西姆·高爾基。但我們知道,高爾基和這樣的傳統(tǒng)毫無關(guān)系。此外,我注意到,不只是文學作品,哲學作品也可能變成強制闡釋的對象。endprint
張江:我很贊同您的這個說法。我認為,強制闡釋在中外文學理論,在我們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生活當中,在各種各樣人類認知實踐和物質(zhì)實踐過程當中普遍存在。不認識它,不在闡釋學的譜系當中建立這個概念,是我們這個行當學者的失誤。
二、文學理論不能脫離文學
拉什米·多拉伊絲瓦米(印度德里賈米爾大學教授):張江先生的《強制闡釋論》一文討論了20世紀各種各樣對文學產(chǎn)生過影響的“場外”理論,并考察了場外理論進入文學的途徑和影響。確實有人在使用其他專業(yè)學科的方式來闡釋文學文本,可我認為,通過這樣的闡釋,文學的確獲得了很多東西。比方說,艾亨巴烏姆對果戈理的《外套》的闡釋,什克洛夫斯基對《項狄傳》的闡釋,巴赫金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闡釋,巴特、德里達和福柯對愛倫坡的闡釋,列維·斯特勞斯和德里達對神話的闡釋……這個闡釋和被闡釋對象的名單還可以列得很長,它們對文學而言都是富有成效的。一系列的理論都是相互連接的,一些理論會引起其他理論的共鳴和發(fā)展,比如種族理論、女權(quán)主義、性別研究、媒介研究、怪異行為研究、環(huán)境研究等等,這些新理論也會促進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發(fā)展,法蘭克福學派、本雅明、葛蘭西、阿爾都塞、馬舍雷等對于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派的發(fā)展發(fā)揮了很大作用。
我們可以從巴赫金的對話理論那里學到很多東西。在巴赫金看來,對話就是生命,獨白就是死亡。文學批評現(xiàn)在要轉(zhuǎn)身面對新的理論,得到新的辦法,從新的角度來觀察自己,反省自己。有不同學科的理論加入文學理論,把文學理論豐富起來,無論這有什么負面效應(yīng),還是會對文學提供很大幫助。在我看來,在20世紀的文學理論中,各種場外理論在各個國家四處旅行,起到了豐富文學和文學研究的作用。
瓦基姆·波隆斯基(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副所長):我想談一談學科之間的競爭和矛盾。柏拉圖的著作中已經(jīng)開始了理論批評,他通過對語言、對文學的看法來表達他對哲學的看法。柏拉圖認為,詩人并不扮演闡釋者和解釋者的角色,闡釋和解釋的作用被哲學家壟斷了。哲學和語言學的競爭在西方歷經(jīng)了幾百年,都沒有分出勝負。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語文學界第一次發(fā)起暴動,語言學家反對哲學家對語言的利用,他們認為語言學和文藝學也是獨立的科學。語言學開始擁有越來越多的權(quán)力。西方基督教《圣經(jīng)》的考證和闡釋原本就有一套方法,自18世紀末以來,傳統(tǒng)方法開始演變?yōu)楝F(xiàn)代語言學與文藝學的方法。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哲學家尼采在研究荷馬經(jīng)典語文學時,認為文學批評要回到單純的語文學,放棄所謂的幻想闡釋。他是語文學的革命人物,他認為我們必須發(fā)現(xiàn)藝術(shù)的唯物現(xiàn)象,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假定一個零散的文本內(nèi)容。尼采革命性的想法基于傳統(tǒng),但他也借助了沃爾夫的看法,就是要把語文學從神學中解放出來。他們將這個傳統(tǒng)傳到20世紀,想要建立解釋學和文體學,放棄對意義和現(xiàn)實的比較。在20世紀和21世紀,還有一些文學理論主要是基于帶有哲學味道的文本解釋方法。德里達的解構(gòu)主義、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貢布里希的藝術(shù)史研究方法,都影響到了當代。
語文學和哲學的競爭與合作,現(xiàn)在依然存在。在面對眾多研究方法的情況下,研究的標準卻越來越不清楚、越來越模糊。作為文學批評家,我們到底該怎么做呢?我們沒有百分之百的解決方法,但我有一個建議,可以合成考證的語言學方法和闡釋的哲學方法。研究語言,研究文化背景,研究作家的個人經(jīng)驗,這對一位文藝學家的學術(shù)研究工作來說非常有幫助。研究文本、研究文學,甚至是對語言語法問題的研究,也都很重要,都是重要的研究方法。
張江:理論發(fā)展到今天,最有生命力、最有生長力的是各學科之間的交叉和融合。沒有人否定這一點。我自己也認為,多種學科的交叉和融合是我們理論生長的最有力的動力,最強大的動力。為什么“強制闡釋論”會反對哲學進入文學場內(nèi)呢?我贊成用哲學理論做指導(dǎo)、甚至做工具來闡釋文學,沒有問題;但重要的是,當用哲學理論闡釋文學的時候,一定要把運用的哲學理論文學化。我們闡釋的,我們需要的,是文學的理論,而不是沒有文學的理論。
瓦列里婭·普斯托瓦婭:我完全同意張江先生的看法,我們絕對不能脫離具體文本進行文學分析。然而,在當代俄羅斯的批評領(lǐng)域,越來越少的人在認真對待這些問題。場外的因素越來越多地進入文學世界,對文本感興趣的專家越來越少,將他們吸引到文學革新中的最有效的途徑和技巧,就是要有盡可能多的非文學信息成分。關(guān)于這個悖論,一位英年早逝的俄羅斯批評家亞歷山大·阿蓋耶夫?qū)懙溃骸拔铱梢砸揽亢芎玫恼Z文學實踐能力,對發(fā)表的文本進行詳盡的分析。文本是豐富的,層次多樣的,其中很多可供進行分析的對象,如果我們調(diào)動最精致的全套批評手段。但是,這些評論并不能給作家?guī)沓晒蜆s耀,就像事實所表明的那樣。讀者會把這些評論當作一系列具有內(nèi)在敘述動力的風景,他們會遺憾地、迫不及待地問道:接下來會是什么呢?”
其結(jié)果,真正的文本不再是文學批評的起點。對于當代批評來說,文學不是一個專門建構(gòu)出來的世界,不是文本,而只是一個具有社會影響的、有趣的言論,與新聞和博客一樣在媒體空間出現(xiàn)的文字記錄。盡管這對文論在社會上的影響非常不利,但對于文學家來說,可以提高他們的知名度。
現(xiàn)在好像只有一位批評家在闡釋文學作品時比較關(guān)注作家的創(chuàng)作動機,但她屬于老一輩批評家,她就是曾經(jīng)獲得索爾仁尼琴獎的伊琳娜·羅德尼揚斯卡婭。她在不斷地解讀文學作品,對她認為最重要的文學作品的“本真性”問題十分關(guān)注。她認為,批評家在闡釋的過程中不能脫離文本,文學作品的本真性并不等同于批評家本人的生活和精神體驗。“本真性,就是藝術(shù)家對自我真實的信仰,這種信仰要擺脫各種外在壓力,比如商業(yè)的、功利的、社會的、甚至宗教的壓力。”
艾倫·梅拉(莫斯科法蘭西學院院長):我結(jié)合法國文藝學的趨勢談?wù)剬鐾庹饔眠@個問題的看法。文論方面的交叉研究是法國文論界當前熱烈討論的一個話題,文論可以跟人類學、民族學、社會學、歷史學相互結(jié)合,甚至還可以有文學和地理學、文學和視覺藝術(shù)、文學和電影的混合。總之,法國文藝學在試圖謀求一種綜合,把各種不同的方法融合在一起。像結(jié)構(gòu)主義,就把文學、歷史、社會學、語言學的方法都糅合在一起,這些不同的方法是互相影響、互相結(jié)合的。可以說,現(xiàn)在的文藝學正處于一個多元、綜合和融合的時代。endprint
要強調(diào)的是,與此同時,現(xiàn)在的法國學者們又意識到了文本的作用,他們已經(jīng)把文本作為分析的重點。他們對文本的分析,首先要研究文本為何會出現(xiàn),出現(xiàn)的背景是什么,而且作家的角色也受到了關(guān)注。例如,結(jié)構(gòu)主義和敘事學的繼承者熱奈特,更加注重文本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一種具有多重意義的工具;福柯繼承者、社會學批評的代表威廉·馬克思研究最近兩百年中作家的角色、作家的生活方式及一些文學制度;遺傳學批評主要對某些作品的手稿進行研究,研究手稿的演變過程等。
總之,文學和文藝學就像一個活的肌體,它需要新的血液補充,不同學科的元素就像是有益的細胞,可以為這個肌體不斷提供新的養(yǎng)料,促進這個肌體的新陳代謝。如果哲學、人類學能為文藝學提供出更多更好的東西,那么就請吧,這是好事,但是有一個前提,就是文藝學不能脫離文學文本。
三、強制闡釋并非過度詮釋
阿納斯塔西婭·德·里亞·福爾特(瑞士洛桑大學教授):張江教授在文章中提及很多很重要的問題,比如,文學理論是不是與生活實踐有關(guān)聯(lián),概念的借用、其他學科的方法在文論里的使用等等,這些問題都很重要,對文論的進一步發(fā)展有建設(shè)性意義。
我認為,張江教授的文章核心的問題是文本和闡釋。什么是闡釋?誰有權(quán)力闡釋?這是西方文論學家?guī)装倌陙硪恢痹跔幷摰膯栴}。任何一個闡釋都必須放在一個歷史語境中,否則,過度詮釋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西方文論中,過度詮釋的現(xiàn)象很早就有。
可以用新的標準來闡釋舊的文本,在文本里面發(fā)現(xiàn)一些秘密的內(nèi)涵,但是不能完全脫離文本,在這方面我同意張江教授的觀點。但是,今天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遇到了更大的挑戰(zhàn),伽達默爾就認為,文本也可能是一個偽造的形式。德國的一些解釋學家也在證明,文本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弄明白作者究竟在寫什么。所以,任何一個闡釋都是過度詮釋。海德格爾認為,任何一個闡釋都是帶有偏見的闡釋。在這里,很難恢復(fù)和還原作家的構(gòu)想,比如找出一個辨別真?zhèn)蔚臉藴剩瑏砼袛噙@是不是符合莎士比亞的構(gòu)思,猜一猜莎士比亞自己是否在有意識地描述女性問題。判斷真?zhèn)蔚臉藴适鞘裁矗恳謴?fù)、還原作家的構(gòu)想,這不是一個好方法。艾柯建議要把闡釋和使用文本分開處理,關(guān)于怎樣避免過度詮釋,他也提出了一些建議。
張江:您的這個報告,我覺得核心問題就是,“強制闡釋”和艾柯先生的“過度詮釋”到底有什么區(qū)別。我的想法是,不能從一個文本的闡釋結(jié)果去區(qū)別過度與強制,要從闡釋的路線去區(qū)別過度與強制。過度詮釋的出發(fā)點是從文本出發(fā)的,在文本中找到闡釋的各個關(guān)節(jié)點,抓住這些關(guān)節(jié)點,做了超出文本本身內(nèi)容的和作者本身意圖的闡釋。而強制闡釋是,從我自己的理論出發(fā),從我的政治意圖出發(fā),然后對文本做文本基本沒有、或者說從來就沒有的意圖的強制闡釋,其目的不是要闡釋這個文本,而是要證明我自己的理論立場,從闡釋路線說,這個路線是非常清楚的。
四、尊重文本是批評倫理的基本規(guī)則
葉夫蓋尼·葉爾莫林(俄羅斯批評家、《大陸》雜志副主編):“強制闡釋”是一個非常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問題。作家和批評家的對話、批評家和讀者的對話,應(yīng)該有一個正當?shù)摹⒄5臉藴屎鸵?guī)則,可是這個規(guī)則往往也不是很正常的,兩者之間沒有和諧的關(guān)系。在社會上,作家和讀者對批評家的認識程度并不是很高,認為批評家的工作并不是必不可少的,認為批評家的工作好像是烏托邦的工作。在變化了的現(xiàn)實條件下,批評家的工作到底會不會繼續(xù)具有價值?我對批評家的工作非常有興趣,可是我也往往感到疑惑,不知道批評家的目的到底什么?
阿納斯塔西婭·巴什卡托娃:當下的俄羅斯文學批評處于一種十分獨特的狀態(tài)之中,它既在自我否定、又在自我確立,在尋找新的理想模式。一些文學批評家說出了這樣的話:“作為一個文學種類的批評已經(jīng)停產(chǎn)”,“寫作批評文章是一項費力不討好的、沒有必要的文學勞作”,“我們尚在,我們的時代卻已不存在。”文學批評家的確有時甚至不知道他們是為誰而寫作、為什么要寫作的。面對文學批評的困境,實踐者和理論家們也試圖提出一些理想的批評模式,但各文學批評流派意見不一,關(guān)于理想模式的探討甚至會使它們紛爭更烈。
第一個模式是把批評家當作財產(chǎn)分類員和系統(tǒng)分類員。這一模式要求作為分類學家的批評家必須對每一個文學現(xiàn)象、每一部作品,甚至是每一個外國文學現(xiàn)象、每一部外國文學作品作出分析和解釋。這一類批評家心知肚明:他的個人趣味遠非樣板,存在著許許多多趣味各異的讀者。不過,這樣的批評家可能想不到,他關(guān)于其他讀者之趣味的報告有可能是前見的,與事實相去甚遠。
第二個模式是把批評家當作神話創(chuàng)造者。這種模式假設(shè),批評家在深入進文學之后,就可以本能感覺到藝術(shù)中的崇高意義,看到新文化的前兆。這位神話創(chuàng)造者在尋求關(guān)于世界的新話語,希望這新話語能像神的喜訊一樣被傳遞給作家、讀者和這位批評家本人。這樣的批評家可以步出族群的、體裁的、風格的界限,摧毀文學批評界的舊藩籬,因為對于他來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描繪他本人的世界圖景,構(gòu)建他自己的文學神話,即便是烏托邦的文學神話。
第三個模式是把批評家當作文學政論家,他首先要考慮的是文學作品的社會和政治層面,是作品的意識形態(tài)內(nèi)容。對于這樣的批評家而言,作品本身如何并不重要,作品只是他用來對當代現(xiàn)實進行社會和政治分析的借口。而且,這一類批評家往往不會滿足于這樣或那樣的分析,他或早或晚會試圖離開文本走向?qū)嵏桑簿褪侵苯又亟ㄉ睢_@個時候,他在讀者面前的形象與其說說一位文學批評家,不如說是一位政治宣傳家。
第四個模式是把批評家當作解構(gòu)者。這是一種非傳統(tǒng)的批評模式,它與19世紀和蘇聯(lián)時期的文學批評模式恰好相反。解構(gòu)者要擺脫文學中心主義,因為他認為除文學之外還有很多其他思想范疇,有些可能比文學更有成效。這類批評家會擺脫先前加在他身上的那種傳教士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不愿再做啟蒙者,不愿再做作家和讀者的中間人。解構(gòu)批評家把一本書拿在手里,他要問的問題不是:“這是什么?我關(guān)于這本書能說出些什么?”而是:“這東西為何如今會出現(xiàn)在這里?”他在為文學在當今的出現(xiàn)尋找哲學的、社會學的、本體論的、語文學的理由,他不解釋作品,而只試圖去弄清作品為何出現(xiàn),其原因、包括非文學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此類言說的主要受眾不是普通讀者,而是專家和其他批評家。endprint
第五個模式是將批評家當作作秀的主持人。為了持續(xù)吸引住公眾,他有時不惜搞怪,對所分析的作品做出一些非同尋常的、異想天開的、夸大其詞的主觀闡釋,他可以不顧被分析的文本,任意發(fā)揮,不惜犯規(guī),甚至覺得制造轟動性的丑聞就是吸引眼球的最好手段。這類批評家并不反對尋求被分析作品的意義,但他常常覺得他找到的意義會與別人找到的有所不同,他在文學批評活動中也在從事一些非文學活動,比如自我推銷、自我形象塑造、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文學。
第六個模式是讓批評家成為文本崇拜者。這類批評家似乎最接近文本,因為這類批評家必須拋棄私欲,遠離自己的文學趣味、小集團的利益、文學等級觀念和教育意義,他感興趣的甚至不是作品的作者,甚至不是作品本身,而是純粹的文本。作為文本崇拜者的批評家應(yīng)該理性地判斷文本的優(yōu)劣,剖析文本,探究其深意。文學批評在這種模式中就好像是圣經(jīng)詮釋學。這種貌似公允的批評有時也會有危險,因為批評家可能會在文本中“發(fā)現(xiàn)”文本中原本不具有的“深層”含義。
這里提到的每一個理想的批評模式都包含著一些可以爭論的方面,但其中也的確包含著一些關(guān)于如何完善文學批評事業(yè)的寶貴建議。就這一意義而言,我們可以同意張江先生的意見,即文學理論應(yīng)該是系統(tǒng)發(fā)育的,它應(yīng)該形成一套完整的文學觀,提出一套研究文學作品和文學過程的系統(tǒng)方法,克服在闡釋文學文本時的各種矛盾、偏見和片面。不過,這樣一種系統(tǒng)發(fā)育的學科之建立目前看來還是一個烏托邦,在生活中落實這一烏托邦還具有很大風險,我們對此必須做好準備。
列夫·安年斯基(俄羅斯文藝學家、文學批評家):我認為,閱讀有三個層面:第一個語境是文本,第二個是社會政治語境,第三個是超任務(wù)語境。第一層面意思就是,應(yīng)該意識到我在讀什么,我要理解作者想要說什么,作者不想說什么。在文本分析過程中,這些因素都要考慮到。第二層面是政治層面,因為我們要評價一個文本,要闡釋一個文本,就離不開具體的社會和政治語境。第三層面,最讓我關(guān)心的層面,它需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我們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事?”這其中包括我寫的和我沒有寫到的,還有我自己都不理解的。我們的社會要往哪里走?這是最重要的問題。“我們究竟發(fā)生了什么?”這是我們的著名作家瓦西里·舒克申提出的一個公式。這個問題是與一切相關(guān)的,與民族和國家,與外部世界和我們的命運,全都息息相關(guān),因此是一個“超級任務(wù)”。所以,怎么評價某一個文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經(jīng)歷過什么,在我們身上發(fā)生了什么,我們的未來是什么,命運會把我們引向何處?
羅伯特·霍德爾(德國漢堡大學斯拉夫研究所教授):文學與其說是在言說生活,不如說是在模仿生活,這個“模仿”就是古希臘人所說的“模仿”。這一情況決定了文藝學和自然科學的巨大差別。如果說在對對象進行自然科學的分析時,在得出一個準確的、完全客觀的表述之前,該對象往往會被分解成若干組成部分來逐一分析,那么,文藝學的分析對象在很大程度上卻總是不可分解的,在心理和社會意義上都是如此。這就是為什么,文藝學旨在創(chuàng)建一套精確術(shù)語的種種嘗試,最終往往都會以失敗告終。
這類嘗試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把一個單獨的文本看作是一個溝通行為,需要重構(gòu)這一行為的歷史語境。但在這種情況下,作品人物要成為文藝學言說的一部分,這就意味著,此類言說所針對的范圍僅僅局限于具體的文學文本。第二,以對某些具體文本的分析為基礎(chǔ)來構(gòu)建一種普遍的文學理論。可是由此會產(chǎn)生一個新問題,即這種理論試圖把握的文本越多,其危險性就越大,這種理論就會變得過于普遍,過于泛化,難以再用來解釋某一具體文本的特性。在這種情況下,“文學文本”的概念所要揭示的東西就像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家族相似”,女兒的鼻子像母親,眼睛像父親,下巴像奶奶,兒子的牙齒像父親,眼睛像母親,發(fā)色和姐姐很像,他們有共同的相似處,但還是弄不清楚,使他們大家都相似的東西到底是什么。這就像是一根線,其中卻并沒有一道貫穿始終的纖維。第三,從其他學科借用術(shù)語,這些學科往往被視為“精確科學”或“社會等價物”。張江先生把這些理論稱為“場外理論”,他使用這一概念是為了強調(diào)此類借用的任性特征,此類借用過于勉強,常常會造成強制闡釋。在實踐中,這些借用來的術(shù)語在文藝學中常常被用作隱喻,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不過是對“精確”和“等值”理念的褻瀆。
文藝學的政治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歸入上面所說的第三種嘗試。它認為在文本之前和文本之外存在著某種真理,文學文本在這種情況下僅僅是為證明這個真理而服務(wù)的,也就是說,對不同文本的選擇和闡釋是用相應(yīng)的“強制”手法進行的。文藝學的政治化在激進的政治大變動時期會表現(xiàn)得尤其突出。同一個文本在不同的話語環(huán)境中往往會獲得迥然不同的闡釋和評價。文學和文藝學,有關(guān)文學經(jīng)典的概念,從一開始就存在于某一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博弈場中。一位文藝學家在研究任何一部文學文本的時候,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參與意識形態(tài)斗爭。但是,這是否是一種激進的相對論,即認為客觀的文藝學評價就總體而言是不存在的呢?當然不是。任何一種文藝學闡釋都還是包含有道德元素,可以將其稱之為研究者的“良心”。在面對外語文本時,這種“良心”還要求研究者能夠很好地理解外國的語言和文化。我認為,張江先生呼吁人們保持對于文本的經(jīng)典態(tài)度,這同樣也是在呼吁人們保持對于外語文學的高水平的專業(yè)學識。
普斯托瓦婭:關(guān)于文藝學的政治化問題,我舉一個例子。有一個叫伊戈爾·古林的年輕批評家,他獲得了著名的安德烈·別雷獎,因為他把文學分析的元素,首先是對詩學過程的分析,引入了報紙文章。在報紙和網(wǎng)絡(luò)中充斥著大量低俗評論的當下,他的所作所為構(gòu)成一個例外。但是,這位批評家的文藝學態(tài)度并非總能保持他的學術(shù)客觀性。讓我感到吃驚的是,當他對年輕的女作家克謝尼婭·布克莎的小說《“自由”工廠》進行分析時做出了激烈的政治化批評,這是不公道的。這部小說描寫首都一家兵工廠的命運,通過曾在該廠工作過的諸多人物的聲音和命運來表現(xiàn)主題。伊戈爾·古林認為,這部小說是在復(fù)興蘇聯(lián)時期的生產(chǎn)題材小說,可他卻忽視了,這部小說采用了一種創(chuàng)新的詩學手段,女作家其實表現(xiàn)出了一種全新的、非蘇維埃式的生產(chǎn)文學敘述方式。批評家指責作家在小說中進行“主人公與工廠的歇斯底里的超身份認同”。在我看來,這就是張江先生指出的“強制闡釋”的一個案例,把文學分析當成了社會爭論和政治爭論的手段。endprint
張江:我對您的這句話非常感興趣。一個批評家對一個作家的作品,對一個文本的批評,“不公道”是什么意思?有“公道”嗎?“公道”和“不公道”的區(qū)別、標準是什么?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批評倫理問題。從倫理學的意義上對批評和批評家提出要求,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藝理論發(fā)展的方向。您可以再解釋一下嗎?
普斯托瓦婭:您問得很好,公道是什么?古林把一些政治的因素、社會的因素加入對小說的闡釋中,他其實是在脫離歷史語境看待這部小說,他的闡釋就是完全不公道的。批評家必須把小說看成一個整體,要理解這個作家的原意,而不是僅以批評家的情緒來對待作家及其作品。
張江:我非常贊成您的這個觀點。我想引申一下您的話,如果說,批評家用自己的政治意圖強加于文本,那么他的這個批評就是不公道的。按照我的想法,這種強加就是一種強制闡釋。按此邏輯推演,是否可以說,批評家對文本的強制闡釋行為就是一種不公道的行為?
普斯托瓦婭:是的。
張江:我正在琢磨一件事,就是批評的倫理。我認為,公正闡釋的基點是承認文本的本來意義,承認作者的意圖賦予文本以意義,嚴肅的文學批評有義務(wù)闡釋這個意義,告訴讀者此文本的真實面貌。在此基礎(chǔ)上,才有對文本的多元理解和闡釋,才能夠?qū)ξ谋咀龀龈侠砀羁痰慕馕龊团袛啵瑢崿F(xiàn)對文本歷史的、當下的發(fā)揮和使用。尊重文本,尊重作者,在平等對話中校正批評,是文學批評的基本規(guī)則,是批評倫理的基本規(guī)則。
五、東西方應(yīng)攜手探索文藝學新路
伊琳娜·巴爾梅托娃(俄羅斯《十月》雜志主編):今天在場者并不是都是強制闡釋的受害者,有些還可能就是強制闡釋的始作俑者,因此我們可能有批評、有抱怨、有吵架。重要的是,我們要嘗試找出一種辦法,以便步出這一狀態(tài)。令我感到十分高興的是,一年前,在莫斯科,張江先生給我介紹了他的這篇文章,然后又把這篇文章寄給了我們,供《十月》雜志發(fā)表。我想,這是我們合作的開始,我們要一起探討步出文藝學困境的新路線,不僅僅是在文論方面,同樣也包括文學批評。我們要做一個橋梁,我們要把中國的聲音傳遞到西方。
在俄羅斯有一個大問題,很少有高水平的中俄文翻譯專家,特別是可以翻譯文學作品的專家。我們俄羅斯和中國都要注重培養(yǎng)一批相關(guān)專家,讓更多年輕人把文學作品從中文翻譯成俄文,從俄文翻譯成中文。今天的討論我覺得遺憾的是,我們很少提到中國文學作品,這并不是因為中國朋友們不愿講,而是因為我們不懂,我們講不出來,所以他們也就非常謙虛地很少提及,所以這是我們的一個很大缺陷。我覺得我們以后要慢慢地彌補這樣的不足,我們要更多地了解中國的作品,其中包括中國的文藝學,這是我的夢、我的希望。
余新華(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副總編輯):文學是人學,文學中存在著人類的憂傷和歡樂,記錄了人類的苦難和輝煌,滋養(yǎng)著人類的心靈和智慧,因為文學是世界人民最容易溝通的語言。從理論上對文學這種現(xiàn)象進行觀照,可以使我們更好地理解人類豐富多彩的生活,當然也會促進文學自身的發(fā)展和繁榮。
今年是俄羅斯文學年,俄羅斯文學在世界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中國也有幾千年的文學傳統(tǒng),它像號角,它像火炬,激勵著中國人民奮勇前行。世界上的人們也關(guān)心著中國的文學,在我認識的俄羅斯學者中,比如圣彼得堡大學的羅季昂諾夫教授,就廣泛深入地研究了許多平素我不太熟悉的中國的作品和作家。所以,我認為我們這次會議的意義也要放到中俄文學、文化交流日漸密切這樣一個大的背景下來理解。因此,我們衷心地希望,這次會議能夠有益于中俄人文交流的不斷深化,通過這次會議,東西方文化平等對話和深度理解能夠得到不斷的拓展,我們愿與俄羅斯和其他國家的學者共同探討文藝學的發(fā)展之路。
張江:20世紀一百年間的文論在不斷地震蕩和調(diào)整,我相信,一個重要的歷史轉(zhuǎn)折就擺在我們面前。我們應(yīng)該認真地去總結(jié)、去辨析20世紀西方文論的優(yōu)長和弱點。我們消解、躲避它的弱點,我們集合、綜合、系統(tǒng)地整合、組織它的優(yōu)長,形成新世紀新的文學理論。讓文學理論走進文學,讓文學理論走進生活,讓文學理論對這個世紀人類的進步和發(fā)展作出應(yīng)有的貢獻。我希望,我們中國學者和在座的各位外國學者,共同努力,去實現(xiàn)這個愿望。
(此文系俄羅斯十月雜志社與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共同主辦的“西方與東方的文學批評:今天與明天”國際學術(shù)研討會紀要。毛莉整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