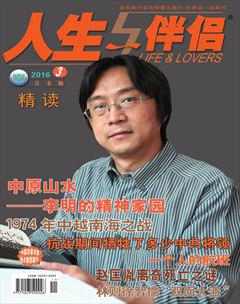我的德國媽媽
馮遠征
“考我的班,我會第一個錄取你”
1986年初,德國人露特·梅爾辛第一次來到中國。那年她將近60歲,在人藝,她成了我的老師。
在訓(xùn)練中,梅爾辛教授大量使用身體技術(shù)來激發(fā)演員的潛能,三四個小時的課程包括翻滾、跳躍等運動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學(xué)也很抵觸。我們班的吳剛(《潛伏》里陸橋山飾演者),就稱病逃避上課。我上課一直特認(rèn)真,不惜力,領(lǐng)悟也快,梅爾辛教授經(jīng)常表揚我。
一天,梅爾辛教授跟我說:“如果你明年去德國,考我的班,我會第一個錄取你。”我卻回答:“不愿意。”人藝是中國最好的劇院,我不想剛進來就離開。不久,梅爾辛教授就回了德國。
1986年下半年,我從學(xué)員班被抽調(diào)到劇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時,劇院第二次把梅爾辛教授請來給我們上課。她再一次鄭重地希望我去德國,我再一次回絕了她。
1987年暑假,梅爾辛教授第三次來到北京,那時我才知道她給我發(fā)過好幾次邀請函,寄到人藝;都被扣下來了。她臨走前,跟我說:“如果你實在不愿意去德國上學(xué),就去三個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學(xué)。”
一年之后,我從人藝畢業(yè),因失戀大受打擊,就給梅爾辛寫信說打算去德國,她特別高興,立刻重新給我發(fā)了邀請函——這次寄到了我家里。
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1989年11月8日早晨7點,我終于敲開了梅爾辛的家門。那一天,我看見了柏林墻——梅爾辛帶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墻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寬的隔離地帶,它空蕩蕩的,只有電網(wǎng)和崗哨,梅爾辛又告訴我,要有人從那兒跑過,士兵就會開槍。
那是我第一次觸摸到柏林墻,那也是它形態(tài)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6點,我在電視屏幕上看到好多人拿著鮮花淚流滿面——東西德的邊境開放了。
我順利在西柏林高等藝術(shù)學(xué)院注冊入學(xué),跟著梅爾辛上表演課,還修燈光、修舞臺美術(shù)、修服裝設(shè)計、修形體……課余時間幾乎所有中國留學(xué)生都忙著打工、找房子,可梅爾辛每個月給我800馬克的生活費,她希望我不打工,專心學(xué)習(xí)。
就這樣在梅爾辛家住了一年,我想搬出來了。因為白吃白喝白住,我自己也覺得不像話。
梅爾辛拗不過我,但她安排我在她一個學(xué)生開的劇團里演戲,每月我有1500到2000馬克的收入。可是一年之后,我開始像哈姆雷特思考“生存或者毀滅”一樣思考“留下或者回去”。相比之下,德國一年語言學(xué)校加四年高等藝術(shù)學(xué)院畢業(yè)之后,很可能根本沒有人找我做演員;如果我繼續(xù)讀書,讀戲劇史或戲劇理論,讀到博士畢業(yè)都快40歲了。這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
“媽媽,再見,一切順利”
我跟梅爾辛談過三次。她想讓我繼承格洛托夫斯基流派,成為她的傳人。
在藝術(shù)領(lǐng)域,格洛托夫斯基流派認(rèn)為任何人只要智商沒問題,都有成為好演員的潛質(zhì),同時,老師的言傳身教特別重要。梅爾辛師從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傳人,這也是為什么她把傳人看得特別重。
可我必須回去,柏林墻已經(jīng)拆了,但是在德國的每一個中國人心里都會有一道墻,就是中國跟德國之間文化的、生活習(xí)慣的墻。
回國的前一天,梅爾辛態(tài)度很冷淡,我知道我是真的讓她難過了。在門外,我擁抱了梅爾辛,說:“媽媽,再見,一切順利。”
在中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會。其實當(dāng)初如果我再在德國待個五年十年,回來可能也能當(dāng)演員,但我就不會遇到《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我感謝梅爾辛,沒有她,沒有格洛托夫斯基,我不會有今天。
(摘自《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