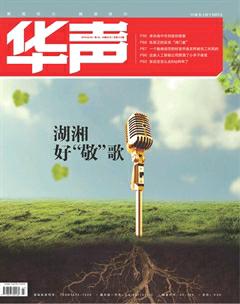《星球大戰》中的政治隱喻
刁大明
“會不會是個sleeping movie?(讓人昏昏欲睡的電影)”在開場之前,硬著頭皮陪我來看的愛人擔心地問道。我一時不知如何回答,畢竟這是中國觀眾第一次在影院里遭遇《星球大戰》。不過,在隨后“原力覺醒”的兩個多小時中,和全場所有人一樣,我們不但沒有被催眠,反而心潮澎湃起來。我的腦海里反復浮現著千年隼在賈庫星上躲過第一軍團飛船追擊的激蕩場面;而愛人會覺得“女英雄”蕾伊令人振奮,這大概也是很多女同胞的同感之一。在踏進影院時對“星戰”還毫無概念的她能有如此共鳴,也足以說明這系列的第七部成功地延續了《星球大戰》的“全民性”了。
事實上,這部“全民電影”在美國大眾心中的意義輕而易舉地得到了白宮的主動背書。12月18日,“星戰七”首映當天,奧巴馬在年終記者會上就請來了“帝國突擊隊”的士兵和原比例大小的R2-D2機器人,甚至他在短暫總結2015、憧憬2016之后,旋即以“趕著去看星戰”為理由匆匆離開。總統如孩子般的猴急,不禁讓人聯想到39年前,那個16歲的孩子看到“星戰一”即《星球大戰:新希望》時的驚奇與欣喜,而喬治·盧卡斯接下來的“星戰二”、“星戰三”也剛好伴隨著奧巴馬度過了大學時光。
就好像在2009年上臺后,一本名為《災難的教訓:邁克喬治·邦迪與通向越戰之路》的歷史書籍在華府外交安保團隊內部被廣泛閱讀一樣,奧巴馬的一代關于國際事務的初體驗大都源自越南戰爭。而這場在1955年到1975年間甚至更長時間段內折磨美國心靈的浩劫也為“星戰”的成功搭建起最為重大的時代幕布。
諷刺的是,“星戰”所抨擊的戰爭政治卻成就了這部電影的全球影響力。如果沒有1999年“星戰前傳系列”的提振,世人更容易找到“星球大戰”這個詞的地方應該是在世界歷史的教科書里。就在“星戰三”即《絕地歸來》上映的同年,時任總統的共和黨人羅納德·里根開啟了針對蘇聯核武器的所謂“戰略防御倡議”。這項將“美蘇爭霸”帶入作為“高邊疆”宇宙層次的宏偉計劃,足以令世人矚目甚至眩暈。按照最初預期,該計劃將耗費超過一萬億美元,相當于40個阿波羅探月計劃的開銷,基本上可以核算為當時美國男女老少每人都要拿出5000美元為該計劃買單。面對神乎其神的目標以及無底洞式的成本效益核算,美國各界紛紛反戈一擊。196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漢斯·貝特就直言,“如果這個計劃不幸成功了的話,簡直就是一場‘星球大戰了!”而順著這個說法,一位資深國會參議員曾唏噓道:還是把這場“星球大戰”留給電影界吧……
與“奧巴馬醫改”類似,“星球大戰”的調侃比喻很快得到了美國朝野的接受和廣泛使用,但盧卡斯本人卻并不高興。1985年,盧卡斯影業甚至發起了訴訟,希望撇清關系,在人們批評里根政府“高邊疆”軍備計劃時不要讓自己的電影跟著躺槍。這件“盧卡斯影業訴高邊疆”案以《商標法》不負責規范新詞匯的新概念闡釋為由被判決不予支持,或許也就注定這部科幻電影無法回避的政治宿命。
1993年5月13日,克林頓政府的國防部長萊斯·阿斯平宣布中止“星球大戰”計劃;也就在同年,美國與蘇聯解體后繼承了絕大部分核武器的俄羅斯簽訂了《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雖然長期以來一直有觀點認為是“星球大戰”計劃拖垮了蘇聯,但可以肯定的是,1990年代帶來美國經濟騰飛的信息技術顯然受益于這場沒有走完的宇宙征程。
6年之后,“星戰四”即《幽靈的威脅》以前傳的面目回歸銀幕。雖然從1997年就開始拍攝,但其上映時間即1999年5月19日卻正值科索沃戰爭的尾聲。當觀眾時隔16年再次被《星球大戰》勾回那些關于戰爭的苦澀回憶時,他們也會自然聯想起當時美國毫無改觀的窮兵黷武。隨后,2002年“星戰五”、2005年的“星戰六”基本上與小布什的反恐戰爭如影隨形。前傳的故事主線,比如在西斯的驅使下,議長帕爾帕廷弄權、排擠絕地戰士、發動戰爭、將共和國蛻變為“銀河帝國”等一系列情節,似乎將矛頭指向了當時美國在新保守主義傾向趨勢下的某種從光明墜入黑暗的墮落嫌疑。
在前六部“星戰”中,自由與專制、正義與邪惡、光明與黑暗,美國的意象并不總在正面,甚至西方意義上的議會民主制度也遭遇了最為徹底的質疑。不過,“一個人就能拯救世界”的“個人英雄主義”甚至是在英雄或梟雄“養成”電影中必不可少的“教父情節”從未缺失,這些價值觀顯然得到了美國公眾的普遍認同。
又過了10年,在盧卡斯首次既不擔任導演又不撰寫劇本情況下,“星戰七”延續起了在1983年結束的故事。收購了盧卡斯影業的迪斯尼雄心勃勃地規劃在未來的2017年和2019年再推出兩部“星戰”系列影片。目測無法應景地搭上政治順風車或者趕上美國海外戰事,“星戰七”卻自動接續了一貫的政治色彩,堪稱是一部標準的政治電影。
比如,“星戰七”中正反兩方的角色設置簡直是“宇宙級”的“政治正確”。第一軍團的士兵可謂千人一面,被隱去個性,而包括凱洛·倫在內的露出面孔的反派人物卻基本都是白人男性;反觀反抗組織陣營,卻在膚色、性別乃至生物類型上刻意突出平衡,甚至連從第一軍團出逃的費恩也是非洲裔。反抗組織的會議上,有亞裔面孔、也有外星生物;而在最后襲擊第一軍團控制星球的戰斗機上也可以有女性和外星生物出鏡。如果一位共和黨人恰好又是“星戰迷”的話,不知道他或她看到如此刻板的安排又會做如何感想。
甚至,在一部主流電影中,一位非洲裔男性和一位白人女性作為主角也并不算多見。一個逃兵、一個拾荒者,除了反復渲染個人英雄主義色彩之外,甚至還預留出了某些可以牽強附會的空間。世界需要一位非洲裔和一位女性拯救,最終非洲裔力不能及,而女性不負眾望地力挽狂瀾……這基本上就是2016年大選希拉里接替奧巴馬入主白宮、領導美國的電影版占卜。而已然老邁的漢·索羅也能在如今的民主黨初選中找到自己的變體:伯尼·桑德斯。雖然這種推測未必太過諂媚,但迪斯尼顯然不會喜歡共和黨的上臺。
最具象征性的情景應該是漢·索羅和凱洛·倫的較量。父親希望通過親情喚回兒子的良知,有一定效果,但卻以人倫悲劇收場,令人嘆惋。而最終得以戰勝凱洛·倫及其背后黑暗力量的卻是激光劍新手蕾伊。當然,蕾伊的決勝法寶肯定是她最初還曾掙扎回避的“原力”。作為一個貫穿了“星戰”的核心概念,“原力”始終沒有明確解釋,只是姑且被理解為是一種源于宇宙所有生物的、超自然的神秘能量場。就像達斯·維德被盧克喚醒一樣,“原力”也終將會為凱洛·倫帶來救贖,并引領光明的一面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
也正是“原力”的存在,“星戰”系列不僅僅是關于宇宙、關于科技的電影,而是關于價值觀的。在“星戰”前三部的冷戰時代,“原力”更像是一種美國價值觀的“自信”。而今,那些受到極端思想驅使、從歐美等世界各地趕往中東、加入ISIS的年輕人們,如凱洛·倫一般,無法被家人感懷悔悟,又該期待所謂美國價值觀的“原力”能發揮多少作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