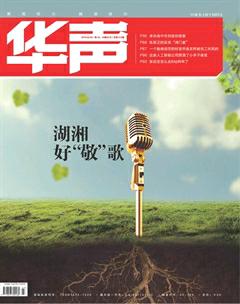軍改若是學美軍,就永遠也攆不上
在中國歷史上,軍隊改革的篇章常常是用血與火寫就。商鞅改革就是很好的例子。
商鞅變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軍事改革。當時列國爭雄,思想正從爭鳴的廟堂走向變革的曠野。在時代澎湃向前的潮流中,向后沒有退路,改革是唯一的活路。商鞅以大無畏的膽魄把秦人引到這條生路上,自己卻走上了死路。他制定了規(guī)矩,然后又用自己的鮮血進一步涵養(yǎng)澆灌了秦人的血性,于是,秦人就變得更加剛烈了。商鞅身體在被撕裂的那一霎間,也預示著秦國與舊制度的徹底決裂,因此,他的死不僅是一種儀式,更是一個境界,百世之后,仍讓人感奮不已。
更新觀念最重要的有兩步
縱觀歷史,由于思想未能及時跟上時代發(fā)展的脈搏,一次次錯過軍事變革機遇的例子層出不窮,例如,元帝國錯過了火藥革命,清朝未能抓住工業(yè)革命。
陳舊的觀念就像泰山一般沉重。幾年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離任時,有記者向他提了個問題:中美之間的距離有多大?這位會講漢語的大使毫不猶豫地說:“一百年!”
筆者為這句話感到震驚。仔細想來,他講的距離不是指經(jīng)濟,不是指硬件,而是指思想觀念。
觀念是軟力量,卻是決定性力量。軍事理論一日千里,美軍一直站在軍事理論創(chuàng)新最前沿,從海權論到信息戰(zhàn),從空地一體到全頻譜作戰(zhàn),差不多每隔幾年就推出一個嶄新的軍事學說。伊拉克戰(zhàn)爭中體現(xiàn)的以“震懾理論”為基礎的“快速決定性作戰(zhàn)”思想,就是對海灣戰(zhàn)爭中“壓倒性力量優(yōu)勢”理論的大膽否定。
不斷地自我否定,強烈的超前意識,這是美軍改革的兩個顯著特點。隨著高科技更新周期越來越短,高科技的內(nèi)容變化越來越大。今日的高科技,幾年后就是古董。當整日都在呼喊“高科技!高科技!”之時,高科技冷笑著從我們身邊呼嘯而過。
思想必須革命,觀念必須更新。更新觀念最重要的有兩步:看到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再想到所有人都沒有想到的。我們的目光應當像探照燈一樣,照射的不是過去,也不是現(xiàn)在,而應該是未來。
軍事領域的變化比想象的要快很多,甚至是所有領域中變化最快的。因為每一個時代的尖端技術和思想都最容易用于軍事目的。
海灣戰(zhàn)爭后,全勝而歸的美軍參戰(zhàn)部隊司令施瓦茨科普夫提出退役,理由是:“我已不適應下一場戰(zhàn)爭了。”施瓦茨科普夫角色的轉(zhuǎn)換在筆者看來是那樣驚心動魄,甚至比世界上第一場“直播戰(zhàn)爭”(海灣戰(zhàn)爭的別稱)中美軍對伊軍疾風驟雨般的打擊還要讓人驚心動魄。
軍隊的強大絕不僅僅體現(xiàn)在高精尖武器裝備上,更體現(xiàn)在思想和觀念的強大上。馬島戰(zhàn)爭以來,世界上所有的戰(zhàn)爭都是不對稱戰(zhàn)爭,根本原因是一方思想觀念先進,另一方思想觀念陳舊所形成的不對稱。
只有革命才能找到真理。真理不會滅亡,但極易受傷。而謬誤則相反。
軍改首先要改人
劉伯承元帥說:“要建設一支現(xiàn)代化的軍隊,最難的是干部的培養(yǎng),而培養(yǎng)干部最難的又是高級干部的培養(yǎng)。”人永遠是戰(zhàn)爭中最重要的因素。
1947年8月,豫東戰(zhàn)役結(jié)束后,毛澤東說:“解放戰(zhàn)爭好像爬山。現(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過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階段已經(jīng)過去了。”解放戰(zhàn)爭剛打了一年,毛澤東敢這么講,不是因為共產(chǎn)黨的軍事實力超過了國民黨,而是我軍在戰(zhàn)爭硝煙中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掌握戰(zhàn)爭規(guī)律、具有高超指揮藝術的將領,構(gòu)筑了一個人才高地。
如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的劉伯承、鄧小平;西北野戰(zhàn)軍的彭德懷、習仲勛;華東野戰(zhàn)軍的陳毅、粟裕;東北野戰(zhàn)軍的林彪、羅榮桓;中原軍區(qū)的李先念等等。由于擁有這批人才,解放戰(zhàn)爭勝利到來之迅速,出乎意料。但是今天,我們這支軍隊曾經(jīng)擁有的人才優(yōu)勢,已經(jīng)成為與強敵較量時的薄弱環(huán)節(jié)。
1963年,毛澤東在憑吊羅榮桓的詩中寫道:“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這首詩既是一個分野,又像一個讖語。自第一代將領凋零之后,我軍一直期待出現(xiàn)席卷天下時的那股人才潮。
今天我軍人才隊伍建設又到了“爬坡”階段。這個“坡”,比當年的“坡”艱難百倍。因為積弊太深,如深淵萬丈。不進行一場革命,不足以煥發(fā)青春。而革命則應覆蓋三個方面——
高層:此次軍改,應在高級將領中刮一場“頭腦風暴”。當今世界,“戰(zhàn)略為王”。《春秋》云:“將軍,身也;卒,支也;伍,指姆也。”士兵是講戰(zhàn)術的,將軍必須是講戰(zhàn)略的。所有的勝利都是戰(zhàn)略的勝利,所有的失敗都是戰(zhàn)略的失敗。
毛澤東的成功在于選擇了正確戰(zhàn)略,鄧小平也是戰(zhàn)略起家。我國“將軍團”如果能成為“戰(zhàn)略團”,軍必興焉。
中層:鑄造一個全新的“參謀團”。“參謀團”即精英集團。一戰(zhàn)后,德國總參謀部被撤銷,軍隊只能保持十萬人。德軍最高首腦馮·西克特設法保留了一個軍官團。馮·西克特制定的標準是,每一個列兵都受到成為軍士的培訓,每一位軍士都受到成為軍官的培訓,每一位軍官都受到成為將軍的培訓。
正是這些精英,構(gòu)成了德國的“十萬陸軍”,后來發(fā)動了二戰(zhàn),一下把世界打懵了。俄國近代雖然擁有一批偉大的軍事統(tǒng)帥,也誕生過一些軍事思想家,但長期以來沒有一個高素質(zhì)的軍官團。雖有源源不斷的兵源優(yōu)勢,但先敗克里米亞,再敗旅順,又敗對馬。
在我軍歷史上,參謀也曾起到重要作用。解放戰(zhàn)爭中,在西柏坡幾間簡陋的土房里,雷英夫和幾個參謀指點江山,橫掃千軍。正是此人,不久后還準確預測到了麥克阿瑟的仁川登陸。
自那以后,我軍參謀隊伍越來越龐大,卻鮮有卓見和建樹。今天,我軍參謀隊伍有兩大問題:其一,缺少吞天吐地的能力。首先是缺少吞天吐地的氣魄。“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就是辛辣而真實的寫照。
其二,缺少干事業(yè)的追求。中層軍官必須把打仗當成一個職業(yè),軍人不把打仗當成一個職業(yè),就更不會把它當成一個事業(yè)。“參謀團”應由我軍最優(yōu)秀的知識分子組成,應在我軍“參謀團”里,讓未來的將軍更早相遇。
基層:士兵要有知識和文化。在過去的戰(zhàn)爭里,一名士兵可能就是練了兩天射擊的農(nóng)民,這名士兵陣亡后,三天后就可再補上一名。
現(xiàn)代戰(zhàn)爭卻不是這樣。一名合格的士兵需要經(jīng)過長期而嚴格的訓練。解放戰(zhàn)爭中“即打即補,隨打隨補”的現(xiàn)象再也不復存在。在美軍近幾場戰(zhàn)爭中,一個班長五分鐘內(nèi)即可呼叫到航空兵火力突擊,一個單兵兩分鐘可呼叫來地面炮火支援。
在美軍設計的未來戰(zhàn)爭中,士兵只需敲擊計算機鍵盤就可以達到攻擊對方軍事樞紐、破壞經(jīng)濟命脈等多種目的。鍵盤就是武器,鼠標即是炮火。這些都需要士兵具有高度文化知識。
筆者曾訪問過美軍一個步兵連隊,和士兵進行交談。他們開闊的視野和活躍的思維令人吃驚。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從印度洋至太平洋,他們侃侃而談,激昂得很。
我們的軍改,為何沒有照搬美軍模式
此次軍改,我們沒有照搬美軍模式。因為,美軍體制固然可鑒,但那是美國政治制度和價值體系的產(chǎn)物,美軍的改革也是基于美國國情的改革。如果一味向美軍學習,我們將會迷失方向,就可能犯“顛覆性錯誤”。
反思各國軍隊近十幾年的改革,基本上都有美軍的影響和色彩。俄羅斯軍隊改革為什么走那么多彎路?就是它照著西方特別是美軍的模式改了6次,矛盾重重,得不償失,最終以難以適應本國國情而告終。
中國軍改不能脫離國情和歷史。國情就是歷史,歷史就是國情。是歷史創(chuàng)造了未來,而不是未來自己創(chuàng)造了未來。沒有歷史的未來是一個黑洞,什么都會被它無情吞噬。丘吉爾說:“看得見多遠的過去,就能走向多遠的未來。”我們以怎樣的態(tài)度對待歷史,歷史就回報你一個相應的未來。
譬如,美軍的統(tǒng)帥部是直接指揮到單兵的,但它并不是強化集中指揮,而是逐步下放戰(zhàn)斗的自主權。如果只看到統(tǒng)帥部直接指揮單兵這一點,那就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美軍的主旨并不是直接掌控單兵行動,而是踐行德國軍事思想上的精確作戰(zhàn)、量化作戰(zhàn)。
這和中國昔日戰(zhàn)時一竿子插到底的情形有著本質(zhì)不同。歷史上蔣介石最愛干一竿子插到底的事。每次蔣介石親自指揮作戰(zhàn),諸將領必頭痛不已。結(jié)果只有一個:必敗無疑。
我軍目前采用的是前蘇聯(lián)軍師團模式,指揮體系是適應于機械化戰(zhàn)爭的金字塔結(jié)構(gòu)。
這種指揮體制應對現(xiàn)代戰(zhàn)爭特別是信息戰(zhàn)爭有難度,但固守本土,保持國家政治穩(wěn)定又是有效的。看上去左右為難,其實這告訴我們:到了讓你換個方向前進的時候了。重新開始不等于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也未必不能重新開始。
毛澤東指揮解放戰(zhàn)爭的歷史是一部教科書,今天我們恐怕還是要有點毛澤東精神。這有點像鐘表,可以回到起點,但已不是昨天。
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讓別人無路可走
馬漢說:“如果一個國家的地理位置,除了具有便于進攻的條件之外,又坐落在便于進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時還控制了一條世界主要貿(mào)易通道,顯然它的地理位置就具有戰(zhàn)略意義。”地理位置決定著軍事變革的方向。
筆者一直研究美軍戰(zhàn)略,發(fā)現(xiàn)它的軍事部署始終沿著一條地理線展開:海灣、紅海、地中海,這是人類文明的海上樞紐,這條地理線就是美軍戰(zhàn)略線。中國軍改也必須考慮地理因素。
中國的地理形狀代表了典型的地緣政治家所描繪的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特征:是大陸國家,同時又有漫長的海岸線,尤其是西部,占據(jù)著全世界最高的地勢。今天的軍隊改革也必須適應國家戰(zhàn)略的需要。當國家戰(zhàn)略轉(zhuǎn)變時,軍事理論也必須轉(zhuǎn)變。軍改,必須服務、服從于國家的整體發(fā)展戰(zhàn)略。
我軍很多將領至今還對解放戰(zhàn)爭和抗美援朝時大規(guī)模超大兵團集群作戰(zhàn)的經(jīng)典戰(zhàn)例津津樂道,還夢想著指揮這樣的作戰(zhàn),但這樣的機會還會有嗎?永遠不會有了。外敵一旦打擊中國,絕不會深入到中國腹地,與我軍進行大兵團決戰(zhàn)。特種作戰(zhàn)已是世界大勢所趨。軍事理論革命濫觴于美國。
美軍已經(jīng)走得太遠了,如果我們一直跟著美軍攆,永遠也攆不上。我們必須對已經(jīng)被美軍革命過了的軍事理論進行再革命。每一支強大軍隊的崛起都是獨一無二的,這種崛起都是探索符合自身特點的成長道路的結(jié)果。只可以超越,不可以模仿。
高手比到最后,比的是自我。這啟示我們,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讓別人無路可走。譬如,美軍最早提出了信息戰(zhàn)的概念,而美軍講的信息戰(zhàn)其實就是計算機戰(zhàn),全世界生產(chǎn)計算機中央處理器的三大公司都在美國。包括我軍在內(nèi)的所有國家軍隊的自動化指揮系統(tǒng),計算機所使用的中央處理器,絕大多數(shù)是美國產(chǎn)品。
這其實就決定了美國的獨占性。筆者把這種計算機戰(zhàn)爭稱為“物質(zhì)信息戰(zhàn)”,打這樣的戰(zhàn)爭,誰能贏得了美國?那么,比照“物質(zhì)信息戰(zhàn)”,能不能提出一個“精神信息戰(zhàn)”的概念呢?
這種戰(zhàn)爭,信息主要用于人的精神層面,即用大量的主觀信息干擾、破壞、降低乃至使敵方完全喪失思維識別能力,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潰不成軍。相比較“物質(zhì)信息戰(zhàn)”的“硬殺傷”,“精神信息戰(zhàn)”造成的作用是“軟殺傷”。“軟殺傷”不會比“硬殺傷”作用小。
新的戰(zhàn)爭形態(tài)已現(xiàn)。
摘編自2016年1期《國防參考》,作者劉亞洲上將系國防大學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