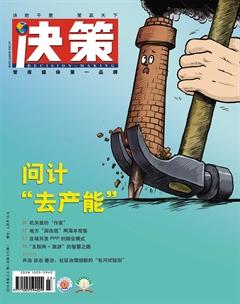僵尸企業的清理之道
夏自釗
僵尸企業比正常企業更愿意增加員工數量,個別僵尸企業甚至還不斷增加投資,而且投資效率普遍較低,這些都導致產能過剩進一步加劇。
從2015年下半年的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開始,僵尸企業開始頻頻被點名。“權威人士”1月4日在《人民日報》頭版明確表態“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尸企業,讓僵尸入土為安”。
僵尸企業不是一個新生事物,為何此時會如此強調要對其進行清理,處置僵尸企業的當下意義是什么?
“僵尸企業不退出,產能過剩矛盾就不能根本化解,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就是一句空話,只有退夠,才能前進。”工信部副部長馮飛表示。同時,大量僵尸企業“屹立不倒”的背后是錯位的政企關系、扭曲的要素資源配置和長期投資沖動形成的路徑依賴。
盡管去產能就必須處置僵尸企業已是各方共識,但究竟僵尸企業的邊界該如何劃定,各界卻看法不一。那么,究竟何謂僵尸企業?“僵尸”為何難以入土為安?
“中國式困局”
根據官方表述,僵尸企業是指那些沒有競爭力和盈利能力,低效占用資源,特別是依靠財政“輸血”、銀行貸款存活,持續虧損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馮飛則認為,僵尸企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難以順利退出市場”。
有學者還給出了量化指標:那些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后、每股收益連續三年為負數的公司,都可以稱為標準的僵尸企業。按照這個標準,滬深兩市共有266家僵尸企業,占上市公司總數的10%,其中197家屬于鋼鐵、有色、造紙、紡織、船舶、石化、化工、機械、水泥、煤炭等傳統制造業,與產能過剩行業高度一致。
僵尸企業既然如此無望,為何沒有在市場中被淘汰掉,反而“屹立不倒”?癥結在于不合理的政企關系和政府對這些企業的“偏愛”。
首先,僵尸企業中相當多數是國企,與各級政府有扯不斷的利益關系。其次,僵尸企業不少是有一定規模的企業,直接影響一地的GDP、稅收和就業。讓僵尸企業生存下去,其代價并不全部由當地和本屆政府承擔,雖然政府要一些投入,但考慮到政績和社會穩定,兩害相權取其輕,政府依然會慷慨支持僵尸企業。此外,產生僵尸企業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政府過度追求投資和速度造成企業投資行為的扭曲。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近期一份研究報告通過分析大量過度投資案例發現,地方政府投資偏好下的高投資與重復建設、信息不對稱、行業準入限制下的民間投資“羊群效應”,是導致“中國式產能過剩”的重要體制因素,也是分析僵尸企業的重要切入點。
地方政府行政力量主導產業發展,造成產業雷同,特別是以土地、礦產資源、投資配套等極具誘惑力的手段吸引大型投資項目落地,使企業更加看重投資項目以外地方政府所給予的資源,造成投資行為異化,背離市場規律。
該報告總結道:“僵尸企業效益低下,卻又不讓倒閉破產,契約精神和優勝劣汰的市場法則失靈,企業抓住政府喜歡GDP的心理,進行政策套利,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在供給端追求產業低端,致使經濟升級的阻力巨大。”
要消滅僵尸企業,方法看起來很簡單:讓銀行停止給這些企業提供貸款即可。但蹊蹺的地方也正在于此,這些銀行從一開始就知道哪些企業是僵尸企業,它們也知道再怎么努力,也救不活僵尸企業,但為什么又要如此“奮不顧身”、“前仆后繼”地去救僵尸企業呢?
財新智庫曾就僵尸企業對幾位國有銀行高管進行過匿名訪談,訪談發現,即使沒有地方政府的影響,銀行自己也會主動“輸血”給僵尸企業。
“企業都不想自己垮掉,銀行也都不希望自己的客戶垮掉。這時候,真正在打擂臺的就不只是企業了,還有企業背后的銀行。這些銀行都希望自己的客戶能夠成為‘剩者’,那自然就會不斷給這些企業放款了。”
“如果企業倒閉會給銀行帶來難以承擔的損失,那么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銀行也會這么做。要知道,救助這些企業本身就符合銀行的自身利益。這種情況下,無論有沒有外在的壓力,銀行都會選擇救助這些企業,地方政府只是一個影響因素而已。”訪談中,一位國有銀行高管表示。
“三宗罪”的背后
盡管僵尸企業是經濟的毒瘤,然而一旦給僵尸企業斷奶斷血,不僅銀行貸款無法回收,還會出現連鎖反應,諸如大量的職工下崗,相關的產業鏈企業、很多靠大企業吃飯的小企業,也會碰到困難。久而久之,各地干脆睜只眼閉只眼,任僵尸企業存在下去。
但是隨著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僵尸企業的嚴重性和危害性日益凸顯,嚴重影響行業正常運行,加大了宏觀經濟潛在風險。因此,才有了“當務之急是斬釘截鐵處置僵尸企業,讓僵尸入土為安”的論斷。
1月11日,《人民日報》再次就僵尸企業發聲,這篇名為《處置僵尸企業不能等》的文章列舉了僵尸企業的“三宗罪”。
其一是“無功受祿”,無經濟效益卻占用大量資源,降低資源配置效率,導致資源無法向收益更高的部門流動。其二是“尋釁滋事”,無競爭實力卻擾亂市場秩序,還以穩定為借口占據社會資金,導致劣幣驅逐良幣,阻礙了新技術、新產業的培育成長。其三是“蟻穴潰堤”,無償債能力卻吸納大量企業拆借與銀行貸款,導致不良資產激增,易引發金融風險。
在各界對僵尸企業危害性的解讀中,嚴重的資源錯配最為詬病。以信貸資源為例,盡管金融危機以來,中央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解決中小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但大量的中小企業融資越來越難,融資成本遠高于歐美等國。究其根源,就是因為大量的僵尸企業占有了信貸資源,導致中國的貨幣政策出現了“發行貨幣越多,流動性越緊張,資金的價格越昂貴”的怪圈。
此外,還有一個邏輯關系需要厘清,通常認為是產能過剩導致了僵尸企業的產生,然而事實卻是,僵尸企業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會打斷去產能的進程。
正常情況下,首先被淘汰掉的產能是那些落后產能,對應的企業自然就會倒閉,這個過程叫做去產能過剩。但是,僵尸企業的存在會打斷去產能過程。在市場需求減少時,這些效率較低的企業卻沒有被淘汰。本該減少的產能卻沒有減少,自然就成為多余產能。
有研究表明,僵尸企業占比較多的行業,產能過剩現象也更加嚴重。不僅如此,僵尸企業比正常企業更愿意增加員工數量,個別僵尸企業甚至還不斷增加投資,而且投資效率普遍較低,這些都導致產能過剩進一步加劇。
然而,其危害遠不止于此。好企業不斷退出,就意味著銀行的優質客戶逐漸減少。這樣,銀行就只能把更多的錢投向僵尸企業。惡性循環于是形成:僵尸企業拿到錢——好的企業被淘汰——銀行沒有好的項目——僵尸企業拿到更多的錢。最終,僵尸企業大行其道,銀行反而成為了僵尸企業的附庸,銀行成了僵尸銀行。長此以往,整個經濟將有可能陷入長期衰退。
破立之道
2015年12月24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后2天,全國工業和信息化工作會議召開,會議就2016年的工作重點布置了八項任務,其中提升供給質量和效率、清理僵尸企業,被放在了工信系統2016年工作重點的首要兩位,并要求地方政府堅決停止給僵尸企業財政補貼、稅收優惠、銀行借貸等政策支持。“能兼并重組的要加快兼并重組,無法兼并重組的企業要堅決拋棄,杜絕觀望等待。”苗圩表示。
與部委頂層政策發力相呼應的是,地方層面已經開始有動作。2016年開年以來,甘肅、湖南、黑龍江、山東、安徽等地紛紛表態,將嚴格處置僵尸企業。
湖南將在2016年停止補貼和保護,實現市場出清。湖南省經信委將對各行各業的僵尸企業進行摸底調查,及時處理,2016年將淘汰1000家以上的產能過剩企業。
山東摸底情況顯示,按照利潤不夠支付企業信貸利息、已停止經營活動半年以上、生產經營活動基本處于停頓狀態的三類評判標準,山東省初步確定了448家僵尸企業。
僵尸企業情況干差萬別,同樣需要分類有序的清理。國內最早對僵尸企業進行摸底,并提出分類清理的是浙江。2012年和訊網一篇關于溫州僵尸企業的報道引起浙江省委主要領導高度重視,隨即相關部門對省內僵尸企業進行調研摸底,并形成調研報告刊發于《浙江經濟》雜志。
報告建議,對僵尸企業不應搞“一刀切”,要“升級一批、重組一批、破產一批、淘汰一批”。一是結合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騰籠換鳥”,加快一批有條件的僵尸企業轉型升級。二是企業雖然資不抵債.但產品有發展潛力的僵尸企業,要通過產權、債務重組等途徑,降低債務負擔,加快發展。三是對經營困難、喪失競爭力的僵尸企業,加快破產,騰出土地、資金等要素發展優勢產業。四是結合國家加快化解過剩產能的部署,加快淘汰已為落后產能的僵尸企業。這雖然是2012年的調研報告和政策建議,對于今天各地如何清理僵尸企業卻不無借鑒意義。
由于僵尸企業大多是國企,因此清理僵尸企業須與國企改革同步進行。比如加快推進國企分類改革,競爭性行業國企要徹底推向市場。2015年12月29日,《關于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發布,國企分類改革的大幕拉開,如果改革能落實到位,更多的國企被推向市場,僵尸企業的問題,將得到有效醫治。
一些地方政府認為去產能、清理僵尸企業就是簡單的“破”,因此等待觀望非常嚴重,但他們沒意識到清理僵尸企業也可以是“立”,通過并購重組,可以有效緩解去產能的陣痛,同時重塑企業活力。其實,清理僵尸企業所帶來的紅利遠不止于此,有地方官員已經在樂觀的看待僵尸企業的清理。重慶市經信委主任郭堅在2016年初的一個論壇上表示,清理僵尸企業,將給政府、產業和企業帶來一次根本的轉型。
郭堅分析說:“對政府而言,是轉變職能的原動力,促使各級政府嚴格遵循市場規律謀事辦事,進一步簡政放權釋放市場活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供給效率;
對產業而言,是逆轉頹勢的加速力,促進傳統產業通過模式重構、路徑優化,從產能擴張轉向內涵延展,新興產業通過接續成長、發展壯大形成經濟增長的新動力群,增加有效供給;對企業而言,是浴火重生的孵化力,促使企業苦練內功、轉型脫困,通過兼并重組、債務重組及破產清算等方式實現市場化退出,僵尸企業、空殼公司得以穩妥處置,去除無效供給。”
或許正是因為冷靜、樂觀看待僵尸企業的出局,重慶的產能過剩才在全國處于較低水平,在經濟下行中展現出別樣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