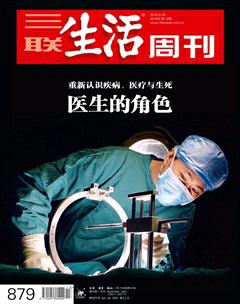暗物質衛星“悟空”:漫漫取經路
曹玲
暗物質探測衛星由中國科學院微小衛星創新研究院總研制,系統總設計師李華旺說:“就拿電視機來比喻,我們負責制造電視機,質檢合格出廠,交由用戶使用,我們負責售后服務,至于怎么用就看用戶的了。”
2015年10月30日,四川錦屏極深地下暗物質實驗室的工作人員正在分析實驗數據
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首席科學家、紫金山天文臺副臺長常進表示,到目前為止,衛星在天上工作了85天,搜集了4.5億個高能粒子,覆蓋了三分之二天區。“我們要測量電子、伽馬質子等,現在探測器完全能夠滿足所有的科學目標。我需要一定的時間,獲取一定量的高能粒子,才能告訴大家有沒有探測到暗物質粒子,暗物質粒子在天上的什么地方。”
暗物質探測衛星和應用型衛星不同,是我國發射的第一顆科學實驗衛星。“科學實驗衛星上天之后要有科學產出,提供科學知識。”中國科學院國家空間科學中心主任吳季說。據他介紹,今年我國將陸續發射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實踐十號衛星、硬X射線調制望遠鏡衛星等科學實驗衛星,“我國空間科學正在進入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
“選擇空間科學衛星的研究目標非常重要,其成果只有世界第一,沒有中國第一。空間科學衛星的目標由科學家來定,而不像應用型衛星目標由用戶來定。”吳季介紹,2011年1月,中國第一個空間科學衛星計劃“空間科學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正式啟動,首批空間科學衛星遴選項目時重點考慮兩個方面:一是科學產出的重大性,即是不是重大前沿,能否實現重大突破;二是考慮它的帶動意義,是不是能廣泛地帶動學科的發展,帶動更多的科學家參與數據分析。
暗物質探測衛星成為“空間科學先導專項”發射的第一顆實驗衛星。為什么要這么迫切地去尋找暗物質呢?
所謂暗物質,是指不發射任何光及電磁輻射的物質,目前人們只能通過引力產生的效應得知其存在。長期以來,暗物質和暗能量都被認為是籠罩在21世紀物理學上的兩朵“烏云”。天文學家推測,宇宙中最重要的成分是暗物質和暗能量,暗物質占宇宙的25%,暗能量占70%,通常所觀測到的普通物質只占宇宙質量的5%。也就是說,我們的宇宙大部分由看不見的物質組成。“宇宙中所占比例最多的東西反而是人類最遲也最難了解的,至今僅知道它們的存在,但還不清楚它們的性質。”科學家認為,暗物質是宇宙大爆炸的產物,在宇宙演化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同時也決定著宇宙未來的命運。
“按照現有的粒子物理標準模型,科學家預測到61種基本粒子,這61種基本粒子都找到了,包括前些年找到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但是暗物質粒子的物理性質和這61種粒子不吻合,現有的物理知識無法解釋暗物質。如果我們探測和研究暗物質粒子,很可能會導致物理學的革命性突破。”常進說,“如果能揭開它們的秘密,就有可能解決宇宙之謎。”
為此,暗物質成為當今科學界面臨的最前沿問題之一,目前中國和世界多個國家已著手籌建或實施多個暗物質探測實驗項目。“悟空”自2015年12月發射升空起就備受關注。國家空間科學中心的數據顯示,“悟空”是迄今為止觀測能段范圍最寬、能量分辨率最優的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超過國際上所有同類探測器。“悟空”預計在軌工作3年,前兩年主要進行巡天觀測,后一年根據前兩年的觀測結果進行定點掃描探測。常進說:“目前數據分析正在進行中,預計今年底將公布首批科學成果。”
暗物質是什么
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才是天空真正的秘密。
了解一些你看不見的東西是很難的,暗物質既不發光也不吸收光,和光沒有任何相互作用。它所謂的“看不見”,不單單是說用我們的肉眼在可見光波段看不見,而是說不論探測什么波段的電磁波,比如紅外線、紫外線、X射線、伽馬射線等,都看不到它。
但是科學家知道它們存在。上世紀30年代,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弗里茨·茲威基(Fritz Zwicky)觀看鄰近的星系時發現了一些奇怪的東西。他研究星系團的運動,對星系團里有多少物質做了估算,然后對比人們能看到的物質數量,結果發現那些星系都轉得太快了,如果僅僅用它們內部所含的物質來計算,巨大的離心力應該早就讓它們分崩離析。如果宇宙中的每一個星系都像一個旋轉木馬,它們轉動得太快,上面坐著的游客們應該都會飛出去才對。
所以其中一定有其他物質在影響星系的運動,那是什么呢?茲威基敏銳地指出,這些物質不能被直接觀察到,但卻同樣能夠產生引力作用,從而幫助將星系聚集在一起而不至于被撕碎。1933年,他成為第一批真正了解暗物質存在意義的人,稱其為“迷失的物質”。
這個革命性的想法一開始卻被大大忽視了,人們尊重茲威基,但沒人愿意認真對待他的觀點。他的偉大洞察和理論都被擱置一旁,無人問津。當時人們認為他是個瘋狂的理論家,有勁沒處使,所以才發明這么一種全新的物質出來。
茲威基的測量基于星體和星系的物質數量,但是怎樣衡量太空中的物質數量?雖然無法直接測量太陽,但可以測量行星圍繞太陽旋轉的速度,太陽的質量越大,行星想要留在它的軌道,旋轉速度就要越快。
牛頓和愛因斯坦都認為,一個物體的質量越大,萬有引力就越大;一個物體離中心越遠,它在軌道里就運行得越慢,因為萬有引力變小了。就拿太陽系來說,水星的運行速度相比海王星來說更快,因為水星離太陽更近。同樣的,對于一個星系你可以預期,如果距離越來越遠,物體運動速度就會越來越慢,以維持在正常的軌道。但事實上,外圍恒星運動的速度遠遠超出了預期。
茲威基沒有意識到這一點。50年后,一個叫維拉·魯賓(Vera Rubin)的年輕女科學家在觀測類似銀河系的星系旋轉曲線時發現,越來越遠的氣體和塵埃的軌道運行速度始終保持不變。如果一個城市是一個星系,道路上的車輛是一顆恒星或者行星,不管道路交通多繁忙或者其他因素多復雜,每一輛車都以相同的速度穿梭在城市里。她又觀測了其他星系,發現也是同樣的情況。魯賓由此認為,宇宙中存在著我們看不見的物質,為彌散于星系各處的氣體提供著引力。
“地球附近也有大量的暗物質。天文學家發現,銀河系里成千上萬顆恒星的實際觀測速度要大于理論上的速度。太陽的速度理論上是每秒160公里,但是現在觀測太陽的速度大概是每秒240公里。如果不存在暗物質的話,太陽系就應該處于銀河系的更外圍,而不是現在這個位置。”常進說。
科學家分析了上百個星系,都有同樣的形狀,運轉速度都太快了,需要暗物質把它們保持在一起。這時,科學家開始注意到這個問題,什么是暗物質,如何在太空中找到一些看不到的物質?
被稱為引力透鏡的效應為暗物質提供了更多的證據。如果有一大團物質,例如星系團恰好位于一個遙遠光源的前方,那么前景天體就能彎曲從其附近經過的背景光,由此會產生一系列的光弧,把這些弧線連接起來就會形成一個“愛因斯坦環”。質量越大,它對光線的彎曲量越大。然而,在星系團中沒有足夠的可見物質能產生出我們所觀測到的彎曲,于是,那里必定隱藏著不可見的額外質量。
暗物質的存在似乎突然間被揭開了。一旦暗物質出現,科學家又懷疑它是不是一種新的沒有被發現的粒子,還是一般的看不見的物質。最初,科學家認為它和組成你和我的物質一樣,但是不會發光。
科學家設想宇宙里不會發光的哪些物質可能會是暗物質。黑洞有可能是,它不會發光,可以透過引力透鏡發現;隱藏在銀河系暈輪里的大質量致密天體可能是,它們可以通過引力透鏡觀測,但它們的質量還不足以描述暗物質的數量;褐矮星同樣是懷疑的對象,它們數量足夠多。除此之外,暗物質的候選者還有中子星、自由行星、白矮星和非常微弱的紅矮星和大質量弱相互作用粒子(WIMP)。
無論暗物質是什么,它們的數量和質量都比恒星和行星的普通物質多上10倍。所有由原子、質子、中子組成的物質,數量都比不上科學家在星體和星團中所觀測到的物質的數量。
科學家繼續尋找新的可能性,繼續研究暗物質,以前發現的奇異粒子,例如中微子成了他們的研究對象。像暗物質一樣,每次數以百萬計的中微子穿過地球,但是它們太輕了,沒有辦法解釋暗物質對萬有引力的影響,而且科學家可以在粒子碰撞實驗中產生中微子。
在考慮了所有的可能性后,許多科學家相信暗物質是一個新的奇異粒子,和地球上的物質完全迥異。每秒有數十億暗物質經過我們,但從來不和普通物質發生碰撞。如今,我們知道暗物質是一些笨重的物質,速度不是很快,我們看不見它,它對我們沒有影響,和普通物質也不產生相互作用。
科學家維拉·魯賓認為,宇宙中存在著我們看不見的物質,為彌散于星系各處的氣體提供引力
目前,對于暗物質是什么,最普遍接受的想法是一些叫作大質量弱相互作用粒子的物質。大質量弱相互粒子對大顆粒的作用力很小,它們的特性和暗物質的可能性很接近。
尋找暗物質
對于這些擅長隱身的暗物質粒子,如何才能找到它們呢?
“如果理論上知道它是什么東西,我們就能很容易地把它找到。通俗地講,我們去找一個人,只知道這個人可能存在,但是這個人穿什么衣服、長什么樣子,我們根本不清楚,只能通過排除法,或者說一步一步篩選,從一些可疑的跡象篩選。”常進說。
目前,人類用來捕捉暗物質的方法僅有三種,可以形象地稱之為“上天、入地、對撞機”。目前國際上有歐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安裝在國際空間站上的阿爾法磁譜儀,以及美國航空航天局的費米太空望遠鏡等設備在尋找暗物質,但目前找到的都還只是一些“疑似證據”。
其中,“上天”是間接探測方法,即捕捉暗物質互相碰撞、湮滅時產生的痕跡。當一對暗物質粒子偶然相撞的時候,會同時湮滅,可能會放出質子、電子及它們的反粒子、中微子和伽馬射線。如果能夠精確測量到這些粒子的能譜,就可能會發現暗物質粒子的蹤影。
我國發射的暗物質粒子探測衛星,采用的也是間接探測的方法。“暗物質衛星只是瞄準暗物質可能產生的一種現象,也就是暗物質粒子湮滅或者衰變的時候會產生一些高能粒子,這叫間接法。至于間接法能不能找到暗物質,我現在也不知道。我知道的是,盡管暗物質粒子探測器最主要的目標是去找暗物質,但是這個探測器本身就是一個望遠鏡,一旦打開這扇新的窗戶,必然有很多新奇的現象。究竟這個新奇的現象是捕捉到了暗物質,還是其他的一些新的天文、物理現象,我們還不清楚。”常進說。
“入地”則是一種直接探測的方法,該方法是直接探測暗物質粒子和普通原子核碰撞所產生的信號。比如美國低溫暗物質搜尋計劃(CDMS),位于明尼蘇達州地下800米深的一個廢棄礦井,費米實驗室在此設計了一個探測器可以探測暗物質。暗物質就在我們身邊流動,任何動靜也沒有,很小的概率它會撞上探測器感應裝置原子的原子核,那就是科學家希望看到的。
位于我國四川的錦屏極深地下暗物質實驗室也是如此,這是我國首個用于開展暗物質探測等國際前沿基礎研究課題的極深地下實驗室,其上方有厚達2400米的巖石層,可以將穿透力極強的宇宙射線隔絕到只有地面水平的大約億分之一,為探測暗物質提供了一個幾乎沒有干擾的環境。
“對撞機”則是在加速器上將暗物質粒子創造出來,并研究其物理特性。常進說,由于暗物質粒子即使被創造出來,也不會被探測器發現,只能通過其他可以看見的粒子來推測出是否有暗物質粒子產生。雖然暗物質粒子不能被直接觀察到,但它一定會帶走“能量”,即創造暗物質粒子需要能量,因此從丟失的“能量”和分布可以推測暗物質的某些性質。目前,歐洲核子中心的大型強子對撞機被認為很有可能創造出暗物質粒子。
“這三種方法互為補充,可以互相印證。如果我們在天上找到一種暗物質粒子,質量超過現有加速器的能量上限,那么加速器的能量就必須進一步提高。如果我們把暗物質的質量弄清楚了,會指導地下的直接探測實驗修改他們的方案,比如現在清華大學、上海交大致力于尋找低質量的暗物質粒子,國際上一些組織主要探測大質量的暗物質粒子。如果我們準確地知道了暗物質粒子的質量,那地下實驗就會變得比較明確了,究竟是找怎樣的暗物質。”常進說,“至于暗物質衛星究竟能發現什么,還要等數據分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