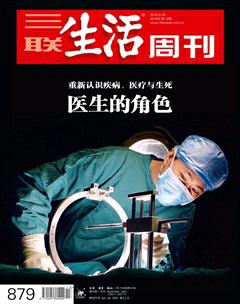“我關注所在,甚過所見”
曾焱++王紫祎++王琪
三聯生活周刊:裝置作品《Host》被譯為《屯蒙》,在《易經》中是“屯卦”和“蒙卦”的并稱,大意為天地萬物之始生。你真的理解它在《易經》中的含義嗎?
葛姆雷(Antony Gormley):為此我們討論了大概兩個月。“Host”這個詞在西方文化中很特殊,指代、含義都很多重。和當初想給作品“field”找到合適的譯法一樣——最后譯成了《土地》,盡管并不準確——這次我們需要找到一個詞足夠表達“Host”的內涵。我17歲的時候就接觸到《易經》了,我認為《Host》很適合用這樣一種具自然力的語言來表達。某種程度上,水、火、空氣、泥土,這些概念是我們內在生命的物質觀照,對我來說也就是最好的語言,可以說它很詩意,但是又很準確。我以為在表達人類情感時,沒有比用你目之所及的自然界的語言更好的方式了。
三聯生活周刊:1991年你就創(chuàng)作了《屯蒙》。為什么會產生這樣一個作品概念?你個人當時處在什么狀態(tài)下?
葛姆雷:我不確定是不是1991年做的。但記得第一次展出是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頓市,想法則出現在完成第一件《土地》(1989)作品之后。《土地》試圖在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重新平衡我們和土地的關系:現代性可以說是工業(yè)化帶來的,而這種工業(yè)化一直以來卻把農民甚而捕獵者對土地的態(tài)度排除在外。對我來說,一切藝術旨在實現精神的再平衡。做《土地》的時候,我想質疑藝術家作為個體存在的現代觀念,所以我用了很多人來共同完成一件作品(注:2003年在廣州,藝術家曾動員300名村民做了近20萬個黏土泥人),并且真的是以土為料,用火燒制。做《屯蒙》的時候,我在想另一個問題:生命出現之前的原生世界是什么樣?《圣經》里,我們有自己的神話起源《創(chuàng)世記》;在《創(chuàng)世記》里,世界是陸地出現之前的無垠的海洋。所以我把“屯蒙”作為一個特定之地,去思考水、陸地以及生命的可能性。和《土地》不一樣,《屯蒙》不曾被破壞、被固化、被定型,所以它在形式上,除了建筑物的框架之外沒有其他任何結構。
為了在22年后重新展示這件作品,常青畫廊進行了空間重建。我認為這是目前為止最清晰的一次展示。作品有三個門框,每一個每一次都只能站一個人。站在門框上,你就是站在一個被構建的世界的邊緣。當內在和外在發(fā)生倒置,你就正好位于代表內外邊界的門檻上。這件作品邀請觀眾來重新平衡心和物的關系。
三聯生活周刊:在TED的一次演講中,你提到兒時總被母親約束在小屋子里,并因此默想出無限空間的經歷。你后來在作品中對門框、房間等意象反復涉及,探討人和空間兩者關系,和這種經驗有關嗎?
葛姆雷:我們能想到和感知到的一切,都由各自經歷形成。我想,早年被母親強制在下午獨處于小房間的經歷,使我最初也最直接地感受到,人在身體受限的情況下,內心卻具有可無限延伸的想象力的“矛盾”體驗。
《房間》(2014)外部:8毫米光面處理不銹鋼內部:20毫米煙橡(130毫米泡沫和膠合隔離板)1060厘米× 650厘米×790厘米永久裝置,倫敦博蒙特酒店《暴露》(2010)鍍鋅鋼第六件弗萊福蘭風景作品永久裝置,荷蘭萊利斯塔德25.64米× 13.25米×18.47 米,阿姆斯特丹
作品《屯蒙》里,門框可以視作身體的“框架”,讓你意識到身體的限制,但是你的目光又被邀請通過“框架”看向外部:在一層空間,看見的是整個展廳空空如也;在另一層空間,你又像是在俯瞰一片風景,看到地平線,看到身體所限之外的事物。我說創(chuàng)作“南宋山水畫”,也是試圖呈現這樣一種場景:在高山之上看見云的形成。但并不是對自然的再現。的確這是一件用了5萬升海水和100噸泥土的大型“水墨畫”,但對我最重要的,它是實實在在的材料,而不是什么幻想,不是技術的產物。這是把我們不能也不該控制自然的事實試圖內化到建筑之中的姿態(tài)。在嘈雜的當下,我需要這樣一種內化的姿態(tài)。
三聯生活周刊:聽說幾年前你去過云南,想在那里尋找地方做一件大型公共藝術作品。為什么放棄了計劃?
葛姆雷:我第一次去云南大概是2004或者2005年。當時確實有人問我愿不愿意在“香格里拉”做雕塑,所以我才去了趟麗江。我花了一周的時間四處游逛,和當地納西人聊天,但最后我還是決定什么都不做了,因為沒有想做的理由。如果我真要完成一件作品,我希望的是和當地人一起來實現,但在那里我發(fā)現,人們想要我作品的動機可能來自政府,或者游客,卻不是當地人。
三聯生活周刊:1971年去印度的那段經歷被認為深刻地影響了你的創(chuàng)作。“披頭士”也去過印度。那大概是當時英國年輕人最感時髦的事吧?
葛姆雷:“披頭士”比我去得早,大概是在1965年。我非常清楚地記得當時聽過一首喬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的歌,《Within You Without You》,是在《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那張專輯里。唱片封面很有意思,是各種人穿著五顏六色的制服。那也是我第一次聽到用印度西塔琴(Sitar)演奏的音樂。因為以上種種,我一心想要去印度。第一次是在1969年,進大學后的第一個長假,去待了大概幾個月。畢業(yè)之后我又立刻動身,路上大概花了一年,之后在印度待了兩年,其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和佛教徒相處。我?guī)煆母鹩】ǎF在已經去世了,當時他教我內觀靜坐(Vipassana),即全神貫注于身體感知。后來又跟卡盧仁波切學過,他是蘇納達的格魯派“黃帽”仁波切,住在喜馬拉雅大吉嶺南部的一座寺院里。
去印度當然不是我開風氣,但是我停留的時間可能比有些人要長一點,不過我也有朋友至今還留在那里。說到時髦,當年和我一起跟卡盧仁波切學習的大概有12人,超過一半的人來自歐美,剩下的是印度人或西藏人。他能同時教這么多學生也是挺令人驚訝的……我覺得其實佛教對人的強烈吸引并不完全關乎宗教信仰,不關乎它可以對著一個全能的神明祈禱,而是因為那種建立在親歷之上的天性。因此,在我這里,“正念”(mindfulness)也就是最重要的藝術理念——我所熱愛的藝術應該成為我存放“正念”的工具。藝術不是放任欲望,而是重獲平衡。
三聯生活周刊:在去印度前,你還經歷了一個對于歐洲來說相當特殊的年份:1968,和社會思潮、社會運動聯系在一起。那年你正好18歲,有什么記憶深刻的事?也影響到后來的創(chuàng)作嗎?
葛姆雷:1968~1969年,英國既發(fā)生過反對“越戰(zhàn)”與核武器的大規(guī)模示威,也有了針對移民政策的第一次游行,這些我全部參與過。當時我們是真正想要社會聽到年輕人的聲音,不僅僅為了摧毀舊秩序,也是為了進入到創(chuàng)造未來的社會結構中。我記得很清楚,那時候我正在劍橋學習人類學、考古學和藝術史,我們占領了劍橋的行政樓,要求董事會里設學生代表,還要求招收女生——劍橋其實有兩所女子院校,但都獨立于其他院校之外,我們覺得在現代體制下這是不正確的。
現在的人談起60年代,總是說中產階級或特權子弟如何放縱自我、游手好閑,我卻不這么認為。我自己從小就被父母嚴格要求言行,包括如何安排時間在內的一切事情都會受到極其苛刻的規(guī)訓。這也合乎情理,畢竟父母們都在戰(zhàn)爭期間背負過巨大壓力。60年代的人在思考很多問題,比如,重建世界之后的真正價值到底是什么?處在后殖民主義思潮和多元文化世界中的我們應該了解,西方傳統(tǒng)和天主教并不是這個世界唯一的模式,人類社會有各種各樣的形態(tài)。在我看來尤其重要的是,60年代實際上既開拓也平衡了各種訴求,成為一種嚴肅的反主流文化的起點:什么是資本主義?它的利益訴求何在?物質主義是衡量價值與進步的唯一標準嗎?
我的大部分學生時代都過著集體生活,從印度回來之后也一樣。直到現在我仍對共同合作的創(chuàng)造性的生活非常感興趣。比如目前的工作室,就是一個將合作性、集體性和創(chuàng)造性相疊加的樣態(tài),即便它是存在于高度發(fā)達的奢華的資本市場中。
三聯生活周刊:你說過,賈科梅蒂也是對你發(fā)生影響的人。我很好奇,對于當代雕塑藝術,有沒有一種雖未命名但實際存在的“賈科梅蒂主義”?就好像達達主義、立體主義。
葛姆雷:我覺得不存在,因為賈科梅蒂是不可復制的。我把賈科梅蒂看作最后一個懂得如何對待身體的重要藝術家。我也認為自己所做的是在和他進行對話。
賈科梅蒂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試圖呈現一種現實的圖景,換種說法,就是呈現一種存在于空間中的物體,以及我們在空間中與物體之間的關系、與距離的關系。他的雕塑和畫作都努力讓物體的空間能夠在某種張力下共存,這是關于視覺的現實,也是關于他記錄自己觀察行為背后的直接經驗的嘗試。我個人對賈科梅蒂的回應是:他給了我們觀察人與人之間的空間的方法,而我想去記錄活在表象背面的感覺。我關注所在,甚過所見。我更感興趣的是找到一種途徑,去感知賈科梅蒂所說的“對現實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