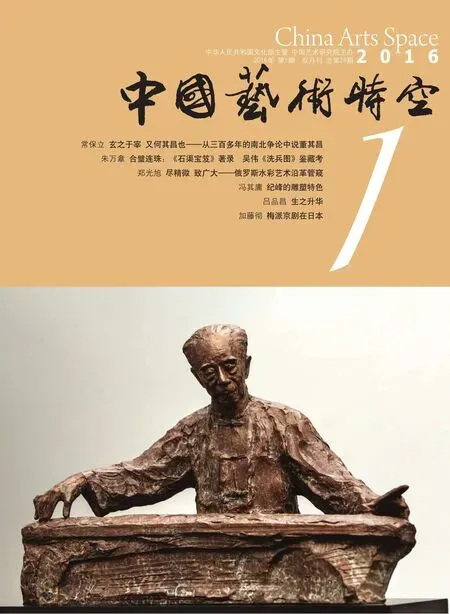疑點(diǎn)重重《女史箴圖》入英倫
徐思原
?
疑點(diǎn)重重《女史箴圖》入英倫
徐思原

【內(nèi)容提要】《女史箴圖》現(xiàn)作為大英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被保存在北區(qū),供世人瞻仰。據(jù)傳它是英國(guó)騎兵隊(duì)長(zhǎng)約翰遜贈(zèng)送給博物館的禮物,但對(duì)于這幅中國(guó)名家的作品到底如何漂洋過(guò)海安身英倫,多方史料的記載中卻存有眾多疑惑之處。
【關(guān)鍵詞】《女史箴圖》、大英博物館、約翰遜、歷史
前不久,英國(guó)好友柴特伍德(Chetwood)太太發(fā)來(lái)了一封她的外祖母留下的親筆信。信中,老人回憶了她父親約翰遜(C.A.K.Johnson)的一段往事。
約翰遜曾經(jīng)是英軍駐守孟加拉的騎兵隊(duì)長(zhǎng)。在義和團(tuán)運(yùn)動(dòng)爆發(fā)時(shí),他隨英軍一起參加了八國(guó)聯(lián)軍侵華,占領(lǐng)了北京。在駐守頤和園時(shí),他幫助了一位貴婦人躲過(guò)了義和團(tuán)的拳腳。作為回饋,貴婦人便把相傳為顧愷之真跡的《女史箴圖》送給了他。歸國(guó)后,他將這幅畫(huà)捐給了大英博物館。至今,此作仍然作為大英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被保存在北區(qū),供世人瞻仰。
這個(gè)故事聽(tīng)起來(lái)十分美好。顧愷之的畫(huà)卷無(wú)形之中成為中英兩國(guó)人民友誼的紐帶。
可是,當(dāng)我仔細(xì)查閱各方資料后,卻發(fā)現(xiàn)了與此截然不同的故事。根據(jù)大英博物館檔案館的資料,此畫(huà)卷并非約翰遜贈(zèng)予博物館的,而是1902年他來(lái)大英博物館為這幅畫(huà)的玉扣估價(jià)時(shí),博物館研究員慧眼識(shí)珠,花了25英鎊買下的。更有趣的是,據(jù)資料顯示,這幅畫(huà)卷也并不是什么友誼的禮物,而是約翰遜行竊的證據(jù)。
由此,這段戰(zhàn)亂時(shí)代不大不小的往事,因多方回憶與記敘的矛盾而最終模糊,失去原貌。
1900年,晚清政府在同治中興與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數(shù)十年間取得的果實(shí)在甲午戰(zhàn)爭(zhēng)的炮火中與北洋水師一起灰飛煙滅。同時(shí),一場(chǎng)令外國(guó)人猝不及防的農(nóng)民運(yùn)動(dòng)導(dǎo)致了北京東交民巷與天津租界的悲劇。英法美日等國(guó)趁此發(fā)動(dòng)了軍事進(jìn)攻。在北京的隆隆炮火中,慈禧攜廢帝光緒一起逃亡關(guān)隴。而此前,慈禧將故宮的大量寶物都轉(zhuǎn)移至頤和園,許多文物因此流落民間或散佚海外。
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后相當(dāng)長(zhǎng)的一段時(shí)間,中國(guó)是被歷史緊緊包裹著的國(guó)家,她是一個(gè)農(nóng)本的、相對(duì)封閉且穩(wěn)定的社會(huì)。余英時(shí)先生引古人之言用“丸之走盤(pán)”形容中國(guó)漫長(zhǎng)的古代史可謂明見(jiàn)。循環(huán)的歷史觀與朝代觀,神秘主義的天命觀,和深厚的儒家觀念是不可能隨著一聲炮火便輕易消逝的。況且清政府畢竟沒(méi)有像印度那樣徹底失去自己的行政權(quán)力。因此許多歷史學(xué)家認(rèn)為,中國(guó)社會(huì)真正開(kāi)始急劇轉(zhuǎn)變其實(shí)是在甲午戰(zhàn)爭(zhēng)甚至八國(guó)聯(lián)軍侵華以后。在甲午戰(zhàn)爭(zhēng)以前,清政府還享受了同治中興與自強(qiáng)運(yùn)動(dòng)帶來(lái)的穩(wěn)定,曾國(guó)藩、李鴻章等重臣延緩了大清的衰亡。自辛丑條約簽訂,立憲運(yùn)動(dòng)與更激烈的革命幾乎并行,不過(guò)十載,大清王朝便徹底落下帷幕。
而約翰遜在這個(gè)中國(guó)歷史真正的轉(zhuǎn)折點(diǎn)上來(lái)到了中國(guó)。這是他的幸運(yùn),亦是他的不幸。他的幸運(yùn)在于,彼時(shí),他屬于帝國(guó)主義侵略者的陣營(yíng)。列強(qiáng)來(lái)到中國(guó),除了名義上對(duì)在華外國(guó)人提供保護(hù),其實(shí)更多的是為了掠奪戰(zhàn)利品,并進(jìn)一步攫取在中國(guó)的特權(quán),為擴(kuò)張期的帝國(guó)主義經(jīng)濟(jì)尋找更廣闊的投資市場(chǎng)。無(wú)論約翰遜先生個(gè)人意愿是否與貪婪的英政府一致,毫無(wú)疑問(wèn),他本身就是大英帝國(guó)對(duì)外侵略戰(zhàn)爭(zhēng)的一顆棋子,并且享受了列強(qiáng)勝利的果實(shí)。而這種時(shí)代的幸運(yùn)其實(shí)也造就了他的不幸:與勞爾·卡斯特羅的劃時(shí)代的演講題目恰恰相反,歷史會(huì)因他的集體歸屬而宣判他有罪。那個(gè)“英雄救美”的故事,本身疑點(diǎn)頗多。比如,一個(gè)深受中國(guó)傳統(tǒng)尊君思想束縛的貴婦人如何敢于從頤和園的皇家藏品中竊取畫(huà)卷并送與一個(gè)“夷人”?再者,大英博物館詳實(shí)的檔案難道會(huì)將“捐贈(zèng)”與“購(gòu)買”隨意混淆?其實(shí),不需過(guò)多的考證,每個(gè)人心中都能想見(jiàn)較為合理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歷史學(xué)家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他的著作《帝國(guó)的時(shí)代》中寫(xiě)道:“對(duì)于我們所有人來(lái)說(shuō),在歷史和記憶之間都有一塊很不明確的過(guò)渡區(qū)。這塊過(guò)渡區(qū)是介于兩種過(guò)去之間,其一是可相對(duì)不帶感情予以研究的過(guò)去,其二是摻雜了自身的記憶與背景的過(guò)去。”人是歷史的動(dòng)物。人之所以區(qū)別于其他生物,就在于人的生活是自覺(jué)的。人類面向未來(lái)的繁星,又不斷拾起身后的貝殼。因此,可以說(shuō),正是記憶成就了人類的偉大。但是,正是記憶的不確定性讓過(guò)去成為永恒的謎題。人在兩種記憶的過(guò)渡區(qū),將事實(shí)與個(gè)人情感融合成一個(gè)奇異的混合體,而當(dāng)來(lái)自不同個(gè)體的此類記憶通過(guò)書(shū)面、口述等形式被聚集在一起時(shí),我們一般意義上的“歷史”也就形成了。記憶是事實(shí)在“哈哈鏡”里變形的鏡像。當(dāng)后世學(xué)人想要去重新發(fā)現(xiàn)并還原過(guò)去時(shí),便又要帶著盡可能少的偏見(jiàn)去撥開(kāi)迷霧。透過(guò)偏見(jiàn)去尋找真相,這也許就是歷史學(xué)存在的理由。
《女史箴圖》一定不曾想到,自己會(huì)經(jīng)歷16個(gè)世紀(jì),輾轉(zhuǎn)于米芾、宋徽宗、嚴(yán)嵩、董其昌、乾隆等風(fēng)流人物之手,最后竟隨著一個(gè)不知名的英軍駐孟加拉騎兵隊(duì)長(zhǎng),漂洋過(guò)海,安身英倫。歲月磨蝕了它當(dāng)初的容貌,漫卷的裂紋和褪去的墨色已經(jīng)成為歷史最精致的雕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