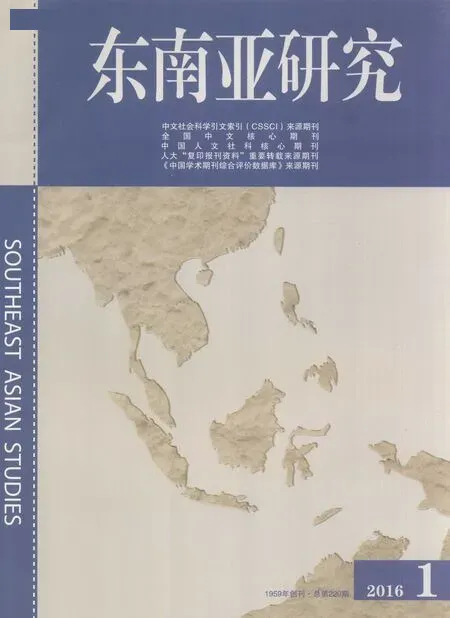西屬菲律賓天主教與華人社會關(guān)系的延展與重構(gòu)
呂俊昌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 廈門 361005)
?
西屬菲律賓天主教與華人社會關(guān)系的延展與重構(gòu)
呂俊昌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廈門 361005)
[關(guān)鍵詞]菲律賓;華人;天主教;西班牙殖民者;社會關(guān)系
[摘要]西班牙殖民時期,面對占主導地位的天主教意識形態(tài),菲律賓華人教徒充分利用了天主教所賦予的制度文化資源,建立了與西班牙殖民者、天主教會以及菲律賓人的聯(lián)系,同時也鞏固了華人族群自身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拓展了華人的生存和發(fā)展空間。菲律賓華人教徒巧妙整合自身與異質(zhì)文化的實踐過程充分反映了華人的靈活性與適應性。
The Catholicism and Chinese Social Relations’ Extens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Lv Junchang
(Research School for Southeast Asia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e Catholic Chinese made full use of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resources given by the Catholicism,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relations with the Spanish colonists,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natives, at the same time strengthened the Chinese ethnic network, and expanded space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n the Spanish Philippines, in response to the dominant ideology. The Catholic Chinese’s practice process which ingeniously integrating of their own and the heterogeneous culture fully reflects the flexibility and adaptability of themselves.
菲律賓是亞洲最重要的天主教國家。西班牙殖民時期(1565—1898),使所有人都成為“上帝的子民”與“西班牙國王的臣民”是天主教會與殖民當局的宗旨,這其中也包括鼎盛時期多達兩三萬的華人移民。據(jù)統(tǒng)計,在整個西屬時期,華人天主教徒最多時有三四千人。華人移民如何面對菲律賓的天主教這種主流意識形態(tài),也是菲律賓華人史的重要內(nèi)容。目前,關(guān)于菲律賓華人史的研究主要側(cè)重政治與經(jīng)濟方面,對于宗教文化層面特別是華人與天主教關(guān)系的研究仍不多見①參見施雪琴《西班牙天主教語境下的宗教政策——16-18世紀菲律賓華僑皈依天主教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因此,本文將從歷史的角度探討華人教徒如何利用、整合天主教的機制,拓展自身生存和發(fā)展空間的過程,以期對當代菲律賓社會的政治與文化生態(tài)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鑒。
一教親制與華人社會關(guān)系的重構(gòu)
根據(jù)天主教禮儀,每個人在受洗時都有權(quán)獲得教父(padrino)和教母(madrina)的保護。這種教父母制或曰教親制(Padrinazgo,西語Compadrazgo,Compadre又被華人音譯為“公巴列”),也就是俗稱的干親制[1],國內(nèi)天主教會一般稱為代父、代母關(guān)系。教父母的設計可能是基于習慣法。按照天主教會的說法,“一個人除了與自己的父母或子女存在血緣關(guān)系之外,還要與其他特定之人保持靈修關(guān)系(spiritual relationship),在這些人的協(xié)助之下使自己的身心得到修持,進而達到終極圓滿之境界。就單個人而言,能夠幫助自己善度宗教生活的有靈修關(guān)系之人主要是教父、教母,以及為自己施洗之人(主教或神父)和為自己施加堅振禮*堅振禮(Confirmation),是天主教的七大圣事(洗禮、堅振禮、圣餐禮、告解禮、婚配禮、終敷禮、授神職禮)之一,一般是受洗的嬰兒在達到能夠運用理智的年齡時,由主禮者在其頭上覆手,再以圣油敷其額頭,并念“請借這印記,領受神恩”,以此堅固其信仰。此禮也是受洗者重新宣示信仰,開始承擔相應的宗教和世俗責任的體現(xiàn),在某種程度上是受洗者的成年禮。——筆者注之人(主教、神父或教父母)。”[2]1563年11月的特蘭特圣公會議第24次會議對建立靈修關(guān)系的人員作了嚴格限制:“一個人在受洗之時,只能有一個人或最多只有2人充當受洗之人的教父或教母,以教父母以及受洗者為一方,以受洗者的生身父母為一方,兩者之間建立靈修關(guān)系;另外,以施洗者和受洗者為一方,以受洗者的生身父母為另一方,二者之間也將建立靈修關(guān)系。”[3]所以,受洗既是一種精神的再生,也是原本無血緣關(guān)系的施洗者、教父母與受洗者及其父母之間精神上的、虛擬的親屬關(guān)系的確立。
不過,在天主教傳播的過程中,上述幾方關(guān)系在不同地區(qū)各有側(cè)重。在西方,嬰兒出生即受洗的家庭中,教父母與受洗的子女和同樣為教徒的親生父母形成一種三角關(guān)系。在菲律賓,更受重視的是教父母與親生父母的互動關(guān)系,同時,教親制所覆蓋的人數(shù)也有所增加,收養(yǎng)教子(godchildren)的機會也比特蘭特圣公會所確定的頻次多得多,諸如子女的首次剃發(fā),新房的竣工都可以成為收養(yǎng)教子的契機。而菲律賓的父母更傾向于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教父[4]。由此,差不多是同代人的教父母與父母之間便建立了一種功能性的社會關(guān)系。
(一)成年華人教徒與教父之間的關(guān)系
在馬尼拉華人社會中,情況又有所不同,因為許多受洗的華人是成年人。據(jù)統(tǒng)計,在1616—1628年受洗的1331名華人都是成年男子[5]。這些人父母大多在中國,當然也不是教徒。這樣,教父母與教子之間便建立起了基于義務和責任的關(guān)系。歷史上,多是單身出洋的華人在異國他鄉(xiāng)建立各種社會組織,比如秘密會社、宗親會、方言組織、地緣組織、行業(yè)公會,或者宗教組織等,都算是一種虛擬親屬(mock-kinship)機制[6]。正是這些社會組織起到了互相幫扶、建立和維護商業(yè)網(wǎng)絡的作用。但上述組織多屬華人內(nèi)部的合作關(guān)系,而與西班牙人建立的教父教子關(guān)系,可謂建立跨越族群的社會關(guān)系的嘗試。
一方面,一些西班牙人經(jīng)常并且樂意充當華人,特別是富裕的華人的教父,并且賜予教名。17世紀初的華人監(jiān)督Juan Bautista de Vera(原名Eng Kang)的教父就是菲島第六任總督Santiago de Vera(1584—1590年在任)[7]。1618年11月22日,F(xiàn)r. Bartolome Marti神父在邦加斯蘭省凌牙延的三王教堂為一名31歲的福建舢板船主施洗,該省省長Don Eronimo Alcaraz擔任其教父[8]。1627年5月14日的一項記載表明,華人木匠Josep Tien Choan的教父地位僅次于總督。實際上,在西屬菲律賓,當時的趨勢是所有上層官員,無論是來自行政部門還是軍事機構(gòu),都爭著去給華人新教徒充當教父[9](原因參見下文)。比如Juan Nino de Tavora總督在16世紀20年代至少有3個華人教子,其中一人是木匠公會的首領,另一個后來成為華人天主教社區(qū)的教父。反過來,擁有有實力的教父這層關(guān)系對華人而言也是一種有力的庇護。
另一方面是華人教父與華人教子的關(guān)系。當華人教徒的社會地位和實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時,他也會成為一個有吸引力的教父。從1626年到1700年,華人社區(qū)八連(Parian)中以華人為教父者占80%(2326人),西班牙人占16.3%(473人),菲律賓土著及密斯提佐僅占3.52%(107人)[10]。不難看出華人教徒對來自同族群的教父的偏愛。19世紀后期著名的華商陳謙善(Carlos Palanca Tan Quien-Sien)曾擔任好幾個人受洗時的教父,而且其中除第3人由于資料缺失不明確外,剩余5人均采用了陳謙善的教名Palanca[11]。具體信息如下:
Mariano Palanca Yap Tamco,1874年7月14日在Pandacan 教堂受洗;
Joaquin Palanca Cotuanco,1874年7月18日在Dilao的圣費爾南多堂區(qū)受洗;
Manuel Yu-Tayco,1878年1月27日受洗;
Ambrocio Palanca Tan-Chioco,1879年12月7日在岷侖洛(Binondo)教堂受洗;
Joaquin Palanca Cue Jongting,1882年9月24日受洗。
Carlos Palanca Tan Quin-lay,1869-1950年,受洗時間不明。
不過,有地位的教父數(shù)量相對教徒來說始終是少數(shù),所以一名教父擁有許多教子的情況非常普遍。據(jù)記載,八連受洗記錄中,一名教父的教子數(shù)量竟然達到141名,另有3名教父擁有超過50名的教子。其余22名教父擁有10名或更多的教子[12]。另一種情況是許多教子擁有不止一位教父,這可能是華人在受洗或堅振時分別請不同的人當教父,或者原本受洗時教父數(shù)量就不止一個,這種情況可能是違規(guī)的。
那么華人教父與教子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關(guān)系?以福建同安人Domingo Zuiteng為例,他在1627年6月(時年45歲)時受洗,在其14名教子中,除3人外都是成年人,其中7人是同安人;4名已注明職業(yè)的成年教子中的3人是來自同安,其中2人為木匠,另1人為零售商。而1626—1636年間來自同安的木匠中除一人之外都受洗了。正如前人研究所證實的,馬尼拉面包店的工人包括店長在內(nèi)都是來自一個叫福建三都(Sandu)的地方[13]。有些想要留在菲律賓的華人,在西班牙人驅(qū)逐不信教華人時便匆忙信教,繼而堂而皇之地在各個華人同業(yè)公會的頭家手下干活[14]。由此觀之,教親關(guān)系的確立與職業(yè)、祖籍地聯(lián)系密切。華人教徒更樂于讓來自同一祖籍地、社會地位更為優(yōu)越的同鄉(xiāng)擔任自己的教父。這種基于業(yè)緣或地緣的教親關(guān)系的確立,已經(jīng)超出原本的靈修意義上的邊界,顯然會讓華人教徒的社會關(guān)系更為廣闊,也更加穩(wěn)固。
(二)因嬰兒受洗而建立的三方關(guān)系
此處所謂嬰兒,是指華人與菲律賓婦女通婚的后代混血兒密斯提佐(Chinese mestizo)或混血女密斯提薩(mestiza)。按照天主教的規(guī)定,嬰兒出生后幾天就會受洗,“生孩三朝,即報至拜禮院,請拜禮命名。”比如華商夫婦Ignacio Sy Jao Boncan和 Francisca Yap的幾個子女均是在出生三四天內(nèi)受洗,其子女的教父、教母或是華人教徒,或是密斯提薩。1868年11月25日出生的女兒Fermina次日即由神父主持受洗,并請Pascuala Yap擔任其教母[15]。
教父母作為其教子女精神上獲得重生的見證人,除負責精神上的引導和信仰上的維護外,在生活中也扮演著類似監(jiān)護人的角色,假如教子女的親生父母在其未成年時即去世,教父母應承擔撫養(yǎng)義務[16]。所以,新生兒的降生在兩個家庭之間充當了類似傳遞者的角色,是兩者之間關(guān)系的有形的、活生生的證明[17]。以下是一個華菲密斯提佐家庭(父親:Diego de Paciencia Ang Quimco,母親:Petronila de Jesus)從1678年至1693年所生子女的教父、教母情況。

17世紀后期一個華菲密斯提佐家庭子女的教父母情況
資料來源:該案例來自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博士候選人Joshua Kueh的相關(guān)研究,感謝該作者提供資料。參見Joshua Kueh,“Adaptive Strategies of Parián Chinese: Fictive Kinship and Credit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nila ”,PhilippineStudies,Vol.61, No.3, 2013,p.369.
從表1可見,兩名男孩只有教父,而女孩除一人外均有教母,而最初的兩名女兒均有教父、教母。從教父姓名后綴(以閩南話的哥/co結(jié)尾)可猜測,所有子女的教父差不多都是華人教徒,僅Luis de Gaspar無法判斷其出身。母親與這些教母之間是何種關(guān)系并不可知,但顯然與Dorothea Mauricia比較密切,因為后者是她兩名女兒的教母,Maria de la Concepción與Theodora de la Concepción有可能出自同一家族。值得注意的倒是沒有教母只有教父的女兒Laura Chitnio,從她的名字Chitnio以及家庭的排序來看,正是閩南話中的“七娘”,這一點在其他兄弟姐妹中格外與眾不同。Joshua Kueh提示,實際上Laura Chitnio在1688年出生時,Diego剛好被賜予了堂(Don)的尊稱,“以富有華人特色的方式取名是否反映了Diego與當時華人社會的密切聯(lián)系,或者說是想與華人教父建立一種策略性的關(guān)系?”[18]這些都不得而知。總之,取名也是一種社會性的策略和選擇。在教親制度下,多子女的家庭也意味著更廣闊的社會關(guān)系,不同時期的教父教母關(guān)系也可能存在深淺之別。
二華人習俗與天主教傳統(tǒng)的內(nèi)在契合
盡管教親制是教會規(guī)定,但在實際操作中,華人收養(yǎng)教子的一些做法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西班牙人的不滿和譴責。1599年5月17日,馬尼拉最高法院主席和審計員審查了敦洛(Tondo)區(qū)長提交的關(guān)于華人教徒之間大量收養(yǎng)教子的報告。其中指出,“華人教徒在發(fā)生緊急事件時利用這些不管是天主教徒或異教徒的教子,充當假證人,或者滿足其他罪惡的目的和企圖。”西班牙人為此發(fā)布禁令:“任何生理人(Sangley,西班牙人對華人的稱呼),不論其地位、等級,只要被發(fā)現(xiàn)擅自擁有教子或擔任教父母,將被判在大帆船上無償劃槳4年。敦洛及其護衛(wèi)區(qū)的長官以及其他所有法官均要特別注意實施和執(zhí)行此法令。”*Blair & Robertso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493-1898,C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1909,Vol.11,pp.75-77. 已有學者注意到此材料,不過并未注明西班牙人采用的是教子(godchildren)的概念,而是作義子處理。參見錢江《古代亞洲的海洋貿(mào)易與閩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西班牙人的反對在于華人利用教親制擅自收養(yǎng)不信教的華人教子,并且動機不純。所謂“罪惡的目的”實際另有所指。1584年7月,某西班牙官員就致信菲利普二世,請求懲處華人在他們的船上發(fā)生的“聲名狼藉的罪名”,“將這些卑鄙的人驅(qū)逐出去”[19]。這里的罪惡指的都是同性戀或雞奸(sodomy)行為。耶穌會也曾被托缽修會指責“雇傭耽于雞奸的華人在莊園中勞作”[20]。如果考慮到歷史上的華人移民多是閩南地區(qū)的單身男子,男女比例懸殊,那么也不排除華人之間的確存在同性戀的行為。“漳人以彼為市,父兄久住,子弟往返,見留呂宋者蓋不下數(shù)千人”[21]。不明實情的西班牙人認為華人之間過從甚密,有違教義,為此采取了一些嚴厲的舉措,“呂宋,最嚴狡童之禁,華人犯者,以為逆天,輒論死,積薪焚之”[22]。《海國聞見錄》的描寫更為細致:“禁龍陽(按:同性戀的代稱),父子、兄弟亦不得共寢席,夜啟戶,聽彼稽察;拭床席驗有兩溫氣者,捕以買(責)罰。”[23]“禁龍陽,倘被獲,二人俱以柴圍而火之。”[24]
王劉波曾經(jīng)對華人之間所謂的同性戀現(xiàn)象及其事實真相進行了分析,認為此種觀念的形成與閩南人由于出海貿(mào)易需要而結(jié)成的契父子、契兄弟關(guān)系,也就是所謂收養(yǎng)義子、結(jié)拜兄弟的現(xiàn)象有關(guān)[25]。筆者基本同意此種看法。在閩商文化的研究中,相關(guān)學者已經(jīng)注意到這一閩商文化的重要特征[26]。所謂義子,包括宗親子弟、他姓窮苦人家、家仆或者招贅的女婿,而結(jié)拜兄弟之間也會成為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比如著名的李旦與歐陽華宇。當時士大夫階層也認可之,“借人錢本令的當兄弟或義男營運生理,此決不害義”[27]。地方志中也有言曰:“閩人多養(yǎng)子,即有子者,亦必抱養(yǎng)數(shù)子,長則令其販洋賺錢者。”[28]閩南商人中的這種“螟蛉子”、“契子”角色相當于代表其收養(yǎng)家庭出洋貿(mào)易,也可以稱為代理商。毫無疑問,這種密切的、虛擬或延展的親屬關(guān)系延伸到海外華人社區(qū),無形之中擴大了家族的規(guī)模,有利于閩商貿(mào)易網(wǎng)絡的擴展。
但更深一層的意義在于收養(yǎng)義子是閩南習俗,教親制是天主教的社會習俗,兩種習俗恰好存在契合的空間:其一,為華人教徒擔任他人教父,建立教親關(guān)系創(chuàng)造了良好的文化環(huán)境。其二,留下了制度空隙。華人教徒完全可以在西班牙人不懂內(nèi)情的前提下,以擔任教父的名義收養(yǎng)未入教的華人為義子。西班牙人大概也發(fā)覺不信教華人擁有教父這種令人疑惑的現(xiàn)象,才以一種矯枉過正的方式斷絕華人非血緣關(guān)系的建構(gòu)。當然這也表明,西班牙人雖然鼓勵華人受洗,可是也對華人充滿了不信任感,擔心華人內(nèi)部的團結(jié)威脅自身的統(tǒng)治。但實際上,華人教徒仍然大量擔任他人的教父或者是義父,在1603 年華人所遭遇的大屠殺慘案中,眾多被收養(yǎng)的教子或義子加入到反抗西班牙人的華人行列。在華人首領Eng Kang(西名Juan Bautista de Vera)被西班牙人關(guān)入監(jiān)獄后,其教子Juan Suntay(或名Juan Ontal)就被推選為起義首領[29]。故而這一習俗并非殖民當局一紙指令就可以輕易禁止的。
正如國外學者指出的,華人被污名化為“耽于雞奸者”,本質(zhì)上是西班牙殖民者中的反華者對華人的責罵和偏見而已[30]。背后的問題在于,正是由于閩南習俗與天主教的習俗具有的一致性,華人才可以毫不費力地接受天主教的教親制,利用這種雙重的制度文化,拓展其虛擬的親屬關(guān)系網(wǎng)絡和自身的生存空間。
三華人教徒與殖民當局、教會間的經(jīng)濟、社會關(guān)系
教會與華人之間不僅僅是宗教上的關(guān)系,還有密切的經(jīng)濟和社會往來。首先,華人所繳納的費用是殖民當局及教會等機構(gòu)相關(guān)經(jīng)費的來源。八連教堂的建設資金來自于教徒和非教徒所繳納的公共基金,西班牙稅務員的薪金也來自于此[31]。華人教徒通過捐獻的形式為教會和殖民當局提供資金,后者則賜予其身份和地位,或者一些神父會直接或間接以儲蓄的名義投資于華商的生意[32]。由此,雙方建立了密切的關(guān)系。
以華人密斯提佐Tuason家族為例,該家族的第一代Antonio Tuason在1756—1783年擔任華人密斯提佐的甲必丹和城市民兵的上校,為西班牙海軍、皇家倉庫以及教堂和辦公建筑的修繕提供經(jīng)費,在1762—1764年英軍入侵期間為西班牙軍隊提供裝備費用,也同樣支持西班牙人在南部對摩洛人的戰(zhàn)爭。除此之外,他還替教會圣職人員支付一半(大約8800里爾)的職祿獻金(Annates)*Benito J.Legarda,After the Galleons: Foreign Trade, Economic Change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Philippine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1999,p.230.1199年,教皇英諾森三世規(guī)定將擔任圣職者第一年收入的全部(實際操作中為一半)獻給教皇作為其批準任命的費用。參見〈美〉威爾·杜蘭特著,臺灣幼獅文化譯《信仰的時代》,華夏出版社,2010年,第802頁。。為了表揚其忠誠,西班牙國王在1775年免除了他們兩代人的賦稅,8年后又提升他為貴族,配有顏色鮮艷的盾徽。Tuason家族也成為唯一沒有西班牙血統(tǒng)的菲律賓貴族[33],許多西班牙人移民也與其家族后代通婚。
其次,對華人來說,受洗入教可以結(jié)識一個身為保證人、貸款者、贊助人和法律事務的保護者的教父[34]。以一位西班牙人或本地權(quán)貴為教父,華人天主教徒就有機會獲得各修會和慈善團體(Obras Pias)提供的信貸資源。在19世紀銀行創(chuàng)辦以前,信貸都由慈善機構(gòu)執(zhí)行。華人只有受洗以及建立與掌握慈善基金的贊助人的關(guān)系,才能獲得信貸資金[35]。這些慈善基金最初來自富商和虔誠的教徒的捐獻,除用于賑濟孤寡、撫恤貧弱等慈善事業(yè)外,便是用于商業(yè)投資、地產(chǎn)經(jīng)營、大帆船貿(mào)易的投資,管理方為平信徒和神職人員,多明我會、方濟各會等修道會在這些慈善團體管理上握有領導權(quán)[36]。
第三,華人與西班牙人之間存在直接的商業(yè)往來。在馬尼拉周邊定居的華人,每周將蔬菜、家禽運送到西班牙人家中或者教會;作為回報,華人從西班牙人那里獲得保護[37]。即使在菲律賓總督?jīng)Q議驅(qū)逐華人移民期間,仍有華人(信教以及不信教者)為皇家倉庫(Royal Warehouse)提供椰油、熟鐵等貨物[38]。或者總有強有力的保護者(實際上是既得利益者)違背驅(qū)逐令而允許華人在城鎮(zhèn)居住、經(jīng)商及工作,甚至修道士也支持他們,給予華人許可證,證明他們正在參與修建教堂或修道院。1661年,當鄭成功檄文馬尼拉而引發(fā)菲島對華人的猜忌和憤恨時,耶穌會還曾到殖民當局那里替華人求情[39]。
第四,華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護與菲島的管理機制相關(guān)。在菲律賓,除了最高法庭之外,還有民政法庭與宗教法庭,分別審理不同案件,有些案件涉及雙方,難免引起摩擦。更有甚者,犯罪者在遭到追捕后往往躲入教堂或其他圣地,而依島上所行法令,凡奔至圣壇所在地者,民政長官不得以強力拘捕[40]。菲律賓人的首位圣徒、實際上是華菲混血兒的洛倫佐(Lorenzo Ruiz),生前曾因卷入一件殺人案件而遭到馬尼拉市政當局的逮捕,后來在多明我會神父的幫助下才免受處罰[41]。不排除洛倫佐與教會之間有私人關(guān)系,但是教會對華人在一定程度上的保護對華人也是有利的。換言之,或許只有在總督、教會、法院三大機構(gòu)之間利益沖突時,華人的利益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照顧。
當然,華人教徒與殖民當局、教會之間的社會關(guān)系也有遭人詬病的地方和灰色的空間。1880年代的一個西班牙人就譴責“這些莫名其妙的教父母關(guān)系”[42]。泉州安海籍華人Don Juan Feilipe Tiamnio(約1639年生)經(jīng)商成功后變?yōu)榭偠絁uan de Vargas的知己和常客,他被任命為華人社區(qū)八連的首領和海關(guān)通事,有謠言稱他低價為總督及其親屬購買中國產(chǎn)品。某西班牙人嘲諷道:“華人知道如何用禮物迎合西班牙人的心思,所以沒有什么事情是兩三天內(nèi)不能解決的!”神父Fray Plácido de Angulo觀察說:“當生理人到達各省后,將從中國帶來的禮物和水果給各市的市長,多次拜訪他,承諾如果幫助他在省政府中謀取職位,就會提供許多資金。”有時華人的賄賂是為了使當局對自己從事的賭博或戲劇表演等活動網(wǎng)開一面,但由此也讓西班牙人賺得滿盆[43]。
不過,問題在于,西班牙人殖民體制的弊端讓華人的行賄無拘無束,西班牙學者胡安·吉爾(Juan Gil)指出,殖民當局根本無法提供充足的工資,而他們最有利可圖的便是將手伸向華人社會,所以腐敗和貪污才甚囂塵上。在西班牙殖民當局對來菲華人船貨實行“整批交易”過程中,掌握貨物定價權(quán)的官員會利用華人想要提高價格的心理趁機索取賄賂,或者以低價任意拿走最好的貨物;也有一些不滿足于被分配到的貨物的西班牙人在正式議價之前,與華人暗中交易,自己破壞這種制度[44]。早在17世紀初,Benavides大主教就指出:“我們的貪欲造成了這一切!”[45]但長此以往,華人(包括教徒)給人的可以通過金錢趨利避害的印象卻愈加深刻,華人便成為破壞西班牙人公正執(zhí)法的罪魁禍首。能夠基于共同利益而“密謀”的應該大部分是富裕華商,他們本是無奈之舉,可是,由此產(chǎn)生的負面因素卻波及華人社會的中下層移民,從而使人對華人社會整體產(chǎn)生不良的印象。
四從婚姻角度看華人族群內(nèi)部社會關(guān)系的建構(gòu)
通婚是華人與菲律賓人社會關(guān)系的重要方面。西班牙人允許并且鼓勵受洗的華人與當?shù)貗D女結(jié)婚。隨著華人和密斯提佐社會地位的提升和財富的增長,他們對菲律賓婦女及密斯提薩也越來越具吸引力。根據(jù)1870年、1875年、1880年、1885年的華人男性的通婚比例來看,在146對夫婦案例中,72對、接近50%的比例是華人男子與密斯提薩結(jié)婚,華人男子與土著婦女結(jié)合的人數(shù)是69對(47%)[46]。顯然,華人選擇結(jié)婚對象時一般傾向于密斯提薩和土著婦女。婚姻關(guān)系也是華人教徒間維護和鞏固社會關(guān)系的重要途徑。在著名的華人混血兒社區(qū)岷侖洛,同一階層、職業(yè)或者地位相當?shù)娜A人家庭間通婚十分普遍。比如,華商陳謙善的女兒嫁給了Ignacio Jao Boncan之子,Joaquin Barrera Limjap的密斯提佐兒子娶了密斯提佐Pedro Escolar Cochay之女,而后者的另一個女兒嫁給了Ignacio Jao Boncan的孫子[47]。
菲律賓華人在選擇婚姻見證人時,更傾向于選擇住在同一地區(qū)或者來自同一職業(yè)、而非名義上來自同一祖籍地的華人,由此成功地拓展了社交空間。比如以下的例子:住在八連的Pantiangco是來自漳州龍溪的31歲蔬菜商販,他在1755年菲律賓總督規(guī)定的最后受洗日(6月30日)受洗入教,三年后申請與混血女Augustina結(jié)婚。他的兩名結(jié)婚見證人都是在八連生活的漳州海澄人,其中一人為Sebastian Chanco,55歲,制糖師傅;另一名為Gaspar Chicenco,40歲,也是蔬菜商販。而Gaspar Chicenco也是另一名蔬菜商販Antonio Tanjoco的見證人,后者來自泉州同安。Tanjoco的另一名見證人Thomas Leongco,祖籍泉州安海,是Bagumbaia的蠟燭商,結(jié)婚后從圣克魯茲搬到了他妻子所住的Bagumbaia。Leongco的見證人之一是來自龍溪、定居在圣克魯茲的理發(fā)師Julian Chinco,而他也擔任另一名華人Pablo Sim Saco的見證人。而Pablo Sim Saco來自福建汀州,Saco有3位見證人,除了龍溪人Chinco外,另外兩名見證人則來自廣東[48]。總之,盡管Pantiangco與最后不知姓名的廣東人之間沒有直接的聯(lián)系,但是他們卻通過選擇婚姻見證人這種形式,通過一長串的關(guān)系的延伸,建立起了跨越祖籍地的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
結(jié)語
總之,天主教不僅僅是一種信仰,也包含一套實踐體系與多種社會功能[49],成為天主教徒對華人而言是一種精明的社會和經(jīng)濟策略。華人充分利用了天主教所賦予的制度文化資源,建立了與殖民者、天主教會以及菲律賓人的聯(lián)系,同時也鞏固了華人族群自身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西屬菲律賓社會這種注重社會關(guān)系的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的民間社會文化有異曲同工之妙,華人教徒巧妙整合自身與異質(zhì)文化的實踐,充分反映了華人的靈活性與適應性。但另一方面,由于西班牙人文化上的“傲慢與偏見”以及殖民體制的不完善,華人在拓展社會關(guān)系網(wǎng)絡的過程也遭受了西班牙人的指責和阻礙,而由此產(chǎn)生的華人基于共同利益的“密謀”行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華人不得不適應這種不完善體制的無奈之舉。由恩主與侍從(patron-client)關(guān)系確立的庇護體制,在當代菲律賓政治與社會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庇護體制的核心是權(quán)力與互惠,天主教文化與此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50]。從這個角度而言,天主教影響下華人社會關(guān)系的重構(gòu)與華人教徒的經(jīng)驗,或許有進一步思考的意義和價值。
【注釋】
[1] 姚楠主編《東南亞歷史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5年,第14頁。
[2] 沃特沃斯英譯,陳文海譯注《特蘭特圣公會議教規(guī)教令集》,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224頁。
[3] 同[2],第225頁。
[4] John Leddy Phelan,TheHispanizationofthePhilippines:SpanishAimsandFilipinoResponses,1565-1700,Madison,Milwaukee: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67,p.77.
[5] Alfonso Felix,Jr. eds.,TheChineseinthePhilippines,1770-1898,Vol.2, Manila: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 1969,pp.55-56.
[6] John Clammer,DiasporaandIdentity:theSociologyofCultureinSoutheastAsia, Suba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2002,p.164.
[7] Blair & Robertson,ThePhilippineIslands,1493-1898,Cleveland:The Arthur H. Clark Co., 1903-1909(abbr.BR),Vol.16,p.291.
[8] Susan L.Pe,“The Dominican Ministry Among the Chinese in the Parian, Baybay and Binondo:1587-1637”,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1983,p.65.
[9] Alfonso Felix,Jr.,op.cit.,p.55.
[10] Joshua Kueh, “Adaptive Strategies of Parián Chinese: Fictive Kinship and Credit in Seventeenth-Century Manila”,PhilippineStudies,Vol.61, No.3, 2013.
[11] Richard T. Chu,ChineseandChineseMestizosofManila:Family,IdentityandCulture,1860-1930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pp.128,135.
[12] Joshua Kueh, op.cit..
[13] Ibid.,p.368.
[14] Nariko Sugaya, “The Life of Chinese Immigrants in Late Eighteenth-century Manila”,尼古拉斯·托馬斯、聶德寧主編《東南亞與中國關(guān)系:持續(xù)與變化》,廈門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頁。
[15] Richard T. Chu, op.cit.,p.185.
[16] 施雪琴:《菲律賓天主教研究:天主教在殖民地的殖民擴張與文化調(diào)試》,廈門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23頁。
[17] Raul Pertierra & Eduardo F. Ugarte eds.,CulturesandTexts:RepresentationsofPhilippineSociety,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1994,pp.50-52.
[18] Joshua Kueh, op.cit.,p.370.
[19] BR,Vol.6,p.63.
[20] BR,Vol.12,pp.109-110.
[21] 許孚遠:《疏通海禁疏》,陳子龍輯《明經(jīng)世文編》卷400,中華書局影印本,1962年,第4332頁。
[22] 張燮:《東西洋考》卷12,《逸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249頁。
[23] 陳倫炯著,李長傅校注《海國聞見錄》,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43頁。
[24] 葉羌鏞:《呂宋記略》,王錫祺輯《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再補編第10帙,第76冊,上海著易堂印行,1897年,第2a頁。
[25] 王劉波:《16-17世紀菲島殖民者視角下的華僑同性戀現(xiàn)象與事實真相》,《“2014年海外華人研究研究生論壇——全球化與華人研究:新視野、新取向及新典范”論文集》,廈門大學,2014年,第38-54頁。
[26] 錢江:《古代亞洲的海洋貿(mào)易與閩南商人》,《海交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7] 蔡清:《蔡文莊公全集》卷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第42冊,齊魯書社,1997年,第627頁。
[28] 周凱:《廈門志》卷15,臺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327頁。
[29] José Eugenio Borao, “The Massacre of 1603: Chinese Perception of the Spaniards in the Philippines”,Itinerario, Vol.23, No.1, 1998,p.8; Edgar Wickberg,TheChineseinthePhilippinesLife,1850-1898,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1965,c2000, p.16.
[30] John L.Phelan, op.cit.,p.186.
[31] BR,Vol.23.p.231.
[32] Richard T. Chu, op.cit.,pp.171-172.
[33] Luciano p.R.Santiago,ToLoveandtoSuffer:TheDevelopmentoftheReligiousCongregationsforWomenintheSpanishPhilippines,1565-1898, Quezon Cit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2005,p.161.
[34] Edgar Wickberg,op.cit., p.191.
[35] 魏安國著,吳文煥譯《菲律賓歷史上的華人混血兒》,馬尼拉:菲律賓華裔青年聯(lián)合會,2001年,第69-70頁。
[36] Robert R.Reed,HispanicUrbanisminthePhilippines:AstudyoftheImpactofChurchandState,Manila: The University of Manila Journal of East Asistic Studies,1967,pp.140-141.
[37] O.D.Corpuz,TheRootsoftheFilipinoNation, Vol.1,Quezon City: The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Press,2005, pp.305-306.
[38] Alfonso Felix Jr.,TheChineseinthePhilippines,1550-1770,Vol.1,Manila: Solidaridad Publishing House,1966,pp.201-204.
[39] 博克塞(C.R.Boxer)著,楊品泉譯《歐洲早期史料中有關(guān)明清海外華人的記載》,《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83年第2期。
[40]張星烺:《西班牙人在菲律賓商業(yè)文化及宗教上之關(guān)系》,《國立大學聯(lián)合會月刊》1928年第1卷第8號。
[41] Catholic Online: http://www.catholic.org/saints/saint.php?saint_id=231,2014-06-25.
[42] Edgar Wickberg, op.cit.,p.192.
[43] Juan Gil Fernández, “Chinese in 16th-17th Century Philippines”,trans., W. de la Pea,Taibei: ForumIberia Asia: Una mirada europea hacia el Pacifico,2014-11,pp.4-6,http://club.ntu.edu.tw/~luisachang/20141223Forum/downloads/juan_gil_chineses_16-17.pdf.
[44] Robert R.Reed, op.cit.,pp.124-125.
[45] BR,Vol.12, pp.108-109.
[46] Richard T. Chu, op.cit.,p.270.
[47] Ibid.,pp.214-215.
[48] Nariko Sugaya,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y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8th-century Philippines”, Teresita Ang See.eds.,InterculturalRelations,CulturalTransformation,andIdentity,SelectedPapersPresentedatthe1998ISSCOCenference, Manila:Kaisa Para Sa Kaunlaran,Inc,2000,p.560.
[49] 同[16],第16頁。
[50] James C. Scott,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Vol.66, No.1, 1972,pp.91-113.
【責任編輯:石滄金】
Keywords:the Philippines; Overseas Chinese; Catholicism; Spanish Colonists; Social Relations
[中圖分類號]D634.33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6099(2016)01-0074-06
[作者簡介]呂俊昌,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中國史專業(yè)2012級博士生。
[收稿日期]2015-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