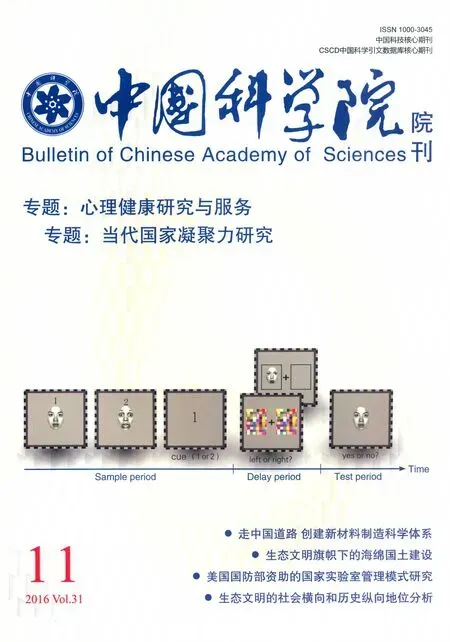我國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發展現狀、問題與對策*
陳祉妍 劉正奎 祝卓宏 史占彪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我國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發展現狀、問題與對策*
陳祉妍 劉正奎 祝卓宏 史占彪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作為“大健康”的重要工作部分,有助于維護和改善國民心理健康水平,減輕疾病負擔,促進家庭和諧,構建良好社會氛圍。我國的心理咨詢與治療始于20 世紀 80 年代,主要在醫療系統、教育系統、社會機構這 3 種模式中發展。近10 余年來,對應著我國國民心理健康需求的大幅增長,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的工作隊伍規模快速擴大,初步呈現職業化趨勢,一些專業標準與服務模式逐步形成。但在工作隊伍的快速擴大中,出現了工作人員良莠不齊,專業工作水平參差不一的亂象。究其原因,在于對心理咨詢與治療工作的專業性認識不足,導致對這一高度專業化的工作規范化不足。具體包括:對工作倫理與標準流程的重視不足;對基礎訓練與實踐技能的重視不足;對療法療效的科學研究重視不足;對專業工作的評估反饋機制重視不足等。為了應對我國未來繼續發展的國民心理健康服務需求,文章提出了未來心理咨詢與治療發展的建議:(1)針對重點人群示范推廣規范的工作方式;(2)在研究與實踐中加強療效評估;(3)完善并推行規范的專業教育培訓;(4)借助互聯網技術,促進優質資源支援落后地區。在規范發展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的基礎上,將我國心理健康服務的各環節有機結合,提高國民心理健康水平。
心理咨詢,心理治療,心理健康,倫理準則,療效研究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6.11.003
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條件,是民族昌盛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標志,也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追求[1]。在“大衛生、大健康”的概念中,心理健康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作為心理健康服務的重要形式,有助于維護和改善國民心理健康水平,減輕疾病負擔,促進家庭和諧,構建良好社會氛圍。
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在理論基礎、工作形式等方面有諸多重疊,因此有時并不區分[2]。而區分這二者的專家通常認為,心理咨詢主要解決健康及亞健康人群的心理問題;而心理治療主要服務于存在心理疾病的人群。但在現實操作中,由于求助者常無法區分自己是否屬于病態,因而二者亦常重疊[3]。在本文中對二者相提并論,不做嚴格區分。
1 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現狀
1.1 國民心理健康需求迫切,形勢嚴峻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1 年世界衛生報告》,全球每4個人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中的某個時段產生某種心理疾病,心理衛生已經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4]。使用“傷殘調整生命年”估算,我國的精神疾病已超過心血管疾病排在疾病負擔首位,占 20.8%,高于全球平均值(14.1%)。2002 年,國際心理治療大會保守估計,中國大概有1.9 億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心理咨詢或治療[5]。
我國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在發達與落后地區,國民心理健康需求呈現不同特征。在發達地區,隨著居民消費需求結構的變化,個人主動的心理咨詢與治療服務需求大幅上升。例如,北京、上海、廣州等發達城市已于1997—2001 年達到人均 GDP 3 000 美元/年,居民顯現出對心理咨詢的消費購買力,推動了心理咨詢業的快速發展[6]。而在貧困地區,居民無力承擔心理健康服務費用,甚至因各種原因無法意識到自身心理健康需求,但其心理健康問題往往更加嚴重,衍生的軀體疾病、刑事案件等亦更沉重[7]。這類地區的心理健康服務需求是被動的,需要政府及有關部門主動介入。
在當前基礎上,可以預期我國未來的心理咨詢與治療的需求將繼續增長,表現在 3 方面。(1)根據國際經驗,伴隨我國人均 GDP 水平進一步提高,醫療保健包括心理健康的服務需求將會增長[6]。(2)隨著我國國民心理健康意識的提高,掩蓋在軀體疾病、意外事故等問題之下的心理疾病將會逐漸剝離出來,顯現為心理健康服務需求[8]。(3)部分人群的心理問題趨向堪憂,形勢嚴峻。例如,筆者研究組在 2010、2014 年前后兩次對科技工作者的調查顯示,科技工作者的心理健康呈現輕微惡化趨勢[9]。更為嚴峻的是,我國當前留守兒童已達 6 102 萬[10],流動兒童已達 3 581 萬[11],研究顯示,早期處于不利環境的兒童,成人后罹患多種心理疾病患的幾率高于普通人群[12]。我國老年精神疾病的發病率達到1.5%[13],而老年人在人口結構中所占比例不斷增高,預期老年精神疾病及心理障礙的絕對數量將隨之增加。
1.2 服務隊伍規模擴大,初步趨向職業化
我國的心理咨詢與治療主要分為醫療、教育、社會3 種機構運營模式。20 世紀 80 年代初期,醫療機構中開始開設心理咨詢門診,醫療模式始見雛形[2]。2002 年,衛生部頒布《心理治療師職稱考核》,隨后舉行了正式考試,標志著醫療系統內心理治療的專業化。教育模式,亦始于 20 世紀 80 年代,高等院校開始設立針對大學生的相關服務機構,其后又從高校逐漸發展到中小學[14]。社會模式始于 20 世紀 90 年代,彼時出現我國最早的社會心理咨詢機構。2001 年,勞動部頒布《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標準》,心理咨詢師被正式列入《國家職業大典》,標志著社會模式走向職業化[15]。除了上述 3 種模式,在公安、部隊等系統內部的心理咨詢與治療也已逐步發展起來。
當前,我國的心理咨詢與治療隊伍已積累了一定規模,持證心理治療師約 5 000 余人,主要在醫療系統內工作[6]。國家心理咨詢師職業水平考試開展以來,獲證人數迅猛增長,當前我國已有持證心理咨詢師約 90萬。然而,調查顯示,無論專業水平如何,其中真正從事心理咨詢的不足 1/10[16]。在教育系統內,根據對已建心理咨詢機構的高校的不完全統計,2007 年心理咨詢/治療師與大學生的比例為 1 : 5287,若按專業人員數量14.27% 的年增長率估計,到 2015 年為 1 : 2364[17]。如果參照西方發達國家現有水平,即每 1 000—1 500 人對應一位專業心理咨詢人員的比例,估算我國需要心理咨詢與治療工作者總數約為 86 萬—130 萬[6],而目前我國在真正能夠提供心理咨詢與治療的專業人員數量與質量上仍存在大大的不足。
除相關職業資格考試外,一系列專業標準也先后形成。例如,2006 年頒布的《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工作倫理守則》[18],2007 年 7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注冊標準》[19],中國標準化研究院與中科院心理所于 2013 年底發布的《心理咨詢服務》國家標準[20],有關專家在 2014年出版的《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技術操作規范》等[21]。盡管精粗不一,但這類關于規范標準文本的出現也是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走向職業化的表現。
1.3 針對特定人群的服務模式初步形成
根據特定人群的需求、不同系統渠道的特征、地區的發展狀況,我國初步形成了一些針對特定人群的服務模式。例如,近年來,中科院心理所針對幾類重點人群進行探索并初步推廣了一些有效模式。
(1)針對受災群眾。我國系統的災后心理援助始于“5·12”汶川地震。此后,以中科院心理所為代表的專業機構又先后連續參與了多次災害事件后的心理援助,從“生理-心理-社會-文化”視野出發,提出了“一線兩網三級”的心理援助體系,即通過一條心理援助熱線,依據全國心理援助聯盟人才網絡開展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干預,以及基于心理創傷嚴重程度的三級干預模式。根據心理創傷的時空特點,提出了“時空二維”的心理援助工作模式,自主研發了一系列心理創傷評估工具、干預設備和網絡平臺,并分別在學校、城市社區和災區開展應用示范工作[22]。
(2)針對農村老年人。通過中科院科技服務網絡計劃(STS)“醫療網底身心健康工程研發與示范”項目,探索了一種促進農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模式,形成了專家指導,醫務工作人員為主體,鄉村醫生配合的三級心理服務團隊。該項目完成了身心健康一體化檢查系統的研發,在軀體健康檢查的基礎上,增加了抑郁、老年癡呆癥的篩查工具。我國地區發展不平衡,偏遠落后貧窮地區需要依賴當地村醫開展基層心理健康服務,而村醫在心理服務上的專業水平不足,該系統為村醫提供了可直接遵循的流程和評估內容,有助于促進基層心理健康服務的規范化。
(3)針對企業員工。中科院心理所建設了“組織與員工促進中心”,以“強健組織、幸福員工”為宗旨,圍繞“健康、勝任、幸福”的員工支持與發展定位,為電力、金融、能源、教育、衛生等行業的 40 余家企事業單位提供了系統心理服務,服務覆蓋人群超過 30 萬人,逐漸探索并建立了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心理健康促進、組織與員工促進項目運作模式,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針對國家公務員。2008 年,中央國家機關工會聯合會、中科院工委和中科院心理所聯合組建了“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為中央國家機關 76個部委職工及家屬開展心理健康促進和咨詢輔導服務,打造了獨具特色的“一線兩網三級四體系”服務模式。“一線”指一條 7×24 小時免費心理咨詢熱線。“兩網”指由督導專家團隊、咨詢師團隊、心理指導員和心理志愿者組成的“人網”,以及由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網絡服務平臺和微信服務平臺組成的“互聯網”。“三級”指咨詢中心服務的三個人群,對“一級”正常人群服務的目標是提高心理素質、維護心理健康以及預防心理疾患;對“二級”心理問題人群服務的目標是消除心理困擾、提供心理自助以及促進心理健康;對“三級”精神障礙人群服務的目標是及時發現問題、及時轉介治療以及預防危機事件。“四體系”包括了咨詢、科、心檢以及培訓的服務體系。
2 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規范化方面的問題
有學者指出[23],“我國心理咨詢隊伍存在著‘一少三多’的現象:專業人員少;半路出家多,出于熱情和興趣的多,不規范工作的多”。專業水平的良莠不齊,導致心理咨詢與治療的質量得不到保障,求助者的利益和心理健康可能受到損害。例如,有調查發現[24],近 40%的大學生認為本校心理咨詢師“跟普通老師沒什么區別”或“還不如其他老師”。另一項對社會心理咨詢機構的調研顯示,求助者反饋了咨詢師不能遵循專業規范(例如在咨詢過程中接聽或回復他人電話)與缺乏專業水平(例如不能很好地在咨詢過程中解釋自己使用的理論)等問題[25]。
我國當前心理健康服務領域存在的“亂象”,根本原因是供需結構不平衡,面對迅速增長的國民心理健康服務需求,高質量的專業隊伍不足,社會各類人員涌入心理咨詢行業,五花八門的心理咨詢與治療方式應運而生。但“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是復雜的專業工作,需要長期、正規的院校教育、繼續教育以及持續不斷的臨床督導,否則也會像其他醫療技術一樣對服務對象造成嚴重危害”[3]。我國目前正處于心理咨詢業初級發展階段,分析起來,在下列 4 個規范化方面存在著不足。
2.1 對工作倫理和標準流程的重視不足
心理咨詢與治療工作具有靈活性,例如因療法流派、個人風格不同而導致的差異。在多樣靈活的特點下,要進行合理的規范引導,就必須厘清哪些是判定專業工作的核心特征。
(1)倫理準則。無論流派、風格如何,心理咨詢與治療工作都應遵循倫理準則,維護求助者的心理健康。我國的《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工作倫理守則》已對知情同意、保密等基本原則進行了規范[18],但在專業人員培訓、臨床實踐操作上,還需推廣和落實。只要從事專業活動,就會涉及到倫理決策。美國心理學會針對 1 319 位會員的調查中,有 679 位心理學家指出遇到過倫理方面的問題或困境[26]。我國也已經出現對咨詢師違反倫理的投訴,但由于社會公眾對于咨詢師應遵循的倫理準則所知甚少,實際上可能有更多咨詢師違反倫理的做法未被識別和報告。
(2)標準流程。標準流程首先體現為設置,心理咨詢的設置是指時間、地點、費用等方面的安排,是專業活動規范的基本表現[27],但其在我國當前的心理咨詢與治療中也常常偏離。例如,心理咨詢的面談時間通常一次50 分鐘。但對 10 家社會機構的一項調查顯示,普遍的咨詢時間都在 1.5—2 小時之間[24]。這一偏離可能體現了咨詢師能力、心態方面的問題。心理咨詢的標準流程從與求助者的初始接觸開始。例如,在咨詢開始前,咨詢機構應將咨詢師的專業資格與經驗、受過的訓練與教育、證書、收費標準等信息向來訪者詳細說明;在咨詢中咨詢師應告知來訪者有關咨詢過程、所需時間、咨詢的限制、可能的危險與益處[28]。標準流程并不能確保心理咨詢與治療工作的有效性,甚至在特定情況下,僵化遵循流程而不能依據求助者的需求進行調整,未必是最佳的做法。但是,在當前心理咨詢人員專業水平有限的狀況下,遵循標準流程往往利大于弊。
此外,隨著互聯網技術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心理健康服務也與互聯網技術結合,出現多種形式。對于專業工作倫理和標準流程的制定與落實,也需要考量到新舊各種形式的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例如電話熱線、網絡視頻、自助訓練等。網絡心理咨詢有其適用范圍,判定求助者是否適合網上服務,也是工作倫理與標準流程的重要內容之一[29]。
2.2 對專業能力的發展重視不足
心理咨詢與治療又稱為“談話治療”,其主要手段是談話。但這種專業性的談話,需要厚積薄發,是以包含著理論、技術、經驗乃至素養的專業能力為基礎的。專業能力的積累,需要長時間扎實的理論學習進而形成理論素養、方法學基礎,需要大量直接與間接的實踐經驗進而掌握實踐技能,也需要個人的自我成長進而培養出專業精神與態度。
我國學者對北美、歐洲、澳大利亞、日本等心理咨詢與治療發展更為領先地區的培訓及管理狀況進行了梳理和探討,作為提高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專業化水平的參考。在上述國家與地區國家,從事心理咨詢與治療的專業人員通常需要具備臨床心理學或咨詢心理學的博士或碩士學位,按要求完成實習并接受督導,再通過專業考試或資格申請而獲得執業資格[30-35]。歐美的心理治療師培訓至少包括 3 大部分:(1)理論學習,至少 8 個學期的課程;(2)自我分析或自我體驗,即接受培訓治療師的分析,例如精神分析學派一般要求接受 600 小時左右自我分析;(3)在督導指導下的臨床實踐,例如精神分析學派在申請資格論定時,要提交至少兩份具有 300 治療小時以上的病歷報告[23]。
相比之下,我國對心理咨詢與治療人員在專業能力發展的各個環節要求都很低,表現在 5 個方面。(1)專業隊伍不穩定。在高校、醫療機構、社會機構中,心理咨詢工作專職與兼職人員的比率為 1 : 1 至 1 : 10 不等[25]。(2)學歷偏低,教育背景不對應。我國心理咨詢工作者中具有碩士和博士學位的不足 2%。近年來雖有所提高,但學歷水平仍然偏低[36]。醫療領域的心理健康服務機構以醫學背景的專業人員為主,僅有約 1/5 為心理學背景[37]。而獲得心理咨詢師資格的人員超過 50% 既無心理學背景,亦無醫學、教育學背景[38]。(3)培訓時數過少。我國的心理咨詢師培訓時長遠遠低于上述各國,不足國際水平的 1/10 甚至更低。一項對上海市 40 家心理咨詢機構從業人員的調查表明,其培訓時間以 6 個月以下者為多[38]。醫院衛生系統及高校的情況也相類似,據調查,從事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工作的專業人員有 78.1% 受到的專業訓練少于半年[25]。(4)實踐技能訓練缺乏。實踐少,且在培訓中亦沒有或無法安排實習。(5)特別需要單獨強調的是,督導制度缺失。心理咨詢與治療工作需要專業人員具備在實踐中運用理論知識的能力,在督導下的實習是培養這一能力的重要方式。但一項對 1 391 名來自 29 個省市自治區的心理健康服務從業者的調查顯示,心理健康從業人員的 42% 從未接受過專業人員的督導,達到督導時數的要求更無從談起[39]。
2.3 對療法療效的科學研究重視不足
一項對社會機構的調查發現,各機構采用的咨詢技術種類繁多,包括“催眠療法、NLP(神經語言程序學)、意象對話心理治療、薩提亞家庭治療、音樂療法、呼吸療法、色彩療法、芳香療法、森田療法、完形療法結合靈氣按摩、瑜伽養生、全息療法、藏御火療等自然療法”[25]。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的療法之紛亂,可見一斑。在專業培訓領域,同樣呈現療法五花八門,某些冷僻的療法反而比幾大主要心理治療流派更加興旺。
療效研究為心理咨詢與治療具有的效果提供了科學證據。只有通過充分數量的療效研究結果的支持,心理咨詢與治療的效果才會為專業領域所認可;在療效得到證實與專業認可后向公眾推廣使用,才是符合專業倫理的做法。精神分析學派或心理動力學的療法,曾因其部分理論難以證實而受到質疑,是大量的療效研究乃至元分析研究,為其療效提供了可靠證據[40]。國際上隨著療效研究數量的充沛,逐漸出現了很多元分析研究,證明雖然認知行為療法的療效研究結果最佳,但在治療抑郁等問題上,幾大主要心理治療流派的療效基本相等[41]。專業人員的培訓內容、醫療保險的覆蓋內容等都與療效研究結果關聯。
我國當前的療效研究數量還非常不足,社會上頻頻出現的許多療法并無任何療效研究。這不僅不利于驗證來自西方的各種心理療法在我國的適用效果,也不利于判斷各種新興甚至流行的療法是否科學有效。
2.4 對評估反饋機制重視不足
對于單個機構、單個專業人員乃至單個咨詢或治療案例的效果評估,與療法的療效研究相似,但更具體而微。心理咨詢效果的評估包括 3 個方面。(1)來訪者咨詢前后個人情緒、人際關系和社會功能方面的改變。(2)來訪者對咨詢的滿意度。(3)咨訪關系狀況。其中,來訪者對咨詢的滿意度是咨詢效果評價非常方便和有效的方法,也常常用作心理服務機構的鑒定標準之一[42]。
療效的評估應得到充分反饋。面向專業人員的反饋,有助于咨詢師或治療師的自省與提高;面向機構的反饋,有助于機構對咨詢師或治療師的評價與管理;但最重要的是,面向社會的信息公布,有助于個體求助者、政府采購方等服務使用者在選擇時有所依據,有助于去蕪存菁,淘汰水平欠缺的服務機構與個人。
目前,國內絕大多數機構未建立評估反饋機制,特別是缺乏從求助者角度收集的療效評估信息,因而對聘任咨詢人員的考評不全面甚至缺乏。從行業管理上來說,目前尚未建立對專業機構、專業人員的療效評估機制,使行業治理與示范推薦缺乏依據。
3 對策與建議
醫療與教育系統內的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因有所在系統的監管約束,其混亂程度較輕,并通過所在系統進一步支持其專業發展以提升服務水平;社會上的心理咨詢與治療服務,因情況多樣、魚龍混雜,是規范化工作中的重點與難點。
心理健康服務工作的規范,既有管理層面的規范,又有專業水平的限制。人員、制度、工作模式等方面的管理,較為外顯,易于評估和規范;專業活動的實際執行方面,幽微隱秘、復雜多樣、流動多變,難以評估和規范。當前亟需建立一套符合我國現實國情的心理咨詢與治療服務體系,促進行業的規范發展。
3.1 針對重點人群,示范并推廣規范的工作方式
有學者指出,我國當前應“深入培養特色治療師,如同臨床醫生分科一樣,一個人很難同時是精神分析治療師和行為治療師。應培養專門人才,而非雜家”[23]。“學有所專,則更容易學有所精”,這是快速解決我國當前心理咨詢與治療專業力量不足的有效理念。我國當前存在大量專業基礎薄弱而懷有強烈從業興趣的潛在心理咨詢師隊伍,針對這一現狀,除了療法上的專長,亦應在服務所針對的人群、問題上有所限制,形成具體而規范的工作方式,以便推廣應用。
規范的工作方式應包含 3 方面。(1)遵循基本的專業倫理和設置。專業倫理并非只有內心的道德操守,更體現在具體的操作流程中,咨詢師或治療師做了什么和沒做什么。以知情同意為例,即表現為咨詢師是否充分解釋了相關內容,是否沒有刻意的誘導,是否獲得了書面簽署。(2)遵循專業人員所應用的療法流派的要求。可兼顧個人風格,但不宜隨意違背療法的基本原則或者將各種療法隨意混搭。(3)將規范的工作方式進一步細化,成為針對特定人群的工作模式。例如針對受災群眾的工作,有推薦的工作次序和優先級別[22]。
3.2 在研究與實踐中加強療效評估
在研究中加強療效評估,目的在于對療法流派的梳理;在實踐中加強療效評估,目的在于對機構和人員的梳理。這兩個層面是提高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工作的科學性、專業性的基礎。
針對療法流派的療效研究具有從寬泛到精細的發展過程。寬泛的療效研究,目標在于驗證某個療法流派的有效性;精細的療效研究,則探討針對何種人群的哪類問題,何種療法最為有效[43]。通過對某類特定人群的特定問題,進行不同療法的干預,并對比干預效果,是當前療效研究的常用模式。針對療法流派的療效研究有 3 點價值。(1)心理咨詢與治療不可回避社會文化的影響,源自西方的療法流派乃至具體技術是否適用于我國,效果是否相似,需要療效研究來驗證、探討。(2)新創的療法對于求助者是否具有積極效果,是否存在潛在的危害,適用或不適用于何種人群,也需要療效研究的探索。(3)在大量療效研究的基礎上,可以進行元分析,得到較為可靠的結果,從而認證并推廣有足夠累計證據證明的有效療法。
在臨床實踐中建立療效評估機制,并進行日常使用,是促使心理咨詢與治療從數量發展轉向質量發展的重要手段。在行業組織的引領下,推廣標準的療效評估方式,積累專業機構、專業人員的療效評估信息,并向社會公布,有助于引導心理咨詢與治療行業的規范化發展。
3.3 完善并推行規范的專業教育培訓
有學者指出[42],心理咨詢師資格證書培訓必須“嚴進嚴出”,并與心理學知識的普及性質的培訓證書相區別。“嚴進”對應著加強學歷教育,而“嚴出”對應著加強實踐技能培訓,特別是加強督導制度。
“只有學歷培養跟上去,心理健康服務質量才能有保障。”有關專家研討認為,當前應制定《臨床與咨詢心理專業研究生培養指南》,對臨床與咨詢心理專業研究生的培養目標、課程設置、實踐教學、師資條件等作出明確規定。同時,鑒于“應用心理學”的培訓中無法突出和針對心理咨詢與治療能力的培養,應考慮對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專業進行某種形式的單獨管理,例如在應用心理學專業學位中單列“應用心理學(臨床與咨詢)”[44]。
在督導制度下,新手咨詢師或治療師應當一邊開始實習,一邊接受資深咨詢師或治療師的督導。建立和完善督導機制和督導體系,不僅是為咨詢師提供專業能力培養的必經之路,而且有助于保障新手咨詢師或治療師實習期間的工作質量,預防對咨訪雙方的可能風險。在制度上,要明確接受督導是心理咨詢與治療專業人員培養中不可缺少的環節,并需確保充足時數;在實施中,為緩解督導人員不足的狀況,要加強培養督導師,并鼓勵督導工作的開展。
3.4 借助互聯網技術,促進優質資源支援落后地區
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的服務資源存在顯著的地區差異。2010 年,一項研究在調查了全國 31個城市的社會心理咨詢機構后,根據專業機構發展規模大致分4類地區(表 1)。

表1 我國城市的心理咨詢機構數量
咨詢機構的發展情況與當地人均 GDP、居民可支配收入、當地開設心理學專業的高校數量相關[25]。總的來說,華北、華東地區好于西南、西北地區。城市之間的資源差異巨大,而城市與農村之間的資源差異更大。
借助我國高度普及的互聯網技術,通過“互聯網+心理健康服務”的形式,可以將優質的心理咨詢與治療資源延伸到落后地區,盡快提高當地的服務水平。借助互聯網而延伸的資源既可以包括人,也可以包括工具和制度。資深的心理咨詢與治療專業人員可以通過網絡為落后地區提供視頻與在線培訓、提供遠程在線督導;通過研制標準的網絡自助訓練模塊,可以為不同地區的需求者提供自助式的心理咨詢服務;通過編制心理咨詢的輔助工具包,提供管理制度、標準流程、評估工具等,為落后地區的兼職人員開展心理健康服務提供支持。這些方式結合起來,有助于快速緩解優質專業資源不足、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
4 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強調[1],“要加大心理健康問題基礎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識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規范發展心理治療、心理咨詢等心理健康服務”。發展心理健康問題的基礎性研究,特別是療效研究與本土化研究,有助于提高我國心理咨詢與治療的專業性、針對性;做好心理健康相關的科普工作,有助于提高公眾的辨識力,形成心理咨詢與治療隊伍優勝劣汰的社會環境;反過來,在心理健康科普工作里,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工作者必然參與其中,構成核心專業力量,在規范發展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的基礎上,其他形式的心理健康服務也能提高科學性、專業性,并將心理健康服務的各環節有機結合、順暢連通。
致謝 本文的寫作中得到錢銘怡老師的支持,特此致謝。
1 習近平. 在全國衛生與健康大會上的講話. 人民日報, 2016-8-21.
2 黃希庭, 鄭涌, 畢重增. 關于中國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建設的若干問題. 心理科學, 2007, 30(1): 2-5.
3 趙旭東, 叢中, 張道龍. 關于心理咨詢與治療的職業化發展中的問題及建議.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5, (3): 221-225.
4 WHO. The world health report 2001 - Mental health: New understanding, new hope. 2001.
5 李國軍. 淺談心理咨詢師發展現狀與對策. 人才資源開發, 2014, (17): 41-42.
6 倪子君. 中國心理咨詢行業分析報告.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4.
7 Saraceno B, van Ommeren M, Batniji R, et al. Barriers to improvement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low-income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Lancet, 2007, 370(9593): 1164-1174.
8 談鈞佩, 華炳春, 周志英, 等. 綜合性醫院心理障礙軀體化調查. 中國誤診學雜志, 2004, 4(1): 149-150.
9 中國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課題組. 中國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報告. 合肥: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2013.
10 全國婦女聯合會. 我國農村留守兒童狀況研究報告. 2014.
11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中國人口流動發展報告 (2015). 2015.
12 Bifulco A, Bernazzan I, Moram P, et al. Lifetime stressors and recurrent depression: Preliminary findings of the Adult Life Phase Interview.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00, 35(6): 264-275.
13 陳立新, 姚遠. 老年人心理健康影響因素的調查研究——從人格特征與應對方式二因素分析. 人口與發展, 2006, 12(2): 63-68.
14 陳紅, 趙艷麗, 高笑, 等. 我國高校對心理咨詢與治療人才的培養現狀調查. 心理科學, 2009(3): 697-699.
15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 心理咨詢師國家職業標準(試行). 2001.
16 張黎黎, 楊鵬, 錢銘怡, 等. 不同專業背景心理咨詢與治療專業人員的臨床工作現狀.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10, 24(12): 948-953.
17 錢銘怡, 陳瑞云, 張黎黎, 等. 我國未來對心理咨詢治療師需求的預測研究.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10, 24(12): 942-947.
18 中國心理學會. 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工作倫理守則. 2006.
19 中國心理學會. 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注冊標準. 2006.
20 中國標準化研究院,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 心理咨詢服務國家標準. 2013.
21 張亞林, 曹玉萍. 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技術操作規范. 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6.
22 劉正奎, 吳坎坎, 張侃. 我國重大自然災害后心理援助的探索與挑戰. 中國軟科學, 2011, (5): 56-64.
21 肖澤萍, 施琪嘉, 童俊, 等. 誰適合作心理治療師?——對心理咨詢與心理治療專業人員資格的討論.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1, 15(2): 214-216.
22 陶金花, 姚本先. 高校個體心理咨詢現狀研究. 中國衛生事業管理, 2015, 32(10): 789-791.
23 周婧. 社會上的心理咨詢服務現狀與對策研究. 四川: 西南大學, 2010.
24 Pope K S, Vetter V A.Ethic dilemmas encountered by members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 national survey.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2, 47(3): 397-411.
25 王超, 李英, 孫春云. 心理咨詢與治療中時間設置問題討論.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4, 18(1): 67-70.
26 劉偉志, 袁瑋, 萬能武. 我國心理咨詢業的倫理學探討. 醫學與哲學, 2006, 27(19): 43-44.
27 崔麗霞, 鄭日昌, 滕秀杰, 等. 網絡心理咨詢職業倫理研究概況及展望.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7, 21(7): 510-512.
28 趙艷麗, 陳紅, 劉艷梅, 等. 澳大利亞臨床心理學的培訓和管理.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8, 22(3): 224-226.
29 高雋, 錢銘怡. 歐洲心理咨詢與治療領域的培訓狀況.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8, 22(5): 372-375.
30 樊富珉, 吉沅洪. 日本心理健康服務體系培訓與管理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8, 22(8): 588-593.
31 王丹君. 英國心理咨詢及心理治療協會的心理咨詢師認證及其他.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7, 21(10): 704-709.
32 姚萍, 錢銘怡. 北美心理健康服務體系的培訓與管理狀況.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8, 22(2): 144-147.
33 江光榮, 夏勉. 美國心理咨詢的資格認證制度.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05, 13(1): 114-117.
34 秦漠, 錢銘怡, 陳紅, 等. 國內心理治療和咨詢專業人員及工作狀況調查. 心理科學, 2008, (5): 1233-1237.
35 張智豐, 易春麗, 錢銘怡, 等. 醫療與教育領域心理健康服務機構管理情況比較. 中國臨床心理學雜志, 2009, 17(6): 773-776.
36 王維玲. 上海市心理健康咨詢服務的現狀和發展. 上海精神醫學, 2005, 17(增刊): 56-57.
37 梁毅, 陳紅, 王泉川, 等. 中國心理健康服務從業者的督導現狀及相關因素.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9, 23(10): 685-689.
38 Leichsenring K, Rabung S. Effectiveness of long-term psychodynamic psychotherapy: A meta-analysis. JAMA, 2008; 300(13): 1551-1565.
39 Cuijpers P, Van S A, Andersson G, et al. Psychotherapy for depression in adults: a meta-analysis of comparative outcome studi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 Clinical Psychology, 2008, 76(6): 909-922
40 李鈺靜, 駱宏. 心理咨詢效果評估量表中文版的信度和效度.中國心理衛生雜志, 2009, 23(2): 105-107.
41 Ebert D D, Zarski A C, Christensen H, et al. Internet and computer-based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youth: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outcome trials. PLoS One, 2015, 10(3): e0119895.
42 胡月香. 上海高校心理咨詢現狀研究. 上海: 華東師范大學, 2009.
43 全國應用心理專業學位研究生教學指導委員會. 臨床與咨詢心理學教學研討會會議紀要, 2016.
陳祉妍 中科院心理健康重點實驗室副研究員,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員,中國心理學會醫學心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心理學會心理學標準與服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中國心理學會科普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委員會首批注冊督導師,中科院心理所國民心理健康評估發展中心負責人。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國民心理健康狀況調查、青少年心理健康追蹤研究、心理健康應用測評及干預。E-mail:chenzy@psych.ac.cn
Chen Zhiyan Received B.S. degree fro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Ph.D. degre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2003. S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d professor,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Psychological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Center in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Committee of Medical Psychology and the Committee of Popularization of Psychological Knowledge in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She is a certificated clinical supervisor by the Committee of Clinical and Counseling Psychology, Chinese Psychological Society. Her current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ational survey on mental health across different groups, longitudinal research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and intervention. E-mail: chenzy@psych.ac.cn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Strategies
Chen Zhiyan Liu Zhengkui Zhu Zhuohong Shi Zhanbiao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ervice for holistic health, help to improve people’s mental health status, decrease the burden of disease,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family life, and build up positive social environment. Beginning from the 1980s,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in China have been developing mainly in medical system, educational system, and social institute. In recent decade or two, the need for mental health service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the number of counselors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multiplied accordingly, taking the course to professionalization. A few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working pattern developed progressively. However, the rapid increasing of counselors and other mental health practitioners also bring about problems such as unqualified professionals and spotty mental health service. Part of the reason lies in wrong knowledge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s a highly professional work,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must be based on qualified professionals and strict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 analysis of present situation shows that the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are in lack of development in several areas, including: not enough importance has been given to ethic code and standard process; not enough importance has been given to basic training and practice skills; not enough importance has been given to research on treatment outcome; and not enough importance has been given to the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system of professional work. Thus, facing the increasing need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develop the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in following ways: (1) promote effective evidence-based working patterns aiming at specific groups; (2) carry out more evaluation on treatment outcome both in research andpractice; (3) improve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to a more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level; and (4) using the Internet techniques to extend high quality professional resources to less developed areas. Developing the quality of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to a higher level, the whole system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 will integrate more effectively, thus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Chinese people.
counseling, psychotherapy, mental health, ethic code, evaluation of therapeutic efficiency
*資助項目:中科院“率先行動”計劃特色研究所項目 TSS-2015-06(Y5CX 234008)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6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