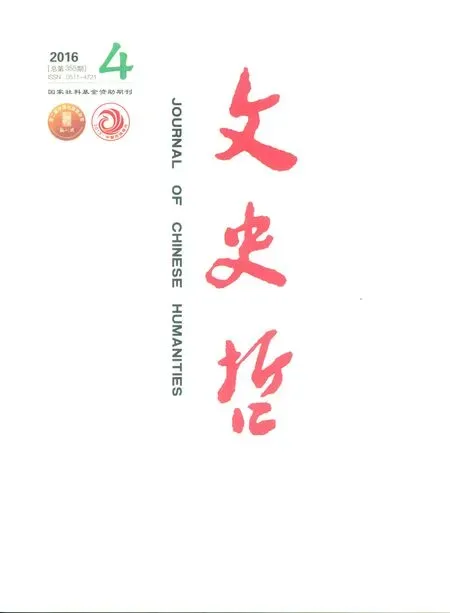六朝貴族的自律性問題
——以九品官人法中鄉品與官品、官職的對應關系為中心
李濟滄
?
六朝貴族的自律性問題
——以九品官人法中鄉品與官品、官職的對應關系為中心
李濟滄
摘要:自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提出官品較鄉品低四品起家的觀點以來,中日兩國學術界圍繞鄉品與官品之間的對應關系作了不少研究,尤其是中國學者進一步提出了鄉品與官職對應的新思路。鄉品只是與起家官品存在著對應關系,而不是與官品有規律性對應;其次,這種對應呈現出一定的趨勢,相差四品應是一個大致的原則,有著上下的浮動;再次,鄉品與官職之間的確有緊密聯系,但并不能以這種關系替代或者否認鄉品與起家官品的對應。這種聯系并非某些具體官職與某些鄉品相對應,而是如晉宋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內官職需由鄉品二品者擔任那樣,九品官制以內的絕大多數品官都需要具有鄉品這一資格。此外,針對官職所作的鄉品規定,南朝以前,還不能確認為國家法律或條文;南朝以降,這些規定主要出現在鄉品三品及以下。在研究九品官人法的實質和歷史意義之際,探討鄉品與官品或鄉品與官職的對應關系固然重要,但鄉品與國家權力之間的關系更應得到澄清,對獲得鄉品二品的門閥貴族階層具有相對于皇權的自律性特質,應予以足夠的重視。
關鍵詞:六朝貴族;九品官人法;鄉品;官品;官職
在中國歷史上,六朝時期最突出的社會現象是門閥貴族階層的形成與活躍*國內外關于六朝貴族的研究綜述,成果可謂豐富,這里舉出兩篇代表性論文。陳爽:《近20年中國大陸地區六朝士族研究概觀》,《中國史學》第11卷《魏晉隋唐專號》(日本),2001年10月。此文開首對六朝貴族研究作了如下定位:“門閥士族的形成、發展及其衰落是中國中古時期特有的歷史現象。漢唐之間,士族成為這一時期社會的統治力量,對于六朝士族的認識和研究直接關系到對整個魏晉南北朝歷史的理解和把握,長期以來,士族問題的研究一直是魏晉南北朝領域一門古老而又常新的‘顯學’。”[日]川合安:《日本的六朝貴族制研究》,《史朋》40號(2007年),楊洪俊譯文載《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日本的六朝制貴族研究,保持著內藤湖南六朝隋唐中世說以來的傳統。”也就是說,六朝貴族的研究與時代區分理論密切相關,是認識六朝隋唐時代性質的核心因素。另,日本學者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六朝貴族研究作了大量學術回顧,其代表性論文,可參見本文注②。。近年,日本學者渡邊義浩對六朝貴族及其特點作了五個方面的歸納:(1)作為一個階層,直接或間接統治農民;(2)世代世襲國家高官;(3)與“庶”相對,擁有“士”這種高貴的地位以及身份;(4)在文化上具有一般庶民無法參與的文化創造能力;(5)相對于皇權,有著一定的自律性。進一步而言,如果將這一時期與中國歷史上其他時代相比,則(1)是從漢代豪族到清代鄉紳的統治階層都具有的性質,(2)、(3)是周代的卿、大夫、士所具有的性質,(4)是宋代以后的士大夫所具有的性質。而最能體現其特色的就是(5),即相對于皇權的自律性*[日]渡邊義浩:《“所有”與“文化”——對于中國貴族制度研究的一個觀點》,《中國——社會與文化》(東京)第18號(2003年6月)。。
上述歸納建立在眾多前人研究成果之上,有一定參考意義。可是,門閥貴族究竟如何獲得了相對于皇權的自律性呢?對此,渡邊指出了重視血統的名門主義和形成封閉性通婚圈的人際關系,以及嚴格區分貴族與非貴族的同類意識等等。然而,這只是一種針對現象的陳述而非原因的分析。不能不說,內藤湖南對六朝貴族自律性的提示至今仍具啟迪性:
這一時代的中國貴族,不是在制度上由天子授與領土與人民,而是由于其門第,作為地方名門望族延續相承的傳統關系而形成的。當然這是基于歷來世代為官所致。當時社會上的實權,是掌握在這些貴族的手中。這些貴族都重世襲家譜,因此當時系譜學頗為盛行。*[日]內藤湖南:《中國近世史》第一章《近世史的意義》,收入夏應元選編并監譯:《中國史通論——內藤湖南博士中國史學著作選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324頁。
據此可知,在思考門閥貴族的所謂自律性特點時,來自與地方鄉村社會的支持與否,應成為關鍵要素。一般而言,六朝的貴族往往以家族為背景,修習家學、禮法,同時依靠家族、宗族以及鄉里社會的支持,通過九品官人法步入政界,持續占據王朝的高官高位,在政治與社會兩個層面享有威望。也就是說,獲得鄉里社會的支持,體現了門閥貴族的社會性特點,而當他們成為王朝官僚,構成國家權力的一部分時,則呈現出代表王朝的一面。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應怎樣從社會性、王朝性的角度來分析門閥貴族自律于皇權以外的特質呢?
在學術史上,谷川道雄援引宮崎市定的九品官人法研究,對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條極富想象力的線索。眾所周知,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主要官僚人事制度,其最大特色是確立了官品體系,官分九品,對官職的高下作了區分,一直影響到了清末。但是,這項制度還有一個其他時代不曾有的特點,這就是在官品以外,還有鄉品的存在。20世紀50年代,宮崎在其《九品官人法研究》一書中,首次揭示出官僚候選者起家任職時,其官品要較鄉品大致低四品的歷史現象。學術界圍繞這一對應關系及其評價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此,谷川作了如下闡述:
按宮崎氏所理解的鄉品與官品的相互關系,就本質而言究竟說明了什么呢?有關這一點,我在上述幾篇書評中并沒有得到滿意的答案。我以為,就官品依鄉品來決定的事實來說,貴族身份和地位雖可認為是由王朝權力所賦予的,但在本源上仍是由其在鄉黨社會之地位和權威所決定的,王朝只不過是對此予以承認的機關——當然這種承認具有很大的作用。直截了當地說,貴族之所以成為貴族,其本源不在王朝內部,而在其外部。而這種承認手續,可以認為就是所謂九品官人法。如果這樣考慮的話,不論六朝貴族有著怎樣的官僚制形態,其本質也應該是比擬封建制的,換言之,可以視其為一種封建制的變形,這就是我對宮崎的本意的理解。

無論邏輯還是思考方法,這一評介對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然而從正面對此加以論證的研究迄今尚未得見。例如,圍繞鄉品與官品之間的對應關系,中日兩國學術界都做了不少研究,尤其是中國學者或否定、或修正,用力較勤,不但如此,還進一步提出了鄉品與官職對應的新觀點,這些都大大豐富了九品官人法的研究內涵。可是,探討九品官人法中的對應關系,究竟對六朝貴族的自律性問題或者六朝時代特質的分析有什么樣的作用呢?遺憾的是,這些并沒有引起前人的足夠關注。
本文首先對前人的相關成果和論點作些梳理,在此基礎上,重新探討鄉品與官品以及鄉品與官職的對應關系及其問題所在。研究目的在于,從鄉品的角度,論述九品官人法的歷史意義以及六朝貴族自律于皇權以外的性質。
一、鄉品與官品
關于九品官人法之中的官品,馬端臨曾有一個概括,“然此所謂九品者,官品也,以別官之崇卑”;“蓋官品之制,即周之所謂九命,漢之所謂祿石,皆所以辨高卑之等級。其法始于魏,而后世卒不能易”*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六十七《職官二十一》,北京:2011年,第2056頁。。也就是官品的作用在于區別官職的高下崇卑,與周漢的九命、祿石的性質相似。

馬端臨對鄉品也有一個概括:“陳群所謂九品者,人品也,以定人之優劣。”這里的人品,就是鄉品之謂,由各個地方的中正對官僚候選人定品。那么,官品與鄉品之間有何關系呢?馬端臨認為:“二者皆出于曹魏之初,皆名以九品。然人品自為人品,官品自為官品……若中正所定之人品,……然決與此官制之九品不相干,固難因其同時同名,而遂指此為彼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六十七《職官二十一》,第2056頁。
馬端臨盡管指出了中正所定“人品”與“官制之九品”為兩個不同的系統,但是對于兩者的聯系,并沒有說清楚,其中最后一句“同時同名,而遂指此為彼也”,針對的是南宋岳珂的觀點,因為后者對官品與鄉品有一個重要的分析:

之所以重要,因為在此之前還從沒有人意識到鄉品與官品的關系問題,更談不上有明確的認識。岳珂首先使用了“九品官人之法”這一用語,也意識到了鄉品并非官品,然而對兩者的關系,卻不能理順,只是使用了一個“逆設”的說法,也就是鄉品二品意味著其人將來可以達到官品二品。對此,馬端臨進行了批判:“岳氏合而為一,以為官品者逆設之以待某品之人,此說恐未然。”
兩人雖然觀點不同,但是都認識到鄉品與官品為兩套系統,并非一回事,至于兩者之間有何對應或者聯系,則完全沒有談到。
20世紀50年代,首次對官品和鄉品的關系發表獨特觀點的是日本學者宮崎市定。根據宮崎的看法,鄉品是中正官給予希望當官的候選人的評價,政府根據此鄉品的上下授予適當的品級官位。官品與鄉品的相互關系,例如鄉品為二品的人才,初任官職的時候,會委任他當低四級的六品官。此后,隨著年資的積累,其政績得到承認,那么逐次晉升,最終可達到二品官。但是如果要晉升為一品官,那就必須要有中正重新審核,改授鄉品一品*[日]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6年;后收入《宮崎市定全集》6,東京:巖波書店,1992年。中譯本韓昇、劉建英譯,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53頁。本文所引均出自中文版。。
鄉品是否有一品,迄今尚無定論,中國學者傾向于持否定性看法,這一點暫且不談。我們看宮崎的上述概括,大致包括兩層含義:首先是官僚步入政界之初,所任官職也就是起家官的官品一般比其所擁有的鄉品要低四品。這應該是首次明確了鄉品與官品之間的關系,意義重大。其次,例如鄉品二品的人物,最終可以達到與鄉品相等的二品官。這一點實際上與岳珂“逆設”之說相似,不過與岳氏相比較,更加明確了鄉品和官品的不同,并且揭示了兩者之間的對應關系。

以上簡要回顧了官品與鄉品的存在及前人的理解。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一部分中國學者之中,重新對兩者的對應關系產生了研究興趣,以下擇其代表性的例子略作說明。
陳長琦將中正所定的鄉品稱作“資品”*筆者曾經對“資品”一詞作過分析,認為是官資與鄉品的合稱,并不等同于“鄉品”,而“中正品第”、“中正品”、“人品”等也是不同學者對“鄉品”的稱謂。參見拙稿《九品官人法中的鄉品稱謂考論》,《江海學刊》2012年第6期。另,除引文以外,本文均使用“鄉品”一詞。,以此探討了其與官品之間的關系,認為某種官職如標明官品二品,就表示這種官職需要鄉品二品的人來擔任,標明三品,就表示這種官職需要鄉品三品的人來擔任。同時,某人如獲得鄉品二品,就表示有了任二品官的資格,若獲得鄉品三品,就表示有了擔任三品官的資格。也就是對宮崎所言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的對應關系作了擴展,進一步指出鄉品與官品之間有著明確的對應關系。至于宮崎所說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相差四品的觀點,陳長琦也進行了修正,認為曹魏時期,兩者之間大致對應關系是相差三品。西晉以后,鄉品二、三、四品的起家官品與其鄉品之間的差距,由相差三品變為相差四品,鄉品五品的起家官品,在與鄉品相差三至四之間浮動,鄉品六品的起家官品仍然保持著與其鄉品相差三品的距離*陳長琦:《魏晉南朝的資品與官品》,《歷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上述觀點首先參考了岳珂“逆設”之論以及宮崎的說法,也就是鄉品二品中的“二品”,其實是指該鄉品獲得者能在政界所能升到的最后官品。而在鄉品與起家官品的對應方面,也以宮崎說為基礎進行了細分,建立了更為整齊的對應關系。
針對陳長琦的論述,張旭華認為,無論從一個人起家官職的官品、遷轉官職的官品還是仕途生涯中的最高官位及其官品來看,鄉品二品與官品之間均不存在這種虛擬的對應關系即統一性。根據他的看法,應將鄉品區分為上品與下品。曹魏時期,名列上品的士族子弟可分別從五品、六品、七品三個任官層次起家。入晉以后,出現同是上品而起家官品分為四個層次的銓選格局,也就是(1)帝室親茂和三公子弟可起家為五品官;(2)高門子弟和某些身有國封者可起家為六品官;(3)中級士族子弟多起家為七品官;(4)低級士族子弟則起家為八品官。由此得出結論,在起家入仕這一環節上,鄉品第二品與官品二品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系,而是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張旭華進一步指出,門閥子弟獲得的上品二品,僅僅是表明其等級身份及其所取得的入仕資格,并不表明他已經獲得了就任二品官的資格。再以入仕后的官職升遷而言,魏晉時期的門閥子弟雖可以上品二品起家為官,但只有少數人獲得二品高官,多數人終其一生也難以躋身二品高位*張旭華:《魏晉九品中正制名例考辨》,《九品中正制略論稿》,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3頁。。
由以上所述可知,陳長琦承認鄉品與官品尤其是起家官之間有著對應關系,同時作了進一步的細分,并且通過逆設之說,揭示鄉品與官品之間的對應關系。另一方面,張旭華通過對鄉品二品的分析,認為兩者之間并沒有對應關系或是不能成為固定的模式,而且鄉品僅僅是等級身份的一種反映和進入官界的資格。
二、鄉品與官職
從前引溫嶠的例子可以看到,每當晉升官職的時候,都因為鄉品不過,而需要皇帝特別發詔。這顯示出,鄉品與官職之間有著某種關聯性。還是看馬端臨的分析,他認為鄉品在吏部授官時具有參考作用,即:
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任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核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十八《選舉考一》,第812頁。
也就是說,吏部委托中正審核人才,品定鄉品,然后在任命官職之際予以參考。
關于鄉品與官職的關系,唐長孺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中正品第并非只是一種褒貶虛名,而是和入仕途徑有不可分割的關系。官位必須與品第相符,降品等于免官”,“從卑品升遷官職的雖不乏其人,但升了官必須同時升品。魏晉之間寒門升上品已非易事,晉宋之間除了軍功以外,就絕無僅有了”*唐長孺:《九品中正制度試釋》,《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外一種),第107、111頁。。即鄉品不夠而升官的話,需要提高其鄉品,反之,鄉品出現下降意味著免官,由此可見鄉品與官職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了一定的聯動性。
與唐長孺的上述見解不同,胡寶國認為鄉品只是與具體官職之間有關系。胡寶國首先指出,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有相差三級、四級、五級的,兩者在品的次第上并無固定聯系,由此否定了宮崎所云兩者之間相差四品的觀點。同時認為,鄉品僅僅是與具體官職聯系在一起的,而且也不只限于起家官職,如《晉書》卷六十六《劉弘傳》載:
被中詔,敕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南郡廉吏仇勃,……尚書令史郭貞,……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令。
胡寶國認為,仇勃、郭貞被劉弘任命為縣令前已經出仕,但他們進一步升遷仍須參考鄉品品級,這就說明鄉品并不僅僅在起家做官時有意義*胡寶國認為劉弘先稱被中詔隨資品補選,后又列兩人鄉品,那么資品就是鄉品。再引《晉書·賀循傳》“才望資品”,指出這里的資品同樣是鄉品。。進而分析《北堂書鈔》卷六十八“從事中郎缺,用第三品”,《宋書》卷六十《范泰傳》“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以及公府掾、長史、祭酒、司馬、東宮官屬與諸王師友文學等職多由獲得鄉品二品的人物擔任等事例,指出:“鄉品與任官確實有一定聯系,或是制度上有所規定,或是不成文的習慣。就官職與鄉品而言,某些具體的官職須具有某些鄉品的人擔任。所以,就個人的鄉品與任官而言,鄉品決定的只是他可以擔任的具體官職。當時人從不提鄉品與官品的等次有何聯系。”*胡寶國:《九品中正制雜考》,《文史》第36輯,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也就是說,通過從事中郎用第三品、助教用二品等例子,認為鄉品只是在官僚就任某個具體官職的時候發生作用。
閻步克在探討了各種對應說之后,認為胡寶國的觀點最為中肯,應當支持,并從以下兩個方面進行了補充。
首先根據具體史料否定官品與鄉品之間的對應關系,在此仍然舉出《北堂書鈔》卷六十八“從事中郎·山簡不拘品位”條引《鎮東大將軍司馬伷表》:“從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內山簡清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三。”*根據版本的不同,“從事中郎缺”一句后,或為“用第二品”,或為“用第三品”,關于此點,參見王鏗:《山簡鄉品考——以〈北堂書鈔〉版本異文為線索》,《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另,王鏗在此文中,主張山簡的鄉品并非三品,應為二品。并作如下分析:中散大夫官品第七,同為七品之官的有太子洗馬,號稱“清選”,其鄉品應為二品,這與官品之間相差五品。由此可見,鄉品并不與官品的各等級相對應,而是與官職相對應*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339頁。。
在地方一級,例如縣令長的鄉品也有等級之差,例如“二品縣”(《太平御覽》卷二六九引《宋武帝詔》)、“秣陵令三品縣耳”、“句容近畿,二品佳邑”*房玄齡等撰:《晉書》卷七十六《王彪之傳》,第2007頁。等,可見就鄉品而言,既有二品縣令、三品縣令,也有四品縣長。尤其是秣陵令與句容令,同為官品第六,但是鄉品卻一為三品、一為二品,這仍然顯示了鄉品與官品的不相對應,鄉品因具體官職而異。
其次,強調鄉品與官職的對應關系源自當時的法律和規定,如“從事中郎缺,用第二品”明顯是在傳述法規條文,它顯示鄉品是就具體官職而具體規定的。《南齊書》卷十六《百官志》載南齊國學“典學二人,三品,準太常主簿;戶曹、儀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禮吏八人,六品”,這是王朝為上述官職規定了鄉品。另如《齊職儀》有三條材料:
每陵令,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舊用三品勛位,孝建三年改為二品。
太祝令,品第七,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用三品勛位。
(廩犧)令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今用三品勛位。
這些都是以相當典型的格式,對官職、官品、祿秩、印綬、冠服以及鄉品資格所作的完整規定,應是王朝選簿之原貌。
據此閻步克得出結論如下:“不管把官品和中正品的對應弄得如何細致入微,它也只是一種大致趨勢而已,而不是法制規定。當時王朝從沒在制度上把二者一一對應起來,如果墨守‘差若干品’則無異膠柱鼓瑟;另一方面卻有充分證據顯示,中正品是針對具體官職而具體規定的,從而證實了胡寶國先生的論斷。”*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338頁。也就是說,諸如二品令史、三品令史、四品令史、五品令史、六品令史及二品縣、三品縣、四品縣等現象的存在,以及上述政府《選簿》所作的正式規定,都說明王朝并沒有對鄉品與官品之間的對應關系作出明確規定,就制度而言,也沒有二者形成對應關系的根據,相反倒是說明一個官職只對應著一個特定的鄉品*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342頁。。
由以上所見,針對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的對應關系,胡寶國、閻步克兩位予以了否定,認為王朝并沒有作這樣的規定,而且根據史料,主張鄉品是針對具體官職而具體規定,鄉品決定的是可以擔任的具體官職。
三、鄉品與官品的對應及其問題所在
迄今針對鄉品與官品、鄉品與官職之間的對應關系所作的討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二點:鄉品與官品的對應與否,鄉品與官職的對應關系。盡管前輩學者的研究相當精致,極具啟發性,但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本節首先探討第一個問題,即鄉品與官品的對應關系。
在討論鄉品與官品對應與否時,有必要先回顧一下首開論題的宮崎市定的論述:
要言之,制定了起家的官品大概比鄉品低四等,當起家官品晉升四等時,官品與鄉品等級一致的原則。然而,在實施過程中,想來會允許在上下浮動一個品級的范圍內酌情調整。如果上述對應關系正確的話,那么,我們應該可以從人物傳記中知道其起家官品,進而在某種程度上推測出鄉品等級。*[日]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第66頁。
我們在正史列傳中能見到的人物經歷,更多屬于打破標準形式的特殊情況。但是,如果因為各個人的情況不相符合,就完全否定原則的存在,那就麻煩了。*[日]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第76頁。
值得注意的是,宮崎反復指出的所謂對應關系,乃是鄉品與起家官品,而非鄉品與官品。而且還強調指出,這種對應關系雖然是一項原則,但也有著上下浮動的可能,并沒有那么嚴整。回頭看國內學者批判這一觀點時,所針對的正是相差非四品以及官品與鄉品的不對應。不能不說,這種批判從開始就似乎沒有對準靶心,而這當然也影響了對九品官人法制度的正確認識。

將兩位先生的解釋作一比較,可以清楚看到,閻步克是從官品推測鄉品,由此判斷兩者的不對應,而宮崎則是從起家官的官品來推出其與鄉品的關系。進一步而言,宮崎強調的是起家官品與鄉品,而非官品與鄉品的簡單對應。所以說閻步克對這條史料的解釋,似過于重視官品與鄉品,而忽略了起家官品與鄉品的關系。
稍微回顧一下,在宮崎提出了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存在四品差之后,就一直受到學術界的質疑,如矢野主稅*[日]矢野主稅:《針對魏晉中正制性質的一個考察——以鄉品與起家官品的對應為線索》,《史學雜志》第72卷第2期(1963年)。另可參見[日]中村圭爾:《六朝貴族制論》,谷川道雄編著:《戰后日本的中國史論爭》,名古屋: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后收入氏著《六朝政治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夏日新譯文見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2卷《專論》,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周一良*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七第與六品”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07頁。等等。而胡寶國、閻步克的觀點則更加鮮明,認為宮崎自己舉出的例子中就有很多不是相差四品的,因而否認兩者之間存在對應關系。但是,宮崎本身已經說明這種對應并非嚴格,而是有著浮動和例外,所以將批判對準這四品之差而發,似非問題核心所在。
相比較而言,陳長琦基本贊成宮崎的觀點,并且根據時代的變化,對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的差距作了詳細的區分,但是受到了張旭華的批判。張旭華原意是要否定陳長琦的起家與鄉品之間有著對應關系的觀點,但是仔細閱讀張文,就會發現,兩者的結論之間并沒有太大的差別。

宮崎指出所謂相差四品,只是一個原則,至于其中存在種種不符合四品的例子,只能是非原則。當你舉出例子論證非四品的時候,同時也有大量例子證明的確是四品。更有意思的是,有些例子還顯示出,一旦起家為六品官,第二官相反卻是就任七品。例如大名鼎鼎的王羲之,起家秘書郎,官品第六,而第二任官卻是庾亮的征西參軍,官品第七*房玄齡等撰:《晉書》卷八十《王羲之傳》,第2094頁。。再如王彪之,也是起家六品的著作佐郎,第二任官卻轉為七品的東海王文學。這不就暗示,從鄉品二品起家,就任官品六品的官職,其間相差四品是一個標準或是一種習慣嗎?當然,對此作過多的論證,意義并不大,其實宮崎只不過說有了鄉品以后,進入官僚世界的時候,要低于這個品級起家,發現并掌握這個大致趨勢就是意義所在。
但是,中國學者在鄉品和起家官品之外,似乎找到了另外一種對應關系,例如前面所見陳長琦的一個論斷,“某種官職如標明官品二品,就表示這種官職需要資品二品的人來擔任,標明三品,就表示這種官職需要資品三品的人來擔任”。不得不說,這種尋求鄉品與官品的統一性的說法看似比較新穎而且整齊,但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是陳長琦并沒有舉出一條相關的史料來證明這個結論,因而只能說是一種推論。再如,官品六品的秘書郎,幾乎肯定是由鄉品二品的獲得者擔任的。此外,如官品三品的尚書令、中書令,顯然不可能讓鄉品三品之人擔任。
進一步而言,倘若某人從官品三品升到二品,難道他的鄉品也要由三品升到二品嗎?實際上并不需要,因為晉宋之后除了個別的例子,也就是唐長孺所言的軍功以外,能夠做到官品三品的人,一般都是鄉品二品獲得者。就這些人而言,首先獲得鄉品,然后進入政界,從六、七品的官職起家,一直升到三品、二品,在這一過程中,當然會出現鄉品遭到貶降的情況,例如溫嶠就是如此,但一般而言,鄉品的變化并不顯著。所以陳長琦尋求鄉品與官品的統一性的這一說法,或可再論。
四、鄉品與官職的對應及其問題所在
如前所見,否認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的對應關系,重新提出鄉品與官職對應關系的是胡寶國和閻步克。胡寶國認為:“鄉品與任官確實有一定聯系,或是制度上有所規定,或是不成文的習慣。就官職與鄉品而言,某些具體的官職須具有某些鄉品的人擔任。”應該承認,發現鄉品與官職的對應問題是中國學者的一大貢獻。以下,我們就來分析這種對應關系。所謂“某些具體的官職須具有某些鄉品的人擔任”,按照二位先生所舉材料,最典型的就是從事中郎用第二品、助教用二品。但是我們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
從事中郎、助教均為六品官,由鄉品二品獲得者擔任。晉宋以降,就任六品官以上者基本上都是獲得了鄉品二品的,到梁武帝天監改革以后,十八班官制之下有流外七班,即“位不登二品者,又為七班”*魏征等撰:《隋書》卷二十六《百官上》,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733頁。,也同樣說明十八班內的官職全都由鄉品二品的人物擔任*宮崎市定的研究首先認為,梁代十八班由宋齊以來六品以上官組成。張旭華后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梁之十八班是將宋以來的八品以上官分為十八班,九品官則無一進入十八班。見《蕭梁官品、官班制度考略》,《九品中正制略論稿》,第241頁。祝總斌也對宮崎的研究作了修正,指出梁代十八班不是宋制六品以上,而是七品以上的重新組合。祝總斌:《門閥制度》,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7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后以《試論魏晉南北朝的門閥制度》為題收入氏著《材不材齋文集——祝總斌學術研究論文集》下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18頁。。即便按胡寶國、閻步克所論,朝廷規定了從事中郎、助教與鄉品二品的對應,但進入六品官這一級別的幾乎全是鄉品二品的獲得者,那么專門對這兩個官職作出鄉品的規定究竟有何意義呢?更重要的是,以這兩條材料來強調“某些”官職和“某些”鄉品的對應,則似乎忽略了更多的官職與鄉品的關系。
實際上閻步克在回答汪征魯“鄉品是與所有的具體官職對應,還是僅僅與某些具體官職對應”這一疑問時說“我們明確回答以后者為是”*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343頁。,也似乎沒有將這種個別對應放大到整個九品官制之中。拿溫嶠為例,前面已見,他首先是舉秀才、灼然,也就是獲得鄉品二品,再據《晉書·溫嶠傳》看其后的官歷(括弧內為官品):
司徒辟東閣祭酒(七)→補上黨潞令(七)→平北大將軍(劉琨)參軍(七)→平北大將軍從事中郎(六)→上黨太守(六)→司空(劉琨)右司馬(六)→丞相(司馬睿)左長史(六)→散騎侍郎(五)→驃騎王導長史(六)→太子中庶子(五)→侍中(三)→中書令(三)→丞相(王敦)左司馬(六)→丹陽尹(三)→江州刺史(四)、持節都督(二)、平南將軍(三)→驃騎將軍(二)、開府儀同三司(一)。
按照胡寶國、閻步克的觀點來看,溫嶠的鄉品二品顯然是與其平北大將軍從事中郎這一具體官職相對應的,可是難道就與他所就任的其他官職無關嗎?如果無關,為什么會出現因鄉品不過亦即遭到貶降之后,需要皇帝特別發詔的問題呢?由此可見,鄉品是與溫嶠所升任的每一個官職都有關系的,不可能在他所有的官歷中,存在某些官職需要鄉品,而某些官職無須鄉品的情況。
綜合以上所述,考慮到進入六品官以上或者說十八班以內的幾乎全都為鄉品二品之人,用“某些”官職與“某些”鄉品對應的說法,就顯得不太全面。即便六品官以下,例如七品、八品之中,存在著鄉品二品及其以下者就任的例子,但這只是鄉品等級的不同,而不是某些官職與某些鄉品的問題。
接下來需要探討的的是,這些官職是否都由王朝作了鄉品的規定呢?
胡寶國、閻步克判斷鄉品與官品不對應以及鄉品與官職對應的主要標準,就是認為王朝對鄉品和官職的關系作出了具體的規定,也就是強調有法律、法規的支持,按照閻步克的話來說,“王朝正式規定了某官的任用資格為中正某品”*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344頁。。這里主要依據的史料為兩類,一類還是從事中郎和國子助教。針對前者,即“從事中郎缺,用第二品。中散大夫河內山簡清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三”作了如下分析:
玩“從事中郎缺,用第二品”語氣,這句話顯然是在傳述法規條文。這種條文顯示,中正品是就具體官職而具體規定的。因為從事中郎須用中正二品之人,而中散大夫山簡“品儀第三”,低下一等,所以司馬伷在打算辟他作從事中郎時,就必須上表特請開恩了。*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339頁。
“從事中郎缺,用第二品”,是司馬伷上表時的一句話,是否就是法規條文或王朝的正式規定,實際上并不能確定,或許是在陳述一種慣例。而“中正品是就具體官職而具體規定的”,這一句就比較費解了。按照閻步克的意思,似乎鄉品二品是針對從事中郎這一具體官職而具體規定的。一般而言,鄉品是由中正為20歲左右的年輕人所下的評價,吏部在授予官職時需加以參考。溫嶠正是帶著這個鄉品進入政界的,而且因為他是二品,所以可以就任從事中郎這一職位。但絕不能說,他的二品就是具體針對從事中郎這一官職而具體規定的。前面已述,其所歷所有官職都與這個二品有關。由此來看,閻步克解釋此條太過注意“具體”,而忽略了二品之人可以就任包括從事中郎在內的其他官職。因此,將此句解釋為“從事中郎缺人,該職位是由鄉品二品者擔任的官職”,似更符合原意,而不必從王朝的規定上理解。
如果說“從事中郎缺,用第二品”這一句是否為法律條文,還需斟酌的話,《宋書·范泰傳》中的“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一句,則基本可以排除法規的可能性。首先看此文:“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穎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準之弟。”再看閻步克的分析:
《宋書·范泰傳》曾提到“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可知西晉朝廷為國子助教一官具體規定了中正二品的資格。……而這也是就具體官職來作具體規定的,并沒有涉及官品高下。*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339頁。
范泰為劉宋時人,他在談論西晉國子時,援引了此例,即陳載起家太保掾,其鄉品自然為二品,后來國子取其為助教,這也就是西晉時鄉品二品任助教的情況。從前后語句來看,并非強調西晉朝廷在法律上為國子助教一官具體規定了鄉品二品的資格,而只是在作一般性的陳述,更何況范泰根本沒有必要使用前朝的法律或規定。
還可以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即如果認為這兩個例子是法律條文的話,那就似乎沒有理由僅僅只對這兩個官職作出鄉品的要求,因為比起從事中郎和國子助教,還有相當多更為重要的官職。而針對這些官職的鄉品規定,完全不見于正史或《通典》、《唐六典》等。盡管該時期的相關史料極其有限,但還是讓人覺得不可思議。例如同為第六品的秘書郎,據《唐六典》卷十引《晉令》:“秘書郎中品第六,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再看著作佐郎,同樣是《唐六典》卷十引《晉令》:“著作佐郎品第六,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晉令》以外,《北堂書鈔》卷六十六引《晉起居注》也有一條記載:“武帝太康八年詔曰:‘太子率更仆,東宮之達官也。其進品第五,秩與中庶子、左右衛率同職,擬光祿勛也。’”需要注意的是,晉武帝通過詔書的形式提到某個官職的時候,并沒有直接涉及鄉品如何。即便是國子助教,據《唐六典》卷二十一的記載:“晉武帝初立國子學,置助教十五人,官品視南臺御史,服同博士。”同樣看不到針對鄉品的規定。
以上種種,都在說明根據現有的史料,還無法得出晉代在法律上或條文上為具體官職規定了鄉品的結論。盡管如此,閻步克在判斷朝廷對某些官職作出了鄉品的規定時,另外舉出了一些極為重要的材料。如前引《南齊書·百官志》所載南齊國學中的典學、戶曹、儀曹、白簿治禮吏以及《齊職儀》所載每陵令、太祝令、廩犧令等等。應該承認,這些的確是政府對上述官職所作的鄉品規定。對于這些史料,應作如何理解呢?對此,筆者想提出兩點看法:
第一,這些例子全都屬于南朝,也就是門第日趨固定的時期,前述唐長孺已經指出,此時除了軍功以外,從卑品亦即二品以下升遷到上品亦即二品的可謂“絕無僅有”。

從這兩點來看《南齊書·百官志》以及《齊職儀》有關官職與鄉品的記載,似乎給我們這樣一個印象:南朝時期,朝廷能夠作出規定的僅僅限于鄉品三品及其以下者。如前所述,進入梁代十八班制以內的幾乎全為鄉品二品獲得者,因此對于這些官職的鄉品,無需朝廷另外作出特別的指示或規定。
綜合以上兩節所述,首先,鄉品只是與起家官品存在著對應關系,而不是與官品有規律性對應;其次,這種對應呈現出大致趨勢,相差四品應是一個大致的原則,有著上下的浮動;第三,鄉品與官職之間也有緊密聯系,但并不能以這種關系替代或者否定鄉品與起家官品的對應。這種聯系,并非如胡寶國、閻步克所言,為某些具體官職與某些鄉品相對應,而是如晉宋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內官職需由鄉品二品者擔任那樣,九品官制以內的絕大多數品官都需要具有鄉品的資格。此外,針對官職所作的鄉品規定,南朝以前,還不能確認為國家法律或條文,南朝以降,這些規定主要出現在鄉品三品及以下的獲得者身上。
五、結語
具有相對于皇帝權力的自律性,這是理解六朝門閥貴族所具有的歷史性,進而探討中古社會性質的重要線索。谷川道雄針對九品官人法中鄉品與官品的對應關系作了獨到的理解,即鄉品決定官品,說明貴族的本源不在王朝內部,而在其外部。本文據此重新審視鄉品與起家官品、鄉品與官職之間的對應問題,得出如下結論:鄉品不但如宮崎市定所言,與起家官品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對應關系,而且還與九品官制之內的絕大多數官職相聯系。
然而,在九品官人法的研究中探討上述對應關系究竟有什么樣的意義呢?胡寶國說:“當時人從不提鄉品與官品的等次有何聯系。”這句話很重要,的確沒有將鄉品與官品高低聯系起來的材料,但是宮崎所推論出來的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的大致對應關系,也是通過史料得出的一種結論。閻步克說:“中正品較高則起家官品也較高一些,對此趨勢我們并無異辭,但至今沒人能夠確鑿舉證,王朝明文規定了任何直接對應。”也就是并不否定這一大致的對應。我們可以就此提出一個問題,即為什么王朝沒有明確規定,但卻會出現這種趨勢呢?我們所要研究的,難道不正是這種趨勢所反映出來的史書記載背后的歷史真實嗎?閻步克還有另外一個表述:“不管把官品和中正品的對應弄得如何細致入微,它也只是一種大致趨勢而已,而不是法制規定。”*閻步克:《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第338頁。在我們看來,或許并非法制規定,但卻是一個大致的趨勢,這實際上也就說明,鄉品與起家官品之間的大致對應關系是法制規定以外存在著的某種影響官僚體制的習慣或意識。應該說,這一點才是問題的核心之所在。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理解鄉品的存在,也就是說為什么鄉品會在貴族起家、王朝任命或晉升官職以及貴族官僚的整個官歷之中持續不斷地發生作用?可以說,前輩學者在研究鄉品與官品或者鄉品與官職的對應時,承認大致的趨勢也好,主張具體的對應也罷,并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從溫嶠這樣擁有鄉品二品之人所經歷的官歷來看,首先是有鄉品,有了鄉品才能起家,才能就任具體的官職,當鄉品遭到貶降后,晉升官職時便需要皇帝特別發出詔書。十分清楚,在鄉品、官品、官職這三者中,鄉品最為重要。唐長孺說,鄉品與貴族入仕的途徑關系密切。張旭華也指出,鄉品決定了貴族的入仕資格。對此,我們可以再補充一點,即鄉品還是貴族就任每一個官職的前提。一個貴族從起家到其后的晉升官職,整個過程始終擺脫不掉鄉品的存在和影響。
那么,應該如何理解鄉品的這種特性呢?根據本文的分析,可作以下提示:前面反復談到,進入晉宋時期的六品官以上或梁朝十八班以內的全是鄉品二品獲得者。這就顯示出,并不需要王朝對其中每個官職都做鄉品的規定,同時與王朝對鄉品三品以下者所做的規定結合起來看,國家權力所能實施的影響似乎只及于鄉品二品以下。也就是說,探討鄉品與官品或鄉品與官職的對應關系固然重要,但是具有獨立于官僚任職制度以外,并且得到鄉論支持的鄉品與國家權力發動之間的關系更應受到關注。我們認為,源于鄉論的鄉品,是門閥貴族在社會性與政治性這兩方面呈現出自律于皇權的決定性因素,它的存在,除了反映九品官人法的獨特性以外,還充分說明,探討中古社會的時代特質時,不能過分強調皇權自上而下的作用或者圍繞皇權的強弱變遷而立論,而應對門閥貴族具有源于地方鄉黨社會的自律性因素予以更多的重視。
[責任編輯范學輝]
作者簡介:李濟滄,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江蘇南京210023)。
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9世紀中國與東北亞各國關系研究”(15BZS038)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