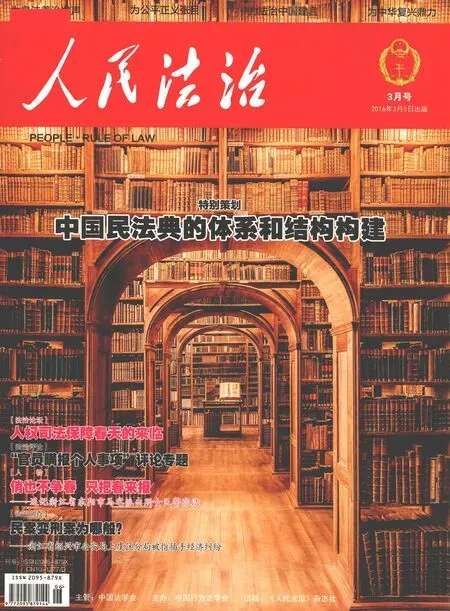環境權益的民法表達
——基于民法典編纂“綠色化”的思考
文/王旭光
環境權益的民法表達
——基于民法典編纂“綠色化”的思考
文/王旭光
如何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回應環境問題挑戰,實現民法制度的生態化拓展,在審判工作中統籌處理好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當前與長遠等多重關系,是當前民法學、環境資源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中國的民法典編纂,必須反映21世紀生態國家時代的社會關系,反映資源環境逐漸惡化的社會特征,應以綠色、正義、弘揚人文與自然精神作為重要的價值目標。
2014年,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加強市場法律制度建設,編纂民法典”。民法是市民社會的基本法,民法典編纂之舉是立法史上的大事業,國家千載之利害、生民億兆之休戚,均依此而定。民法典編纂需要有宏大開闊的視野和面向當下問題的意識,需要民法學與法理學、經濟法學、環境法學等不同學科的對話,需要法典編纂與法學理論研究、司法審判實踐的互動。
民法典編纂“綠色化”的整體構想
黨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對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作出了專門部署。2015年,中央先后審議通過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和《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進一步明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任務目標和重要措施。十八屆五中全會對生態文明建設再次作出專門部署,并將“綠色”確定為十三五時期必須樹立的發展理念。如何踐行綠色發展理念,回應環境問題挑戰,實現民法制度的生態化拓展,在審判工作中統籌處理好人與自然、經濟與環境、當前與長遠等多重關系,是當前民法學、環境資源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面對的重大課題。中國的民法典編纂,必須反映21世紀生態國家時代的社會關系,反映資源環境逐漸惡化的社會特征,應以綠色、正義、弘揚人文與自然精神作為重要的價值目標。
整體而言,民法典編纂的“綠色化”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價值理念的生態倫理化、基本原則的綠色改造、民事主體的適當擴張、權利體系的生態化拓展、權利救濟體系的私法構造等多個方面的問題。民法典的制定,應在尊重民法邏輯自洽和制度體系的前提下,在基本精神、理念和原則上順應生態規律、回應時代關切,為環境資源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留有足夠空間。
環境權益民法表達的必要性分析
民法典編纂“綠色化”以環境權益的民事立法化為核心表現。現行民事立法中關于環境權益保護方面的規定,主要集中在侵權責任和相鄰關系兩個方面,但在定位上存在問題:一是環境權益侵權責任構成上最終仍落腳于民事主體的人身或者財產損失,單純的污染環境本身不構成民事責任,失卻了侵權責任法以及侵權責任法司法實踐創設和催生環境權利(益)的應有功能;二是與環境有關的相鄰關系主要涉及通風、采光、油煙、噪聲、惡臭等小范圍環境權益,對從整體上確立民事主體環境權益意義有限,且傳統民法上相鄰關系多用以處理鄰里關系,將其升華為環境制度需在價值尺度上做較大調整。尤其是《民事訴訟法》第55條和《環境保護法》第58條雖然規定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但其訴權理論和所對應的實體民事權利卻處于缺位狀態,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實踐和發展造成困難。實體法上請求權基礎的確立是法律解釋適用的邏輯起點。環境權益的民法表達是民法典編纂“綠色化”和環境民事審判實踐共同面對和亟需解決的問題。
傳統民法學者多因環境權權利主體不特定而拒絕接納,但民事權利主體特定是歷史現象而非邏輯必然,環境權主體的廣泛性并不排斥其權利內容的民事性。實際上,環境權作為一個權利類型能否進入民法典主要涉及民法上兩個基本問題:一是民法上究竟有哪些民事權利,二是誰有資格成為民法上的民事權利主體。對第一個問題的實證考察表明,不僅我國民法通則、擔保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等民事法律對民事權利的列舉不相一致,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等不同國家和地區關于民事權利的范圍界定也有不同。民事權利體系是開放的不斷變化的體系,環境權納入民法并不存在“門檻”上的障礙。由此引發第二個根本性的問題,即環境利益是否可以被權利化從而成為民法上的權利?實證表明,以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為背景凸現出來的對環境利益的權利需求激增,現有的民事權利不能提供足夠的制度保障。環境侵權行為的二元性、環境侵權責任的雙重性以及環境侵權糾紛的復合性,使得環境權及其背后的利益難以為現有權利類型所包括,現有民法規范無法為環境權益提供充分保護。環境民事審判中普遍存在法官難以“找法”和不同法域的規范不成體系的困境。解決難題既需要以公權限制私權,也需要將公法義務納入私權體系,兩種路徑則分別對應環境法的系統化和民法典的綠色化。民法典的制定,應在對傳統民事權利體系進行揚棄的基礎上回應環境權益保護需求,改變環境法和民法相互割裂的現實,通過確立民法上的環境權來實現兩個法域的溝通,構建完整的環境保護請求權規范體系。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環境權的形成和成熟亦面臨與民法上既有權利的關系、內涵外延的界定以及司法實踐的發展等諸多問題,需要理論界和實務界共同推動。
環境權益的類型化研究和民法上的制度設計
環境權并非一項孤立權利,而是以環境為客體形成的一束權利或者權利體系。事實上,即使環境權肯定論者對環境權的內容也存在不同認識。從權利主體來看,最廣義的環境權包括公民環境權、法人環境權、國家環境權和自然體環境權。從權利內容來看,包括實體性環境權和程序性環境權,前者有生態性權利如清潔空氣權、清潔水權、景觀權等,也有經濟性權利如自然資源所有權、自然資源利用權、環境容量權等;后者則包括環境知情權、環境決策參與權和訴諸司法權等。環境權中各種權利的性質、構造各不相同,各自演進和法治化程度也不同。民法典的制定應基于類型化的研究路徑,針對不同類型的環境權利作出不同回應,尋求具有科學性、現實性和可行性的內容涵蓋和制度設計。
從權利類型看,與民法典相關的環境權利主要包括國家的自然資源所有權、企業的自然資源利用權和環境容量權以及公眾環境權。其中,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權在公法意義上作為自然資源主權的替代概念,可形成自然資源管理權力的理論基礎,在私法意義上則是非所有者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權源。民法典的制定應注重其多重構造的特殊屬性。如自然資源利用權,我國現行物權法中已將其定位為用益物權,其與典型的用益物權并沒有本質差別,只是在權利行使過程中具有較大的環境負外部性,在民法典的制定中可在對其財產權屬性予以確認的同時,采用但書或者轉致等立法技術將控制負外部性的管理性規定指引至相應的環境資源立法之中。再如公眾環境權,《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中明確指出,“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 環境作為公眾共用物的品性,已為我國政府、學界和社會所共識。共用物是傳統民法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如《法國民法典》第714條規定:“不屬于任何人之物,得為公眾共同使用之。有關治安的法律規定此種物的使用方式。”域外立法例中亦多在公眾共用物、公眾共用物使用權與環境公共物品、環境權之間建立聯結。民法典的制定,應參照、借鑒傳統民法理論和域外立法實踐,回應社會共識,引入“共用物”概念。為作為公眾共用物的環境資源提供權源,并從公眾共用物、公眾共用物使用權和環境權的維度出發,構建環境資源法學自身的概念體系、理論體系和規范體系,為發展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和環境資源司法專門化提供理論基礎和法律依據。
加強對環境權益的多元化實證研究
盡管從立法論的立場來看,各種實證研究方法的成果必須經由法教義學的路徑才能整合到法律實施之中。任何忽略現行法上的依據去討論法律層面上的解決方案,都會背離法治最基本的要求。但同時,法律非經解釋不得適用,法官亦不得以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不完備為由拒絕裁判。在環境權益民事立法缺失的情況下,應通過民法解釋學的方法對現有的民法概念、制度和規范進行有利于環境資源保護的解釋。從解釋論的立場出發,通過司法解釋、案例指導、實證研究來分析闡明法律適用中的疑義,推動司法三段論的適用,在個案裁判中容納、包含綠色理念,實現環境正義、保護環境權益。
民法典的制定在基于人們對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共識,加大對具體環境法律制度配置的同時,應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切實推動、實現法解釋學、法社會學等方法論的運用與轉化,回應民法學的實踐性品格,在民法學理論研究、民法典編纂和民事審判實踐之間構建良好互動和良性循環。就環境民事審判而言,通過民法典的“綠色化”,在民法典中完整體現對環境權益的全面保護,才能有力地推動司法實踐,而獲取更多實踐經驗,才能形成、豐富中國特色的環境法學和環境司法實踐理論。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環境資源審判庭副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