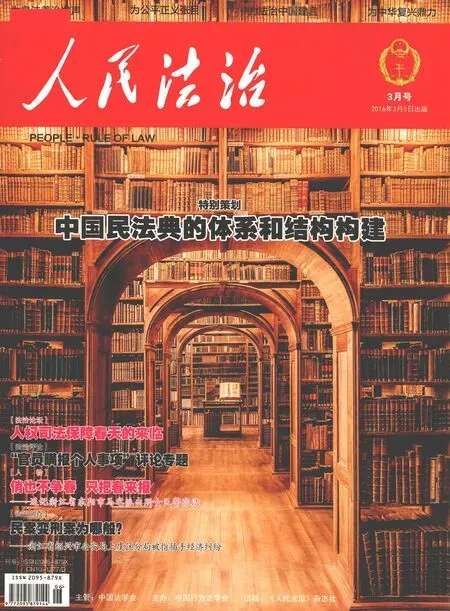期盼漢語世界的民法典
——以“合同”概念取代“法律行為”切入
文/申惠文
期盼漢語世界的民法典
——以“合同”概念取代“法律行為”切入
文/申惠文
正義需要法律,法律需要語言。我國民法典應當是中國語言的集大成者,應當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如果我國民法典采用的概念不符合漢語的基本語義,便很難獲得民眾的認同,也就很難走向世界,成為21世紀具有標桿性意義的民法典。
語言是民法典的生命,我國民法典編纂必須采用規范的漢語,用中國語言描述中國人的生活場景。德語世界的“法律行為”,是以意思表示為要素的設權行為,僅為民事行為的一部分。而漢語世界的“法律行為”,是指法律意義上的所有行為,包括犯罪行為和行政行為等。《民法通則》創設的“民事法律行為”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德語翻譯的困境,但依然與漢語語義相差甚遠。《合同法》采取廣義“合同”概念,已經替代“民事法律行為”。不制定《民法總則》,只啟動《民法通則》的修改,刪掉“民事法律行為和代理”一章,修改完善“基本原則”、“公民(自然人)”、“法人”和“民事權利”等章節。不制定債權總則,采取合同法、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依次遞進的民法典結構,符合漢語的思維規律,通俗易懂、層層遞進,符合社會大眾對民法典的期盼。
2015年6月,中國法學會民法典編纂項目領導小組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民法總則專家建議稿(征求意見稿)》第六章的標題是“法律行為”。2015年9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公布的《民法總則(室內稿)》第五章的標題是“法律行為”。梁慧星教授、王利明教授、徐國棟教授和龍衛球教授分別主持的民法典總則建議稿,也都專章規定了“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是德國民法典的基礎概念,在德語語境下相對容易理解。而漢語世界的“法律行為”與德語世界的“法律行為”卻明顯不同,如果我國采納“法律行為”的概念,就會產生“違反法律的法律行為無效”的表達,而這種表達不符合漢語語法,民眾無法理解,中文系學生也無法理解。中國夢需要中國民法典,中國民法典需要中國語言,中國語言可以走向世界。
漢語世界的“法律行為”不同于德語世界的“法律行為”
日本學者借用漢語中的“法律”和“行為”兩個詞,把德語“Rechtsgeschaft”譯為“法律行為”。“Rechtsgeschaft”是由“法律”(Recht)和“行為”(Geschaeft)兩個詞合成,中間加了一個連詞符s。德語中的“Geschaft”一詞主要是指“交易”,并非關于“行為”最為常用的詞。因此,德語“Rechtsgeschaft”可以翻譯為“交易行為”“設權行為”。德語表示“行為”,最常見的詞語是“Handlungen”。如“侵權行為”使用的是“unerlaubten Handlungen”一詞。“Rechtshandlung”可以翻譯為“法律行為”,即法律調整的所有行為的總稱。
我國民法學者所稱的“法律行為”與德語“Rechtsgeschaft”對應,并非是“符合法律的行為”,而是“意欲發生私法上效果的行為”。法理學者所稱的“法律行為”與德語“Rechtshandlung”相對應,是指“法律意義上的行為”“法律調整的行為”“能夠引起一定法律后果的行為”。德語世界是兩個單詞,漢語世界是一個單詞,這就造成中國民法學界和中國法理學界長期的論證。民法學者所稱的“法律行為”,實質上可以翻譯為“表意行為”“交易行為”“設權行為”。《民法通則》創設“民事法律行為”概念,在一定程度解決了德語概念翻譯的困境,緩解了民法學界和法理學界的概念紛爭,但與漢語語義依然相差很遠。
目前主流學者和幾位民法典總則建議稿學者均主張將“民事法律行為”改為“法律行為”,與德國民法典的概念保持一致。此舉脫離了中國語境,不僅不符合漢語基本常識,還抹殺了《民法通則》的改革嘗試。生搬硬套德國法上的“法律行為”概念,即便與國際接軌了,但也與中國漢語脫軌了。在漢語世界中,無論如何解釋“法律行為”這四個字,也無法解釋為“私法自治的工具”。基于準確性和嚴謹性,法律專業術語即使可以脫離日常語言,但也應當符合基本的語言規范。正義需要法律,法律需要語言,語言需要傳播。我國民法典應當成為中國語言的集大成者、成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作品。如果我國民法典采用的概念不符合漢語的基本語義,便很難獲得民眾的認同,也就很難走向世界,成為21世紀具有標桿性意義的民法典。
我國民法典應當用“合同”概念取代“法律行為”
我國民法典可使用“合同”概念來取代“法律行為”概念,不必保留“民事法律行為”概念,或創設“表意行為”概念。法律行為實質是對1/12事物的抽象,是以合同為模板編制的行為規范。《合同法》與《民法通則》并非簡單的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還具有新法和舊法的關系,“合同”概念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取代“民事法律行為”概念。
1.合同”概念取代“法律行為”的必要性。第一,身份法律行為是偽命題。根據學界通說,法律行為可分為財產行為和身份行為,然而財產行為與身份行為具有重大區別。財產行為可以分為單方行為、雙方行為和多方行為,而單方的婚姻、多方的婚姻在法律上是不可行的;受欺詐的婚姻、重大誤解的婚姻、顯失公平的婚姻,是無法撤銷的;也不存在無權代理的婚姻、無權處分的婚姻。此外,婚姻也不能附條件、附期限。合同簽訂后,原則上不能單方解除,而結婚后,如感情破裂,則可以離婚。身份行為的自治空間非常有限,法律行為原則上只適用于財產行為。如此,法律行為就是對1/2事物的抽象。
第二,物權行為是偽命題。根據德語世界的民法典,財產行為包括債權行為和物權行為。買賣一根黃瓜包括3個行為,買賣一根黃瓜的債權行為、移轉黃瓜所有權的物權行為和移轉貨幣所有權的物權行為,而按照漢語世界的理解,物權契約或物權合意不具有法律拘束力,只是重復債權合意。法律行為實質上就是債權行為,如此,法律行為就是對1/4(1/2×1/2)事物的抽象。
第三,單方行為和多方行為可以參照雙方行為。按照傳統理論,債權行為可以分為單方行為、雙方行為和多方行為。單方行為可以視為準契約,如我國合同法司法解釋已經將懸賞廣告定位為合同。多方行為是團體行為,包括各種決議,如股東會決議、董事會決議等屬于廣義的合同。單方行為和多方行為必須依附于雙方行為,立法技術要求將雙方行為作為一般規定,然后參照適用。如此法律行為就是對1/12(1/2×1/2×1/3)事物的抽象。
2.“合同”概念取代“法律行為”的可行性。1986年頒布的《民法通則》第四章“民事法律行為和代理”已經失效,不再具有法律效力。當時以佟柔教授為代表的學界主流觀點認為,民法的調整對象是我國社會主義商品關系。王漢斌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草案)〉的說明》中指出:“這幾年民事糾紛、特別是經濟糾紛大量增加,迫切需要制定需共同遵循的規范,使民事活動有所遵循,調整民事關系有法可依。民法是反映社會經濟關系的,民法的準則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綜上,《民法通則》的制定者,無意去解決婚姻家庭糾紛,也無意去解決繼承糾紛,而主要解決有計劃商品經濟的法律構建問題。《婚姻法》自1980年9月頒布,直到2001年才進行修改。而《繼承法》自1985年4月頒布以來,至今尚未修改。
1999年頒布的《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第三章“合同的效力”和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等基本替代了《民法通則》第四章的功能。《合同法》第2條將“合同”定義為“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具有較強的包容性,可以涵蓋股東大會決議、董事會決議等多方行為。司法實踐擴大“合同”的概念,把單方法律行為也視為一種合同,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3條對懸賞廣告的規定。總之,將《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第三章“合同的效力”和第二十一章“委托合同”等內容剝離,抽象加工形成“法律行為”和“代理”兩章,一方面破壞了《合同法》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也沒有太多的制度創新價值。
3.“合同”概念取代“法律行為”的合理性。合同是中國土生土長的概念,具有明顯的符號優勢。從社會需求來看,新時期民法典承載著思想啟蒙的文化重任,需要大力弘揚契約至上的精神,追求通俗易懂的文風。新時期需要弘揚契約精神,需要民法典通俗易懂,需要培育市民社會。法律至上意味著良法,意味著限制公權力、保護私權利,也意味著社會生活契約化。契約意味著合意,意味著意思得到尊重,也意味著自由得以實現。崇尚契約,堅守契約至上,無論對公法還是私法都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法律至上的命題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轉換為契約至上,把契約作為社會主導、作為衡量權利義務的標尺。采納“合同”概念可以倡導通過契約的社會治理引導政府遵守契約觀念,以實現法治的夢想。
啟動修改《民法通則》,而非制定《民法總則》
主流觀點主張按照德國民法典的模式制定《民法總則》。然而制定德國式的《民法總則》,同時啟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和婚姻法等單行法的修改,立法成本過高,也不具有可操作性。民法總則最核心的是法律行為,法律行為最核心的是合同,而合同的成立及效力等問題已經通過《合同法》予以解決。此外,權利客體也即物的法律規范是民法總則的另一個核心內容,也就是關于物的法律規范。《物權法》采取了廣義的“物”的概念,規定不動產和動產、原物和孳息、主物和從物等“物”的類型,因而沒有必要再對“權利客體”或者“民事權利客體”予以規定。因此,將現行《合同法》和《物權法》等諸多條文調整到《民法總則》中,并沒有實質法律意義。
官方對于民法典的表述是編纂而非制定,這便意味著需要更加尊重現有的立法資源,而絕非推倒重來。尊重現有的立法資源,著眼于現有制度缺陷的完善,方能使民法典肩負起頂層制度設計的歷史使命。《合同法》《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是我國民法典編纂應當科學對待的本土資源,在《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和《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適用法》等法律已經出臺的背景下,《民法通則》可以繼續發揮作用的內容少之又少。據此,應當盡快啟動《民法通則》的修改,刪掉“民事法律行為和代理”一章,修改完善“基本原則”、“公民(自然人)”、“法人”和 “民事權利”等章節。
采取合同法、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依次遞進的財產法結構
我國民法典不應當制定債權總則,而應當采取合同法、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依次遞進的三元財產法結構。債權物權的二元劃分是一種形式理性,而按照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的邏輯編排,也是一種形式理性。合同法與物權法相鄰,作為廣義的交易法;侵權責任法置后,作為絕對權救濟法,符合邏輯體系的要求。該模式擴大了合同法的內容,縮減了物權法的內容,同時又擴張了侵權責任法的內容,是歷史的、邏輯的和現實的統一。
從立法史看,先制定合同法,其后制定物權法,最后制定侵權責任法,后制定的法律對先前的法律有一定的補充和修正,我國已經成了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的三元民法典結構。我國民事立法先繼受德日、后繼受蘇聯,現又繼受英美,多元法律繼受形成新的邏輯關系。《德國民法典》于1896年8月24日公布,1900年1月1日才實施,其歷史使命只是形式上統一既有的私法制度,債權物權并列的二元財產法結構,是德國法學家對現實生活的一種建構,而不是唯一的建構。
從法律規范看,我國合同法應當排列在物權法之前,物權法應當排列在侵權責任法之前。《物權法》共使用40次“合同”,14次“協議”,77次“約定”,包含大量的合同規范。物權法規定的合同是合同法的特別規定,物權變動要以合同為前提,因此合同法應當排列在物權法之前。關于“責任”二字,《民法通則》使用了77次,《合同法》使用了91次,《物權法》使用了23次,《侵權責任法》使用了168次。民事責任制度是現行民法體系的重要特色,民事責任思維比民事請求權思維更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侵權責任法吸收了物權請求權的內容,物權法對物權保護的功能位移到侵權責任法,因此物權法應當排列在侵權責任法之前。如此我國財產法的結構,應當采取合同法、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依次遞進的邏輯順序。
合同法、物權法和侵權責任法應當合理分工,盡可能避免制度的錯位和越位。現階段應當按照財產法三元結構的要求,整合并修改現行的法律體系。啟動合同法的修改,將擔保法中保證合同和定金合同等內容整合到合同法中,及時廢止擔保法;無因管理準用委托合同的規定,可以通過立法技術,囊括到合同法中;不當得利屬于民法中的兜底性規定,可以規定在總則中,實現其統領整個民事領域的功能;《合同法》第133條買賣合同標的物所有權轉移的規定等內容以及《物權法》第32-38條物權保護的規定,應當適時刪除;此外,《侵權責任法》要適時對返還原物、排除妨害和消除危險的侵權責任作出特別的規定。
(作者系鄭州大學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