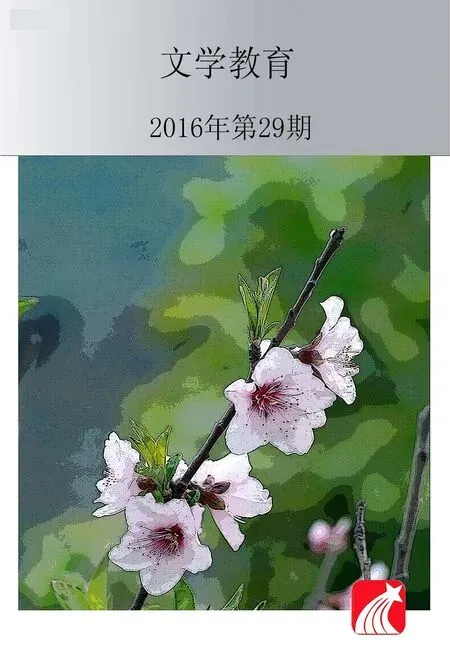《多余》中的沖突關(guān)系及文化反思
劉淑華 丁夏林
《多余》中的沖突關(guān)系及文化反思
劉淑華 丁夏林
李翊云因斬獲國(guó)際大獎(jiǎng)而聲名大噪,其小說(shuō)凝練精悍,以描寫(xiě)小人物的瑣碎生活來(lái)表達(dá)其對(duì)人性的探討。《多余》為其典型的一幅短篇小說(shuō)。文章擬從三個(gè)沖突關(guān)系即:人與社會(huì),人與他人,人與自己的關(guān)系入手,以具體文本分析為方法,深入文本,對(duì)三種關(guān)系進(jìn)行分析并以此進(jìn)行文化反思。通過(guò)對(duì)《多余》的分析,以管窺豹,領(lǐng)悟李翊云小說(shuō)的獨(dú)特魅力,傾聽(tīng)她的“孤獨(dú)之聲”。
《多余》 孤獨(dú)之聲 小人物 沖突關(guān)系 文化反思
一.背景介紹
自文學(xué)傳統(tǒng)以來(lái),短篇小說(shuō)就有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價(jià)值和魅力。弗蘭克奧康納認(rèn)為要判斷短篇小說(shuō)家是否優(yōu)秀,我們不妨看看他們是否刻畫(huà)出一系列的令人難忘的淪落人的形象。短篇小說(shuō)關(guān)注底層民眾的生命與命運(yùn),而短篇小說(shuō)之為短篇小說(shuō)的關(guān)鍵在于它對(duì)這樣的邊緣群體體現(xiàn)出的本能興趣,它是一種將自己與邊緣民眾的命運(yùn)聯(lián)系在一起的“孤獨(dú)之聲”[1]。2005年弗蘭克奧康納國(guó)際短篇小說(shuō)大獎(jiǎng)的獲得者李翊云憑借《千年敬祈》獲得此殊榮,這使得這位華裔女作家獲得文學(xué)名聲和關(guān)注。該獎(jiǎng)的評(píng)委會(huì)對(duì)其小說(shuō)的評(píng)價(jià),稱(chēng)“它展現(xiàn)出一種短篇形式令人欽佩的駕馭,不斷展現(xiàn)出非常絢麗的瞬間”。李翊云沉著客觀的敘事口吻,平淡無(wú)奇的含蓄敘事之下暗流涌動(dòng)。她著力去刻畫(huà)那些小人物以及他們命運(yùn)被吞沒(méi)的微小時(shí)刻。當(dāng)然,不得不提的是,李的小說(shuō)人物刻畫(huà)尤為迷人,通過(guò)描寫(xiě)他們的瑣碎生活來(lái)表達(dá)對(duì)人類(lèi)生存苦難以及人類(lèi)精神普世的感悟和關(guān)懷。
李翊云堅(jiān)持用英語(yǔ)寫(xiě)中國(guó)故事,而且拒絕翻譯成中文,這使她備受爭(zhēng)議。而李翊云解釋道:中國(guó)背景是不可抹掉的印記。她希望她的讀者更好的去關(guān)注她的人物,關(guān)鍵是人的本質(zhì),不管你是從哪個(gè)國(guó)家出來(lái),人性是共通的。正是由于李翊云堅(jiān)持自己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繼承關(guān)注小人物的命運(yùn)的文學(xué)傳統(tǒng),通過(guò)自己的不同感悟,發(fā)出自己的“中國(guó)聲音”。
二.《多余》
小說(shuō)《多余》是李翊云用其獨(dú)特的眼光去審視小人物的生存和精神境遇的典型作品,是她為底層民眾發(fā)出的“孤獨(dú)之聲”。《多余》主要講述了一位下崗女工林奶奶的故事。林奶奶是工廠的一位普通女工,然而工廠體制改革,林奶奶被迫下崗,后經(jīng)人介紹嫁給患病的老唐。不幸因一次意外老唐去世,而后林奶奶被介紹到一個(gè)貴族學(xué)校做工,然后跟學(xué)校里的學(xué)生小康做朋友,對(duì)其呵護(hù)照顧,后又因小康的一次惡作劇而被學(xué)校開(kāi)除。小說(shuō)刻畫(huà)了這樣一位普普通通的底層人在下崗后的生活困境。文章首先對(duì)其故事發(fā)生的社會(huì)背景進(jìn)行簡(jiǎn)要陳述,后將通過(guò)分析小說(shuō)主人公林奶奶的故事所表現(xiàn)出的三種關(guān)系,即人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人與他人的關(guān)系以及人與自己的關(guān)系進(jìn)行說(shuō)明并對(duì)其進(jìn)行文化反思。
小說(shuō)聚焦于改革開(kāi)放后的中國(guó),而這個(gè)時(shí)候的中國(guó)正途徑一系列的變化,無(wú)論是經(jīng)濟(jì)體制,工業(yè)生活,社會(huì)價(jià)值觀心態(tài)乃至人們的家庭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巨大的改變。整體表現(xiàn)出邊際性和兩極化[2]。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拮抗作用在價(jià)值觀上,人們還沒(méi)完全擺脫過(guò)去,但突如其來(lái)且又無(wú)孔不入的改變卻或多或少的讓有些人無(wú)所適從,這些人被時(shí)代甩開(kāi)了,然后成了一個(gè)個(gè)“多余”之人。一夜之間,冒出來(lái)的私人公司和學(xué)校,“車(chē)道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chē)”這樣的商業(yè)廣告人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就是在這樣的社會(huì)背景下,像林奶奶這樣的小人物顯得尤其悲哀。
三.三種關(guān)系的分析及文化反思
在人類(lèi)生存的過(guò)程中,生命不可避免地要在以下三個(gè)方面收到困擾:人與社會(huì),人與他人,人與自身。而這些困擾也是導(dǎo)致相應(yīng)的苦難。當(dāng)然,具體來(lái)考察這些關(guān)系不僅反映出作家的創(chuàng)作緯度而且了解作者的思想意識(shí)。
1.人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壓抑性社會(huì)對(duì)人的基本壓抑和額外壓抑。人與社會(huì)的沖突關(guān)系體現(xiàn)在人與文明的關(guān)系。人的歷史也就是人被壓抑的歷史。西格蒙特弗洛伊德認(rèn)為,文明以持久地征服人的本能為基礎(chǔ),人的本能需要的自由滿(mǎn)足與文明社會(huì)是相抵觸的[3]18。基本壓抑一般指在生產(chǎn)水平低下的情況下,人的物質(zhì)資源處于匱乏狀態(tài)所造成的本能性壓抑,這也是苦難形成的原始形態(tài)。首先小說(shuō)開(kāi)頭就提及到了林奶奶被工廠“光榮下崗”,實(shí)則為工廠破產(chǎn),而且不穩(wěn)定的下崗補(bǔ)貼,這都導(dǎo)致林奶奶要為以后的謀生發(fā)愁。不得不經(jīng)鄰居介紹做了癡呆患者老唐的妻子。文明不僅壓抑了人的社會(huì)生存還壓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但這樣的壓制恰恰是進(jìn)步的前提[3]3。經(jīng)濟(jì)物質(zhì)的匱乏致使林奶奶沒(méi)有選擇只能服從生活的安排。
額外壓抑來(lái)源于倫理道德,社會(huì)的權(quán)利體制,政治的形態(tài),文化機(jī)制等各方面。具體透析林奶奶的性格特點(diǎn),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林奶奶是個(gè)沉默少言的人,她恪守舊的生活習(xí)慣,這也跟她在服裝廠做女工的經(jīng)歷有著直接的關(guān)系。人受制于機(jī)器,受役于工業(yè)社會(huì)所帶來(lái)的文明,在勞動(dòng)中被“異化”。林奶奶不會(huì)選擇為自己辯解,而看到大家都為老唐的去世難過(guò)時(shí),她覺(jué)真的是她的過(guò)錯(cuò)導(dǎo)致了老唐的去世,而有了負(fù)罪感。負(fù)罪感在文明的發(fā)展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文明的進(jìn)步所付出的代價(jià)就是負(fù)罪感的增強(qiáng)而導(dǎo)致的幸福的喪失[3]54.其次小說(shuō)有關(guān)林奶奶給老唐洗澡的描寫(xiě),由于一輩子沒(méi)結(jié)過(guò)婚,所以對(duì)于老唐的裸體頗感驚訝,甚至?xí)孟肜咸颇贻p時(shí)候的樣子。后又自覺(jué)這種思想“不干凈”,驅(qū)逐了這種幻想。這段描寫(xiě)深刻的突出了林奶奶被壓抑的性意識(shí),折射出她深深的情欲孤獨(dú),這種孤獨(dú)源于文化對(duì)情欲的壓抑[4]24。
2.人與他人的關(guān)系—人群中的他者及精神的漂泊者。生物化的需求并非人性中唯一的強(qiáng)制性需求,還有另外一種同樣重要的需求,那就是精神需求。每個(gè)人都需要與自身之外的的世界取得聯(lián)系,以免孤獨(dú)[5]12。人感到完全孤獨(dú)與孤立時(shí)會(huì)導(dǎo)致精神崩潰,就像肉體饑餓會(huì)導(dǎo)致死亡一樣。而親密的人際關(guān)系是精神及安全的重要標(biāo)志,是人生意義與幸福的主要源泉甚至是唯一源泉[6]。相反,如果一個(gè)人缺乏這種親密關(guān)系,則表明其與他人的聯(lián)結(jié)的失敗,他的人生將會(huì)陷入漫長(zhǎng)的孤單狀態(tài),成為一個(gè)人群中的他者以及孤獨(dú)的精神“漂泊者”。小說(shuō)講了林奶奶分別與老唐以及小康的兩段親密關(guān)系。首先,我們要談及林奶奶與老唐的夫妻關(guān)系。與其說(shuō)是夫妻關(guān)系,實(shí)質(zhì)上則為保姆與病人的關(guān)系。他們兩人之間鮮有對(duì)話,即使在老唐的清醒的狀態(tài)下,張嘴就對(duì)林奶奶質(zhì)問(wèn)“你是誰(shuí)”“你不是我的妻子”,這些都說(shuō)明林奶奶在這段關(guān)系中悲哀以及微薄的存在感。
其次是與小康的“愛(ài)人”關(guān)系,在這里解讀為林奶奶愛(ài)的人,一個(gè)讓林奶奶感受到愛(ài)的人。小說(shuō)中有不少有關(guān)他們兩人肉體接觸的描寫(xiě),在許多讀者看來(lái)用詞相當(dāng)曖昧不清因而被解讀為愛(ài)情。在一次參訪中李翊云表示“l(fā)ove”的意思不止是愛(ài)情,而她想表達(dá)的是林奶奶這樣的一個(gè)人在與小康的相處的時(shí)刻中體驗(yàn)到了一種溫情,這個(gè)愛(ài)是一種大愛(ài),而非狹義的愛(ài)情。這段關(guān)系也因小康的一次惡作劇而終結(jié)。不難看出林奶奶迷戀于親密關(guān)系帶給她的溫暖,她不惜在發(fā)現(xiàn)小康有偷女生襪子習(xí)慣時(shí)選擇包庇,并小心翼翼地去守護(hù)這段親密關(guān)系。通過(guò)這兩次親密關(guān)系的失敗,林奶奶微乎其微的存在價(jià)值被徹底否定。小說(shuō)臨近結(jié)尾時(shí)作者寫(xiě)道“這條街上所有的人似乎都知道自己的腿該邁向何處,她還在想不知從什么時(shí)候自己不是他們中的一員”[7]21,這段描寫(xiě)極富畫(huà)面感,臨摹出把林奶奶置于人群中的迷茫和無(wú)措。林奶奶又成了一名情感無(wú)所投注的的精神“漂泊者”。
3.人與自己的關(guān)系—命運(yùn)之手和自然之愛(ài)。總的來(lái)說(shuō)李翊云筆下的小人物,他們隱忍且沉默,性格不具爆發(fā)力,但也極少會(huì)感到幸福。他們或許會(huì)與命運(yùn)抗?fàn)幍菭?zhēng)不過(guò),或臣服于命運(yùn)之手,但仍不得好過(guò)。這就營(yíng)造出人這一存在在命運(yùn)之手的無(wú)力感,也就是人的孤獨(dú)宿命。李翊云也表示出小說(shuō)中宿命論色彩是她的性格使然,也是她的作品的性格。林奶奶在面對(duì)生活中的困境和選擇時(shí),她都不會(huì)主動(dòng)做出抗?fàn)帯N恼轮档靡惶岬氖牵?dāng)小康惡作劇時(shí),林奶奶認(rèn)為這是對(duì)她的懲罰,懲罰她沒(méi)有滿(mǎn)足他的所有的要求。就像無(wú)論怎樣,他都無(wú)法“滿(mǎn)足”命運(yùn)對(duì)她的要求,逃避命運(yùn)對(duì)她的懲罰。
小說(shuō)關(guān)于林奶奶又這樣的一段描述“有時(shí)候,當(dāng)孩子們上課鈴還沒(méi)想起,她就離開(kāi)學(xué)校去往山里走走。早晨的霧水下在她的皮膚上頭發(fā)上濕濕的,鳥(niǎo)兒成群的唱著,這在城市中是見(jiàn)不到的”[7]12。這段講述了林奶奶自己一個(gè)人的時(shí)候在山里感受到的景象,而這美麗的自然風(fēng)光使林奶奶忘卻了自己之前在工廠的生活:每天呼吸著煤爐場(chǎng)放出來(lái)的煙以及擁擠菜市場(chǎng)人們?yōu)槟切┍换瘜W(xué)肥料催熟的蔬菜的討價(jià)還價(jià)的聲音。然后林奶奶采了一手的花放在每個(gè)班級(jí)內(nèi)。這說(shuō)明她愿意把她看到的美帶給學(xué)校的學(xué)生。這是個(gè)溫暖的時(shí)刻,我們看到林奶奶寄于生活的美好。林奶奶通過(guò)自發(fā)的與自然取得聯(lián)系,并從中得到了美的享受,建立人與自然的情感聯(lián)結(jié)。在大自然中,自己與自己相處,并從中忘卻工業(yè)社會(huì)的喧囂。而后林奶奶與小康一起在山里散步,也讓她感覺(jué)這是最幸福的事就是牽著“愛(ài)人”的手,遠(yuǎn)離社會(huì),親近大自然。
四.結(jié)語(yǔ)
不難看出通過(guò)上述三種關(guān)系的闡述,我們看到林奶奶這樣一個(gè)小人物,在文明社會(huì)的洪流中的顛沛流離,在與他人聯(lián)結(jié)中的失敗稱(chēng)為精神漂泊者,臣服于命運(yùn)之手仍會(huì)在大自然中吸取能量。所以,就是這樣一個(gè)小人物的瑣碎生活,我們很難去評(píng)價(jià)這種人物的好與壞,善于惡。因?yàn)槔铖丛乒P下的人物鮮少有臉譜化的人物,即有所謂的明顯的善惡之分,我們能看到就只有這些人物的不完美,以及李翊云對(duì)人物流露出的憐憫與同情,讓讀者在不經(jīng)意間捕捉溫情光輝的瞬間。吳帆這樣評(píng)價(jià)她,說(shuō)她就像一個(gè)隱藏在暗處的觀察者和敘述者,平靜的講述著筆下人物的故事,娓娓道出他們的哀傷,處處流露著她對(duì)人物最坦誠(chéng)的同情[8]。林奶奶的故事也是中國(guó)生活在底層民眾的故事,同也是一部苦難史。更深刻的說(shuō),李翊云超越個(gè)人具體的身體苦難與精神苦難,更多的關(guān)注人根本的生存意義及存在困境,并對(duì)這種終極性問(wèn)題發(fā)出她的思考與探尋。曾有讀者寫(xiě)信給李翊云,說(shuō)她讀完《多余》深深的被林奶奶所感動(dòng),表示自己就是林奶奶,而且總有一天你我都將變成林奶奶。我們不禁反思,當(dāng)人類(lèi)進(jìn)入后工業(yè)化社會(huì),社會(huì)物質(zhì)逐漸與精神發(fā)展脫節(jié),人與人的冷漠,親密關(guān)系的斷裂,孤獨(dú)將成為一個(gè)社會(huì)景象以及人類(lèi)普遍困境。
[1].王臘寶,短篇小說(shuō)與意識(shí)形態(tài)[J],浙江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7,(04).
[2].周曉虹,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與中國(guó)體驗(yàn):理解社會(huì)變遷的雙重視角 [J],學(xué)術(shù)評(píng)論, 2011,(6):12-19.
[3].赫伯特.馬爾都塞,愛(ài)欲與文明[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4].蔣勛,孤獨(dú)六講[M],臺(tái)灣:聯(lián)合文學(xué),2007.
[5].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北京:國(guó)際文化出版公司,2000.
[6].周?chē)?guó)平,論孤獨(dú)的價(jià)值[J],粵海風(fēng), 1998,(1):22.
[7].Yiyun,Li,A Thousand Years of Good Prayers,New York:Random House, 2005.
[8].http://wxs.hi2net.com/home/blog_ read.asp.id=4242&blogid=69420
(作者單位: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