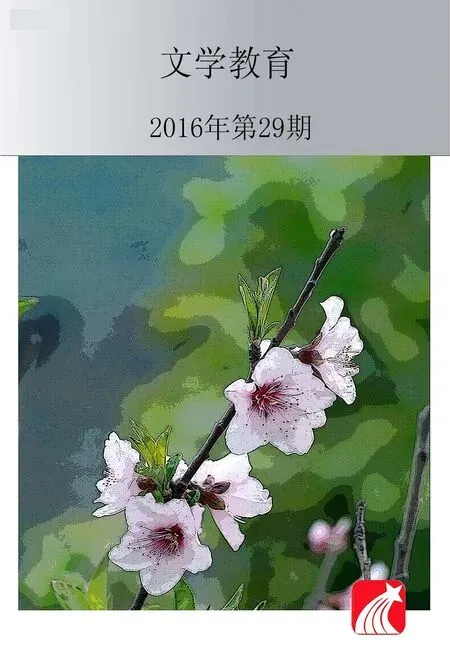論《文心雕龍》象喻批評的邏輯建構特征
李家惟
論《文心雕龍》象喻批評的邏輯建構特征
李家惟
《文心雕龍》五十篇在“綱領”和“毛目”的理論系統下展開,呈現出嚴謹縝密的思理邏輯。劉勰在文體論部分運用象喻批評論述了文體淵源、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作家才能等一系列問題,正體現了這一邏輯建構特征,由此成為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史上一部辭理兼贍的批評佳作。
《文心雕龍》 象喻批評邏輯建構
在“論文敘筆”部分,《序志》篇曰:“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因此,“論文敘筆”的論述過程就包括這四個方面,即先敘述各種文學體裁的起源和流變,然后解釋不同體裁的名稱,并闡明其意義,接下來從選取不同時期的典型作品進行評價,最后總結不同文體的創作方法和寫作特點。以如此全面而系統的方式考察各類文體,便使《文心雕龍》的文體論首先具有了相對獨立的意義,即成為一部空前的分體文學史。筆者試以《明詩》篇為主并結合其他篇目,分析劉勰象喻批評中的邏輯建構特征。
一.原始以表末
對于詩歌的源起,劉勰說:“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具有不同的思想情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影響產生感觸,心有所感而吟詠情志。劉勰的觀點本于他的“自然之道”的基本思想,這對當時文壇創作缺乏真情實感而矯揉造作的文風有救補時弊的作用。接下來,劉勰將詩歌的源頭追溯到葛天氏樂辭。其曰:“昔葛天樂辭,《玄鳥》在曲。”對于文學的起源及上古傳說時期的詩歌創作情況,劉勰無法作出明確解釋。劉勰先依據神話傳說和史書記載對先秦詩歌的發展情況作了簡要概述。漢以來,從“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到以《古詩十九首》為代表的成熟的五言詩體,詩體經過了從雅潤的四言向清麗的五言轉變的過程,然后出現了建安時期“五言騰踴”的盛況,自此,劉勰開始詳細論述了五言詩的發展脈絡。建安五言“慷慨以任氣”,骨氣爽朗勁健;正始年間“詩雜仙心”,詩歌流入淺薄;西晉詩歌“稍入輕綺”,筆調靡麗,內容膚廓;東晉詩壇“溺乎玄風”,多寡淡無味;宋初一改談玄風潮,詩人們“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力求華美和新變。這樣,劉勰就基本概括了先秦至今的詩歌發展的歷程。
二.釋名以章義
在釋名章義部分,劉勰強調詩歌“持人情性”的教育作用,即體現了其“道圣經”三位一體的思想。劉勰說:“詩者,持也,持人情性。”就是說,詩歌必須扶持陶冶好的情性。他把“詩”訓為“持”,“持”的含義是扶持,可引申為端正、規范。而“持”的對象是人的“情性”,所謂“三百之蔽,義歸‘無邪’,實際上是要求詩發揮教化作用。劉勰在中國兩千多年以來“詩言志”的基礎上,主張“為情而造文”。自陸機在《文賦》中提出“詩緣情而綺靡”的明確主張后,“言情”說大量出現,且成了眾多詩人創作實踐的指導思想。但是,六朝時期的言情之作由于“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很快偏離了正軌,滑向邪路:或“艷歌婉孌”、“淫辭在曲”,或“嗤笑徇務之志,崇盛忘機之談”,而多作“無貴風軌,莫益勸戒”之作。因此劉勰論詩講究情志并重,正如《征圣》所云:“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并且,“情”的表達要符合中國傳統儒家的政教觀,“為情者要約而寫真”“情深而不詭”,思想感情簡要而真誠,深厚而不虛假,從而突破狹義的志,約束泛濫的情,走向“情志合一”。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文人五言詩的頂峰之作,劉勰也以其“婉轉附物,怊悵切情”的特點為情志合一的詩歌典范,喻其為“五言之冠冕”。詩人把主觀的情形象化,融于具體的物象之中,即通過鮮明可感的客觀外物,透露出詩人內心的哀樂,使讀者如親歷身受,才能在潛移默化中起到“持人情性”的作用。
這種釋名章義的方法被劉勰廣泛應用于解釋不同的文體名稱,如《銘箴》篇曰:“箴者,針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針石也。”箴,是一種具有規誡性質的韻文,攻疾防患,諷刺缺失。劉勰在這里將其喻作治病的石針,可謂恰如其分。《書記》篇曰:“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其事也。”將“牒”喻作葉,用短小的竹簡編成碟,就像樹枝上的樹葉,形象切物。《頌贊》篇曰:“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可見,劉勰的“釋名以章義”主要采用形象喻事的思維方法,以訓詁來解釋各種文體名稱的含義。盡管有些解釋是不免牽強,甚至比較陳腐,缺乏周密性和準確性,但他能用極其簡潔的形象喻示概括各種文體的主要特征,時有新見,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說,劉勰是第一個為各種文體全面定名的人,后世論文體者,如明吳納《文章辨體序說》、徐師曾《體明辨序說》、清林紓《春覺齋論文》等,其中對文體名稱的不少定義,都受劉勰的影響很深。
三.選文以定篇
劉勰縱觀歷代詩歌創作,論述了從漢代的韋孟、枚乘到三國的王粲、曹植,西晉的潘岳、陸機,以至東晉的孫綽、郭璞等十余位作家的創作風格,通過對各個時期作家的代表作進行簡要而精確的評述,反映歷代不同的文體的創作情況,在僅用八百多字的短小篇幅,就把先秦至今的詩歌創作情況,作了宏觀的描摹勾勒。事實上,“選文以定篇”的部分可以看作一部語言精煉的分體文學史,不同時期的文體發展情況如何,讀者可以從中把握其清晰的脈絡。《明詩》篇說:大禹治水成功,因而得到歌頌;夏帝太原荒淫失國,就有“土子之歌”發出怨恨。劉勰據此提出“順美匡惡,其來久矣。”呼頌美德和匡正過失是古代詩歌的優良傳統,劉勰認為“持人情性”是詩歌藝術的特點所起的作用.它既可以熏陶人的善良之性,也可以誘發人的邪惡之情。《樂府》篇就講到這種情形:“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雅正的樂府詩是溫和嚴肅的,但人們聽了厭煩得打呵欠、瞪眼睛;奇異的樂府詩卻使人聽來十分親切,甚至喜歡得拍著大膽跳起束。這也是詩歌藝術“持人情性”的作用。
四.敷理以舉統
這是“論文敘筆”的最后一個部分,主要通過分析歷代不同文學體裁的創作實際,從中總結前人的創作經驗,得出不同文體的寫作規律,從而避免其失而汲取其優長,為后人的文學創作指明道路與方向。可以說,這部分是整個“論文敘筆”的核心所在,也是劉勰《文心雕龍》的寫作意圖,即建立一定的原則與標準去規范當下文學創作,為后世文體寫作提供理論指導。《明詩》篇末,劉勰主要闡述了四五言詩歌的異同:四言“雅潤”,五言“清麗”。從藝術表現手法上看,四言簡單、粗糙,而五言因比四言多一字,而顯得字詞間的轉折承遞圓美流轉,更多一重婉轉回環的美感,比四言更富有表現力,建安文壇“五言騰踴”,故形成了比先秦時期更為梗概多氣,風清骨峻的文風。但從儒家傳統的詩教觀來來看,劉勰又認為四言勝于五言:“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華實異用,惟才所安。”他以一“華”一“實”為喻指明四五言風格之異,四言為正體,“雅潤”而偏樸實;漢魏以來新興五言則是流調,“清麗”而偏華美。顯然,劉勰一方面試圖從宗經的角度來提高四言詩的地位,另一方面肯定了建安以來五言詩主導詩壇的事實,力贊五言清麗的特征,并用較多的篇幅細述了五言詩的演進與流變。
由上述分析可知,劉勰運用象喻批評論述了文體淵源、文學創作、文學批評、作家才能等一系列問題,不僅沒有紛繁雜亂之感,反而使讀者感受到其條分縷析、緒密思清的闡述過程,這與《文心雕龍》“綱領明、毛目顯”的邏輯建構體系是分不開的。也正因如此,《文心雕龍》才能在“師圣體經”的同時,窮究古代文學的流變,“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成為我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的重要著作。
[1][梁]劉勰撰,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M].1958年.
[2][梁]劉勰撰,劉永濟校釋.文心雕龍校釋.中華書局[M].1962.
[3]張少康.中國古代文學創作論.北京大學出版社[M].1982.
[4]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上海古籍出版[M].1984.
[5]王運熙.文心雕龍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M].2005.
(作者介紹:李家惟,華中師范大學第一附屬中學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