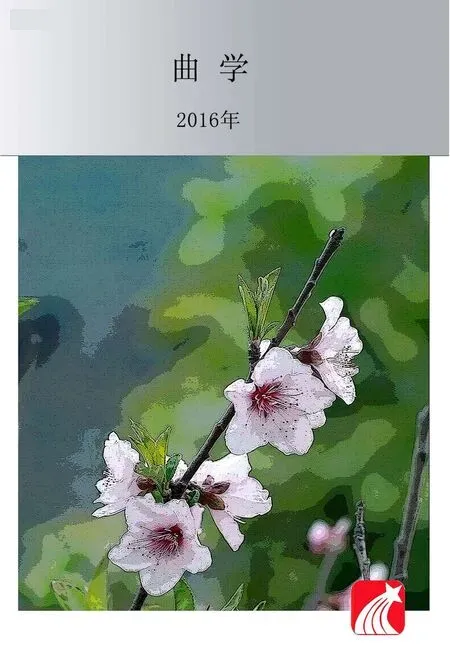論板腔
——兼論戲曲音樂創作
莊永平
《曲學》第四卷
論板腔
——兼論戲曲音樂創作
莊永平
“板腔”曲式是中國傳統文化在音樂領域內容與形式上的最佳結晶之一,也是中國傳統音樂最主要的樂曲結構形式之一。“板腔”曲式常被稱為“板腔體(制)”,它在中國音樂曲式結構中的形成是比較晚的。在它之前中國傳統音樂的曲式,幾乎是“曲牌體(制)”的一統天下。然而,正因為形成得較晚,它不僅繼承了曲牌體許多優秀的成果,更主要的是突破了曲牌體制于音樂發展上的一定壁壘,因而所體現出的音樂藝術成就更高,更集中地反映了中國傳統音樂的精髓。可以說中國音樂相比于西洋音樂所具有的特色東西,在板腔體制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因此,研究板腔體就是尋找中國傳統音樂的特色,總結中國傳統音樂的成果,使之在今天接受和借鑒外來音樂方面,不至于失卻自己的立足之本。同時,也能尋找與現代音樂相結合的可能與切合點,使之蛻變為一種現代的,富于民族特色的結構形式。
“板”“腔”與“板腔”釋義
“板腔”就字義上來分析:“板”字,《辭源》解釋是:“片狀的木頭。后片狀物皆稱板,如鐵板、石板等。”*《辭源》,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1542頁。《說文解字》中“板”作“版”,這個“片”字旁就是釋“板”字為“片狀物”的來源。而后改為“木”字旁顯然先是引申指的是木板,然后才擴大至其他物質的片狀物。“板”字用于音樂是與一種木制樂器聯系在一起的,這種樂器就是魏晉以來的“拍板”。《辭源》引《景德傳燈錄(二七)〈善慧大士〉》:“大士登坐,執拍板唱經,成四十九頌。”*同上,第1244頁。“拍板”一詞的“拍”字原是動詞,“板”字是名詞,最早就是指一種擊節的動作,即“拍著板”,后來兩字合在一起成為一種節奏樂器的名詞。因此,在“拍板”成為一種樂器名稱之前,“拍”字的出現比“板”字要多得多,也早得多,這是因為“拍”字已由動詞轉為樂曲的一種結構名詞了。早在東漢(約公元208年左右)蔡琰《胡笳十八拍》之“拍”,就是一種寬大的拍,大約相當于文章中的“段”或“章”,可稱為“段拍”或“章拍”。還有如我國現存記譜年代最早的琴曲《碣石調·幽蘭》,全曲四個樂段就稱為四拍,到了唐時才縮小到以句為拍。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中對“拍板”作的解釋是:“拍板本無譜。明皇遣黃幡綽造譜,乃于紙上畫兩耳以進。上問其故,對:‘但有耳道,則無失節奏也。’韓文公因為樂句。”*(唐) 段安節《樂府雜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58頁。宋張炎《詞源》也說:“眾部樂中用拍板,名曰齊樂,又曰樂句。”*(宋) 張炎著、蔡楨疏《詞源疏證》(下),中國書店,1985年,第14頁。以樂句為拍就被稱為“句拍”。我們從現留存的《敦煌樂譜》*莊永平《琵琶、古譜、戲曲音樂——莊永平音樂文集》,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194—230頁。中可以發現,有眾多的“囗”符號,而且,每兩“囗”之間的譜字數都是相等的,或六個譜字或八個譜字,甚至四譜字不等。還有唐樂流傳到日本后產生的樂譜,如《仁智要錄》、《三五要錄》、《博雅笛譜》*葉棟《唐代古譜譯讀》,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年。等中有“百”字(“拍”字的通假字或簡筆字),每兩“百”之間的譜字數也都是相等的。這就說明那時不僅在實際演奏中是用“拍板”來分割樂句,起到節(制)拍的作用,而且更進一步化為譜面的節拍符號了。當然,唐段安節《樂府雜錄》中又說:“鼓,其聲坎坎然,其眾樂之節奏也。”*(唐) 段安節《樂府雜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第58頁。這個節奏顯然是指的如今天樂曲的旋律進行,包括小拍(如以四分音符為一拍的單位拍),至于大拍(如一小節中有四拍的4/4拍的小節)就是用“拍板”來分割的。可見,那時它們并不是經常組合在一起指樂曲的節拍形式。唐代“拍”的組詞很多,如大曲中的“拍序、序拍、破拍、催拍、促拍、歇拍”以及“拍彈”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那時“拍”就是節拍的最小單位了。因此,即使拍被分解了,也只能稱為“破拍”或“曲破”,至于“破”到何種程度,我們從日本傳自唐代的《三五要錄》等樂譜上,表示[破][急]段的,大致相當于今天的8/4、6/4、4/4拍的都有,4/4拍大概是最小的節拍形式了。看來,它們有的僅是一種速度上的差異而已,“破”與“急”就是其名稱。另外,以《樂府雜錄》的說法,那時拍板打不打無所謂,旋律(包括節奏)照樣可以進行下去,但它作為樂曲的樂句分割也就必須打的。可見,那時的“拍”還很寬大,還沒有真正介入到旋律節奏之中去。后來,拍板的“板”的作用才逐漸凸顯出來。雖然那時“板”字僅與“拍”字連在一起,但至少為今后“以板代拍”埋下了伏筆。到了宋代基本上也還是保持“拍”或“拍板”的稱呼,如宋張炎《詞源》中寫有“拍眼”一節,大多是言“拍”不言“板”的,有“拍眼、待拍、拍板、應拍、樂拍、按拍、無拍、均拍、前拍、后拍、艷拍、花拍”等。提到“板”的如:“王感化善歌謳。聲振林木。系之樂部,為歌板色。后之樂棚前用歌板色二人。”*(宋) 張炎著、蔡楨疏《詞源疏證》(下),中國書店,1985年,第14頁。所謂“歌板色”就如現在唱京韻大鼓的演員,一邊演唱一邊自己執板打鼓;“色”者,即今行當角色之分類。宋王灼《碧雞漫志》中也提到“曲拍”“花拍”等。*(宋) 王灼《碧雞漫志》,《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第132—133頁。可見,用“板”字最早可能與宋元時的說唱形式有關連,但真正大量出現以“板”替代“拍”或“拍板”的,大約要到明代了。首先,是出現了各種“板”的打法,如明魏良輔(約1522—1572)《曲律》中就有“迎頭板、徹板、絕板”等名稱。其次,出現“鼓板”與“板眼”兩詞。明魏良輔《曲律》提到“南曲之鼓板”,又講到:“拍,乃曲之余,全在板眼分明……其有專于磨擬腔調,而不顧板眼;又有專主板眼而不審腔調,二者病則一般。”*(明) 魏良輔《曲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五),第5—6頁。之前,在宋張炎《詞源》中稱為的“拍眼”,現被“板眼”一詞所替代。由于注重拍板的實際操作,大概當“拍”變為樂譜符號,“板”就成為拍板樂器的簡名了。而且,拍板樂器本身也由最早的九或六片雙手操作,減為三片單手操作了。那么,首次較完整地為昆曲曲譜點上板眼節拍的是明沈璟(1553—1610)的《南曲全譜》。他在蔣孝的《南九宮譜》基礎上增訂并圈定了板眼。另一方面,魏良輔只是論到“板”而未能論及“眼”。后明王驥德(?—約1623)《曲律》為“板眼”下了確切的定義:“蓋凡曲,句有長短,字有多寡,調有緊慢,一視板以為節制,故謂之‘板’‘眼’。”*(明) 王驥德《曲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第118頁。而且,他在推崇沈璟點板眼的做法時,提到了“鼓”與“板”兩種樂器的互為作用:“詞隱于板眼,一以反古為事。其言謂清唱則板之長短,任意按之,試以鼓、板夾定,則錙銖可辨。”*同上。這樣,我國傳統音樂最富于特點的板眼節拍形式,不僅在實際操作中,而且于譜式上就此基本肯定了下來。因此,“板”字于傳統音樂中的涵義,不僅是“板”(檀板)樂器本身,它還引申為板的打法以及各種節拍形式,等等。這些,當然主要是指聲樂歌唱方面,但要做到節拍的定性與定量也不易。不過,這里要著重指出的是,現在人們常常過分強調我國音樂的特點,是所謂的“韻律性節拍”特征,也就是不定性、不定量的節拍形式,這似乎是有些以點概面了。實際上從唐代的《敦煌樂譜》等古譜來看,那時的節拍是基本定性、定量的,而且有時還很嚴格的。例如,兩“囗”之間是八個譜字,如果多于8個譜字,就要運用“火”字將多余譜字合在一個譜字節奏單位之中;如果少于8個譜字就要運用“引”“T”等符號,增加譜字節奏單位使之合于既定的拍數,也就是“拍”是以譜字為“節”的,這可能與唐代近體詩嚴格的字數、句式格律有關。而所謂的“韻律性節拍”是后來進入詞與曲的時代,尤其是在聲樂的說唱音樂方面才凸顯出來的節拍特征。由于我國歷來聲樂占了音樂的主導地位,因此,給人以中國音樂節拍特征是不定性、不定量的。其實,今天從整個民族音樂來考察,事實上規整節拍與韻律性節拍都是存在的,只是前者器樂曲中多些,后者聲樂曲中多些。因此,我們在指出這些特征的同時,是不應以偏概全的。
那么,關于“腔”字,其涵義則更是廣泛了。最早“腔”字就是指人和物體內的空處。*《辭源》,商務印書館,1987年,第2563頁。對于人體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口腔”這一空處,它是人們講話和歌唱的重要器具,也是使用最為頻繁且最為外顯的人體空處了。首先,講話和歌唱的發聲源“聲帶”就在口腔之中,這是口腔排在諸腔之首的最直接原因。其次,口腔中由于有牙、齒、舌、唇、喉等器官,借以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傳統發聲法上總結出的“五音四呼”,就涉及聲母的“牙、齒、舌、唇、喉”五類與韻母的“開口、合口、齊齒、撮口”四類,這些都是歌唱發聲最主要的部位與口型。除此之外,起發聲共鳴作用的還有鼻竇腔、蝶腔、頭腔、胸腔等腔體部位。因此,我國古代用“腔調”一詞來指音樂的旋律曲調,確實是十分高明的,也是非常經典的用詞。因為畢竟音樂的旋律曲調是從口腔中發出來的(唯鼻音例外,但不能成字)。因此,“腔調”一詞不僅強調了發聲器官和音樂曲調的種種關系,而且更突出了我國的音樂歷史一直是以聲樂為主的,聲樂的特點也就成為我國民族音樂的主要特點及來源。然而,到了器樂開始發展繁榮起來之后,用“腔調”一詞來指音樂的旋律曲調就不很合適了。所以采用“旋律”,即活動(旋)著的各音(律)之意,以及借用詞曲的“曲調”(曲的調名),來指樂曲實質性各音高低連接線條的進行,且以“旋律”與“曲調”來互為釋義。其實,“旋律”一詞是借用于東瀛日本,“曲調”一詞則是我國古代詞曲名稱的重新定義。*莊永平《簡論我國音樂的旋律及特征》,《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正由于此,傳統上以“腔”字組詞的極多,如“聲腔、腔調、唱腔、板腔、腔體、腔格、腔句、腔節”等聲樂全稱與結構方面;“高腔、梆子腔、皮黃腔、西皮腔、二黃腔”等腔系或腔調方面;“嚯腔、豁腔、疊腔、墊腔、帶腔、撮腔”等曲調裝飾及演唱技巧方面;還有音樂處理方面的“橄欖腔、頓挫腔、喇叭腔”等,甚至引申出“油腔滑調”“荒腔走板”之類的生活用語,可以說在那時凡是涉及旋律曲調進行與演唱、演奏技巧及音樂處理等方面,一切以“腔”字囊括之。另外,還可注意到,20世紀奧地利音樂學家霍恩博斯特爾曾將全世界樂制分為中國、希臘和波斯—阿拉伯三大體系,那么,中國體系就可以用“腔”字來囊括。筆者曾撰文提出以“腔格、音格、拉格”*莊永平《音格·腔格·拉格》,《音樂探索》2001年第4期。與此三種體系相對應,其“格”指的就是音樂上特定的規范,而“腔、音、拉”三字就是指的他們音樂旋律與結構上各自特點的集中表現。
總之,“板腔”一詞,顧名思義就是“板”與“腔”的結合。“板”就是指節拍、節奏,“腔”就是指唱腔的旋律曲調。也就是唐時以“鼓”的坎坎然之聲,泛指旋律節奏的進行,加上以“拍板”樂器的節拍來操控歌唱與樂隊。后來就以一人操作的“檀板”與“鼓”,來具體指揮演唱、演奏的進行。為什么我國傳統的演唱、演奏要用“板、鼓”從頭至尾打入,而西洋音樂的演唱、演奏“則合自然之度”而不用?其實,這是與我國節拍、節奏概念的生成與結合密切相關的。不僅如此,更為重要的是我國音樂發展到后來,以“板”與“腔”結合成“板腔”一詞,以“板”在前引領“腔”,說明“板腔”體制十分強調節拍、節奏的重要性。這種節拍、節奏與旋律曲調的關系,即所謂“以腔生板、以板節腔”,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腔詞關系與發展機制,最終成為我國傳統音樂最為成熟的一種曲式結構。
板腔體的起源與板式形成
有意思的是,我們今天稱為的板腔體曲式結構,它的起源并不是以“板”為節拍、節奏樂器而來的,之所以稱為板腔體是后來當這種曲式結構較為成熟時,用“檀板”來操控指揮演唱與樂隊后的稱謂。實際上板腔體首先是來自西北的梆子腔,梆子腔是以梆子樂器擊節而得名的。梆子與檀板是兩件不同的樂器,北方梆子稱為北梆子,是由兩根長短、粗細不同的檀木棒互擊,其發音高脆、堅實,后來才有了用于南方戲曲的“南梆子”,樂器及音色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正是由于梆子腔的興起,打破了曲牌體于音樂上的一定壁壘,使傳統音樂發展上了一個更高的層次。“梆子腔”最早起源于明代的“西秦腔”、“甘肅調”或“琴腔”。清吳長元《燕蘭小譜》(1785序)載:“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肅調’,名‘西秦腔’。”《金臺殘淚記》說:“南方人們謂‘甘肅腔’為‘西皮調’。”*轉引自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下),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第983頁。秦腔,據清李調元《劇話》載:“俗傳錢氏《綴白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陜西,以梆為板,月琴應之,亦有緊、慢,俗呼‘梆子腔’,蜀謂之‘亂彈’。”*(明) 李調元《劇話》,《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47頁。后來最先演變而成的,也是當時影響最大的是陜西同州梆子和山西蒲州梆子(今蒲劇),之后隨著不斷的流布形成了龐大的梆子腔系統,包括陜西同州梆子、秦腔、漢調桄桄;山西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河南梆子(豫劇)、河北梆子、老調梆子;山東梆子、章丘梆子、棗梆;安徽淮北梆子,等等。還有后來在進入了其他腔系中,成為多腔系劇種中的一部分,如“皮黃腔”中的“西皮腔”以及川劇中的“彈戲”、滇劇中的“絲弦腔”,還有浙江紹劇中的“二凡”,等等。由于我國北方語所占的人口與地區比例最大,雖然內部有北方、西北、西南等次方言區之分,但與南方的方言相比它們之間的區別并不大,所以腔調結構上較為一致,故而形成了這樣一種龐大而單一的聲腔系統(腔系)。那么,對于“梆子腔”的結構而言,它并不是在曲牌體結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僅從唱詞方面就可以明顯發現,不僅與曲牌體運用的是“曲”的長短句結構不同,它是運用整齊的七、十字上、下句結構;而且這種整齊句體與唐代整齊詩體也是不能同日而言的,這倒不是在具體唱詞結構上有多大區別,主要是音樂上節拍、節奏等方面已與唐時大不相同了。正是由于唱詞結構的變化,也引起了唱句結構的變化,比較突出的就是曲牌體唱腔是不用過門的,而板腔體唱腔在各腔節樂句之間,插入大小不等的器樂間奏與過門,致使二者的旋律結構就明顯的不同了。在樂器運用上,“梆子腔”所用的梆子擊節也僅于板位上,眼位一般是不打的,因此常常也無從區分板與眼。例如,所常用的主要板式[流水板]就無眼位可言。后來梆子大概在其他腔系如“皮黃腔”中率先被檀板與鼓替代,很可能是受了昆曲等曲牌體制的影響。因為一方面檀板與鼓聽起來比梆子雅致,而且,更主要的是檀板與鼓是既打板位又點眼位,這對唱腔的板眼節拍厘定是有很大促進作用的,同時以板替代梆子也就為板腔體制立名了。
另一方面,對于板腔體各板式的形成,先從戲曲所表現的情感上看,像昆曲那樣明顯是突出了它的音樂抒情性。因為它本身就是一種“曲”,經過魏良輔等音樂家的加工,出現了像[贈板]那樣極其緩慢而抒情的唱腔。我們今天感到昆曲聽起來是那樣的優美動聽、悠揚雅致,其實就是這種極慢速的[贈板]唱腔給我們帶來的感受。因此,昆曲在達到曲牌體聲腔的巔峰之時,它在戲劇(戲曲)三要素即抒情性、敘事性、戲劇性中,后兩者明顯是先天不足的。因為它基本上沒有其他快的曲牌及大小唱段的調劑,因而唱腔的敘事能力不強,戲劇性則更是不足。例如,它還沒有產生出后來板腔體中的[流水板][快板]等頗具戲劇性效果的板式來。甚至像明王驥德在《曲律》中認為:“今至‘弋陽’‘太平’之滾唱,而謂之[流水板],此又拍板之一大厄也。”*(明) 王驥德《曲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四),第119頁。我們知道,真正向快的板式方面發展,正是由板腔體制來推動完成的。當然,曲牌體中后來出現了[流水板]的滾唱,確實也是一種對曲牌唱腔體制的突破,其實也是受了板腔體的影響而產生的。但是,很顯然這種突破已不可能在成熟曲牌體制的昆曲上進行,而是在“青陽”“石臺”“太平”等當時一些新興崛起的曲牌聲腔上開始的。那么,板腔體在戲劇(戲曲)三要素中,顯然首先是來源于它的敘事性,這種敘事性實際上與民間說唱音樂有著密切的關系。表現于唱句上它是以上、下句結構,落音通常相差大二度為主的,例如,京劇中主要的[西皮]唱腔,上句落2音、下句落1(或 6音),構成宮調式或羽調式;[二黃]唱腔上句落1音、下句落2(或 5音),構成商調式或徵調式。這種上下大二度音相差的敘事樂句結構,確實是我們中國人的一大發明,追其源大概與語言唱詞結構上的平仄對應關系有關的。當需要抒情性時可以加大上、下句落音的對比;當需要戲劇性時又可以節奏的變化來驅動。這樣,在整個戲劇(戲曲)中它比曲牌體結構要靈活得多,表現力也就更為豐富了。其實,像“梆子腔”開始時都是些[流水板]之類的板式,腔情亦即“繁音激楚、熱耳酸心”是也。后來[慢板]等板式的產生,可以想見最早可能是受了昆曲的影響而發展形成的。而且,在“梆子腔”“皮黃腔”等板腔體的[慢板]與[流水板]之間,又衍化出快慢不等的其他板式,加上曲牌體上已有的[散板],以及發展出的一些特殊板式,如[搖板][快板][垛板]等,從而形成了較為完整的成套板眼曲式體系。這種套曲結構而后也就成為我國民族音樂最主要的曲式結構,顯然這是板腔體制的一大功勞。至于板眼節拍的厘定上面已有所談及,其實早在曲牌體的昆曲時代,已有所謂北方多用活板,南方多用死板的說法,雖不免有點過頭,但實際上這種現象確實是存在的,看來這又是與運用不同的方言聯系在一起的。大致北方言婉轉即可成腔調,旋律伸縮性較大,因而不易控制板眼節奏,所以被稱為“活板”。而南方言聲調調值不明顯,常要靠旋律來引申其語言字調,因此節拍較易固定,眼位節奏也被逐漸細化,最終形成一定的較為固定的板眼節拍形式,這就是所謂的“死板”。實際上這也說明了固定板眼的節拍,是于南方的昆曲腔調上開始的。但昆曲階段僅是厘定了慢節奏板式的板眼,至于后來戲曲中整個板式系統的板眼,卻是由“梆子腔”及后來的“皮黃腔”等板腔體制,在吸收了曲牌體制板眼基礎上,產生出一系列快慢不同的板式才大有建樹的。
板腔體各板式的特點與功能
正如上述,板腔體結構的最主要特點,是產生出一系列板式來。“板式”一詞原有兩種涵義:
1. 下板方式,這在昆曲的曲牌體結構中已經有了,也就是以“板”來指示旋律曲調的節奏。在魏良輔《曲律》中已提到: 字隨板出的[迎頭板];后半拍出字的[腰板];一句唱腔唱完后下的[底板]等。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板”看似下得各各不同,但實際上都是下在相對于反拍的正拍位置上的,其功能就在于指示旋律節拍節奏的不同方式而已,它不可能來替代旋律本身的進行。正如今天指揮的打拍那樣,通常也是打在正拍上的,僅有時為了突出節奏或其他方面,偶然也打在反拍上。不過,這也說明到了明代,“板”(節拍)至少已經縮小到了能介入一定的具體旋律節奏中去了,這在唐的“句拍”時代是做不到的。另一方面,我國后來的記譜方式,如工尺譜就是以這種板的指示為依據的,因此對于音樂的記錄來說,它只能是一種粗略的規范,還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詳細記錄旋律曲調節奏的要求。
2. 板眼形式,簡稱板式,這是板腔體結構的一大特征。由于板腔體結構是以一對上、下樂句為基礎,以節拍、節奏的變化為主線,同時帶動旋律的變化,產生出一系列快慢不等的腔調樣式,這就是板式的產生。這種方法的特點: 一是由于其他板式都是由[原板]發展而來,因而從音樂素材等方面來講是比較統一的。當然,少數腔系也有可能是以比[原板]慢或快的板式為基調的。二是常根據由慢至快漸層發展的節拍、節奏原則加以組合,形成結構較為龐大的套曲,成為板腔體中表現力最為豐富的結構形式。
例如,京劇中[西皮]的[導板][回龍][慢板][原板][二六][流水][垛板][散板]等組成大型的成套唱腔,表現力非常的豐富。一般來說,[原板]與[慢板]的關系,結構上常就是2 ∶1的關系。也就是[原板]采用2/4拍,[慢板]采用4/4拍,后者速度約放慢一倍而已,在此基礎上旋律可以進一步加花撐開。[原板]與[快三眼]猶如指揮打整拍與分拍那樣,是一種反過來1 ∶2的關系。前者采用2/4拍,后者采用4/4拍,但它們采用同一個速度,其趣味就在于節拍的打法上,表現出不同的抑揚頓挫感覺來。除此之外,[原板]與[二六][流水]等快板式的關系,結構上常就不一定是這樣較嚴格的對應關系了。這是因為唱詞的字位節奏關系發生了變化,因此腔調上也有所變化。而[原板]與[垛板]等更是由于字位節奏關系的變化,聯系上就不那么直接了,但它們都是一種總體上的緊縮或放大(多疊)。正如上面所述的,從敘事性與戲劇性方面來講,上、下句結構的疊置就是為了戲劇中的宣敘而形成的,它與西洋歌劇中的宣敘調功能相類似。這種結構我們在說唱音樂中可以大量見到,實際上它就是由歷史上的寶贊、變文及唱賺、鼓子詞、諸宮調等形式發展而來的。它的好處就在于可以根據敘事的長短,任意疊置多少對上、下句均可,這種敘事部分常處于唱段頭、尾部分外的[平板]結構部分。一般而言,上、下句結構不如昆曲的曲牌體抒情性那樣強。因為曲牌體可以換用一個同宮調的曲牌,而板腔體只能在原有腔調基礎上發展而有所限制。但是,這顯然不是絕對的,前者即使換用曲牌情緒的變化常也是不大的,而板腔體結構由于易于分解與綜合,它可以運用拖腔(擴展)與垛句(緊縮,但可疊置)兩大利器,來發展變化它的腔調旋律,因而馳騁的余地也就更大了。例如,在上、下句落音上加以變化,就能發展出四句式的起、承、轉、合樂段,這就打破了上、下句的落音關系,使通常偏向于敘事性的結構,朝著抒情性方向轉化。有時運用長大的拖腔使其情感得到進一步的發揮,這在板腔體的[慢板]中常得到集中的體現。至于戲劇性主要表現在較快的板式上,如運用[垛板][快板]或整、散板的交叉等使情緒陣陣上推,產生出強烈的戲劇性效果來。如果說昆曲的曲牌體“水磨腔”結構,使唱詞字調與音樂腔調的慢速配合上,達到異乎密切的程度,那么,板腔體結構不僅在[慢板]中吸收了昆曲[贈板]的做法,同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它又開發出[垛板][快板]等快的板式,把漢語單音節的連接速度,推進到了無以復加的快速程度,能造成極大的情緒波瀾,使它的表現功能大大超過曲牌體結構,特別是在敘事性與戲劇性方面的能量更大。如果從語言的根本點上講,只有漢語這種單音節詞根占多數的語言,才能產生出如此強烈的、戲劇性的效果。這種現象外國音樂家們有時雖然感到中國戲曲音樂“顯得不優美、粗笨、生硬和喧鬧的”,但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合乎天生稟性的、充滿生命活力的音樂的印象”。*〔德〕 費里茨·波澤著,范額倫譯《非歐洲諸民族之音樂》,上海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所、安徽省文學藝術研究所編《音樂與民族》,內部資料,1984年,第98頁。外國人認為中國戲曲音樂的諸如缺點,現在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而它原有的稟性特點則越來越鮮明、突出。
相比西洋語言的多音節結構,輕、重音節似搭配好的互相制約,因而不可能分拆開來表述的。即使是他們現在的“饒舌歌”,也不可能像我們戲曲唱腔中那種極快的板式節奏。它只能加快單位拍內的音數,如兩個八分音符轉為四個十六分音符那樣,即使這樣也達不到漢語繞口令的速度。而漢語還能加快單位拍本身,如1/4拍轉為分解的1/8拍那樣。因此,如果使用漢語而不運用這種節拍形式,這不就放棄了中國最富于戲劇性表現的工具了嗎?除了[垛板][快板]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板腔體結構中還有一個強大的利器就是[搖板]的運用,這種板式也是以漢語單音節詞根占多數為基礎的,它是一種獨一無二且十分奇特的音樂結構,那就是以無板的散唱與有定板節奏的伴奏相結合的一種板式。為什么會形成這樣一種奇特的板式?實際上也與漢語的單音節結構有關。因為單音節(字)之間可以靈活地組合在一起,又可以靈活地拖音,這樣一來,如在拖音時伴奏又是有衡定節奏的,這就成為了一種看似散拍節奏,又是有定次節奏的組合體,這樣,就形成那種內緊(伴奏)外松(唱腔)特點的[搖板],富于強烈的戲劇性效果和獨特的表現功能。一旦形成了這種結構,各劇種唱腔上又可以各自加以發揮,形成豐富多彩的形式。如京劇的[搖板]、越劇的[囂板]、滬劇的[快板慢唱],等等。想必西洋多音節語言是不可能產生出這種奇特板式來的,試想如果用西洋多音節語言來演唱[搖板],這不成了“疙瘩腔”了嗎?要么幾個音節擠在一塊兒,要么一個音節硬拖在哪兒顯然是不行的。因此,音樂上很多有特色的東西都是語言所使然的,不僅不容易改變它而且更應該很好地利用它發揚它,這才是民族特色的所在。
板腔體的創腔手法與特征
板腔體是我國傳統音樂最高級的曲式結構,因而它也集中了我國傳統音樂創腔手法最精髓的部分。雖然我國戲曲創作特征之一,就是其“創作是在本劇種戲曲腔調的基礎上進行的”*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編《民族音樂概論》,人民音樂出版社,1964年,第215頁。,然而,板腔體與曲牌體創作不同的是,曲牌體基本上是一種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倚聲填詞”的創腔方式,它注重的是文學唱詞的方面,而這種局面從板腔體開始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觀。正如我們今天不會認為創作設計京劇唱腔是一種“倚聲填詞”,說明板腔體于唱腔音樂方面已有了更大的創作回旋余地,認識到這一點是頗為重要的。這也是我們說板腔體制在現今的形勢下,還可以被充分利用和發展的原因所在。下面將板腔體的創作手法簡述如下:
1. 節拍、節奏的變化,也就是上面已經分析到的各種板式的產生,其特點是以二之冪的進行來劃分的。這在運用板腔體的各個腔系劇種發展上是并不平衡的,但總體上已經發展得較為俱全了。例如,相當于今天1/4拍的有板無眼;2/4拍的一板一眼;4/4拍的一板三眼及散、搖板等。其間,值得注意的是,1/4拍的有板無眼節拍,是比較能體現與語言緊密關系的拍式。因為漢語的單音節(字)本身就是一個單位,因此形成有板無眼的1/4拍是極其自然的。比字再小的單位勢必割裂了字是行不通的,因此,即使運用比1/4拍小而快的1/8拍,它必然又會以1/8拍為字單位了,這是典型的以一元起步的節拍形式。在我國民族音樂中凡是節拍上有翻拍之感時,均可用有板無眼的1/4拍來解決。正如楊蔭瀏所舉的鑼鼓曲《下西風》*楊蔭瀏《語言音樂學初探》,載《語言與音樂》,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年,第72頁。的例子,來說明用1/4拍的曲調也不全是強拍的,它有與小節節拍輕重規律相符合的地方,也有不相符合的地方。而西洋音樂中由于語言的多音節關系,常是一輕一重或一重一輕,即稱為“抑揚格”或“揚抑格”的組合,因而音樂上常就是以二元節拍起步的。他們的一拍子運用是極少的,如果出現翻板現象,那肯定就是節拍本身沒有搞好平衡。其實,西洋音樂也有類似我們板式的東西,它們的板式是以速度來表示的,例如,每分鐘多少拍稱為[慢板],多少拍稱為[行板]等;如果還不夠清楚時只能加上文字的表達,如“不太快的快板”之類。只是我國的板式除了速度上的一些區分之外,更著重強調旋律發展上的同一性。另外,為什么傳統板腔體沒有產生出3/4拍的一板二眼板式?這也是因為漢語在組詞上,從《詩經》開始就是以成雙的二字詞組、四字詞組為多。三字詞組是不穩定的,中間一字靠前靠后均是可以的。更重要的是,三字詞組各字往往沒有輕重的區別,因此,不很適應3/4拍這樣的拍式。相反,西洋語言的輕重音組合特別適應3/4拍,因為3/4拍本身是強、弱、次弱的輕重節奏特點,與西洋語言的輕重特點甚為吻合。正由于此,他們一度認為三拍子是完全的拍子,而二拍子或四拍子倒是不完全的拍子,這就很能說明問題了。當然,現在只要唱詞提供一定的條件,完全可以開發出這種一板二眼板式,但要特別注意中西語言上的這種異同關系。
2. 旋律變奏手法的運用。在曲牌體上較多運用的是變形手法,在板腔體結構上已有所突破。現代音樂上“變形”與“變奏”是有所區別的。〔蘇〕 瑪采爾在《論旋律》中講到:“變形大多被用在悠長的抒情歌曲中,允許旋律的動機可以較自由的變化,特別是音和音調的節拍移動和動機一般長度的改變,等等。”“變奏較常出現在快速歌曲、民間舞曲和器樂曲的旋律中,變奏在節拍的重心上不改變動機基本要素的相互關系。”*〔蘇〕瑪采爾著、孫靜云譯《論旋律》,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年,第184頁。由于我國音樂多用五聲或七聲音階,有時就不太可能運用較嚴格的音程模進變奏關系,因而只能采用不很嚴格的變形手法。現代的模進、分裂、倒轉等手法就常需要音階的細分如十二聲音階,在傳統五聲或七聲音階上運用起來就比較困難了。因此,所謂變形者多用于聲樂曲,如上述所謂的悠長歌曲;變奏者多用于器樂曲,器樂旋律不受唱字的牽連變化可以自由得多。因此,曲牌體唱腔多用變形手法是與它們的腔詞關系聯系在一起的。那么,雖然在板腔體中還是運用著大量的變形手法,那就是“依字行腔”原則所帶來的。但是,它已可以根據具體的情況而有所突破,尤其是它有著“拖腔”這一利器,運用變奏手法就更為自由了。因為拖腔旋律大都脫離了與唱字的關系,具有純器樂般的音符連接。當現今在進入更高級的創腔階段,在處理腔詞關系上出現運用諸如“特性主題音調”等手法,就是把變形與變奏二者結合起來,既可用于“拖腔”的純音調的部分,也可巧妙地用于腔詞關系密切的腔格部分上。總之,可以說“變形”與“變奏”也不是絕對的,只要處理得恰當任何變化發展都是可以運用的。
3. 各行當唱腔的形成,當然與旋律曲調的發展有關的。從曲牌體最為成熟的昆曲唱腔來看,雖然已有行當唱腔的一定區別,但還沒有解決好男女聲的音域、音區問題。例如,唱腔上經常出現八度的翻唱,也就是應該下行落音的,但由于音區太低只能將此音翻高八度來唱,這就造成了整個旋律線的跳動與斷裂,令人聽來就很不舒服。這是因為男女聲的音域、音區大致相差四五度,男女演唱同一曲牌必然會產生那種男高攀、女不就,或女高攀、男不就的情況。然而,在比較成熟的板腔體如京劇唱腔中,就根據五度或四度的旋律移位法,形成同一宮調上的“同調異腔”解決了這一難題。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在男女聲各自分唱的基礎上,給予人物音樂形象上的特定性格等,形成各行當的唱腔,這就更具有當今戲曲音樂作曲設計的意義。從這一點上講,行當唱腔在音域、音區運用上,具有類似西洋男女分聲部演唱的特征。因為像青衣用小嗓,老旦用大嗓演唱,說明有一定分聲部的因素。不過,這還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洋的女高音與女中音等的劃分。因為行當只是一種戲劇角色上的劃分,并不是演唱曲調包括音域、音區上的劃分,女高音與女中音之類才是從音域、音區出發來劃分的。當然,行當劃分似乎也有比西洋聲部劃分有所優越的一面,例如,青衣與老旦或老生與凈的區分,特別是演唱方法上的不同,對角色的創造是十分有利的。
4. 調性、調式的進一步發揮運用,這是音樂上有力的表現手段之一。首先,各種調式變化及暫轉調等手法的運用,是旋律曲調充分擴展的標志之一。例如,“梆子腔”系統中早就有了旋律上“歡、苦”音的運用,由于改變了調式的結構,從而形成調式色彩的變化。還有后來“皮黃腔”大量的暫轉調與雙重調式性的運用,如以“變宮為角”“去工添凡”“以變為宮”等造成調式色彩的變化,給人以一定的音樂新鮮感。其次,在調性、調式變化的基礎上,創造出反調唱腔來,這確實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是板腔體旋律結構發展的又一功績。
在曲牌體唱腔上常只能集合同一宮調的曲牌,偶有所謂的“犯調”運用,但總體上它還沒有能意識到反調及其結構變化所帶來的音樂發展動力,而且曲牌的旋律結構本身常也不能提供這種調式變化的可能性。而板腔體上一旦反調唱腔成立以后,它又可以拓展形成各種板式,從而大大加強了唱腔的表現力。例如,京劇的[反二黃],越劇的[弦下調]等等,使劇種的腔調更為豐富。一般而言,“梆子腔”系統中就很少運用反調唱腔,這是因為它本身唱腔上運用“歡、苦”音的調式對比,具有綜合調式性七聲音階的變化,這就不太適合反調的調性對比運用。相反,在“皮黃腔”等板腔體唱腔上,既可以運用旋律中的“歡、苦”音的調式對比,又可以采用幅度更大的調式對比手法,以致產生出反調唱腔來。而且,反調唱腔不僅是拓寬了旋律的發展,更是造就了音樂性格上的一種變化。如果說西洋聲樂上的音樂性格,常是另起爐灶作曲而成的話,中國傳統聲腔上采用的就是類似反調唱腔的手法,其特點就是音樂素材上較為統一,同時常形成一種特殊的旋律情感色彩。
5. 板腔體的具體創作手法大致有以下幾種形式:
(1) 加帽,句首的擴充,常用于句首第一詞組。主要來自“句前襯字”,這在曲牌體中已常運用。從性格上講,有偏于敘述性與偏于抒情性兩類。從結構上講,有單、復式之別。
(2) 插腰,唱腔句中擴充手法之一。主要也是由唱詞的“句中襯字”引起的。從性格上講,也有偏于敘述性與偏于抒情性兩類。
(3) 加垛,泛指在段式或句式內加(夾)用“垛句”形式。常由唱詞的“垛句”直接引起,用于唱腔句式之前、中部,加用由若干規整性的樂型或樂逗排比構成。有句前加垛、句中加垛形式;根據落音有單、復垛等結構。
(4) 搭尾,唱腔句末擴充手法之一。主要功能是補充基本句式敘述的不足,增強表情分量,加強句式結束的圓滿與穩定。有偏于敘述性與偏于抒情性兩類;有單、復式之分。
(5) 加腔,加用“拖腔”的簡稱。在板腔體中加腔常以句末加用無詞(字)樂匯的“拖腔”著稱,其表情的功能非常突出。
(6) 伸腔,即伸長唱腔基本句式的全部或局部的幅度,唱腔句式擴充手法之一。也就是擴大有詞樂匯的節奏時值,常僅是拉長音的幅度,并不具有旋律高低的變化。
(7) 縮腔,即縮短唱腔基本句式的全部或局部的幅度,唱腔句式緊縮手法之一。也就是縮短有詞樂匯的節奏時值,常僅是壓縮音的幅度,并不具有旋律高低的變化。
(8) 減腔,指裁減唱腔基本句式的某一部分,唱腔句式減縮變化手法之一。即把基本句式局部(包括其腔格旋律)裁減掉。
(9) 綜合運用上述變化手法。*于會泳《腔詞關系研究》(任珂、陳應時、沈庭康編輯、校對),據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理論系1963年油印教材翻印,第201—260頁。
板腔體的推陳出新與現實意義
板腔體作為我國傳統音樂的最佳曲式,是我國傳統音樂精華的積淀,也是我國傳統曲式鏈上最終端與最重要的一環。因此,直到現在還是有著它強大的生命力。為什么這么說呢?首先,人類有很多本質性的東西在歷史的長河中,是存在著很大凝固性的,時代的變遷不可能促使它們發生什么根本性的變化。例如,語言這個東西就是這樣。像漢藏語系單音節特點可以說自古以來沒有多大變化,因此,仍然維系著它與音樂方面的特定關系。像西洋印歐語系多音節語言的情況也是同樣。正如早在一千五六百年之前,人們就發現那時天竺(印度)的梵音(屬印歐語系),就“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即表音文字)、“梵音重復,漢語單奇”*(南朝梁) 慧皎《高僧傳》,引自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上),第159頁注1。,那么,這種現象可以說直到現在仍無多大改變。我們仍可以發現今天的漢語與英語互譯,顯然是英語長而漢語短。在古代由于運用文言文,這種現象想必就更為突出了。因此,只要現在人們仍然使用著各自的語言,歷史上那種對聲腔音樂的種種影響都還是存在著的。板腔體制在今天仍然具有它強大生命力的深層原因,就應該歸功于根本上由漢語所帶來的影響。但是,問題是涉及音樂腔調具體的曲式結構等方面,它們則是在不斷演變進化著的。我們只要看看傳統曲式鏈上兩大壁壘的曲牌體與板腔體結構,就可以非常明確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來。例如,曲牌體主要是直接受詞、曲結構形式的影響,其音樂唱腔曲式就十分偏向和依賴于文學唱詞結構。這種結構正如諸文體及自身之間的區分那樣,你若是要改動一些原有的規律,那它的結構也就發生了動搖。例如,《蝶戀花》詞,它的格式是雙調、六十字;前后段各五句、四仄韻。如果取消了哪怕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一個,它就不能成為《蝶戀花》詞了。這是因為在傳統的各詞調之間,它就是以這些條件作為區分你我的,如果抹殺了這些條件,它們也就類同了。當然,實際上也可以有些小的變動,但大的變動那時就稱為“又一體”,也就是已不同于原來的體式,產生出又一種新的體式了。這種新的體式要么或許與其他詞調多少有些類同,要么就成為一種新的形式。但是,由于新形式常容易模糊與原有詞調的界線,而且往往也不一定成熟。因此,聲腔音樂發展到曲牌體結構,它已有了較嚴格的自身條件,如果你變動了它的立足之本,就很難說這是[山坡羊]那是[風入松]了。其次,正由于曲牌體結構的特殊性,現代音樂發展的很多手法,就很難運用到它的結構上去,這樣,也就談不上進一步來推動它的發展了。例如,從句式上看,詞、曲音樂因受文學上句子押韻的影響,多用“換頭”的變化手法。因為二者結尾已經有了相對的約束(押韻、落音),只能變化句的前部與中部了,這種體式也深深影響了器樂曲的結構。我們只要聽聽《陽關三疊》、《梅花三弄》等古琴曲的旋律,大都具有這種“換頭”結構的特點。還有如圍繞中心音旋轉的手法,像《夜深沉》等樂曲大都出現由不同旋律線進入相同的落音,實際上也是一種“換頭”手法的運用。后來詞曲音樂逐漸過渡到板腔體時代,音樂上“換尾”結構才多了起來,由此,我們現在可以較明顯地來區分這兩種結構,也可來大致判斷樂曲產生的時代。板腔體上、下句大二度的不同落音,既是為了唱詞宣敘的需要,也是出于唱腔音樂上發展的需要。因為樂句、樂段的尾音不同,落音上就有了對比,以致造成調式等更大的變化,這是音樂腔調發展的自然結果。而且,中國歷來的詩、詞、曲文體,是只講究字調而不甚講究句的語調的。因此,造成昆曲等曲牌體上的字調旋律設計得非常縝密,各種腔格的腔、詞表達幾乎達到了異常緊密的程度。相反,對于句的語調因整體結構較渙散,句子的跨度又過于長大,幾乎就體現不出各種語調的區別來。實際上在腔詞關系的各要素中,樂句長短的不規則和其對應的腔調,與音樂發展手法的關系最為密切,因此,和現代音樂發展手法運用與否的矛盾也最大。可以說曲牌體結構是一種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狀況,要在曲牌體結構上改革發展,已經是非常困難的了。除非造就一種新的不倫不類的結構形式,但人們就不認為這是某某曲牌,那或許也就另當別論了。歷史上昆曲作為曲牌體結構的典范,在取得輝煌成功后的幾百年來,總體上這種“雅部”腔調卻一直是呈式微趨勢的。從大的方面講,其中自然有藝術盛衰的規律和原因在內。然而,音樂曲式結構上的羈絆看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否則就很難理解它會被板腔體結構的“花部”腔調所取代的事實。雖然后來人們一直對曲牌體改革發展傾注了很大的心血,但似乎收效甚微。現代以來這種改革嘗試也作過不少,即使像20世紀50年代《十五貫》的排演,被譽為“一個戲救活了一個劇種”,但也僅是較多從劇情、表演等方面而言的,至于體現戲曲特征及成功與否的唱腔音樂方面,與傳統的幾乎沒有什么大的變化。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說(如唱功戲等),戲曲改革的根本乃在于音樂上。正如西洋的歌劇成功與否,主要不僅是劇本、表演、舞蹈、舞美等方面,而更在于音樂創作與表演(唱和奏)的方面。從這一點上看,西洋把中國的戲曲看作是猶如他們的歌劇,確實是有同一的地方,事實上也正是這樣。因此,曲牌體制作為一種歷史積淀主要是傳承保存下去,給后人留下一種參考的結構樣式,至于板腔體制應該可以在傳承的基礎上,做到與時俱進、有著更大的發展空間。那么,為什么說板腔體制可以做到與時俱進呢?這應該首先還是從它的結構特點上來談。可以說我國戲曲聲腔發展到以板腔體制為主,說明事實上已自覺或不自覺地發現了曲牌體結構上的極大弊端。事實上我國的文學藝術,一方面文學的詩、詞、曲(元曲、南北曲)發展到后來,逐漸趨向于散文體了,如散文小說的出現與繁榮就是最好的證明。換句話說,實際上就是已經在不斷地打破曲牌體森嚴的格律規范,到了現代隨著提倡白話文,曲牌體的整個結構也就被邊緣化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在腔調上隨著板腔體制的崛起,也說明了在傳統聲腔中的腔、詞關系,開始由歷史上以腔詞一方為主,轉到以腔調一方為主的局面。雖然,真正打破這種局面的是近代學堂樂歌的興起和西洋音樂等一系列形式的引進。但是,從曲牌體與板腔體結構的異同,即可發現這種局面的打破,首先是來自傳統聲腔的內部,是傳統音樂不斷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聲腔中腔詞關系開始發生逆轉的契機,其次才是對外借鑒所起的推動作用。所以,我們說板腔體制不僅匯聚了傳統音樂的很多精華,是現今體現我國民族特色的主要方面,而且,它也具有與現代音樂創作手法接軌的可能性。這是因為,板腔體基本整齊對稱的樂句結構,對于音樂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說現代音樂的本質是趨向于樂句的整齊對稱;結構的便于分解與綜合,這樣有利于運用各種模進等旋律發展手法。就是像西洋音樂發展到后來,也是放棄了以前那些不整齊的結構而歸結為所謂的“四方形結構”*〔蘇〕 瑪采爾著、孫靜云譯《論旋律》,第199—201頁。,就很能說明問題。曲牌體之所以式微就是因為它是長短句式,特別是它的偶數唱句常常拉散了結構,這對音樂的發展是很不利的。歷史上如詞調中慢詞的產生,可以說就是因為偶數句的節律所導致的結果。而板腔體的上、下句樂段結構,一是唱詞相對集中,如七字句是4(2+2)+3的形式;十字句是3+3+4(2+2)的形式。雖然它對唱句語調的體現仍是比較薄弱的,但相比曲牌體上幾乎渙散和平均排比的唱詞來說,已經有了很大的改進。二是在各詞逗間插入大小不一的過門,這對調劑音樂是有很大功能的,而曲牌體唱腔是不用過門的。沈知白認為:“過門是中國音樂中的特點,這特點是中國文字的特性和歌曲的結構造成的;研究民間說唱音樂和戲曲音樂的人,都應該重視這一點而作分析的研究。西洋音樂有和弦終止法,所以不必用類似中國音樂的過門來劃分樂句的起訖。”*沈知白《中國音樂、詩歌與和聲》,姜椿芳、趙佳梓主編《沈知白音樂論文集》,上海音樂出版社,1994年,第71—72頁。事實上中國文字的特性和歌曲的結構,正是板腔體制仍有很大發展空間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其中“中國文字的特性”帶有文學藝術根底的性質,板腔結構則是這種性質的部分反映。說是部分反映說明它還可以有更多的反映,需要我們不斷地去開拓創造。另外,板腔體中還可以運用拖腔及垛板等形式,造成樂句結構上長短方面等更大的變化,這種變化仍是反映出文字的單音節結構在組合上的極大靈活性,反映在腔調上就是沈氏認為的“加的節奏”,它與西洋的“倍的節奏”有著較大區別。*沈知白《節奏的基本原則及類別》,同上,第116頁。因此,如何來平衡這兩者就顯得十分重要了。事實上這兩種節奏以致引申到結構方面也不是完全對立的,很多傳統唱腔都經過“點板眼”的匡正過程,其實也就包含有二者合一的可能性,也就是所謂“強弱”與“尺寸”(長短)盡可能的同一。總之,板腔體結構變化的可塑性還是很強的,只是以往我們對它的認識還遠遠不夠,像沈知白那樣有卓識遠見的音樂理論家還太少。當然,傳統的板腔體制還有很多不適應現代音樂發展的方面,例如,有過于程式化的傾向;樂句規則與不規則的調劑平衡;[散板]與[搖板]運用的過于“水化”(俗語的“水”就是運用上太隨意、太隨便之意);[垛板]的運用還可以進一步增加它與其他板式的對比性,等等。也就是說這些方面,就是我們現在可以努力加以改進與發揮的地方。因此,如何充分發揮板腔體制的優越性,又大力借鑒現代音樂創作的諸元素,不僅對傳統戲曲改革,而且對創立中國式的歌劇,均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現代京劇音樂創作給我們的啟示
對于戲曲的改革與新歌劇的創作,實際上也已經過很長一段時間了。近代以來,所謂的“舊戲改造”也曾經轟轟烈烈過,但那時大都是一些能人志士的義舉,很少有總盤全局上的考慮。當然,藝術的改進也不必來總盤考慮,“百花齊放”才是成功之路。問題是限于那時藝術生存與發展的條件,在其他一些方面如政治、經濟、文化等還不能提供較為成熟的條件下,真正的戲曲改革本身幾乎是談不上的。至于歌劇的創作則更是剛剛起步,能談得上經驗總結的東西更是不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舊戲改造才真正走上了一條較為踏實之路。但是,又由于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的一些干擾,其間反反復復充滿著艱辛與顛簸。首先,音樂對于戲曲的功用方面,長期以來是認識不足的。外國人認為中國的戲曲就如他們的歌劇,那歌劇就應該以音樂創作及唱、奏表演為主的,這就從根本上顛覆了我們舊戲中的理念。因此,現在仍有必要來再認識這個問題。現在還有不少提倡劇本決定制,導演主導制、名演員支撐制,等等。這些當然是能起到一定作用的,但對戲曲音樂方面仍有著莫大的忽視。例如,像理論上論及諸如度曲四聲字音時,沒有同時結合旋律曲調來談總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感,也不可能把問題講清楚;還有像宮調的問題,必須結合樂器、樂譜才能具有說服力,等等。自然,其間也有傳統的音樂記譜、傳統音樂創作方式等方面明顯不足的原因,但正由于此,現今就更應該加強這方面的研究。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使得現代京劇的音樂創作有了一定的發展機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一方面是脫穎而出的、杰出的音樂創作人才的出現,這不是說能出現就能出現的,它本身就有著很大的政治、文化等方面集聚合力的原因,也是時勢造英雄和英雄造時勢的必然結果。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個別音樂主創人員政治地位的上升,在整個戲曲創作中占有主要地位,這就無形中使得戲曲創作出現重視以音樂為主導的局面,這恰恰又是符合現代戲曲及其音樂創作規律的,也為歷來外國歌劇的成功創作所證實。問題是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認真地加以總結,不管什么原因這種總結對于整個戲曲創作上的得失乃是極其重要的,可以說是我們避免重蹈戲曲改革反反復復走老路的覆轍的有效途徑。跳過這種經驗的總結,來奢談今天的創作及作品,往往是不著邊際、不得要領,也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來的。再者,從技術層面上講,戲曲音樂創作的成功經驗,并不局限于現代戲本身,它同樣可以用于新編傳統戲等創作。也就是說,創作手法的創新等也僅是一種技術手段,雖與內容有一定的聯系,但技術就是技術,古今中外作品內容均是可以運用的。
除此之外,從另一種意義上說,現代京劇的創作成功又開辟了中國歌劇創作的一條新路。歌劇這種形式是外來的,從引進到中國來之后,也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然而,在創作上一直存在著兩種理念: 一種是幾乎全盤接受西洋歌劇的形式,從旋律到曲式等各個方面都按照西洋的格式辦事,僅語言是使用漢語而已。這些歌劇自產生以來就一直很難入鄉隨俗,很難被中國人所接受。因為聲樂作品與器樂作品不同,它必須更深入地適應中國人的生活習性、審美觀念和欣賞習慣。直到今天還有人興致勃勃地想創作出成功的準西洋歌劇的作品來,其初衷是好的、富于理想的,但往往資金耗費巨大,沒有演出幾場就刀槍入庫了。就是因為這些作品常常洋味十足,不僅受眾面極小,而且在觀眾中幾乎也沒有留下什么印象。實際上以中國觀眾欣賞角度來看,西洋歌劇的抒情性、敘事性、戲劇性三者,在運用上常也有割裂之嫌。要么詠嘆調,要么宣敘調,戲劇性效果(主要是節奏方面)有時也不夠強烈。而且,把它們連成一片好像還是比較困難的(西洋歌劇中基本沒有語言對白),但這是他們歌劇藝術創作的觀念與欣賞習慣,無可非議。問題是他們認為是順理成章的事,在我們來看則未必,這是因為我們習慣于中國戲曲那一套,尤其是戲曲音樂中有生命力的東西,常常會在聲樂創作與觀賞中頑強地表現出來。
另一種就是仿照西洋歌劇的模式,打造出民族化的歌劇來,從《白毛女》到《洪湖赤衛隊》、《江姐》等,也已走過了幾十年的創作歷程了。這種理念的立足點就是,在創作上大力吸收中國戲曲有特色的成分,來打造中國人喜聞樂見的歌劇,可以說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為,雖然歌劇形式是外來的,但內容是中國的,不管怎樣形式多少是要為內容服務的。而且,你的觀賞對象是中國人,也就不可避免地產生出如何為中國人所欣賞、所接受的問題。雖然這種習慣是可以改變的,但也應該是慢慢地、自然地、循序漸進地變,如果突然來一個大轉彎,那就必然要翻車。問題是能否可以另辟蹊徑,既完善我國的戲曲,又消化外來歌劇的形式,把二者統一起來呢?我們從現代京劇改革的成功,可以看出另一條走向中國歌劇的成功之路,那就是通過戲曲改革,突破原有的戲曲音樂形式,實際上不就成為一種新穎的中國歌劇形式?可以說民族歌劇與現代京劇的創作發展,必將成為一種殊途同歸的藝術之路,事實上它們二者均為中國人所喜愛,如果發展下去完全可以成為一種嶄新的聲腔形式,既是中國現代戲曲,又是中國的歌劇,具有更強烈的現代氣息和鮮明的民族風格特點。我們從以前走過的道路,可以發現現代京劇的一些唱腔比起歌曲化的中國歌劇腔調,不僅具有表面上的那種優美、順暢,而且更具有一種民族音樂的內在張力,因而聽起來更有勁,也更耐聽;更熟悉,又更有新意。其實,這就是民族板腔體制的旋律結構所發揮的作用。因此,對于戲曲音樂改造和中國歌劇的創作,板腔體制仍具有極大的潛力。這種潛力既集中了這種結構所代表的中國音樂特色元素,又在于它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與現代音樂接軌的可能性。總之,現代京劇及其音樂對我們的啟示,具體地來說是多方面的,這里也不可能一一來加以分析,只是簡要地加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1. 選擇京劇作為戲曲及其音樂改革的突破口是十分明智的。不僅因為京劇本身的藝術成就在我國戲曲中是最高的,而且從使用語言上講受眾面也是最大的。其次,傳統京劇的語言用所謂的“中州韻”和“湖廣音”,但之所以成為京劇,除了運用“京音”的行當之外,即使是老生、青衣等這些行當的念唱,從某種程度上還是有“京音”的成分。也就是說實際上可視為是在京音基礎上,擴大“陰、陽”聲調值的對比,“上、去”兩聲作各種變化插穿。*莊永平《京劇中州韻辯正及聲調研究》,上海藝術研究所《戲曲音樂資料匯編》,1986年第3期,收入《琵琶·古譜·戲曲音樂研究——莊永平音樂論文集》,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1年,第390頁。問題是雖然傳統的這種用韻確實能加強戲劇(戲曲)語言的音樂性特征,但畢竟與現代社會有了一定的距離,正如“中州韻”形成本身與現在的用韻已產生距離一樣。因此,“京劇完全可以改用普通話的聲調系統,而不會失掉或破壞其原有風格基調。這里因為: (1) 其陰平和陽平字與普通話的調值本來就很吻合。(2) 上聲可以用上趨腔格,去聲可以用下趨腔格,因此與普通話的調值也能吻合”*于會泳《腔詞關系研究》,第33—34頁。。這就是選擇京劇作為改革戲曲及其音樂,與開創中國歌劇新路所具有的優越性。因為歌劇之用國語(普通話)與京劇改用京音(亦可理解為普通話),可以說就是殊途同歸的,為新的聲腔音樂創作奠定了基礎。
2. 把傳統的板腔體制不斷推向前進。這里涉及很多方面,只能涉獵一二。例如,創造新的板式這是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例如,《海港》中的[排板][吟板][寬板]等,像[吟板]的清唱樣式,在其他的劇種板腔體中早已存在,特別是南方的聲腔如越劇、滬劇中已有。但是,作曲家之所以稱為[吟板],更著眼于各板式及演唱方式上的對比。《海港》的“忠于人民忠于黨”唱段中,[吟板]唱句就是放在前后處于強大動力的[搖板]之中,板式對比極為強烈,極大地提升了[吟板]唱句的表現力和藝術感染力。值得指出的是,這里把傳統的[搖板]賦予如此強烈的情感,這是任何傳統唱腔及民族歌劇中所沒有的。這種只有漢藏語系才有的節奏形式,才真正體現出我國民族音樂的特色。因此,[搖板]的有定節奏與[吟板]的散唱,強烈的節奏緊松對比,富于情感的旋律沁人肺腑,把主人公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情感闡發得淋漓盡致。試想,在西洋歌劇中有如此戲劇性效果強烈的唱段嗎?有如此能打動中國人心的唱段嗎?另外,像“細讀了全會公報”的[寬板]唱段,可以說就是一種全新的板式,其出新的程度相當高,完全可以認為是一種新穎的歌劇唱段。但是,由于有了京劇音樂的底子,這種歌劇唱段就更富于民族化、現代化了。除此以外,引進西洋歌劇的“特性主題音調”,結合唱腔旋律的出新,這是借鑒西洋歌劇的成功做法。還有對原有行當唱腔的突破,結合對新的聲腔音域、音區的劃分,吸收和創造新的腔調,以及對調式對比的充分擴張,等等,*莊永平《于會泳的京劇音樂創作》,《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都不僅僅是對傳統京劇唱腔的革新,也可看作是開創中國歌劇的一條新路。
3. 對傳統京劇樂隊的革新也是極其重要的。我國傳統戲曲樂隊雖然有簡練多用、以少勝多的特點,但是,這只是傳統場面用法的最低要求,已經完全不能適應今天戲曲音樂的需求了。像傳統京劇樂隊中偏向于武場樂器,有過于喧囂之嫌。這是歷史上散樂、百戲中遺留下的,實際上在整個舞臺音樂中,它主要并不是來合作音樂,增加音樂表現力的,它是為了配合念白、動作與舞蹈的,似乎就這樣硬是闖進了音樂的領域。因此,如是要真正成為音樂的一部分,要進行精心的設計才行。沈知白認為:“舊戲中有個最大的缺點,就是用大鑼大鼓時,絲竹就停奏,而用絲竹時,鑼鼓也停奏。我以為鑼鼓、絲竹同時并用是值得提倡的。”*沈知白《怎樣改革舊戲的音樂》,姜椿芳、趙佳梓主編《沈知白音樂論文集》,上海音樂出版社,1994年,第48頁。那現在《智取威虎山》、《杜鵑山》等很多現代京劇中已基本上做到了同時并用,且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效果。相信外國人聽了不會有以前那種“不優美,粗笨,生硬和喧鬧的”印象,而是猶如他們交響樂隊中金鼓齊鳴式的樂隊全奏音響。現代京劇中采用中西混合樂隊,不僅富于中國器樂的音色特點,而且,增加了樂隊的厚度,豐富了織體,極大地提升了樂隊的綜合表現力,這是現代京劇音樂非常成功的一方面。像《智取威虎山》第五場“打虎上山”的前奏;《海港》第四場的前奏,是如此打動觀眾的心弦,完全可以與西洋歌劇的前奏曲相媲美。*莊永平《論現代京劇中西混合樂隊的組建與功能》,《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結 語
綜上所述,板腔體制是繼我國傳統聲腔音樂曲牌體制后,產生的又一最佳的樂曲結構形式。板腔體制是以節拍、節奏的發展變化為緯線,以旋律曲調的變化發展為經線,編織而成的一種充滿活力與發展生機的曲式結構。這種結構體制就是以“板”的樣式,簡稱“板式”為標志來體現的。也就是“以腔生板,以板節腔”成為它不斷發展的既定原則,以板式變化來帶動旋律曲調上的一系列變化。因此,板式囊括了我國幾乎所有的傳統音樂精華,如節拍、節奏上二之冪的發展進程;旋律上的變形與變奏;曲式結構上曲牌與板腔體制的變化;腔詞關系的對應與變式,等等。可以說正是由于板腔體的這些特征,即使是在今天,只要還是使用漢語歌唱,那傳統音樂歷史上產生與總結出的原則就不會過時。因為這種優勢就是在于與語言密切相關的、具有最本質的民族音樂特征和特別適合中國人的欣賞習慣。要說變化,也僅在于本質基礎上的腔詞對應及其形式等方面。正是由于板腔體結構上的優勢,在現代音樂的氛圍下,它還是有著很大的發展空間。當然,在發展中很多東西是要經過再平衡的,例如,“加的節奏”與“倍的節奏”的關系;單旋律與復調的關系;旋律發展的變形與變奏關系,等等,常常會產生出矛盾來,這就要看在處理上如何來平衡了。總之,如果說要創作出我國新型的民族歌劇甚至音樂劇等,板腔體制的很多東西,如長大套曲(相對于歌曲的短小只曲)等方面,還是具有相當優勢的。可以這么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能超過板腔體成套唱腔表現力的歌曲長套體制。相信,無論是戲曲音樂改革還是民族歌劇創作,當它們殊途同歸時,很可能就產生出一種既符合中華民族欣賞習慣,又富于時代特征的新戲劇來。
2016年,1— 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