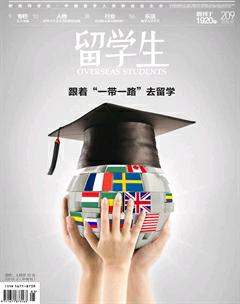中科院院士劉嘉麟:以天地為己任,把山川作課堂
劉嘉麒,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英國開放大學地質系客座教授,我國著名的火山地質與第四紀地質學家
劉嘉麒,1941年出生于遼寧丹東,200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英國開放大學地質系任客座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火山地質與第四紀地質學家。
作為我國火山和瑪珥湖古氣候研究領域的主要學術帶頭人,他率先查明了中國火山的時空分布和巖石地球化學特征,在火山地質、第四紀地質等領域做了大量系統性、原創性工作。
他十進長白山,七上青藏高原,三入北極兩征南極,曾訪問考察過日本、美國、墨西哥、智利、南極、新西蘭、留尼汪、英國、德國等37個國家和地區,把七大洲四大洋那些人跡罕至的地方幾乎走了個遍。
對一個地質工作者來說,跑野外、背著沉重的標本一天跑百八十里路是家常便飯。有一次,他帶一隊人馬進可可西里無人區考察,早上各考察組分頭出去工作,晚上都要到預定的地點宿營;可是到了傍晚,各考察組人員都相繼到了預定的宿營地,唯獨不見載著帳篷和食品的后勤車,從早上出發地到晚上宿營地約20公里,科考人員邊工作邊走路都到了,后勤車早該到達,卻連車影也見不到,顯然是走丟了,漫無邊際地到哪去找?當時天色已黑,考察人員跑了一天,又饑又累,食宿沒有著落怎么辦?那時沒有手機,沒有GPS,無法與走失的汽車聯系,甚至不知道后勤車是否已經出事?當務之急是先把車找到,有著豐富野外工作經驗的劉嘉麒挑選了兩位能辨識車輪痕跡的司機跟他一起去找車,經過一夜的搜尋,終于在另一個山坳里,把迷路的后勤車找到了。
在另一次考察西昆侖時,他們沿著崎嶇的克里雅河河谷攀登,夏天剛剛融化的高山冰雪形成山洪,在涉水過河時,他被急流沖倒,落在冰冷的洪水中,多虧身后的年輕人急忙抓住他的衣服,把他從急流中撈出來,才有驚無險。
對于火山的考察更是充滿驚險。劉嘉麒到過美國的圣海倫斯、夏威夷,意大利的埃特納,留尼旺的富爾奈斯,印尼的喀拉喀托,埃塞俄比亞的埃列塔拉等正在噴發的火山現場考察,親自測過巖漿的溫度,采集剛噴出來的火山物質,觀察火山噴發動態……不僅火山噴出的巖漿、火山灰、火山氣體對人體有危害,若是在現場趕上火山噴發就更危險。劉嘉麒回憶,“2000年,我和他國的同事考察印尼喀拉喀托火山,快爬到火山口了,突然發生了地震,地動山搖,估計有4級。在火山區,地震往往是火山噴發的前兆,如果火山噴發,巖漿和碎石鋪天蓋地落下來,我們就必死無疑,好在那次我們贏得了往山下跑的時間,躲過一劫”。
去南極,18天的航程他因暈船幾乎從頭吐到尾,但照樣船一靠岸便投入工作。在南極北地,他和他的同事進行了地質環境考察,湖泊、冰蓋打鉆,獲取了豐富的地質、古氣候、古環境資料和樣品。
苦嗎? “當時的信念是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鉆進去了,苦在其外,樂在其中。如果你把你做的事情作為一種事業去追求,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他說,“地學工作,以天地為己任,把山川作課堂,為人類謀福祉,是無比豪邁的!”
從2007年開始,劉嘉麒在科研之外,還擔任中國科普作家協會理事長,這個協會已有35年的歷史,凝聚了3000多名科普作家。談到學會工作時,他說:“我已經盡力,還比較滿意,不是很滿意,有的工作還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對于科普界普遍關心的問題——怎么做才能使中國科普更上一層樓?劉嘉麒心底也有自己的答案。
1978年劉嘉麒進入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學習,200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從研究生到中科院院士,歷經25年。四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劉嘉麒說,“院士聽起來好,但是壓力大,社會責任更大,我有好多科研工作沒干完,我想為祖國的發展再好好干上十幾年”。
留學生:有科學家指出“當前我們的生活方式過度消耗自然資源,按照目前的發展模式,可能到2030年我們需要兩個地球來滿足我們每年的資源需求”,對此你怎么看?
劉嘉麟:我對這個事情的看法分兩個方面。
一是整個地球資源、環境、生態方面的問題。如果我們繼續掠奪資源,破壞生態環境,就會給自己帶來災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引起全人類的高度重視。但是,人類確實需要資源、環境,我們要相信人類的智慧和能力能夠改造自然和適應自然。到2030年還有16年,這16年是不可能再生出一個地球來了。如果說到2030年人類就無法生存了,就要毀滅了,這一點我是不相信的。
二是在所有的自然科學定律中,物質不滅定律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定律。盡管人們不斷地從自然界獲取資源和物質財富,但反過來說,這些財富會轉變,原來的資源不夠用了,會有新的資源;原來的能源不夠用了,會有新的能源。我是樂觀主義者,我相信到了2030年全球超過80億的人口還是能養活的。而且社會在不斷地前進,人類的生活也會不斷地變好。
留學生:近年來世界各地的地震似乎比以前多了,是不是和生態變化有關?
劉嘉麟:地震和生態沒有直接關系。地震是地球內部引力的釋放,需要有強烈的地球引力;生態是地球表面的。生態對地震這種大的地質活動起不了作用,只能說地震引起的災害方面,與生態有關系。假設生態比較好,水土不流失,那么地震造成的災害就會減少。
地震除了由火山活動引起之外,最主要的是構造活動引起的。很多地方都有構造引起的地震,但并不一定有火山。從整個地球地震和火山分布來看,它們幾乎都是伴生的,比如環太平洋沿岸。它們都是地球構造運動的集中表現。
我國地震很多,但是火山不一定很多,幾百年來沒有火山噴發,但地震幾乎每年都有。火山和地震不一樣,火山會造成很多資源,除了礦產資源、能源,還有旅游資源。
留學生:地震頻發的原因是什么?
劉嘉麟:地震是地球構造運動的一種重要表現形式,這種運動有時表現得比較消沉,有時表現得比較活躍。最近全球范圍內地震頻發就是地球構造運動活躍的表現。實際上,近20年來,地球一直處于構造活動的高峰期,而且這個地質構造活動期并沒有結束。所以,近年來全球地震、火山噴發發生的頻率和強度明顯增加,造成的災害也明顯增加。
留學生:作為一種自然災害,地震對于我們來講是神秘而又可怕的。應該如何科學地看待地震現象?
劉嘉麟:就像我們人類一樣,地球也是個有生命的物體,它擁有巨大能量,不斷地運動——地震好比它的脈搏,巖漿好比它的血液,火山噴發好像它在通過鼻孔呼吸;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地球有生命力的一種表現。對于近期頻繁發生的地震現象,民眾不必恐慌。盡管地震等自然災害似乎發生得多了一些,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仍屬于地球構造運動的正常范疇。
留學生:地震是不是無法準確預測的?
劉嘉麟:要想準確預報地震,至少需要解決三個參數:時間、地點和強度,以目前的科學發展水平還不能準確地求解這些未知數。
但是,我不認為地震是永遠不可知、不可預報的。任何自然現象最終都可以被認知,只是時日的問題——越復雜的東西,認識它需要的時間就越長。過去我們對于天氣的預報也常常不準,現在預報的準確率卻大大提高,這說明人類對天氣這種自然現象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掌握了它變化的機理和規律,能夠進行預報;同樣,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進步,對地震觀測研究的深入,人類早晚能夠掌握地震發生的機理和規律——總有一天,地震是可以預測的。
留學生:在地震無法準確預測的現實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劉嘉麟:既然目前不可能準確地預測地震,那么當務之急,就應該把工作重點放在如何防范地震帶來的災害上。例如,在地震風險大的地區,要提高建筑物的抗震設計標準和建設標準,嚴格執行有關規范;也可以把一些老百姓從災害風險大的地區早點轉移出去。此外,還應加強地震科普教育,提高民眾的防震自救能力。總之,要多做些“防患于未然”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