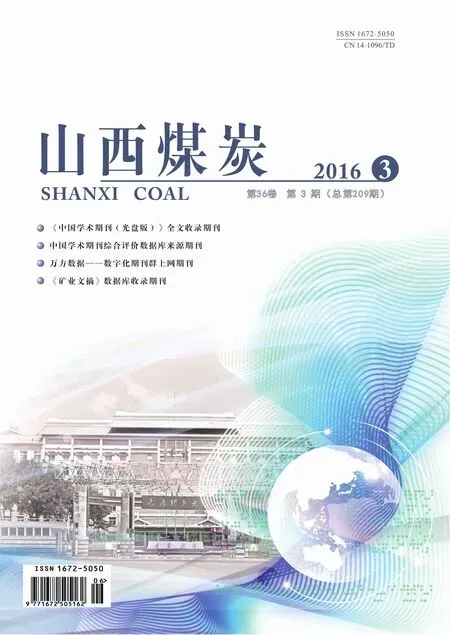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視野下的煤炭企業(yè)污染治理分析
孔翠翠
(1.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北京 100088;2.山西省晉中市司法局,山西 榆次 030600)
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視野下的煤炭企業(yè)污染治理分析
孔翠翠1,2
(1.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北京 100088;2.山西省晉中市司法局,山西 榆次 030600)
摘要:煤炭是我國(guó)基礎(chǔ)能源之一,但煤炭行業(yè)也是我國(guó)高耗能、高污染行業(yè)之一,存在煤炭開(kāi)采利用率低以及大氣污染、水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等一系列的環(huán)境污染與破壞,這日益成為制約煤炭行業(yè)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發(fā)展的主要阻礙。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實(shí)施后,明確了“保護(hù)優(yōu)先”原則,強(qiáng)化企業(yè)的污染治理責(zé)任和違法責(zé)任追究等,在規(guī)范煤炭企業(yè)污染治理方面提出了新的標(biāo)準(zhǔn)和要求。增強(qiáng)環(huán)保責(zé)任意識(shí),加強(qiáng)環(huán)保設(shè)施管理,提高污染治理能力和水平是煤炭企業(yè)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轉(zhuǎn)型發(fā)展的關(guān)鍵。
關(guān)鍵詞:煤炭企業(yè);污染治理;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對(duì)策
目前全球能源供應(yīng)仍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為主,我國(guó)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產(chǎn)國(guó)和消費(fèi)國(guó)[1],煤炭資源的開(kāi)采和利用為我國(guó)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但也造成了環(huán)境污染與破壞的沉重代價(jià)。
1 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實(shí)施前煤炭企業(yè)污染治理概況
改革開(kāi)放初期,我國(guó)面臨著能源短缺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低的問(wèn)題,鼓勵(lì)煤炭資源的開(kāi)發(fā)利用,形成了“多、小、散、亂”的格局[2]。此后國(guó)家先后多次對(duì)煤炭行業(yè)進(jìn)行整改,2009年,中央下發(fā)了《關(guān)于深化煤礦整頓關(guān)閉工作的指導(dǎo)意見(jiàn)》,提出加快煤炭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淘汰落后生產(chǎn)能力,鼓勵(lì)煤礦企業(yè)兼并重組,以煤炭資源大省山西為例,山西省率先開(kāi)展煤炭資源整合及企業(yè)兼并重組,大量關(guān)停了生產(chǎn)力不足、環(huán)保要求不達(dá)標(biāo)的小煤礦,將辦礦企業(yè)數(shù)量由原來(lái)的2000多家減少到130家,到2011年基本上完成煤炭資源整合[3]。提高了煤炭產(chǎn)能和管理水平,對(duì)大型煤礦企業(yè)通過(guò)環(huán)保技術(shù)對(duì)廢水、廢氣、固體廢棄物進(jìn)行“綠色轉(zhuǎn)型”,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環(huán)境污染的壓力。
當(dāng)前與煤炭企業(yè)污染治理和環(huán)境保護(hù)相關(guān)的法律主要有:《環(huán)境保護(hù)法》,《礦產(chǎn)資源法》(1997年),《煤炭法》(2011年修訂),《大氣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訂),《清潔生產(chǎn)促進(jìn)法》(2012年修訂),《環(huán)境影響評(píng)價(jià)法》(2003年)等,在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實(shí)施前,在環(huán)境污染治理上的法律規(guī)定多為輔助性、倡導(dǎo)性規(guī)定,可操作性差。主要表現(xiàn)在:
1)立法理念上,將立法目的定位為“促進(jìn)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的發(fā)展”、“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環(huán)境的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等,使污染治理與環(huán)境保護(hù)輔助或協(xié)調(diào)于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容易形成“經(jīng)濟(jì)發(fā)展優(yōu)先”的思想。此外,將環(huán)境保護(hù)工作主要放在污染“防治”上,而缺乏“治理”、“保護(hù)”的工作思路和方法。
2)環(huán)境污染治理的主體和責(zé)任模糊,可操作性差。目前的環(huán)境管理主要是“自我管理”,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體系不完善,內(nèi)容模糊。將煤炭企業(yè)定位為污染治理主體和環(huán)境責(zé)任主體,讓煤炭企業(yè)進(jìn)行環(huán)境的“自我監(jiān)管”,這種道德要求對(duì)于企業(yè)自身趨利性本質(zhì)而言是難以達(dá)到理想效果的。由于政府部門(mén)的工作考核并未將環(huán)境責(zé)任列入目標(biāo)責(zé)任考核中,煤炭管理部門(mén)和環(huán)境監(jiān)管部門(mén)對(duì)煤炭企業(yè)的環(huán)境監(jiān)管也往往以GDP論,使得企業(yè)的污染治理能力得不到提高,環(huán)境保護(hù)更加弱化。法律法規(guī)對(duì)污染企業(yè)的責(zé)任追究多為口號(hào)性、倡導(dǎo)性規(guī)定,對(duì)違法行為的責(zé)任追究缺失,“沒(méi)有強(qiáng)制性懲罰措施的規(guī)定是無(wú)用的。當(dāng)懲罰不再適用時(shí),制度也就失效了”[4]。
3)環(huán)境污染與破壞的處罰力度弱,環(huán)境違法現(xiàn)象屢禁不止。從企業(yè)的環(huán)境保護(hù)責(zé)任而言,“是道德責(zé)任與法律責(zé)任的統(tǒng)一體”[5]。目前環(huán)境責(zé)任追究主要有:行政責(zé)任,主要為警告、罰款、責(zé)令停產(chǎn)、關(guān)閉等;民事責(zé)任,主要為損害賠償責(zé)任;刑事責(zé)任,對(duì)污染企業(yè)處以罰金,對(duì)主管人員和直接責(zé)任人員追究刑事責(zé)任。由于現(xiàn)實(shí)執(zhí)法行為不規(guī)范以及違法成本過(guò)低,而使環(huán)境違法現(xiàn)象泛濫,法律規(guī)定難以為煤炭經(jīng)濟(jì)發(fā)展保駕護(hù)航。
2 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的新的制度規(guī)定
2014年4月24日十二屆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第八次會(huì)議表決通過(guò)了新的《環(huán)境保護(hù)法》,并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為規(guī)范煤炭企業(yè)法律行為及煤炭行業(yè)的環(huán)境保護(hù)提供了新的法律保障。
1)將環(huán)境保護(hù)融入到國(guó)民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確立為國(guó)家的基本國(guó)策。明確立法目的為“推進(jìn)生態(tài)文明建設(shè),促進(jìn)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可持續(xù)發(fā)展”,同時(shí)將舊法中“使環(huán)境保護(hù)工作同經(jīng)濟(jì)建設(shè)和社會(huì)發(fā)展相協(xié)調(diào)”調(diào)整為“使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發(fā)展和環(huán)境保護(hù)相協(xié)調(diào)”。首先,將環(huán)境保護(hù)上升為我國(guó)的基本國(guó)策,確立了環(huán)境保護(hù)在我國(guó)社會(huì)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shè)中的重要地位,其次,改變了以前“經(jīng)濟(jì)優(yōu)先”的立法思維模式,變環(huán)境保護(hù)輔助于經(jīng)濟(jì)發(fā)展為環(huán)境保護(hù)與治理和經(jīng)濟(jì)發(fā)展并行的強(qiáng)制性保障。此外,這對(duì)我國(guó)現(xiàn)行的《煤炭法》第十一條規(guī)定進(jìn)行了明確和加強(qiáng),從法律層面對(duì)于煤炭企業(yè)污染治理起到很大的推動(dòng)作用。
2)明確了政府對(duì)環(huán)境監(jiān)管的責(zé)任和追究制度,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規(guī)定,“縣級(jí)以上人民政府應(yīng)當(dāng)將環(huán)境保護(hù)工作納入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規(guī)劃”,“國(guó)家實(shí)行環(huán)境保護(hù)目標(biāo)責(zé)任制和考核評(píng)價(jià)制度”。明確將環(huán)境保護(hù)工作納入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規(guī)劃、確立了環(huán)境保護(hù)考核評(píng)價(jià)制度,同時(shí)規(guī)定考核結(jié)果向社會(huì)公開(kāi),接受公眾監(jiān)督。這些“硬性”的規(guī)劃、考核指標(biāo),使政府部門(mén)在工作中有憚?dòng)诃h(huán)境保護(hù)的考核,有利于環(huán)境監(jiān)管更加科學(xué)、規(guī)范。此外,新法增加了重點(diǎn)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制度,有利于降低重大環(huán)境污染的發(fā)生風(fēng)險(xiǎn),使對(duì)煤炭企業(yè)排放污染物的監(jiān)管更加明確、清晰,增強(qiáng)了實(shí)際工作中的可操作性。對(duì)于新法頒布以前煤炭環(huán)境部門(mén)“多頭執(zhí)法”而導(dǎo)致出現(xiàn)監(jiān)管“真空”的現(xiàn)象起到減少作用,防止出現(xiàn)監(jiān)管部門(mén)互相扯皮,推卸責(zé)任,有力解決了一些地方政府環(huán)境監(jiān)管部門(mén)不作為、慢作為的問(wèn)題,亦能有效抵制腐敗。
3)擴(kuò)大環(huán)境責(zé)任追究主體,加大環(huán)境污染的處罰力度,強(qiáng)化煤炭企業(yè)的環(huán)保意識(shí)和責(zé)任。首先,新法增加了追究第三方機(jī)構(gòu)的連帶責(zé)任,根據(jù)新法規(guī)定,第三方機(jī)構(gòu)包括環(huán)境影響評(píng)價(jià)機(jī)構(gòu)、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機(jī)構(gòu)以及從事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設(shè)備和防治污染設(shè)施維護(hù)、運(yùn)營(yíng)的機(jī)構(gòu),此類(lèi)機(jī)構(gòu)除依照有關(guān)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接受處罰外,還應(yīng)當(dāng)與造成環(huán)境污染和生態(tài)破壞的其他責(zé)任者承擔(dān)連帶責(zé)任。其次,新法賦予了環(huán)境監(jiān)管部門(mén)的強(qiáng)制執(zhí)行權(quán)力,加大對(duì)污染企業(yè)和個(gè)人的處罰,同時(shí)對(duì)受到罰款處罰而拒不改正的,實(shí)行“按日計(jì)罰”,增加企業(yè)的違法成本。此外,規(guī)定了實(shí)行按日連續(xù)處罰的六類(lèi)行為:違法排放污染物的,未經(jīng)批準(zhǔn)擅自拆除、閑置防治污染設(shè)施的,重點(diǎn)排污單位不公開(kāi)或者不如實(shí)公開(kāi)環(huán)境信息的,污染物集中處理單位不正常運(yùn)行或者未經(jīng)環(huán)境保護(hù)主管部門(mén)同意停止運(yùn)行污染物集中處理設(shè)施的,建設(shè)單位未依法提交建設(shè)項(xiàng)目環(huán)境影響評(píng)價(jià)文件或者環(huán)境影響評(píng)價(jià)文件未經(jīng)批準(zhǔn),擅自開(kāi)工建設(shè)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其他行為。這些規(guī)定意味著,煤炭企業(yè)要加強(qiáng)污染治理力度和水平,否則就面臨著巨額罰款的風(fēng)險(xiǎn)。
3 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對(duì)當(dāng)前煤炭企業(yè)污染治理方面存在的不足與對(duì)策
新環(huán)保法出臺(tái)了諸多“新舉措”,其實(shí)施無(wú)疑對(duì)于煤炭環(huán)境保護(hù)與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但與當(dāng)前的環(huán)境污染治理情況依然存在銜接漏洞,一些法律規(guī)定原則性強(qiáng),有義務(wù)無(wú)法律責(zé)任的法條依然存在,操作性差,有待進(jìn)一步細(xì)化。
1)新法仍停留在管理法范疇,而非權(quán)利法范疇。表現(xiàn)在:a.新法未將環(huán)境權(quán)列入其中,環(huán)境權(quán)是“環(huán)境立法和執(zhí)法、環(huán)境管理的基礎(chǔ),也是環(huán)境法學(xué)和環(huán)境法制建設(shè)中的基本理論”[6]。b.內(nèi)容上,新法突出的是政府環(huán)境監(jiān)管的權(quán)力,民眾保護(hù)環(huán)境的義務(wù)[7],在立法設(shè)計(jì)上并未體現(xiàn)權(quán)利法的立法思維邏輯設(shè)計(jì),而是按照管理法的方式修訂,雖規(guī)定了公民享有公眾對(duì)環(huán)境的知情權(quán)和參與權(quán),但未對(duì)公民的環(huán)境權(quán)做出一般性規(guī)定。
2)處理好新環(huán)保法與其他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的關(guān)系。目前在煤炭環(huán)境保護(hù)方面的法律主要是《環(huán)境保護(hù)法》、《煤炭法》、《清潔生產(chǎn)促進(jìn)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法律規(guī)范多是原則性、抽象性規(guī)定,操作性差,且法律空白點(diǎn)較多。司法實(shí)踐中法官往往只能通過(guò)一些原則性法律規(guī)定進(jìn)行裁決,司法裁決的難度大,而且執(zhí)行效果差,許多法律規(guī)定需要進(jìn)一步明確具體。根據(jù)新法優(yōu)于后法、特殊法優(yōu)于一般法等原則,在煤炭環(huán)境保護(hù)方面對(duì)污染物排放的監(jiān)管和處罰措施應(yīng)使用新環(huán)保法的規(guī)定,單行法如《大氣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應(yīng)進(jìn)行相應(yīng)修訂,引入環(huán)境監(jiān)測(cè)預(yù)警、環(huán)境信息公開(kāi)、環(huán)境公益訴訟等新內(nèi)容,并進(jìn)行細(xì)化,提出明確具體的規(guī)定,以適應(yīng)新環(huán)保法的規(guī)定。
3)完善相應(yīng)的司法解釋和配套法規(guī)定。對(duì)新規(guī)定中提出的對(duì)違法排污企業(yè)實(shí)行“按日計(jì)罰”,固然增加了違法成本,但應(yīng)考慮企業(yè)的環(huán)保責(zé)任承受能力,對(duì)“按日計(jì)罰”有無(wú)上限,上限是多少尚無(wú)解釋性規(guī)定。對(duì)于環(huán)保監(jiān)管部門(mén)執(zhí)法操作帶來(lái)了困難,增加了執(zhí)法部門(mén)任意執(zhí)法的風(fēng)險(xiǎn)。下一步應(yīng)當(dāng)對(duì)“按日計(jì)罰”的標(biāo)準(zhǔn)進(jìn)行明確,促進(jìn)行政機(jī)關(guān)依法行政,科學(xué)執(zhí)法。此外,新法提出環(huán)境保護(hù)公益訴訟,對(duì)于訴訟主體的認(rèn)定、法院判決和執(zhí)行問(wèn)題需要落實(shí)細(xì)化的規(guī)定。新環(huán)保法實(shí)施后,2015年11月出現(xiàn)了我國(guó)首個(gè)環(huán)境保護(hù)公益訴訟案件——“南平生態(tài)破壞案”,在南平市中級(jí)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宣判,引用專(zhuān)家輔助人對(duì)生態(tài)環(huán)境功能損失的認(rèn)定作出判決,在我國(guó)環(huán)境保護(hù)公益訴訟司法實(shí)踐中邁出了第一步。對(duì)于公益訴訟判決執(zhí)行問(wèn)題仍有待司法實(shí)踐的檢驗(yàn),需要制定相應(yīng)的法規(guī)規(guī)章進(jìn)行細(xì)化和明確。
4)環(huán)境保護(hù)是一項(xiàng)綜合治理問(wèn)題,需要企業(yè)、政府和社會(huì)公眾共同參與。企業(yè)是環(huán)境保護(hù)的落實(shí)主體,煤炭企業(yè)經(jīng)過(guò)整改,依然存在污染治理的遺留問(wèn)題,如設(shè)備更新淘汰的融資問(wèn)題,環(huán)保技術(shù)引進(jìn)問(wèn)題,需要政府給予財(cái)政投入和政策引導(dǎo),對(duì)企業(yè)環(huán)境保護(hù)責(zé)任進(jìn)行積極正面引導(dǎo),使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環(huán)境保護(hù)并行而互不拖累。對(duì)于政府環(huán)境監(jiān)管部門(mén)的執(zhí)法力度和執(zhí)法人員的綜合素質(zhì)需要進(jìn)一步跟上新環(huán)保法的要求。還應(yīng)加強(qiáng)執(zhí)法人員的培訓(xùn)以及面向社會(huì)公眾尤其是企業(yè)主體的執(zhí)法宣傳。
參考文獻(xiàn):
[1]陳剛.煤炭環(huán)境保護(hù)的探討及治理對(duì)策[J].北方環(huán)境,2012(4):147-149.
[2]伍超.山西煤改法律問(wèn)題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xué),2011.
[3]山西煤礦兼并重組接管率達(dá)85%六產(chǎn)煤省區(qū)赴晉考察調(diào)研[EB/OL].鳳凰網(wǎng),[2015-12-10].ht tp://f inanee.i feng.com/news/spcial/ sxmqcz/20091116/1469943.html.
[4]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社會(huì)秩序與公共政策[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0.
[5]葉曉丹.論循環(huán)經(jīng)濟(jì)條件下的企業(yè)環(huán)境責(zé)任[J].福州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7(4):77-82.
[6]莊敬華.環(huán)境污染損害賠償立法研究[M].北京:中國(guó)方正出版社,2012.
[7]彭本利,李?lèi)?ài)年.新《環(huán)境保護(hù)法》的亮點(diǎn)、不足與展望[J].環(huán)境污染與防治,2015,37(4):91.
(編輯:楊鵬)
中圖分類(lèi)號(hào):DF468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672-5050(2016)03-076-03
DO I:10.3969/j.cnki.issn1672-5050sxmt.2016.06.023
收稿日期:2015-12-16
作者簡(jiǎn)介:孔翠翠(1988-),女,河北滄州人,在讀碩士研究生,從事民商法學(xué)研究。
Pollution Controlof Coal Enterpris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KONG Cuicui1,2
(1.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rve and Law,Beijing 100088,China;2.Justice Bureau of Jinzhong City,Shanxi Province,Yuci030600,China)
Abstract:Coal is one basic energy in China.However,with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and high pollution,coal industry has a seri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including low mining and utilizing rate of coal,air pollution,water pollution,and solid waste pollution,which have been themajor obstacles against the transformation ofeconomic development.Theenactmentofnew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Law clarifies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y to protection and enhance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liability investigation of the pollution control of the coal enterprises.New criteria and requirements are proposed in respect of the pollution control specification.It is the key fo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al enterprises to improve consciousness,equipmentmanagement,and control levelof theenvironmentalprotection.
Keywords:coalenterprises;pollution control;new EnvironmentalProtection Law;mea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