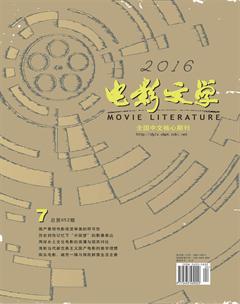電影《人性的污點》中流動意識的現象學
王玉霞
[摘 要] 電影《人性的污點》改編于菲利普·羅斯的同名小說,并繼承了小說中作者對創作材料的內省式處理方法,本文運用現象學意識的內時間結構對其創作軌跡進行梳理以及反思。現象學認為,在流動中統一了自身的意識是在與社會共同體交互體驗中形成的,自我的展現須內置于社會的辯證關系之中。作者的這一探究過程是通過在文中的自我意識流動所架構的內結構來實現的。由此,作者印證了唯有通過現象學文本中的不間斷的自我揭示、自我張揚,方能使得人不再成為種種偏見的受害者。
[關鍵詞] 內時間結構;體驗維度;被給予性;意識統一性
電影《人性的污點》改編自小說《人性的污穢》(2000),后者獲2001年筆會/福克納小說獎、2002年法蘭西梅迪契外國最佳圖書獎和WH史密斯文學獎,與《美國牧歌》《我嫁給了一個共產黨人》一起并稱為“美國問題小說”三部曲。這部無論電影還是小說都贏得了多種獎項的作品正如《紐約時報》所評說的那樣,乃是一部表明時代潮流的作品。
一、現象學:流動意識的內時間結構統一了敘事
影片繼承了羅斯對該小說創作材料的內省式處理方法,小說的整個結構是以主人公自身覺知的時間性結構為脈絡安排,指出這一現象學的文本結構構成是嚴肅文學中思考人之為人的社會適應性的表達途徑,它將自身覺知的時間性生存片段分解在文本的適當角落,這種自我的文本化、自我的展現不是基于發泄自我的焦慮、憤怒、恐懼,也不是一種極度困惑感的問題解決,而是將人內置于社會的辯證關系中,去思考人的存在,警醒社會——一個混雜的后現代社會。
也許,人性的污點是一種色情的表達,抑或種族的表達,或是背棄家庭和社會道義的表達,其實在羅斯建構的這部多層面、多聲部的流動對話里,甚至在作者與作品的對話過程中,對某個主題的思考已滲透在對社會辯證關系主體體驗的被給予性當中,成為其一部分,這種流動意識結構更有助于深入地刻畫真實的生存現狀。
鑒于對現象維度的關注,歐文·弗萊那根在1992年《對意識的重新思考》一書中就曾主張“自然的方法”的研究思路,如果我們想要從事一種嚴格的意識研究,那么我們并不能僅僅進行心理學功能的分析,我們也需要給予現象學重視。現象學自最初由胡塞爾所開創并在其他哲學家那兒歷經了各種發展以來,如舍勒(Scheler)、海德格爾(Heidegger)、古爾維奇(Gurwitsch)、薩特(Sartre)、梅洛龐蒂(MerleauPonty)、萊維納斯(Levinas)以及利科(Ricoeur)等,能夠提供比單純內省證據匯編更多的東西。內省(introspectionism)通常被理解為一種使得我們能夠報告并且描述自己內心狀態的心理操作。然而,嚴格說來,現象學并不關注或基于這樣的操作,而是關注意義的結構。它研究現象、顯相、生活世界的結構和它們的可能性條件。[1]羅斯在《人性的污穢》中,關注的正是生活世界的結構,并以其中的內時間結構為主線貫穿整部小說。這也是我們之所以不采納意識流理論的原因,盡管這一理論和現象學頗有淵源,盡管小說也如伍爾夫強調的那樣把人物頭腦中宛如微塵般的印象都記下來,認為只有這樣才算寫出了“生活的本來面目”。然而意識流只對意識的活動進行分析,并不涉及對意識對象進行深入探究,也許它更適合于羅斯《對立人生》中那種按照原始的方式展現在讀者面前的潛意識活動畫面,這些畫面有的和《鬼作家》之中的一樣是對立的、矛盾的。但是這只是表象,在這兩部小說中孕育的并不是意識流的雜亂無章,卻是精神分析式的嚴謹的結構。不得不忠實地說,羅斯的小說和意識流看似聯系千絲萬縷,實質是不搭邊的。而對現象維度的思考,《人性的污穢》則是難得的范本。它與羅斯其他元小說不同的是文本突出構建了自身性流動意識的統一,小說中的心理世界無不被一個無時間的中心自我的統一化、綜合化以及個體化功能所支撐。正如薩特所說,在這里“意識作為時間化活動(qua temporalizing)而統一了它自身”[2]。
關于自身性流動意識的討論實際上是高度跨學科的,它或是對于人生存現狀的思考,或是一種社會建構,抑或是一種神經學上誘發的幻覺,有如《人性的污點》中,當科爾曼看到使他大吃一驚的情人福尼亞的頭發,“那頭在他的經驗里,從來都是緊緊地束在一個橡皮圈里的,在自己的伙伴們面前全都放了下來時”[3],他被動地體驗著自己“存在”的可能性和“存在”的價值。不論律師還是女兒,甚至同事的指控都沒有使他確認任何東西,而這毫無意義的一幕卻終于徹底向他揭示了自己的恥辱。一種病態的孤獨癥式的體驗充斥著他。筆者此時并非落入讓·保羅·薩特所倡導的一種存在主義者哲學,在薩特的存在主義世界里,人的基本生存狀況是孤獨、煩惱、焦慮、絕望和荒誕。這里的科爾曼則大不同,他一貫保持著處于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的理性思維,并且并不絕望。他客觀地分析道:自己“絕不是個政治上煽風點火的人,不是個瘋子,甚至從知識或哲學層面上來說都不是”[3]。由此,倒是讓我們看到了在科爾曼身上,一種鮮明的自身體驗的可通達性(accessibility)。羅斯在這部小說中把對于自身的可通達性(accessibility)運用在多個角色的第一人稱視角中,而非局限在某個旁白的人或主人公身上。這一多角色的第一人稱視角卻是通過主人公意識的流動來實現的,從而達到了流動著的統一。
許多現象學家曾通過關注其在體驗上的被給予性而重視第一人稱視角的問題。小說以作者的第一人稱視角開頭,“我”對科爾曼最初的印象猶如壞蛆被激發出來。[3]為了證實這一體驗的真實性,“我”開始調用文本的互文,回憶起了幾年前科爾曼還曾是“我”渴望拜求的EI霍諾夫,為此“我”寫了《鬼作家》。同時他還回憶起了他接任院長的事。這些敘事看似無序,實際上屬于同一時間性生存片段,也都是為了表明在故事的開頭“我”尚且對主人公不熟悉,只有一些大致瑣碎的印象而已。
在薩特看來,意識的特征在于它根本的自身被給予性或者自身顯現,因而它沒有任何隱匿或被遮蔽的部分。然而,自我卻是不透明的,它的本性需要逐漸被挖掘出,也始終余留著有待揭示的方面。在這部小說中,羅斯所安排的流動意識的內時間結構使得文本一點點地揭示出科爾曼·西爾克這個主人公的所有的真實。因而,在隨后的流動意識中,上述認識被推進、更新,甚至顛覆:“我笑了。不,這可不是那個被生活排斥、逼瘋的復仇者(指主人公)——甚至都不是另外一個人。這是另外一顆心……”作者方才意識到,“我實際上已經不假思索,未經盤算,把他當作了朋友”。到小說的最后,作者才說道:“現在我知道了一切……”[3]體驗具有第一人稱被給予性,即我屬性(the quality of mineness)。在這里作者向讀者展示的是“我”正在經歷或度過的經驗悄無聲息地被給予。它們必須是主體所覺知到的狀態,而這顯然涉及了一定程度的自身覺知;事實上,是一種反思的自身覺知。[4]整本書中,作者和主人公,乃至其中的任何一個人都無暇困惑,也來不及苦悶,然而都處在一種簡單的、看似復雜的流動意識當中,權衡著人生。而值得強調的是,這種現象意識,不像存在主義者那樣,缺乏主體性維度,而是一種假借體驗來積極思考的、有意識的信念、欲求或感知。在現象學看來,自身隨著在敘事中自我意識的流動而成為一種建構過程,而不是對一個已經存在著的自身的探討。相反,自身在敘事過程中被建構,敘事本身即成為一個開放的構建活動,它經受著持續的修正,也受到其所在共同體的制約。
二、現象學:客觀而嚴謹的敘事解釋
正如前文所說,在自身覺知的內時間結構中,敘事隨著流動的意識被構建起來,自身理解和自身認識并不是某種一下子完全被給予的東西,也受到其所在共同體的制約。文中作者以社會研究的一種,即現象學來探究社會,關懷自身的意識,實質賦予了敘事客觀性和嚴謹性:現象意識的直接性(immediacy)雖然涉及了第一人稱通達的特征,但是它與絕對可靠性(infallibility)和不可糾正性(incorrigibility)的認識論論斷并無聯系。在主人公科爾曼草率的陳述中,他的第一人稱的信念被他人修正或被外部證據所推翻,而且,并非所有的自身認識都是直接的。正如墨蘭所說,有許多自身認識都是基于他人亦可進行的同類思考而被艱難獲得的。[5]法利(情婦的前夫)的自身體驗是:作為一個農場主,為國出征,第一次回家的時候,人家都不認識他了,而他知道他們說得對——他們全都怕他。他們不賞識他就算了,反倒怕他,所以不如回去。[3]
現象學作為一種解釋學,它的客觀性還在于:對敘事性自身理解的實現具有一個明顯的社會性維度,其視角如同社會廣角一般具有高度的俯瞰性。現象學認為敘事性的自身理解需要成熟的社會化,它也需要一種能力來通達和報告那些使某人成其所是的社會狀態、氣質和傾向。因而,這部小說中處處可見大膽直白的對社會、時代和政府的評論,而這種種評論不晦澀、不暗指、不隱藏、不保留。科爾曼“寧可將自己的前途攥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把命運交由一個愚昧的社會任意處置——在這個黑奴解放宣言發表八十多年后的社會里,偏執狂們碰巧發揮的作用過于巨大而不適合他的胃口”。小說甚至直接熱議了當下的時局,對克林頓下臺丑聞在多處章節給予長篇累牘地注解。他提醒人們回顧以往的社會“半數以上的人屈從于作為社會政策的病理性虐待……民族淪為將個人的尊嚴洗劫一空的思想罪犯的奴隸……這些可怕的試金石,在這里他們卻端著武器對付福尼亞·法利”[3]。
三、結 語
撮其要以概之,現象意識將它的目標指向其自身狀態和活動的問題,一個自身指向性(selfdirectedness)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質決定了小說作者及其主人公必然采取一種嚴謹的自我評估來探究生命在當下社會的適應性。而這一探究過程作者是通過在文中的流動意識所架構的內結構得以實現的。值得強調的是,在流動中統一了自身的意識是在與社會共同體交互體驗中形成的。正如自身是處于其世界性關聯中的,從根本上來說,自身體驗并不是一個“內感知”、僅僅通過內省或反思的問題,《人性的污穢》在“我”的所作所為和所遭受事件中實際地體驗著自身,現象學作為社會學的一門學科被作者當成一種文學策略來影射社會,影射社會中的人,通過文本不斷地自我揭示,自我張揚,唯有如此才能使得美國人不再成為種種偏見的受害者。現象學的這種廣闊的社會維度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不要企盼著在其中尋找某個“自我”,相反,我們應當面向世界的體驗,在那里我們將發現那置于境域中的自身(situated self)、[6]現象學的自身是世界性的(selbstweltliche)。[7]
[參考文獻]
[1] [丹]丹·扎哈維.主體性和自身性[M].蔡文菁,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6.
[2] Satre.La transcendence de lego[M].Trans.F.Williams and R.Kirkpatrick.NY:The Noonday Press,1957.
[3] [美]菲利普·羅斯.人性的污穢[M].劉還珠,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4] Carruthers P.Language, Thoughts,and Consciousness:An Essay i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55.
[5] Moran R.Authority and Estrangement:An Essay on Self-Knowledg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
[6] Heidegger M.Gesamtausgabe Band 58:Grundprobleme der Phanomenologie[M].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3:258.
[7] Heidegger M.Gesamtausgabe Band 61: Phanomenologie Interpretationen zu Aristoteles[M].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