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三替”的江湖
章形
【采訪筆記】見(jiàn)到蘇煥時(shí),他剛做完一筆“業(yè)務(wù)”,笑呵呵地回寢室。這個(gè)即將畢業(yè)的大四男孩身材微胖,相貌神色間透著山東人普遍具有的那種憨厚勁。
“可惜啊,下個(gè)月我這個(gè)‘三替公司就要關(guān)門(mén)了,我這CEO得出去實(shí)習(xí)了。”蘇煥笑呵呵地說(shuō)——他在大學(xué)里開(kāi)了3年的服務(wù)公司,賺了七八萬(wàn)元,外帶一個(gè)女朋友。
更可貴的是,他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收獲到別人難以企及的閱歷和經(jīng)驗(yà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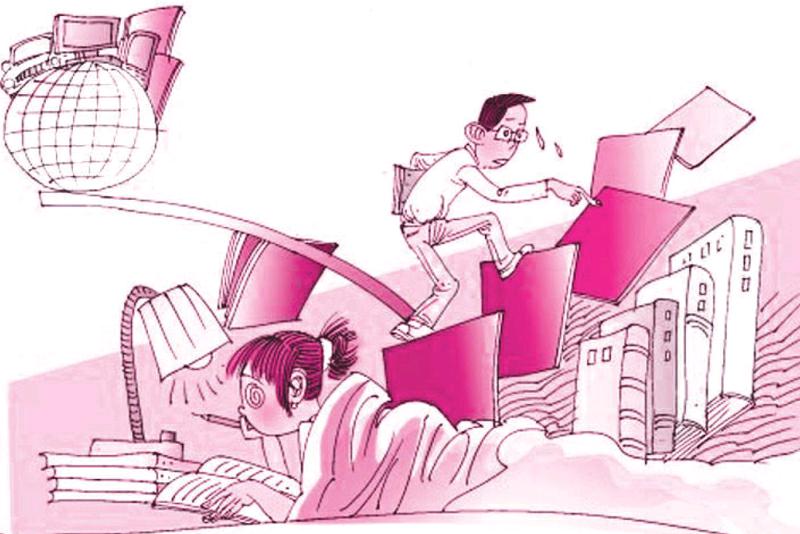
有的人上大學(xué)后,天天合計(jì)如何創(chuàng)業(yè)成為下一個(gè)扎克伯格;有的人在大學(xué)里一門(mén)心思當(dāng)情圣;還有的學(xué)生終日只研究考研或如何留校。而蘇煥踏入浙江的一所大學(xué)校門(mén)后,滿腦子想的是“怎么解決吃飯問(wèn)題”。
另類(lèi)勤工儉學(xué)
和別人不同,蘇煥能上大學(xué)是靠領(lǐng)“家庭經(jīng)濟(jì)困難學(xué)生補(bǔ)助”,他必須想辦法賺點(diǎn)錢(qián)。
本來(lái),上大學(xué)之初,學(xué)生會(huì)勤工儉學(xué)部也給他安排了一個(gè)兼職工作,但收入太少。上學(xué)同時(shí)還要貼補(bǔ)家里的蘇煥,無(wú)奈之下開(kāi)始自己謀劃“開(kāi)公司”。
蘇煥是文科生,沒(méi)什么技能,只好在服務(wù)行業(yè)上想辦法。他自己用筆寫(xiě)了上百?gòu)埧ㄆ厦鎸?xiě)著“三替公司——只要合法、只要給小費(fèi),各種難辦的事都可替您做,電話********”
隨后他逐個(gè)寢室樓發(fā)小卡片,無(wú)論新生還是老生,看到卡片后大多是一愣,然后笑著問(wèn):“什么都干?”蘇煥點(diǎn)頭說(shuō):“不做普通事,只做難事,尤其是不方便出面的那種。”
確實(shí),蘇煥搞的這個(gè)“三替公司”,并不是像校園里那些跑腿公司,做一些替同學(xué)送東西、收快遞、打飯、道歉、簽到之類(lèi)的普通業(yè)務(wù),而是專(zhuān)門(mén)做一些看上去比較麻煩的事。
“我也喜歡稀奇古怪的事,因?yàn)榉?wù)費(fèi)會(huì)比較高,呵呵。”蘇煥說(shuō),他接的第一筆業(yè)務(wù),就是替人寫(xiě)檢討,他按對(duì)方要求手寫(xiě)了一份4000多字的檢討,用了一下午時(shí)間。對(duì)方問(wèn)該給多少錢(qián),蘇煥試探著說(shuō),150元行不行。對(duì)方很爽快就掏錢(qián)了。
接到的第二個(gè)活,是陪一個(gè)女生去電子市場(chǎng)里退筆記本電腦,那女生已經(jīng)去過(guò)一次,商家不肯退,這個(gè)女生置氣,花錢(qián)雇蘇煥站在這家店門(mén)口,連續(xù)喊了兩個(gè)多小時(shí)“某某牌電腦是垃圾,誰(shuí)買(mǎi)誰(shuí)上當(dāng)。”蘇煥的嗓子徹底喊啞了,雖然到最后,這個(gè)女生的電腦也沒(méi)退成,但女生給了蘇煥300元的辛苦費(fèi)。
很多學(xué)生在校外租房住,女學(xué)生到了深夜不敢單身回去,可以聯(lián)系蘇煥,陪回家一次通常是30元,如果加10元錢(qián),蘇煥還提供“騎車(chē)送回家”服務(wù)。好在學(xué)生們的住所都在學(xué)校附近,最多20分鐘,不會(huì)太費(fèi)力氣。還有的學(xué)生在學(xué)校沒(méi)有朋友,生病了打點(diǎn)滴,花錢(qián)雇他陪同,一次50元。
校園灰色業(yè)務(wù)
賺了點(diǎn)錢(qián)后,蘇煥把高中時(shí)別人資助給他的二手諾基亞手機(jī)換掉,買(mǎi)了一款能裝微信的二手智能手機(jī),然后重新在校園里發(fā)帶微信號(hào)的自制名片。
自從裝上微信 “神器”后,蘇煥業(yè)務(wù)量明顯增長(zhǎng),幾乎每天都有“特別的事”做,但接到的“業(yè)務(wù)”卻越來(lái)越灰色。
“有些是比較隱私性的,比如突然有微信加我,讓我晚上去學(xué)校附近買(mǎi)一盒避孕套,或者是那種事后的避孕藥、驗(yàn)孕棒,然后放到某某樓某個(gè)隱蔽的地方,我做完之后,走出不遠(yuǎn),就會(huì)收到‘雇主發(fā)給我的微信紅包。”蘇煥說(shuō)。
蘇煥的微信名字叫做“替人做事絕對(duì)保密”,時(shí)間長(zhǎng)了,校園里很多知道他的人,都默認(rèn)他是一個(gè)守口如瓶,值得信賴(lài)的窮學(xué)生。干了兩年多的“三替公司”,他曾經(jīng)兩次陪女生去私人診所墮胎。雖然只是陪同,卻讓他對(duì)生活,有了很多說(shuō)不出的感慨。
另外有一些違反校規(guī)的事情,如果無(wú)傷大雅蘇煥也是樂(lè)于做的。比如買(mǎi)酒,通常是在熄燈后,甚至后半夜,蘇煥接到這樣的微信后,騎上自行車(chē)去校外很遠(yuǎn)的地方買(mǎi)啤酒、白酒回來(lái),這種跑腿的勞務(wù)費(fèi)通常按瓶收費(fèi),跑一次就能賺四五十元。
還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有人微信聯(lián)系他,出100元,讓他去校外把一包衣服給燒掉,他嚇夠嗆,不肯,對(duì)方加到200元,他最終去了一個(gè)宿舍樓下墻角,拿到那包衣服。打開(kāi)看了一遍,是幾件比較新的男士衣服,上面沒(méi)有血漬或破損。他小心翼翼拿到校外燒掉,拍了照片發(fā)給對(duì)方,對(duì)方也立刻付款。但蘇煥到現(xiàn)在也不知道是因?yàn)槭裁础?/p>
但有些“業(yè)務(wù)”,幾乎站在法律邊緣,有時(shí)到了晚上,會(huì)突然有新的人加他微信,讓他去外面的藥房買(mǎi)蘭邦泰洛奇、可非或者是鹽酸曲馬多。而且一次就要買(mǎi)10多瓶甚至20多瓶。
對(duì)方給的費(fèi)用很高,告訴他一個(gè)藥店買(mǎi)不夠數(shù),可以打車(chē)去幾個(gè)藥店買(mǎi)。蘇煥雖然是貧困生,但也知道這些止咳藥會(huì)被當(dāng)成搖頭水來(lái)用。起初堅(jiān)定拒絕,但對(duì)方給出很高的勞務(wù)費(fèi),一次買(mǎi)10瓶,送到指定的隱蔽處,就可以賺400元紅包。蘇煥承認(rèn)自己曾多次代買(mǎi)過(guò)這類(lèi)東西。
“到大三的時(shí)候,我就明確不再代買(mǎi)這種東西了。因?yàn)槟菚r(shí)我已經(jīng)真正成立公司了,需要規(guī)范化了,不能搞歪門(mén)邪道。”蘇煥說(shuō)。
蘇煥的“三替公司”后來(lái)真的發(fā)展成了公司,他雇傭了兩個(gè)下屆的老鄉(xiāng),微信里一旦有新老客戶發(fā)出“訂單”,如果是以前做過(guò)的類(lèi)型,蘇煥會(huì)安排兩個(gè)老鄉(xiāng)去做,如果是第一次打交道的客戶,或者是從未做過(guò)的內(nèi)容,蘇煥就親自出馬。
改變?nèi)^
干這“三替公司”的另一個(gè)收獲,就是讓蘇煥收獲了愛(ài)情——一個(gè)浙江寧波的女學(xué)生,平時(shí)在校外租房住,幾乎每周都有一兩次,要花錢(qián)雇蘇煥跟她作伴回住所,蘇煥特別愿意和這個(gè)女孩邊走邊聊,這筆業(yè)務(wù)持續(xù)了將近一年時(shí)間,送一次的費(fèi)用,從最初的30元,變成20元,再變成包月100元,然后,變成了不收錢(qián)。
“其實(shí),大學(xué)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只是一群年輕人聚集的學(xué)府。它實(shí)際上是一個(gè)更加沖動(dòng)的社會(huì)形態(tài),甚至有很多地方?jīng)]有法律的覆蓋,充滿原始的需求。正是因?yàn)檫@個(gè),我賺了錢(qián),又懂了很多別人一生都不知道的事情。”蘇煥說(shuō),干“三替公司”讓他在上學(xué)期間賺到不少錢(qián),除了貼補(bǔ)家里,自己還攢下了七八萬(wàn)元,如果找工作吃力,可以靠這筆錢(qián)做點(diǎn)小生意。而且,他對(duì)人、對(duì)人生、對(duì)這個(gè)世界的看法,已經(jīng)和所有同齡人都截然不同。在即將離開(kāi)校園時(shí),能把這樣的經(jīng)歷說(shuō)出來(lái),心里也覺(jué)得輕松了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