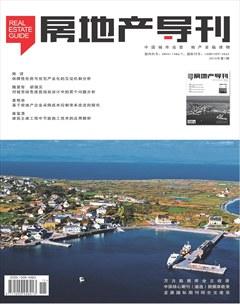常州110畝玫瑰園主入口構筑物設計
周紫菱
【摘要】常州110畝玫瑰園為中國第八屆花博會的展場之一。我做為本項目景觀專業負責人,親歷了無論硬景設計還是軟景設計的復雜艱辛過程,見證了本項目從概念設計到落地的每個環節及細節。每一個項目的主入口設計,尤其是有重要影響力的主題公園的主入口設計,對一個項目的設計成敗起著重要的作用。常州110畝玫瑰園已于2013年國慶順利開園,在此我將最有挑戰性的主入口構筑物從設計到施工的過程整理成文,便于與同行進行設計、技術交流,促進行業發展。
【關鍵詞】花博會 玫瑰園 主入口 構筑物 水玫瑰雕塑
常州110畝玫瑰園位于常州市,東與太湖相近,南臨滆湖,并與“陶都”宜興隔湖相望,西鄰金壇市,北望常州市區,地理位置得天獨厚。現狀基地內水系豐富,主要河道為夏溪河,水路可以直接通向西太湖。項目旨在打造世界珍稀玫瑰的交流展示體驗平臺,深耕玫瑰文化,推廣玫瑰生態精致生活,為常州乃至全世界熱愛玫瑰、熱愛自然、熱愛生活、熱愛健康、熱愛年輕的人們,奉獻一座經典而神圣的精神家園。110畝玫瑰園景觀設計總體概念為盛放的玫瑰,為現代、簡潔、明快的設計風格。本文著重對主入口核心構筑物——水玫瑰雕塑進行設計闡述。
(一)水玫瑰概念設計
呼應110畝玫瑰園的總體設計理念,主入口核心構筑物經過多輪設計比稿后,最終以“水玫瑰”雕塑獲得甲方認可。契合本項目的設計理念,設計提煉了玫瑰花瓣橢圓倒卵形、單瓣環抱特點,簡化玫瑰花形體,從平面轉化到立面至立體效果,采用能映射周邊景觀的不銹鋼材質,融入到藍色的水體中,并加以曲線條平面紋樣,增加水體流動感。水玫瑰由四個不銹鋼托盤組成,每個托盤邊緣有均勻水簾,托盤上有流水。設計圖紙表達的效果美輪美奐,我們設計團隊起初甚至沒做更深的考慮:一個傾斜的斜面,由于重力原故,周邊一圈怎么能做到水簾的效果?斜面上又如何保證流水?
(二)水玫瑰深化設計
1. 水動力設計
水動力設計原理是:根據設計水玫瑰有四層托盤,由四根主水管供水,每層托盤有三根支管分水;(從下往上)一、三層是傾斜托盤,分水管供邊緣打孔的鋼管水簾用水;二、四層是平行地面托盤,分水管供涌泉用水。其中,一、三層斜面托盤邊緣鋼管按照φ2mm的間距均勻打孔。因在有厚度的鋼管上打孔,打孔的方向及力度需保持一致,如方向不一致,將會導致后期水簾角度不一。
2. 降成本策略
設計之初,從設計效果考慮,水景收邊用了大規格爵士白大理石,從面寬、厚度及加工
難易方面,成本都比較高。經過與甲方多次溝通優化設計,經過如下細節設計:其一,水景收邊爵士白大理石邊緣壓頂從150mm降到120mm厚,水景收邊石材從1000mm寬調整為兩塊400mm寬組合,內部看不到厚度的石材只需20mm厚度;其二,側立面石材凹進去1500mm深調整為1000 mm。經過優化,水景收邊所用的爵士白大理石費用從100多萬元下降到55萬元左右。
(三)水玫瑰施工
1.水玫瑰雕塑泥坯制作
項目組從細節方面提建議,包括體量,各層平面投影的相互關系,凹槽的平面投影連貫性等。建議如下:①保證下層不銹鋼板全部包住上層跌水后,最窄處還需留有足夠的寬度,避免跌水從一層跨層落到第三層;②凹槽部分在做實體雕塑時,是光面不銹鋼,需要與周邊磨砂面不銹鋼共面,防止不共面導致水從凹槽大量溢出,破壞均勻的水幕效果;③從立面上看,建議第二級跌水的左側略微向內收,以免超出第三級水盤的范圍,另外,水盤底側弧度略微向內收,呈銳角狀態。④第一、三級,二、四級立面成平行關系。
我很高興的看到,因為這些細致到位的建議,甲方和雕塑廠家都非常愿意傾聽并且在雕塑制作過程中不斷改進。因為專業細致的服務,甲方和雕塑廠家都給予了我們設計團隊莫大的信任。因為多方的眾志成城,我們攻克了一個一個難題。
2. 水玫瑰雕塑水簾效果實驗過程
按照設計方要求,需甲方做一個縮小比例的實體模型,但由于成本、工期、復雜度等方面原因,只能一次施工到位,沒有實驗的機會。
現場實驗方法:將鋼管按照間距2cm打φ2mm孔。灌入水,現場觀看水簾效果。經過現場多輪實驗,最終歸納以下三點結論:
第一:打孔鋼管水平放置時,水簾的弧度一致。 但設計要求是水簾垂直落地。
第二:打孔鋼管傾斜放置時,水簾的角度都會出現遠近不同的弧度 。
第三:打孔鋼管加角鋼后水簾垂直均勻落下,達到預期效果。
3. 雕塑實體加工過程
工廠里模型骨架已經搭完了。龐大的實體鋼骨架占據了諾大的廠房。投入的巨資和緊張的工期都在給在場的設計方、甲方、監理、承包商、工人施加壓力:怎么對鋼管打孔?打孔間距,大小,方向要求怎樣?達到什么樣效果及怎么達到效果?來往于水模型實驗基地和加工廠房,結合模擬實驗,與大家交流、溝通,最后我提議,在鋼管邊上加一圈角鋼。增加的角鋼可以遮擋孔洞,對斜面不同角度的水簾可以有效的擋回成直線落下,同時也解決了圓鋼對托盤邊緣的不利形象,以折角收口,更現代簡潔。做為設計方,我同時指示施工方,打孔時務必保證間距均勻,用力大小及方向均勻一致,任何方向偏差都將影響出水弧度的不一致。一個作品的成果與否,施工工藝占有極大的功勞,全是純手工的打孔,精細的工藝要求對工人而言是很大的挑戰。
4. 雕塑現場施工
現場需預埋好各種規格的管線,泵坑也需設置在合適的位置。因為每層托盤所用的給水管、泵坑位置都不一樣,所以給水管預埋需考慮不銹鋼盆的朝向,需一次準確施工到位。混凝土澆筑后,再將最大直徑達9米的鋼骨架搬到現場,每層鋼骨架分成兩塊組裝。鋼骨架也需結合建筑的門廳、主入口的位置,設計需要每個玫瑰托盤相互疊加的關系以及面對的各入口關系合理,與已安裝好的給水管等達到完美的空間關系。
這是考量技術的施工,將體量巨大的雕塑搬到現場,縱多的管道需避開水玫瑰雕塑眾多交錯復雜的鋼骨架,現場需不斷校正雕塑與管道的位置。所以一個成功的作品,光鮮的形象背后,傾注了眾多人的心血。設計到施工整個過程的精益求精,是出佳作的整個團隊的必要追求。
(四)主入口水玫瑰建成效果
如圖所示:水幕均勻,斜面周邊也有均勻水幕;托盤邊緣銳利,簡潔現代;石材收邊線條優美,如一塊整石;建筑的玻璃幕墻上映射了一朵宛如盛開的玫瑰,景觀設計與建筑能達到如此完美的融合,建筑也在時刻訴說著玫瑰和愛情,以玫瑰為主題的水玫瑰雕塑,無疑把玫瑰園的主題詮釋的很美。 結語:項目總體概念于2011年9月啟動,主入口做為最重要的形象入口,設計方案最后確定已到2013年1月。主入口從設計確定到落地不到一年的時間。做為110畝玫瑰主題園的景觀設計負責人,個人在整個項目設計管理過程中,充分悟到景觀設計是傾注了每個設計師、雕塑家、各方人員的細膩、豐富的情感,浪漫的情懷,對工程與美學的完美結合的追求,對設計精益求精的追求,對社會的責任感。在此,我特別感謝當時我任職的深圳奧雅景觀規劃與建筑設計有限公司;項目合作的甲方、雕塑廠家以及施工單位。因為對設計的不懈追求,我們的社會也更加精彩,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將更和諧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