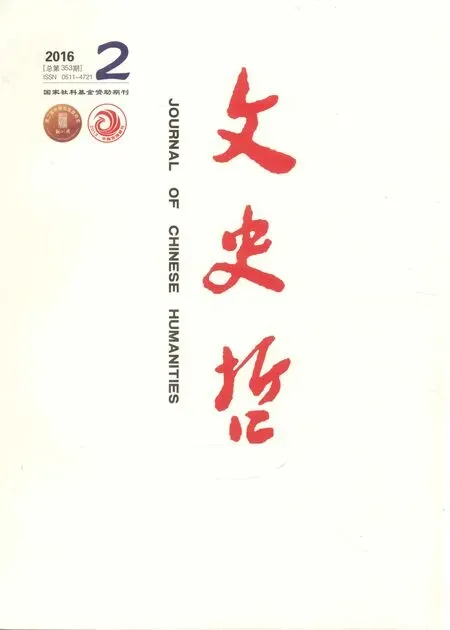橫跨中外 通達(dá)古今
——詮釋學(xué)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反思
洪漢鼎
?
橫跨中外通達(dá)古今
——詮釋學(xué)與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現(xiàn)代轉(zhuǎn)型的反思
洪漢鼎
摘要:“西方與東方”、“古代與現(xiàn)代”的關(guān)系,是中國(guó)對(duì)外文化交流特別是哲學(xué)研究的重要問(wèn)題。一種流行觀點(diǎn)認(rèn)為,借鑒西方哲學(xué)來(lái)發(fā)展中國(guó)哲學(xué),乃是在按照西方模式建構(gòu)中國(guó)哲學(xué),而對(duì)古代經(jīng)典進(jìn)行詮釋,則是強(qiáng)迫古代經(jīng)典現(xiàn)代化。這是一種錯(cuò)誤的看法。實(shí)際上,不論中外關(guān)系,還是古今關(guān)系,凡“學(xué)”都是學(xué)“共相”,學(xué)優(yōu)于自己的東西,從觀念的進(jìn)展來(lái)看,都是一種融合過(guò)程。當(dāng)代詮釋學(xué)的宇宙恰好包含這兩個(gè)主題,它既橫跨中西又通達(dá)古今。從詮釋學(xué)角度探討中國(guó)哲學(xué)的“中西”與“古今”之爭(zhēng),可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人類心靈的共振既能夠逾越中西又能夠通達(dá)古今。
關(guān)鍵詞:中國(guó)哲學(xué);詮釋學(xué);中西關(guān)系;古今關(guān)系
BridgingChina and the West, Connecting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Hermeneutics and Reflection on Modern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Hong Handing
East-West relationship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re very important issues in China’s cultural exchanges with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in the field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 popular view is that, to develop Chinese philosophy with reference of the West, means to construct our philosoph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estern model, and to interpret the classics means to compel the ancient texts to be modernized. This opinion is untenable. In fact, whether with regard to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or as t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any “l(fā)earning” means to learn “the universal”, to learn anything superior to oursel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rogress of idea, this is a kind of fusion process. In a sense, these two subjects are just contained in the universe of contemporary hermeneutics, which stretches across China and the West, and binds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In sum, discussing these two topics in Chinese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rmeneutics,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resonance of human being’s minds could both bridge China and the West, and connect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自清末民初以來(lái),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需要實(shí)現(xiàn)現(xiàn)代轉(zhuǎn)型,似乎是一個(gè)公認(rèn)的事實(shí)。但20世紀(jì)90年代以來(lái),學(xué)界對(duì)此似乎又提出了異議,所謂中國(guó)哲學(xué)理論的“失語(yǔ)”問(wèn)題開(kāi)始引起反思。異議者認(rèn)為,近代以來(lái)由于借用西方話語(yǔ)來(lái)進(jìn)行所謂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現(xiàn)代化,中國(guó)學(xué)者在國(guó)際對(duì)話中發(fā)不出自己的聲音,中國(guó)哲學(xué)在語(yǔ)言表達(dá)和文本解讀上長(zhǎng)期處于“失語(yǔ)”狀態(tài)。通過(guò)賽義德所謂“東方學(xué)”,這種異議被強(qiáng)化到了更尖銳的程度,上述“失語(yǔ)”被認(rèn)為是中國(guó)學(xué)人的一種“自我閹割”。西方對(duì)東方思想的支配和控制、西方對(duì)東方的文化霸權(quán),很大程度上竟是通過(guò)東方學(xué)者對(duì)自己文化的“再現(xiàn)”來(lái)實(shí)現(xiàn)的。東方學(xué)者通過(guò)西方敘述框架和概念系統(tǒng)再現(xiàn)自己的歷史,對(duì)自己的傳統(tǒng)進(jìn)行所謂“現(xiàn)代闡釋”和“現(xiàn)代轉(zhuǎn)換”,被認(rèn)為本質(zhì)上乃是對(duì)自己傳統(tǒng)文化的“閹割”。
這里涉及到中國(guó)的文論和哲學(xué)的現(xiàn)代轉(zhuǎn)型,也就是所謂現(xiàn)代化或世界化的問(wèn)題。按照某些人的看法,這種“現(xiàn)代闡釋”并非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現(xiàn)代化和世界化的必經(jīng)之路。從20世紀(jì)初胡適“整理國(guó)故”開(kāi)始的所謂現(xiàn)代轉(zhuǎn)型過(guò)程,被認(rèn)為只能導(dǎo)致失語(yǔ)或自我閹割,因?yàn)檫@里的現(xiàn)代化、世界化其實(shí)就是西方化,而“西方即現(xiàn)代”、“西方即世界”其實(shí)是附屬于西方文化霸權(quán)的一種殖民話語(yǔ)。于是,要實(shí)現(xiàn)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的現(xiàn)代化和世界化,似乎必須另走一條相反的道路,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簡(jiǎn)言之,必須擺脫一切西方概念和敘述系統(tǒng),回歸我們民族原本的語(yǔ)言和概念,回歸原點(diǎn),走過(guò)去兩千年的老路。

這里的問(wèn)題實(shí)際上就是“西方與東方”、“古代與現(xiàn)代”的關(guān)系問(wèn)題。當(dāng)代詮釋學(xué)的宇宙恰好包含這兩個(gè)主題,它既橫跨中西又通達(dá)古今。我們完全可以從詮釋學(xué)的角度,探討中國(guó)哲學(xué)的中西與古今之爭(zhēng)。
一、中西或中外關(guān)系
首先,從近代中國(guó)學(xué)術(shù)史角度看,中西方是否真的可以分開(kāi)?早在民國(guó)時(shí)期,王國(guó)維和陳寅恪就認(rèn)為,這兩者是統(tǒng)一而不可分的。王國(guó)維說(shuō):“余非謂西洋哲學(xué)之必勝于中國(guó),然吾國(guó)古書(shū)大率繁散而無(wú)紀(jì),殘缺而不完,雖有真理,不易尋繹,以視西洋哲學(xué)之系統(tǒng)燦然,步伐嚴(yán)整者,其形式上之孰優(yōu)孰劣,固自不可掩也。”*王國(guó)維:《哲學(xué)辨惑》,《王國(guó)維文集》第3卷,北京:中國(guó)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5頁(yè)。此說(shuō)開(kāi)中國(guó)哲學(xué)研究必須借鑒西方哲學(xué)之“形式系統(tǒng)”的先河。王國(guó)維說(shuō):“欲通中國(guó)哲學(xué),又非通西洋之哲學(xué)不易明也……異日昌大吾國(guó)固有之哲學(xué)者,必在深通西洋哲學(xué)之人,無(wú)疑也。”*王國(guó)維:《哲學(xué)辨惑》,《王國(guó)維文集》第3卷,第5頁(yè)。又說(shuō):“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學(xué),勢(shì)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學(xué)。異日發(fā)明光大我國(guó)之學(xué)術(shù)者,必在兼通世界學(xué)術(shù)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王國(guó)維:《奏定經(jīng)學(xué)科大學(xué)文學(xué)科大學(xué)章程書(shū)后》,《王國(guó)維遺書(shū)》第3冊(cè),上海:上海書(shū)店,1983年,第647頁(yè)。陳寅恪也說(shuō):“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tǒng)、有所創(chuàng)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lái)之學(xué)說(shuō),一方面不忘本來(lái)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tài)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陳寅恪:《馮友蘭中國(guó)哲學(xué)史下冊(cè)審查報(bào)告》,《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4頁(y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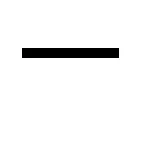
在這里,有必要對(duì)“國(guó)學(xué)”一詞略加評(píng)議。近年來(lái),“國(guó)學(xué)”一詞在中國(guó)漸成顯學(xué),以致有“國(guó)學(xué)叢書(shū)”出版,有些大學(xué)組建了國(guó)學(xué)院,北京大學(xué)還搞了“乾元國(guó)學(xué)”教課班。但是,“國(guó)學(xué)”概念實(shí)有令人困惑之處。“國(guó)學(xué)”一詞始于晚清,近人王淄塵在《國(guó)學(xué)講話》中說(shuō):“庚子義和團(tuán)一役以后,西洋勢(shì)力益膨脹于中國(guó),士人之研究西學(xué)者亦日益多,翻譯西書(shū)者亦日益多,而哲學(xué)、倫理、政治諸說(shuō),皆異于舊有之學(xué)術(shù),于是概稱此種書(shū)籍曰‘新學(xué)’,而稱固有之學(xué)術(shù)曰‘舊學(xué)’矣。另一方面,不屑以舊學(xué)之名稱我固有之學(xué)術(shù),于是有發(fā)行雜志,名之曰《國(guó)粹學(xué)報(bào)》,以與西來(lái)之學(xué)術(shù)相抗。‘國(guó)粹’之名隨之而起。繼則有識(shí)之士,以為中國(guó)固有之學(xué)術(shù),未必盡為精粹也,于是將‘保存國(guó)粹’之稱,改為‘整理國(guó)故’,研究此項(xiàng)學(xué)術(shù)者稱為‘國(guó)故學(xué)’”*王淄塵:《國(guó)學(xué)講話》,轉(zhuǎn)引自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shí)期期刊介紹》第2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39頁(yè)。,而“國(guó)故學(xué)”,以后又漸演化成“國(guó)學(xué)”。顯然,“國(guó)學(xué)”一詞乃是近代中國(guó)民族主義興起之后的產(chǎn)物,它與當(dāng)時(shí)所謂“國(guó)貨”、“國(guó)煙”、“國(guó)醫(yī)”、“國(guó)樂(lè)”一道,目的是為對(duì)抗外國(guó)入侵的“洋貨”、“洋煙”、“洋醫(yī)”、“洋樂(lè)”,以及“洋學(xué)”。就此而言,“國(guó)學(xué)”一詞飽含著對(duì)西學(xué)東漸的焦慮,甚至可說(shuō)是對(duì)西學(xué)的反動(dòng)。另外,如果從語(yǔ)言學(xué)角度認(rèn)真思考,則“國(guó)學(xué)”一詞頗為可疑。錢穆在其《國(guó)學(xué)概論》中說(shuō):“學(xué)術(shù)本無(wú)國(guó)界。‘國(guó)學(xué)’一名,前既無(wú)承,將來(lái)亦恐不立。特為一時(shí)代的名詞。其范圍所及,何者就列為國(guó)學(xué),何者則否,實(shí)難判別。”*錢穆:《國(guó)學(xué)概論》,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1997年,“弁言”,第1頁(yè)。而換個(gè)角度看,“國(guó)學(xué)”一詞可用于任何國(guó)家,德國(guó)學(xué)者可以用“國(guó)學(xué)”稱呼他們的德國(guó)學(xué)術(shù),美國(guó)學(xué)者也可以用之稱呼自己的美國(guó)學(xué)術(shù)。就此而言,“國(guó)學(xué)”是一個(gè)普遍通用的概念,正如“國(guó)家”一樣。按照國(guó)人使用該詞的用意,“國(guó)學(xué)”應(yīng)替換為“中國(guó)學(xué)”或“漢學(xué)”,正如德國(guó)所謂Germanistik(日爾曼學(xué))。不過(guò),這些學(xué)問(wèn)主要是語(yǔ)言文化方面的,而非一般學(xué)術(shù)理論或哲學(xué)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19世紀(jì)末晚清帝國(guó)的守舊派官僚張之洞看來(lái),學(xué)習(xí)西方也不是一種錯(cuò)誤。他主張中學(xué)為體,西學(xué)為用,兩者不可偏廢。在《勸學(xué)篇》中,張之洞說(shuō):“圖救時(shí)者言新學(xué),慮害道者守舊學(xué),莫衷于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歧多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wú)應(yīng)敵制變之術(shù),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張之洞:《勸學(xué)篇》,苑書(shū)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c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706頁(yè)。所以他主張:“新舊兼學(xué)。四書(shū)五經(jīng),中國(guó)史事政書(shū)地圖為舊學(xué),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xué)。舊學(xué)為體,新學(xué)為用,不可偏廢。”*張之洞:《勸學(xué)篇》,苑書(shū)義、孫華峰、李秉新主編:《張之洞全集》第12冊(cè),第9740頁(yè)。
當(dāng)然,我們并不否認(rèn)各個(gè)民族的文化有其自身特征。文化既有時(shí)代性,也有民族性。文化的時(shí)代性指該文化在社會(huì)發(fā)展某個(gè)特定歷史階段上的時(shí)代特征,它反映的是世界各民族在相同的時(shí)代或相同的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上的落后與先進(jìn)的差別。文化的民族性則指各個(gè)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特征,特別是各自具有的不同傳統(tǒng)。就民族性而言,文化確實(shí)沒(méi)有高下優(yōu)劣之分,都有其存在的價(jià)值和意義,但就文化的時(shí)代性來(lái)說(shuō),各個(gè)民族文化則存在發(fā)展程度上的先進(jìn)與落后的差別。如果用文化的這兩種屬性來(lái)分析近代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那么從文化的時(shí)代性來(lái)看,五四時(shí)期討論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在性質(zhì)上屬于古代特別是封建時(shí)代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則屬于近代資本主義文化,它們是一古一今;但就文化的民族性來(lái)考察,中西文化體現(xiàn)的是兩種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彼此各有特色。在20世紀(jì)末21世紀(jì)初的今天,這種觀點(diǎn)特別具有“持平”的重要意義。今天的中國(guó)不再處于救亡時(shí)期,而是國(guó)家強(qiáng)盛、經(jīng)濟(jì)繁榮,擁有當(dāng)代先進(jìn)的科技。現(xiàn)在的中西方關(guān)系不再是落后與先進(jìn)的關(guān)系,現(xiàn)在的中西方交流也不再是單向交流,而是一種雙向的交流。我們學(xué)習(xí)西方更重要的目的是創(chuàng)立我們自己的學(xué)說(shuō)理論,不再追求西方化、西學(xué)化,而是追求國(guó)際化、世界化、先進(jìn)化、普遍化。就此而言,中國(guó)的哲學(xué),就是“有中國(guó)特色的世界哲學(xué)”,正如“有中國(guó)特色的社會(huì)主義”、“有中國(guó)特色的世界城市”一樣。這里,中心詞是共相,而非殊相。共相應(yīng)當(dāng)以普遍而先進(jìn)的內(nèi)涵為主,而非一種特殊的個(gè)別之物。
二、古今關(guān)系

這一觀點(diǎn)其實(shí)也為中國(guó)哲學(xué)家所認(rèn)識(shí)到。程頤在其文論輯錄中說(shuō):“圣人之語(yǔ),因人而變化;語(yǔ)雖有淺近處,即卻無(wú)包含不盡處。如樊遲于圣門,最是學(xué)之淺者,及其問(wèn)仁,曰‘愛(ài)人’,問(wèn)知,曰‘知人’,且看此語(yǔ)有甚包含不盡處?他人之語(yǔ),語(yǔ)近則遺遠(yuǎn),語(yǔ)遠(yuǎn)則不知近,惟圣人之言,則遠(yuǎn)近皆盡。”*程顥、程頤著,王孝魚(yú)點(diǎn)校:《二程集》上冊(cè),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1年,第176頁(yè)。儒學(xué)正典對(duì)于儒家哲學(xué)家來(lái)說(shuō)不是超人的啟示,而是每個(gè)人原則上都能明見(jiàn)到的圣人見(jiàn)解。他們的解釋并非先在其原初意義上闡釋正典,而后再根據(jù)自己的明見(jiàn)對(duì)此意義進(jìn)行肯定和吸收。相反,如果根據(jù)本己的經(jīng)驗(yàn)和思考獲得了某種明見(jiàn)和真理,那么他們會(huì)相信,出自偉大圣人和賢人的儒家正典一定會(huì)證實(shí)這種明見(jiàn)和真理。例如王陽(yáng)明在1508年龍場(chǎng)悟道后,就試圖通過(guò)保留在記憶中的“五經(jīng)”論斷來(lái)證明自己這種領(lǐng)悟,并發(fā)現(xiàn)這些論斷與自己的領(lǐng)悟是一致的。王陽(yáng)明非常強(qiáng)調(diào)“自得”、“得之于心”。在1520年的一封信中,他說(shuō):“夫?qū)W貴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王守仁:《答羅整庵少宰書(shū)》,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yáng)明全集》上冊(c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6頁(yè)。陽(yáng)明弟子王艮則說(shuō):“‘經(jīng)’所以載道,‘傳’所以釋經(jīng)。‘經(jīng)’既明,‘傳’不復(fù)用矣,道既明,‘經(jīng)’何足用哉?‘經(jīng)’、‘傳’之間,印證吾心而已矣。”*王艮:《語(yǔ)錄上》,《王心齋全集》第2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頁(yè)。學(xué)習(xí)經(jīng)典,無(wú)非是自己知識(shí)的印證。此種看法,張載也有,他強(qiáng)調(diào)“心解”,即:“求義自明,不必字字相校。譬之目明者,萬(wàn)物紛錯(cuò)于前,不足為害,若目昏者,雖枯木朽株皆足為梗”,“且滋養(yǎng)其明,明則求經(jīng)義將自見(jiàn)矣”*張載著,章錫琛點(diǎn)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shū)局,1978年,第276、275頁(yè)。。朱熹則謂之“心印”,將心比心,以自己的心體驗(yàn)圣賢的心。正是經(jīng)典型或古典型的這種無(wú)時(shí)間性的當(dāng)下存在,體現(xiàn)了歷史存在的一種普遍的本質(zhì),即通過(guò)變化而形成自身,既是他者又是自身。對(duì)于世界各民族來(lái)說(shuō),這種經(jīng)典型或古典型的歷史,各自形成了互有區(qū)別的漫長(zhǎng)的精神傳統(tǒng)。此為一個(gè)民族的文化特征或文化傳統(tǒng)。
伽達(dá)默爾說(shuō):“這種關(guān)于古典型概念的解釋,并不要求任何獨(dú)立的意義,而是想喚起一個(gè)普遍的問(wèn)題,這個(gè)問(wèn)題就是:過(guò)去和現(xiàn)在的這種歷史性的中介,正如我們?cè)诠诺湫透拍罾锼吹降模罱K是否作為有效的基石成為一切歷史行為的基礎(chǔ)?當(dāng)浪漫主義詮釋學(xué)把人性的同質(zhì)性設(shè)為其理解理論的非歷史性基石,并因此把同質(zhì)性理解者從一切歷史條件性中解放出來(lái)時(shí),歷史意識(shí)的自我批判最后卻發(fā)展成不僅在事件過(guò)程中而且也同樣在理解中去承認(rèn)歷史性運(yùn)動(dòng)。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認(rèn)為是一種主體性的行為,而要被認(rèn)為是一種置自身于傳承物事件中的行動(dòng),在這行動(dòng)中,過(guò)去和現(xiàn)在不斷地進(jìn)行中介。”*[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295頁(yè)。譯文略有改動(dòng)。
施萊爾馬赫曾經(jīng)把同質(zhì)性(Kongenialit?t)和同時(shí)性(Simultaneit?t)作為古典作品理解和解釋的基礎(chǔ),認(rèn)為古典作品的意義可以無(wú)須現(xiàn)代的參與而客觀地發(fā)掘,只要理解者與古典作品的作者達(dá)到同質(zhì)性,并返回到該作品原來(lái)的時(shí)代,則理解和解釋就會(huì)成功。歷史主義者也曾經(jīng)主張,我們必須舍棄自己現(xiàn)時(shí)的當(dāng)代境域而置身于過(guò)去傳承物的時(shí)代,只有這樣,我們對(duì)傳承物的理解才會(huì)正確。對(duì)于這些觀點(diǎn),伽達(dá)默爾反問(wèn)道:“說(shuō)我們應(yīng)當(dāng)學(xué)會(huì)把自己置入陌生的視域中,這是對(duì)歷史理解藝術(shù)的正確而充分的描述嗎?有這種意義上的封閉的視域嗎?我們想起了尼采對(duì)歷史主義的譴責(zé),它毀壞了由神話所包圍的視域,而文化只有在這種視域中才能得以生存。一個(gè)人自己現(xiàn)在的視域總是這樣一種封閉的視域嗎?具有如此封閉視域的歷史處境可能被我們?cè)O(shè)想嗎?”*[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309頁(yè)。
在伽達(dá)默爾看來(lái),理解永遠(yuǎn)是陌生性與熟悉性的綜合,過(guò)去與現(xiàn)在的綜合,他者與自我的綜合。文本的意義既不可局限于原作者的意圖或文本的原意,同時(shí),文本也并非完全開(kāi)放可以任由理解者或解釋者按其所需地任意詮釋。也就是說(shuō),理解者或解釋者并非僅從自身的視域出發(fā)去理解文本的意義而置文本自己的視域于不顧,當(dāng)然,理解者或解釋者也不可能為了復(fù)制或再現(xiàn)文本的原意而舍棄自己的前見(jiàn)和視域。這種既包含理解者或解釋者的前見(jiàn)和視域又兼顧文本自身視域的理解方式,伽達(dá)默爾稱之為“視域融合”:“其實(shí),只要我們不斷地檢驗(yàn)我們的所有前見(jiàn),那么,現(xiàn)在視域就是在不斷形成的過(guò)程中被把握的。這種檢驗(yàn)的一個(gè)重要部分就是與過(guò)去的照面(Begegnung),以及對(duì)我們由之而來(lái)的那種傳統(tǒng)的理解。所以,如果沒(méi)有過(guò)去,現(xiàn)在視域就根本不能形成。正如沒(méi)有一種我們誤認(rèn)為有的歷史視域一樣,也根本沒(méi)有一種自為(für sich)的現(xiàn)在視域。理解其實(shí)總是這樣一些被誤認(rèn)為是獨(dú)自存在的視域的融合過(guò)程。”*[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311頁(y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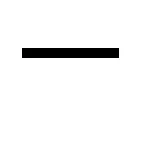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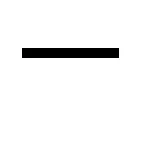

按照伽達(dá)默爾的看法,文字傳承物的歷史生命力就在于“它一直依賴于新的占有(Aneignung)和解釋(Auslegung)”*[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401頁(yè)。。所謂的解釋就是:“讓自己的前概念發(fā)生作用,從而使文本的意思真正為我們表述出來(lái)。”*[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401頁(yè)。一切解釋都必須受制于它所從屬的詮釋學(xué)語(yǔ)境。
傳統(tǒng)是活的,歷史要在不斷的重構(gòu)中生發(fā)出新意。凡是不能與時(shí)代、社會(huì)的當(dāng)下需要建立起活生生聯(lián)系的傳統(tǒng)話語(yǔ),就不可能獲得真實(shí)的生命力。如果有人想用“以中解中”、“漢話漢說(shuō)”這種提法表達(dá)“中國(guó)哲學(xué)的重建”,那么,如果說(shuō)后一個(gè)“中”和前一個(gè)“漢”理解為“傳統(tǒng)的中”和“傳統(tǒng)的漢”,則前一個(gè)“中”和后一個(gè)“漢”就必須理解為“今中”和“今漢”——民族生命/意志在當(dāng)今時(shí)代的現(xiàn)實(shí)需要。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滿足民族生命的舒展,打通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shí)、歷史與未來(lái)。這樣,“中國(guó)哲學(xué)的重建”就與當(dāng)前生活世界聯(lián)系在了一起。
三、伽達(dá)默爾與施特勞斯關(guān)于“古今之爭(zhēng)”的爭(zhēng)論

施特勞斯與伽達(dá)默爾的爭(zhēng)論是這樣發(fā)生的:1960年伽達(dá)默爾的《真理與方法》出版,伽達(dá)默爾將該書(shū)寄贈(zèng)施特勞斯。施特勞斯在看了《真理與方法》之后,于1961年2月26日給伽達(dá)默爾寫了回信,在信中施特勞斯稱贊伽達(dá)默爾這本書(shū)是“海德格爾學(xué)派成員寫出的最重要著作,它是一部長(zhǎng)期工夫之作(a work de longue haleine),它再次展現(xiàn)了期待的智慧(the wisdom of waiting)”*[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邁爾編,朱雁冰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12年,第403頁(yè)。。不過(guò)接下來(lái),施特勞斯就對(duì)伽達(dá)默爾進(jìn)行了批評(píng),他首先指出伽達(dá)默爾的學(xué)說(shuō)乃是“在很大程度上把海德格爾的提問(wèn)、分析與暗示轉(zhuǎn)化成一種更加學(xué)術(shù)化的形式”*[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04頁(yè)。,而轉(zhuǎn)化的基本原則乃是所謂“方法的”(methodical)與“實(shí)質(zhì)的”(substantive)的區(qū)分,而這種區(qū)分在施特勞斯看來(lái),乃是與海德格爾所謂的“生存論的”(existential)與“生存狀態(tài)的”(existentiell)區(qū)分相關(guān)的。因此,施特勞斯認(rèn)為,伽達(dá)默爾的詮釋學(xué)徹底化與普遍化只不過(guò)是與海德格爾所謂“世界—黑夜”的臨近或西方的沒(méi)落同時(shí)發(fā)生的東西。繼而,施特勞斯就伽達(dá)默爾的詮釋學(xué)經(jīng)驗(yàn)理論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見(jiàn),特別講到它具有一種應(yīng)時(shí)(occasional)的特性,并具體提出以下幾個(gè)難題:⒈解釋者必須反思他的詮釋學(xué)處境,但詮釋的文本也必須有其自身的真理,即“我必須把它當(dāng)作正確的而接受它,或把它當(dāng)作不正確的而拒絕它”*[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06頁(yè)。。我們不能用視域融合來(lái)忽視其真理,“假如一種對(duì)柏拉圖學(xué)說(shuō)的修正證明是優(yōu)于他自己的敘述,卻很難講柏拉圖的視域被擴(kuò)大了”*[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06頁(yè)。。⒉人的有限性難道就必然導(dǎo)致不可能有充分的完備的正確的理解嗎,所有解釋者難道不都希望達(dá)到同一高點(diǎn)嗎?⒊解釋者必須理解作者自身設(shè)定的東西,因此解釋者對(duì)作者的理解并不比作者對(duì)自己的理解更好。施特勞斯舉出萊因哈特的“古典的瓦普幾斯夜會(huì)”為例,說(shuō)萊因哈特的巨大價(jià)值就在于能夠理解歌德自己明確思想過(guò)但沒(méi)有以讀者能直接理解的方式所表述的觀點(diǎn),萊因哈特作為中介因而“僅僅是代文本作傳達(dá)并因此而最為睿智、值得稱道”*[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07頁(yè)。。⒋針對(duì)作者與解釋者的區(qū)別有如范例與追隨范例者的區(qū)別,施特勞斯提出有些文本不是范例,如《尼各馬可倫理學(xué)》和《利維坦》。⒌關(guān)于解釋者的創(chuàng)造性,如果歷史學(xué)家從經(jīng)濟(jì)史語(yǔ)境去研究修昔底德,這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嗎?
除上述五個(gè)問(wèn)題外,施特勞斯還提出下述疑問(wèn):效果歷史概念有問(wèn)題,它把對(duì)解釋者并非必然成為論題的東西看成了對(duì)其必然成為論題的東西。另外,施特勞斯還認(rèn)為伽達(dá)默爾的藝術(shù)概念也成問(wèn)題。知識(shí),特別是哲學(xué)的知識(shí),不是藝術(shù),哲學(xué)與詩(shī)有本質(zhì)性的張力,阿里斯托芬的《云》早已闡明了詩(shī)歌與哲學(xué)的對(duì)立。在這方面,對(duì)“阿里斯托芬喜劇最深刻的現(xiàn)代解釋(黑格爾的)遠(yuǎn)不及柏拉圖在《會(huì)飲篇》中對(duì)阿里斯托芬所作的阿里斯托芬的呈現(xiàn)”*[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09頁(yè)。。關(guān)于伽達(dá)默爾的相對(duì)主義,施特勞斯也提出意見(jiàn):既然我們的認(rèn)識(shí)是相對(duì)的,那么我們?cè)趺磿?huì)有絕對(duì)與無(wú)條件的認(rèn)識(shí)呢,特別是當(dāng)伽達(dá)默爾談到“完滿經(jīng)驗(yàn)”的時(shí)候。
針對(duì)施特勞斯的批評(píng),伽達(dá)默爾在1961年4月5日給施特勞斯回了一封信,對(duì)施特勞斯提出的幾個(gè)問(wèn)題作了回答。首先,伽達(dá)默爾回答了他是否只是無(wú)改變地發(fā)展了海德格爾的問(wèn)題:“我可以訴諸海德格爾《存在與時(shí)間》的先驗(yàn)意義,但是通過(guò)我試圖把理解設(shè)想為一種生發(fā)事件(Geschehen),我則轉(zhuǎn)向了一個(gè)完全不同的方向。”*[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12頁(yè)。并且,他還說(shuō):“我的出發(fā)點(diǎn)并非完全的存在遺忘,并非‘存在黑夜’,恰恰相反,而是——我如此說(shuō)是反對(duì)海德格爾和布伯——這樣一種斷言的非現(xiàn)實(shí)性。”*[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12頁(yè)。這里,我們可以對(duì)柏拉圖的理解為例。海德格爾在柏拉圖那里看到了存在遺忘的黑暗時(shí)代的開(kāi)端,而伽達(dá)默爾則在柏拉圖對(duì)話里發(fā)現(xiàn)了理解事情本身的本真方式。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文本最好被解釋為對(duì)問(wèn)題的回答,以致解釋的關(guān)鍵就是理解文本所預(yù)設(shè)的問(wèn)題。對(duì)于施特勞斯說(shuō)他的詮釋學(xué)經(jīng)驗(yàn)理論具有“應(yīng)時(shí)”的特征,伽達(dá)默爾回答說(shuō),這一點(diǎn)絕不構(gòu)成對(duì)恰恰宣稱這一點(diǎn)的理論的反駁,而是這一理論的一個(gè)先聲。伽達(dá)默爾對(duì)于前五個(gè)問(wèn)題也一一作了回應(yīng)。⒈關(guān)于視域融合,伽達(dá)默爾說(shuō),它是歷史意識(shí)興起之后的一種特殊的應(yīng)用形式,因此它只是歷史意識(shí)的后果,它所證明的是,它只有得到應(yīng)用才會(huì)有認(rèn)識(shí)。⒉對(duì)于人因有限性不能達(dá)到正確理解這一點(diǎn),伽達(dá)默爾說(shuō),施特勞斯太過(guò)片面地理解他的論題。⒊關(guān)于萊因哈特的歌德解釋,伽達(dá)默爾說(shuō),萊因哈特的解釋除了代文本作傳達(dá)外,其實(shí)還有另一方面,也許在五十年后人們會(huì)比今天更清楚地看到這另一方面是什么。“為什么他闡釋這一點(diǎn)而非另外一點(diǎn)、這樣闡釋而非那樣闡釋,他忽視了什么、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了什么。這樣一個(gè)使您和我都懷著感激地獲益的精彩的、值得稱道的闡釋,恰好說(shuō)出了我們的意思。”*[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13頁(yè)。譯文有改動(dòng)。⒋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利維坦》可能也包含一種值得追隨的真理,而非僅是錯(cuò)誤教導(dǎo)。⒌伽達(dá)默爾認(rèn)為,經(jīng)濟(jì)學(xué)史家在做這種洞察時(shí)也不得不對(duì)他自身進(jìn)行反思,在這里正有其理解的創(chuàng)造性。

施特勞斯在收到伽達(dá)默爾這封來(lái)信后,立即在同年5月14日寫了回信。首先,他要求伽達(dá)默爾反思他的新詮釋學(xué)的處境,而這種反思將必然揭示一種徹底的危機(jī),“一種史無(wú)前例的危機(jī)”*[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18頁(yè)。,而這正是海德格爾“世界黑夜”的臨近所意指的東西。其次,施特勞斯再次強(qiáng)調(diào),一種地道的解釋所關(guān)心的就是如某人所想地理解某人的思想,因此“如果一種詮釋學(xué)理論不比您所做的更加強(qiáng)調(diào)解釋本質(zhì)上代文本傳達(dá)的特性,我依然是不能接受它”*[德]施特勞斯:《回歸古典政治哲學(xué)》,第418頁(yè)。。最后,施特勞斯明確地把他與伽達(dá)默爾之間的根本區(qū)別表述為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s(古代人與現(xiàn)代人之爭(zhēng)),在這場(chǎng)爭(zhēng)論中,他們各自站在不同的一邊,并說(shuō)他們關(guān)于詮釋學(xué)的分歧其實(shí)只是這根本區(qū)別的一個(gè)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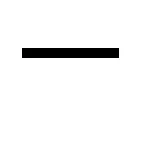
伽達(dá)默爾說(shuō),施特勞斯乃是被他“對(duì)現(xiàn)代災(zāi)難的洞察”所推動(dòng),諸如正確與不正確的區(qū)別這樣一種基本的人的要求,自然要假定人必須能夠超越他的歷史條件性,但是任何歷史思想本身也有其產(chǎn)生的歷史條件。伽達(dá)默爾說(shuō):“單純地論證說(shuō)古典思想家乃是另外地、非歷史地思維,這并不能說(shuō)明今天我們就可能非歷史地思維。”*[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Ⅱ:真理與方法》,第416頁(yè)。這里的意思很清楚,比如,施特勞斯所強(qiáng)調(diào)的柏拉圖的國(guó)家觀念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經(jīng)驗(yàn)與近代的政治觀念有很大的不同,但要真正理解柏拉圖的國(guó)家觀念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經(jīng)驗(yàn),難道真能離開(kāi)近代的政治觀念嗎!單純地論證說(shuō)古典思想不同于現(xiàn)代的思想,這不能說(shuō)明我們確實(shí)可以拋棄現(xiàn)代視域而非歷史地思維。
當(dāng)然,伽達(dá)默爾也反對(duì)簡(jiǎn)單地將現(xiàn)代應(yīng)用于過(guò)去。他說(shuō):“所謂要借助現(xiàn)代才能把所有過(guò)去都完全揭示出來(lái),這難道不正是一種現(xiàn)代的烏托邦理想?我認(rèn)為把現(xiàn)代的優(yōu)勢(shì)觀點(diǎn)應(yīng)用于一切過(guò)去身上并不是歷史思維的本質(zhì),相反倒標(biāo)志出一種幼稚歷史主義的頑固的實(shí)證性。”*[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Ⅱ:真理與方法》,第416頁(yè)。但是,歷史的過(guò)去并不是什么固定不變的東西,它的意義不斷地隨著時(shí)代的改變而變化。伽達(dá)默爾說(shuō):“歷史思維的尊嚴(yán)和真理價(jià)值就在于承認(rèn)根本不存在什么‘現(xiàn)代’,只存在不斷更換的未來(lái)和過(guò)去的視域。說(shuō)某種表現(xiàn)傳統(tǒng)思想的觀點(diǎn)是正確的,這絕不是固定不變的(也絕不可能是固定不變的)。‘歷史的’理解沒(méi)有任何特權(quán),無(wú)論對(duì)今天或明天都沒(méi)有特權(quán)。它本身就被變換著的視域所包圍并與它一起運(yùn)動(dòng)。”*[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Ⅱ:真理與方法》,第417頁(yè)。
其次,伽達(dá)默爾指出,盡管施特勞斯正確地批判了后人能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的觀點(diǎn),然而,當(dāng)他說(shuō)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必須像作者自己的理解那樣理解作者,他就低估了一切理解的困難。他似乎認(rèn)為,我們有可能理解并非我們所理解的而是他人所理解的東西,并且僅僅像這位他人所理解的那樣進(jìn)行理解。施特勞斯曾以古典政治哲學(xué)為例,說(shuō)它的基本概念是“友誼”,而不是近代起源于笛卡兒的“我你我們”關(guān)系,如果我們用現(xiàn)代的概念去構(gòu)造古典政治哲學(xué),那就是錯(cuò)誤。伽達(dá)默爾說(shuō):雖然在此例中我完全同意施特勞斯,“但我還要問(wèn),是否可能通過(guò)由歷史科學(xué)訓(xùn)練過(guò)的眼光‘閱讀’古典思想家,同樣地重構(gòu)出他們的意見(jiàn),然后可以在可信任的意義上認(rèn)為這些意見(jiàn)是正確的,從而使我們不費(fèi)力氣地獲得這樣的見(jiàn)解?——抑或我們?cè)谄渲邪l(fā)現(xiàn)了真理,因?yàn)楫?dāng)我們?cè)噲D理解它們時(shí)我們總是已經(jīng)進(jìn)行了思考?但這也就是說(shuō),它們所陳述的東西對(duì)我們之所以顯示為真,乃是因?yàn)榻柚谡诹餍械南鄳?yīng)的現(xiàn)代理論?我們無(wú)須把它理解為更正確的東西就理解它嗎?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還要進(jìn)一步追問(wèn):如果我們發(fā)現(xiàn)亞里士多德所講的要比現(xiàn)代理論(當(dāng)然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現(xiàn)代理論)更為正確,那我們就說(shuō)亞里士多德不可能像我們理解他的方式那樣理解他自己,這種說(shuō)法是否有意義?”*[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Ⅱ:真理與方法》,第418頁(yè)。


四、語(yǔ)言中介

這里涉及到中國(guó)學(xué)界目前廣泛討論的比較哲學(xué)或比較研究話題。說(shuō)實(shí)話,筆者不大贊成這種意義上的“比較哲學(xué)”,即借用抽象的方法,建構(gòu)不同質(zhì)的哲學(xué)的最小公倍數(shù)來(lái)研究它們的同與異。打個(gè)比方,1、3、5三個(gè)質(zhì)數(shù)本來(lái)各具自己的特殊性,但通過(guò)最小公倍數(shù)15來(lái)進(jìn)行比較,就會(huì)出現(xiàn)抽象化的結(jié)果。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所有試圖比較或概括中西哲學(xué)的說(shuō)法,都不免有“以偏概全”的危險(xiǎn)。真正的比較研究乃是對(duì)跨文化思想傳統(tǒng)的哲學(xué)研究,即首先通過(guò)比較而認(rèn)識(shí)一種普遍性的共識(shí),再通過(guò)這種共識(shí)來(lái)詮釋、理解和發(fā)展一種哲學(xué)。也就是說(shuō),通過(guò)對(duì)比而加深對(duì)自身和他者的理解,而且是同情的理解,并進(jìn)行創(chuàng)造性的整合而發(fā)展自身的傳統(tǒng)。接納新學(xué)說(shuō)、新思想、新方法,首先必須在自身的思想文化系統(tǒng)中建立起共識(shí)的基礎(chǔ)。兩種根本不同的東西,其中一個(gè)絕不會(huì)影響另一個(gè)。要使兩種不同的哲學(xué)傳統(tǒng)相互影響,首先必須達(dá)成共識(shí)。如果中國(guó)哲學(xué)是以西方哲學(xué)為模式構(gòu)建起來(lái)的,那么它就不應(yīng)當(dāng)被稱為中國(guó)的哲學(xué),而應(yīng)稱為中國(guó)的西方哲學(xué)。所以,當(dāng)我們說(shuō)中國(guó)的哲學(xué)時(shí),這種中國(guó)哲學(xué)與其說(shuō)是按照西方模式構(gòu)建起來(lái)的,毋寧說(shuō)是現(xiàn)代世界哲學(xué)審視下的中國(guó)哲學(xué)。因此,這里沒(méi)有什么西方模式,有的只是現(xiàn)代共識(shí)的先進(jìn)模式。任何一個(gè)民族的文化要發(fā)展,只要它不是被封閉的,就總是要朝著最先進(jìn)的方向發(fā)展。
不論中外還是古今的學(xué)習(xí)關(guān)系,實(shí)際上都是一個(gè)語(yǔ)言中介問(wèn)題。學(xué)習(xí)外國(guó)語(yǔ)言和閱讀古代語(yǔ)言,都離不開(kāi)自身的現(xiàn)有語(yǔ)言。語(yǔ)言是思想的表現(xiàn),因此,這種學(xué)習(xí)關(guān)系既是外國(guó)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又是自身思想文化的發(fā)展。實(shí)際上,語(yǔ)言只有在它休閑即非應(yīng)用狀態(tài),才可以被當(dāng)作一個(gè)對(duì)象;而在使用時(shí),即當(dāng)語(yǔ)言在履行工作時(shí),對(duì)于當(dāng)事人來(lái)說(shuō),語(yǔ)言的主體性就取代了它的對(duì)象性。它們被充滿了它們所意指的東西,并且沒(méi)有形式內(nèi)容的分離。在使用時(shí),語(yǔ)言總是在說(shuō)什么東西。兒童并不是先學(xué)會(huì)他們發(fā)聲的普遍形式,然后再學(xué)會(huì)如何把這些普遍形式應(yīng)用于個(gè)別事件;他們其實(shí)是橫向平行地學(xué)會(huì)的,即從使用到使用。他們從講話中學(xué)會(huì)講話,從應(yīng)用中學(xué)會(huì)應(yīng)用。伽達(dá)默爾論證說(shuō),語(yǔ)言是最具自身性的(most itself),假如語(yǔ)言最少被對(duì)象化,假如形式和內(nèi)容、話語(yǔ)和世界無(wú)法分割的話。母語(yǔ)是橫向習(xí)得的這一觀察,對(duì)學(xué)習(xí)外國(guó)語(yǔ)言也有意義。盡管洪堡曾經(jīng)說(shuō)過(guò),學(xué)會(huì)一門外語(yǔ)肯定是在迄今為止的世界觀中獲得一個(gè)新的角度,但他繼續(xù)說(shuō)道:“只是因?yàn)槲覀兛偸腔蚨嗷蛏俚匕盐覀冏约旱氖澜缬^,或者說(shuō)我們自己的語(yǔ)言觀帶入外語(yǔ)之中,所以這種結(jié)果很少被人純粹而完全地感到。”*[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445頁(yè)。在這里,作為一種限制和缺陷被談及的東西,實(shí)際上表現(xiàn)了詮釋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實(shí)現(xiàn)方式。把一種新的角度引入當(dāng)事人現(xiàn)有世界觀中的,并不是對(duì)某門外語(yǔ)的領(lǐng)會(huì),而是對(duì)這門外語(yǔ)的使用。確實(shí),洪堡關(guān)于把我們的語(yǔ)言觀帶入外語(yǔ)中的觀察是正確的。伽達(dá)默爾稱它為視域融合,詮釋學(xué)經(jīng)驗(yàn)的范式。通過(guò)這種范式,我們不離開(kāi)舊的視域而獲得一個(gè)新視域,這種新視域允許更大的觀看、學(xué)習(xí)和理解的范圍。在學(xué)習(xí)外語(yǔ)時(shí),盡管我們會(huì)很深地置身于陌生的精神方式中,但我們絕不會(huì)因此而忘掉我們自己的世界觀,也即我們的語(yǔ)言觀。學(xué)會(huì)一門外語(yǔ)和理解一門外語(yǔ),只是指能夠使在該語(yǔ)言中所說(shuō)的東西被自己說(shuō)出來(lái),而如果我們沒(méi)有把我們自己的世界觀即語(yǔ)言觀一起帶入的話,我們就不能達(dá)到這種要求。伽達(dá)默爾說(shuō):“盡管我們會(huì)很深地置身入陌生的精神方式,但我們決不會(huì)因此而忘掉我們自己的世界觀,亦即我們自己的語(yǔ)言觀。也許我們所面臨的其他世界并非僅是一個(gè)陌生的世界,而是一個(gè)與我們有關(guān)聯(lián)的其他世界。它不僅具有其自在的真理,而且還有其為我們的真理。”*[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445頁(yè)。從詮釋學(xué)觀點(diǎn)來(lái)看,這就是一種語(yǔ)言融合。為了實(shí)現(xiàn)這種語(yǔ)言融合,既不可以忘記自己原有的語(yǔ)言觀,也不可貶低其他語(yǔ)言而不讓它們發(fā)生作用。任何語(yǔ)言都可以被任何其他語(yǔ)言使用者所學(xué)習(xí)。即使在我們研究另一種語(yǔ)言時(shí),我們也從來(lái)不是一味地貶低這種語(yǔ)言,講話者也絕不會(huì)因?yàn)樗哪刚Z(yǔ)本身能融合其他語(yǔ)言而必然被限制在他的這種母語(yǔ)的界限內(nèi)。因此,我們也無(wú)須使自己擺脫我們的母語(yǔ)或破壞它,而只需利用它的開(kāi)放和發(fā)展的內(nèi)在能力。因著這種能力,語(yǔ)言具有無(wú)限擴(kuò)張的可能性。的確,每一種語(yǔ)言都帶著它自己的世界觀,但這種多樣性的事實(shí)本身卻也意味著,其他語(yǔ)言和其他世界觀為我們自己語(yǔ)言和世界觀的擴(kuò)大提供了多種具體的可能性,因?yàn)槲覀兡軐W(xué)會(huì)在它們之中生活和講話。如果我們確實(shí)學(xué)會(huì)了它們,它們就與我們自己的語(yǔ)言和世界實(shí)現(xiàn)了融合。
伽達(dá)默爾說(shuō):“如果我們形式地對(duì)待語(yǔ)言,我們顯然就不能理解傳承物。如果這種傳承物不是以一種必須用文本的陳述來(lái)傳達(dá)的熟悉性(Bekanntes und Vertrautes)加以表現(xiàn),那么我們同樣不能理解它所說(shuō)的和必然所說(shuō)的內(nèi)容。”*[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446頁(yè)。另外,伽達(dá)默爾還說(shuō),學(xué)會(huì)一門語(yǔ)言就是擴(kuò)展我們能夠?qū)W習(xí)的東西,詮釋學(xué)經(jīng)驗(yàn)就在于:“學(xué)會(huì)一門外語(yǔ)和理解一門外語(yǔ),只是指能夠使在語(yǔ)言中所說(shuō)的東西自己對(duì)我們說(shuō)出來(lái)。這種理解的完成總是指所說(shuō)的東西對(duì)我們有一種要求(Inanspruchnahme),而如果我們沒(méi)有把‘我們自己的世界觀,亦即自己的語(yǔ)言觀’一起帶入的話,則這種要求就不可能達(dá)到。”*[德]伽達(dá)默爾:《詮釋學(xué)Ⅰ:真理與方法》,第446頁(yè)。
總之,人類心靈的共振能夠逾越中外,并通達(dá)古今。
[責(zé)任編輯鄒曉東]
基金項(xiàng)目:本文系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重大項(xiàng)目“伽達(dá)默爾著作集漢譯與研究”(15ZDB026)及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基金重點(diǎn)項(xiàng)目“比較視域下中國(guó)經(jīng)典詮釋傳統(tǒng)現(xiàn)代化路徑研究”(14AZD09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jiǎn)介:洪漢鼎,山東大學(xué)中國(guó)詮釋學(xué)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山東濟(jì)南 250100)、北京市社會(huì)科學(xué)院哲學(xué)研究所研究員(北京 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