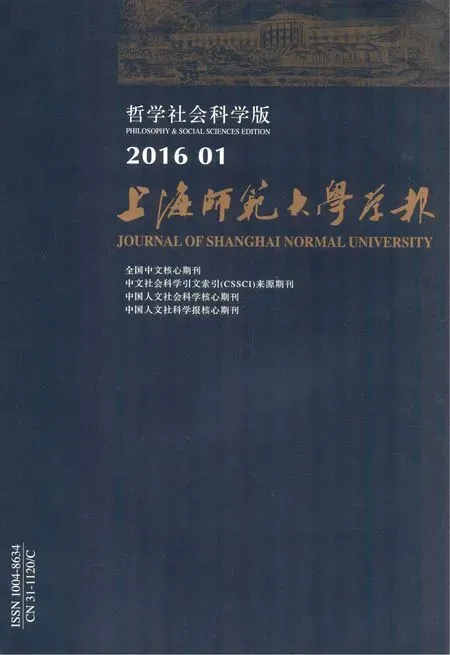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產業研究
張劍光
(上海師范大學 人文與傳播學院,上海 200234)
產業狀況是衡量一個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對六朝隋唐五代時期城市中的產業發展進行探索,是對城市進行研究的一個重要側面,必將更加深入地認識城市經濟的發展程度。因此,本文選取江南城市經濟產業進行研究,應該有助于對江南城市的整體研究。
本文所談及的江南,大致上相當于六朝揚州的東部地區,包括丹陽、宣城、吳、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義興、晉陵等郡,在唐中期以后主要是浙東、浙西、宣歙三道的范圍,相當于今浙江全部和蘇南、皖南地區。
一、愈益興盛的商業活動
商業興盛是江南城市經濟發展的突出表現。盡管六朝以來的江南城市商業常常被限定于一定的區域之內,但商業的繁盛是各個城市的共同特點,而且商業漸漸在向城市的各個角落推進,來到了城門附近,來到了交通便利處的河邊橋頭。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商業從其所有者的性質來說,可以分成官營商業和私營商業兩大部分,但由于江南遠離唐代的政治中心,官營商業主要局限在政府控制的商品種類的經營中,如食鹽、酒類等官榷商品的交易。比如唐代說浙西地區“有鹽井銅山,有豪門大賈,利之所聚”。[1](卷413,常袞《授李棲筠浙西觀察使制》,P4231)元和十二年至長慶元年(817—821),薛戎為越州刺史,“仍以御史中丞觀察團練浙東、西。所部郡皆禁酒,官自為壚。以酒禁坐死者,每歲不知數。而產生祠祀之家,受酒于官,皆醨偽滓壞,不宜復進于杯棬者,公即日奏罷之”。[2](卷53《薛公神道碑文銘》,P572)也就是說,浙東各州官制官銷,城市中出售的酒當然是官營的。浙西各州情況也是如此:“榷酒錢舊皆隨兩稅征眾戶,自貞元已來,有土者競為進奉,故上言百姓困弊,輸納不充,請置官坊酤酒以代之。既得請,則嚴設酒法,閭閻之人舉手觸禁而官收厚利以濟其私,為害日久矣。及李應奏罷,議者謂宰臣能因湖州之請推為天下之法,則其弊革矣。”李應上奏的實質是要將官制官酤改成私制私酤交榷錢,他認為一旦改過來,將大大有利于江南釀酒生產的發展。次年,浙西觀察使竇易直又上奏要求在浙西六州都推行這樣的政策,穆宗同意了,說:“不酤官酒,有益疲人,管內六州皆合一例宜并準湖州敕處分。”[3](卷504《邦計部·榷酤》,P6043)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江南各城市都是官坊酤酒,政府實際控制了酒的銷售。
江南城市中的商業,大部分是民營商業,這是城市商業中的主體部分。民營商業的個體規模有大有小,有的是專職的商業從業者,也有的是官員或城市居民、農民等短期經營。民營商業分布于城市的各個市場,既滿足城市上層人物對奢侈品的需求,也滿足城內普通人對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是構成城市商業繁榮的最主要方面。
民營商業的大多數經營者是城市的普通居民,卷入商業活動的居民相當多。東晉應詹曾上表云:“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仆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4](卷26《食貨志》,P791)說明有很多百姓在從事販賣經商,就連社會底層的僮仆奴隸也不事農桑而從事起輕便能賺錢的商業。商人是否真有十萬,也許應詹有所夸大,但他的意思是經商人數眾多。梁朝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為業”。[5](卷77《恩倖傳》,P1935)周石珍的社會地位不高,但以販賣紡織品為生,是一個處于商品交換過程末端的零售商人。商人經商很容易發財致富,而且還與官方權力相結合,擴大和保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如梁吳郡陸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資以事權貴”。陸驗與大權在握的朱異勾搭上,“苛刻為務,百賈畏之”。[5](卷77《恩倖傳》,P1936)
棄本從事商業的農民也有很多,南朝時這種現象十分常見。沈約說南朝前期“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6](卷56《孔琳之傳》,P1565)顯然是指有不少農民進入城市從事商業活動,因而城市里的商人越來越多。也有不少官員經營商業。南朝貴族官僚經商之風盛行,“在朝勛要,多事產業”。[6](卷77《柳元景傳》,P1990)宋孔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余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6](卷84《孔覬傳》,P2155)有時官員自己不出面,讓他們的仆人經營商業。如宋明帝時,晉安王劉子勛長史鄧琬“使婢仆出市道販賣”。[6](卷84《鄧琬傳》,P2135)
不少城市婦女投入到經商中去。如東晉時的吳中風俗,“衣冠之人,多有數婦,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7](卷31《地理志下》,P887)衣冠士人家里的女性常于市肆拋頭露面,從事經營活動,幫助丈夫一起賺錢。唐代婦女經商的就更多了。李白《金陵酒肆留別》云:“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喚客嘗。金陵子弟來相送,欲行不行各盡觴。”[8](卷15,P928)婦女開設酒店,經營上有著比男性更大的優勢。
江南城市商業,從大的方面來說,主要是販運和店鋪零售兩種形式。
江南城市中的販運貿易,是指商人利用水陸交通路線,將產品從其他地方運輸到江南地區。六朝隋唐五代時期,江南參與販運貿易的商人數量眾多。從商人們販運的商品來看,品種豐富,既有大量城市上層人物需要的奢侈品,又有大量農副產品、地方特產及手工業品。大宗農產品作為販運的主要物品,是城市販運貿易的一個特點。劉宋大明八年,孝武帝曾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6](卷6《孝武帝紀》,P134)到了隋唐五代,販運業更為興盛。如唐代的江寧縣城附近,“暮潮聲落草光沉,賈客來帆宿岸陰”。[9](卷743,沈彬《金陵雜題》,P8456)杭州“南派巨流,走閩禺甌越之賓貨,而鹽魚大賈所來交會”。[1](卷736,沈亞之《杭州場壁記》,P7604)明州象山縣和臺州寧海縣交界處的祚圣廟,“唐貞觀中,有會稽人金林數往臺州買販,每經過廟下,祈禱牲醴如法,獲利數倍”。[10](卷6《祠廟》,P4899)
城市中商業經營的主要方式是店鋪零售。一般商人都是在市肆中擁有肆店或商鋪。如南齊柳世隆“在州立邸治生”。[11](卷24《柳世隆傳》,P452)唐末建康江寧縣廨之后有酤酒王氏,經營“以平直稱”。后來江寧大火,“此店四鄰皆為煨燼,而王氏獨免”。[12](卷6,P101~102)王氏開設的酒店以誠信、價格公道而著稱。唐代杭州人稱“駢檣二十里,開肆三萬室”,[1](卷316,李華《杭州刺史廳壁記》,P3206)雖不見得店肆真有3萬家,但說城內商店眾多還是可信的。江南城市商業在經營方式上有一定的變化發展,[13]市場上的商品列肆交易,分類很細,但同時零售的商業店鋪又往往開設在市場之外的居民生活區。尤其是到了唐代后期,城市中新市場在孕育增加,而居民生活區的店鋪漸漸增多,城市的商業出現繁盛跡象。
從總體上看,江南城市的商業活動越來越活躍。隨著販運商貿的發展,各個城市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都有一定的聯系。江南許多大城市的商業活動已不再局限于本州郡或本縣范圍內簡單地互通有無,而是在整個江南地區已初步形成市場銷售網絡。雖然這個網絡還是簡單粗疏的,但江南每個城市往往成為整個商業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二、新興的生活服務業
隨著城市商品經濟的發展,生活服務業依托城市發展而興起,從傳統的商業中分離出來。服務業是城市商業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其興旺程度標志著中國古代城市經濟的發展水平。服務業在城市經濟中占的比重越大,說明城市經濟的發展水平越高。
在江南的一些大城市中,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個行業的手藝工人來為他們服務,所以城區內生活著大量的手藝工人。如城市建筑需要木工,日常生活家具要有人來制造,大量的木匠于是出現在城市各坊里中。建康城內有木工在做家具,有人送給建康人杜魯賓三根木棒,杜“命工人剖之”。[12](卷5,P91,P120)大城市內已有專門的清潔工,《金華子雜編》卷下云:“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小民棹扁舟業以淘河者。”這可能就是保養河道的工人。南唐周則年輕時專以制造雨傘為業,李后主曾問及其事,周則說:“臣急于米鹽,日造二傘貨之,惟霪雨連月,則道大亨。”[14](卷上,第一編第二冊,P86)城市還需要大量的簡單勞動力,于是就出現了勞動力雇傭市場。浮梁縣令張某秩滿到京師,在華陰碰到了一個黃衫吏,對他說:“吾姓鐘,生為宣城縣腳力,亡于華陰,遂為幽冥所錄。”[15](卷350,P2775)這個腳力就是宣州的自由勞動力。而在延陵縣,陳生欲“求人負擔藥物”,到傭作坊中尋人幫忙,[15](卷74, P464)想來這樣的勞動力市場在大城市中都是存在的。
服務性商業的興盛是城市經濟功能增強的重要標志。六朝至隋唐,城市服務業在整個商業中所占比重明顯增加,行業種類繁多。江南城市中,服務性商業主要有飲食業、服裝業、房產業、旅店業、租賃業、修補業等。唐朝富人賈三折,“夜以方囊盛錢于腰間,微行市中買酒,呼秦聲女置宴”。[16](P156)百姓夜間可進入市中,而且還可以購買東西。在一些比較發達的城市中,夜間經商是官府允許的,只是限于照明條件,夜晚做生意總不如白天來得興盛。大城市中,酒店特別多。杜牧曾談到潤州市中酒樓:“青苔寺里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17](卷3《潤州》, P43)金陵地處南北要沖,酒樓最為多見。李白云:“朝沽金陵酒,歌吹孫楚樓。”孫楚酒樓在金陵城西,秦淮河邊。[8](卷19《玩月》,P1122)蘇州酒樓特別多,有街巷以酒店聞名,“唐時有富人修第其間,植花浚池,建水檻風亭,釀美酒,以延賓旅。其酒價頗高,故號大酒巷”。[18](卷下《往跡》, P60)白居易云:“皋橋夜沽酒,燈火是誰家?”[19](卷24《夜歸》, P541)蘇州皋橋邊白天商業活動興盛,但到晚上仍有酒店在營業。湖州出名酒,市內有大量酒樓,杜牧曾云:“金釵有幾只,抽當酒家錢。”[17](卷3《代吳興妓春初寄薛軍事》, P54)
各種飲食攤店遍布江南城市。吳縣朱自勸死后,其女入寺為尼,大歷三年(768),“令往市買胡餅,充齋饌物”,[15](卷338, P2686)可知市內有專門出售餅類的商店。鲊是用鹽腌制的魚、肉食品,是人們特別喜愛而在市場上常見供應的一種食品,“池州民楊氏以賣鲊為業。嘗烹鯉魚十枚,令兒守之”。[12](卷3,P56)湖州儀鳳橋南有魚脯樓,吳越國時在此專門曝魚脯上貢,但“春月尤多,作以供盤饤”,“今鄉土魚脯甚美”。上貢用不了這么多,就用來出售,因此魚脯樓十分有名。[20](卷18《食用故事》,P4842)
江南各城市中,出現了許多著名食品。吳越杭州“有一種玲瓏牡丹鲊,以魚葉斗成牡丹狀。既熟,出盎中,微紅,如初開牡丹”。湖州有“吳興連帶鲊”,“不發缸”,被收進韋巨源《家食賬》。吳興人“斂牛乳為龍華飯”,“設客以吳興臠團糟”。南唐金陵,北方士大夫大量涌至,講究飲食之風大盛,金陵面點制作有“建康七妙”,如虀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硯、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面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等名品。[14](卷下,P107)
城市內有大量公私逆旅供外地人住宿。官方有館驛,但一般老百姓是沒辦法入住的。對普通老百姓來說,他們可以入住民間開設的各種逆旅客舍。武則天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將債主“于客舍遂飲之醉”,最后將其殺死。[21](卷2,P19)客舍大多開設在州縣城市里。大歷中,洛陽人劉貫詞和蔡霞在蘇州認識后互相照顧,蔡對劉說:“逆旅中遽蒙周念,既無形跡,輒露心誠。”[22](卷3,P180)說明兩人都是借住在逆旅中。蘇州這樣的大城市,逆旅決不僅一兩個。前欽州刺史李漢雄,天祐丙子歲游杭州,住宿在“逆旅”中,[12](P122)說明杭州城內的客舍數量應該很多。交通發達,人們的商品意識較強,商品經濟總體發展水平較高,人員流動量大,因而在城市中開設私人客舍是十分多見的。
江南城市中房屋買賣十分普遍,還有中間人居間撮合。南齊崔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慚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11](卷52《崔祖慰傳》,P901)這里的買者,實為中間人,他在中間想賺一萬的好處費。梁代徐陵說:“吾市徐樞宅,為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23](卷5《與顧記室書》,P1B)如果外地人要長久住在江南,許多人想到了購置、求租房產這一辦法,因此江南大城市中房產出租、買賣比較盛行。蘇州華亭令曹朗官秩將滿,來到蘇州“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后逼冬至,朗緣新堂修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斤,東間窗下有一榻,新設茵席,其上有修車細蘆廢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庫,一房即花紅及乳母,一間充廚”。[15](卷366,P2906)從曹縣令在蘇州購房居住,同時添置了大量日常生活用品上可以看出,城市房屋的買賣對促進城市經濟繁榮的作用是相當大的。房屋可以出租,虔化縣令王瞻罷任歸金陵,“自出僦舍”,租借房子居住。[12](卷1,P19)
城市中服裝鞋帽的制造和銷售,是服務性商業的一個重要行業。在金陵、杭州、越州、宣州有各種各樣的裁衣肆,專門為城市居民制造衣服和鞋帽,同時在大城市中也出現了銷售衣帽的行業。劉茂忠為刺史時,有一女養在金陵,及金陵“城陷,為兵人所掠在師,茂忠使女仆入諸營部,托鬻衣而竊求之”,[24](卷10《劉茂忠傳》,,P224)可知出售衣服在城市內是比較常見的。衣帽鞋制造業主要在會稽、杭州、宣城、金陵、蘇州等一些較大的城市中出現。天寶時,會稽主簿季攸“乃為外甥女造作衣裳、帷帳”。[15](卷333,P2645)季主簿不可能自己動手做,肯定是找了裁衣鋪中的工人縫制。陶谷《清異錄》卷下談到“宣城裁衣肆”,說明城市中成衣制造越來越為人們所接受。同書又說:“韓熙載在江南造輕紗帽,匠帽者謂為韓君輕格。”韓氏為南唐高官,后期主要活動在金陵,因此制帽匠當在金陵城內。
江南城市的服務業總體上說六朝時已有初步嶄露的跡象,到了唐代漸漸在大城市中有較為興盛的表現。服務業經營內容已擴大到城市居民生活的各個方面,只要有利潤可以賺取,服務業就會往那個方向發展。服務性行業的經營方式靈活多樣,如有的是白天經營,有的是全天候經營。與城市生活休戚相關的服務業,如剔糞業、修理業、拾荒業、器物租賃業等,限于史料的記載,我們無法做詳細的介紹。服務業的發展,既適應了城市發展過程中城市民眾不同的生活需求,同時也為城市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增長點,優化了城市的經濟結構,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使城市人口不斷增加,直接促進了城市消費。
三、門類眾多的手工業生產
手工業生產水平是衡量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經濟的一個重要標志。與商業的發展一樣,城市手工業由官營和民營兩部分組成。由于六朝和南唐的中央政府在江南,因而城市手工業中官營的那部分所占分量較重。
官營手工業集中在大中城市和部分小城市中,主要有紡織、造紙、金銀器制造、兵器制造、鑄錢、造船等產業。六朝都城建康有眾多的官手工業工人。孫權時“諸織絡,數不滿百”。吳景帝孫休永安年間,交趾郡太守“科郡上手工千余人送建業”,[25](卷48《吳書·三嗣主傳》,P1161)將這部分手工業工人充實到孫吳官營作坊中來。吳幼帝、景帝時,“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25](卷61《吳書·陸凱傳》,P1402)吳國的葛、麻紡織品生產在當時有較高的技術水平。東晉末年,大將劉裕率軍滅后秦,遷關中“百工”于江南,在建康設立了專門的織錦機構——斗場錦署。大量外地熟練的紡織工人來到江南城市,使南方絲織業獲得長足的發展。南齊時,芮芮虜(即柔然)使臣曾向南朝政府求賜錦工,南齊以“織成錦工并女人,不堪涉遠”為由加以拒絕。[11](卷59《芮芮虜傳》,P1025)唐末潤州的錦工享有盛名,天復二年(902)潤州人徐綰在杭州發動叛亂,城中有兩百余錦工,全是潤州人,錢镠長子元瑛恐怕他們參與徐綰叛亂,宣布“百工悉免今日工作”。[26](卷83《錢傳瑛傳》,P1194)可以確定,潤州在戰亂前有數百人的織錦隊伍。至南唐,官府里設有作坊,生產物品種類眾多,數量很大。
南朝官手工業造紙技術相當高超。《文房四譜》卷4《紙譜》引《丹陽記》稱,南朝建康城內有“紙官署,齊高帝于此造紙之所也。嘗送凝光紙贈王僧虔”。唐《元和郡縣圖志》卷26載婺州開元貢藤紙、元和貢白藤細紙。《冊府元龜》卷719《幕府部·清廉》云:“杜暹為婺州參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三萬余張以贈之,暹唯受一百,余悉還之。時州僚別者見而嘆曰:‘昔清吏受一文錢,復何異也。’”以紙3萬余張相贈,可見生產量是很大的。
六朝墓葬中出土的很多金銀器,反映了城市金銀冶鑄技術的進步。羅宗真對南京附近有金銀器隨葬的18座六朝墓統計,共出土金銀器411件,其中金器即達363件,金器中飾件又達232件,說明當時金器主要用來裝飾或做饋贈的禮品。這些金銀裝飾品制作非常精細,提煉十分純正,含純金達95%以上,足可說明建康和南徐州的金銀器制造水平之高。[27](P12)到了唐朝,江南城市中的官手工業繼續保持著金銀器制作的高水準。如敬宗即位后不久,詔浙西造銀盝子妝具20件進內。時任潤州刺史的李德裕說:“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回市。去(年)二月中奉宣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余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妝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并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于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迨。”[28](卷174《李德裕傳》,P4512)敬宗要浙西貢金銀造妝具,證明潤州所造產品由于工藝水平較高,很合皇室胃口。1962年,在西安北郊坑底村出土了唐代金花雙鳳紋銀盤1件,盤底刻有銘文:“浙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大中大夫守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臣裴肅進。”[29]裴肅在貞元十四至十八年(798~802)間為越州刺史,該金花銀盤應該大致上是這一時期制造的。
民營手工業是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手工業的主體,其發展伴隨著城市商業的繁盛而興旺起來。民營手工業的發展有這樣一些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手工業門類眾多。學者指出,六朝手工業形成了冶煉、造船、制瓷、紡織、制鹽、造紙、制茶等七大手工業部門。[30](P144)不過從實際來看,冶煉、制瓷、制鹽、制茶等一般是在城市外的,真正在城市里的手工業估計主要是造船、紡織,此外還有銅器制造、制酒等。如六朝京口出好水,因而京口酒的質量很高。曲阿縣的新豐酒和曲阿酒也很有名。《魏書》卷70《劉藻傳》談到北魏南侵,魏孝文帝與將軍劉藻辭別,相約于石頭城相見。劉藻說:“臣雖才非古人,庶亦不留賊虜而遺陛下,輒當釃曲阿之酒以待百官。”孝文帝大笑說:“今未至曲阿,且以河東數石賜卿。”說明江南的曲阿酒名播北方。至唐五代,手工業的種類就更為增多,如紡織業(絲紡、麻紡、刺繡)、金銀器和銅器制造、造船、漆器制造、食品制造(制酒、制糖、副食品)、服裝、文具制造、印刷等,行業十分繁多。《南唐近事》卷2記載:“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幸,每曰:‘我富貴之日,為你置銀靴焉。’保大初……語及前事,即日賜銀十觔以代銀靴。權遂命工鍛靴穿焉,人皆哂之。”城市里有專門制靴的工匠。因為是要鍛銀為匠,所以這個工匠又是個金銀匠。慈溪縣東35里的香山智度寺,“咸通十四年,有途人負漆器五百入寺,曰:‘湯和尚于浙西丐緣,先遣至此,和尚濯足溪邊隨至矣。’”[31](卷17《寺院》,P5217)時浙西節度駐地在潤州,文中的“浙西”應該指的是潤州,說明潤州是漆器的重要生產地。
第二,地方特色比較明顯。江南城市手工業的門類在增多,大中小城市都有不少手工業,不過各城市的手工業發展速度并不一致。如絲綢業,在一些城市出產的特殊織品很多,技術比較先進;而有的城市絲織技術比較落后,生產不出新產品。東晉南朝時,江南蠶繭生產有突破性進展,如據左思《吳都賦》稱,吳郡出現了“鄉貢八蠶之綿”,即實現了一年蠶多熟。《隋書》對唐以前江南絲織業做過概括:“一年蠶四五熟,勤于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雞鳴布。”[7](卷31《地理志下》,P887)唐代宋之問任越州長史,曾描述越州的情形:“妾住越城南,離居不自堪。采花驚曙鳥,摘葉餧春蠶。”[9](卷52《江南曲》,P634)開元時徐延壽見到的越州:“金釧越溪女,羅衣胡粉香。織縑春卷幔,采蕨暝提筐。”[9](卷114《南州行》,P1165)天寶時,越州的綾、紗、羅作為地方特產上貢朝廷,證實能夠生產的精美織品越來越多。越州綾有白編、交梭、吳綾、越綾、十樣花紋等品種,名目繁多,體現了織法和紋飾的多樣性。尤其是吳綾,有一般吳綾及異文吳綾、花鼓歇、單絲吳綾等品種。蘇、潤、宣、常、杭等城市都是絲織品較為發達的城市,但睦、婺、衢、處、溫、州、歙、池等城市絲紡技術比較低。再比如金屬制造和加工,潤、蘇、衢、杭、宣、越等城市發展較有特色,而其他城市加工水準就較低。鐵器制造,睦、臺等城市發展很有特點。由于各城市手工業門類在不斷增多,生產技術經常在改進,但同時各城市有自己的發展特點,所以江南手工業以太湖周圍及浙北的一些城市最為發達,而南部城市手工業發展速度較慢。
第三,城市周圍原料的支撐是江南城市民營手工業生產發展的重要原因。無論是絲綢、麻織類紡織工業,還是制茶、制酒類的食品工業,以及造紙、制衣等,都是由于城市四郊的農村提供了豐富的原材料,城市才能進行技術上的加工。因此,江南城市手工業是依賴了農村的原材料生產才發展興旺的。當然,也有一些手工業原材料的供應并不是本地,如江南城市的漆器制造比較發達,但漆器材料并不全是本地的;沿江沿海城市是重要的造船中心,但木材往往使用的是其他地方的,如金陵常使用的江西木材;金屬制造所用礦產一般而言是本地開采的,但江南不產金,如潤州的金銀器制造技術較高,而原材料卻是從淮南收購而來,蘇州的情況也基本相同。不過從總體上看,江南各城市手工業的發展,與各地原材料的供應有著直接關系。
第四,江南城市民營手工業產品有相當部分是進入到商品市場的。由于六朝至隋唐社會的特殊性,民營手工業的生產物有一部分并不進入流通領域。比如宣州涇縣城中,絲織生產十分普遍,“尋街聽繭繅”,到處都是織機的聲音。[9](卷588,李瀕《送許棠歸涇縣作尉》,P6823)《元和郡縣圖志》談到宣州貞元時期上貢五色線毯,《新唐書》稱絲頭紅毯。這是一種以染色絲線織造的地毯,白居易《紅繡毯》詩有詳盡描寫:“宣城太守加樣織,自謂為臣能竭力。百夫同擔進宮中,線厚絲多卷不得。”[9](卷4,P78)這樣的民營手工產品其實不是商品,而是作為貢品獻給了朝廷。不過,江南的民營手工業產品大部分仍是能進入商品市場的。比如溫州別駕豆盧榮妻母金河公主隨婿居住在溫州多年,寶應初,“時江東米貴,唯溫州米賤,公主令人置吳綾數千匹”,[15](卷280,P2230)這些吳綾可能是溫州本地生產的,是溫州市場上的商品。李白《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說宣州是“魚鹽滿市井,布帛如云煙”,[8](卷12,P780)可知宣州城內的手工業品是大量供應市場的。
第五,民營手工業生產規模小,一般都是以家庭作坊或個體生產為主。個體生產的技術有不少世代相傳。如諸葛筆是宣州最有名的筆,《白孔六帖》卷14《筆硯》云:“宣州諸葛氏能作筆,柳公權求之,先與三管,語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以常筆與之。’未幾,柳以不入用,別求筆,遂以常筆與之。先與者三管,非右軍不能諸葛筆也。”傳說從晉朝開始,諸葛氏世代制筆,唐五代更是代出名手。大歷十才子之一耿湋有《詠宣州筆》云:“影端緣守直,心勁懶藏鋒。落紙驚風起,搖空見露濃。”[9](卷268,P2980)皮日休云:“宣毫利若風,剡紙光與月。”[9](卷609《二游詩》,P7028)五代宣州筆特別受到宮廷宗室的喜愛,《清異錄》卷下談到南唐宜春王“喜書札,學晉二王楷法,用宣城諸葛筆一枝,酬以十金,勁妙甲當時,號為翹軒寶帚,士人往往呼為寶帚”。宣州的筆應該都是家庭手工業生產的。又云:“唐世舉子將入場,嗜利者爭賣健豪圓鋒筆,其價十倍,號定名筆。筆工每賣一枝則錄姓名,俟其榮捷,則詣門求阿堵,俗呼謝筆。”筆工就是個體手工者,制筆的技術精湛,講求質量。再比如蘇州地區草鞋編織歷史久遠,上可推到晉朝。《說郛》卷43引唐王獻《炙轂子雜錄》云:“靸鞋舄……西晉永嘉元年,始尚用黃麻為之。……梁天監中,武帝以絲為之,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及大歷中,進五朵草履子。至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至今其樣轉多差異。”蘇州蒲鞋遠銷越州,特別博得城里女孩子的喜愛,繡上花朵以后甚至可作為定情之物。民營手工業也常以作坊的形式出現在江南城市中。唐文宗開成時宰相李玨曾談到南方的銅器鑄造:“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為數器,售利三四倍。”[28](卷176《楊嗣復傳》,P4557)他認為銅器制造成肆成列,顯然都是一個個作坊在銷錢。
相比較官營手工業,民營手工業的生產都是小規模的,不過商品的總量往往超過官營手工業。私營手工業有時會和官營手工業生產相同的商品,但更多的時候往往會生產官營手工業所不愿生產的產品。如《清異錄》卷上云:“時戢為青陽丞,潔己勤民,肉味不給,日市豆腐數個,邑人呼豆腐為小宰羊。”豆腐的制作由來已久,而州縣城內官營手工業是不屑于生產這種小商品的,而民營手工業就填補了空白,滿足商品經營的需要。因而民營手工業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日趨活躍的外貿業
隨著商品經濟的興盛,江南地區的外貿業開始出現。東吳黃武五年(226),吳國交趾太守將來到交趾的大秦商人秦論送到建業,孫權曾親自接見。時亶洲商販常到會稽來販布,而會稽人也有飄洋過海到亶洲的,反映了東吳和海外地區已有外貿的存在。在日本的一些古墓中出土過一些吳鏡,應該是日本和東吳人員往來攜帶的證據。還出土了許多三角緣神獸鏡,雖然生產于日本,但與吳鏡有不少關聯,有關專家認為“這意味著它們是中國的吳國工匠東渡日本,在日本制作的”。[32]東晉時期,江南城市與日本、朝鮮、南海諸國的來往更為密切,民間貿易出現。如《晉書》卷97《林邑傳》載:“徼外諸國嘗賚寶物自海路來貿貨。”南朝時期,與南海諸國的交往更趨活躍,一些國家如林邑、扶南等國遣使建康貢獻禮物。《梁書》卷54《丹丹傳》談到中大通二年(530)時曾獻牙像及塔、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535)獻金、盆腔、琉璃、雜寶、香藥。其時南朝也遣使往南海,帶去了諸如鎧仗、袍襖、馬匹等物品。雙方互獻的都是上層人物喜愛的奢侈品,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特殊貿易。
唐五代,江南與海外之間的貿易比較常見。我們以前曾做過研究,發現唐五代江南地區有大量的少數民族商人和外國商人在活動,有朝鮮、日本、阿拉伯、波斯、印度、渤海國、契丹、西域等國家和地區的,主要經營著珠寶業、香藥、火油等各類奢侈品和茶葉、糧食、絲綢等商品的買賣,還有一部分從事著酒店業的經營。[33]
隨著經濟的發展,江南靠近江海的一些大城市成了對外交通貿易港口。浙東沿海地區的一些城市由于占有優越的自然條件,外國來船眾多,而國內船只也常從這些地區起航赴國外貿易。如明州是江南與日本等國商業運輸和人員往來最重要的港口。唐末從明州出發到日本的船有6只,日本到達明州的船有1只。宋人稱明州是“海道輻湊之地”,“南接閩廣,東則矮人國,北控高麗,商舶往來,物貨豐衍”,是“東南之要會也”。[34](卷7《慶元府》,P121)而實際上這種情況在唐末五代就已是如此。臺州是江南與日本、高麗等國海上商船來往的重要城市之一。浙江南部地區的瓷器出口,一般認為是直接從臺州出口的。有學者認為臺州地區瓷器對外貿易時,“從臨近的海門港、楚門港和松門港出口,遠銷日本、菲律賓和南洋群島”,[35]這大致上是可信的。溫州也是日本船只靠岸的重要地區,溫州向南的船只經南海可直通印度、阿拉伯。越州也是外國商人上岸的一個港口。日本島東面海中有島嶼邪古、波邪、多尼等,“北距新羅,西北百濟,西南直越州,有絲絮、怪珍云”。[34](卷220《日本傳》,P6209)吳越時期的杭州,前來的外國人很多,高麗人和日本人最為常見。僧契盈陪侍忠懿王游碧波亭,“時潮水初滿,舟楫輻湊,望之不見其首尾”。[26](卷89《契盈傳》,P1290)譚其驤認為杭州是唐五代重要的通商口岸,他引述了杜甫詩“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認為西陵是當時海船出入杭州的必經之地,“唐代西陵之所以時有商胡蹤跡,其目的地亦必在杭州”。[37](P420)
沿長江的各大城市不時有外國船只前來。五代時的金陵,是江南的重要港口之一。金陵城內居住著一定數量的外國商人。曾有大食國使者前來進貢龍腦油,南唐元宗愛惜異常。鄭文寶《耿先生傳》云:“南海常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上實寶之,以龍腦調酒服,香氣連日,也以賜近臣。”[26](卷34,P479)王貞白《娼樓行》云:“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38](卷11,P465)看來大食國帶來的龍腦油數量不少,連一般的娼樓中也在大量使用。潤州常見外國船只,許棠《題金山寺》云:“剎礙長空鳥,船通外國人。房房皆疊石,風掃永無塵。”[9](卷603,P5973)李棲筠為常州刺史,城下“海夷浮舶,弦發望至”,到常州城來貿易的中外海船必定不少。楊琎任常州司戶參軍時,“海稅孔殷”,[39](開元一一《大唐故楊府君墓志銘》,P1230)說明地方政府向前來商貿的外國商人征取一定比例的商稅。
江南有對外貿易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和長江沿岸,其中以明州、臺州、杭州、金陵等城市貿易最為興旺。頻繁的交易,必然是大量的貨物相互往來。從實際情況來看,江南運出的貨物往往是本地區的特殊產品。日本自奈良朝以后,對唐朝的物品極其嗜好,每每以擁有某種唐貨互相夸耀。如光孝仁和元年(885),日本政府下令大宰府司,禁止王臣家使及管內吏民私自以高價搶購舶來品,說明唐朝貨物是十分受人歡迎的。[40](P115)
江南內陸腹地較為廣闊,各地生產的貨物集中于各大城市,再輸向國外。運向城市的貨物主要有以下數種:
一是瓷器。江南各地生產的瓷器,大多運向明州,再向外輸出。1973年,在寧波遵義路唐宋時代的漁浦門城門遺址的清理中,在唐代城墻墻基下出土了700多件唐代瓷器,其中絕大部分是越州窯瓷器,還有部分為長沙窯產品。林士民認為唐代的明州北面緊臨余姚江水路,東南是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匯合的地方,“設有海運碼頭,是對外貿易的重要集散地”,應該說是比較真實地描繪了當時的情況。[41]這些瓷器,顯然是當時外銷的一部分,而長沙窯瓷器是從長江水道運抵后在明州中轉的。
二是絲綢。絲綢是江南較有特色的一種手工業產品。后周廣順三年(953),吳越商人蔣承勛代表吳越王錢弘俶向日本送上錦帛,而日本右大臣藤原師輔托蔣承勛帶回吳越的信中說:“抑人臣之道,交不出境,錦綺珍貨,奈國憲何。”因而估計蔣承勛所運貨物中有不少絲綢織品。木宮泰彥認為:“客商等輸入的商品雖屬不詳,但可能和前代一樣,以香藥和錦綺等織物為主,而日本方面用來做交易的似乎以沙金等物為主。”[40](P226)
三是香藥、中藥和家禽、牲畜動物等。《三代實錄》載清和貞觀十六年(874)六月,大宰府令大神己進、多治安江等人入唐求香藥。3年后,多治安江從臺州回國,帶回貨物眾多,估計主要是香藥類商品。《扶桑紀略》載延喜三年(903),唐朝商人景球到達日本,獻羊1頭,白鵝5只。其時北方戰爭不斷,景球或許也是江南商人,有可能銷往日本貨物中的一部分是家禽、牲畜。天慶元年(938),吳越商人蔣承勛向日本大臣進獻羊2頭。
從這些輸出的產品來看,一般不是城市自己生產的,大多來自周圍農村地區。不過城市作為運輸的關節點,將這些產品運向國外,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視。
五、其他產業
除商業、服務業、手工業、外貿業外,江南城市還有一些其他產業,對城市經濟同樣也產生著一定的影響。
城市中有一部分較為富裕的人從事高利貸業。作為城市金融業的一種,高利貸是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常見的一種賺錢方式,從事的人數也有一定的數量。吳郡人陸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5](卷77《恩幸傳》,P1936)陸驗通過經商致富,但最初的資金是向郁吉卿借貸的。雖然并沒有明說他是通過高利率借錢給陸驗,但利益追逐的本性決定了陸驗的借貸不會是無息的。在江南城市,放貸的人還真不少。南朝宋明帝時,“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為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6](卷57《蔡興宗傳》,P1583)放高利貸帶來的利潤吸引了王公妃主。梁臨川王蕭宏在“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迄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5](卷51《梁臨川王宏傳》,P1278)他是舉放高利貸,以田宅邸店為抵押,逾期不還,所押不動產即被沒收。
城市中還有少量的種植業。如有的豪族在京都為官,賜田就在都城建業附近。東吳名將潘璋死,其“妻居建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25](卷55《吳書·潘璋傳》,P1300)復客應是依附農民,是一種區別于編戶的奴仆,所以推測建業城內應該是有農田的。這部分復客是城市居民,主要是靠農業勞作而生活。建康城北地區在六朝以前人煙荒蕪,當時為了安置北方移民,曾在此地設郡縣,結果城北地區人口增多。楊吳筑城時,將這些地區劃至城外。城北地區人口相對較少,城內的交通不如城南繁忙,故僅開一個城門出入。這些地區的居民利用玄武湖,發展養殖業,獲利甚豐。南唐時,玄武湖中“每歲菱藕罟網之利不下數十千”。[42](卷1,P210)由于城北地區面積廣大,尚不具備發展工商業的條件,所以即使到了南唐,金陵城周圍仍有很廣大的農業區,居民以農業人口為主。
運輸業也是重要的產業之一。吳都建業時,就已“樓船舉帆而過肆”,市肆中的商品是遠道運輸而來,時“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賈作上下”。[25](卷48《吳書·孫休傳》,P1158)劉宋大明八年(464),孝武帝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雜稅。”[6](卷6《孝武帝紀》,P134)作為商品的糧食,全是通過運輸后再販賣的。《唐國史補》卷下云:“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揚子、錢塘二江,則乘兩潮發棹。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為帆,大者八十余幅。”江南城市的商品都得靠運輸,所以長江運輸就極為繁盛,成為當時的主要航路。《中吳紀聞》卷4云:“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曲。皮日休答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榨酒三瓶寄夜航。’”皮日休詩收在《全唐詩》卷614。江南重水上航運,客貨運輸以船運為主,從很早以來就發明了夜間航行的船只,可以日夜兼程地趕路。開元時,張九齡在江寧縣,見到長江中間“萬井緣津渚,千艘咽渡頭。漁商多末事,耕稼少良疇”。[9](卷49《候使登石頭驛樓作》,P604)這些商船中,想必很多就是專門跑運輸的。開元時,長城縣尉陳利賓從會稽出發,沿浙江回東陽,“會天久雨,江水彌漫,賓與其徒二十余船同發,乘風掛帆。須臾,天色昧暗,風勢益壯。至界石竇上,水擁閼眾流而下,波濤沖擊,勢不得泊。其前輩二十余舟皆至竇口而敗,舟人懼”。[15](卷104,P705)這些舟人都是通過交通運輸作為生活來源的。此外,運送貨物用船或車輛外,還有靠人力的。茅山陳生,“偶到延陵,到傭作坊,求人負擔藥物,卻歸山居。以價賤,多不肯”。[15](卷74,P464)傭作坊就是專門雇人的區域,通過人力挑擔運輸貨物。
高利貸業、城市農業、運輸業,對江南城市的經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它們完善了城市的經濟結構,推動了城市經濟產業的多樣化、多層次,使城市的經濟功能更為多樣化。
六、余論:江南城市產業的特點
城市產業是城市經濟發展水平的反映。六朝以來的江南城市經濟,以商業為主、手工業為輔。到隋唐五代,城市服務業開始興盛,成為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在經濟結構上呈現出消費性和生產性、服務性并存的特點,并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手工業和服務業的比重不斷加重,城市的產業結構在不斷調整,產業特色漸趨紛呈的局面。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經濟產業,大體而言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江南城市產業結構基本合理。江南城市的經濟功能在逐漸顯現,這主要歸功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商業長足發展后,不再是政治性城市的依附,而是有自身獨立的發展體系,商業不斷展現出一些新現象。城市手工業盡管技術要求不高,還是比較粗放的,但手工業門類在增多,利用了有利的材料供應,手工業發展越來越有特點。城市服務業是城市商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是為人口增多的城市居民生活服務的一個新興產業,它直接輻射到周圍廣大的農村地區,使更多的城郊農村卷入商品交換中來。對外貿易等行業雖然在整個城市經濟中所占比重不算太高,但在完善城市經濟結構體系上的作用不可忽視。江南城市創造出的經濟實力,通過水陸交通線路,與相鄰地區的城市,乃至中原地區的城市,構成經濟網絡,大大有利于全國經濟的發展。
我們認為,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產業結構基本合理,可以大體滿足一個城市發展對經濟的需要,符合當時城市發展的實際情況。當然,這些產業還是比較粗疏和簡單的,與宋朝以后城市經濟產業的發展是不能相提并論的。不過,宋朝以后城市產業發展的色調在六朝唐五代已經顯現,只不過宋朝以后更加濃重而已。
第二,江南城市產業地域性明顯,不同城市形成了各自的產業特色。比如江南城市商業的發展在大城市發展較快,而小城市,特別是縣城,商業的發展比較緩慢。處于江南運河沿岸、長江沿岸、錢塘江沿岸的城市,由于倚恃了交通業的發展,商業和城市服務業發展較快。六朝的建康、山陰,唐中期以后的蘇州、杭州、越州、潤州,唐末五代的金陵、杭州,城市規模較大,城市經濟的內涵比較豐富,影響力較大。手工業的發展更是與各地的原材料提供密切相關。如金銀器制造主要分布在潤州、蘇州、宣州等地;沿海、沿江城市的造船業比較發達,而內陸城市沒有發展造船業的條件;外貿業的發展主要在明州、臺州、溫州、杭州、金陵等一些有港口的城市中。
總體上說,蘇州、建康(金陵)、杭州等大城市的產業門類比較齊全,商業和城市服務業發展比較興盛;而沿海、沿江的城市發展交通運輸、外貿業等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有自然資源的城市手工業發展具有地域特色。
第三,江南城市產業分工與城市發展相適應。城市產業分工與城市的規模比較一致,當城市規模達到一定程度時,城市中的產業分工就越來越細化。城市人口增多,城市中既居住著貴族官僚、軍隊、各種政府服務人員,同時又居住著大量的普通居民,這時分層次的各色商業服務就會應運而生,就會產生對不同質量和檔次的手工業品的需求。官員及其子女、士族子弟對商業服務和手工業品的需求,與城市中的各種從業人員,如出賣體力者、巫醫卜相、娼妓、奴婢、官戶、雜戶、樂戶及太常音聲人、僧尼道士等,肯定各不相同。因此,城市中人口的多少、階層的不同,直接會促使商業、手工業、服務業和外貿業的發展起落。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和現象,表現在產業結構上,服務業和外貿業快速發展。這與同時期各地其他城市的發展有較大的不同,是江南城市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特色,是我們在評論江南城市發展不應忽略的。不過從總體上說,我們也不應夸大城市經濟生產的作用,因為江南城市主要是消費型的,并不是生產型的。無論是商業、手工業還是外貿、服務業和其他一些產業,最主要的是為了滿足城市中日益增長的消費。城市中有些部門的生產力的確超過了城市本身的需要,但這種生產局限在一定的領域,生產能力還是有限的。這是我們正確認識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產業時應該注意的一點。
注釋:
①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815《布帛部二·錦》引山謙之《丹陽記》:“斗場錦署,平關右遷其百工也。”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624頁。
[1] 董誥.全唐文[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 元稹.元稹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82.
[3] 王欽若.冊府元龜[M].北京:中華書局,1960.
[4] 房玄齡.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5] 李延壽.南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3.
[6] 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62.
[7] 魏徵.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3.
[8] 瞿蛻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 彭定求.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0] 張津.乾道四明圖經[A].宋元方志叢刊[C].北京:中華書局,1990.
[11] 蕭子顯.南齊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2.
[12] 徐鉉.稽神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6.
[13] 張劍光.六朝唐五代江南城市市場的形制與變化[A].唐史論叢(第十五輯)[C] .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2.
[14] 陶谷.清異錄[A].全宋筆記[C].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15] 李昉.太平廣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2.
[16] 馮贄.云仙雜記[A].筆記小說大觀[C].臺北:臺灣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84.
[17] 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8] 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M].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19] 白居易.白居易集[M]. 北京:中華書局,1979.
[20] 談鑰.嘉泰吳興志[A].宋元方志叢刊[C].北京:中華書局,1990.
[21] 張鷟.朝野僉載[A].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2] 李復言.續玄怪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3] 徐陵.徐孝穆集[A].四部叢刊初編[C].北京:商務印書館,1919.
[24] 龍袞.江南野史[A].全宋筆記[C].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
[25] 陳壽.三國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
[26] 吳任臣.十國春秋[M].北京:中華書局,1983.
[27] 羅宗真.探索歷史的真相——江蘇地區考古、歷史研究文集[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28] 劉昫.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9] 李長慶.西安北郊發現唐代金花銀盤[J].文物,1963,(10).
[30] 簡修煒,等.六朝史稿[C].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
[31] 方萬里.寶慶四明志[A].宋元方志叢刊[C].北京:中華書局,1990.
[32] 王仲殊.日本三角緣神獸鏡綜論[J].考古,1984,(5).
[33] 張劍光.唐五代江南的外商[J].史林,2006,(3).
[34] 祝穆.方輿勝覽[M].北京:中華書局,2003.
[35] 臺州地區文管會、溫嶺文化局.浙江溫嶺青瓷窯址調查 [J].考古, 1991,(7).
[36] 歐陽修.新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37] 譚其驤.杭州都市發展之經過[A].長水集[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38] 童養年.全唐詩續補遺[A].全唐詩初編(第三編)[C].北京:中華書局,1992.
[39] 周紹良.唐代墓志匯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0] 木宮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
[41] 林士民.浙江寧波市出土一批唐代瓷器[J].文物,1976,(7).
[42] 鄭文寶.南唐近事[A].全宋筆記[C].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