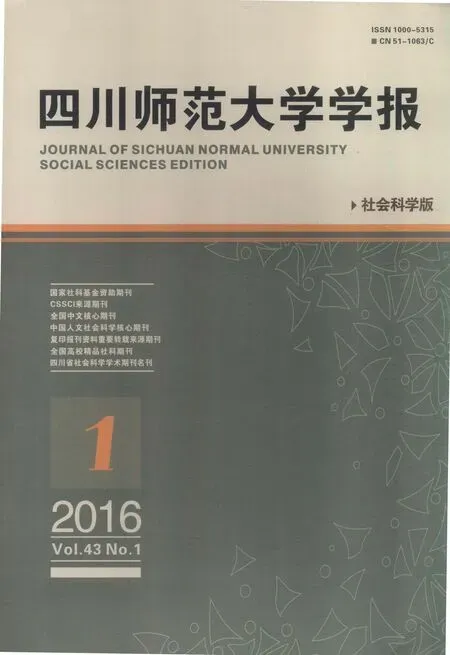論《最藍的眼睛》佩科拉瘋癲之路的食物話語
劉 芹 利
(四川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成都 610101)
?
論《最藍的眼睛》佩科拉瘋癲之路的食物話語
劉芹利
(四川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成都 610101)
摘要:美國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在表現非裔種族與性別問題、權力與欲望關系時將食物意象運用得淋漓盡致。她的代表作《最藍的眼睛》中主人翁黑人女孩佩科拉瘋癲過程充滿豐富又頗有象征意義的食物意象。這些交織著欲望與權力的食物話語揭示了非裔女性在父權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壓迫下“自我”嚴重扭曲異化的現狀以及非裔女性長久壓抑的欲望。
關鍵詞:托尼·莫里森;《最藍的眼睛》;食物話語;黑人女性文學

人類通過進食滿足自身生理饑餓并維持生存,然而飲食與進食的主要意義卻不僅存在于簡單的生理層面,更在于其象征領域上的特殊含義。美國人類學家卡羅爾·M·科尼漢(Carole M. Counihan)在1999年就提出,“食物的食用規則是人類構建現實的重要方式。他們是對社會所關注之物的一種諷喻,亦是人們規范自己身邊的物質、社會及象征世界的一種方式”[1]113。人們在特定的場合選擇不同的食物,這種特定的飲食行為表達了人們紛繁復雜的思想,例如欲望、儀式、性別、階級、種族、政治與權力等。文學作品是社會的縮影與再現,因此文學作品中食物意象的運用比比皆是,尤其是女性因為生理、社會與歷史等原因在家庭內務方面舉足輕重,飲食在女性作家作品中更具有特殊的象征含義。正如美國學者哈瑞特·布羅杰特(Harriet Blodgett)所說,“在原型意識的加強下,女性的家庭經歷激發了她們的靈感,將飲食這一基本需求轉化成一種藝術形式”[2]87。食物敘事不僅是女性文學中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也是“女性表達其生活中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基本方式”[3]XI。許多女性文本如瑪格麗特·米切爾的《飄》(1936)、湯亭亭的《女勇士》(1976)、托尼·莫里森的《最藍的眼睛》(1970)、愛麗絲·沃克的《紫色》(1982)、路易斯·厄德里克的《愛藥》(1984)等都曾運用女性熟悉的食物意象來表達小說人物在遭遇到愛情、家庭、族裔群體、文化乃至社會問題時那些微妙細膩與潛意識的情感,言說其中的欲望與權力關系。
在這些女性作家中,美國非裔作家托尼·莫里森在表現非裔種族與性別問題、欲望與權力關系時將食物意象尤其運用得淋漓盡致。她的第一部小說《最藍的眼睛》,隨后的《柏油娃》(1981)和《寵兒》(1987)均涉及到各種各樣的食物意象。近二十年來國外對于美國少數族裔文學中的食物研究逐漸形成氣候,尤其是跨文化領域中食物的象征意義受到許多西方和中國學者的關注。對于托尼·莫里森小說,國外的研究學者主要從政治、族裔以及文化等方面對食物意象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探討。其中,英國學者愛瑪·派克(Emma Parker)分析了《最藍的眼睛》與《寵兒》中的黑人的饑餓、糖的意義與胃口的政治[4];美國學者Andrew Warnes討論了《柏油娃》涉及到的主要食物的象征意義,剖析其中反映的不同族裔的二元對立、歐洲中心主義與種族主義[5]123-164;美國學者Allison Carruth從環境正義的角度論述了小說《柏油娃》中涉及到饑餓與飲食的文化意義[6];美國學者Cecily E. Hill讓讀者從《柏油娃》中主要的三頓飯認識不同階級、族裔文化以及各種人物之間的微妙關系[7]283-298。與國外頗具氣候的食物意象研究相比,國內從食物角度對莫里森小說的研究卻屈指可數。近十年主要有陸薇、王晉平、李霞等學者發表了相關文章[8-10]。這些文章雖然論證角度不同,但都從微觀的食物角度分析討論《最藍的眼睛》里白人文化價值觀對于非裔的腐蝕與傷害。綜合國內外研究現狀,這些對莫里森小說中的食物意象研究既有宏觀也有微觀的研究,但這些研究較少集中分析《最藍的眼睛》的主人翁黑人女孩佩科拉瘋癲過程中食物意象的作用與特殊含義。相較于莫里森其他幾部小說,《最藍的眼睛》盡管發表得較早,但是其中豐富繁多的食物意象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隨著小說故事情節的推進,可憐可悲的佩科拉因為外貌丑陋不為主流社會接受,逐漸由“胃口”的奴隸,慢慢陷入周圍朋友與親人用“饑餓”與“欲望”編織的網,直至最后在瘋癲中認為自己獲得了一雙最美的藍色眼睛。鑒于佩科拉這一瘋癲過程既豐富又頗有深意的食物意象,基于以往國內外對于莫里森作品中食物意象的分析,本文結合福柯的權利話語理論集中分析主人翁非裔女孩佩科拉瘋癲過程中的一系列食物意象如何反映內在欲望與權力的話語,揭示非裔女性在主體權利缺失的惡劣生存環境中,欲望逐步將主體異化并推向癲狂的這一過程。
一佩科拉無邊的“胃口”:迷人的牛奶與甜食
根據福柯的權力理論,“話語始終是與權利以及權力運作交織在一起的,社會性的和政治性的權力總是通過話語去運作”[11]9。福柯認為話語是權力關系的網絡,“話語”與權力是密不可分的,權力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與控制“話語”的產生與運動。對于福柯的話語理論,女性主義學者米切爾·巴瑞特認為:“這意味著各種話語都處在某種權力關系中,權力是話語在爭奪控制主體過程的動力體,也是這個過程的總和。”[12]136從這個意義上講,“話語”與權力是密不可分的,權力無時無刻不在影響與控制“話語”的產生與運動。運用福柯的權力話語理論分析《最藍的眼睛》中非裔女孩佩科拉的生活狀況與遭遇中涉及到的各種食物意象,可以更加清晰地揭示權力是如何彌漫在食物話語中,一步步駕馭黑人小女孩的欲望,牽引她不斷內化種族主義霸權話語,使其成為“胃口”的奴隸。
美國非裔的歷史交織著種族主義與性別歧視,他們幾百年來由于歷史、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原因飽受白人的奴役、壓迫與歧視。非裔長期以來被經濟的匱乏與生理的饑餓所困擾,例如莫里森在一次訪談錄中就曾提到,“我認為黑人作家擁有一種無休無止的饑餓與憂患氣質”[13]429。莫里森在《最藍的眼睛》中通過各種各樣的食物意象揭示了非裔群體,尤其是非裔女性生理與心理的饑餓。小說《秋天》這章里談到了作為邊緣階層的黑人對于物質與財富的強烈欲望:“意識到有被趕出門的現象存在,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對財富和擁有的渴望”[14]18。因為缺乏穩定的物質保障,為了能衣食無憂地度過寒冷的冬天,黑人“就像受驚絕望的鳥兒……對他們好不容易掙得的一份家產盡心盡力地守護;整個夏天都忙碌著在吊柜和貨架上堆滿自己腌制的食品”[14]18。非裔經濟上的劣勢地位決定了他們政治上權力的缺失與受到歧視,最終映射到內心。對此馮品佳認為,“在白人霸權社會,黑人覺得自己是下等人。當黑人內化了這種自卑時,物質方面的極度匱乏導致了心靈的極度扭曲”[15]59。
佩科拉生活在物質匱乏、政治上遭受歧視與壓迫的黑人家庭,無論白人還是黑人都認為她很丑陋,紛紛排斥與打擊她。她生活困頓,地位低下,缺乏作為一個獨立主體應有的基本權利,更缺乏父母的關愛與最基本的社會認同。因此,佩科拉渴望擁有一雙最藍的眼睛,這樣就能贏得父母的喜愛以及社會的接受。隨著遭受的打擊與歧視日益增多,她渴望得到社會認同與關愛的欲望日益強烈,這種“饑餓感”漸漸束縛并扭曲她的心靈。小說中莫里森運用了如糖果、漿果餡餅、牛奶、冰激凌、蘿卜、面包和黃油等食物意象,表達佩科拉由于種族主義內化以及主體權力缺失導致的無邊欲望與“胃口”。在這種欲望的驅使下,她沉醉于一切有可能讓自己變得美麗的方法,哪怕是用食物填滿空虛的“胃口”,迷惑并麻痹自己。主體權力的愈加缺失,欲望則越強烈,隨之產生的自我憎恨就越具摧毀性,從而加速了種族主義霸權話語的內化,由此加劇了主體的異化。
隱藏在佩科拉無邊欲望與“胃口”背后的法則正是福柯的“權力話語”。在福柯的權力理論中,抽象的話語建構、支配、控制于言說主體,而主體通過這樣的言語實踐時時體現著他者話語與權利體系[16]220。“權力”支配著佩科拉與其他人物的關系,牽引著她的“胃口”與欲望,讓她對牛奶與甜食有著不同尋常的迷戀,心甘情愿淪為權力的傀儡。小說中佩科拉迷戀潔白香甜的牛奶,連帶著印有白人女童星的牛奶杯子也成為了她膜拜的對象。“牛奶盛在藍白色的印有雪莉·坦布爾頭像的杯子里。她喝牛奶喝了很長時間,看著雪莉·坦布爾帶有酒窩的頭像時充滿愛慕之情……(她)喜歡印有雪莉·坦布爾頭像的杯子,一有機會就用它喝牛奶,好擺弄和欣賞雪莉的甜臉蛋”[14]22。印有美國20世紀30年代著名童星秀蘭·鄧波兒(Shirley Temple,即引文中的“雪莉·坦布爾”)的杯子對于佩科拉來說具有特殊的魅力。首先,這個白人童星代表的是一種主流意識形態方面的審美觀,這種意識形態的影響正如希臘神話中的塞壬女妖用妙曼的身姿與歌聲一般向佩科拉哼唱“喝下去吧,你會變得和我一樣美麗”。其次,藍白色杯子里盛滿的牛奶,潔白、甜蜜與芳香,增強了主流意識形態的魔力,迷惑著小女孩,讓她貪婪地侵占全家人的牛奶,不惜迷失自我也要投身于這美妙的白色漩渦。佩科拉寄宿在黑人麥克迪爾家里的時候,能在一天內喝完三夸脫(約2.84升)牛奶。這種對牛奶超乎尋常的狂熱在派克看來是具有毀滅性的:“這種親密關系的危險在于她對杯子的熱愛促使她貪婪的喝光了全家喝的牛奶,這種狂熱最終以佩科拉精神錯亂得以告終。”[4]614因為佩科拉對幸福與關愛的渴望,使其無論是對實體的牛奶杯和牛奶,還是對其中代表的意識形態與權力話語都極度迷戀,乃至具備了貪婪的“胃口”。貪婪的“胃口”無節制地吞噬食物時,這個群體中的其他成員也被剝奪了享受食物與獲得營養的權力,同時“胃口”的主體也被吞下的白人美學與意識形態逐漸反噬。
佩科拉除了對牛奶的狂熱外,對甜食也有著不同尋常的迷戀。在17世紀與18世紀的美國南方蔗糖種植園,制糖業的飛速發展與黑人奴隸制度密不可分。制糖業的發展史既是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擴張史,也是黑人奴隸的壓迫史。糖作為不能飽腹的食品,給白人種植園奴隸主帶來了巨大的財富與權力,給黑人留下了奴役壓迫的傷痛。結合黑人奴隸制的歷史,派克認為,由于糖是奴隸主種植園的主要產品之一,在莫里森的作品中,糖與甜品具有特殊涵義,他們往往象征著種族與性別力量[4]608。佩科拉去糖果店買糖的經歷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黑人言語上的無能感與所遭受的屈辱。當佩科拉走進糖果店時,她默默忍受著白人店主歧視的折磨,用比嘆息聲高不了多少的微弱聲音說到:“那個。”黑黑的小手指著商品櫥柜里的瑪麗·珍糖果。“每張淺黃色的糖紙上都印有一個頭像,瑪麗·珍的頭像……一雙藍眼睛從一個清潔舒適的世界里向外看著他……佩科拉認為那雙眼睛實在是太漂亮了。她吃了一塊糖,真甜。吃了糖塊就好像吃了那兩只眼睛,吃了瑪麗·珍,愛上了瑪麗·珍,也變成了瑪麗·珍”[14]43。糖紙上的白人女孩與甜蜜的糖果雖不能填飽胃口,卻能暫時麻痹饑餓的心靈。盡管“人們的身份由所食之物來限定”[17],佩科拉由于內化了種族主義話語,在強烈欲望的驅使下逆轉了這一模式,并試圖用食物改變其身份。她將她的身體乃至心靈當作祭品,誠惶誠恐中步入了“種族主義”的“圣殿”,吃下甜蜜的糖果,虔誠地期望與“圣殿”中的白人女孩融為一體。對于糖的象征意義,派克指出,“莫里森小說中那些特別熱愛糖的主人翁們總是拒絕認同非裔文化價值觀而擁護主流意識形態價值觀”[4]620。例如,《最藍的眼睛》中的佩科拉的媽媽波林與《寵兒》中的黑人女性賽斯和她的孩子寵兒,對糖都有著異乎尋常的鐘愛。這種欲望進而轉化為所尊崇的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糖的意象一旦與白人美學和意識形態相結合,即轉換成了一種佩科拉夢寐以求的權力話語。
佩科拉渴望著牛奶、奶糖、冰激凌、煎餅及一切甜蜜美好的食物。當她越迷戀瑪麗·珍糖果時,就越堅信作為黑人的丑陋與低劣;越渴望白人的優越權力,則越愿意內化種族歧視與權力話語并不惜獻身于白人主流意識形態的漩渦。佩科拉因為主體權力的缺失所以內心饑餓,因為無比渴望這種代表權力話語的食物,所以愈加胃口貪婪,導致主體的異化直至最后瘋癲。權力永遠是意識形態幕后的那只指揮棒,而她心甘情愿地充當權力的傀儡、胃口的奴隸,直至主體被完全摧毀。
二“奶油水果派”的特權與優越感
如果說佩科拉心甘情愿充當胃口的奴隸,在權力的漩渦越陷越深,那么她的同學莫麗恩、佩科拉父母與皂頭牧師無疑是她走向癲狂之路的重要推手。他們一個接一個嘲笑、歧視與傷害佩科拉,使她陷入日益膨脹的饑餓與欲望交織的網,無法自拔直至精神最終崩潰,瘋癲狀態下認為自己獲得了最藍的眼睛。借用福柯的觀點,權力是一種相互交錯關系復雜的網絡,“權力以網絡的形式運行在這個網上,個人不僅流動著,而且他們總既處于服從的地位又同時運行權力”[18]98。福柯認為權力產生的同時并支配話語的實踐,話語實踐的同時即建構主體,又強化與重申了包含權力法則的話語規則[19]28。佩科拉瘋癲之路的主要推手們也處于這樣的一張大網中,話語實踐的同時也操縱著權力法則。他們一方面自覺自愿地內化與復制種族主義的霸權話語,另一方面又將這種霸權體系不斷碾壓在佩科拉身上,加速了其主體的徹底崩潰與異化。
首先,莫麗恩的故事里豐富的食物意象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非裔群體對權力的渴望與種族主義內化的自我摧毀性。莫麗恩是個家境富裕、外形甜美的黑白混血兒,深受佩科拉學校師生的喜愛與崇拜。她的優越感與受歡迎的程度充分體現在她吃的食物中:
在餐廳里吃中飯時她從來不用尋找同桌伙伴——她選中的餐桌大家都會蜂擁而至。她打開豐盛的午餐盒,有切成四塊的雞蛋色拉三明治,帶粉色奶油的紙杯蛋糕,切成條狀的芹菜和胡蘿卜,還有深紅色的蘋果。讓我們只帶果醬面包的人感到無地自容。她甚至還喜歡喝牛奶。[14]53
與黑人小女孩克勞迪婭單調的果醬面包相比,莫麗恩精致的午餐是這些窮人家的非裔孩子們經濟上無法承受與期望的。莫麗恩精致的食物加上甜美的外形仿佛被包裝成了代表白人欲望、權力及意識形態的“奶油水果派”(黑人小姐妹弗麗達和克勞迪婭因為莫麗恩深受大家喜愛而滿懷嫉妒,為了尋求心理平衡,她們給莫麗恩取的綽號)。這種甜膩的奶油水果派似的人物傾倒與征服了大多數的黑人孩子和老師們。
正是這樣一個偶像似的人物為了玩弄與享受自己的權威,從黑人男孩手上救出受欺負的佩科拉,然后向佩科拉伸出虛偽的“友誼之手”,用一個冰激凌收買了她,結果又無情地打擊與侮辱了她:
佩科拉拿著兩勺橘子菠蘿味的,莫麗恩拿著黑草莓味的……“你們也應該來點兒,”她說,“他們有各種口味的。別吃蛋卷的尖兒。”她告誡佩科拉。她卷起舌尖,沿著蛋卷的四周舔了一圈,吃進一口紫色的冰淇淋,讓我看得好眼饞。我們正等著交通燈變燈。莫麗恩不停的用舌頭舔著蛋卷四周的冰淇淋。她不像我那樣用牙咬著吃。她的舌頭圍著蛋卷轉。佩科拉已經吃完了;很顯然,莫麗恩不愿將她的東西一下子吃光用盡。[14]59
小說中涉及到莫麗恩的食物描寫如此細致,甜膩的冰激凌瞬間融化于口腔,給人的滿足感盡管那么短暫,但此時卻成為了這個黑人偶像般的女孩彰顯特權的工具。她在打著圈兒舔舐冰激凌的同時,不僅享受了比佩科拉優越的特權,而且還操縱這種特權從心理上折磨著無法享受這種甜品的佩科拉。不難看出,食物在文本中被賦予了特殊的象征意義,已成為莫麗恩彰顯特權與優越感的權力工具。盡管同樣是黑人,莫麗恩明顯代表內化的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特權話語,并且不惜傷害著自己的族裔來維護這種特權話語。在佩科拉與莫里恩發生爭執后,莫里恩對著佩科拉罵道:“我就是可愛!你們就是難看!又黑又丑。我就是可愛!”[14]61短暫而虛偽的友誼無疑是場滑稽的鬧劇,這場鬧劇最終以兩個人的針鋒相對、相互咒罵與仇恨收尾。莫麗恩的話語讓脆弱的佩科拉再次從內心強化了“黑人又黑又丑,一無是處”的種族主義和權力美學觀念。
三“燙人”的水果餡餅與“毒藥般”的“愛”
最終將佩科拉推向欲望無窮深淵的卻是她的父母。從某種程度上講,佩科拉的父母成為了白人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幫兇,從精神與肉體上摧毀了自己的女兒。佩科拉的母親波林有著極強的自鄙情結,終日生活在絕望中,她認為她的女兒乃至家庭每個成員都丑陋不堪,于是一度沉溺于好萊塢電影的夢幻世界聊以自慰。波林坐在電影院里,一邊看著電影里的幸福麗人與完美生活,一邊咀嚼著甜蜜的糖果,只有在這一刻她才能暫時逃離困頓潦倒的生活,為自己尋到一片安寧愉悅的避風港。最終浪漫完美的愛情故事麻痹了她的心靈,甜蜜的糖果腐蝕了她的牙齒。自此之后,她的生活變得越來越糟。這里電影與糖果成為了那種如同塞壬女妖般既有吸引力又具破壞性的象征。好萊塢式的夢幻電影與甜蜜的糖果麻痹著她的心靈與胃口,使她對擁有無限權力的白人世界愈加癡迷。她對自己的家庭與孩子漠不關心,全身心投入到幫傭的白人家庭,因為這里沒有黑人的貧窮與丑陋,只有那種讓她著迷的幸福生活、完美世界與權利體系。由此她越來越迷失自我,與家人越來越生疏。當她安排佩科拉去白人家幫忙洗衣服的時候,她與女兒之間矛盾不斷激化。比如,當佩科拉從白人家的后門進時沒有看到波林,卻看到廚房里放著一盤餡餅。這盤餡餅是波林為這家白人小女孩準備的甜點。匆忙中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紫黑色的甜餡餅,被滾燙的糖漿燙傷。這時她沒能得到母親應有的關愛,相反遭到了母親的一頓毒打與咒罵。波林的話在佩科拉幼小的心里“比冒著熱氣的餡餅還要燙人”[14]86,佩科拉害怕地往后退縮著。然而波林繼續罵道:“把衣服拿上,趕緊滾出去,我也好把這一地的東西清掃干凈。”[14]87她的咒罵在佩科拉眼中好似“爛漿果一樣”朝她襲來。母愛本應該如剛烤好的漿果餡餅般甜蜜溫暖,在佩科拉的故事里卻變質成了有毒的爛水果。波林只關心白人女孩能否吃到她做的餡餅,白人家的地板干凈與否,而自己應有的母愛乃至女兒的尊嚴卻被她無情地踐踏在地上。餡餅這種甜食對于窮困的黑人來說無疑是一種奢侈品,而這種奢侈品是溫飽線上掙扎的黑人無法企望得到的。一盤打翻在地的餡餅讓波林無情地踐踏女兒的自尊,加劇了佩科拉的自我憎恨,并加速了種族主義話語的內化。這樣的黑人母親被種族主義話語閹割了母親的功能,并自覺自愿地保衛為白人家庭烤制的冒著熱氣的甜餡餅,捍衛象征凌駕黑人之上的白人價值觀與權力體系。
佩科拉的生活中從來沒有溫情的愛存在過,父母的愛從來都不曾存在,因此她內心對愛的渴望愈加強烈。也正因為這樣一個黑人女孩極度缺乏愛與被愛的權力,缺乏表達自我與得到認可的權利,所以對權力的渴求愈加強烈,最終淪為父親獸欲的犧牲品。從小說中可以看出佩科拉父親也許曾經試著去愛自己的女兒,然而種族主義霸權話語已然內化,父親的主體由于遭受白人的歧視與凌辱早已異化,這種霸權話語不僅閹割了佩科拉母親母愛的功能,同時也閹割了父親的父愛功能,使正常的父女關系扭曲變態成亂倫。正如小說描述的,他對佩科拉的撫摸是致命的,他的愛就像毒藥一樣讓佩科拉原已痛苦的生活更為窒息。父親亂倫的愛讓佩科拉懷上了孩子,受到世人的譴責與唾棄。
絕望無助中她來到了黑人社區皂頭牧師的家里,然而騙子牧師的“幫助”卻成為壓垮佩科拉的最后一根稻草。皂頭牧師打著上帝的旗號實施著心理醫生的功能,這賦予了這個混血黑人男性雙重的話語權威。這種話語權威復制了父權制和主流社會的權利體系和審美標準,促使牧師從內心深處理解佩科拉想要一雙藍色眼睛從而獲得美麗與認同這一愿望。然而虛偽的假牧師卻誘騙佩科拉用毒藥毒死他厭惡已久的一條老狗,并告訴佩科拉,“把這吃的給睡在陽臺上的那條狗。一定要讓它吃了。要特別注意它的表現。如果沒有異常,你就知道上帝拒絕了你的請求。如果狗的舉止反常,你的請求在一天之后就能滿足”[14]138。雖然感到惡心與恐懼,毫不知情的佩科拉最終用沾了毒藥的腐肉毒死了皂頭牧師討厭的老狗。皂頭牧師誘騙佩科拉用“吃的”毒死老狗的同時,佩科拉飽受摧殘的“自我”因為長久受困于欲望與權利交織的網,極度扭曲與異化,慢慢“麻痹致死”。于是癲狂中的佩科拉終于相信自己得到了一雙最美的藍眼睛。
四結論
托尼·莫里森借女主人公佩科拉的瘋癲,證明了非裔女性瘋癲是父權文化與霸權文化雙重壓迫的產物,也反映了非裔女性長期缺失關愛與認同、遭受多方面歧視、主體異化、身心極度扭曲并且缺失話語權的生存現狀。如果以福柯的觀點來看瘋癲,“雖然(瘋癲)是無意義的混亂,但是當我們考察它時,它所顯示的是完全有序的分類……遵循某種明顯邏輯而表達出來的語言”[20]97。瘋癲表現出來的非理性話語是對權威的抗爭,從某種意義上講最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質。正如同小說最后一章佩科拉在瘋癲后和她臆想中的朋友有大段意識流般的對話,這也是她長久失聲后第一次清楚地言說自我并表達了對權威的抗爭:她認識到自己缺少朋友而且很孤獨,她不愿再與莫麗恩做朋友,她意識到大家對她存有偏見等。非理性的話語借由瘋癲的佩科拉之口實際表達的卻是顯而易見的真理,也反映了種族歧視下黑人女性糟糕的生存狀況以及痛苦感悟。因此福柯才會認為瘋癲往往會比“理性更接近信服與真理,比理性更接近理性”[20]112。
回顧佩科拉瘋癲之路所涉及到的食物意象,從她最初對牛奶、糖果有著不同尋常的渴望,慢慢發展淪為“胃口”的奴隸,再到她身邊朋友、親人用饑餓與欲望交織的權力之網一步步將其囚禁直至墮入瘋癲的深淵,佩科拉一直是一位可悲的犧牲者或者說是白人價值觀與權力體系的殉道者。在欲望與權力的漩渦中,她迷失了自我,千方百計尋找出路以獲得白人世界的認同。她天真地相信一雙藍色的眼睛能徹底顛覆自己的命運,最終在父權文化與霸權主流文化雙重壓迫下,受困于欲望與權力交織的網絡,非裔女性欲望與“胃口”一步步扭曲,導致主體異化甚至癲狂,最后只有借瘋癲的言語言說自我。莫里森在敘述佩科拉瘋癲過程中借用豐富的食物意象再現了非裔女性在父權文化與主流意識形態壓迫下“自我”嚴重扭曲異化的現狀以及非裔女性長久壓抑的欲望。這種帶有強烈女性色彩、非理性、反傳統的運用食物意象言說欲望、反思權力關系的敘事語言,賦予了“失聲”已久的非裔女性群體新的聲音,從而解構與顛覆了西方/白人傳統文本的話語權力體系。
參考文獻:
[1]COUNIHAN C M. The Anthropology of Food and Body: Gender, Meaning and Power[M].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2]BLODGETT H. Mimesis and Metaphor: Food Imagery in International Twentieth-Century Women’s Writing[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4,40(3).
[3]CHERNIN K. The Hungry Self: Women, Eating, and Identity[M]. New York: Times Books, 1985.
[4]PARKER E. “Apple Pie”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Appetite in the Novel of Toni Morrison[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98,39(4).
[5]WARNES A. Hunger Overcome: Food and Resistance in Twentieth Century African-American Literature[M].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4.
[6]CARRUTH A. “The Chocolate Eater”:Food Traffic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oni Morrison’s Tar Baby[J]. Modern Fiction Studies,2009,55(3).
[7]HILL C E. Three Meals: Eating Culture in Toni Morrison’s Tar Baby[J].The Midwest Quarterly, 2012,53(3).
[8]陸薇.“胃口的政治”:美國華裔與非裔文學的互文性閱讀[J].國外文學,2001,(3).
[9]王晉平.心獄中的藩籬——《最藍的眼睛》中的象征意象[J].外國文學研究,2000,(3).
[10]李霞.論《最藍的眼睛》中的食物意象[J].理論月刊,2010,(12).
[11]辛斌.福柯的權力論與批評性語篇分析[J].外語學刊,2006,(2).
[12]MICHELE B.The Politics of Truth: From Marx to Foucault[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3]MORRISON T, MCKAY N. An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J].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83,24(4).
[14]MORRISON T. The Bluest Eye[M].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70.
[15]FENG P.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7.
[16]FOUCAULT M. The Subject and Power[C]//DREYFUS H L, RABINOW P.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7]LINDLAHR V. You Are What You Eat[M]. New York: National Nutrition Society, 1942.
[18]FOUCAULT M. Power/ Knowledge[M]. Bright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19]米歇爾·福柯.必須保衛社會[M].錢瀚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0]米歇爾·福柯.瘋癲與文明:理性時代的瘋癲史[M].2版.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
[責任編輯:唐普]
作者簡介:劉芹利(1979—),女,四川宜賓人,四川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廳面上項目“美國少數族裔女性文學中的食物情結”(11SB050)、南昌大學肖明文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美國南方女性小說解讀研究”(14CWW023)之成果。
收稿日期:2015-01-05
中圖分類號:I712.0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0-5315(2016)01-01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