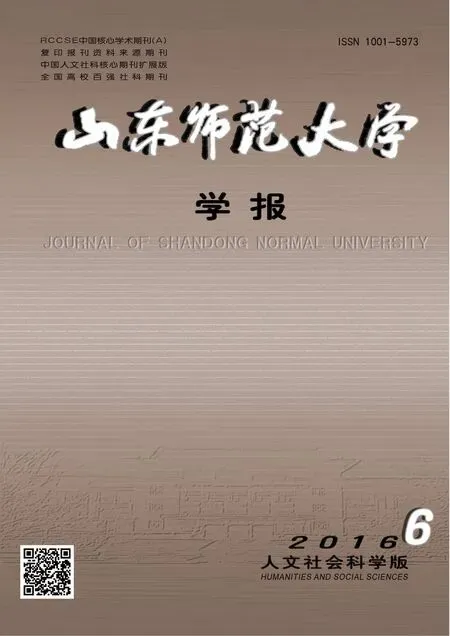“諸眾”還是“人民”?
——從《大同世界》看西方左翼內部關于革命主體的論爭*
李 靜
(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100871 )
“諸眾”還是“人民”?
——從《大同世界》看西方左翼內部關于革命主體的論爭*
李 靜
( 北京大學 中文系,北京,100871 )
國內學界已經熟知斯拉沃熱·齊澤克、阿蘭·巴迪烏等人針對邁克爾·哈特、安東尼奧·奈格里合著的《帝國》一書所做出的批判。然而,《帝國》三部曲的后兩部《諸眾》《大同世界》卻沒有引起國內學界足夠的重視。在《大同世界》一書中,哈特和奈格里針對齊澤克、巴迪烏等人關于諸眾能否成為革命主體以及諸眾斗爭的方向性等問題提出的質疑,做出了嚴肅回應。哈特、奈格里認為,“諸眾”是在“非物質勞動”中逐漸生成的不同于“人民”的革命主體。諸眾自發地形成革命的組織與紀律,不再依靠外部力量的領導,進而持續地對“帝國”發起沖擊。這場論爭為我們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經驗以及當下政黨政治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因而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大同世界》;諸眾;人民;非物質勞動;生命政治
國際數字對象唯一標識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6.06.007
2000年,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思想家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與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合著的《帝國》甫一出版,就在國際左翼思想界引發了巨大轟動,圍繞該書的討論層出不窮。*①例如羅崗主編的《帝國、都市與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一書,就收入了部分西方左翼思想家的討論。2004年和2009年,兩人合著的《諸眾》與《大同世界》相繼在美國出版,至此“帝國三部曲”*②三部曲分別為:《帝國》(Empir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諸眾》(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2004 )和《大同世界》(Commonwealth,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最終完成。前兩部曲《帝國》和《諸眾》分析了全球權力秩序的當代變遷,認為 “帝國”(empire)是取代帝國主義的新的全球主權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去中心、無疆界與超民族國家等。進而,一個差異的、多元的、自由流動的新主體,亦即“諸眾”(multitude),將取代現代民族國家對應的“人民”、“階級”等范疇成為新的歷史主體。《大同世界》則在前兩部曲的基礎上,將批判矛頭對準了以私有權為核心的財產共和國(republic of property),在政治和經濟的層面上重新思考了“共同性”(the common)的問題,進而重新定義了共產主義,其理論旨歸在于努力去創造一個共同財富(commonwealth)的新世界。“帝國三部曲”由破到立,層層遞進,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理論構想,可謂西方當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的最新成果。
然而遺憾的是,盡管國內馬克思主義學界也曾熱議過《帝國》,但卻尚未充分認識到后兩部著作的價值,其中尤以《大同世界》的接受情況為甚。*③《大同世界》的中譯本于2015年7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而《諸眾》一書迄今尚沒有中譯本。事實上,正是在《大同世界》中,哈特、奈格里認真回應了馬舍雷(Pierre Macherey)、拉克勞(Ernesto Laclau)、維爾諾(Paolo Virno)、巴里巴爾(Etienne Balibar)、阿甘本(Giorgio Agamben)、齊澤克(SlavojZizek)和巴迪烏(Alain Badiou)等人對“諸眾”理論提出的批評。*針對“帝國三部曲”的批評,除了來自激進左翼之外,還有來自馬克思傳統政治經濟學角度的批評,后者以阿瑞吉和大衛·哈維的批評為代表。比如,哈維認為,哈特和奈格里并沒有建立起一套金融分析,沒有觸碰資本通過貨幣和信用卡的生命政治策略腐化諸眾共同性的這一難題。這雖非本文論述重點,但無疑是爭論的另一重要向度,值得重視。尤其是針對齊澤克與巴迪烏的批評所做出的回應,最能代表哈特、奈格里的思維方式。
論爭雙方的核心話題是“諸眾”能否成為現實的革命主體以及反抗斗爭的方向性問題,這將直接關涉到“大同世界”的革命籌劃是否具有現實性。而中國革命中人民戰爭的歷史經驗也與諸眾理論存在對話關系。“人民”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是否必然為“諸眾”所取代,同樣是值得深思的問題。在人民戰爭的“對立”視域中考察諸眾理論,不僅會進一步推進關于諸眾理論的思考,更會為我們反思中國革命的普遍經驗與直面政黨政治危機提供寶貴的契機。
一、《大同世界》的回應之一:“諸眾”能否成為革命主體
“共同性”(the common)是《大同世界》中最為核心的概念。它既指物質世界的共同財富,又是社會生產的結果以及社會交往與再生產的前提,比如語言、知識、情感等。《大同世界》的前三章便是對妨礙“共同性”發展的三大阻力——“共和國”、“現代性”和“資本”——進行的分析,后三章則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套創造更多的“共同性”的理論方案。在由破到立的“關節”處,哈特和奈格里系統回應了關于“諸眾”理論的兩個關鍵性質疑。在第三章臨近收尾處,他們寫道:“我們看到,最具生產性的批判和挑戰主要集中在兩個核心問題上:一個涉及諸眾采取政治行動的能力;另一個涉及其行動的進步或解放特征。”*[美] 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1頁。
哈特、奈格里在書中回應的第一個質疑是諸眾沒有政治行動的能力,無法成為革命主體。按照西方主流的見解,人可以分為兩個部分:zoē和bios。前者是指動物性的、欲望性的生命,后者則屬于城邦性的、公民性的生命。因此,經濟領域被認為是完全自足的,勞動者只關注物質性需求,而沒有自覺的政治訴求。例如阿倫特就認為zoē是屬于經濟層面的,僅需純粹私人的動物性滿足,這與屬于政治層面的bios判然有別。她甚至說:“按照古代思想,‘政治經濟學’本身就是個詞語的矛盾,因為任何‘經濟的’事情,即與個人生命和種族延續有關的一切,按定義都是非政治的家庭事務。”*[美] 阿倫特:《人的境況》,王寅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頁。如是觀之,作為生產者的“諸眾”似乎并不具備政治行動的意愿和能力。
阿倫特的這一觀點揭示出諸眾理論一般批評者的邏輯前提。而在西方左翼思想界內部,同樣存在對于諸眾政治行動能力的質疑。例如,馬舍雷與拉克勞就認為“諸眾”只是通往政治行動的過渡角色,而非革命主體本身。在他們看來,即使諸眾具備政治行動的能力,其雜多性、流動性與不可化約性也將阻礙其政治行動能力的發揮,有可能導致其無法完成政治性的集體行動。諸眾要想成為現實中的行動主體,就必須依靠工會、政黨等外在的組織力量。
馬舍雷認為諸眾具備的只有革命潛能,一旦采取政治行動,他們便不再是諸眾,否則將無法做出政治決斷和革命行動。而拉克勞也持有相近觀點,他認為政治行動的主體必然是人民,人民“因其統一性而具備進行政治行動和決斷的能力”*[美] 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2頁。。
面對這些質疑,哈特與奈格里在《大同世界》中堅持了諸眾可以成為革命主體的主張。對此,需要回到兩人的自主主義的思想脈絡中加以理解。他們始終認為,對于統治者的反抗是第一位的,相對于統治權力來說具有優先性。在此基礎上,他們創造性地發揮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論。“生命權力/生命政治”(biopower/biopolitics)這一對概念在福柯筆下并沒有嚴格的區分,都是指調控生命要素(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等)的權力形式。而哈特、奈格里則貫徹了毛澤東“一分為二”的主張,將“生命權力”和“生命政治”區分開來。“毛澤東的這個口號抓住了我們在本章所分析的資本的危機。生命政治勞動變得日益具有自主性,并且變得與資本主義管理和控制日益具有對抗性,資本越來越難以將勞動整合進其統治結構中。”*[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25頁。也就是說,帝國不只創造了生命權力(biopower)這一統治方式,更孕育了摧毀帝國本身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因此,統治實際上并不依賴于統治者的意志,而是受制于被統治者的反抗。這便是反抗之于統治的優先性。
哈特、奈格里認為,在后福特制時代資本運作方式和主體生成方式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相應地,主體的反抗形式也將發生變化。由此,他們提出“諸眾”可以成為新的革命主體,而“諸眾”的政治行動能力正是在后福特制時代全新的生產方式中逐漸生成的。
具體而言,自動化機器生產體系的出現使得人與生產工具的關系發生了倒置。在自動化機器生產體系出現之前,工具是工人的器官,工人以其技能和活動賦予工具以靈魂。但在機器化大生產之后,“機器則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過在自身中發生作用的力學規律而具有自己的靈魂”*《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1頁。。在這一過程中,人的直接勞動越來越貶值,而生產工具,比如機器的生產卻變得越來越重要。因此,固定資本和生產工具的再生產也就越來越成為了資本增殖的主要方式。那么,相對剩余價值的形成也就越來越依賴于社會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提高,而不再是工人技能的提高。正如阿爾都塞所言*奈格里曾于1978年應阿爾都塞的邀請,在法國巴黎高師講授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可以說,如果沒有對馬克思《大綱》的創造性解讀,就沒有自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奈格里在1978年寫就的《〈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Marx Beyond Marx: 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是理解“帝國三部曲”的一把鑰匙。奈格里與阿爾都塞雖在《大綱》的文本評價上存在分歧,但都非常關注文本中對革命主體性問題的論述。,為了盡可能地擴大社會生產力,“勞動力技能的再生產(作為大趨勢)傾向于越來越少地(通過生產內部的學徒期)‘當場’獲得,而是越來越多地在生產之外,通過資本主義的教育制度以及其他場合和機構來完成”*[法]阿爾都塞:《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孟登迎譯,陳越:《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4頁。。因此,在自動化機器大生產的時代,勞動者直接投身物質生產的比例越來越低,且越來越成為了機器的從屬部分。相較于他們勞動技能的提高,機器的更新換代以及與此相關的教育、科技與管理制度的完善越來越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途徑。
上述觀點似乎印證了福柯一脈思想家的觀點,即資本強大而全面的規訓力量已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在這一背景下,勞動者自然也就逐漸被“去技能化”,其能動性隨之日益弱化。但是,以莫利茲奧·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為代表的意大利自主主義思想家們對此卻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們雖然也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已經由工廠的四道圍墻內擴大到了社會的方方面面,但卻更看到了生產者在這一過程中具有的能動性。這一全新的生產過程被他們命名為“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按照拉扎拉托的定義,“非物質勞動”是指“生產非物質商品的勞動,例如一種服務,一種文化產品、知識或交流”*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90. 關于非物質勞動的具體定義,參見Maurizio Lazzarato, “Immaterial Labor”,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ed.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133-147. 該文中譯參見[意]拉扎拉托:《非物質勞動》,收于《帝國、都市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其勞動方式是合作、交往與分享,其勞動產品包括信息、文化、知識、情感與服務等形式。非物質勞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越來越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了決定資本主義剩余價值攫取程度的關鍵性因素。
非物質勞動不僅使得工廠和社會的界限被打破了,勞動時間和非勞動時間的界限被打破了,更意味著勞動主體與勞動客體的界限被打破了。哈特、奈格里這樣說道:“在生命政治的語境下,可以說資本不僅吸納了勞動,而且吸納了作為整體的社會,或者說是社會生命本身,因為生命既是生命政治生產過程的要素,也是其產品。”*[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13—114頁。在生產資本主義商品的同時,更有文化的社會勞動者也被生產出來。換句話說,“生產者和產品都是主體:人既生產,也被生產。”*[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09頁。勞動者的生產與勞動對象的生產合二為一,生產發展的程度越高,勞動者的能力也就越強。因此,勞動者的自主性、能動性以及反抗資本的可能性也就重新被發掘出來了。在這點上,非物質勞動也就相當于帝國時代的生命政治。
在馬克思看來,只有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才能滿足所有人的物質性需求,徹底把人從純粹的經濟生活中解放出來,保證每個人自由多元地發展。而哈特和奈格里則看到,以合作、交往與分享為主要形式的非物質勞動能夠打破經濟/政治的二分法,賦予勞動者以自主性。在他們看來,經濟生產的過程不再被分解為生產流水線上一個個孤立的原子,相反,建立在自主、交往、協作與創造力基礎上的非物質生產(亦即生命政治的生產)日益具備了政治行動的能力。如他們所言,諸眾“在經濟領域所出現的能力,在政治領域也讓民主組織的發展具備了可能性”。*[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73頁。
哈特、奈格里筆下的政治,已經不再是福柯所謂的規訓、監視或治理,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協同行動”。在他們的論述中,諸眾的反抗并不依賴于外在力量的組織領導,而是內在于非物質生產的過程。對他們而言,諸眾是唯一具有行動能力的革命主體,而且他們的能力趨于無限。因此,在回應了“諸眾能否成為革命主體”的質疑之后,一個更為關鍵而復雜的問題也就被他們提了出來,即如何在非物質生產的過程中持續地“制造”諸眾,從中展開自主的政治籌劃,更好地發揮其革命性。
二、《大同世界》的回應之二:在持續革命中“制造”諸眾
在闡釋了諸眾足以成為新的革命主體的論斷之后,哈特、奈格里需要面對的另外一個關鍵性質疑在于,諸眾的行動是否一定導向進步與解放。從20世紀的人類歷史來看,無產階級可以是共產主義的群眾基礎,也可以是納粹主義的滋生土壤。究竟是倒向共產主義,還是倒向納粹主義,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是哪個組織領導了他們。對諸眾而言,外部力量顯然是不可依靠的。可倘若不借助外部力量,諸眾僅憑其自發性進行的政治行動又如何保證其進步性與解放性呢?上述對諸眾斗爭方向性的質疑,構成了對于這一理論更為根本的挑戰。
例如,意大利自主主義思想家維爾諾就認為生命政治生產具有兩面性,“任何對諸眾積極政治能力的討論,都要清醒地認識到其消極作用”*[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3頁。。法國學者巴里巴爾認為諸眾的概念缺乏內在的政治標準,如同航程沒有舵手,無法預知前進的方向。在激進哲學的脈絡上,齊澤克和巴迪烏認為諸眾并非具有進步和反動的兩面性,而是必然與現實的統治力量結盟,并不具備解放的能力。齊澤克徹底否定了資本主義會自發地生產出自己的掘墓人,諸眾的反抗不過是在重復和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統治;巴迪烏亦認為僅憑權力內部的因素就想逃脫權力宰制,無異于癡人說夢,結果反倒推動了現實權力的發展。
在《哈特和奈格里為21世紀重寫了〈共產黨宣言〉嗎?》一文*[斯洛文尼亞]齊澤克:《哈特和奈格里為21世紀重寫了〈共產黨宣言〉嗎?》,何吉賢譯,羅崗:《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知識分子論叢”第4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頁。此文也曾以《〈帝國〉:21世紀的〈共產黨宣言〉?》(張兆一摘譯)為題發表于《國外理論動態》2004年第8期。中,齊澤克批評了哈特、奈格里并沒有對當前的歷史條件作出馬克思式的分析,認為《帝國》仍是一部前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事實上,哈特、奈格里并不缺乏政治經濟學的洞見。齊澤克的犀利之處在于,他嗅到了哈特、奈格里的方案即便是馬克思主義的,也有淪為考茨基主義的可能。齊澤克指出,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即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借用拉康的術語,這是資本主義永遠無法真正克服的“原始性創傷”。資本主義的存在就是要不斷克服這個“原始性創傷”給其帶來的困擾,這反而成為了資本主義不斷發展的動力。*參見羅崗:《“機器論”、資本的限制與“列寧主義”的復歸》,羅崗:《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知識分子論叢”第4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哈特、奈格里即便像馬克思那樣找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也只是意味著他們找到了資本主義揚棄“舊我”與繼續發展的動力。這與真正克服資本主義根本是兩碼事,亦即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未必一定導向解放政治,反倒有可能恰恰服務于資本主義自身的不斷完善。
與齊澤克的看法類似,巴迪烏也指出了諸眾斗爭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同構關系。他發現:“奈格里的信念總是認為在系統中存在著為革命政治或者解放政治創造新事物的資源。他總是堅信資本主義的強力同時即是諸眾的創造力”,所以“事件在奈格里那里是不必要的,因為在解放運動中仍有某種結構性的東西”*[法]巴迪烏:《飽和的工人階級一般認同》“第五問”,引自“人文與社會”: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0/607。。在巴迪烏看來,問題的解決顯然沒有這么樂觀,因為這“不能說是黑格爾意義上的辯證統一”。“事件”一旦被取消,資本主義現有的權力關系就無法被中斷。諸眾發展自我以及揚棄資本主義的政治訴求也就非常容易被現實世界中更為強大的資本運動邏輯所收編,結果反倒與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更具有一致性,而與建設“大同世界”的政治理想漸行漸遠。
在如何對抗資本主義的問題上,齊澤克等人主張“不是僅僅回到馬克思,重復馬克思的分析”,“還需要回到列寧那兒去”*[斯洛文尼亞]齊澤克:《哈特和奈格里為21世紀重寫了〈共產黨宣言〉嗎?》,何吉賢譯,羅崗:《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知識分子論叢”第4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5頁。。換句話說,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新發現列寧主義的現實可能性。因為對資本的反抗不可能從資本內部實現,它必須有賴于我們從外部介入。
資本內部生產出來的諸眾只不過是反抗的質料以及新社會的潛能,并非是新社會的現實。質料是沒有內在規定性的,它不僅可能發展出共產主義,還可能發展出工聯主義,更可能發展出納粹主義。究竟是哪一種結果,要看是誰領導了它。一度令西方左翼興奮不已的“阿拉伯之春”,不就正是被伊斯蘭極端主義收編了嗎?如果在這一根本問題上缺乏認識,那么在諸眾與歷史進步力量之間也就無法完全畫上等號。
巴迪烏在回應奈格里時指出:“人民,一無所有——沒有權力,沒有金錢,沒有媒體——唯有他們的紀律,這是人民得以強大的可能。馬克思列寧主義界定了人民紀律的最初形式,那就是工會和政黨。它們有許多不同之處,但歸根結蒂,這都是人民紀律的形式,是現實行動的可能。”*[法]巴迪烏:《飽和的工人階級一般認同》“第五問”,引自“人文與社會”: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c10/607。人民便是在諸眾這一質料上施加了形式而產生的。所謂形式,就是政治紀律與組織方式。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諸眾如何自發地揚棄帝國,而在于究竟是哪種紀律領導了諸眾,并將其塑造為人民,盡管這種紀律形式是一種全新的有待發明的紀律。這便是齊澤克等人給出的思想方案,從而與哈特、奈格里的主張構成了西方左翼思想內部的革命主體之爭。
在《大同世界》中,哈特和奈格里對上述質疑作出了系統回應。他們指出,上述質疑實質上是一種自發性與組織性的二元對立思維使然。在他們看來,組織性與自發性并非是矛盾的。諸眾的斗爭當然需要組織和籌劃,但其組織性必須自發地形成。任何借助某個外部力量來領導諸眾對抗資本主義的想法,不過是寄希望于某種超越的理念而已,進而陷入到“彌賽亞的狂熱”之中。他們認為,“帝國”沒有外部,沒有什么外部力量是能夠引導共同性(the common)并打擊“帝國”的。在這一點上,哈特、奈格里堅持了馬克思的基本思路,即掘墓人只能在資本主義內部自發地產生。
“是/成為(being)諸眾”與“制造(making)諸眾”在哈特、奈格里那里并不是相互對立的兩件事。“自發性和霸權并不是唯一的選擇。諸眾可以通過在共同性中所進行的沖突性或協作性交往而發展出組織自身的力量。”*[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9頁。針對巴迪烏“事件在奈格里那里是不必要的”的批評,二位作者回應道:
我們也考察了事件的生命政治觀念,但與那種將事件視為“自外而來”的觀念不同,在后者那里,唯一的政治責任就是忠于事件以及事件所昭示的真理,在事件到來之后維持紀律。持那種事件觀的人,只能靠彌賽亞的狂熱去等待另外一場事件的到來。生命政治事件就棲身在共同性生產的創造性行動中。的確,在創造行動中存在神秘的要素,但這是每天都產出自諸眾的奇跡。*[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39頁。
在巴迪烏那里,事件是對舊的連續性的中斷,并對新的連續性的開啟。但哈特、奈格里強調,諸眾就是在生命政治事件中不斷生產自己與制造自己的,新的世界正是在一次次“事件”中被逐步打開的,而不是如巴迪烏所理解的那樣,是通過幾次徹底的革命決裂就可以開啟的。在此,哈特、奈格里的持續革命論與巴迪烏的斷裂論劃清了界限。
為了說明諸眾革命的組織性與制度性,哈特和奈格里引入了葛蘭西的“消極革命”的概念。這是非革命時期的革命行動。葛蘭西強調“陣地戰”而非“運動戰”,在革命處于低潮時,不可能通過一兩次起義就推翻統治階級,而需要利用文化和政治領域內的一系列斗爭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我們今天面臨的并不是一種有限的暴力形式,而是持續不斷的、無終止的或看似無終止的戰爭形式。”*尹晶、朱國華:《帝國與諸眾的交鋒——邁克爾·哈特訪談》,《文藝理論研究》2010年第1期。與之相應,反抗也應當是多層次的、持續不斷的和無終止的。這是一個長期的拉鋸式的斗爭過程。換言之,這是場“沒有革命的革命”。它追求的不是一攬子式的奪取政權,而是各行各業的人們在各自不同領域斗爭的累積。
基于這一判斷,哈特和奈格里還提出了“接合與平行論”的構想。《帝國》中最重要的反抗意象是“躍擊的蛇”,而《大同世界》中的反抗意象則是扁平而多足的“蜈蚣”。不管是蛇還是蜈蚣,其實都象征著一個去中心、去等級、絕對多元與絕對民主的革命模型。他們認為,“只有在由平行論和雜多性所構成的生命政治斗爭領域,為了共同性的革命斗爭才有成功的可能”*[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4頁。。“平行與接合論”意味著不同類型的革命可以毫無障礙地統一于“共同性”的“最高指示”,所有的身份(特別是階級身份)在這一過程中都將被徹底棄絕。這無疑是對傳統階級斗爭觀念的否定。諸眾的組織性和制度性,正是在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斗爭中不斷構成(constitute)的,它們不是靜態的,而是運動發展著的。
通過比較哈特、奈格里與齊澤克等人的不同思路,可以清晰地看出論爭雙方觀點分歧與思維方式差異。例如,在1969年的紐約石墻事件后被美國政府默認的同性戀組織,以及在1970年代的意大利工人運動中深化的工人委員會,在哈特、奈格里眼中都是典型的諸眾組織。但在齊澤克那里卻只不過是資本主義自我更新的表現而已。這體現了“反抗先于權力”還是“權力先于反抗”的根本區別。前者容易采取內在性和連續性的視角,重視后者則往往傾向于外部性和斷裂論的視角。這便是論爭雙方的根源所在與現實所向。
三、重新發現“人民”:中國革命經驗對“諸眾”理論的修正
哈特和奈格里曾斷言帝國作為資本主義統治世界的新形式,必將代替帝國主義,并成為新的世界主權者。故而,對帝國的反抗不可能像對帝國主義的反抗那樣,通過兩大陣營對立斗爭或者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方式來進行,而只能通過內在揚棄的方式完成。這意味著當下的反抗不可能完全重復列寧的先鋒隊模式,憑借社會主義組織在帝國主義體系的外部與之展開對抗。
在哈特、奈格里看來:“在進步的力量中,沒有先鋒隊的位置,甚至也沒有葛蘭西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的位置。知識分子是且只能是一個激進分子,作為諸多奇異性中的一員,參與到共同研究的籌劃中,去制造諸眾。知識分子既非‘外在于行動’,去決定歷史的運動,也非僅作為‘旁觀者’對運動進行批判,而是需要完全‘參與進去’。”*[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95頁。“參與進去”的反面便是“外在于行動”的超越性思維。而超越性思維的結果,要么像傳統的無產階級先鋒隊那樣從外部“去決定歷史的運動”;要么就像阿甘本等人一樣,只是不斷地控訴資本主義的罪惡,其實質不過是“僅作為‘旁觀者’對運動進行批判”而已。而馬克思的辯證法則是一種內在性思想,需要從壓制性的力量中發掘出解放的因素。列寧和毛澤東既繼承了馬克思內在性思想的一面,又有各自關于階級專政的超越性學說。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傳人,哈特、奈格里選擇發揚的是前者,因為他們看到了后者可能滋生出斯大林主義式的專斷。
與之對應的是,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無論是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還是北歐、西歐的社會民主主義,都已不再具有真正的進步性。“社會主義政權對工業社會有效地施加了規訓,但一旦開始向生命政治生產過渡,社會主義規訓就變成其所需要的社會自主性和文化創造性的障礙。”*[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09頁。蘇聯能在1930年代迅速從落后的農業國轉變成為工業強國,正是因為它實施了有效的勞動規訓。然而,也正是這種勞動規訓反過來變成了“社會自主性和文化創造性的障礙”*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6-279.。這便是蘇聯模式走向僵化的根源。
在非物質生產占據主導的時代,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不再有效,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共同性”基礎上的共產主義方案。諸眾正是源于“共同性”生產中的全新革命主體。而選擇“諸眾”,也就意味著哈特和奈格里棄絕了帝國主義時代中的社會主義革命的主體——“人民”。
在《諸眾》的序言中,哈特和奈格里闡述了諸眾與人民的區別:
就傳統而言,“人民”是一個整一的概念,人群當然是以各種各樣的差異為特征的,但人民把這種多樣性縮減成了一致性,把人群變成了一種單一的身份:“人民”為一。與此相比,諸眾則是多。諸眾由內部的種種差異構成,這些差異決不會縮減成統一的或單一的身份——不同的文化、種族、族裔、性別和性取向;不同的勞動形式;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欲望。諸眾是所有這些個體差異的多樣性集合。*[美]邁克爾·哈特、[意]安東尼奧·奈格里:《〈大眾〉序言:共同的生活》,薛羽譯,羅崗:《帝國、都市與現代性》(“知識分子論叢”第4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1、52頁。原文中“Multitude”一詞翻譯作“大眾”,這里引用時都改成了“諸眾”。
簡言之,人民是一元的、均質的,諸眾則是多元的、異質的。人民是不可能憑借生命政治勞動就自動生成的,它需要外力的施加才能被塑造出來。例如,在主流的西方現代國家學說中,主權者按照自己的意志將復數的諸眾化約為了單數的人民。但這憑借的是一種外在的、超越性的力量。然而帝國卻是至大無外的,沒有力量能夠真正超越于帝國的范圍,任何試圖跳出帝國范圍的舉動都將最終阻礙新的革命主體的生成。所以,在哈特、奈格里的筆下,“人民”是前帝國時代的產物,而在帝國時代的非物質生產中是不可能產生出“人民”的。在哈特、奈格里看來,大工業時代的工廠空間需要各級領導者,所以在政治領域中也就需要領導、政黨和紀律;但在后現代,非物質生產讓生產空間內的自主組織變為可能,因此也就不再需要領導力量了。為此,他們在《大同世界》中設想了一套去中心、去等級、絕對民主平等的扁平組織方式。
盡管哈特、奈格里與阿甘本存在諸多思想上的分歧,但在反對同質化的“人民”概念這一方面,他們卻所見略同。阿甘本在《什么是人民》一文中*[意]阿甘本:《無目的的手段政治學筆記》,趙文譯,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7-46頁。,區分了大寫的人民(the People)和小寫的人民(the people)。他認為前者是政治性的建構,吸納了共同體中的所有人口,而后者則是碎片性的多樣的人民,他們成為了被排除出一定的政治共同體的“赤裸生命”。赤裸的小寫的人民始終對抗著作為統治者的大寫的人民。阿甘本將這一對抗關系稱為“分隔性結構”(structure of separation)。在他看來,大寫的“一”只是“多”的“表面”和虛構,“整一”、“單質”的人民必然在兩種人民的“內戰”中被還原為混沌的烏合之眾。
無論是阿甘本,還是哈特、奈格里,他們的理論追求都是將人民的“一”還原為諸眾的“多”。但這一“還原論”在本質上只是一種簡單的理論設想而已,況且是一種去歷史化的思維方式的產物。因為將所有的研究對象通通還原為現象上的復數,實質上擱置了對歷史情境的具體分析。還原論可以破解作為“一”的人民概念,然而卻無法在理論生產之外對當下危機與現實難題做出有效回應。在英國學者E.P.湯普森看來,“復數的階級”不過是一種描述方法甚至只是語言上的堆積——
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它把一批各各相異、看來完全不相干的事結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經歷中,又包括在思想覺悟里。我強調階級是一種歷史現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種“結構”,更不是一個“范疇”,我把它看成是在人與人的相互關系中確實發生(而且可以證明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英] 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錢乘旦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第1頁。
與“階級”這一概念的生成方式類似,人民也是一個歷史性的事實(fact),它唯一的定義方式便是在具體的歷史關系和相應的思想—文化建制中確立自身的意義,而不是一種真空環境中的概念推演。
以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為參照,“人民”正是一個多元的、運動著的、不斷生成的歷史動力與現實存在。它的內涵隨著革命實踐的推進而改變,這與西方政治學意義上的被主權者塑造出來的同質化的人民判然有別。事實上,在中國革命的歷史實踐中,人民本身即是共和國的締造者與主權者。這就意味著在中國革命中生成的“人民”與作為西方政治學概念的“人民”存在本質區別。
在中國革命中,盡管不得不堅守生存論意義上的“敵我之辨”,但包納異質性成分的統一戰線始終存在,并且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國成立前后開展的各類“改造”與“教育”運動中,原本被改造的對象先后轉化成為了共和國的人民。即便是阿甘本所謂的“赤裸生命”,也始終是爭取、教育與改造的對象。對于人民的改造與教育,極大地豐富了人民的多元性,同時不斷召喚出他們的潛能、力量與尊嚴。
其實,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是部分地符合哈特與奈格里的理論設想的,他們所主張的通過改造與教育人民進而賦予其反抗能力與真正主體性的方案,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得以實踐的。但遺憾的是,他們對于中國革命的歷史并不了解,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也并未進入他們的考察范圍。他們對于“諸眾”與“人民”兩者異同的論斷,完全是從西方社會的歷史與理論語境中作出的。在他們筆下,已為中國與蘇聯革命所實踐的先鋒隊組織并不是革命的必需品,而中蘇兩國的社會主義模式也被認為無法實現共同性的目標。盡管他們相當重視列寧與毛澤東的理論創見,但列寧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生成的歷史語境及其在艱苦實踐中的豐富經驗卻被他們忽略掉了。這是我們在吸取其理論啟示的同時,也必須加以注意的。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自主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之間也存在諸多相通之處。中國革命既體現了先鋒黨的紀律性,又多少含有一些自主主義原則。如果沒有后者,解放戰爭恐怕就不可能進行得如此順利,而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于社會生產的恢復也不可能如此成功地展開。在解放戰爭時期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中不僅包括了正面戰場的軍事行動,也包括了國統區人民“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第二條戰線上的斗爭。這就意味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既依靠紀律嚴明的人民軍隊,同樣也依靠國統區中各行各業群眾在自己領域內的反抗行動。這是中國革命不同于俄國革命那樣由先鋒黨決定一切的地方。而哈特與奈格里對于諸眾作為一種新的革命主體的期待,似乎可以在這一實踐形式中得到呼應。當然,新中國成立以后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出現的諸多失誤,也與未能運用好這一形式有關。確切地說,失誤的造成并非源自人民不具備自主性,而是由于人民的自主性未能被合理引導。
如何看待人民的自主性,始終是對于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作出反思時的核心議題。而哈特、奈格里與齊澤克、巴迪烏等人關于革命主體的論爭對于我們認識這一問題正具有獨到的啟示作用。尤其是諸眾理論所提供的新的視野,構成了我們理解中國革命的動力與前景時的重要參照。當然,這一理論本身的缺陷也是十分明顯的,畢竟廣大的第三世界還遠未達到這一構想得以展開所應當具備的后福特主義的社會條件。
與如何看待人民的主體性相連的,是怎樣在新的歷史條件中重新激活人民自主性的問題。在人民—政黨之間的血肉聯系,即政黨代表性出現某些偏差的當下,這無疑也是一個值得追問的話題。而對于這一問題的回答,同樣可以在這場革命主體論爭的延長線上展開。換句話說,既參照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修正哈特與奈格里理論的不足,同時也參照諸眾理論打開思考中國問題的新的視野,正是我們需要的一種思想立場與實踐態度。
責任編輯:寇金玲
Multitude or People: Argument over Revolutionary Subject by the Western Left Wing
Li J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ese academia has already been familiar with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sEmpireand Slavoj ?i?ek and Alain Badiou’ s critiques ofEmpire. However, the last two volumes,MultitudeandCommonwealth, in the Empire trilogy written by Hardt and Negri, haven’t attracted sufficient attention in Chinese academia. As to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i?ek and Badiou of whether or not multitude can be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 and the direction of multitude's resistance, there is a serious response inCommonwealth. Hardt and Antonio argue that "multitude", which is differemt from "peple", is the revolutionary subjects gradually formed in "immaterial" labor. Multitude can spontaneously form the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and discpline, no longer rely on the leadership of external forces, and give the "empire" constant strikes.This debate will provide us a new way of thinking about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of the plight of the current party politics.So, it also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Commonwealth;multitude; the people; immaterial labor; biopolitics
2016-10-30
李靜(1989— ),女,山西長治人,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D05
A
1001-5973(2016)06-008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