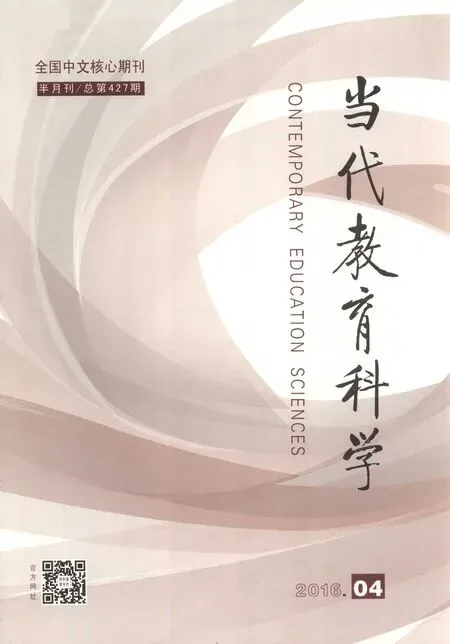當代西方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述評
●王艷霞
當代西方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述評
●王艷霞
摘要:自20世紀初期德國哲學家胡塞爾創立現象學以來,現象學以其“回到事實本身”的研究態度和“回到生活世界”的哲學取向,促成了20世紀歐洲大陸最重要的哲學思想運動之一——現象學運動。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無疑是西方現象學運動發展的產物。客觀上來說,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除了現象學自身固有的艱深、晦澀的局限性外,正如現象學本身所具有的主觀唯心主義性質一樣,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也同樣帶有濃重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然而,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面向教育實事,面向教育本身,回歸教師的日常教學生活世界,具有濃厚的人文意蘊和人性色彩。這在當今教師教育越來越工具性與技術化、實用性與技能化、功利性與形式化的今天的確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關鍵詞:教師教育;現象學;回到事情本身;生活世界
自 20世紀初期德國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1859-1938)創立現象學以來,現象學已存在了一百多年,然而,現象學的影響遠不止于哲學,并以其特有的世界觀、方法論,如“回到事情本身”(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的精神、“生活世界”(lived world)理論以及“本質直觀”、“懸置”、“還原”等哲學方法廣泛而深刻地影響了現代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領域。現象學對20世紀的西方哲學,包括教育學在內的其他學科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無疑是西方現象學運動發展的產物。
一、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的興起與發展
長期以來,由于近代現代主客二分的認識論以及由此發展起來的科學實證主義研究范式的影響,教師教育忽視了教師教學實踐的豐富性和鮮活性而過于重視理論的普適性和工具性。教師培訓的工具性與技術化、實用性與技能化、功利性與形式化使教師遠離自己的教學生活,忽視了對教學生活世界的關注和教師個體在教育實踐中的體驗與反思。教師教育變成了實用知識和技能的培訓,追求功利與形式,變成了意義缺失的教師教育而無須關注教育實事本身。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在對這一思想方式的質疑、批判的背景下應運而生。
追根溯源,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的興起與發展離不開現象學的理論滋養。現象學哲學是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的哲學基礎。20世紀70年代以來,教育科學領域發生了重要的“范式轉換”:開始由探究普適性的教育規律轉向尋求情境化的教育意義。正是在這種“范式轉換”的背景下,現象學以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思維方式以及“回到實事本身”的研究態度和“回到生活世界”的哲學取向被引入教育研究領域。
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的興起始于歐洲20世紀40年代,20世紀70年代已經影響到北美實踐諸領域,20世紀七八十年代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迅速傳播,并產生了國際化影響。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的范梅南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其代表作如 《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生活體驗研究——人文科學視野中的教育學》等被翻譯成多國語言,成為被廣泛引用的經典之作。
目前,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為教師教育提供了一種研究的態度和取向,一種獨特的視角和思維方式,但還只是作為教師教育的一種方法,遠遠還沒有在現代性這一意義上進行思考。隨著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的不斷成熟和判斷力的提升,這有可能成為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未來發展的趨勢和方向。
二、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的主要觀點
現象學首先是作為本體論意義的理論基礎引入教育領域的。在現象學哲學的總體背景下,人們開始關注教育的生活世界,回到事情本身,注重人的情感體驗與反思,探尋教育的價值與意義。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從現象學哲學的邏輯出發,用現象學哲學的世界觀、方法論分析和研究教師教育,為教師教育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和思維方式,這對教師教育的本體論建構和方法論探索有直接的啟示意義。
(一)“面向教育本身”的教師教育
現象學的綱領精神是“面向實事本身”。“回到事情本身”的現象學精神帶給我們的是對教育本身的理解。現象學“面向實事本身”的精神要求教師以自身的日常教學生活為起點,將教育生活體驗作為反思的對象,懸置已有的偏見以及自己已有的行為規范、價值觀和情感態度,“面向教育本身”。
1.教師培養:注重教育實踐
在現象學看來,現象本身即為本質,在現象之外不存在一個先驗的本質,現象本身可以自我顯現,現象會向我們顯現其自身而無需我們賦予其另外的本質。教育活動也是一種現象,也許教育的本質就是教育自身所顯現出來的,我們需要關注這種顯現。因此,我們應回到教育現象本身,即教育實踐去認識和了解教育現象。
范梅南(Van Manen,M.)注重教育實踐。他認為教師的知識是直覺的,教育行動依賴于在不確定的情境、思考規則和實踐中。[1]他在《實踐之實踐》中強調實踐邀請人們觀察學校生活世界的一般現象,[2]在《連接知識和實踐的途徑》認為基于不同層次的實踐而產生不同水平的反思。[3]蘭格威爾德(M.J.Langveld)認為教育學作為一門實踐科學是以分析生活世界之情境的實踐為先決條件的。他曾強調,“通過事先預設的理性前提是不能走進教育情境的”。[4]對于教育問題,他認為應多從現象學角度,而不是從教育思想的先入之見著手。他強調說,否定教育的先入之見,并不是要人們拋開自己的文化和歷史背景,而是要以此引導人們從此時此地的體驗的情境出發來看待問題,認識教育現象。
教育在本質上是培養人的社會實踐活動。教師的教學是一門源自實踐、運用于實踐的藝術。現象學“回到事情本身”的精神在教育實踐中就是回到教育的生活世界,注重教育實踐,面向教育實事本身。回到“實事本身”,就是要回到活生生的課堂教學中去,應當具有明確的意向性來還原教育生活的目的和本真形態。教育本身最根本的也就體現在教育發生的現場——課堂,教師的工作不是脫離了課堂情境的一種技術的和社會的勞動。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教師職業具有不可替代的實踐性質,而教師的培養其目的則是在教育實踐中培養具有教育智慧、判斷能力和豐富經驗的反思性實踐者。
現象學的教育實踐是一種“懸置”前見、“括去”偏見之下的行動,只有將已有意見懸擱起來才能獲得對教育本質的理解。當教師面對教育實事時,應該把有關這個實事的周邊東西“懸置”起來,排除干擾直接面對教育事情本身,形成現象學的視域,這樣面對的就是一個純粹的教育生活世界中的教育實踐本身,從而使教育的本源意義得以顯現。
2.課程與教學:采用案例與案例教學
“回到事情本身”的現象學精神啟發我們回到最原初的、前理論、前概念、未經定義的教育的“生活世界”中去,以“回到事情本身”的態度去面對教育中的各種問題和具體真實的情境,在教師教育中以豐富而鮮活的案例為載體進行教學,體驗原初的真實生活和教育情境。
范梅南在《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一書中認為,教育學存在于情感的親身體驗中——也就是說,在極其具體的、真實的生活情境中。[5]蘭格維爾德在其作品《教育學的科學本性》強調關注兒童和成人日常生活中的具體事件,要求每一位教育者直接地面對教育最原初的真實生活,在不斷實現教育意義的生活世界中顯現教育學自身的本質。
現象學“回到實事本身”的看待事情的態度和方法,要求“回到教育生活本身”,以恢復教育生活的本來面目。然而,“實事本身”的顯現不是通過固定的概念或抽象的理論,而是用不為概念所規定的一個個具體的案例顯現的。因此,教師教育應該減少抽象的理論知識的灌輸,加強聯系實際和案例分析是“回到實事本身”的體現。而一個個具體的案例是“實事本身”的顯現,是現象學生活世界中一個個鮮活、豐滿而又真實的情境的再現。以案例為載體的案例式教學不是單純的理論說教,而是在真實的教育實踐中、在課堂參與的過程性體驗中。案例教學引導教師在具體的時刻、此時此地的情境參與真實的體驗中,認識、思考真實體驗中蘊含的意義及存在的教育問題,有利于教師認識、理解教育,培養教師的教育機智。
3.教師培訓:注重教師生活體驗的寫作與研究
教師在日常的教育教學實踐中有各種各樣的經歷和體驗。然而,由于教育的技術化、工具化傾向,使得教師失去了對鮮活的生活世界及生活體驗的敏感性。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正是強調教育者(父母或教師等)拋開成人的一切先入之見、成見和偏見,站在兒童的角度和立場重新審視和反思日常生活及教育現象,通過生活體驗的寫作與研究回到實事本身,回到教育生活本身。
范梅南在《生活體驗研究——人文視野中的教育學》一書中向教育研究者介紹了如何從事現象學研究的寫作,認為現象學的寫作應從軼聞、故事等個別的案例開始,不追求宏大的理論框架,而是試圖從個案中尋找生活和教育的意義。通過軼事、故事等敘事形式的表達,教師在敘事過程中可更清楚地認識自我,彰顯自我的存在及自我的身份認同,也有利于教師思維的訓練、個人知識的管理和反思習慣的養成。同時,教師的生活體驗寫作亦是一種教育科研的基本方式,這使“教師成為研究者”獲得了基本的現實性。范梅南認為,寫作是檢驗我們思考的一種途徑。[6]通過生活體驗寫作,教師將成為敏行的反思性實踐者。
現象學“回到實事本身”的看待事情的態度和方法,要求“回到教育生活本身”,關注事情本身是什么樣子,不要先下診斷(prescribe)而是首先“懸置”前見,將事情如何在意識中顯現 “如其所是”地描述(describe)出來,讓人們知道事情本身(如教師或學生的體驗)“是什么樣子”,以恢復教育生活的本來面目。現象學所要求的是對“前概念”、“前反思”及原初的教育生活體驗的“還原”或“客觀”的描述,即對生活體驗本身的書面描述。
生活體驗寫作是一種隨機寫作。在描述過程中,教育者審視生活世界及教育現象,保持對教育學生活世界及教育現象的敏感性與親切性,在“現象”面前懸置自己的前認識和偏見,排除沉淀在意識的文化、歷史、知識的影響,以質樸、簡單、直接的語言及描述性語言全身心地投入到現象體驗的描述之中,呈現生活世界及教育現象,并要求教師在不斷“重寫”的過程中實現“描述”與“解釋”的統一。因此,教師的生活體驗寫作是促成中小學教師對日常的教學生活與教育實踐進行有效的反思與學習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
生活體驗研究是一種現象學的研究方法。它試圖通過對人類生活體驗或意義的研究而更好地理解人類的生活世界和各種現象,因此,生活體驗或意義是現象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現象學研究的目的在于獲得我們對日常生活體驗或意義更深刻的理解和解釋,從而回到事情本身。蘭格維爾德在其作品《教育學的科學本性》中強調研究教育生活體驗。范梅南則更進一步強調,做現象學研究意味著我們向生活發問,向生活體驗的方式發問。[7]教師按照現象學的反思方法進行生活體驗研究,可以使教師回到原初的教育生活世界,對教育事情本身原初的意義進行解釋,尋找奠基在教育生活世界基礎上的教育意義。生活體驗研究把教師帶到了對事情本身的“看”和“思”上來,可以真正實現對事情本身的本質認識。在研究過程中既須“入乎其內”——體驗生活世界,又須“出乎其外”——進行反思,“入”是為了獲得生動、豐富的感性材料,“出”是為了從研究情境中抽身出來,超越特定境域的限制以回到現象本身,把握現象的意義和本質。
在現象學理論中,人是思維的中心。“生活體驗研究”是解釋現象學的教育學研究方法,不同于科學主義的理性的方法論,而是以人為中心的解釋性模式。教育生活體驗研究包含三個主要環節:“懸置”的原理——投身并體驗教育生活;回憶與反思的原理——反思生活體驗;運用語言符號表述的基本原理——描述體驗與文本呈現 (寫作)。[8]現象學研究是對生活體驗本質的研究,而現象學研究的文本邀請我們與之對話,激活自己的生活經驗,喚起我們對自身經歷的反思,產生對生活體驗的共鳴性解釋與理解。
(二)回歸教師“生活世界”的教師教育
生活世界(lived world)是胡塞爾晚年出于對社會現實的關注,為批判實證主義、唯科學主義思維,挽救歐洲科學的危機而提出的。胡塞爾把現象學分析從超驗的自我和意識轉向了日常生活經驗的前反思生活世界。現象學中的生活世界是一個原初性的世界,是前概念、前理論、未經定義的,其出發點是出于對日常生活世界的關注。生活世界理論對于教師教育的啟示在于直接面對教師最原初的真實生活,關注教育生活世界的本真狀態。
1.教師培養:從教育生活世界出發
現象學關注普通日常生活經驗,注重具體經驗的反思,而不是理論的抽象。教師的經驗不是抽象的,而是生活化的,即在與學生的相處過程中觀察教育本身,體驗教育的意義。蘭格威爾德認為,教育必須從“生活世界”出發,因為只有“從對產生所有可能形式的人類生活世界的現象的理解出發”,我們才會“理解我們自己,理解我們的存在和生命的意義”,最重要的是“理解我們對其負有教育責任的人們的生活”。[9]
(1)在教育生活世界中生成教育智慧
胡塞爾認為,生活世界的本質是由生活在社會現實中人的意向性意識所決定的。人有意向性地意識事物,意味著人的意識總是指向一個方向并且是有意義的。當意向活動的指向聯系在一起就構成一個人的意向活動的世界視域,而這個世界就是胡塞爾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意向性意識是對傳統形而上哲學中主客二分思維方式的反動,旨在克服主客二分的二元對立的認識論模式,追求事物的本源性的統一。
人的存在以追求意義的方式生活著,教育是教師與兒童相處的一種具有教育意義的實踐活動,而教育智慧是由教育的意向性形成的意義構成物。范梅南認為,教育智慧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而教育智慧的現實表現即為教學機智。他在其專著《教學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中,以教師、父母和學生的生活經歷為原材料,以他獨到的現象學研究方法和豐富的教育經驗對教育學的諸多方面進行了深刻和有益的思考,探尋如何在瞬息萬變的生活情景中機智地采取行動。
教師是教育活動的組織者、實施者,因此,教師教育關注教師的技術層面,更關注教師的實踐智慧,即教師的教學機智和教育機智。范梅南認為現象學視野中好的教師應該是機智的教師。[10]教育本身是指向兒童的規范性活動,而不是一種技術或生產活動。“這種規范性活動不斷地期望教育以一種正確的、良好的或恰當的方式從事教育活動。”[11]
胡塞爾認為,任何意識活動都是意向性的,意向性是人的意識活動本身所特有的。教師專業成長的意向性就是關注教師在其教育實踐活動中如何認識其教育對象以及如何形成教育智慧。教師專業在本質上是教師在與兒童相處時所顯現出來的教育智慧,教師專業成長的過程就是教師在與兒童相處中形成教育智慧的過程,即教師在教育生活世界中生成教育智慧。它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教師的專業成長必須是指向兒童的。二是教師教育智慧是一個構造形成的過程,是在教師與兒童的相處中不斷形成的。[12]因此,教師只有回到生活世界,去追尋其與兒童相處的生活意義和教育意義,在教育生活世界中才有可能形成教育智慧。
(2)在教育生活世界中形成反思力
現象學關注的是日常的生活世界和生活體驗,強調對日常生活世界中所發生的現象和體驗的反思,對反思意識的研究構成現象學的主要任務。教師反思力的形成源自對教育生活世界體驗的反思。因此,范梅南認為,“讓我們直接面對學生的生活世界和生活體驗,并對它們做有益的反思,從而形成一種對教育具體情況的敏感性和果斷性”。[13]
在現象學看來,生活世界中最大的阻力不是來自未知,而是已知的“意見”“遮蔽”了我們的視野。在教育生活世界中,由于教育者受舊有的偏見、習慣、信仰和價值觀的影響,暫時蒙蔽了教育生活世界中的“新”意義。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反對那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和傳統承續下來的凝固的信念和理論,為了讓事物“赤裸”地顯示其自身,從各種理論模型中展露被遮蔽的現象,就要剝開人們在生活世界中所遭受到的道德、倫理、社會和文化的層層影響來發現這些“新”意義。因此,現象學主張要把認識對象的存在信念放在括號里,并且把作為經驗主體的人的存在信念懸置起來,只有這樣才能作出沒有任何先設的論證。現象學反思的對象是純粹的意識。因此,在反思過程中要求反思者與當下的生活情境保持一定的距離,也就是說,只有割斷與這些先入之見的聯系,懸置并超脫于經驗之外,進行高于生活的素樸性的反思,才能進入“純粹現象”的領域,向生活的素樸性回歸。
范梅南認為,“反思使教育者具有責任感”,“看待問題就會有新的視角和理解”。[14]在反思過程中,教育參與者將自己的心智與情感從當下的教育情境中抽離出來,將已有的成見、概念、理論和看法等懸置起來,超越特定境域的限制以期對那些教育現象、教育體驗所隱含的教育意義進行系統的理解和把握。范梅南在《反思實踐的認識論》認為,運用追溯人的最原初體驗的方法,首先直接關注學生的生活世界和生活體驗,獲取未經反思的生活體驗。在反思過程中,教師只有懸置舊有的經驗,關注日常生活中鮮活的生活體驗,理解兒童創造生活的可能性,關心學生的具體生活體驗,并在與孩子的相處中不斷反思自身的行為意識才能回到生活世界本身,從而提高教學的機智,實施適當的教育活動。
范梅南認為,“教育者生活的中心就是反思,這一點是無可質疑的。”[15]教師教育中要引導一線教師在教育生活世界中形成自己的反思力,主要可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加強對教育生活世界體驗的反思。另一方面通過閱讀教育故事進行文本反思。通過這兩方面的反思引導,教師在教育生活世界中逐步形成反思力。反思力的形成是教育智慧與教育機智形成的必由之途。
2.課程與教學:回歸教育的生活世界
由于受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的影響,教師教育的課程與教學忽視生活世界,習慣于用科學概念來描述教育,強調概念的演繹和邏輯推理,關注概念與概念、范疇與范疇之間的邏輯關系以及教育知識的規范性、系統性和邏輯性,重視教材的理論體系與知識結構,遠離了豐富生動的生活世界。
(1)課程:以教育生活世界為依托
在現象學視域中,教育世界被理解為“生活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課程理論受科學主義和技術理性的支配,致力于探尋普適化、客觀化的課程開發規律和程序,忘卻了教育起源于生活世界的事實。
范梅南認為,教育學應該在生活的世界中去尋找,探索教育學本質有兩條途徑:一是從建立一個教育理論著手,然后用理論指導實踐;另一個是從生活本身開始,通過反思與孩子的交往理解教育生活世界。[16]從生活本身開始,不是概念的邏輯建構,不是按照某個已經在先的規則邏輯地運作,也不是教師在教科書上習得的邏輯,而是來自生活世界的活生生的體驗。因此,教師教育課程內容的選擇要與現實的教育相適應,關注教師的生活世界和內在需求,回到教育生活本身。具體而言,在內容的選擇上突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一、重視教師作為一個專業人員面對教育所必需的基本素養。教師個體的成長是內在自我逐漸增強和外在培養相互結合的過程,需要教師從封閉的“罐裝”接近現實生活的教育。因此,教師教育內容要選擇那些真實教育過程中較為需求的內容。[17]二、從教師的專業發展來說,教師教育內容的選擇要從生活本身開始,注重人的內在需求和整體的發展。
(2)教學:師生之間形成互為主體的“人—人”關系
胡塞爾主張的生活世界還是一個主體間的世界。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亦譯為交互主體性)理論的提出使傳統認識論中主體對客體的認識轉向主體對主體的認識,實現了“主體—客體”認識論朝著“主體—主體”認識論的轉向。在現象學看來,主體間性是主體與主體關系的規定性,表現為理解、通融和共識。教育是在人與人、教師與學生的主體間性關系中展開的,教育關系集中地體現為師生關系。對于近現代以后的教育研究而言,教育被視為一種實體性存在,是為達到某一特定的目的而存在的可以操作、可以安排的工具或手段。在現象學看來,本真的教育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種關系。對這種關系的理解,不是基于對經驗的分析,而是基于本質直觀。它要求一種基于生活世界的對話形式的教育,把教師和學生都看作為主體,在主體間進行對話,相互自我建構。[18]現象學突破了原有教育研究視域中的盲點,突出了教育活動的兩個主體——教師和學生在其中的突出地位。范梅南在《教學中的教育學、美德和敘事認同》用了大量生動的故事來闡釋師生關系問題,認為教室中的交往總是關系性的。[19]范梅南曾說,教育活動的核心不僅是教師“教”學生的過程,更主要的是一種師生的關系,而且在本質上教育活動就應該是一種關系。
在教育活動中,師生的角色、地位不同,處在人生不同的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然而,教師和學生都是具有豐富的多樣性的完整的人、獨立的人,師生之間是“人—人”之間心靈的溝通和交往,是平等的對話與理解的交往的關系,師生之間不是“我—它”關系,而是“我—你”關系。因此,師生關系應該從一種基本的社會關系轉化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作為教師的人”與“作為學生的人”之間的關系。范梅南認為正是因為這一倫理基礎,我們的教育實踐才是智慧性的(thoughtful)和反思性的(re-felective)。”[20]
交互主體性既包含主體性的特征,又強調“交互”的含義,即同樣具有主體性的人與人之間是一種主體之間的關系。交互主體性為我們理解教育關系提供了現象學的視角,克服了傳統“主體—客體”認識論看待教育現象所遭遇的各種困境和窘迫,有助于我們在師生豐富的交互作用和關聯中理解教師與學生的真實關系。因此,教師教育應通過對話和交流達成主體間的理解,從外在規訓轉向體驗世界,從塑造轉向教化,從教師的個體道德轉向教育倫理。
3.教師培訓:走進教師的生活世界
教育是培養人的社會實踐活動,教師作為培養人的實踐者,首先面對的是日常的教學生活世界,也就是教師日常的教育教學實踐。可以說,教師的日常教學生活是其生活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以生活世界為其哲學立場的基點,認為教師并不是進行知識灌輸的機器人,而是有血有肉可以與學生進行經驗溝通的個體。教師教育不是理性堆積和灌輸的結果,而是在生活體驗中個體意向性意識形成的過程。因此,教師教育者要關注教師的日常教學生活世界及其對教師教育活動的體驗。然而,當我們有了諸多的理論之后,往往容易變得自以為是和想當然,很容易忽視教師真正的生活世界。范梅南認為,“生活世界”是教育工作者思考教育的邏輯起點。因此,教師教育者應將已經擁有的成見、概念、理論、看法等懸置起來,關注教師的種種生活體驗,走進教師的生活世界。
教師教育走進教師的生活世界,回歸教師的“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中的教師教育關鍵在于使這種教育體現出生活性的特色,其根本是使這種教育過程成為教師自主體驗、激發自我情感的過程。范梅南認為,“教育的生活世界是一個不斷地進行闡釋性思考和行動的實踐體驗。”[21]教師的教育生活世界是鮮活的、豐富的,也是生動的。只有將教師個人已有的教育生活經驗、生活實踐性知識挖掘出來,并與一般的教育教學“原理性知識”加以整合和對接,教師在接受外來理論時才能找到結合點,并進一步去思考是否要改變自己已有的行為規范、價值觀和情感態度等。教師教育應走進教師的“生活世界”,體現出它的生活特點,即從教師的生活意義出發來進行。
三、對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的評價
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是西方教育學者由于不滿教育中盛行的實證主義、理性主義和技術主義等科學主義范式而提出的一種新的研究取向。他們把教育理解為參與其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生活方式,在教育生活世界中去體驗,強調教育理論必須關注教育實踐,并對其進行反思。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從現象學哲學的視角,以現象學哲學的世界觀、方法論分析和研究教師教育。因此,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因其研究視角和思維方式的獨特、理論與方法的深刻及其研究的實踐品性而得到許多教育學者的青睞,然而,由于現象學哲學的艱深、晦澀、難以捉摸而令很多研究者望而生畏,因此同時也不斷遭到批評。
就教師教育而言,以前的教師教育研究往往脫離教師所處的職業生存狀態、教育生活情境和教師自身的實踐進行一種宏大敘事式的研究。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從現象學汲取理論營養,以現象學方法為方法論,不追求構建宏大的理論體系,不追求普遍規律,面向教育實事,回歸教師的日常教學生活世界,研究教育生活世界中的教育生活體驗,關注個體體驗的獨特性,承認個體體驗的價值,吸引更多教育工作者從事腳踏實地、基于教育生活體驗的教育研究。然而,現象主義教師教育思想卻不斷遭到批評。批評者一般認為,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所希望的還原是不可能的,主觀性太強、語言模糊;有的批評者還責備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沒有可以具體操作的程序;更有人認為太理想化,對實際問題的解決無益等。事實上,這些批評者往往沒有理解現象學中“現象”的所指、“現象”的特征以及研究的目的。
現象學作為一種研究微觀領域的方法,面向教育實踐本身,把教育行為、行為的意義、教育情境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研究者更加注重教師角色的整體性和多樣性,深入教師的職業存在狀態、教育實踐情境,注重教師自身的實踐參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以參與觀察、開放型訪談、原始材料的真實描述和深入分析以及扎根原始材料的理論建構為主,從而實現教育意義的解釋性理解。然而,現象學方法,如懸置、還原、本質直觀等具有令人望而生畏的學院派氣息。因此,它的艱深、晦澀、難以捉摸以及語言的復雜表述使人們對于現象學方法又愛又恨。
客觀上來說,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除了現象學自身固有的艱深、晦澀、難以捉摸的局限性外,正如現象學本身所具有的主觀唯心主義性質一樣,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也同樣帶有濃重的主觀唯心主義色彩。加之現象學理論基礎的艱澀、難以捉摸,現仍停留在理論建構階段,還沒有在教育實踐中生成本源性理論,在實踐中出現了諸如“直觀”地“描述”現象而無解釋、將現象學等同于或降格為“行動研究”的誤區。因此,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究竟會有什么樣的定位?會不會構建出一種新的學科體系?會有多大的發展空間?諸如此類的問題,我們無法看到也不可預測。然而,現象學主義教師教育思想面向教育實事,面向教育本身,回歸教師的日常教學生活世界,具有濃厚的人文意蘊和人性色彩。這在當今教師教育越來越工具性與技術化、實用性與技能化、功利性與形式化的今天的確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鑒。
參考文獻:
[1]Van Manen,M.,Shuying Li.(2002).The pathic principle ofpedagogicallanguage.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Vol.18,pp. 215-224.
[2]Van Manen,M.(1999).The practice of practice.In:Lange,Manfred,Olson,John,Hansen,Henning&B·Y·nder,Wolfgang (eds.): ChangingSchools/ChangingPractices: Perspectiveson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eacher.
[3]Van Manen,M.(1997).Linking ways of knowing with ways of being practical.Curriculum Inquiry,Vol.6,No.3.pp.205-228.
[4]Langeveld,M.J.(1984).Reflection on phenomenology and pedagogy.Phenomenology+Pedagogy,Vol.1,No.1,pp.5-10.
[5][11][16][20][21][加拿大]馬克斯·范梅南.教育機智—教育智慧的意蘊[M].李樹英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32.14.36.2.174.
[6]Van Manen,M.(1989).Pedagogical text asmethod: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as writing.Saybrook Review,Vol.17,No.2,pp. 23-45.
[7]Van Manen,M.(1984).Action research as theory of the unique: frompedagogicthoughtfulnesstopedagogicaltactfulness. PresentedattheAmericanEducationalResearchAssociation Conference,New Orleans,April.
[8]金美福.生活體驗研究:含義、原理與主要環節[J].外國教育研究,2004,(6).
[9]Langeveld,M.J.Reflection on Phenomenology and Pedagogy PhenomenologyPedagogy[J].Edomonton:UniversityofAlberta Publication Services,1982,(1):80-82.
[10]Van Manen,M.(1991).Can teaching be taught?Or are real teachers found or made?Phenomenology+Pedagogy,Vol.9,pp.182-199.
[12]何菊玲.教師專業成長的現象學旨趣[J].教育研究,2010,(11).
[13]李樹英.教育現象學:一門新型的教育學——訪國際教育現象學大師馬克斯·范梅南教授[J].開放教育研究,2005,(3).
[14]Van Manen,Max.(1996).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and the Question of Meaning InD[J].Vandenberg(Ed),Phenomenology and Educational Discourse Durban Heinemann higher and Further Education,1996:182-196.
[15]VanManen,Max.OntheEpistemologyofReflective Practice[J].Teachers and Teaching:Theory and Practice,1995(3).
[17]胡春明.論“生活世界”理論視野中的教師教育[J].江蘇高教,2006,(6).
[18]寧虹,鐘亞妮.現象學教育學探析[J].教育研究,2002,(8).
[19]Van Manen,M.(1983).On pedagogic hope.Phenomenology +Pedagogy,Vol.1,No.2,pp.1-3.
(責任編輯:劉君玲)
王艷霞/北京市昌平區第一中學,博士、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