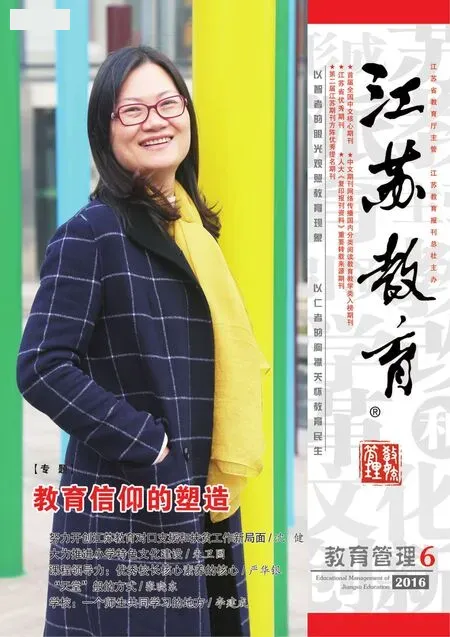超越烏托邦與敵托邦*
——教育技術應用的技術現象學審視
陳向陽
?
超越烏托邦與敵托邦*
——教育技術應用的技術現象學審視
陳向陽
【摘要】技術現象學在批判工程技術哲學與人文技術哲學教育技術觀的基礎上,超越技術樂觀論和懷疑論的局限,提出了第三條道路。技術現象學是面向“技術實事”的現象學研究,在技術現象學的視野下,初步分析了教育中技術異化的現象及其深層次根源,在此基礎上,勾勒出一幅較為完整的“人-技術-教育”關系的教育技術理論與實踐圖景:教育技術本身由裝置范式走向聚焦物范式;技術與教育關系由消費走向設計;人技關系從離身走向具身。
【關鍵詞】技術哲學;教育技術;技術現象學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技術在各領域高歌猛進,并帶來了整個社會生活的信息化改造。在教育理論與實踐領域,同樣呈現出一片眼花繚亂的“概念叢林”,人們對多媒體教室、智慧校園、慕課、翻轉課堂、微課、混合式教學、大數據、云計算等不斷涌現的新名詞趨之若鶩,尤其在《教育信息化十年發展規劃(2011-2020年)》明確提出堅持“現代信息技術與教育的全面深度融合”之后,這些新名詞更是伴隨著行政介入、資本運作和運動式操作進入到教育技術和信息化實踐中去。在這種種合力的推動下,倘若誰不知這一波又一波的時髦概念,儼然就是教育變革的落伍者。然而,當前教育信息化的喧囂和非理性狂熱,不僅未使教育產生預料的系統性變革,反而帶來了更多新的問題,要真正理解并把握教育技術的未來,需要審慎的理論自覺與哲學思考。
一、技術樂觀論與懷疑論的局限性
在《通過技術思考——工程與哲學之間的道路》中,米切姆指出:“技術和哲學是像一對孿生子那樣的孕育的,工程的技術哲學明顯具有技術哲學孿生子長子的特點,更偏向于親技術并注重對技術進行分析,第二個孩子則更傾向于批判和解釋技術。”[1]
工程技術哲學的倡導者多是技術專家或者工程師,他們著眼于技術的合理性,堅信由技術的自然邏輯必定會導向其價值邏輯,技術只是實現外部目的的工具與手段,技術專家的使命就是如何使技術更“先進”。這種技術樂觀論投射到教育領域就表現為,盲目追逐物化的新技術,認為其必然會推動教育的文明、進步與現代化,由此,在使教學變得更有效率和更有趣的宣言之下,各種花樣翻新的技術不斷被引入教育教學中,尤其是博客、移動學習、MOOCs等新技術一時成為時髦話語。當這些新技術不被教師所認可和接受時,技術樂觀論者總是把問題歸結為教師因循守舊,教師因此成為被指責和培訓的對象。這種技術的樂觀主義延續了啟蒙時代以來人們對技術所持的一貫態度,他們多從工具的視角來看待技術,追求技術至上。
然而,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是否可以如此樂觀對待而不加任何批判?在人文技術哲學看來,技術越發展,就越成為一種自主的、異己的力量。波茲曼就
從教育技術應用的實踐來看,以上諸多亂象和觀點紛呈的背后,實際上隱藏著兩種技術哲學。但是,這兩種技術哲學都有其突出的缺陷,那就是用工具和實體的思維來看待技術,正如海德格爾在《技術的追問》中所指出的,對于“技術的正確的工具性規定還沒有向我們顯明技術的本質”。沒有掌握技術真正的本質就無法在人與技術之間顯出一種自由的關系。由海德格爾開端,面向具體“技術實事”的現象學技術哲學,將為我們思考和分析教育技術實踐提供第三條道路。
二、教育技術應用的技術現象學考察
在教育實踐領域,人們已基本形成共識,即教師和學生對于信息技術的認識和理解,不僅要掌握“器、術、法”等層面的有效使用方法,還要構筑“道”層面的關于技術與教育、技術與人的關系等教育技術哲學問題。技術現象學以其人技關系的獨特理論,為我們對教育技術實踐的學理分析提供了理論支援。
“首先,工具不是具有一定屬性的簡單對象,相反,所謂的工具依賴于一種使用的情境,技術是與具體的使用情境有關的。”[2]海德格爾極力強調情境對于技術存在的意義,在海德格爾那里,用具的存在方式與情境的關系非常獨特:一方面,如果沒有情境,用具無法存在;另一方面,只有借助情境,用具與世界現象之間的通達才具有可能。“嚴格地說,沒有一件東西可以單獨‘是’用具。存在的一向是用具器物的整體。只有在這個整體中一件用具才能夠是它所是的東西。”[3]這實際上啟示我們,教育技術作為一個整體的存在,僅僅只是使用現代信息技術,還不能稱之為教育技術,唯有在教育世界諸要素(如教育價值、教育目標、教學設計、教學方法等)的聚集中,它才真正成為教育的一部分。
海德格爾關于技術的現象學分析,為我們深刻理解教育技術的本質開辟了道路。然而海德格爾還主要是從“之外”與“之上”來研究技術,從形而上的抽象層面來反思技術,這種分析方式無疑具有深刻性,然而也存在不可忽視的固有缺陷。因為他只停留在抽象的層面,把技術處理為一個沒有差異的整體。而對于教育技術本身所呈現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僅靠這種形而上的分析是不夠的。從電影、電視、計算機到今天的移動互聯網,只有對他們進入教育領域進行具體的經驗描述,技術的社會批判才有存在的空間。在技術現象學看來,技術不再只是單純的、赤裸裸的工具,它既向自身敞開,同時也向人與教育敞開,從這里出發,我們可以思考教育技術自身、技術與教育、技術與人等諸多的理論命題。通過對這些命題的揭示,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技術之于教育的深層次意義。
在當代,現象學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是以伯格曼和伊德等為代表,使技術哲學出現了經驗轉向。在伯格曼看來,對技術的哲學反思,必須建立在對現代技術的復雜性與豐富性的適當經驗描述上,他的“聚焦物和聚焦實踐”的思想正是對海德格爾“天地神人”四重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把對“物”的思考從形而上學的層面轉向了倫理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層面。“當我們所用的東西僅僅是用品的時候,我們就剝奪了世界公民的權利。所以我們要通過聚焦實踐回歸到這個世界的深處,回歸我們作為存在的完整性。”[4]在這里,聚焦實踐體現著一種“參與的實踐”,只有我們每個人都參與了技術與教育互動發展的過程,才能真正實現技術與教育的深度融合。
伊德將現象學和實用主義緊密聯系起來,同時關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具體技術和案例研究,形成了所謂的“后現象學”。用伊德自己的話說,后現象學是“現象學+實用主義+經驗轉向”。伊德最著名的經驗研究就是其提出的“人-技術”關系四種模式,即具身關系、解釋學關系、他者關系和背景關系。通過這一研究,伊德認為,“不存在純粹的技術本身,技術是一種關系性存在,技術就在于技術與人和世界的相關性”[5]。
通過對現象學技術哲學家觀點的簡要考察發現,盡管他們對于技術的理解各異,所提出的克服現代技術的可能路徑也不完全相同,但深入他們的根本立論,可以感受到一種共同的關切,那就是超越技術烏托邦和敵托邦的局限,回到技術本身,從實踐哲學和文化哲學出發,直面人的存在這一根本問題。而這無疑為我們思考教育技術實踐提供了極大的啟發。
三、教育技術可能方向的現實分析
上述現象學技術哲學發展進路的分析,為我們思考教育技術實踐提供了理論背景,尤其是面對日益增長的技術宰制,我們既不是天真地接受技術,也不消極地逃離技術,而是深入技術實事本身,洞悉問題的根源與解救之道,這不僅是這個時代緊迫的問題,也是當前教育必須做出回應的問題。
(一)對教育技術的認識:由“裝置范式”到“聚焦物范式”
雖然新技術應用之下的教育改革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但原有教育中一些本真美好的東西似乎失落了。以伯格曼的觀點來看,問題的根源或許在教育場域中“裝置范式”的技術本質觀。這一范式揭示了現代教育技術真正的本質,一方面,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進行知識的傳遞,另一方面又隱蔽與縮減了事物牽連的整個世界。這一范式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純技術的運作上,它對人的力量、注意力和思考方面要求愈少,遠離了那些富有教育價值與意義的事情。例如,隨著多媒體教學的興起,黑板在教室里的使用越來越少,代之以碩大的多媒體控制臺,教師常常被束縛在臺前操作著程序化的PPT,原本在講臺上談笑風生、充滿智慧的教師,成為照本宣科的操作員,課堂不再被作為詩意的存在,教學的藝術世界轟然倒塌。更進一步的,隨著傳統教室被多媒體教室取代、印刷書本被移動終端取代、學生管理被各種監控技術所取代、師生的面對面交流被虛擬交往所取代……教育最終所追求的目的被丟失了。
面對這樣的問題,伯格曼同樣給我們提供了解救之道,他并沒有簡單沿著海德格爾的思路,回到聚集“天地神人”的“物”的前現代技術之中。在伯格曼看來,物的轉變不能是一種取消,更非對技術的逃離,而是要構建一種“聚焦實踐”,這種構建包括三方面的內容,“一是應為聚焦物和聚焦實踐清理出一個核心位置;二是簡化圍繞和支撐聚焦實踐的背景;三是盡可能擴大親自參與、身體力行的活動的范圍”[6]。這也就意味著,教育雖然被各種現代技術所控制,但只要人們仍然從事各種圍繞“聚焦物”而展開“聚焦活動”,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當今教育中的技術問題。諸如重構多媒體教室的布局,引入融傳統黑板與多媒體功能為一體的交互式白板,打破技術對師生活動限定的可能,營造適合師生互動學生學習的環境等。只有守護著 “聚焦物與聚焦實踐”,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技術教育化。
(二)技術與教育關系的新認識:由“消費”走向“設計”
對于技術與教育的關系,著名教學設計專家梅瑞爾(Merrill)曾形象地比喻:“教育技術領域的許多參與者很像買新奇玩具的孩子們,總希望他們所在的學校能夠啟用一些新的技術設備或應用程序,但新鮮感慢慢褪去后,這些最新最好的技術就被蛛網塵封,完全過時了。”[7]回顧20世紀的教育技術史我們很輕易就會發現這一事實,電影與電視教育20世紀初曾獲得極大的關注,愛迪生在1913年曾滿懷信心地預言:“在公立學校里,書本將很快過時,人類知識的所有門類都可以通過動態影像來進行教學。我們的學校系統會在十年內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8]與此同時,一些影片制作廠家則從中尋求商機,他們“打著視覺教育的旗號,兜售其產品”,并大肆渲染電影在教育中的作用。但這一預言并未得到驗證,電影或者電視沒有取代傳統的教科書。今天,人們同樣認為網絡將對學校教育產生革命性的影響,有學者預言,MOOCs將使教育受到顛覆性影響,進而引發系統性的變革。但據北京師范大學遠程教育研究中心對國內96個慕課平臺統計,千余門課程80%基本無互動,只是傳統課堂搬家,跟過去的電視教育沒有太大差別,慕課越來越像是教材的附贈光盤,沒做任何設計就放在網上。
由此看來,技術與教育結合的重點不在于引進最新穎、最酷炫的新技術,亦非教會師生使用和操作這些技術。“僅僅把學習材料放到網上不構成‘學習環境’,僅僅把以傳統講授為主的教學電子化不可能產生顯著的學習效果”[9]。只有讓技術應用回歸教育的本質,圍繞學習者進行有效的設計,才有可能避免20世紀教育技術的歷史重演。芬伯格正是從技術的“設計批判”出發,提出“計算機設計不僅在工具意義上是重要的,而且還具有人性的意義,因為在設計工具中我們設計了存在的方式”。[10]這種設計是一種存在論的設計,它不僅需要知識和技術,還需要更成熟的人類情感,而這恰恰呼應了當今時代對學習本質的認識,對學習來說,最核心的是情感、情境或者高質量的啟發式技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設計”將成為教育技術未來關注的重要議題,每當引入一種新的教育技術時,必須在其設計時就要考慮到對話和情感參與,這種設計活動需要轉向藝術化,只有通過藝術化,才能在教育發展的暗礁中走出一條“回歸自己的路”。同時,其設計主體絕不能僅限于少數技術專家或者工程師,更要發動廣大師生參與其中,他們不只是教育技術的消費者和使用者,按照設計好的程序進行消費和表演,而是作為設計者、生產者參與著開發的全過程,他們的價值觀念、設計思維通過博弈轉化為技術代碼。惟此,才能真正設計出更加人性化、受學習者歡迎、充滿生命活力的新一代教育技術,從而在更深的層次上激發無窮的教學智慧。
(三)人-技關系的新認識:從“離身”走向“具身”
“在大多數情況下,學習者與學習環境之間不直接發生交互作用,而是需要借助相關技術的支持方可進行。”[11]在這個數字化生存的新時代,尤其是大數據正在進入教育的方方面面之時,師生、生生的關系,更要通過人與技術的關系來實現。人們在熟悉數字化技術提供工具、空間和可能性的同時,也在構建一種新的學習環境和學習文化,由此,揭示人與技術的關系,對于理解正在發生的教育變革至為關鍵。伊德關于人與技術之具身關系的解讀為我們提供了基本的認識框架。在他看來,人與世界之間的關系總是被技術所中介。在具身關系中,技術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抽身而去”,它以一種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暗中與人發生交互,正是這種方式使技術具身成為可能。當然,完全透明的技術是不存在的,現實中的技術總是呈現部分的透明性或準透明性。教育技術的目標就在于努力實現人、技術與環境的具身,從而讓學習者調動所有的感覺器官,獲得更強的在場體驗感。
從人與技術關系的視角看,教育技術發展史體現的正是從離身到具身的轉化。從書寫、印刷到黑板、電影、電視、計算機網絡等莫不如此,如柏拉圖曾強烈譴責,書寫技術具有破壞對話關系的能力,而這種對話關系是師生之間的紐帶,但隨著書寫變成習慣,它與人走向具身關系,并開始退居背景,成為教育的一部分。當前,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技術發展遠不像當初書寫技術那樣緩慢地發展,它處于快速的變化之中,一種技術進入教育領域還未被教育化,就很快被更新的技術所替代。如果我們只是盲目地引入技術,把技術作為外在于人存在的一種工具,這種變革注定要失敗,諸如目前實施的多項教育信息化工程,包括多媒體教室建設、精品課程建設等,都還只是形式上的“新瓶裝舊酒”,這種技術根本上還只是離身的技術,即使是當前被認為是開啟未來教育的大數據,“如果沒有人的加入,依舊只是促使人類快速做決定,依舊是資本大爆炸、技術大爆炸,那么人類是沒有未來的”。[12]著名哲學家斯蒂格勒這番振聾發聵的忠告,實際上是在提醒我們,在將技術應用于教育的過程中,不能操之過急,技術既然已經深深嵌入教育世界,就必須努力實現教育技術的具身轉向,構建一個與技術和諧共生的詩意棲居的教育世界。
【參考文獻】
[1]卡爾·米切姆.通過技術思考——工程與哲學之間的道路[M].陳凡等譯.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23.
[2]唐·伊德.讓事物“說話”:后現象學與技術科學[M].韓連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42-43.
[3]陳嘉映編著.《存在與時間》讀本[M].北京:三聯書店,1999:49.
[4]傅暢梅.伯格曼技術哲學思想探究[M].沈陽:東北大學出版社,2010:86.
[5]舒紅躍.技術與生活世界[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31.
[6]傅暢梅.伯格曼技術哲學思想探究[M].遼寧:東北大學出版社,2010:88.
[7]戴維·梅瑞爾.玩具、原則和數字化學習[J].開放教育研究,2016(1):4.
[8]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與大數據同行——學習和教育的未來[M].趙中建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16.
[9]董麗麗,呂巾嬌等.教育技術領域的基本問題與未來走向——2014-2015年美國教育傳播與技術專家視點述評[J].開放教育研究,2015(5):16.
[10]安德魯·芬伯格.技術批判理論[M].韓連慶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133.
[11]王美倩,鄭旭東.在場:工具中介支持的具身學習環境現象學[J].開放教育研究,2016(1):63.
[12]李丹.專訪德里達弟子斯蒂格勒:如果大數據只是促使人類快速做決定,那么人類是沒有未來的[N]·東方早報,2015-03-12.
【中圖分類號】G40-05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6009(2016)27-0023-04
【作者簡介】陳向陽,江蘇省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與終身教育研究所、職業教育與社會教育課程教材研究中心(南京,210013)副研究員,博士,碩士生導師。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教育部2014年度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 “當代技術哲學新進展與職業技術教育哲學研究”(項目批準號 14YJC880006)和江蘇省 2013年度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 (編號2013SJB880022)階段性成果。始終警惕電子技術對文化素養的侵蝕。在《童年的消逝》中,他抨擊新技術,尤其是電視文化,認為電視文化抹殺了成人和兒童的界限;在《娛樂至死》里控訴電視對讀寫能力的危害,影射電視掏空了人的頭腦和心靈;在《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中揭示信息失控的現實危險,指控技術壟斷對人類文化的危害。波茲曼對于技術的批判與質疑的確有助于對技術在教育實踐中的消極作用保持警醒。比如傳統的PPT的使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教學與聽講方式,大家都成為受某種技術邏輯影響的工具,甚至有教師沒有電就沒辦法進入課堂教學,這就是典型的技術對人的異化。課件控制了教學過程,從而控制了學生,也成為教師自身的桎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