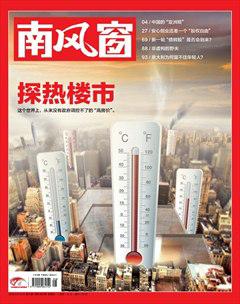安心創業還差一個“股權自由”
譚保羅

簡政放權,降低創業的注冊資本門檻這是好事。但在資本過剩、流動性泛濫的時代,尊重創業者“人力資本”和“股權自由”的制度配套或許更為重要。
在2016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小米CEO雷軍遞交了關于修訂《公司法》的提案。這已經是雷軍第3次提議修改《公司法》,本次提案提出了諸如允許人力資本出資設立公司、允許設立優先股等建議,其指向是給與公司股東內部更大的“自由約定”權利。
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為鼓勵創業,中國推行了商事登記制度改革。2014年,中國《公司法》大修,放松了關于公司最低注冊資本、登記前部分實繳等限制,一定程度上放低了設立公司的“門檻”。
從某種程度上講,放低設立公司門檻的制度改革,只是調整了公司股東與公司外部人的利益關系,給與了雙方更大的意思自治空間。但另一方面,對公司股東之間,并沒有給與足夠的自由意志的空間。
當下,流動性泛濫、資本過剩已經成為了中國經濟領域的一個現實,放低公司注冊資本的限制,起到的作用恐怕有限。相反,創業精神和企業家資源的缺乏才是關鍵。在這種情況下,允許股東內部的意思自治,既能改變創業者與資本之間的博弈格局,提高創業者對資本的議價能力,也能規避創業過程中的法律風險,讓創業者安心創業。
人力資本
公司資本制度改革的重點,不只是降低“資本數量”的門檻,而是還必須放松對“資本自由”的限制。
2013年11月9日~12日,十八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一個多月后,經濟體制領域的改革便有了動作。12月28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便審議并通過了《公司法》修正案草案,修改了《公司法》的12個條款。
本次《公司法》大修的核心指向只有一個,即放松注冊資本的限制,降低設立公司門檻。一是取消了法定最低注冊資本,注冊資本改由公司章程規定。此前,對注冊資本要求最低的有限責任公司,其最低注冊資本是3萬元。從理論上講,按照新法,股東用1分錢就可以設立一家公司。二是取消了登記前部分實繳的要求。此前,法律要求登記前實繳20%的注冊資本,但修改后則不再需要,出資時間由公司章程規定。三是設立登記時,驗資證明不再是必要的法律文件。后兩方面的限制放松,通俗來說,就是即使股東設立公司時沒錢也沒關系,只要后面賺到了錢或籌到了資,再補繳就行。
而雷軍在提案中的觀點是,修改后的《公司法》有進步,但在出資形式上依然有問題,即沒有承認人力資本可作為出資。
隨著科技的高速發展和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和物力資本相比,人力資本將成為創業企業發展的主導因素。但目前,創業者的人力資本出資不能被認可,使創業投資實踐產生了法律障,也增加了投資人、創業企業的法律風險。
實際上,關于出資形式, 2014年的《公司法》大修也有所進步。按照修改后的《公司法》和《公司注冊資本登記管理規定》(下稱《管理規定》),可以作為出資的,除了貨幣,還包括了實物、知識產權和土地使用權等。
從立法角度來看,可以作為出資的非貨幣財產,不外乎擁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可以用貨幣估價”,二是“可以依法轉讓”。人力資本顯然無法滿足這兩個條件,因此也無法作為出資。
這種立法的改動和維持,體現了立法者的一種平衡思想,即取消貨幣出資的比例限制,放低成立公司的資本門檻,鼓勵創業。但另一方面,也要保護債權人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利益。特別是在社會整體信用環境有待改善,資產評估可能存在“貓膩”的情況下,符合以上兩個特點的出資更能有效保護債權人利益。
在修法建議中,雷軍認為,要允許人力資本的自由約定,接受人力資本作為出資形式。同時,在公司營業執照、章程等文件中,對人力資本出資和物力資本出資分別進行公示,明確兩類出資人不同的股東責任。換言之,通過列明不同的出資形式,好讓公司的債權人或者生意伙伴“明辨風險”。
在《管理規定》中,法條列舉了不得作為出資的內容,第一項就是“勞務”。盡管“勞務”和“人力資本”有所不同,但兩者在法律上的重合度極大。在民商法中,奉行“法無禁止即自由”的原則,即只要法律沒有禁止,那么就是合法的。但人力資本作為出資,在現行法規中卻可以說是被明確禁止。
當然,中國在美國上市的“科技公司”早已是過江之鯽,一些創業者和他們背后的風投早已找到了“變通方案”。
“變通方案”
在中國,創業其實可以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技術導向的創業,一類是商業模式導向的創業。在出資形式上,目前的法律規定對技術導向的創業者是有利的。在《公司法》和《管理規定》中,專利技術作為“知識產權”,在依法評估之后,是可以作為出資的。
現實中,中國更多的創業者都屬于商業模式的創新,而商業模式難以申請專利,并成為法律所肯定的“知識產權”。實際上,拿雷軍所提到的TMT(Telecommunication,Media,Technology)行業而言,中國創業企業更多是美國同行的模仿者或者“模仿式創新者”,和“知識產權”根本毫無瓜葛。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假如創業者的“人力資本”很強大,比如提供的商業模式很好、個人和團隊執行力很不錯,而且人品一流,但偏偏“窮二代出身”,身無分文,那怎么辦?
在多數情況下,創業者固然會以自有資金進行一部分的原始投入,但“燒錢”的生意更多還是需要風險投資的進入。在這種情況下,創業者和風險投資,他們都面臨著一種微妙的股權上的“權衡”。
對投資者而言,創業者只要項目好,即便真的“身無分文”也必須拿到一定的股權。因為,沒有股權的創業者是無法真正全身心投入創業的,這是在打工,而不是創業。因此,投資者也希望創業者自己持股,并且份額不要太低。
另一方面,創業者自己也希望拿到的股權不能太少,因為初創企業將不斷面臨新一輪的融資,這意味著股權將被不斷稀釋,所以必須給自己預留足夠的“空間”。因此,讓創業者持股,這是投資者和創業者雙方都愿意發生的事情,也是一個行業約定俗成的規則。
但問題在于,一些創業項目的首輪投資就達到百萬美元,創業者即便要拿50%的股權,也要自己掏出數百萬人民幣。創業者未必有這個實力,也未必有這個意愿,因此在不違反法律的情況下,進行適當的“變通”,給與“人力資本”一定的“照顧”勢在必然。
實踐中并不缺乏這樣的例子。當下,流行的模式之一是以合伙企業成為公司的股東。即創業者的創業實體是A公司,但創業者可以成立合伙企業B來持有A公司的股份,那么實際起到了持股A公司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創業者可以以勞務出資成立合伙企業B。比如,萬科管理層以盈安合伙入股萬科就是利用了這種形式,盡管萬科管理層并非投資初創企業,也不一定以勞務出資,但法律上的邏輯是一樣的。
我國《合伙企業法》規定,合伙人可以用貨幣、實物、知識產權、土地使用權或者其他財產權利出資,也可以用勞務出資。更重要的是,出資的“自由度”還體現在勞務出資的“評估上”。
按照《合伙企業法》,合伙人以勞務出資的,其評估辦法由全體合伙人協商確定,并在合伙協議中載明。換言之,在不違法的前提下,勞務折算為資本到底被評估得多高,合伙企業的合伙人之間有相當的自由度。
從法理上講,因為合伙企業的普通合伙人對外需要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因此給與合伙企業較大出資形式上的自由,這并不影響對債務人的保護。在合伙中,風險投資可以給與創業者更多的份額,而無需創業者支付相應的對價。這種模式既達到了激勵創業者的目的,也并不違法。
股權自由
“變通辦法”還有很多。比如,可以將創業者未來從公司領取的工資或者獎金,提前支付并“折算”為公司股份。特別是新《公司法》取消了出資時間限制之后,這種以薪酬作為創業者股份的模式,無疑給了創業者和投資者帶來了更大的操作空間和時間上的靈活性。
近年來,中國誕生了如此多的創業公司,在實踐中,合法地規避“勞務”不得出資的情況并不少見,以上模式只是眾多模式中的一部分。
實際上,當前的中國創業領域面臨著的主要問題不是資金的缺乏,而是“靠譜項目”以及高素質創業者的缺乏。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個市場早已經是個“賣方市場”,即優質的創業項目,往往是投資人擠破頭皮,而創業者反倒有極大的議價本錢,這種局面和20年前早已是天壤之別。
雷軍提案的另一個建議是允許股東權利自由約定,比如,全面開放優先股和允許股東自主約定股權比例等。目前,我國優先股已經在逐步推行之中,《公司法》中并不存在發行優先股的法律障礙,而《優先股試點管理辦法》也為上市公司發行優先股提供了法律保障。

2016年3月29日,小米創始人、董事長兼CE0雷軍宣布對小米生態鏈進行戰略升級。
此外,允許股東自主約定股權比例這一提議更有現實價值。目前,我國法律原則上規定公司股權必須“同股同權”,即每一股具有同等權利,其中最主要的是表決權。
但另一方面,從互聯網行業的創業趨勢來看,不同表決權的“雙重股權”結構正在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潮流。所謂雙重表決權的,即兩份同樣面值的股票享有的分紅權相同,但投票權不同。投票權分為高、低兩種投票權,同樣價值的股票擁有的投票權可能是低投票權股票的10倍。
我國的阿里巴巴和百度都采取了這種雙重股權結構, Facebook、谷歌等國外互聯網企業也同樣如此。公司創始團隊手中的原始股都屬于高投票權股份,而其他后續入股,或者在公開市場購買股票的投資者擁有的是低投票權股票。后者可能擁有更多的股份,更多的分紅,但投票權卻不如創始團隊。
這種模式的好處在于,可以較大程度確保創業者對公司的控制,在經營中,減輕來自于機構投資者的影響和干預。同時,也可以在成長過程中,避免被比自己強大的對手收購,而收購策略正是互聯網巨頭“消滅”或者“收編”潛在對手的常用方式。
長期以來,中國互聯網企業多采取VIE(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可變利益實體)結構,這個結構可以簡單理解為:創業者要在國內設立創業的實體公司A,與此同時,還要在海外比如開曼群島設立一家母公司C,然后C在國內全資投資設立一家公司D。然后A通過一系列協議把自己的權益和債務等全部轉給D。在VIE模式之下,等于C是A的實際控股公司,而最終上市的則是C公司。
最初,這種模式興起的原因是中國國內資本缺乏,創業者必須依靠外資風投,但國家對外資投資互聯網產業(電信增值服務)有嚴格限制。為了規避這一限制,才有了這種VIE模式。因為A是內資企業,可以投資這些外資受限的行業。
此外,另一個原因也不容忽略。在這種結構下,其在國內的創業實體公司A要受到中國法律的規制,而其協議控制方D公司的的母公司C,由于注冊地在海外,這些離岸金融中心法律較為寬松,允許更多的股權操作。
比如,A公司在國內顯然無法采用雙重股權結構,但位于海外的C公司則可以,這對創業者顯然是有利的。因此,即便在外資風險投資已經不再是必需,我國對外商投資限制的行業限制不斷放寬的情況下,VIE模式對創業者依然有相當的吸引力。
簡政放權,降低創業的注冊資本門檻這是好事。但在資本過剩、流動性泛濫的時代,尊重創業者“人力資本”和“股權自由”的制度配套或許更為重要。